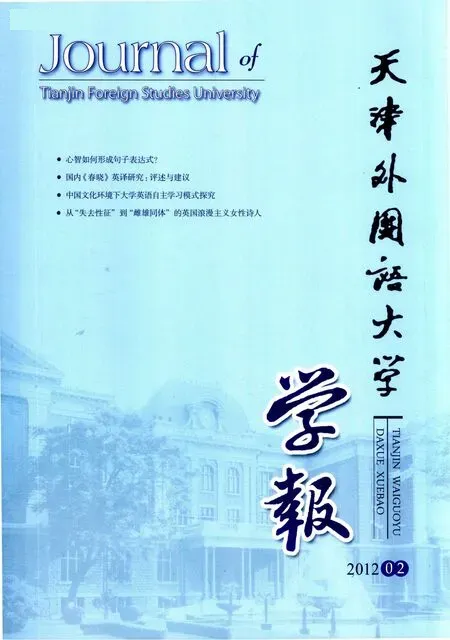清末翻译文本的伦理选择
涂兵兰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长沙 410205)
一、引言
所谓伦理,便是人际关系如何以及事实行为应当如何(Thiroux,2006:2-3),即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人们据此来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伦理既是社会的,是在人类社会中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和行为的秩序规范;也是个人的,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伦理目的,物质价值、政治价值、道德价值以及个体价值的不同导致在社会中的具体行为呈现出个体差异。任何道德价值的判断都是以一定的社会语境为基础的。
二、清末翻译的伦理特点
1 清末译者的政治伦理观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而且是一个以家族伦理为中心的社会。社会伦理关系处处表现为下者、卑者、贱者对上者、尊者、贵者的依附关系以及家族成员对家族、臣民对君主的依附关系。因为所受的传统教育以及家庭环境的影响,清末译者很早就把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作为自己的理想人格和伦理模式。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中代表提出 “士志于道”的价值规范和人生信念。他所提出的“内圣外王”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外王”即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士人没有不想参与公共事物管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 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就不得不投身于势,而君主也需要士人的知识技能为其服务。此外,士人那种“求道”、“修道”、“卫道”的信念从一开始就要求其保持精神上的独立与情操上的高洁及对国事的关注和对信念的坚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他们一直把“明道救世”、治理社会的责任自觉地扛在自己肩上。
传统士人伦理的影响使他们在社会实践中自觉地把儒家伦理模式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并且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变化自觉地调整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国家与世界局势的变化、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新学堂的建立使他们不可能像古代士人一样安然躲在书斋里,在书本中去寻找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途径。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积极走出自身的生活圈子,寻找自己和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出路。他们希望通过宣传西学废除封建伦理纲常,大力引进和吸收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用资产阶级伦理道德改良封建伦理道德,使人人树立起自由、平等的观念。只有树立个体自由的意识,才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的国民,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2 清末译者的经济伦理观
儒家传统士人推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提倡“贵义贱利”、“重义轻利”。人们在面临两难选择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取义而去利。清末社会政治的变化使很多士人失去了往日的特权和优势,一些士人生活落魄。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促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日趋平等。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逐渐受到尊重,因为交换价值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现实基础。商人依靠自己的经济基础逐渐在社会上取得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并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宋明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倚仗自己的经济势力和地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逐渐取得了话语权,他们的地位仅次于士人。清末虽然还是重农轻商,但是商人为政府和士人在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这些都为转型期的传统士人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随着社会分工的门类细化及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一些士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劳动赚取生活资料,他们的传统义利观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处于过渡期的清末文人既有士人干预社会政治的道义感,又有追求自身价值的世俗功利性。他们关心社会合理秩序的重建,但实践方向已经从朝廷转移到了社会,实践方式也从空谈政治转向办实业,以开启民智,培养民德。这一方面从经济上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给他们提供了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有些士人借此机会接近重要官员,影响他们的政治决策,实现自己政治上的追求。
三、清末译者的翻译目的
完整的翻译活动是由谁翻译、为什么翻译、翻译什么、为谁翻译、怎样翻译、产出什么效果等几个要素构成。对于翻译伦理研究来说,为什么翻译起着纲领性的作用,涉及到译者翻译的动机和目的。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导致译者所选择翻译文本的迥异。清末译者的翻译动机是复杂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并确定翻译活动的目的:(1)有助于改良群治,挽救危机中的国家;(2)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3)有助于宣扬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或者重新确立一种新的道德体系;(4)使社会个体获得新知识,满足健康的感官享受和精神享受。这些目的并不一定同时存在于每一次翻译活动中,甚至有时会有很大的冲突。这就需要译者根据自身的需要衡量相互冲突的价值的大小,确定哪些应居于优先地位。
除了译者的价值取向之外,译者的服务对象也会影响翻译目的。翻译活动必然涉及译者、作者、读者以及赞助人,译者应对谁负责呢?一般来说,译者在进行选择时不会也不可能把他们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是按一定的等级顺序来排列。排列的顺序不同也就意味着翻译目的有所差异。对读者负责,译者必须把社会责任和义务放在首位。对赞助人负责,译者应该恪守诚信和互惠互利的原则。对作者负责,就要尊重原作。对自己负责,做一个正直、负责任的译者,保持自身人格道德的纯洁性。
译者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让不懂外文的读者能够理解原文的思想和风格,了解外国文化和生活,并获得一种审美体验。而清末大多数译者显然并不是以此为意图,即使有也并不占首要位置。明末清初翻译文本已经开始突破宗教领域,而涉足科技方面。译者已经开始忧患中国的积弱,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超胜”。这就已经从单纯的宗教虔诚发展到了爱国情怀了。到了清末,这种爱国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清末译者选择文本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翻译是传达政治言说、干预社会的工具。大多数译者把翻译当成政治改良的工具,多选择政治和科学小说。第二,翻译可以获取经济利益,对于某些译者来说,翻译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具有经济价值。这类译者在民国前后才逐渐增多,多选择社会和侦探小说。
四、翻译伦理在文本选择上的表现
1 政治价值
率先通过翻译实现政治价值目标的是梁启超。为了改良群治,从1899年开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连续发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三个革命。这三个口号互相关联,共同主旨是取法国外文学,达到改良民智的目的。梁启超力倡翻译小说,因为 “小说为国民之魂”(陈平原、夏晓虹,1997:38)。这可以说是受傅兰雅的影响。傅兰雅一直认为小说能改易风俗。1895年他组织了一场小说竞赛,这场自上而下的竞赛使人们对小说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梁启超看到了小说的巨大功能,便将其作为改革的工具。
中国传统上一直以来最常用的方法和手段就是“文以载道”。梁启超认为,一般民众不具备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因为他们不具备相应的政治意识和觉悟。如果要动员民众参与政治,首先得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政治觉悟。梁启超对日本小说作过一番认真的考察,认为在小说的框架里载上政治理想,小说就“高尚”了。翻译西方小说成了译者们主要的教导工具。
从1897年严复、夏曾佑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述说小说功用到1898年梁启超作《译印政治小说序》明确表示:“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同上),各地报刊、杂志上大量刊登翻译小说,翻译政治小说蔚然成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把创刊宗旨定为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爱国精神,所刊登的文章著译各半。以后的《绣像小说》和《新新小说》也是著译参半。鲁迅在 《月界旅行 · 辩言》中写道: “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同上:67)基于对西方文化的迫切需求,众多译者雄心勃勃地把翻译科学小说当成是输入“智识”最可靠的方法。
而译者们对国家、社会的这种高度责任感却在清末的读者那里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出于救国的需要,译者主要把译本当成是政治的喉舌和工具。译者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选择文本,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翻译来唤起国民的觉醒。翻译对他们来说是对读者的一种施舍给予。他们明显具有优越感,以先生的身份来指引读者。这些译者的假想读者是广大民众,是社会的大多数。但真正对译本感兴趣又买得起书的人并不占多数。大众不喜欢枯燥的政治,缺乏议政的习惯,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吃穿住行。为了达成宣扬政治的目的,译者在选择文本时也会相对照顾读者的需求,扩大译本的社会功能,延续译作的生命。
从理论上来说,把翻译用于政治宣传固然可以达到启发教育国民的目的。而具有政治教育、启蒙意识的小说往往容易让读者厌倦。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文体“三不像”(王宏志,1999:139),再加上文中很多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使得他的政治小说遭人诟病。政治的枯燥与读者对小说的审美期待无法融合,而启发教育程度低的国民又必须以趣味性为诱饵。当译者的翻译动机和效果无法达成一致时,理想中的价值在现实中也就难以实现。
2 经济价值
被梁启超认为“诲淫诲盗”的通俗小说正是注重经济利益的译者所寻觅的文本。在清末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也试图通过自己的翻译唤醒、教育民众,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甚至也希望以崇尚个性自由的西方新道德取代以专制为特色的封建主义旧道德。但生活的社会化分层及仕途被切断使他们成为落魄的一族,赡养家庭,通过翻译改善自身经济条件就成为这类译者的基本初衷。而多数条件还比较优越的士人大多好风雅之事,有交谊伶界、载酒看花的爱好。关于这一点包天笑(1971:216)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中就有描述,特地谈到了在南京、上海和朋友方漱六等人逛妓院的经历。以风雅才子自居的士人在此方面的花费定然不少,他们的翻译目的自然也是为满足个人私欲。
这类译者必然在选择文本时更关注读者的喜好,更愿意对赞助人负责,对读者负责。他们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为一定的读者服务的,所拥有的读者越多越好。译本就是商品,译本的销售量是衡量翻译好坏的主要指标。销售量越大,利润就越高,译者的名声就越大,就意味着翻译的译本好。为了追求销售量,就要满足读者的需要。一般来说,读者购买书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信息,得到文化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译文的内容和语言就成为译者要慎重考虑的因素。因此,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大受青睐,不仅能影响读者,还能产生经济效益。
清末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译者能以全新的观念看待、适应社会。美好的政治理想逐渐被现实生活所取代,译者也不再相信小说真的有扭转乾坤的神力了。出现了一大批以娱人娱己、赚取金钱为目的的译者,他们的翻译伦理也从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倾斜。为了摆脱教书先生的命运,包天笑早年就尝试翻译,但他英文水平太差,日文还可以,便托在日本的友人购买日文小说母本,并确立了两个选购标准:“一是要译自欧美的,一是要书中汉文多而和文少的。”(包天笑,1971:173)包天笑的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当时的译者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市场意识,迎合读者的口味。林纾、包天笑等翻译的成功之路无疑为边缘译者所效仿(刘小刚,2006:5-6)。他们的翻译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所以会更多地受制于市场。
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很多译者失去了作为译者的身份认同感,淡化了翻译责任感。他们在翻译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理性的行为,不断加入到重复、冲动的情绪化甚至是破坏性的行动中去。相对丰厚的稿酬第一次使文学建立在商业化的经济基础之上。商业化是这一时期翻译事业发展的动力和主要表现之一。在商品化的文化市场中,市场消费促进了翻译小说的繁荣。陈平原的最新统计显示,1899年至1911年期间共有615部外国作品的中文全译本,其中,狄更斯、小仲马、雨果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广受读者欢迎,而柯南道尔、哈葛德和凡尔纳的作品则稳居畅销小说前三名(王德威,1998:102)。晚清最后十年里至少曾有170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落。
把翻译当成商品的译者追求新鲜、刺激的译本,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尽可能地获得最多的读者。觉我在《余之小说观》(1908)中分析了此类翻译盛行的原因,即域外风情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今得于译籍中,若亲见其美貌,若亲居于庄岳也。且得与今社会成一比例,不觉大快”(陈平原、夏晓虹,1997:333)。这样的翻译“呈功易,卷帙简,卖价廉”(同上)。像严复那样精心挑选《原富》,再花上三五年去翻译,如果售价非常低廉,那这个译本很可能就要亏本。依照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说,购买一本小说或一份报纸、杂志对于平常人家来说仍然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只能偶尔为之。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他们有能力购买又能够看懂的只有言情、侦探之类的小说。
五、结语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译者的天平越来越向经济伦理一方倾斜。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每个译者试图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动机促使每个具有起码经济理性的人自发地参与市场竞争,寻求经济效用的最大化。清末小说固然繁荣了,出版的图书除教科书外,“什九皆小说”。梁氏提倡的是能够新民的教导大众的政治小说,实际繁荣的却是“诲淫诲盗”迎合下层劳动人民的通俗小说。
清末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关系、各种思潮还未完全理顺,人们对经济利益的关注与理性化的市场规则之间还未建立平衡点。大量非理性的翻译行为要求有职业准则来规范。译者是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个体,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他的翻译伦理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处理体现出伦理价值。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应视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定,读者是翻译市场兴衰的风向标。译者要真正实现自己的伦理价值目标,则要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
[1]Thiroux,J.P.Ethics: Theory and Practice[M].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
[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3]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王宏志.重释“信达雅”——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