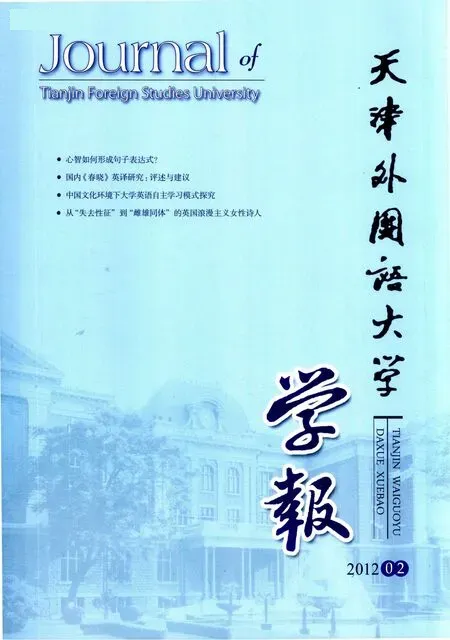从“失去性征”到“雌雄同体”的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人
王 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上海 200083)
一、引言
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歌的再解读与再接受是当代西方新浪漫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产物,也是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对文学“经典”问题重新审视的结果。实际上,很多浪漫主义女性诗人,在诗艺上都可以称得上是男性诗人的前辈。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引领了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十四行诗创作,影响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堪称名副其实的英国浪漫主义先驱。玛丽 · 罗宾森 (Mary Robinson)和安娜 ·芭波德(Anna Barbauld)不但是卓有成就的诗人,还身兼文学编辑之职,在当时的文学圈里颇有名气。弗雷西亚·海曼斯(Felicia Hemans)和利蒂希娅 ·兰登(L.E.Landon)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女诗人,她们在济慈、雪莱和拜伦去世后活跃在浪漫主义诗坛。应该说正是女性诗人开启了浪漫主义时代,又是女性诗人圆满地结束了浪漫主义时代,实现了从浪漫主义诗歌到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创作的衔接与过渡。
这些女性诗人在浪漫主义时代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当时的评论界对此既有褒扬和肯定,也有颇带酸味的讽刺和挖苦,将她们称为“失去性征的女性”。而这些女性之所以失去女性性征,不过是因为她们有了独立的思想,涉足了男权主导的文学创作领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女性诗人在文学创作中,是否真的有意识地融入一些男性特征的元素呢?她们在创作的时候是否处于柯勒律治所说的“半雌半雄”的状态呢?
二、“失去性征”的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人
“失去性征的女性”是18世纪末男性评论家对于当时女性作家的讽刺之词,1797年由马赛厄斯(T.J.Mathias)在其《文学的追求:一首对话体的讽刺诗》(The Pursuits of Literature: A Satirical Poem in Dialogue)的前言中首次使用。“失去性征的女性”指的是不具备柔美、温顺、矜持等女性特质的女性,那么,这些女性文人为什么会被称为“失去性征的女性”呢?
18世纪中后期的西方社会,处于传统向现代更替的交接阶段,政治上革命频发,思想上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主义引领了整个意识形态,文学创作上求新求变、回归自然的创作理念开始滋生发展。可以说,18世纪末期正处于历史的某种临界点,新的事物通过各种变革而对旧的事物进行冲击、实现超越,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经历一场裂变,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开始被关注、被强调。
进步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对当时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深刻分析与揭露,对于当时人们,尤其是女性的觉醒有着一定的启蒙作用,但其对女性的态度依然是传统的、男权思想的。其教育学名著《爱弥儿:论教育》(1762)中“归于自然”的教育思想带有新兴资产阶级的先进性,但作者在第五卷谈到女性教育问题时,却流露出了男权的思想,他说:“我们确切知道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具有人类的特点,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性……所有这些相同和相异的地方,对人的精神道德是有影响的……每一种性别的人在按照他或她特有的方向奔赴大自然的目的地时,要是同另一种性别的人再相像一点的话,那反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完善了!”(卢梭,2009:579)而对于男女性别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异,卢梭是这样阐述的:“一个是积极主动和身强力壮的,而另一个则是消极被动和身体柔弱的……女人是特地为了使男人感到喜悦而生成这个样子的。”(同上: 580)卢梭这样的论述,无疑暗示出女性由于其性别的差异,无论在体格力量上还是在精神道德上都弱于男性,而且这种男女性别的优劣是自然的法令,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这就有意无意地维护了父权社会的男性权威。
卢梭在性别差异的论调上受到了以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为代表的女性文人、女性思想家的抨击,促使她们开始对女性的主体性进行深入思考,引领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女性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中就批判了卢梭的女性教育观,强烈呼吁对女性的教育进行改革。针对卢梭的性别差异论,当时的女历史学家格雷厄姆(Catharine Macaulay Graham)也反驳说,不存在实质上的性别差异,所谓的差异,也即女性在身体与智力上都弱于男性的差异,实际上都是教育的结果。
在卢梭的《爱弥儿:论教育》之后,对女性行为规范进行规诫的书主要是詹姆斯·福代斯(James Fordyce)的《对年轻女性的劝诫》(Sermons to Young Women)(1765)以及约翰·格雷戈里(John Gregory)的《一位父亲留给其女儿的遗产》(A Father’s Legacy to his Daughters)(1774),这两本书都代表了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要求与束缚,具有强烈的男权色彩。福代斯(Fordyce,2008:90)说:“带有男人味的女性在本质上一定是不和蔼的动物,我承认每当我看到性别被混淆的时候我都极度震惊。”这里福代斯将不合乎当时女性行为规范、侵犯了男性行为范畴的女性称为“带有男人味的女性”,也就是没有女人味、不具备女性美的女性,毫不掩饰地对其进行抨击和挖苦。格雷戈里(Gregory,2008: 92)对女性美的总结则是“女性所具有的美主要是谦虚的保守,是含蓄的优雅,要避开公众的眼睛,即使是在崇敬的注视中也应感到不安”。
为什么这些男性突然对女性的行为规范如此敏感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在这段时期,教育水平的提高、流通图书馆的出现以及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促使女性作家作品风起云涌。她们“作为小说家、诗人及社会评论员,开始在数量上、作品的销量上、文学声誉上与男性竞争匹敌;仅仅在诗歌领域,大约有900名女性被列入到了杰克逊 (J.R.de J.Jackson)最近的研究书目《女性创作的浪漫主义诗歌》之中”(Abrams,2000:4-5)。她们没有“避开公众的眼睛”,在文学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才华横溢的女性诗人却受到了男权社会的舆论抨击,“当时的杂志抨击女性作家和知识分子为‘失去性征的女性’(unsexed females)或 ‘装作有学问的女人’(bluestockings)”(Bainbridge,2008:89),女性涉足一向被认为是男性领域的文学自然会招来男性“正当防卫”式的抨击。这些女性由于撰写诗歌、发表诗歌而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由此失去了女性该有的优良品质。其二,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人的影响下,女性诗人在作品中表达女性的呼声,积极参与为女性争取权益的运动。正如戴维·辛普森(Simpson,2009: 406)所总结的那样,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权力辩护》“对于理解同时代的诸如史密斯、罗宾森……等许多女性作家的小说和诗歌,可谓是一个批评准绳”。史密斯政治观点激进,通常被认为是18世纪90年代与沃斯通克拉夫特同道的女性雅各宾派作家(Vermeule,2009:29)。罗宾森在1799年发表其《就智力劣等问题的不公平性致英格兰女性书》(A Letter to the Women of England on the Injustice of Mental Subordination)表达了她的女性观,勇敢而又直接地对男权社会的传统发出挑战和抗议。对此,艾德里安娜·克勒琼(Craciun,2009: 382)总结道:“罗宾森努力在其作品中将政治激进性、理性、情感和戏剧风格融合在一起,这对我们理解浪漫主义文学和政治传统以及理解早期的女性主义都有着独特的价值。”可以说,女性诗人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女性主义萌芽,使得更多的女性开始质疑自己的性别身份与社会角色,挑战并动摇了父权文化。
理查德·波尔威尔(Richard Polwhele)在1798年撰诗攻击女性文人,题名即为《失去性征的女性》(The Unsex’d Females)。作者在诗中公然提到了大量同时代女性文人的名字,而其 “对安娜·芭波德、玛丽·罗宾森及夏洛特·史密斯的蔑视性评论,则源于她们成功表现为沃斯通克拉夫特式的理想女性:所谓理想女性就是要用自己的才智去挑战不公平的社会规范 ”(Pascoe,2004: 212)。对此,帕斯科 (Judith Pascoe)总结说:“在波尔威尔看来,沃斯通克拉夫特及她的追随者们是没有性别的,或者说是由于她们激进的情感而失去了令人称道的、女性必需的性别特质。”(ibid.: 212)而这些女性之所以失去女性性征,不过是因为她们涉足了男权主导的文学创作领域,并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女性的呼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女性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是否真的有意识地融入一些男性特征的元素呢?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升华为“雌雄同体”的创作论了。
三、从“失去性征的女性”到“雌雄同体”
如同新批评的课堂一样,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的教授朱莉娅·瑞特(Julia M.Wright)也在文学课堂上做了有趣的实验,她将诗歌的作者隐去,只让学生专注于诗歌文本自身。朱莉娅在课堂上分别将雪莱的《幽灵骑手》(The Spectral Horseman)、罗宾森的《1795年的1月》(January,1795)及布莱克的《歌》(Song)这三首诗歌隐去作者,告诉学生一首诗的作者来自下层百姓,一首诗的作者是贵族,而另一首诗的作者则是一位女性。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给出同样的答案:“政治诗是贵族写的,哥特风格的诗是下层诗人所作,而唯一的女性所写的则是抒情诗,一首他们认为是以女性的口吻所写的抒情诗。”(Wright,2007:271) 而实际的情况是,贵族雪莱写了哥特风格的《幽灵骑手》,来自社会下层的布莱克写的是抒情诗,而唯一的女性罗宾森写的则是政治歌谣《1795年的1月》。这个实例说明,好的诗歌应该是超越性别、超越阶级的,文本与作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唯一的、固定的联系,诗人通过自己非凡的想象力和高于常人的感悟力,男性诗人可以写出具有女性特质的诗歌,女性诗人也可以在诗歌中畅谈政治。因此,很难说女性文学是截然不同于男性文学的。实际上,正如浪漫主义诗人、文论家柯勒律治所认为的那样,伟大作家的大脑应该是“半雌半雄”的,伟大的诗人在写作时并不总是因循自己的性别感悟,而是有所兼顾,着力表现作品的完整性与统一性。这体现出浪漫主义诗学的有机整体论思想,也被视作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雌雄同体”创作论的前身。
“雌雄同体”(androgyny)源于希腊语,指的是兼具男性和女性特点的人,在20世纪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中,“雌雄同体”被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阐发为“艺术创作的一种最佳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下创作的作品也是最好的”(沈建青,2007: 205)。她说:“如果一个人是男性,他头脑中那部分女性因素必定仍然在发挥作用;如果是个女性,她也必须和头脑中的男性因素沟通对话”(伍尔芙,2001: 578),这是一种心理状态,正如潘健所总结的那样,“伍尔夫的‘雌雄同体’不是生物学上的概念,而是指某种精神状态:‘大脑统一’和‘自然的融合’,它不是简单的一元状态,而是由异质构成的‘整体’”(潘建,2008:102)。伍尔芙的这种观点承袭了柯勒律治的“半雌半雄”论和有机整体论,而之前她所提出的“一个作家是没有性别的”之说(伍尔芙,2001:195),也与济慈的“消极感受力”颇为相似,都谈及作家的创作心理,只不过前者是以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为核心,而后者是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因此,从内因来看,无论是基于浪漫主义诗学的创作论,还是基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创作论,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人就应该是“失去性征的”,因为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处于最佳的艺术创作状态,也即处于“没有性别的”、“雌雄同体”的创作状态。
而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人“雌雄同体”创作论的形成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外因。一方面,许多女性诗人进行文学创作的初衷是赚钱谋生,这就要求她们不仅在创作中表达女性的呼声,还要兼顾主流男权文化的接受。史密斯15岁就被迫出嫁,夫家虽家境殷实,但丈夫是个游手好闲的败家子,使得史密斯始终挣扎在贫困的边缘。为了抚育十个孩子,史密斯不得不写作赚钱。罗宾森16岁结婚,婚后不久便发现丈夫深陷债务纠纷,为了替夫还债罗宾森不得不在陪伴丈夫的狱中开始写作,并且不久开始登台演出舞台剧赚钱。海曼斯和兰登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流行女性诗人,写作已然成为一种职业,她们的诗作要迎合大众的欣赏品位。在这些情况下,女性诗人在创作中就必须要避弃过分女性特质的东西,而将自己的女性视野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之中,这就在客观上驱使女性诗人在创作中要“雌雄同体”。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女性诗人可以接触到当时先进的启蒙思想,也能够认真思考女性自身的社会角色与主体地位。女性是社会不公平的多重受害者,她们在政治上没有话语权,在情感上被动、顺从,在经济上依赖男性,是男性的附庸。对于这样的生存现状,女性文人自然通过创作来表达诉求,用 “自己的才智去挑战不公平的社会规范”:文学创作上的成功使她们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她们因而能够表达也勇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反过来,她们视野的开阔与观点的进步又通过作品表达出来,使她们的声音能够成为公开的、公共的声音。关注政治、渴求平等使她们站在了一定的高度上,使她们拥有了男性权威的气势,在作品中便也反映出这种“雌雄同体”式的创作来。
在浪漫主义时期,由于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公平的社会状况或者说社会性的差异,在女性文人那里突出表现为性别差异,她们通过创作中“雌雄同体”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表达出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以及消除社会不公的美好愿望,同时也体现出诗歌美学意义上的完整性以及对狭隘视野的超越。
四、浪漫主义女性诗人的“雌雄同体”创作
在浪漫主义时代,男性诗人的缪斯多为女性,好比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好比《忽必烈汗》中阿比西尼亚的少女,使其作品中自然带有女性特质的东西。多考 (Dokou,1997: 3)在其研究中就肯定了当代女性主义者的论断,也认为“将女性特质的因素移入男性意识之中实际上是浪漫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主题”。而对于浪漫主义女性诗人来讲,也同样有男性特质的因素移入女性意识之中,女性诗歌作品的“雌雄同体”也可以理解为浪漫主义女性诗歌的一个创作原则、一个传统主题。
海曼斯是一位多产的女性诗人,也拥有很大的读者群,她为《爱丁堡月刊》(EdinburghMonthly Magazine)和《新月刊杂志》(New Monthly Magazine)等有影响的杂志撰稿,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对于究竟该如何对待这样一位天才的女性诗人,评论家们颇感尴尬。《评论月刊》(Monthly Review)将她对于某些场景的描绘称为‘大师级的’(masterly),但又在脚注中质疑说‘我们可以将这个词应用到一位女性身上吗?’”(Kennedy,1992:259)这是当时评论界对海曼斯的肯定,但又似乎在百般挑剔,原因更多的是由其女性的性别身份所引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样的评论也说明了海曼斯创作的“雌雄同体”,单纯从诗歌文本来看,并没有突出的女性特质的痕迹,而是体现了一种更为开阔的、完整的表达视野,而也正是这种视野成就了海曼斯诗歌创作生涯的成功。
《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1826)是海曼斯非常著名的一首诗歌,描绘的是1798年发生在埃及的英法之间的尼罗河战役。卡萨布兰卡是一位法国舰队司令的儿子,年仅13岁,在尼罗河战役中他一直坚守在船上,在坚定与忠诚中与船只同归于尽。海曼斯作为一个爱国的女性诗人,她居然在讴歌法军将领的孩子,这是一种悖论式的表述。对这首诗的解读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是对敌军男孩的热情赞美,还有人认为,讴歌与赞美只是表面现象,其真实意图是对卡萨布兰卡的谴责和嘲讽,因为他的忠诚实则是一种愚钝、无知的顺从。
在这首诗歌中,诗人将历史上的一次战役与一个小男孩联系在一起,通过一个天真的孩子来描写这次战役,更透过这次战役来描写战争。卡萨布兰卡孤身坚守在炮火纷飞的战船中,他身体里流的是“英雄的血液”(heroic blood),尽管有着一副“孩子的身形”(child-like form),但却表现出凛然的傲气,他一遍遍喊着他的父亲,追问“我的任务是否已完成?”(If yet my task is done?)“我是否可以走开!”(If I may yet be gone!)第一次追问时还是问句,在没有得到父亲的回答后,第二次追问已然变成了叹句,以叹句来表达自己的呐喊。这表现出了孩子的茫然与惶然,这时的他已经陷入到了“勇敢的绝望”(brave despair)之中。在这里,诗人用一种悖论式的语言暗示出了对男孩勇敢行为的批判,这种勇敢注定是绝望的,是鲁莽的,是天真的。在诗歌的结尾部分诗人写到:
忽来一阵雷声响——
那男孩——哦!他身在何处?
试问狂风在远方
纷飞碎片海面露!——
男孩最终为自己的勇敢和忠诚付出了代价,可怜他也在炮火声中灰飞烟灭。在最后两句诗行中诗人写到:
只是消失彼处的最珍之物
是那年轻的忠效之心!
忠诚是一种宝贵的品质,但若忠诚失去了方向,是一种孩子所有的天真的忠诚,它就会成为毁灭的导索。诗人一次鞭挞战争的残酷,战争毁灭的不仅是年轻的生命,还有一颗忠效之心。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海曼斯作为一名女性诗人,能够以这样的气魄、这样的视野来描写战争,已然完全超越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界定。实际上,“在海曼斯作品众多的主题中,爱国主义和军事行动频繁再现”(Abrams,2000: 812)。不仅如此,她的许多诗歌的主题都是欧洲文化与历史,如《艺术作品的意式回归》(The Restoration of the Works of Art to Italy)(1816)、《现代希腊》(Modern Greece)(1817)以及《故事与历史场景》(Tales and Historic Scenes)(1819)。1826 年,海曼斯写出了21首诗歌的集子《多国叙事诗》(Lays of Many Lands),对各国的事件进行评论,这些都说明了海曼斯“雌雄同体”式的创作主题。
从“雌雄同体”创作的角度来看,芭波德也得到了当时评论界的肯定。《威斯敏斯特杂志》在1776年的一篇文章对芭波德的诗歌赞誉有加,但这种赞美是基于男权审美观的,芭波德的诗歌之所以好是因为具有“男性的力量”:“实际上,她诗歌中除了表达之优雅外,毫无女性特质的东西,而表明这些诗歌是出自女性之笔的标志也就是优雅的表达了。”(Pascoe,2004: 216)这说明芭波德的诗歌创作具有男性特质,其伟大之处正在于恰当地结合了女性的优雅和“男性的力量”,是一种“雌雄同体”的表达。此外,在芭波德诗歌中还有一个较为常见的主题,就是 “可见的”(visible)和“不可见的”(invisible)之间的对照,“可见的”只是表象,“不可见的”才是本质。人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和其诗歌创作也不谋而合,她发表诗歌作品或匿名、或以简称、或以“一位女士”(A Lady)自称,这也是在呼吁人们透过这样的现象去挖掘诗人的真实身份,而这种情况下再现的诗人之女性身份,无疑有着更为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应该说,“雌雄同体”这一概念本身就表达了一种矛盾的统一,体现了浪漫主义的辩证观、有机论。在浪漫主义诗人艺术创作的层面,“雌雄同体”是一种创作心理,在中性的状态下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但“雌雄同体”不仅仅体现出有机的、融合的、伟大的创作思想,而且不同的性别主体会体现出不同的主体意识与主体认同。男性诗人的“雌雄同体”更多反映出的是情感主义意识、是一种自我否定。比如,多考(Dokou,1997:10)在分析拜伦的 《唐璜》时认为, 《唐璜》所体现的“雌雄同体”并不是对男性英雄主义的歌咏,而是对男性权威的一种批判,也即“雌雄同体的声音在挑战父权文化时与女性的声音同样有效”。男性权威是当时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敏感的男性诗人们也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对社会的失望、无奈和抗议似乎通过这个可以抒发表达出来。
相比之下,女性诗人的“雌雄同体”更多反映出的是女性主义意识、是一种自我肯定,这在女性诗人有关萨福(Sappho)之主题的诗歌创作中有所体现。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可谓是“失去性征的”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人心中的先驱,是她们的缪斯女神,但这位缪斯复杂的性别认同传说使其在个人形象上更偏向于中性的“雌雄同体”:萨福身边围拥着众多年轻美丽的女子,她们崇拜萨福、奉萨福为师,萨福也毫不掩饰地表露对这些女子的爱慕之情、同性之恋。甚至在萨福的诗歌作品中,也有似乎从男性心理视角的对女性之美的观察与歌咏,这些都赋予了萨福以 “雌雄同体”的意味。浪漫主义女性诗人们在作品中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及萨福,有的诗歌直接以萨福命名:海曼斯的《萨福的最后一歌》(The Last Song of Sappho);兰登的《萨福》(Sappho)和《萨福之歌》(Sappho’s Song)、罗宾森的《萨福与法翁》(Sappho and Phaon)等等。萨福作为一名女性诗人,表达了一种女性的欲望,这种女性的欲望又带有阳刚之气的霸道,正如文森特(Vincent,2004:54)所总结的那样,“海曼斯、兰登……的萨福诗歌有意识地重构了一个‘自身情欲能自我满足的’萨福”,对女性欲望的直接表达是女性意识的体现。萨福身边的众多少女以及萨福诗歌中若隐若现的性爱描绘,暗示出一种女性欲望的自足,这是女性独立于男性、解放于男性的体现。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人希望通过萨福来获得“对她们自身伦理道德的认同”,也是通过在作品中对萨福的诠释,女性诗人“建构了一种同时具有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意味的主体身份”(ibid.: xix)。 通过这样一种建构,浪漫主义女性诗人笔下的萨福实际上成了她们的代言人,不仅传达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同时也是“雌雄同体”的化身,是女性诗人“雌雄同体”式创作的缪斯。
五、结语
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人通过“雌雄同体”那既矛盾又统一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反映了时代精神、抒发了女性意识,既有对不平现实的否定与批判,也有对美好世界的追求与向往。她们从“失去性征的女性”到“雌雄同体”,实现了诗歌创作的升华和文学生涯的成功,也成就了浪漫主义女性诗歌在当代的再解读与再接受。
[1]Abrams,M.H.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C].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2000.
[2]Bainbridge,S.Romanticism: A Sourcebook[C].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
[3]Craciun,A.Mary Robinson[A].In D.S.Kastan(ed.)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4]Dokou,C.Androgyny’s Challenge to theLaw of the Father: Don Juan as Epic in Reverse [J].Mosaic,1997,(30): 3.
[5]Fordyce,J.Sermons to Young Women [A].In S.Bainbridge(ed.)Romanticism: A Sourcebook[C].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
[6]Gregory,J.A Father’s Legacy to His Daughters [A].In S.Bainbridge(ed.)Romanticism: A Sourcebook[C].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
[7]Kennedy,D.Hemans,Felicia[A].In L.Dabundo(ed.)Encyclopedia of Romanticism: Culture in Britain,1780s-1830s[C].London: Routledge,1992.
[8]Pascoe,J.Unsex’d Females: Barbauld,Robinson,and Smith [A].In T.Keymer & J.Mee(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1740-1830[C].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9]Simpson,D.Romanticism[A].In D.S.Kastan (ed.)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10]Vermeule,B.Charlotte Smith[A].In D.S.Kastan(ed.)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11]Vincent,P.H.The Romantic Poetess: European Culture,Politics,and Gender,1820-1840[M].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4.
[12]Wright,J.M.Baillie and Blak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llegory and Drama[A].In H.P.Bruder (ed.)Women Reading William Blake[C].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7.
[13]陈璟霞.劳伦斯的女性意识和双性主题[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2): 76-80.
[14]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M].张学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5]卢梭.爱弥儿:论教育[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6]潘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与文学创作[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96-102.
[17]沈建青.双性同体[A].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8]张智义.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华氏兄妹创作[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3): 5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