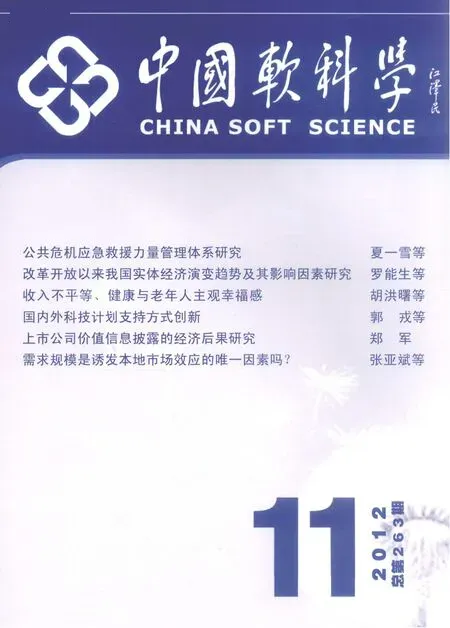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水平分析
姚建平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2206)
一、导论
针对目前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简称“低保标准”)水平如何有大量的研究。例如,唐钧采用“恩格尔系数法”、“收入比例法”对2010年的我国城市低保标准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的城市低保标准明显偏低[1]。有学者根据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测定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理论标准,并将其与近几年的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发现,实际给付水平明显偏低。现行低保线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无法满足低保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2]。彭翔和徐爱军同样采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测算江苏省城乡居民的基本消费支出,并以此评价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合理性。结果表明,江苏省的最次生活保障标准未能满足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3]。其他类似的研究也大都证明了我国低保标准偏低。例如有学者采用收入分布函数法对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测算,结果发现北京市的低保标准存在明显偏低现象[4]。高清辉将当地上一年度年平均工资作为参照基础设定救助力度系数,来衡量该地区低保标准水平的高低。结果发现,名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较高的城市,如深圳、上海等,其实质救助水平并不高[5]。吴碧英根据36 个中心城市的主要经济指标(人均可支配收人、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收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各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偏低,有的城市可能过低[6]。
从计算方法本身也能大体判断该方法计算出来的贫困线是偏高还是偏低。贫困线计算方法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贫困定位,另一类是绝对贫困定位。一般来说,采用相对贫困定位的计算方法所计算出来的贫困线会偏高,而采用绝对贫困定位的计算方法所计算出来的贫困线会偏低。例如,国际贫困标准方法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收入或中位收入的50% ~6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这种方法就属于相对贫困定位,计算的贫困线通常比较高,因此主要被发达国家采用,发展中国家较少采用此法直接实施社会救助项目[7]。以消费挂钩来计算贫困线的方法非常多,但是绝大多数都属于绝对贫困定位。例如,1990年,世界银行按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出每年370 美元为贫困线,后被简化成“1 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2008年,世界银行以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进行测算,将国际贫困标准提高到“1 天1.25 美元”[8]。毫无疑问,“1 天1美元”法是国际通行的绝对贫困衡量标准。市场菜篮法最早由英国人朗特里在1601年提出。他当时按照营养学家给出的一个人每天应该需要的各种营养要素,将他们折合成相应的食品。在此基础上,按照市场上的最经济的价格将这些基本的消费品折算成货币单位,以此作为划分贫困线的标准。市场菜篮法的根本理念是维持生存,因此该法计算的贫困线也会偏低。再如,恩格尔系数法是建立在恩格尔定律基础上,贫困线的确定是以食品消费支出除以已知的恩格尔系数求出所需的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法以食品支出为基础,也是明显的绝对贫困定位。世界银行贫困问题专家马丁·瑞沃林认为贫困线=食品支出 + 基本非食品支出(简称“马丁法”)。食品支出即达到一定的营养需要所必需的营养支出;在此基础上,利用回归模型方法,找出这样一些贫困家庭——其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刚好等于食品贫困线,计算他们的非食品支出,就是非食品贫困线[9]。马丁法从本质上是基于食品支出和贫困人口的非食品支出,因此采用该法计算的贫困线也会偏低。
消费支出比例法既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相对贫困定位,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定位,是两者的折中。这是因为消费支出比例法所确定的贫困线是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一定比例。它既不像收入比例法(例如国际贫困线法)那样所确定标准往往过高,也不像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法等法所确定的标准往往过低。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考虑到要让贫困群体一定程度上分享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采用消费支出比例法来计算和评价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水平的高低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另外,从操作层面来看,与其他方法相比,消费比例法最大的特点是计算简单、调整方便、形象直观且易于理解。从计算的角度来看,大部分以消费支出为基础的方法需要计算食品线和非食品线两个部分,并且一些方法的食品线和非食品线计算非常复杂,非专业人士很难理解和掌握。例如,马丁法和扩展线性支出模型。从贫困线调整的角度来看,很多贫困线计算方法调整时通常也需要考虑食品和非食品两个部分,因此调整起来比较复杂。而消费比例法具有自动调整功能的计算方法。只要当地人均消费支出发生了变化,那么贫困线就按照既定的比例自动调整[10]。有鉴于此,本文采用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简称“消费支出替代率”)来衡量低保标准的高低。消费支出替代率概念界定如下:消费支出替代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当地居民平均消费支出。消费支出替代率越高,说明该地区的低保标准越高,反之亦然。
二、当前中国城市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水平
目前能找到的低保标准的统计口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各区县确定低保标准后逐级上报,最后由民政部按照省、地级市和区县汇总。二是36 个中心城市低保标准由民政部社会救助司低保处进行统计。从时间上来看,36 个中心城市低保标准是目前已公布的低保标准资料中最完整的。36 个中心城市一般都是各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36个中心城市消费支出替代率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见表1):

表1 36 个中心城市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2010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0年我国36 个中心城市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平均只有0.26。最高的天津市为0.33,最低厦门市只有0.17。从消费支出替代率分布情况来看,替代率在0.30 及以上的城市包括天津、石家庄、太原、武汉、海口、拉萨、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九个城市。除了天津以外,其他城市均属于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而消费支出替代率最低的九城市(低于或等于0.23)包括上海、福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贵阳、昆明、银川,其中既有经济最发达东南沿海城市,也有西部最不发达地区城市。
对36 个中心城市进行测算只考虑了经济最发达地区的情况。全国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特别是数量庞大的中小城市的消费支出替代率情况是否与大城市一样呢?各省的数据不仅包括了该省经济最发达地区情况,也包括了该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情况。这里仅以省为单位,对各省城市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进行分析(见表2):

表2 各省城市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2010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0年我国各省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平均只有0.24,低于中心城市。最高天津市为0.33,最低的广东省只有0.17。从消费支出替代率分布情况来看,替代率在0.30 及以上的只有天津和河北两个省/直辖市。而消费支出替代率最低的12 个省/直辖市(低于或等于0.23)包括吉林、上海、福建、河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宁夏、新疆。由于各省数据既包括中心城市也包括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因此通过比较可以推断出不发达地区的消费支出替代率总体平均应该比中心城市还要低。
通过以上对消费支出替代率的分析可以判断,目前中国的低保标准应该是比较低的。从前文关于我国低保标准水平研究的文献回顾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我国目前的低保标准水平会偏低呢?这和我国目前低保制度的目标定位密切相关。从制度名称来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能是保障基本生存的需要,以起到一个最低层次的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定仅仅考虑了衣服、食品、水电煤气等生存维持必须项目,而医疗、教育、住房、交通、通讯、社会交往等项目考虑得非常少[11]。从计算方法来看,我国各地普遍采用绝对贫困取向的低保标准计算方法。例如,市场菜篮法按照营养学家给出的一个人每天应该需要的各种营养要素,将他们折合成相应的食品,再根据对实际生活的调查,确定一个家庭需要在非食品方面的最低消费。由于市场菜篮法主要考虑基本营养需求,因此按此法测出的低保标准肯定偏低。再如,恩格尔系数法确定贫困线是用食品消费支出除以已知的恩格尔系数,求出所需的总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法基本思路是保障食品需求基础上适当考虑非食品需求,因此采用此法制定出来贫困标准也会偏低。从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低保制度从绝对贫困定位向相对贫困定位适当发展,让低保对象一定程度上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应是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从长远来看必然会涉及到提高低保标准水平的问题。

表3 部分省市低保标准的最低工资替代率(2010年)
三、当前低保标准福利依赖情况判断
提高低保标准一个重要担心是福利依赖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削减福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福利依赖现象严重。福利依赖本质是由于福利待遇水平过高,导致福利接受者丧失工作动机。从理论上来看,福利接受者一般会对接受福利条件下的成本、收益和参加工作条件下的成本、收益比较。只要接受福利条件下的收益水平等于或大于工作条件下的收益水平,一个理性的福利接受者通常都会选择依靠福利生活而不是参加工作,进而形成福利依赖。如何来判断低保制度可能产生的福利依赖程度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低保标准对最低工资的替代水平。实际上,目前我国很多地区已经将低保标准的调整盯住最低工资,低保标准的计算就是最低工资的一定比例,用以防止福利依赖。表3 是我国部分省市低保标准的最低工资替代率。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低保标准的最低工资替代率并不高,全国平均只有0.30,最高的天津市为0.47,而最低的新疆只有0.24。如果和欧洲的情况进行比较,当前我国城市低保标准的最低工资替代率也明显偏低。从欧洲7 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英国、荷兰、瑞典)社会救助制度的实际收入替代率情况来看:1994年,低收入单身汉失业时收入替代率最高的瑞典为81%,最低的是英国是34%,平均为54.5%;有两个孩子的低收入单职工家庭失业时收入替代率最高的丹麦为145%,最低的法国为57%,平均为102.29%;有两个孩子的低收入单亲家庭失业时收入替代率最高德国为89%,最低的法国为55%,平均为73.86%;有两个孩子的低收入双职工家庭失业时收入替代率最高的丹麦为115%,最低的荷兰为63%,平均为91.5%①注:(1)收入替代率(原著译为更新率)指失业时,扣除房屋费后的经济标准占工作时的经济标准的百分比。也就是当家庭的赚钱人(糊口人)失业时家庭可支配收入与他或她就业时可供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2)低收入指就业时家庭收入占一般产业工人收入的50%,与最低工资水平接近。参见爱纳汉德,M.等.欧洲七国失业与社会援助制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8-12.。从欧洲7 国的社会救助的收入替代率来看,其标准应该远高于我国现有的低保标准。那么收入替代率多少比较合适呢?有关欧洲7 国的研究显示,当其社会援助对低收入的替代率超过80%,救济累加等于或高于工作收入时,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动力大大减弱。由于文化背景和国情不同,欧洲7 国“80%”的临界值放在中国仍然值得商榷。但通过和欧洲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低保标准的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是一个趋势。
针对福利依赖问题,各地在具体执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过程中针对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制定了一些防范措施。例如《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在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不能享受低保。在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人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一个月内无正当理由2 次以上拒绝参加社区公益性劳动的也不能享受低保。尽管对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的就业要求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福利依赖,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一项对北京低保户的研究表明,对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低保户来说,低保救助金只是对其家庭收入的补充而不是其主要的收入。实际上,之所以产生上述“福利依赖”现象,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低保资格附带着很多连带的利益。例如,很多辅助性的社会救助制度如医疗、教育和住房救助等都是优先甚至完全针对低保户的。如果低保户失去低保资格,他们就会自动地失去这些利益,而这些帮助对很多低保户来说是更重要的[12]。也就是说,低保制度在多重福利捆绑下,其“含金量”实际上非常高。例如,根据南京市物价局等10 个部门《关于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收费减免问题的通知》(宁价费[2002]238 号)文件精神,南京市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有资格享受费用减免待遇的项目达到30 多项,具体涉及提供就业信息和推荐就业的相关收费、进入市场经营的各种收费、从事个体经营的相关收费、子女教育相关费用、医疗费用、房租、有线电视安装费及月收视维护费、园林景点门票、各项对再就业者的收费减免、婚姻登记的工本费、丧葬火化费,等等。
四、不同消费支出替代率下的财政状况分析
提高低保标准的另一担心是会给国家财政造成负担。从理论上看,提高消费支出替代率必然会导致财政支出的增加,这里的问题是财政支出会增加多少。目前,政府和理论界对于提高低保线的一个重要顾虑是担心低保线提高后会增加大量符合资格条件的低保对象,进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但是从实际经验来看,有很多证据表明替代率(低保标准)提高后并不一定会导致低保人数增加:
第一,从全国的情况来看,自2002年低保制度实现“应保尽保”以来,低保标准每年都在提高,但并没有导致低保人数的显著增加。下图是1996-2010年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人数及年增长率:

图1 1996-2010年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人数及年增长率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保制度推行之初,受保人数比较有限。1996年,全国接受低保的城市居民只有84.9 万。但1999年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后,受保人数随着低保制度的完善迅速增长。1999年低保覆盖人数为265.9万,2000年增长了近一倍为402.6 万,2001年又增长了一倍多达到1170.7 万,2002年在2001年的基础上再次翻倍达到2064.7 万,并且基本上保障了城镇所有贫困人口,从而实现了应保尽保。此后一直持续到2010年近10年的时间里,我国城市低保人口总数基本上维持在2000 多万人左右,既没有显著增加也没有显著减少。
第二,从地方实践来看,提高低保标准也不一定会导致低保人数的增加。例如,从南通市市区城市低保历年提标历史来看,2004年市区城市低保标准由200 元提高到220 元,而人口却由6740人减少到6560 人;2005年标准提高到240 元,人数减少到6205 人;2007年标准提高到270 元,当年保障人数仅为5732 人;2008年标准提高到320元,人数减少到5196 人;2009年标准提高到340元,人数减少到4936 人[13]。南通市的实践表明,低保标准的提高过程却伴随着低保人数的减少。
为什么提高低保标准而低保人数可能不会显著增加呢?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低收入户的家庭收入变动。当低收入户的家庭收入增加平均水平高于低保标准增加水平时,低保人数不仅不会增加还可能会减少。二是家庭收入调查机制问题。目前我国低保制度家庭收入调查机制不完善,与居民收入相关的基本信息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相当多的地方还要依靠民主评议和张榜公示等传统手段来确定低保对象,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如果基层工作人员从严把握政策的话,就很容易造成符合资格条件的贫困家庭难以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符合低保救助资格条件的人可能并不会都去申请。有很多原因会造成符合资格条件的人不去申请救助。例如,低保制度的“标签效应”可能导致很多符合条件的贫困者并不会去申请低保。还有一些贫困者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符合申请低保的资格条件而不去申请低保。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符合社会救助项目资格条件的人不去申请社会救助也比较常见。以美国的食品券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研究表明,符合条件家庭的食品券参与率大约为50%,也就是说有数百万符合食品券计划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并没有领取食品券。符合条件的人不去领取食品券的原因有很多,1993年一项在宾夕发尼亚州艾黎格尼(Allegheny)县的调查表明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很多人自认为他们不符合领取食品券的条件(59.7%)。二是很多有资格的家庭(22%)不去领取食品券是因为觉得食品券项目每月的收益有限,他们觉得不值得或不需要领取。三是也有一些人(6%)认为不去领取食品券跟个人耻辱有关[14]。表4 是在假设消费支出替代率提高后低保人数不变的条件下,以2010年12月低保情况为基准计算全国低保财政支出的变动状况:

表4 低保人数不变条件下提高消费支出替代率后的各省财政支出状况(2010年12月为基准)
2010年,全国平均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为0.24,考虑补差后全国每月低保总支出大约为495.86 亿元。2010年全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为83101.51 亿元,2010年全年低保支出约占财政总支出的7.16%。从上表可以看出,如果以采用0.3的消费支出替代率,那么每月总支出将增加到282.48 亿元,考虑补差后实际增加189.05 亿元,全年实际增加的低保支出将约占财政总收入的2.7%。如果以采用0.35 的消费支出替代率,那么每月总支出将增加到约412.21 亿元,考虑补差后实际增加275.86 亿元,全年实际增加的低保支出将约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3.9%。由此可见,如果替代率提高后不考虑低保人数的增加,替代率即使从0.24 增加到0.35(增加11 个百分点)的财政支出增幅也并不是很大。
从提高消费支出替代率对各地区财政支出的影响情况来看,如果将平均替代率提高到0.30,天津和西藏因为消费替代率本来就高于0.30 而都将减少支出,其他各省市都会增加低保支出。增加最多的四川省将增加15.97 亿,其次是湖南省将增加11.28 亿,以后依次是河南、辽宁、湖北等省/市。财政支出增加最少的青海省只增加1509.24 万,以后依次是北京、海南、浙江等省/市。如果将平均替代率提高到0.35,全国所有省市低保财政支出都将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较大的主要是人口众多且经济欠发达的省市,例如四川、河南、辽宁、湖北等省。而支出增加较少的省市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经济不发达但消费替代率较高的地区,例如青海、宁夏。由于这些地区本身人口少且人均消费支出很低,因此增加的低保支出不多。另一种情况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区,例如北京、江苏、浙江等。由于这些地区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低保人数相对较少,加上其消费替代率已经不低,因此增加的支出也不多。目前我国低保资金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担制度,中央财政对于低保财政支出较大的省市分担的比例更大。例如,中央财政对于四川、湖南、湖北、辽宁、吉林、河南、陕西、内蒙等低保资金增加较多的省份分担比例分别达到了88%、98%、100%、102%、82%、90%、71%、59%。因此,提高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而引起的低保支出增加的负担将主要落在中央财政上。
如果不考虑前文所述影响低保人数变动的现实因素,那么替代率提高后低保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理论上应当是增加的。由于找不到全国和各省的收入/消费分布函数,因此很难准确计算替代率提高后低保人数会有多大的增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假设现有低保人群收入分布是均匀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低保标准提高后低保人数增加的情况进行推断①现有低保人群收入分布是均匀的假设应该比较合理,其原因是:目前我国城镇低保标准比较低,因此低保人群的收入分布应该不会相差太大。例如,2010年12月全国平均低保标准是267.47 元,也就是说全国低保接受者的收入在0 到267.47 元之间分布应该不会相差太大。。表5 是基于替代率提高后低保人数增加的假设,对财政支出状况进行的计算。
2010年,全国平均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为0.24,考虑补差后2010年全年低保实际支出约占财政总支出的7.16%。如果采用0.3 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并考虑低保人数增加因素,那么每月总支出将增加到484.19 亿元,考虑补差后实际增加为324.04 亿元。消费支出替代率提高到0.3 后全年实际增加的低保支出将约占财政总收入的4.68%。如果采用0.35 的消费支出替代率,那么每月总支出将增加到约838.11 亿元,考虑补差后实际增加560.89 亿元,消费支出替代率提高到0.35 后全年实际增加的低保支出将约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8.09%。由此可见,提高低保标准后如果低保人数显著增加的话,那么财政支出将大幅度增加。
五、结论
通过对主要贫困线计算方法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消费支出比例法既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相对贫困定位,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定位,而是两者的折中。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考虑到要让贫困群体一定程度上分享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采用消费支出比例法来计算和衡量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水平的高低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结合现有研究文献,再测算36 个中
心城市和各省城市地区的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发现,中国低保标准水平仍然偏低。这表明,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低保标准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存在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表5 低保人数增加条件下提高消费支出替代率后的财政支出状况(2010年12月为基准)
低保标准水平提高后导致的担心之一是福利依赖问题。对低保标准的最低工资替代率和各地福利依赖情况进行分析表明,低保制度的福利依赖问题并非由于低保标准水平过高,而是附加在低保制度上的种种其他福利。由于低保制度连带福利是导致福利依赖的重要原因,因此逐步剥离捆绑在低保制度上的各种福利才是减少福利依赖的根本途径,而不是降低保标准。由于这种剥离有可能会带来大量的交易成本与寻租活动,因此在具体操作过程需要特别重视不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整合和衔接,尤其是要通过研究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的功能相互替代来实现制度整合。此外,还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和行政监督,尽可能减少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寻租行为。
低保标准提高后另一个担心是财政支出增加。在消费支出替代率提高后分别假定低保人数不变和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对低保财政支出增加情况进行测算发现:财政支出增加较大的都主要是人口众多且经济欠发达的省市,而支出增加较少的主要是经济最不发达和最发达且消费支出替代率较高的省市。由于中央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的比例要远远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因此由于提高消费支出替代率而带来的财政支出增加的负担将主要落在中央财政上。但是,未来提高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究竟会对财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容易估计。除了低保人数变动外,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低保财政支出状况。例如,低保补差。如果低保标准很高,但补差幅度很小的话,低保资金的增加幅度也会减小。
[1]唐钧.城市低保标准偏低了[J].中国社会保障,2011,(12):28.
[2]柳清瑞,翁钱威.城镇低保线:实际给付与理论标准的差距与对策[J].人口与经济,2011,(4):77-89.
[3]彭翔,徐爱军.基于消费视角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与评价——以江苏省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11,(10):65-70.
[4]刘黎明,梁志军.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收入分布函数测算方法[J].统计与决策,2008,(4):31-32.
[5]高清辉.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比较与评价[J].城市问题,2008,(6):96-100.
[6]吴碧英.中国36 个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4):36-39
[7]吴碧英.城镇贫困:成因、现状与救助[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116-117.
[8]王萍萍,方湖柳,李兴平.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2006,(12):62-68.
[9]马丁·瑞沃林.贫困的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7-57.
[10]姚建平.基于消费支出比例法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2,(1):78-85.
[11]姚建平.我国城市贫困线与政策目标定位的思考[J].社会科学,2009,(10):68-76.
[12]刘晨男.中国式“福利依赖”的制度设计探源——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案例研究[J].社会工作,2009,(6)下:38-41.
[13]杨立雄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方法及调整机制实证检验[R].北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财政部社会保障司研究项目报告,2010.31.
[14]DAPONTE B.Q.SANDERS S & Taylor L.Why do Low-Income Households Not Use Food Stamps?[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99,34(3):61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