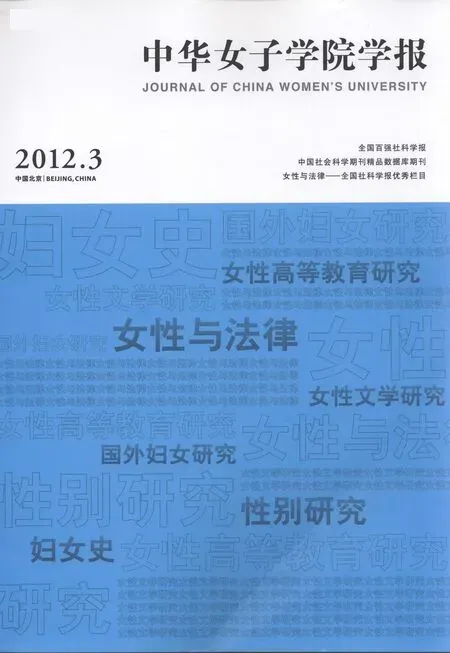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的宋庆龄与女权主义
苏卫平
20世纪上半叶的宋庆龄与女权主义
苏卫平
20世纪上半叶,宋庆龄的妇女思想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三民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逐渐在革命实践中放弃了女权主义,转而将妇女解放问题纳入民族革命的一部分。宋庆龄的革命历程是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的一个缩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女权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走向。在民族革命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近代中国,女权主义必然被介入民族主义,从而被边缘化,这同时也为妇女解放找到了可行的道路。
宋庆龄;女权主义;妇女解放;民族革命
宋庆龄是20世纪的伟大女性,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袖。争取妇女的自由与平等权利是她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她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13年发表《现代中国妇女》一文开始,宋庆龄始终对妇女问题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发表了许多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与言论,并曾亲身实践了妇女运动,为妇女解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试图从女权主义①本文提到的女权主义(Feminism)主要指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以争取男女平等、妇女所应有的政治社会权利为目标的观点。现在学术界倾向于将“Feminism”译为“女性主义”。从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来看,20世纪上半叶“Feminism”的核心是争取平等的社会权利,采用“女权主义”更符合当时的语用意义。参见朱晓敏:《由“Feminism”的中译引发的思考》,转引自章梅芳、刘兵《性别与科学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2页。另外,从宋庆龄自身的观点来看,也采用了“女权”的概念。的视角梳理20世纪上半叶宋庆龄关于妇女问题的思想之发展脉络,分析其与时代背景、思想潮流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探究宋庆龄为何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妇女运动的道路,进而评价近代中国妇女追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选择,同时对女权主义思潮在近代妇女运动中的状况与地位作一诠释。
一、留学时期的宋庆龄:准女权主义者
1913年4月,宋庆龄在《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校刊》上发表了《现代中国妇女》一文,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早的宋庆龄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该文章对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教育、平等普选权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结尾处描述了宋庆龄所期望的中国妇女运动:
在不久的将来,从这些妇女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出现潘克赫尔斯特和贝尔蒙特式的人物。但希望她们的口号是“争取女权不要像男子那样去打架”。既然人类一半人口的提高不可能不同时提高另一半人口,既然中国正在鼓励办好女子高等教育,我们深信,用不着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1]7
为什么妇女问题是学生时期的宋庆龄感兴趣和关注的重点?①在现存的文献中,学生时期宋庆龄发表的文章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辛亥革命、留学生与妇女问题,分别体现在其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与《现代中国妇女》中,均发表在《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校刊》。其中,《现代中国妇女》一文是宋庆龄临近毕业才发表的,相比于其他两篇,时间约晚一两年,其发表的见解应该认为是更为成熟的观点。这必须与当时英美等国的妇女运动相联系才能理解。首先,以宋庆龄提到的潘克赫尔斯特②潘克赫尔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今一般译为艾米琳·潘克斯特。为与《宋庆龄选集》一致,本文译为潘克赫尔斯特。和贝尔蒙特为切入点,来了解20世纪初期西方妇女运动之概况。
潘克赫尔斯特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妇女参政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英国女性争取民主权利的象征符号。在其生涯中最重要的就是在1905年创立了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该组织在成立的十年内,在潘克赫尔斯特的领导下,为了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激烈运动。从干扰政治家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到砸窗户、纵火、制造爆炸事件等,甚至采取绝食抗议行动,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将英国的女权运动推向一轮又一轮的高潮,几乎吸引了当时西方政治界所有人的眼光。在这一“战斗”中,有两点尤为值得关注:第一,这次运动的参加者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她们的方式从温和逐步过渡到激进,获得了大众的广泛同情;第二,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充分利用了宣传媒体工具,扩大了社会影响。尽管这次运动并没有直接导致妇女获得投票权,但是从社会影响来看,无疑潘克赫尔斯特是成功的。③关于潘克赫尔斯特的研究,参见王赳《激进的女权主义: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参政运动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书中对潘克赫尔斯特的一生及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对同盟采取的宣传方式等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贝尔蒙特则是美国著名的亿万富翁、社会名流,也是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因曾嫁给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④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1794—1877),美国企业家,主要从事航运和铁路业,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是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创建人。的孙子威廉·基萨姆·范德比尔特,而在离婚后获得了大量的财产,据说超过了一千万美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天文数字,正是这一财产成为她资助女权运动的重要资金来源。20世纪初期,贝尔蒙特将大量的精力与金钱投入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先后创立了政治平等联盟与全国妇女党,曾为确保通过宪法第19条修订案⑤《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1920)第1款: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缘故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第2款: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第19条修正案保证了所有美国妇女的投票权。而奋斗,为争取女性权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19年6月4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第19条修正案,并于1920年8月2日正式生效。美国妇女终于取得了选举权,取得了一项作为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⑥关于贝利蒙特的介绍,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Alva_Belmont.这可以称作是美国女权运动在20世纪初的最大胜利。
可以说,潘克赫尔斯特和贝尔蒙特是西方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的十数年间,正是女权运动日益走向高潮的时期。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席卷英国和美国的每一个角落,斗争的方式也一改以往的演讲、游说等传统手段,变得日趋多样化和激进化,如有组织地示威游行、诘难政治候选人等,甚至采取砸窗户、绝食、自杀等极端方式,规模和声势空前浩大。这些无疑吸引了宋庆龄。第一,宋庆龄出身于较为富裕的基督教家庭,一直接受西方教育,因此女权运动的主体——中产阶级能够得到宋庆龄的身份认同;第二,女权运动中的宣传攻势波及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关注政治社会问题的宋庆龄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可以说,正在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读书的宋庆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这一社会大环境。1913年4月,宋庆龄连续发表《现代中国妇女》和《阿妈》⑦《阿妈》发表于1913年《威斯理安院刊》上,文章主要描述了一位女性——宋家的保姆,可以说是宋庆龄关注女性问题的开始。两篇文章,文中对妇女问题密切关注,表明在这个时期她明显地受到西方女权运动与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一运动潮的波及下,宋庆龄真正开始了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宋庆龄认为,在将来的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出现是必然的趋势,女权主义是解决中国妇女问题的最佳选择。不过,宋庆龄并没有完全沉溺于女权主义。针对女权运动中出现的激进行为,她希望她们的口号是“争取女权不要像男子那样去打架”。
在宋庆龄看来,当时中国的妇女地位是比较高的,“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以及受尊重的程度,都毫无疑义地比过去提高了。”中国妇女不仅拥有了受教育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自由。“尤其是城市妇女,她们都和男人一样平等。”甚至认为,“平等普选权”成为现实也是不太遥远的梦想。宋庆龄认为,将来中国的妇女地位较之于同时代的英国,可能也要“引起英国姐妹的妒忌吧”。[1]5-7
身在美国的宋庆龄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社会,对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发生的“平等普选权”运动也有所了解。20世纪初,为了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中国女界中的先进分子——秋瑾、何香凝、唐群英、林宗素等人曾加入孙中山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组织妇女团体,如女子革命军、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等,成为近代女子参政的先声。至中华民国成立,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导,妇女参政者开始了争取“国民”权利的努力。然而,在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的临时约法中并没有男女平等的规定,因此引发了3月19日的请愿风潮及《民立报》的妇女参政论战。宋庆龄可能通过某种渠道得知了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并对妇女在这一运动中获得选举权抱有胜利的期盼。这一认识使得宋庆龄认为,中国妇女运动应该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而不要是“像男子那样去打架”。她理想地认为,当时热烈讨论的妇女选举权问题,将很快成为现实。
在女权主义运动中,除了选举权外,另外需要争取的是受教育权。这一点也深刻影响了留学美国期间的宋庆龄。她对于教育能够产生的效果抱有非常大的期望,这从其另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①指宋庆龄在1911年发表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一文,文中论述了留学生对国内政治、文化教育和社会改变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一名学生,相信教育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是合理的,但存有一定的幻想成分。而妇女地位提高的最关键方式是教育,“中国正在鼓励办好女子高等教育”将意味着“用不着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样,“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1]7
女权主义无疑是宋庆龄试图解决中国妇女问题的第一个切入点,宋庆龄认为当时的中国妇女问题与西方国家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她推测中国妇女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大同小异。正是在女权主义的影响下,宋庆龄开始关注自己的社会身份——女性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希望找到一个途径使得妇女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从这一点来看,女权主义给宋庆龄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象。可以肯定地说,学生时代的宋庆龄的政治观点还是不成熟的,随时会随环境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她对女权主义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表面的,但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女权主义是宋庆龄政治思想的萌芽之一。
二、孙中山的学生:“中立”的女权主义
宋庆龄在发表《现代中国妇女》一个月后,即1913年5月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这成为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其思想转变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婚后的宋庆龄进入了“当孙中山学生的时代”[2]140,宋庆龄这样形容自己:“结婚对我来说,好比迈进了一所没有‘考试’来麻烦我的学校。”[2]138在孙中山身边,宋庆龄学习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孙中山的女权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二是“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三是“惟女子须急求法政,学知识,了解平等自由之真理”,重视女子教育事业。[3]这表明,曾在英美等国长期生活的孙中山对女权运动也有着一定的了解。在其思想中,充分接受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参政、教育等问题上完全赞同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因此在这些方面,孙中山与宋庆龄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孙中山的政治道路来看,他的女权思想处于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交织之中。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一直无法建立理想的政权。因此在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中,妇女问题只是革命的附带任务,应该伴随着革命的胜利而解决。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正在学习革命思想的宋庆龄。
《现代中国妇女》发表11年后,1924年11月28日,宋庆龄在陪同孙中山北上的途中,在日本神户县立高等女子学校发表了关于妇女问题的演讲。从这篇演讲中可以看出,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宋庆龄的妇女观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第一,宋庆龄开始客观地述说西方女权运动。她说:“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1]22此话透露出她仍然认为西方女权运动是在追求正义,也等同于在追求更合理的平等权利与地位。如果说留学时期的宋庆龄是充满激情地称赞女权运动的话,而这时的宋庆龄已经抛去了感性,更多的是理性的认识。将西方女权运动归结为“正义的要求”,证明宋庆龄仍相信它是正确的、值得学习借鉴的。
但是这一“正义的要求”已不再是独树一帜,而是成为了“强大的世界运动”。宋庆龄对世界妇女运动的关注从欧美转向了更多的国家,“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斯的妇女也开始起来维护她们的权利。今天,在库尔特斯坦山区的广阔版图上,有一位妇女当了总统;在土耳其,妇女当上了教育部长。”[1]22这一点恰好反映了世界妇女运动的变化。英美等国的妇女运动在女性获得选举权后走入低潮,受此影响的亚非国家的妇女开始觉醒,努力争取妇女的权利,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之英美等国,亚非国家与中国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从而引起了宋庆龄的注意。
在这篇演讲中,宋庆龄还提到了妇女的性格,认为日本妇女有着“通情达理,质朴,忍耐性,以及对重大牺牲的承受力”等突出的性格,而“这些品质,使日本妇女足可担当亚洲妇女运动的领袖。”[1]22这与留美时期宋庆龄在《阿妈》一文中对理想妇女性格的描述有很多相似之处,并没有提到为争取权利所需要的“战斗”精神,也承袭了宋庆龄希望通过非“打架”的方式来获得与男性平等权利的思想。
第二,在宋庆龄看来,妇女应该争取的权利主要指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争取与妇女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等,这些公共事务更多地涉及妇女自身的利益。从争取政治权利、受教育权等,到反对歧视妇女,争取参与公共福利活动的权利,宋庆龄的妇女观已经不局限于当初的女权主义范畴,而是更重视影响妇女生存生活的条件与基础性权利。
宋庆龄称,“妇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换言之,妇女并不是非要参加政治活动的,不一定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这意味着宋庆龄不再将政治参与、公民权作为男女平等的标志,政治权力运动仍应该是男性的舞台。从这一时期的宋庆龄来看,妇女能够参与公共事务,关心与自身相关的事情及国家公共福利事业,似乎是妇女运动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现实的。
第三,妇女斗争的方向是“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1]23宋庆龄认为,东西方妇女共同的利益是“为正义而斗争”,这一“正义”指代的应该是反对歧视妇女与争取妇女权利。不鼓励妇女独立地争取权利,而是参与争取公共福利的事业(很大程度上与国民革命的目标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政策,这些都与当时孙中山的政治诉求基本吻合。这次演说是事先预约而非即兴的,因此可以猜想宋庆龄应该和孙中山曾经商讨过内容,如果说这是他们俩观点的契合也是恰当的。
第四,认为妇女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①有学者认为,这句话“从她对理性的强调,可以看出她当时的思想接近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参见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笔者认为此说法有不妥之处。[1]23这个观点源自早期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论述:“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这段话后被马克思在《神圣家庭》里引用。或许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开始阅读部分马克思的论著。
在时隔11年之后,宋庆龄再次发表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不论是主题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演讲内容来看,宋庆龄对女权主义保持着较为中立的态度。而对于妇女问题,则糅合了孙中山的政治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由于孙中山在1923年接受苏联的帮助后,其思想也逐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所以宋庆龄的思想基本上是孙中山政治观点的反映。
从这篇演讲中可以看出,宋庆龄已经开始逐步将妇女运动与“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普遍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过,二者在政治诉求上的差异,即使在宋庆龄看来也是明显的。尽管宋庆龄认识到妇女运动与民主运动之间可能存在的一致性,也希望将二者融为一体,但是她仍然没有找到消弭分歧的解决方法。
三、国民革命中的宋庆龄:“女权”与“妇女解放”
在神户演讲后不久,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孙中山的去世给宋庆龄带来巨大悲痛的同时,也促使宋庆龄走上政治舞台,捍卫孙中山的旗帜,投身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在1925年4月宋庆龄返回上海至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的两年多时间里,宋庆龄以孙夫人的身份参加各种政治社会事务,其中直接参与的主要是妇女工作。①东京朝日新闻社第一位女性记者竹中繁曾于1926年12月26日在革命总司令部与宋庆龄见面,她在日记中提到宋庆龄“奉孙文遗志领导革命妇女”。参见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从被任命为妇女部长(未曾到任),到号召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再到1927年1月创办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都显示出宋庆龄与妇女运动的紧密联系。从现存的文献看,这段时期宋庆龄较有影响的政治观点主要体现在《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论中国女权运动》等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中。
宋庆龄认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妇女参加革命运动,思想已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且“对改变之速已惊骇万分矣”。[1]41但较之英美等西方国家,中国妇女的现状是落后的,因为“我们的妇女同胞,受了国际上重重压迫之外,还要多受一层男女不平等的压迫”。[1]37其中,“国际上重重压迫”指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不平等条约以及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争取民族独立与妇女解放,妇女应该参加国民革命。②关于国民革命时期宋庆龄的妇女革命活动和妇女解放思想,学界多有论述,参见刘家泉《宋庆龄与大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人民日报》,1985年5月5日)、雷慧清《大革命时期宋庆龄与妇女解放运动》(《江苏文史研究》1997年第4期)。在盛永华《宋庆龄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宋庆龄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2—67页)、吴淑珍《论宋庆龄的妇女观》(《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等文章中也有所涉及。此处不复赘述。
1925—1927年,中国社会陷入国民革命的高潮中。作为孙中山遗志的继承者,宋庆龄的首要任务是支持国民革命,所以她的全部活动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在妇女领域也不例外。在其参与的妇女解放斗争中,必然将妇女解放纳入国民革命的范畴中,希望妇女参加革命并作出贡献,在革命胜利后得到法律承认的国民身份与各项权利,最终实现妇女的解放。
从当时的社会来看,国民革命冲垮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妇女问题在经历了20世纪初的数年争论后,不再是舆论与社会的焦点。尽管在20年代,妇女参与社会的活动日益增加,各种妇女组织不断建立,但是并没有单纯为争取妇女权益而努力,大都是为了社会的进步或国家利益而表现在妇女身份上的结果。在这一背景下,将国民革命与女权运动结合起来成为必然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于1925—1927年间多次使用了“女权”一词。③宋庆龄在《在广州女校女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载《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页)与《论中国女权运动》(载《宋庆龄选集》第41—42页)中都使用了“女权”一词;而“妇女解放”一词仅在《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载《宋庆龄选集》第39—40页)中提及。宋庆龄对妇女应享有的权利作了较明确的定义,即“公民资格、选举权、财产所有权、社会地位等”,并将这些划入了“革命中之根本事项”。[1]4142这一点,与其在神户演讲中的观点相左。甚至,宋庆龄成立政治训练班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现在之背景,国民党之主义,着手训练政治领袖”。[1]42最终推广一批拥有世界眼光、有解决政治问题能力的新妇女。这意味着鼓励妇女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宋庆龄回顾了英美的女权运动,认为“余在美留学四年,英美之妇女对选举问题及法律平等之奋斗,并不若何热中”。[1]41这等于说,当时英美国家的妇女进行的战斗在1927年的宋庆龄看来,已经算不上激进,并且参加的妇女比例似乎不高。国民革命下妇女的解放运动远远超过了西方女权运动的激进程度,宋庆龄期盼:“吾等祖母虽较美国妇女落后五百年,但吾等之女儿未始不可先进五十年。”[1]41
在国民革命思潮下的宋庆龄,将女权运动的目标定义在国民革命的范畴之内。宋庆龄同时使用“女权”与“妇女解放”两个词语,并没有区分二者间的差异,说明当时的国民党与中国社会同时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妇女运动阐释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宋庆龄把妇女需争取的权利与社会地位纳入了国民革命的奋斗方向,承诺只要妇女为革命作出贡献,在革命胜利后就能够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
四、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宋庆龄:否定女权主义
国民革命失败后,1927年9月初,宋庆龄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宋庆龄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对妇女问题的阐释明显趋向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妇女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国家里最受压迫的阶层。如果想“做一个自由的妇女”,那么必须来一场“根本的社会革命,而不只是政治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妇女“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革命工作,来帮助并配合男子们及其领导者们的创造性劳动”。在将来的中国,妇女的责任是“必须为明日的中国抚育优秀的工人和领导者”。①后面两句话,更大程度上体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国内关于妇女的主流言论。[1]64
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间,宋庆龄关于妇女的言论甚少。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再次广泛参与妇女活动,才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妇女解放的言论。[4]经过十数年后,宋庆龄的妇女思想日趋成熟。宋庆龄对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历史,特别是对民国的妇女运动了如指掌、如数家珍。②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载《宋庆龄选集》第348-362页)一文中,对这一历史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她还关注在抗日战争局势下全国各地妇女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说国民革命时期的宋庆龄将妇女权利定义在法律层面,将妇女解放限制在参加政治活动,将妇女斗争归结于国民革命的话,十年后的宋庆龄对妇女解放的认识则全面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以宋庆龄盛赞根据地的妇女运动与各地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妇女工作为例,根据地的妇女被组织起来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在生活的一切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从而“摆脱了过去的封建黑暗而得到一种崭新的地位”;[1]357工业合作社的妇女通过识字班、技术训练班和妇婴医疗所等,学习到了自治和共同生活的本领,合作社里的妇女“都已经成为本身有价值而对于国家的目前与未来也有价值的人了,再也不是‘女人而已’,而是受人尊敬的十足的公民了。”[1]359妇女通过参加社会劳动实现自身的解放,通过参加政治、社会活动提高自身的地位,都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内容。可见,宋庆龄已经熟悉了马克思主义中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式与内容,并能运用在实践中。
反过来,这时期中的宋庆龄已很少提及女权主义,仅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用“内容贫乏”一词来形容西方的女权主义。“内容贫乏”,宋庆龄似乎指的是女权主义致力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行为,而没有涉及更多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从这一带有贬义的词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宋庆龄不再满足争取政治权利,而是希望达到完全的自由与男女平等。
那么,为什么宋庆龄会抛弃女权主义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上半叶女权运动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隔阂有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以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遭到批判。斯大林实行的是“强化家庭”、批判“自由恋爱”及鼓励生育的政策。1936年,苏联通过了反堕胎法、反离婚法,并且使同性恋非法化。从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主义的思想和观点被视为越轨,被排除在主流政治文化之外。[5]21因此,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宋庆龄表现出对女权主义的反感也是很正常的。
当然,20世纪30年代的宋庆龄开始逐步信仰共产主义,在妇女解放道路上也找到了理想的道路,即通过国家独立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来实现妇女的解放。[1]478-498这意味着,宋庆龄已经成功地将妇女运动介入了民族革命之中。那么,放弃在20世纪上半叶半殖民地中国根本行不通的女权主义观念,是确定无疑的了。
五、结论:被边缘的女权主义
从1913年发表《现代中国妇女》到1949年12月发表《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近40年的时间里,宋庆龄从一个出身富裕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到坚持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夫人,最终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宋庆龄的妇女观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三民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转变。这一过程中,宋庆龄由一个准女权主义者逐渐在革命中放弃了女权主义,转而将妇女解放问题纳入民族革命中的一部分。
宋庆龄的这一转变,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缩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女性在面对民族革命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时,所作出的必然的历史抉择:在理论与实践中把女权主义介入民族主义,将女性置于民族革命中合适的位置。[6]1-6
然而,在民族主义范畴下的妇女运动实际上是将女权主义边缘化了。民族主义革命假设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主体,在高度同质性的种族群体基础上,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而女权主义则以天赋人权为依托,在个体基础上,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两者之间固有的内在张力,预示着仅以民族主义无法实现女性主义的目标,但如果将女权主义从民族主义话语中剥离,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因此能否找到中间道路成为女性主义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7]尽管二者的表述形同水火,但是在实践的复杂层面却能彼此介入、相互渗透。在整个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女性自觉地将女权运动向民族主义靠拢,强调女权与民族革命的政治诉求的一致性。“妇女实际处境不仅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加以理解,根本上就是民族/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6]4“女权主义”一词也因其含有“对抗并超越民族主义”的可能,在日趋激进的民族革命中被否定,直至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在民族主义命题中整合女权主义的政治诉求。
女权主义的缺失为中国未来的妇女运动留下了隐患,妇女解放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成为革命的附庸。尽管在革命胜利后,妇女得到了承诺的法律权利,但是依附男性群体的女性仍处于弱势地位。宋庆龄也感觉到了这一点,“除非男子完全理解,而且坚持男女平等,否则这一切都会落空。”[1]494
历史在轮回。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的妇女地位和发展状况均处于世界的前列。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妇女的发展却受到了阻力。1989年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发表了报告,将中国的妇女地位状况列于受调查的99个国家中的第51位。[8]59这足以说明,中国的男女平等进程再次落后于世界水平。百年之后,重新检阅女权主义的观念,回顾女性为自身权利而奋斗的历史,从中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
[1]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盛永华.宋庆龄年谱(1893—1981)[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3]刘振华.孙中山的女权思想[J].学海,2007,(6).
[4]尚明轩.宋庆龄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J].抗日战争研究, 1995,(4).
[5]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6]陈顺馨,戴锦华.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7]万琼华.在女性与国家之间——20世纪初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构与碰撞[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2).
[8]赵津芳,岳素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简明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张艳玲
Soong Ching-ling and Feminism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U Weiping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Soong Ching-ling’s thoughts on women underwent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from feminism to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then to Marxism.In the process,first as a quasi-feminist,Soong Ching-ling gradually abandoned feminism during her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while integrating women’s liberation into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Her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was an example of the history of women’s movements in modern China,largely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minism in this period.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feminism was inevitably bound up in nationalism and therefore marginalized.However,this also offered a feasible path for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in China.
Soong Ching-ling;feminism;women’s liberation;national revolution
10.3969/j.issn.1007-3698.2012.03.018
2012-03-04
D442
A
1007-3698(2012)03-0098-07
苏卫平,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宋庆龄陵园文博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人物思想研究。200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