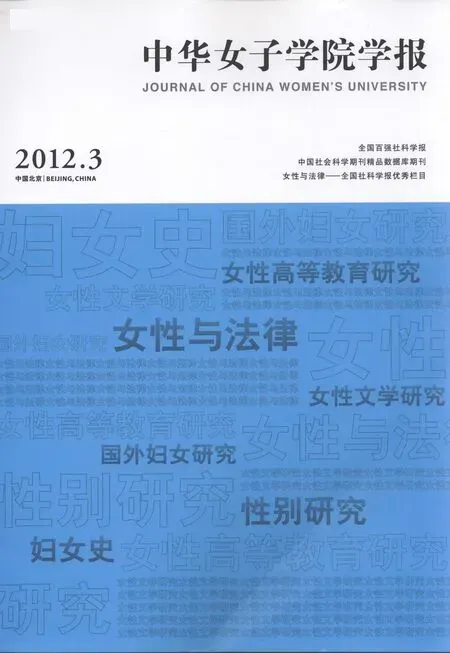二元家庭暴力证明标准初探
刘淑芬 李琼宇
家庭暴力离婚案件的激增使学者对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两性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1]8-13,继而引发了对家庭暴力内涵、社会干预、司法救济(尤其体现为民事保护令制度的构建)等问题的全面探讨。①当前家事法学界关于家庭暴力问题探讨的范围与基本观点,参见陈苇、李欣《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综述》(《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19页文,及陈明侠《家庭暴力防治法基础性建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与学界的热情相反,司法实践中对家庭暴力认定的数字并不乐观,其间充斥着因举证不能而得不到救济的受害人和逍遥法外的施暴者;由此,很有必要探讨家庭暴力的证明标准问题。现笔者结合自己于2011年10月13日在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调查的结果②指笔者于2010年10月13日针对2010年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家庭暴力离婚诉讼案件进行的调查,检索案号自(2010)南民初字第0001号至(2010)南民初字第3545号,其中离婚诉讼案件262件,涉家庭暴力案件45件。,对家庭暴力证明标准问题作一探讨。
一、传统家庭暴力证明标准及其弊端
(一)现状及问题的提出
除了性虐待、冷暴力等是否属于家庭暴力尚存在概念上的争议外③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界定问题,参见张曙、李熠《论家庭暴力的内涵——对现行婚姻法中家庭暴力概念的质疑》(《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107页至109页文。,传统的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无法得到法院认定的原因只能是证据问题。笔者一直坚持认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是“举证难”而是“证明难”。在我国,家庭暴力难以得到认定的根本原因是法院采取了对受害人过于严苛的证明标准,即侵权责任的证明标准。
该标准认为:家庭暴力也是一种侵权行为④关于家庭暴力行为是否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问题,参见秦志远《论家庭暴力侵权》(《家事法研究》2009年卷,陈苇主编,则其成立必须同时具备构成侵权责任的四个要件,即“行为的违法性、损害后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如果受害人无法证明四要件其中任何一个,都将承担家庭暴力不被认定的法律后果。
采纳侵权责任的证明标准来认定家庭暴力的做法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婚姻家庭法是民法的特别法①受苏俄民法的影响,我国婚姻法一直游离于民法之外,但向民法回归一直是婚姻法学发展的总体趋势;然而,向民法学回归,并不意味着将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财产制度完全照搬到具有特定身份的家庭成员之间,其归根到底是民法的特别法。,其主要调整对象为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财产关系附随于身份关系而存在。正如夫妻财产关系不能简单地通过物权制度来解释一样,家庭暴力也不能与侵权行为完全等同。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1)家庭暴力的主体之间具有特定的身份关系,这种身份关系使施暴人与受害人之间互负同居、扶养乃至忠实的义务,而侵权责任则是建立在陌生人的基础之上;(2)相对于普通侵权的受害人来说,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基于传统观念、子女利益或其他因素更不愿意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②这里的权利指请求赔偿的权利。按照前述调查结果,涉家暴的45例离婚诉讼案件中,原告主动撤诉的有17例,占总数的37.78%,居第一位,而大多数撤诉案件的撤诉理由都与子女利益有关。(3)依据我国的现行法律,除了在离婚诉讼中家庭暴力受害人无法向施暴人要求侵权损害赔偿;(4)从目的上讲,对侵权责任的认定是为了补偿受害人使其恢复到侵权前的状态,而家庭暴力进行认定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离婚,这一点尤为重要。
(二)采纳侵权责任证明标准的危害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用侵权责任的证明标准来认定家庭暴力不过是债法对婚姻家庭领域的一种牵强附会,其至少会产生下述危害:
首先,严苛的证明标准使家庭暴力被认定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其体现在:(1)基于家庭暴力的私密性特征,使得受害人收集直接证据困难重重,甚至根本不存在任何直接证据;理由在于任何人都不会选择在卧室里安装摄像机,而丈夫也往往不会选择在公开场合殴打妻子。③实践中,即使丈夫在公开场合殴打妻子,妻子取证也并不容易。(2)根据笔者前一阶段调查的结果,在离婚诉讼中大多数家庭暴力受害人都能够向法院提供受伤照片或门诊病历以证明损害结果的发生④按照前述的调查结果,在涉家暴的45例离婚诉讼案件中,受害人向法院提交证明家庭暴力存在证据的案件共有13例,其中11例的受害人提交了受伤照片或病历资料。,而对于施暴行为本身及其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得不到有效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法官对遍体鳞伤的受害人充满同情,其也无权认定家暴成立的事实。(3)在一些暴力轻微但长期施暴的案件中,由于损害后果尚且具有不确定性,这对受害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4)受害人在证据采集过程中也往往遇到困境。在前述调查中,有施暴人将受害人拍摄的照片撕毁的情况,而最为常见的情形则是受害人从司法鉴定机关取得的证据往往不敷应用。
其次,家庭暴力不被认定无疑会使受害人遭受到“二次伤害”。由于传统“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家庭暴力受害人诉诸法院请求司法救济时往往已经走入绝境,再无其他办法可想;法院依据严苛的证明标准对家庭暴力予以否认,对于受害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使其心理上再受创伤,甚至可能使其走上极端,激化社会矛盾。
第三,严格的家庭暴力证明标准为家暴受害人解除婚姻设置了重重障碍,其不符合现代婚姻法无过错离婚制度⑤关于无过错离婚制度的经典表述,参见哈里·D·格劳斯、大卫·D·梅耶著,陈苇译《美国家庭法精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发展趋势,试图挽回一个充斥暴力的婚姻绝对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二、立法改革中矫枉过正的倾向
基于传统采用侵权责任证明标准认定家庭暴力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家庭暴力认定难问题已经为多数学者所诟病[2],家庭暴力立法改革似已势在必行,反家暴专门立法进程的推动也给这种改革提供了客观条件。降低家庭暴力的证明标准与减轻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几乎已经是学界的共识[2],特别是反家暴网络2009年提出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学者建议稿》中提出了“举证责任分担”的提法[3]106,更有学者直接提出举证责任倒置的观点。上述改革无疑是善意的,但是却透露给我们一个危险的信号:在用心良苦的“受害人”面前,所谓的“施暴人”可能蒙受不白之冤,甚至为了其莫须有的“过错”承担高额的离婚损害赔偿责任。[4]80
无论是前述举证责任倒置,还是举证责任分担,都具有某种意义的共同点,其体现在:由“受害人”先提出一定的证据证明其受损害的事实(当然有直接证据证明因果关系更好)及近期发生过家庭纠纷,举证到一定程度后,由“施暴人”对其没有实施过暴力行为进行举证;如果“施暴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没有施暴,法院将对家庭暴力予以认定。
很明显,与侵权责任的证明标准一样,这种立法改革的趋势也具有表面上的合理性,为受害人提供了充分的救济,给了她们逃离婚姻樊笼的钥匙。但是笔者却认为认定家庭暴力过于宽松的证明标准是对传统证明标准的矫枉过正,并为之感到深深不安,其至少会导致下述问题的产生:(1)过于宽松的证明标准将会使因家庭暴力而离婚变得过于容易(其他证明感情破裂的事由则相对难以证明),以致给急于摆脱婚姻的当事人一个作伪证的动机,而我国又没有设置离婚等待期制度,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离婚的激增与泛滥,离婚的泛滥绝非无过错离婚制度设置的初衷;(2)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施暴人将因其家庭暴力行为而支付离婚损害赔偿。①这里笔者无意于对离婚损害与离因损害作出区分。参见马忆南《离婚救济制度的评价与选择》(《中外法学》2005年第2也就是说,一旦家庭暴力得到认定,其不仅是作为证明感情破裂的事由那么简单,其也成为受害人向施暴人索赔的依据。过于宽松的家暴证明标准会对所谓的“施暴人”造成明显的不公,因为让一个人证明其没有做过的事(又是在家庭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本来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5]54
三、利益衡平的结果:二元家暴证明标准
无论对于“施暴人”还是“受害人”来说,家庭暴力发生与否,可能本就是一件根本无法证明的事,故而让谁来承担举证责任,实际上谁就等于领到了一份败诉的判决书。而与环境侵权(其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等特殊侵权行为不同,家庭暴力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法院对认定家庭暴力采取何种证明标准,实际上是在作一个利益平衡的考量,即法院既不能让受害人因无法证明家暴而受困于失败的婚姻,也不能让所谓的“施暴人”蒙受不白之冤,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出衡平。
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家庭暴力的司法认定(民事认定)问题,应采取二元证明标准。其主要内容与基本理由为:
第一,对于作为离婚理由的家庭暴力和作为提出离婚损害赔偿依据的家庭暴力的认定应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作上述区分的主要理由在于认定家庭暴力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使受害人摆脱暴力婚姻的牢笼,而后者的受害人则希望通过类似侵权责任的方式获得经济赔偿。
第二,对于作为离婚理由的家庭暴力认定问题应采用相对宽松的证明标准(第一元证明标准),即前文提到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由“受害人”负担较轻的证明责任,而由“施暴人”负担较重的证明责任。例如,如果妻子基于家庭暴力向法院起诉与丈夫离婚,按照二元家暴证明标准,则由妻子证明其受损害的事实和并陈述发生家庭纠纷的时间、地点和原因,再由丈夫对其没有实施家庭暴力进行举证。
采取相对宽松的证明标准明显使利益天平偏向受害人,其基本理由在于:(1)给受害人一个摆脱暴力婚姻的机会(依据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是否实施家庭暴力是认定夫妻感情破裂与否的标准之一),严苛的证明标准将使大多数家庭暴力受害人深陷暴力婚姻无法自拔;(2)避免受害人遭受“二次伤害”,同时降低受害人提起离婚诉讼的心理负担;(3)其符合无过错离婚制度的基本原理;无过错离婚制度要求没有过错不能作为离婚案件被告的抗辩事由,故而对于作为离婚理由的家庭暴力认定采用相对宽松的证明标准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第三,对于作为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理由的家庭暴力认定应采用相对严格的证明标准(第二元证明标准)。这里的相对严格的证明标准与侵权责任的证明标准不能等同,是在“受害人”与“施暴人”之间对于证明责任作一个均衡的分割。相对于作为离婚理由的家暴证明标准(第一元证明标准)来说,将适当增加受害人的证明责任,降低施暴人的证明责任。
采取相对严格的证明标准的理由在于:(1)“受害人”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获得经济利益(以弥补其损害),其类似于一种侵权责任;如果给“施暴人”苛以过重的证明责任,很可能使其蒙受不白之冤,遭受经济损失;对于“受害人”来说也可能引发道德风险;(2)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可能的“施暴人”给予适当的保护,但是由于性别差异的现实,即女性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成为受害者[6],而不宜直接采用侵权责任的证明标准,以避免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形同虚设。
四、应该注意的相关问题
笔者认为,相对于传统严苛证明标准与立法改革中提出的相对宽松的证明标准来说,二元家暴证明标准更能实现“受害人”与“施暴人”利益的平衡,但是采用二元家暴证明标准至少应注意下述问题:首先,采用二元家暴证明标准并不必然导致法院在判决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中同案不同判。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只能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故而很容易出现受害人既基于家暴提出离婚诉求,又同时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况;那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如果法院依据相对宽松的家暴证明标准认定家庭暴力,并据此判决离婚,而在离婚损害赔偿中又采用严格的家暴证明标准,是否会在同一份判决中出现认定家庭暴力又否认家庭暴力的情况。笔者认为上述担心虽有道理,但正如前文所述家庭暴力很可能是难以证明甚至是无法证明的,故而对认定家庭暴力不能采取“一刀切”的证明标准,前述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判决书中文字或技术处理的方式解决。
例如:在前述调研中获取的“顾某诉汪某离婚纠纷案”①案件来源于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0)南民初字第2427号案件。中,妻子顾某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诉称,其多次遭到丈夫汪某殴打与辱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请求判决离婚,并主张2万元的离婚损害赔偿,同时向法庭提交门诊病历一份、受伤照片六张、居委会证明一份。丈夫汪某在庭审中对妻子顾某提出的事实予以否认,称双方为家庭琐事偶有争执,但并不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形。南明区法院最终依据现行侵权责任的证明标准,认为妻子顾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家庭暴力存在,判决不准离婚。
本案如果援用二元家暴证明标准来认定家庭暴力,则会得出支持离婚诉请,驳回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结论。法院可在判决理由部分表述如下:原告所提出的证据虽并不能使本院确悉被告殴打、辱骂原告事实的存在,但其提出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被告存在实施家庭暴力之可能;经本院调解,原告仍坚持解除婚姻诉请的前提下,本院亦不能坐视原告人身权益继续处于可能被侵犯的危险环境之中,故原告要求与被告离婚之诉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由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家庭暴力事实确实存在,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以在离婚判决生效后一年内另行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之诉。
其次,即使采用二元家暴证明标准也需要法院对家庭暴力进行积极主动的调查,并通过民事保护令等多种形式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可以说,采用二元家暴证明标准是在家庭暴力案件证据收集困难前提下的无奈之举,其与法院对家庭暴力的积极认定之间并无矛盾。
[1]夏吟兰,郝佳.家庭暴力法律防治理念刍议——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社会正义观[J].妇女研究论丛,2010,(3).
[2]陈苇,李欣.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综述[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1).
[3]陈明侠,等.家庭暴力防治法基础性建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陈苇.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探讨[J].法商研究,2002,(2).
[5]林晶,郭丽红.论家庭暴力法律事实的诉讼证明[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6]陈苇.我国农村家庭暴力调查研究——以对农村妇女的家庭暴力为主要分析对象[J].法商研究,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