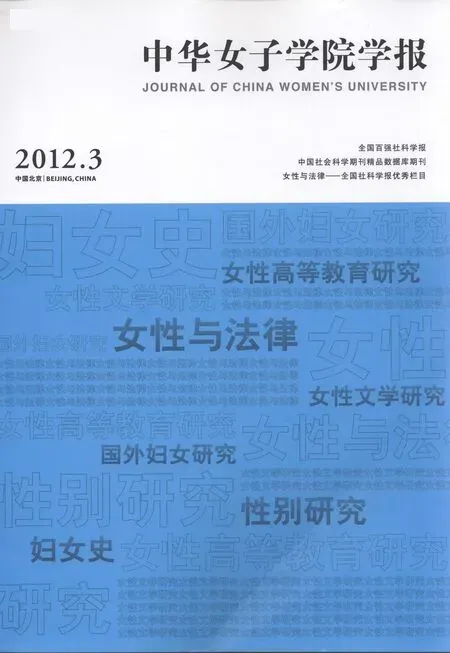中国妇女发展的社会政策演进
周爱萍 孔海娥
中国妇女发展的社会政策演进
周爱萍 孔海娥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妇女发展的社会政策,取得了诸多成绩,为促进妇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六十多年来妇女解放和发展的经验表明,只有将社会性别视角运用于各项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才能真正推进性别平等。
妇女发展;社会政策;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主流化
一、社会政策与社会性别
一般认为,最早提出社会政策概念的人是19世纪德国社会政策学会的骨干成员之一瓦格纳(Adolph Wagner)。他在1891年发表的论文中把社会政策定义为:“运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以争取公平为目的,清除分配过程中的各种弊害的国家政策。”[1]165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社会政策是为了应对各类社会问题,以争取最终的公平、公正为目的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其具体内容也随着社会问题的出现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一开始,人们对于社会政策具体内容的理解不全面,范围比较狭窄和单一,大都只限于狭义上的“社会福利”(资源分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社会福利同社会权利密不可分,因而社会政策还有必要包括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内容,亦即“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2]有学者认为,凡是同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息息相关的政策都应纳入社会政策的关注视野,这样,社会政策的具体内容就相当丰富,如社会救助、救灾、社会保险、医疗卫生服务、就业、妇女儿童保护、性别平等、种族(民族)平等、老年人权益、房屋住宅、劳资关系、劳动者工作保护条件、人口政策、婚姻家庭保护、残疾人福利保障、孤儿扶养、退伍军人优抚与安置、职业训练、义务教育政策,等等。[3]社会政策的主要领域分为社会保障政策、公共医疗卫生政策、公共住房政策、公共教育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社会福利服务政策、针对专门人群的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政策的其他内容。本文所指的社会政策是指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涉及妇女权益或权利的各项政策。[4]16-18
社会政策和社会性别虽然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但二者也有共同之处:它们都以追求社会的平等、公正为已任,都强调每个个体或者每个男性和女性都有分享社会成员各项权利的机会,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为社会政策的性别主流化提供了可能性,成为社会性别视角运用于各项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基础。
社会性别(Gender)是与自然性别(Sex)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基于两性自然性别差异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包括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社会性别概念的核心在于,它认为历史和现实中两性的境遇差别不是由于生理差别导致的,而是由于社会形成的,是社会通过制度化力量将两性差别合法化、并代际复制的产物。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理论,旨在探讨两性社会差别形成的内在机制及重塑两性关系的制度革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视角,是将人还原为有性别的人,进而发掘制度对两性产生的不同影响。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于1997年就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定义达成共识,即社会性别主流化是评估任何领域和层面——包括立法、政策或项目计划在内的任何一项行动——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社会性别主流化将妇女和男人的关注与经验作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中设计、执行、监测、评估政策和项目计划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来加以考虑,从而使男女两性平等受益,其最终目的是达到社会性别平等,从而推动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社会性别以基本人权框架为基础,重视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和社会性别机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人们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注重通过改革制度、法律、政策消除社会性别歧视,把赋权妇女作为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中心,强调妇女共同参与和受益。将社会性别分析应用于发展,可以揭示出男女的社会性别角色和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分析出哪些政策和项目真正使男女在改变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上受益,哪些项目虽然是针对妇女的需要,但是非但没有促进妇女发展,反而强化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加剧了男女间的不平等关系。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性别视角在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但在社会政策、福利国家的研究中,对性别的关注则是在70年代以后,之前对福利国家的研究大多忽略了性别关系这一变量。随着性别关系话题的不断升温,90年代后,性别关系与福利国家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一方面,社会政策的定义和发展受到了性别关系及其话语的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家所实施的社会政策同样也在形塑着新的性别关系。二者之间的彼此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若干有利于女性的社会政策的出台。本文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至1995年,以及1995年世妇会之后三个阶段来回顾我国有关妇女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进行反思。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妇女政策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生活极为悲惨。政治上,妇女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无法参政议政;经济上,妇女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生活上,妇女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必须遵循“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近代以来,许多开明人士开始倡导妇女解放,试图改变中国妇女的状况和地位,但由于没能将女性解放运动同整个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因而并不能影响和改变妇女整体的境况。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随着各项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国女性的状况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郑重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和实施,使妇女在婚姻家庭领域获得了解放。婚姻法确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从根本上解除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有力地荡涤了长期积淀在社会心理深处的“男尊女卑”意识。妇女不仅获得了择偶、离婚、再婚等方面的自主权,而且在人格上受到充分的尊重,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1947年的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5]1261-1262经过土地改革之后的农村妇女,“同男人一样分得了法定的一块土地,在家庭拥有的土地财产中,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一份子,这从根本上为妇女力争在家庭中成为平等的一员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资料,为其实现自身的进一步解放奠定了经济基础。”[6]219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明确规定:男女劳动要同工同酬。1951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事部发布《关于废除招考工作人员及学员时“不收孕妇”规定的通知》,规定不准“不收孕妇”,对此类违反国家保护妇女权利的规定以及存在助长歧视妇女封建思想可能性的规定予以废除,保障了已婚妇女的工作权利。1953年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凡年满十八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明文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1955年公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也对男女同工同酬作出规定,这一政策在农村成为维护妇女劳动报酬的重要依据,在城市成为女工获取合理报酬免受歧视的坚强保障。
由此可见,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一样,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社会政策的关注对象从一开始便超出了狭义的社会福利范围,包括了妇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无疑是中国妇女社会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回顾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政府及大众对于社会政策的核心即“公平、公正”的理解不是以个人的自由、平等为基本出发点的,而是基于一种十分朴素的平等观,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和一致性,着力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平均性。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关于妇女解放制定的政策或开展的工作,基本上延续了革命时期对妇女的动员精神,有相当多的妇女确实在集体劳动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成就感,但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当时的人们往往无视两性固有的生理差异,凡事要求男女并驾齐驱,比如在“文革”时期提出的“男人能办到的,女人也能办得到”之类的倡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被扭曲的女性解放目标的最真实写照。这种忽视生理差异、无视历史所形成的社会差异而寻求形式上男女平等的后果,只能造成本质上的男女不平等。另外,在这一时期国家虽然提出了同工同酬的机制以保证男女的平等,“但是机会的平等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比如由于妇女受教育状况普遍不及男性,因此从事的工作大多简单乏味,获得提升的机会远较男性为少”。[7]这些最初未能解决的问题似乎延续至今。
三、改革开放以来至1995年中国妇女权利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妇女立法有了很大的进展。1980年修订的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按照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决”。婚姻法还具体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之间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1985年的继承法全面地保障了我国公民的财产权利,规定男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80年代中期还出台了《女职工健康保护暂行规定》(1986)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义务教育法(1986)规定,所有适龄儿童,无论性别、民族或种族,必须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民法通则(1986)规定,妇女享有和男子同等的民事权利。199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以及财产、结婚、离婚和家庭生活方面,享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利,它重申男女平等,并主张保护法律赋予妇女的特殊权益。
与50年代立法更多地注重妇女的社会性解放、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不同,这些法规、条例的意图和效果是对妇女有利的,但其对女性生理、生育特点的强调本身是以女性有着先天的生理上的不利条件及能力缺陷这一观念为指导的,从而掩盖了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和观念。[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原来的“男女都一样”逐渐关注两性不同的生理差异,更多地强调妇女生理、生育的特点和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然而妇女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她们有着不同的复杂的身份认同,有权利和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社会应该不断满足这种需求。男女不是二元对立和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建构的。[8]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妇女问题”大量出现。首先是婚姻家庭问题,继而是妇女回家、女干部落选、女大学生就业难、打工妹权益被侵犯、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女工下岗、对妇女的暴力、一些农村妇女丧失土地使用权等问题相继出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比较充分保障的妇女地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部分妇女的权益在市场机制、资源短缺和男性中心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受到或多或少的剥夺和侵害。市场经济不可能是绝对公平的,不会自然实现社会公正,男女平等的实现有赖于国家的介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给了中国妇女发展一个新的契机。
四、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后关于中国妇女的社会政策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切实维护妇女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及各项权益。”中国的妇女运动迎来了一次新的高潮,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大众媒体都更加关注社会性别平等问题,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促进和保护妇女权益。1995年8月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我国政府第一部关于妇女发展的专门规划。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妇女发展的总目标是:妇女的整体素质有明显提高,在全面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使法律赋予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进一步得到落实。同时,纲要在政治权利和参与决策、就业和劳动保护、教育与职业培训、卫生保健、计划生育、法律保护、改善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扶持贫困地区妇女事业发展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政策和措施。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通过《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这是中国出台的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鉴于贫困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别差异,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向贫困妇女倾斜的社会政策。例如,《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将消除妇女贫困作为国家扶贫战略的重要内容。2001年建立性别敏感的扶贫指标,推动了扶贫工作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此外,为扶持妇女自主创业,政府制定和实施了扶持妇女自主创业政策,并在职业培训补贴、小额信贷、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优惠。
到20世纪末,纲要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权利得到进一步实现。为实践新千年国际社会提出的妇女儿童行动计划,促进妇女儿童的持续发展,根据我国妇女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确定了六个优先发展领域,即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并把促进妇女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纲要的制定和实施,目的是强化政府的有关职能,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妇女的进步与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鼓励妇女在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争取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为了更好地贯彻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促进妇女发展,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规定实行公平就业,反对性别歧视,它的实施为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提供了具体保障。
五、性别平等政策回顾与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社会中性别矛盾突出的问题,我国加快了对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将男女平等确立为基本国策;制定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将妇女发展纳入国家行动规划;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和谐提供了法律保障;制定了构建先进性别文化的政策,为促进妇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社会政策和女性生活密切相关,而性别差异是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进而也成为社会政策需要面对的问题。妇女作为个体要求与男性在各方面的完全平等和作为一个处于相对脆弱状态的群体希望得到特殊保护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忽视这一事实,假设男女人口是同质的,并有相同的需求,就无法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一项社会政策的制定不仅要同社会现实相适应,还要与目标群体的基本需求相吻合,才能实现制度预期的社会功能。在对妇女相关政策的制定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妇女与其他领域、其他阶层剥离开来,单独制定一个妇女政策,而在现实中我们的政策却无法直接或仅仅面对女性群体,必须将妇女群体还原到不同的领域、阶层和地域,通过相关的政府领域来实施这些政策。这就需要各个领域在制定自己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时,将妇女发展纳入其中,并通过该领域具体地予以执行和落实。
社会性别主流化,即是对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以发现差距、促进现实中性别平等的全部过程。如何使社会性别分析进入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制定与实施的主流,是摆在研究者、决策者及政策执行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有研究者指出:“如果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中嵌入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会有与以往不同的社会政策出台,就会产生带有性别平等的社会效果,特别是弥补妇女利益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社会政策缺失,将会促进性别平等的进程。”[9]因此,政府、学界及非政府组织应该加强合作,共同促进社会性别分析成为社会政策理论的一个视角和实践的主流。
【参考文献】
[1]曾繁正.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
[2]王卓祺,雅伦·获加.西方社会政策概念转变及对中国福利制度发展的启示[J].社会学研究,1998,(5).
[3]吴忠民.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J].社会学研究,2004,(1).
[4]关信平.社会政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孔海娥.国家土地政策变迁过程中农村妇女的个体经验[A].朱炳祥,等.土地制度与土地文化——武汉市黄陂区油岗村的田野调查[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7]张宇莲.新中国性别平等政策与妇女地位[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6,(2).
[8]杜芳琴.妇女研究的历史语境:父权制、现代性与性别关系[J].浙江学刊,2001,(1).
[9]李红.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政策探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2).
责任编辑:董力婕
The Social Policy Evolution of Chinese Women’s Development
ZHOU Aiping,KONG Hai’e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leased a series of social policies on women’s development and many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which have provided a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development.This essay reviews the related policies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s promulgated during the sixty years after the set-up of New China,and discusses the related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status associated with women’s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social gender perspective.This essay indicates that only if social gender elements are included in the dec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can real social gender mainstreaming be realized.
women’s development;social policy;social gender;social gender mainstreaming
10.3969/j.issn.1007-3698.2012.03.012
2012-03-12
C913.68
A
1007-3698(2012)03-0067-05
周爱萍,女,纳西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农村发展;650031孔海娥,女,江汉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43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