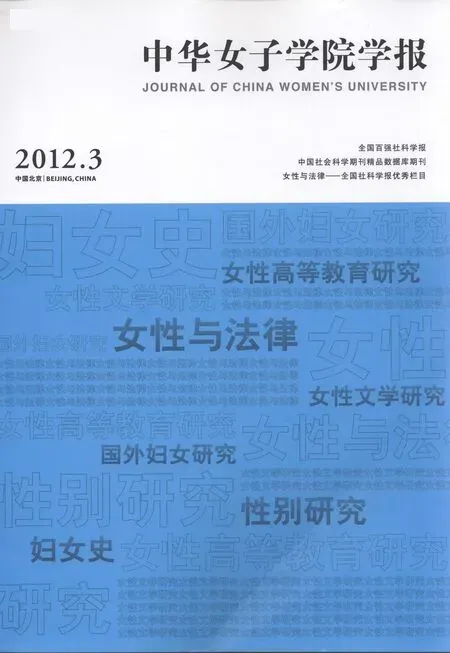托马斯·怀亚特宫廷诗的女性意识与性别书写
王 进 陈卓雯
托马斯·怀亚特是英国亨利八世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英国文艺复兴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宫廷诗人。与他同时代的御用诗人托马斯·莫尔,重视的是对君主王权的各种政治寓言,着迷的是对公民社会的乌托邦想象;作为宗教诗人的提尼代尔(Tyndale)倾心的是对宗教神权的各种文字符咒,痴迷的是精神世界的宗教神谕;怀亚特作为英王亨利八世的宫廷诗人,更加关注宫廷生活的各种权力意识和男性政治,呈现文艺复兴主体在君权和神权之间的性别空间。一般认为,文艺复兴不仅是新人文主义崛起的思想启蒙时代,而且是男性意识崛起的性别重塑时期。欧美古典文学界通常盛赞文艺复兴文学的性别观念,首当其冲的必然是怀亚特诗歌的男性书写。从桂冠诗人萨里(Surrey)对怀亚特“男子汉形态”的赞美,到浪漫主义诗人邓恩对其“男人腔调”的模仿,再到各种现代英国诗集对其“爱情当中男性独立观念”的欣赏,怀亚特宫廷诗已经被塑造成文艺复兴时期男性气概的英国典范。然而,怀亚特的宫廷诗歌明显区分出早期的忏悔赞美诗和晚期的揶揄讽喻诗这两种形式,其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男性视角和性别意识:前者的内敛特征体现出宗教改革和君主王权对男性主题的权力语境,后者的揶揄态度反映出历史主体的女性视角对性别意象的政治隐喻。本文借助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在赞美诗和讽喻诗两个不同层面上解读怀亚特宫廷诗的女性意识和性别政治,回到文艺复兴的历史语境当中重新评价和探讨怀亚特本人的女性意识和性别书写。
一、赞美诗:男性主体的自我塑型
作为英王亨利八世的宫廷诗人,怀亚特创作的早期诗歌大部分是宫廷赞美诗和宗教忏悔诗。欧美评论家关注的“忏悔赞美诗”指的是,怀亚特在16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创作的赞美诗第六首、第三十二首、第三十八首、第五十一首、第一百零二首、第一百三十首以及第一百四十三首。这些早期的赞美诗反映的都是当时的宗教问题和宫廷生活,H·A·梅森在《人文主义与诗歌》当中甚至强调,它们是“对亨利八世王朝的社会学研究”。然而,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恰逢英王亨利八世脱离天主教自立英国国教,他的宗教和政治婚姻受到前所未有的朝野批评,位高权重的托马斯·莫尔因为拒绝支持英王的宗教改革而在1535年9月被处决。怀亚特与莫尔所持的政见大致相同,但是与后者截然不同的是,他的诗歌创作却始终集中在宫廷婚姻和男性塑造的历史主题,他的具体做法就是翻译意大利诗歌、创造韵律诗新诗体,以及选用历代宫廷题材。宗教改革的意识形态,君主王权的宫廷政治,造就了怀亚特诗歌在政治主题上的内敛特征,然而却更加渲染出它在性别主题上的启蒙风格。
正如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强调,“伟大艺术都是某种异常灵敏的记录,它承载的是既定文化当中各种复杂斗争和和谐关系”。[1]5如果说莫尔的政论诗直接呈现的是对亨利八世王朝的现实针砭和对乌托邦公民社会的未来想象,那么怀亚特的宫廷诗围绕的则是英王大卫和情妇巴斯瑟巴(Bathsheba)之间的宫廷生活和性别政治,间接影射的却是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和政治婚姻。在这种以古讽今的寓言结构当中,怀亚特考察的是政治婚姻的权力关系和宫廷政治的焦虑情节,质疑的是君主王权和性别欲望的相互运作,提倡的却是忏悔意识和赎罪观念的宗教关怀。正是这种不良的性别欲望驱动着英王大卫滥用君主王权,驱除情妇的合法丈夫尤利恩以及维持自己的情欲关系。然而,在“这种罪行的暴政之下”,他本人作为“绅士表率”却良心未泯、寝食难安。在赞美诗第三十九首当中,大卫提到自己的内心焦虑,“夜晚的快乐不再拥有,我以泪洗面;消惰我未泯灭的眼睛,让内心为这样的堕落翻腾”;同时,他更加坚定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内心充满着更多的火热效果/因为现在与上帝同在,而不是与巴斯瑟巴”。这种“火热效果”从情妇到上帝的彻底转移,或者说是权力和欲望的道德转向,正是怀亚特倡导忏悔赞美诗的真正目的。对于他来说,上帝不仅是仁慈的道德说教家,也是严厉的末日审判者。面对亨利八世的宫廷政治,怀亚特对“上帝之城”的宗教理想由此彰显。[2]27
怀亚特诗歌专注描述宫廷生活的性别政治,始终伴随着的是自我忏悔和现世赎罪的宗教理想;与此同时,它同样注重男女形象和性别意象的意识形态,完全充满着男性气概和男性书写的文化臆想。对怀亚特来说,在英王大卫、情妇巴斯瑟巴和其丈夫尤利恩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性别、婚姻、道德和宗教的复杂网络。尤利恩是彻底无能的受害者的男性形象,他因为妻子与英王的不良关系而受到后者的迫害,但是他最终可以作为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去坦然面对自己的厄运。大卫虽然是罪恶行径的直接实施者,因为与情妇的暧昧关系而承受后者的堕落,但是他最终可以作为光明磊落的男子汉去勇敢忏悔自己的罪孽。与顶天立地的丈夫和光明磊落的情夫相比,巴斯瑟巴承担的则是充满邪恶和不可饶恕的情妇形象,她既不能寻得来自丈夫和情夫任何一方的相互理解,也不可能获得来自上帝恩赐的忏悔和赎罪机会。换句话说,英王大卫和尤利恩在怀亚特宫廷诗歌当中都是作为无辜或者有缺陷的自我意识,他们代表正面、积极和主动的男性主体,巴斯瑟巴却只能作为诱惑或邪恶的对立形象,她承担的恰恰是反面、懒惰和反动的女性客体。正如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强调所谓“表演”的性别概念,“它显示了我们以为是自身的某种‘内在’的特质,其实是我们期待并通过某些身体行为生产的;推到极致来说,它是一种自然化的行为举止的幻觉效果”。[3]9无论是通过忏悔赎罪的男性形象,还是借助邪恶无度的女性意象,怀亚特宫廷诗实质上塑造的是“绅士”君主和“道德”王权的宗教理想,产生的是男性气概的幻觉效果,最终服膺的则是二元结构的性别话语。
二、讽喻诗:男性书写的女性意识
正如文艺复兴学者库威指出的,怀亚特的宫廷诗总是充满诸如“笨拙、柔弱、天真、被动、边缘的男性欲望”,他作为崇尚绅士君主和宗教道德的宫廷诗人,“在他的诗歌平台上建构超越时空的硬汉形象,沉溺自己编织的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各种梦想”。[4]2如果说,怀亚特的早期赞美诗呈现出性别主题受到王权和神权制约的内敛特征,那么他的后期讽喻诗则更多的是显露出性别差异受到父权和神权压制的揶揄风格。桂冠诗人萨里曾经认为,怀亚特的早期赞美诗为英国君主们致力树立各种端正言行的“正容之镜”,那么对于当代读者来说,诗人后期的讽喻诗则为作为模范男性的他们提供出另外一种理解她者的“反思之镜”。对此,托马斯·沃顿强调怀亚特的讽喻诗是“精神性的男性反思”,它们具有“独立哲学家的真实愤怒,贺拉斯式的自由和愉悦”,充满着“个体情感的力量”,以及“自我言说的自由气氛”。[5]44称呼怀亚特是“哲学诗人”似乎言过其辞:他的宫廷诗歌不太纠结生死沉思的宗教哲学,也不太关注统治苍生的政治哲学,它更多重视的是自我塑型的性别视角。因此,如果说怀亚特的赞美诗屈服于神权和王权这两种父权形式,专注男性气概的自我塑型,呈现出营造“上帝之城”和塑造“绅士君主”的男性独白;那么他的讽喻诗强烈质疑两性差异和性别政治的二元模式,重视女性意识的塑型过程,反映出反思男性权力和重塑自我主体的她者意识。
对怀亚特后期的讽喻诗来说,《我母亲的女佣》《沉默寡言的夫人》和《湿润你的眼睛》这三首诗最具有女性意识的她者视角,男性欲望和言说权力之间的矛盾关系成为焦点话题。与他早期提倡忏悔的赞美诗相比,讽喻诗不再维系权力压制欲望的内敛特征,更多的是彰显出欲望调侃权力的反思风格。如果说赞美诗通过权力关系的压制机制呈现出的是所谓男性气概的自我塑型,那么讽喻诗则通过言说主体的反思方式体现出女性意识的书写视角:前者祈求上帝“告诉我如何靠近你,我将会与你一样”,后者坦言“我的言行不会像圣人,我也不会委屈我的舌头去假装”;前者恪守对上帝的信念以求得对自我的宽恕,后者质疑以宗教信仰和自我慰藉为幌子的权力话语;前者充满对自己的忏悔赎罪和对绅士君主的期待情感,后者揶揄宗教神权和君主王权的虚伪本质;前者提倡放弃自我意识和塑造绅士品质的宗教理想,后者主张自我想象和自我满足的主体欲望。正如马卓塔指出的,“欲望是一种纯粹的隐私,是堕落状态产生的某种缺失”,在这种欲望和话语的错位当中,“诗人不断失败但不断尝试获取欲望的一种形式对等,因为这种从未停止通向总体性的欲望,超越任何形式上的对等”。[6]60与早期赞美诗极力提倡男性气概的自我塑型有所不同,后期讽喻诗更多关注女性意识的书写视角。作为言说主体的男性欲望不再沉溺于自说自话式的性别独白,而是将这种错位的欲望关系投射到以往被忽视或消声的女性主体,呈现出同情女性她者和反思男性自我的塑型意识。
《我母亲的女佣》关注到的是底层妇女的社会命运或者说是生存权利,“她只能睡在寒冷,而又潮湿的困境;更惨的是,要吃剩余饭菜/在做完活之后,为犒劳自己,偶然些许古物,偶尔些许豆类/为此她要没日没夜的劳作”。与她形成巨大反差的则是男性主体的各种虚妄谬想,“男人们总是寻求最好,却只能得到差的,是因为他们迷失方向”。《沉默寡言的夫人》思考的是贵族女性的选择困境或者说是言说权力,“你有同情或者仁慈,直接回答他,是或否/如果是,我也高兴;如果否,我们同样是朋友/你将会遵循另一个男人,而我也会拥有我的,而你的却不再”。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夫人只有聆听而没有言说的权力,对于她丰富的内心情感却只有“是”和“否”这两种非常简单的断然抉择。《湿润你的眼睛》探讨的则是女性群体的性别特征或者说是思维差异,“尽管你发誓它不是/我同样可以发誓和言说;我向上帝和十字架起誓/如果我可以模仿,你将会面对损失”。与男性气概崇尚上帝的单一思维相比,女性群体的思维方式更多地显示出复杂多变和意义延宕的隐喻风格。或许正如巴特勒所指出的:“男性主体表面上不证自明的独立自主性,试图掩盖作为它的基础、同时又让它永远有失去基础之虞的压抑。然而,这个意义建构的过程需要女人去反映那男人权力,并处处对这个权力一再保证它那虚构的独立自主性是真实的”。[3]69怀亚特讽喻诗似乎意识到男性权力的脆弱本质,通过言说主体的反思视角和移情意识,试图为女性客体代言立命。然而,在没有赋予女性言说权力之前,任何的同情言辞和代言行为最终只能是造作的煽情表演和徒劳的性别臆想。
三、宫廷诗:性别观念的历史写照
C·S·利维斯在其著作《16世纪的英国文学》当中曾经贬低怀亚特宫廷诗及其性别取向,批评诗人谈及两性关系的时候总是同情心泛滥,完全抛弃自己的男性身份。他甚至宣称:“任何女人找到怀亚特这样的爱人都是非常不合适,我知道这样反应不太公平;它使用那些本不应该被使用的诗歌”。[7]23然而,从赞美诗和讽喻诗这两种不同文体类型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和性别观念来看,怀亚特宫廷诗书写的实际上是男性欲望的自我独白和女性意识的她者旁白。正如齐泽克强调,“男性欲望通过‘虚构’秩序呈现出的是象征秩序的谜团(Paradox):在我们戴着的面具当中,在我们玩耍的游戏当中,在我们服从和遵循的‘虚构’当中,要比面具下面掩藏着更多的真相”,对于男性权力的自我书写来说,“欲望核心的外在呈现是通向他保持其恒定距离的这种表演游戏”。[8]152怀亚特的宫廷诗歌尤为擅长这种以男性欲望为权力意识的表演游戏,以及以文体差异为性别视角的张力关系。在早期赞美诗当中,怀亚特盛赞男性思维的单一性,排斥女性视角的多维度:作为异类她者的女性群体缺乏主体意识且无法信任,既然无法避免与女性她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作为绅士和君主的男性主体更加需要向上帝忏悔,按照宗教神权的道德标准自我塑型;在后期的讽喻诗当中,他却批判男性思维的单一性,同情女性意识的多样性:作为权力主体的男性群体无法换位思考且缺乏同情,既然无法回避与女性他者之间的性别差异,作为绅士和君主的男性主体更加需要她者意识和情感投射。如果说赞美诗直接反映出亨利八世的宫廷政治和男性权力,讽喻诗则突出表现女性意识的她者视角和性别观念,那么怀亚特宫廷诗的这种文体差异则更多呈现性别欲望的塑型意识和男性权力的表演过程。
作为文化符号的性别差异,始终是作为在男性欲望和言说权力之间的想象空间和表演平台。对新历史主义来说,“每个文本都是作为16世纪文化聚合力量线的聚焦点”,“它不仅呈现在其作者的职业生涯,而且是作为组成自我塑型的单一和复杂过程的大型社会世界,通过这样的阐释,更接近的理解文学和社会的多种身份如何在此文化当中得以成型”。[1]6怀亚特宫廷诗并不是感怀天下和直抒胸臆的思想产物,反而直接是受制于文学生产的社会过程和美学规则,更多的是呈现出诗人自身在宗教神权、君主王权和自我意识之间的协商过程和塑型结果。然而,当代女性主义者极力批判这种男性视角的言说权力和提倡女性自我的身体书写,强调“这个身体自我在性别化的想象秩序规则里,也许符合了一个能够有所欲望的身体的要求,这个想象的欲望情境总是超越它所由以运作、或它作用于其上的物质的身体”。[3]95当代性别研究视角的分析介入,或许有利于更加合理地理解怀亚特宫廷诗横亘在赞美诗和讽喻诗之间的矛盾关系,更加公允地评价怀亚特游戏在性别欲望和她者意识之间的文学立场。如果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是世俗人性的解放时代,也是男性意识的启蒙时代。在性别观念和文化传统的这个时代转型期间,怀亚特宫廷诗对男性气概的自我塑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历史贡献,与此同时,在女性意识的她者视角当中也呈现出难能可贵的性别关怀。
[1]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5.
[2]Jonathan Crewe.Trials of Authorship[M].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0.
[3]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4]Catherine Bates.Masculinity,Gender and Identity in English Renaissance Lyric[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5]Patricia Thomson.Wyatt:The Critical Heritage[M].London:Routledge,1995.
[6]Giuseppe Mazzotta.The Worlds of Petrarch[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7]C.S.Lewis.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Excluding Drama[M].Oxford:Clarendon,1954.
[8]Slavoj Zizek.The Zizek Reader[M].Elizabeth Wright,(trans).Oxford:Blackwell,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