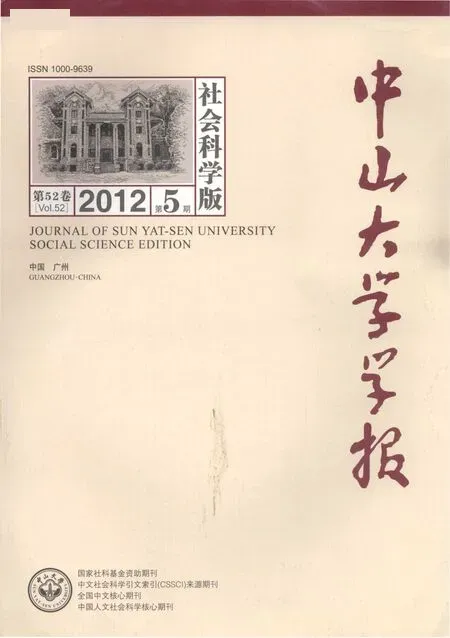《诗品》疑难问题二证*——兼说《诗品》考证的原则和方法
梁临川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下品序的“子卿‘双凫’”和“谢客‘山泉’”是否出自钟嵘手笔;第二,钟嵘所见陆机拟古诗是十四首还是十二首。两个似乎都不是大问题,但都是未有定论的疑案,可见问题虽不大,难度并不小,而研讨中的轻率和失当又可能加大研讨难度。因此,探讨问题,固然是为解决问题,其意义又常常不止于问题解决本身。研究文献,细读文本是必要的,恰当地选择视角也是必要的。根据我们的认识,《诗品》原是有评有选之书,并非单纯的诗评①参拙作:《钟嵘〈诗品〉原貌考索》,《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诗品》原貌的揭示,就新建了研究视角,重构了话语基础,对《诗品》疑难的解释有钥匙作用。由新视角看“子卿”、“谢客”,便涣然冰释。
一、关于“子卿‘双凫’”和“谢客‘山泉’”
下品序: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
这是评赞文字。虽是韵文,但文意平浅,理解不难,费解的是“子卿‘双凫’”和“谢客‘山泉’”。
先说“子卿‘双凫’”。是“子卿”还是“少卿”,问题看似简单,实际并非如此。如果说“子卿”“于文理难通,且与《诗品》原意乖悖”②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60页。,那么,《诗品》的“文理”何在?“原意”又是什么?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文理”和“原意”就是研究者反复指陈的一个事实:《诗品》未列苏武,由此,不可能是“子卿”。但排除了“子卿”,是否一定就是《诗品》列品的“少卿”呢?未必。要是没有庾信《哀江南赋》“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作旁证,单由《诗品》未列苏武这一点,是不能否定“子卿”而肯定“少卿”的,今本《诗品》也不存有“二卿”去取的“文理”依据。如力之先生所指出,《诗品》正文品列的作家,有序中不曾提及的,如阮籍;有正文没有列品的,序里却提到了,如桓温、庾亮①力之:《关于〈诗品序〉与〈诗品〉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兼辨“子卿双凫”与“谢客山泉”无误》,《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评赞作为序言的一部分,并不一定要遵守一个《诗品》之外的一定之规,即正文没有说的,序里便不能讲。因此,以《诗品》今存文本为话语基础来讨论并确认“二卿”的此非彼是,是困难的。
本文认为,要是转换视角,从《诗品》是诗选的认知出发来审视“二卿”,会有明确而合理的解释。根据我们的研究,《诗品》是诗选,《诗品》的品等和评论,都是以入选诗篇为基础和依据的②参拙作:《钟嵘〈诗品〉原貌考索》第5节,《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列品和评论都以诗选为依据,评赞所举也一定出自《诗品》之选,是选中之选③评赞标举警策之作的用意,应是提拔中品诗人之作,构成对三品截然分等的补充,否则无法解释二十二条警策诗例,中品诗人的竟占一半;也无法解释高列上品第一条的古诗,钟嵘给予歌颂性评价,而评赞中只字未提。评赞大篇幅列举中品诗作,很可能暗示钟嵘深感批评的难度,也显示中序所说“三品升降,差非定制”,确然出于真诚。。既是选中之选,自然不会把不在选的苏武诗列入“警策”名榜。而由于《诗品》录有李陵诗④本文不介入苏李诗真伪的讨论,同时认为,钟嵘、萧统诸人的肯定性意见当有其依据。,所以在排除“子卿”的同时,“少卿”就成为必然而合理的惟一选择。否定“子卿”而肯定“少卿”的理由,不在于《诗品》是否榜列苏、李之名,而在于《诗品》是否载录苏、李之诗。从诗选的视角看问题,就有圆满的解释,而无需任何旁证。
这又引出一个问题:《诗品》是分品载诗的,既然赞语举列是选中之选,就应该全是上品之作,为什么会有中品诗作呢?这不难理解。正因为是诗选,所以其重点是作品,不是作家,是以作品为中心而不是以作者为中心;列品是以列选诗篇的总体面貌为依据的,品等反映的是诗家入选之作的总体成就,而事实和逻辑都不排除中、下品作家也有“警策”,甚至可称“独绝”之作。也如力之先生所说,中序标举“直寻”之句,有出自上品诗人(曹植、谢灵运);也有出自中、下品诗人(张华、徐幹)的⑤力之:《关于〈诗品序〉与〈诗品〉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兼辨“子卿双凫”与“谢客山泉”无误》,《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也就是说,评赞标举“五言警策”而及中品诗作,也有其“文理”条例,并不违背《诗品》的自身逻辑。
再说“谢客‘山泉’”。与“子卿‘双凫’”类似,“谢客‘山泉’”主要也是作者问题;区别在于,苏武之名不曾在《诗品》正文出现,而评赞前文称举名篇,已有“灵运《邺中》”之语。研究者认为,赞语里只能一人一题;“灵运”在前,“谢客”必误。由此,或以“谢客”当为“谢脁”(车柱环),或以为当是“谢庄”(立命馆大学《诗品》研究班)、谢瞻(清水凯夫)。问题是:改易文本而没有文本依据,也没有其他方面的充足理由,这就难以找到合适的答案。本文认为,可以回过头来审视一下问题本身——问题本身的合理性。问题起因是认为赞语称举,一人不应有两次。其实这是囿于今本《诗品》内容的见解。如果改换语境,在总集的立场上看问题,就很好解释:钟嵘手笔如此,“谢客‘山泉’”不误。《诗品》的主干文本是诗,评赞则是诗中选诗;其所标立,明言是五言诗之警策,是“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因是选诗,不是举人,所以并无人名不可重复之理。诗主之名虽有重复,诗篇之名没有重复。这样,问题就解决了。问题的解决得益于视角的转换——总集的视角,这是关键所在⑥“谢客‘山泉’”,力之先生也认为不误,笔者赞同,但论证路径有异,录此以就教于力之。。
至于“山泉”的校订,比较简单,但由于疏忽,纠错时出了差错。“谢客‘山泉’”,《竹庄诗话》、《诗人玉屑》引作“谢客‘山水’”。路百占先生不以“谢客”为误,是;但以“山泉”当为“山水”,误⑦路氏校语转引自《诗品集注》。。评赞是韵文,“泉”与上文“仙”、下文“边”押韵,改作“水”,则失韵。车柱环先生说:“‘泉’与‘宴’、‘边’为韵,则《诗品》本不作‘山水’,明矣。”⑧[韩]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首尔:首尔大学文理学院出版部,1967年,第53页。车先生的意见是对的,但举例有误。“泉”与上下文“仙”、“边”相押,“宴”字不与焉。“宴”是去声字①此据《广韵》,南朝时当亦是去声。,不与平声字通押,且不在韵脚,无需押韵②《诗品集注》及增订本校“平叔衣单”,谓“鸾”、“单”、“乱”、“泉”、“宴”押韵(漏上文“仙”、下文“边”字),亦未能辨“乱”、“宴”之声调及是否在韵脚,且中间跳过不同韵部的“安仁倦暑”至“士衡《拟古》”一节,亦误。。
二、陆机拟古诗:“十四首”,不是“十二首”
《诗品》卷上《古诗》:
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
《规范》对车站细水雾灭火系统的相关条文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部分条文对于地铁车站的特点仍存在一些适用性争议,而原细水雾灭火系统在地铁车站中的成熟应用方案是基于地方规范或行业标准,是否仍可沿用尚需验证及讨论。本文主要描述了细水雾灭火系统在地铁中的一种成熟应用方案,以及《规范》实施后相关的条文所带来的主要影响,在必须执行《规范》的前提下,结合原设计方案,提出一种新的细水雾灭火系统的应对方案,以供参考。
“十四首”,曹旭《诗品集注》、《诗品笺注》据《竹庄诗话》和《诗人玉屑》所引改为“十二首”;此外,《文选》及今传《陆机集》所载拟古诗的篇数(十二首)也是注者改“十四”为“十二”的依据③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5页;曹旭笺注:《诗品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按,集注增订本虽已改回“十四首”,但在大篇幅申述“十二首”主张的同时,并未具体陈述回改的理由,这一疑难项目的是非问题仍未解决,仍有探讨之必要。。
按,有研究者认为,陆机所拟本为十四首,理由有二。第一,钟嵘与萧统为同时代人,钟嵘既见有十四首,萧统便不得谓二首已佚失。第二,《文选》所存十二首之外,唐人所编《艺文类聚》卷41复有《驾言出北阙行》一首,题下注有“驱车上东门”五字,而《拟驱车上东门》恰为今存陆机拟作所无者,且《驾言出北阙行》之辞意均同于古诗《驱车上东门》,故《驾言出北阙行》必为十四首拟作之一。吴汝纶《古诗钞》卷1《古诗十九首》题解④吴汝纶:《古诗钞》,民国十七年(1928)刻本。、许文雨《诗品讲疏》⑤许文雨:《诗品讲疏》,成都:成都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第31—32页。、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⑥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9—140页。证之已详。
复按,据上述三家论证,陆机拟作虽还因差一篇而不能全部确考(许文雨认为《遨游出西城》是《回车驾言迈》的拟诗,本文暂不论列),但不止十二首则可成定论。既然与萧统同时的钟嵘已明言“十四首”,此十四首文字就必是钟嵘亲见;另外,现在并没有材料证明“十四首”是《诗品》的传写错误,所以应该认定陆机拟作是十四首。《文选》到底选了多少陆机拟作,不得而知;在没有可靠材料支持异见的情况下,自应以十二首为是。但即使《文选》原来就选了十二首,也应视为选家弃选二首,而不应倒过来以《文选》所录定陆机拟作之数,进而改动《诗品》评语。如邬国平先生所说:“《文选》对于多篇诗歌组成的一组作品,全录的例子很少,绝大多数是选录,这与其书名曰‘选’正相符合。比如紧随陆机《拟古诗》十二首之后,是张载《拟四愁诗》一首,张衡原作《四愁诗》一组四篇,张载拟诗也是四篇,《文选》却只选了第四首。可见不能将《文选》选入的作品视作陆机《拟古诗》原来有多少首的铁证。”⑦邬国平:《略谈陆机拟古诗》,黄霖主编:《云间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页。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另一部总集《玉台新咏》里,张衡《四愁诗》和张载《拟四愁诗》,还有傅玄的四首拟作,都是完收全录。不过这正说明,总集的作品采录全凭选家的旨趣和眼力,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而随意偶然的过程和结果,自不能视为铁律或铁证。不要说《文选》还是选本类总集,即使是以保存文献为宗旨的全集性总集,也要看它的资料来源是否充沛和完整。至于今传陆机的本集所载也是十二首,那很可能是陆集初编本散佚的缘故。据《隋书·经籍志》,梁时陆集有四十七卷,《录》一卷⑧魏徵等:《隋书》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63页上。又陆云曾编陆机诗文为二十卷(见陆云《与兄平原书》,陆云撰,黄葵点校:《陆云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7页),恐未得流传。又此本编于陆机生前,非全集,亦不知此编与梁本关系如何,兹姑不论。梁本当是全集初编本。,到唐初还存十四卷。十四卷本是四十七卷本散佚后的重编本。重编本的拟古诗采自《文选》,今传陆集拟古诗的篇数和排序都与《文选》相同,原因就在于此①《郡斋读书志·〈陆机集〉》标注:“(陆机)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今存诗、赋、论、议、笺、表、碑、诔一百七十余首。以《晋书》、《文选》校正外,余多舛误。”又《谢脁集》标注:“《文选》所录脁诗仅(近)二十首,集中多不载,今附入。”(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16、821页)以《文选》为六朝文章辑佚和文字校正的取资,很可能是唐宋时普遍的做法。。钟嵘看到的当是四十七卷本,此本所载陆机作品远远多于宋人所见,所以钟嵘说“十四首”应该是有根据的。
还有一条材料值得注意:《诗品》的《吟窗杂录》本也作“十四首”。今存吟窗、考索二本分属两个传本系统,但都从宋本而来,皆存宋本之旧。因有宋本渊源,所以二本的可靠性都不弱于《竹庄》和《玉屑》,在版本价值和文本可信度上还高于《竹庄》、《玉屑》。第一,从成书年代看,《吟窗杂录》成书早于《竹庄》、《玉屑》(确切地说,是五十卷本《吟窗》成书早于《竹庄》、《玉屑》;据张伯伟先生的研究,是五十卷本《吟窗》才收录《诗品》的,此前的本子未收②张伯伟:《论〈吟窗杂录〉》,《中国诗学研究》,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44页。)。《吟窗》成书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竹庄》成书在宁宗开禧二年(1206),《玉屑》成书在理宗淳祐四年(1244)③《吟窗杂录·序》末署:“绍熙五祀重阳后一日浩然子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6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146页;郭绍虞先生据方回《桐江集》,定《竹庄》成书在开禧二年,见郭绍虞:《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9页;《玉屑》黄昇序末署:“淳祐(四年)甲辰长至日,玉林黄昇叔旸序。”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当然,《山堂考索》成书在《吟窗杂录》之后,但因为考索本《诗品》也作“十四首”,与吟窗本相同,所以《山堂考索》的成书早晚并不重要;第二,从文本的载体形态来看,二本都是《诗品》本集(吟窗本虽是删节本,但本集的轮廓还在),在内容完整性上都胜过诗话。因此,“十四”还是“十二”?《诗品》本集的可靠性和证明力大于宋诗话,何况还有唐人类书所辑十二首之外的佐证。
在“十四”与“十二”问题上,陆集、《文选》不必信,《竹庄》、《玉屑》更不可信。先看《竹庄》卷3所录《诗品》文字后的自注和引注:
……王微风月,谢客山水,叔元离燕诸诗,《文选》并阙。
(阮籍)咏物诗,《文选》阙。
《文选》注云:“阮籍属文,初不苦思,率尔便成……非大作者不能探测之。”④何汶撰,常振国、绛云校点:《竹庄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9,50,13,45页。
《文选》注云:“《游仙》之制,文多自叙,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⑤何汶撰,常振国、绛云校点:《竹庄
可以看出,《竹庄》的《诗品》引录与《文选》校读相伴,而从前两条引文来看,《竹庄》用《文选》与《诗品》对勘时,并未考虑《文选》的选本文献性质。此种情况下,校《诗品》而以《竹庄》为据,难免以讹传讹。
再看《竹庄》对《诗品》古诗评语的安置。《竹庄》卷2至卷4选录汉代至南齐诗人诗作,其名题之下,多附列《诗品》文字。就在这里,《竹庄》对古诗评语的处理令人生怪。第一,《竹庄》引录的《诗品》文字多为正文评语,惟独古诗评语例外。“古诗十九首”题下不是《诗品》正文的评语,而是序文的“古诗眇邈”一段话⑥何汶 撰,常 振国、绛 云校点:《竹 庄诗话》 ,北京:中华 书局,1984年,第39,50,13,45页。;第二,不是像安排其他评语那样,把古诗评语单独立条,而是附在“陆士衡拟古诗十二首”题下的评语之后⑦何汶撰,常振国、绛云校点:《竹庄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9,50,13,45页。,全然不顾古诗评论在《诗品》中单独立条,且是上品第一条的显眼位置。这个位置移换和篇幅合并表明,《竹庄》作者以《文选》的陆机拟诗篇数为陆机拟诗的总数,并据此而视《诗品》的“十四”为误文。此外,《竹庄》收录的陆机拟诗十二首,诗题、诗文和篇章排列全同《文选》,可见《竹庄》所录来自《文选》,也可见《竹庄》是在既无《诗品》版本依据,又未注意《文选》文献性质的情况下,以“现存”篇数为据来“修正”《诗品》,把“十四”改为“十二”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合适且充足的理由。
《竹庄》收载的陆机拟诗和引录的《诗品》文字来历如此,那么还能不能用《竹庄》定“十四”与“十二”之是非,结论自然是否定的。
与《竹庄》一样,《玉屑》的“古诗十九首”题下也不是《诗品》正文评语,也是序文的“古人(诗)眇邈”一段话①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上册,第272,278页。。还有,古诗评语也不是单独立条,也还是附在“陆士衡”题下的陆机评语之后②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上册,第272,278页。。这就说明,与《竹庄》一样,《玉屑》也是以《文选》所收陆机拟诗来确认拟诗总数,从而把《诗品》的“十四”改为“十二”的③这里暂不考虑后人“改合”的可能。车柱环先生说:“又《诗人玉屑》引‘十四首’作‘十二首’,与今传陆机所拟古诗之数合,疑《诗人玉屑》本不如此,盖后人改合。《山堂考索》至《诗薮》所记此文皆作‘十四首’,可证《诗品》原本不作‘十二首’。”[韩]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第30页。。
很明显,《诗人玉屑》的《诗品》引文,也不是确认陆机拟诗总数的依据,也不能用作校改《诗品》本集的依据。
这里需要说明,不应一概否认《文选》和宋诗话对六朝文籍校勘的意义,但是对二者的使用应更加审慎。还需说明,《竹庄》、《玉屑》的引文与一般诗话的引文不一样。二书对《诗品》和诗歌文字是格式体例化的、有规模的完整抄录,不是仅凭记忆的单文只句引录(尤其是《竹庄》,本来就是诗选和诗话的结合体)。二书引文的校勘价值远高于一般诗话,《诗品集注》对二书的引用有合理性,但有尽信书的倾向。
三、关于《诗品》考证的原则和方法
讨论《诗品》考证的原则和方法,有必要先读《诗品集注》增订本的一段文字。增订本在中品序“嵘今所录,止乎五言”一语的注文后加按语: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因“沈约条”有“剪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语,以为《诗品》除评论外,另有诗选。此论为日本中沢希男《诗品考》所反驳。笔者曾与日本《诗品》研究家高松亨明先生信函往返,高松亨明谓青木正儿氏非专治《诗品》者,不过论中国文学偶涉之耳。其所著《诗品详解》亦谓“剪除淫杂,收其精要”为“如剪除沈约淫滥芜杂之作,仅观其精要之诗,可居中品之第”。日本由二十多名研究家(包括兴膳宏先生)发起《诗品》研究会,后由高木正一执笔完成《钟嵘诗品》,其释“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谓“批评前人,确定以五言诗为评论对象”,说法与高松亨明相同。惟兴膳宏《异域之眼》谓《诗品》“评论之外,可能还列有诗人五言诗作品”,当为揣测之词。近梁临川力证《诗品》除评论外,另有诗选;继承前说,发覆旧案,开拓思路,精神可嘉。然兴膳宏所著《诗品》(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监修《中国文明选》之十三)“沈约条”即未言及钟嵘另有诗集;释“嵘今所录,止乎五言”亦谓“本书所论述对象,仅限定为五言诗”。笔者曾在京都大学与兴膳宏先生探讨此问题,先生亦谓其《异域之眼》为随笔集,不过“感想”而已,以目前资料,不能证钟嵘另有诗选也。④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第246—247页。
这里所引是按语全文。篇幅虽长,但内容集中,观点明确,即认为钟嵘没有编过诗选。不过,观点的表述与一般论证路数颇有不同,兹略作分析。
第一,关于青木正儿。青木的观点是否正确,这可以商量,但以中泽希男曾有驳议和青木不专治《诗品》为由,否定或轻视青木观点,则颇为不妥。中泽是有过驳难,但驳难能否成立,还是问题。中泽说整部《诗品》里找不到钟嵘编诗选的证据,但事实上青木举证都出自《诗品》。只能说中泽对书里的材料视而不见,不能说书里没有证据;以有问题的驳难否定驳难对象,这样的否定本身就有问题。此外,青木虽非专治《诗品》,但这完全不妨碍其《诗品》见解的独到和正确。只有专攻一书,其观点才可能正确——天下古今固无此等道理。
第二,关于高松亨明和《诗品》研究班。《诗品详解》和《钟嵘诗品》代表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深度,也反映了国外学者的认识水平,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但是,任何研究者的观点,都不应不加论证就用作认识基础和论证前提。关于钟嵘是否编有诗选,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应以《诗品》内外的文本为依据,不应以研究者的结论为依据,不应以现有结论的引述代替对原始材料的阐述。面对相反论点,单单对第三方论点的引述,既不构成证明,也不构成反驳。而恰恰在这里,增定本按语走了与事实说明和逻辑论证相反的路线。按语反复陈述的,是学者们如何不认可青木的见解,即都是以他人的认识为认识基础,以他人观点为论证前提和判断依据,也就是说,按语都是以引证代替论证。
文献考订,就其说明过程来说,无外乎证明与反驳二端。无论是证明还是反驳,原则和方法都是以可靠材料为依据,在材料基础上引出结论。
就反驳而言,最关键的是对对方证据进行分析,评估证据的指向和效力。首先是直面证据,而不是回避它。只有在正视和分析对方证据的前提下,对观点的攻驳才可能是正当和有效的。当然,如果所攻驳的观点没有或无须证据支持,自然另当别论。
关于证明,其实大家都知道,证明过程是论证过程。所谓论证,一是用材料证明观点,二是论证者自己观点的叙述,不是他人话语的转述,就是说,不可以引证代替论证。顺带谈一下左思和任昉评语的异文问题,这也与《诗品》考证有关。先说任昉。
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考索本《梁太常任昉诗》)“博物”,《诗品集注》据吟窗本改为“博学”(增订本同),并引《南史·任昉传》为证:“博学,于书无所不见。”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语词改易是否必要。改为“博学”,句子固然可通,但句子本来就通,“博物”即“博学”之义。《左传·昭公元年》:“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①《春秋经传集解》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97页。;《盐铁论·杂论》:“然(桑大夫)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②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14页。“博物”都作“博学”解。所以说,此处不必改,而从校勘原则来说,底本不误,也不应改。第二,以“博学”改“博物”,还可仅认作不必改;以《南史》为据,则思路就是错的。《南史》的载述不是《诗品》文字的引录,与《诗品》没有版本性质的关联,因而对《诗品》校勘来说,《任昉传》不具有校本身份,没有校勘价值。
再看左思。
其源出于刘桢。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喻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常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考索本《晋记室左思诗》)
这是左思评语全文。“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诗品集注》改“野”为“浅”(增订本同),理由有四:一是吟窗本作“浅”;二是批评术语“文”与“野”、“深”与“浅”分别相对,“野”与“深”不对应;三是六朝人共认陆诗为“深”,“野于陆机”不词;四是钟嵘屡以“深”、“浅”比较陆机与时人③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第194页。。
按,此处不必改,也不能改。吟窗本作“浅”,固然可证《集注》改文有版本依据,但若底本没有疑误,则不能据他本改底本,此为校勘通例;吟窗本作“浅”,不能独立证明考索本“野”字为误(若单以二本相较,原本作“野”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改“野”为“浅”易,改“浅”为“野”难)。后三条理由,亦失之表面。批评术语使用,可以反义对举,也可以非反义并举,而《诗品》评语多属后者。如评张协:“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评范云、丘迟:“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雄”与“靡”、“浅”与“秀”皆非互为反义,“野”与“深”亦属此例。既如此,《诗品》他处以“深”评陆,以及六朝人以陆为“深”,就不能视为改“野”为“浅”的依据,“不词”之论,也就无从谈起。钟嵘评左思,首语先言:“文典以怨。”要是注意到六朝文论术语有“典”、“野”二目,并且注意到二目之关联,就可看出,“野于陆机”正从上文“文典以怨”而来——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064页下。“野于陆机”,则“典”有落实,文从意顺;改“野”为“浅”,则“典”字落空,“浅”句亦突兀。要之,“野”、“浅”孰是? 曰:当从考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