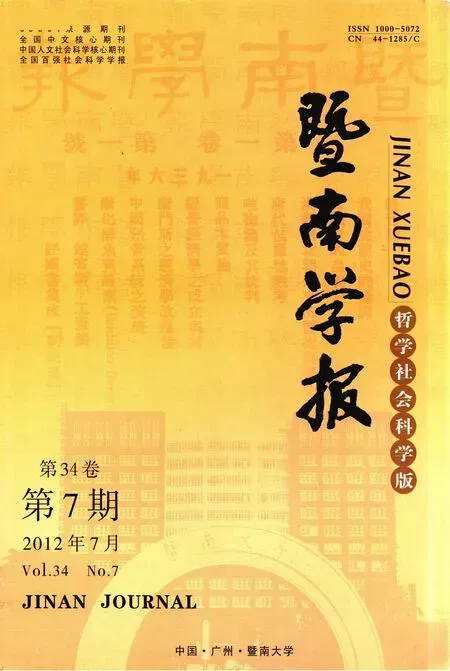粤方言变调完成体问题的探讨
甘于恩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32)
粤方言变调完成体问题的探讨
甘于恩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32)
广州话的动词可以通过变调表示完成。根据对粤语其他次方言的调查发现,除了动词本身变调表示完成外,一些体标记虚词也可以变调,模式是“动词+体标记词(变调)”。这种变调有两类,一是经历体标记通过变调,表示完成体;二是表完成体的标记词通过变调,表达强调意。这种体变调可以看作是内部屈折。不过,粤语中这类曲折变调已经萎缩退化。
完成体;变调;粤方言
形态研究是普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汉语是比较缺乏屈折形态的语言,但这不等于说,汉语没有形态,更不能说,汉语方言没有形态。方光焘先生曾经说过:“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一定的形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应该承认各种语言构成形态的手段并不相同,词形变化是一种语法手段,是形态,词序也是一种语法手段,也是形态。”[1]49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应该承认,普通话的形态构成与方言的形态构成亦不尽相同,普通话没有的现象,方言不一定没有。我们曾经研究了广东粤方言中通过变调表现人称代词的单数与复数的差异[2],说明就形态这一问题而已,我们对汉语及各地方言的面貌,认识还不足够。本文讨论粤方言变调表示完成体这一问题。
一、粤语变调完成体是否存在?
(一)有关粤语变调表示完成体的两种不同看法
不少粤语研究都指出,各地粤语存在以词形变调表示完成体的现象。如詹伯慧等举了“我食啦”为例,说明广州话“食”[sek2-35]“通过变调表示动词的完成体”[3]245。侯精一也说“广州近郊增城的粤语,动作行为的完成可以像广州话那样用变调来表示”,“增城也说sek22-35la33”[4]197,表示“吃”这一动作的完成。不过由于这类动词比较有限,大多局限于“食”、“去”等日常用词,李新魁等(1995)就认为这实际上是动词+体助词(咗)在语流中产生音变而脱落了“咗”。他们指出:“口语中,‘咗’常常和前面的音合音。合音的结果,是‘咗’丢掉了声母和韵母,只剩下声调和前面音节的声调‘融合’,构成一个读高升调的音节。”[5]422举的例子是“食咗饭未”[sek35fan22mei22],认为这是“取前一音节的声、韵而融入后一音节的声调”[5]47。张洪年也有类似的看法:“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因为‘咗’本身是高升调,又是轻读的音节,说得快时,就很容易只取其调,加之于谓语本身,成为一种浓缩体,也就是说用谓词的音节来表示动作,用变调来表示完成貌。”[6]152又说:“不过这种现象可能是广州粤语的残留,现在的香港人已经不大用了,特别是阴平阴入的字,大多用‘咗’。然而我们偶尔还是会听到这种变调的说法,所以不得不提。”[6]153彭小川同意这种观点:“不难看出,这两种形式(指“咗”与变调——引注)是有内在联系的,因为‘咗’本身是高升调,人们连读时读得快,容易把声、韵母省略而只保留35这一声调,并加在前面的谓词上来表示完成。由此可见,后一方式是前一方式的变形,在表示完成体的广州话中,‘咗’的用法是最基本的。”[7]40
(二)形态变调的可能性
从粤语的大环境来看,语义变调是一种较为能产的构形手段,变调表完成体是可能的。我们在粤语中发现不少方言有变调表人称代词单复数、变调表近指与远指、变调表词性变化等语法意义的现象[8]。不妨再看看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述。以下分两点来谈。
二、谓语动词本身的变调
(一)已有研究评述
早在1990年,黎纬杰在《粤方言的变调表完成体》一文中提到广州话可以“通过动词内部的语音变化,即用变调表示动作行为已经完成。有的同志称这种变调为省略‘咗’字的‘省略性变音’。”他认为:“广州人习惯多用‘咗’,但也用变调。粤西肇庆地区沿西江一带没有‘咗’或相当于‘咗’的动态助词,全用变调表示完成。”[9]182并举例说明各种变调规则。说“粤西肇庆地区沿西江一带没有‘咗’或相当于‘咗’的动态助词,全用变调表示完成”可能不一定符合语言事实,但粤西、粤中一带确有通过动词本身变调表示体貌差异的现象。如佛山地区内的禅城、南海桂城有些常用单音动词如“食”、“去”、“行”等可用高升变调来表示完成体:
①我食[sek2-35]饭就上学。(我吃完饭就上学。)
②佢去[hœy33-35]办手续啦。(他已去办手续。)
③课室扫[sou33-35]啦。(教室打扫了。)
顺德大良亦有类似变调,“表示动作已经完成”[10]86,例如:
④只雀飞啦ʧek3ʧœk25fei53-55la33
中山小榄话“用变调表示动作的完成体”[11]96-97的情况就更多,分布在阴平(53)、阴入(5)、阳平(32)以及去声(22)、阴上(35)、阳上(13)、中入(34)、阳入(2)各调,阴平、阳平阴入调变为超高平变调(记为5*或55*),其余变为25调,如:
⑤今朝劏鸡kɐm53tsiu53thoŋ53-55* kɐi53(今早杀了鸡)
⑥咬佢一啖ŋɐu13-25ky13jɐt5tam22(咬了他一口)
林柏松提到“石岐话中存在着用高升变调来表示动作完成的现象”[12]60,如:
⑦我喫[iak33-35]啰。(我吃了饭了)
⑧我买[mai213-35]啰。(我已经买了)
他推断石岐话“用高升变调来表示动作完成的形式是外来的、零碎的。”[12]61认为赵元任的《中山方言》未记录这种现象,因此这种现象可能来自周边粤语尤其是广州话的影响。这个看法未必确切,因为《中山方言》基本上属于音系研究,赵氏不一定顾及这种形态变调。我们觉得从石岐话的混杂性来看,更大的可能是早期的这种形态变调处于退化状态。林氏还指出中山沙田话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说中山沙田话(或顺德话)“任何调类的单音动词都可以用变调来表示完成体”[12]61。
余霭芹先生在其《台山淡村方言的变音》(2002,P381)也提到淡村话“高升变调可表实现态”[13]381和持续态,她所说的“实现态”即相当于本文的“完成体”,涉及的动词、形容词有“来”、“高”、“碰”,原例之一如下:
⑨却(他们)来咯[khiεk21lɔi22-35lɔ55](他们已经来了)
“来”的本调为22,变调后为35,表示动作已经完成。
(二)最新的调查材料
根据我们近斯的调查材料,广东粤方言明显存在通过动词变调表完成体的点有:澳门、德庆(高良)、番禺(市桥)、高要(白土)、广州(海珠、黄埔)、怀集(上坊)、连南(三江)、南海(桂城)、清新(龙颈、太和)、香港(市区)等10余点,加上前面提及的禅城、增城、顺德(大良)、中山(石岐、小榄)、台山(淡村)诸点,有变调表完成体的点,应该不下于20个。例如:
⑩我食[sik33-35]喇。(澳门、广州海珠、南海桂城等:我吃了饭了)
[11]我喫[jak33-35]啰。(广州黄埔:我吃过饭了)
[12]我搬[pun33-35]屋。(高要白土:我搬了家)
不过,各点的变调完成体相对集中于少数一些动词(如“食”、“搬”等),其类推功能稍弱,我们推测早期粤语可能较多使用这种表义手段,但目前逐渐退缩,让位于“咗”、“休”等显性的完成体标记。
(三)变调的范围
单韵鸣谈到广州话的体貌时指出,“广州话可以通过动词读作35调的形式来表示完成(下面记作“V*”①作者认为广州话完成体有两个变式,V*是变式1,“V+咗”是变式2。)。如果动词是阴平调、阴入调或阴上调,表示完成体,声调比原调音长加长,有时调值再稍稍提升。”[14]36她还指出:“通过动词的变调来表示动作的完成,这一形式不敌动词后加体标记的形式。文化水平越高的人,越倾向于使用体标记来表示完成体。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同声调的动词用于变式1常用度的高低在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的群体中表现较为一致,再结合对语料库的调查,我们得出,动词用于变式1的常用度的高低与动词本身相关,高频动词用于变式1的机会相对会大些。变式1的褪变现正处于词汇扩散的过程。”[14]43
变式1(即变调表完成体)的褪变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普通话影响的加深,“文化水平越高”这一因素表面上看是“(人的)文化程度”,但与地理因素息息相关,广州是广东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又是广东的行政中心,语言上受普通话影响非常明显。假设将广州定为一个圆点,受普通话的影响将随着这个圆点距离的外延而减弱,而变调表完成体现象则保留较多。这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如图:
三、完成体标记的变调
除了动词本身变调表完成体之外,某些方言体标记也可以变调,这实际上是“谓语动词+体标记【变调】”的格式,可以说是谓语动词+体助词与词根变调的叠置,只不过变调的位置移到体标记上。目前发现两类。
(一)从经历体到完成体的变调
一类如肇庆鼎湖经历体用“过”,完成体则用“姑=”,这个“姑=”其实就是“过”的高平变调,请看例子:
[13]我去过上海。(我曾经去过上海)
[14]我冲姑=凉。(我洗澡了)
(二)完成体标记“咗”强调性变调
另一类则是“咗”的变调,变调仅起强调作用。黎纬杰[9]184指出:“一般地说,动词和形容词后面有了‘咗’字”,便不需要用变调来表示完成。但有时候,为了特别强调‘完成’这个意义,‘咗’字也可以变调,重复地强调‘完成’的意思。如‘食咗嘞’ʃik22 ʧɔ355* la33(吃过了)、‘讲咗嘞’kɔŋ35 ʧɔ355* la33、‘高咗嘞’kou53 ʧɔ355* la33(高了)、‘肥咗嘞’fei21 ʧɔ355*la33(胖了)。这样的说法,在广州人的生活中是可以经常听到的。”这种强调性变调现今似乎甚少见到,也许在市井语言里,这种变调还存在,需要我们过细地进行调查。
四、形态变调萎缩的佐证
形态变调在早期粤语中,应该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手段,用于表示动词的体貌、人称代词的数(单、复数)以及小称等语法意义,但由于汉语双音化和显性语法标记(如普通话的“着、了、过”、广州话的“咗”、“紧”、“哋”)的影响,形态变调的范围逐渐缩小,使用频率也越来越低。我们从新会(会城)话第一人称单复数形式的使用上,可以观察到变调萎缩的痕迹:

表1 第一人称单复数的表现形式
新会(会城)话第一人称复数既可以说[ŋɔk1],这是一种浓缩型的变调(第一人称词根“我”加“屋”,然后变为低调),亦是早期四邑方言典型的复数表现形式。但是,因为广州话复数形式“哋”的侵入,现在会城也说“我哋”。变调萎缩的趋势在第三人称代词单复数的表现形式上,表现得更加清晰:

表2 第三人称单复数的表现形式
第一格式基本上是以变调为主的手段来表单复数意义,而第二格式则是附加词尾“哋”来表复数。但是我们观察新兴(天堂)话,发现其第一格式亦采用“哋”表示复数,有趣的是,其表人称的词根[khiak5]本来便包含数的信息,就是“佢”的复数(与新会话略有差异的是,新兴天堂话用高平调表示复数,高平调表复数的现象,见于阳春马水镇话[2]353),后来[khiak5]复数的色彩淡化(这一带粤语“入声形式的复数有时也可指单数”[2]353),成为第三人称单数,便再附加强势的粤语词尾“哋”来表复数,而不沿用早期的变调手段。这充分说明,“哋”和“咗”一样,对广府片周边的方言,产生重大的冲击力,使得早期粤语普遍运用的形态变调手段,慢慢退缩至有限的范围,而不再具有能产性。因此,可以断言,只要广府片粤语继续维持强势的势头,则粤语形态变调萎缩的趋势将难以逆转,这又与整个汉语形态变调萎缩的大趋势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变调表完成体的现象在早期粤语和现代粤语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现代广州话确实存在“咗”弱化并入前一音节的合音现象,但这不能否定粤语同时存在形态变调的情形,因为在各地粤语中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有的方言完成体标志并非“咗”(如四邑话),说是由“咗”弱化而来便显得十分牵强。因此,从事实出发,应该认可粤语这种独特的语法现象。但必须指出的是,目前这种功能正处于萎缩的状态中。当然,要对粤方言变调表完成体的现象有全局性的认识,有待于学者做一个更加详细更加广泛的专题调查。
[1]方光焘.语法论稿[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2]甘于恩.广东粤方言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形式[J].中国语文,1997,(5).
[3]詹伯慧,主编.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4]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5]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等.广州方言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6]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2007修订.
[7]彭小川.广州话助词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8]甘于恩.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9]黎纬杰.粤方言的变调完成体[C]∥《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10]林柏松.顺德话中的“变音”[C]∥《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11]郑伟聪.小榄话变调现象初探[C]∥《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12]林柏松.石岐方音[D].暨南大学硕士论文,1987.
[13]余霭芹.台山淡村方言的变音[C]∥《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4]单韵鸣.广州话语法变异研究[D].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5]刘若云,赵新.汉语方言声调屈折的功能[J].方言2007,(3).
[16]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2版.
[17]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18]詹伯慧,主编.广东粤方言概要[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On Perfective aspect through tone change in the Yue dialects
GAN Yu-en
Institute of Chinese Dialects,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China
Morphology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general linguistics.Morphology of Putonghua and dialects are not quite similar.Som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beyond our knowledge.This paper studies the possibility,typ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Yue perfective aspect with tone change,and points out that the function of tone change is in shrinkage.
Perfective aspect;tonal inflection;Yue dialect
H17,H14
A
1000-5072(2012)07-0070-04
2012-02-23
甘于恩(1959—),男,福建福州人,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粤方言地图集》(批准号:04BYY032);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粤方言比较研究》(批准号:07JDXM74003)。
[责任编辑 范俊军 责任校对 王 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