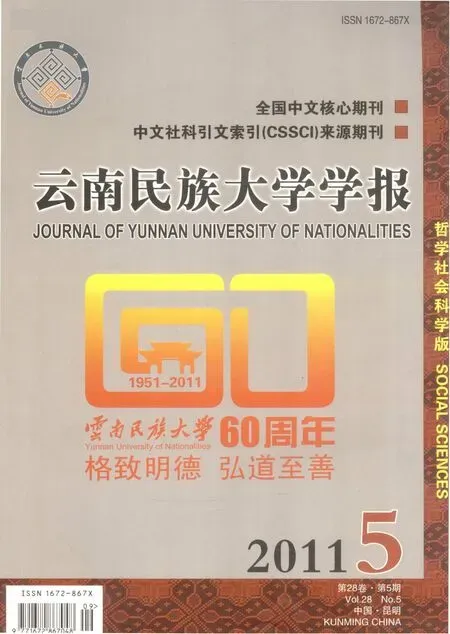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变化
方素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081)
20世纪初期发生的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实现了中国从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推动了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给中国带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思想大解放。在五族共和思想和民族平等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清王朝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的影响,缓解了满族与其他各族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合,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由于时代的局限,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逐步建立起平等、团结、互相、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共存和矛盾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在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下,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部分少数民族之间,历来存在着冲突、对抗和压迫;另一方面,在各族人民之间和部分民族政权之间,也保持着较为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交流。各民族人民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以及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都是中国这个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古老、传统的中国被强行拉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之中,逐步走上成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附属国的道路。中国各民族人民在受到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与统治的同时,又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中国的民族关系在外来侵略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扩张,求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对内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和压迫,争取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成为近代中国各民族的共同使命。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所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2]在完成这个使命的过程中,中国各族人民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结成了更加紧密团结的整体,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伟大转变。
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面对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变革已到了十分必要和十分紧迫的关头。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等,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高官,都有仁人志士对变革进行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仅不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相反却卑躬屈膝,大肆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一些满族权贵竟然发出“亡于汉人,吾族无噍类;亡于外人,尚得为小朝廷”[3]的荒谬言论,使中华民族越来越沦入被帝国主义列强恣意掠夺和压榨的悲惨境地;对内则不同程度地继续执行民族压迫政策,少数民族人民在经济上遭受剥削和掠夺,在政治上遭受歧视甚至遭到镇压和残杀,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更加突出,各民族人民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更加激化。特别是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与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之间,矛盾越来越尖锐和复杂。即使是力主君主立宪的杨度,也对清政府的抑汉政策大力抨击:
入关以后,以排斥汉化为第一政策,以贬抑汉权为第二政策,务求二民族之不相混合,以得长保存其特质。其第一政策之最著者有三:一曰语言。乾隆以前,屡代皆以学习清语训诸满人,而自命为国语,切切焉以满人作汉语为戒,此为排斥汉化之一。二曰文字。满洲本无文字,乃以蒙古字合满语联缀成句者,虽苟简不适于用,然亦欲自保之。入关百年之后,满诸臣中尚有以不识满文被谴者,诏诰等类皆用满、汉文各一通,此其排斥汉化之二。三曰血胤。入关之初,即下满汉通婚之诏,旋复禁之,正所谓宗法社会以羼杂为厉禁者,此其排斥汉化之三。其第二政策之最著者亦有三:一曰政治上,一切京外诸官缺,有专为满缺者,如理藩院之类;有满汉分缺者,如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大约满缺多于汉缺;有满汉并用缺者,如各省督抚以下诸官。凡此皆以示满人之优势,而不宜与汉人平等者,是为贬抑汉权之一。二曰经济上,满人虽亦有旗租等制,然其数无多,多数之满人则以兵之名额,坐领饷糈,而汉人则无不纳税者。以全体之满人为被养者,以全体之汉人为养之者;以全体之满人为分财之人,以全体之汉人为生财之人,是其贬抑汉权之二。三曰军事上,满人中殆无所谓民也,布于国中者,皆曰八旗驻防兵,则实无一人而非兵,又无一人而非防汉之人也。故与其谓中国有一部之旗人,不如谓中国有一部之旗兵,此无非欲以满人全体掌握一国之兵权耳。是其贬抑汉权之三。[4]
民族国家建构是近代世界的一个潮流。中国要自强自立,就必须完成现代国家转型,取得与西方各国一样的地位。历史事实证明,清王朝的软弱、腐败以及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才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因。不推翻封建帝制,不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永远不能摆脱被欺凌和被奴役的命运,永远不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欲戢列强鹰瞵鹗视之态,以纡华族豆剖瓜分之祸,惟有发挥民族种种特性,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当以建民族国家为独一无二义”。[5]因此,打破传统皇权统治秩序、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同样成为中国奋起的必经之路。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被日本打败之后,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像潮水一般喷涌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们更是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国家”的具体设想,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进入了一种自觉的状态。
在推翻封建帝制、实现由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斗争中,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及满汉矛盾成为资产阶级发起革命的有力工具。因此,排满兴汉浪潮日益高涨,一民族一国家的西方建国思想在清末十数年得到广泛传扬。其中以章太炎、陈天华、邹容等人的言论最具有代表性。章太炎认为:“夫满州种族,是曰东胡,……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6]陈天华鼓吹:“那异族非常凶狠,把汉族当作牺牲,任凭你顺从他,总是难免四万万共入了枉死城”,号召人们“弃邪归下,共结同盟,驱除外族,复我汉京”。[7]邹容宣扬:“吾同胞今日之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即吾曩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子,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其土则秽壤,其人则膻种,其心则兽心,其欲则毳俗,其文字不与我同,其语言不与我同,其衣服不与我同。”甚至要“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州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8]实际上,具有浓厚民族革命性质的“排满”、“反清”思想和活动,一直贯穿于整个清代。到了清末的最后几年,这种思想和活动在革命党人的极力宣传和鼓动下,更是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社会上各种排满和反满的事件不断增加。据统计,1905年这类事件有80件,1907年有132件,1909年有113件,1910年有285件。[9]至于讨伐清廷、鼓动反满的文件,更是汗牛充栋、不绝于书。
革命党人的理想和目标直接指向建立汉族主政的民族国家,并集中反映在同盟会纲领中著名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方针。激进者甚至认为一国之内不能有不同的民族,所谓“异类之民,集于一政府之下者,实人类之危輈仄轨也”,[10]“一国的人民,一定要是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言语的民族,断断没有好几种民族,夹七夹八的住在一国,可以相安的道理”。[11]因此,当革命党人宣扬的民族主义发展到极致,必然提出了在以18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的思想和主张,而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排除在外。[12]
然而,对2000多年来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而言,这样的政治选择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也就是说,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在地理分布、经济活动、文化交流、政治联系、族际融合等诸多方面形成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即使是革命党人提出的较为极端的18省建国意图,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构想,更遑论被分离或抛弃的边疆民族地区,在那样的境况之下根本无力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最后只能沦为帝国主义或外国列强的附庸。一旦这样的状况出现,对于以18省为地域建立的汉民族国家,何尝又不是一种困境或危险。因此,大汉族主义的建国思想及其带来的危害,清末就遭到了有识之士的痛斥。如杨度说道:
若汉人忽持民族主义,则以民族主义之眼视之,必仅以二十一行省为中国之土地,而蒙、回、藏地皆非;仅以汉人全部为中国之人民,而蒙、回、藏人皆非;排满之后,若不更进而排蒙、排回、排藏,则不能达其以一民族成一国家之目的,而全其民族主义。使其如此,则蒙、回、藏固亦主张民族主义之人也,不仅我排彼,彼且排我。于是全体瓦解,外人乘之,俄罗斯之国旗,必飞扬于长城之下。俄既乘之而得蒙、回,则各国亦不得不谋所以抵抗,英势不得不据西藏,日势不得不据东三省及福建,德势不得不据山东以侵黄河流域,法势不得不据两广、云贵以窥江海之间,英势不得不据长江流域以联由藏入蜀之兵。[13]
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排满口号在当时的中国的确是抓住了救亡的中心环节,起到了唤起民众,为辛亥革命的发起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但把反满和“杀尽满人”及收回汉族的政权联系起来,就带有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和大汉族正统观念的缺陷。尽管孙中山讲过:“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14]但排满风潮的消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为革命后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族关系留下了隐患。因此,辛亥革命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起来。
二
辛亥革命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的真实反映,革命党人宣扬的排满兴汉虽然占据社会思潮的主流,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创建现代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目标却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辛亥革命时期,各少数民族人民或积极参加革命党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或组织和参加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士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自觉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有力地支持了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及至中华民国建立,边疆民族地区纷纷以各种形式,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表示承认、支持和庆贺。如青海章嘉活佛特派大喇嘛却吉为专使,代表章嘉和青海蒙古各盟旗王公及各大寺院,于1912年3月10日到达北京,祝贺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拥护共和政体;[15]3月15日,甘肃都督赵惟熙、咨议局长张林焱、昭武军统领马福祥自命代表全省行政、民意、军界,联合致电民国政府,承认共和;12月,哲里木盟盟长齐默特色木丕勒代表该盟10旗发出通电,公布东蒙古王公会议取得的成果及哲盟各旗倾心内向之意;[16]1913年1月,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16旗札萨克王公在归绥召开西盟王公会议,一致决议拥戴共和,联合东蒙反对库伦独立;[17]1913年农历8月,马麒联合会盟祭海的青海蒙古各部王公,联名致电中央,表示拥护共和政府,等等。
应当看到,在辛亥革命风暴的影响下,部分地区的民族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和激化,民族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复杂微妙的局面。一方面,排满兴汉风潮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满族内部,还蔓延到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之中。如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发出了“本军于今夜十二时举义,兴复汉族,驱除满奴”的[18]命令;起义“三天来杀旗人不下四五百人,横尸遍地,不及时处理,恐发生瘟疫”。[19]湖南、四川、江西、江浙、上海、陕西、河南、山西等地的起义也高喊“兴汉灭满”、“驱满复仇”等口号,满族民众和官吏一道受到起义军的镇压乃至杀戮。中华民国军统领黎元洪发布的檄文,更是将蒙、回、藏与满族一同列入了排拒对象:“又尔蒙回藏人,受入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尔若忘我汉德,怙恶不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20]尤其是蒙古族上层与清王朝统治者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共同利益,“驱除鞑虏”的口号给他们的心理冲击不亚于满族,蒙古王公对南北议和南方代表伍廷芳的质问“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21]就足以反映这种疑惧心理。为了在满蒙地区开展反清活动,东北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在传单中说:“民主立宪是其宗旨,种族排挤,岂其主义?谓为排满,尤属无稽。满蒙回藏,咸与汉一。排满谣传,官忌所致。有心肝人,谁能信此?”[22]以极力消除排满口号在当地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即使这样,革命党人长期以来的排满思想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宣传,对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消极影响仍然不可低估。
另一方面,外国列强利用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政治局势不稳及社会动荡的时机,加紧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侵略和渗透,使这些地区的社会状况更加复杂,民族问题日益激化。如英国和俄国利用中国出现政局混乱之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怂恿支持西藏“独立”,以达到控制西藏并攫取各种利益的目的。沙皇俄国先后煽惑和支持外蒙古“独立”、内蒙古呼伦贝尔“独立”和乌泰叛乱,同时在新疆大肆扩张殖民势力,策动阿尔泰地区“独立”,并出兵强占了唐努乌梁海地区。日本不仅将东北和内蒙古划为自己独占的势力范围,后来更是妄图独霸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这些侵略和分裂活动,使得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形势十分严峻。凡此种种,都对中国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以及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带来了压力和影响。
三
辛亥革命是在高举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大旗下爆发的,又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节节胜利。当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之际,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派人,都无法忽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国情,以及边疆民族地区复杂严峻的形势。毫无疑问,西方影响下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现实发生了严重冲突,一民族一国家的理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遭遇破灭。因此,革命党人逐渐摈弃了排满兴汉的大旗,在民族建国方面与其他派别逐步达成共识。其中,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为国内民族关系的改善提供了精神土壤。
五族共和口号是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首先提出来的。①关于五族共和的研究已经有诸多成果问世,目前一般认为其来源于清末梁启超、杨度等人的思想和观点。日本学者片冈一忠则认为“五族共和”是南北议和时期,张謇因担心外国势力从边疆地区逐渐瓜分中国而提出来的。参见片冈一忠:《辛亥革命期の五族共和讑をめぐって》,中国近现代史の诸问题《田中正美先生退官纪念讑集》,东京,国书刊行会,1984年,第287~295页。他们曾议决有关事项共14款,其中前四款是:“(一)以咨议局为军政府,(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三)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四)规定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23]②第130页;林家有:《论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民族平等思想》,载《海峡两岸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辑要》,台北,财团法人逸仙文教基金会出版,1995年。也有学者认为,武昌起义的湖北革命党人主张以铁血十八星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而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与一些立宪派人士,则议决以五色旗作为国旗。参见李学智《民元国旗之争》,《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后经新闻媒体传播,五族共和一词在全国普遍流传并成为革命党人的政治号召。它基本体现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和现状,表达了中国各民族团结与联合的要求和愿望。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东北的革命党人为消除“排满”的消极影响,就在东北提出了各民族联合的主张,同盟会员张榕等人在沈阳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时,率先提出:“尊重人道主义,且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的主张。[24]黑龙江国民联合会发布的《国民联合会通知书》则提出:“为今之计,急宜联合满、汉、回、蒙及索伦、达呼哩各族,化除私见,共庆共忠。”[25]
五族共和口号成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口号之一。1911年12月初在上海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决:“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定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26]当时多数代表与程德全、汤寿潜、黄兴等人认为五色旗“既可表明革命行为,系为政治改造而起,非专为种族革命;又能缓和满、蒙、回、藏各族的心理,与汉人共同努力赞同共和。此议发出,群以为是”。[27]南北议和期间,南方代表伍廷芳在给蒙古各王公的电复中说:“民军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欲与汉满蒙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力,决无偏畸。”[28]其中不仅谈到了五族共和,还明确提出了五大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压力下,清皇室被迫同意交出政权,并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只是在五族的排序上,仍将满族排在首位,蒙古族排在第二。1912年2月隆裕太后在以其名义颁布的《退位诏书》中表示: “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29]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的第一年,在《劝谕蒙藏令》、《大总统令》、《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令》,以及下令恢复达赖喇嘛名号、下令国务院晓谕蒙旗、致电库伦哲布尊丹巴中,①分别见《东方杂志》第8卷11号《中国大事记》,1912年3月25日;《东方杂志》第8卷12号《中国大事记》,1912年4月22日;《东方杂志》第9卷5号《中国大事记》,1912年9月20日;《东方杂志》第9卷6号《中国大事记》,1912年19月28日;《东方杂志》第9卷7号《中国大事记》,1912年11月23日;《袁世凯致库仑哲布尊丹巴电》,电一、电二,程道德、张敏孚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7页。多次申明五族共和的主张。
五族共和主张在少数民族中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在民族成分最多的云南,革命党人建立的云南军都督府较早接受了五族共和主张,提出了符合云南各民族实际的“七族共和”思想,在辛亥革命响应武昌首义的各省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30]1912年10月及1913年初,内蒙古民族上层分别在长春和归绥 (今呼和浩特)召开东蒙古王公会议和西蒙古王公会议,讨论赞助五族共和,拥护民国,反对外蒙古“独立”。其中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在通电中声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31]1916年,章嘉呼图克图常与藏中通信,他受北洋政府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之托,“致函达赖,解明五族共和原理,与汉族和好之必要”。[32]1924年,九世班禅从西藏出走内地后,通电全国,赞翊五族共和,“共和布政,五族归仁,布岭萨川,同隶禹甸”。[33]1925年,班禅给善后会议提交《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提出以“联合、平等”为“五族共和”真谛。联合,即中国各民族“联合一致,毫无畛域歧视之见”;平等,即“五族人民皆能平等、公允,无丝毫畸轻畸重之弊”,“五族人民无上下、无远近、无贫富、无贵贱,一切平等,共图治理,共进文明”。[34]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领袖,九世班禅在当时对于国内民族问题能提出这样的真知灼见,并在随后的日子里不辞劳苦,在北京、上海、南京、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不遗余力地宣传他“消弭战祸,实现民族联合、平等”的主张,十分难得,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深远的影响。[35]
关于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是否主张五族共和,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孙中山赞成和肯定五族共和;有的认为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态度初则怀疑附和,后则批评放弃;有的认为五族共和根本不是孙中山的主张。[36]实际上,五族共和思想是孙中山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认为种族革命的目的已经完成,但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国家,就必须冰释和化解民族之间的矛盾,号召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共同为实现中国近代化而奋斗。因此,尽管孙中山对毫无革命历史的五色旗并不满意,在感情上更倾向于以青天白日旗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旗。但他也认识到此时共和力量已占优势,清王朝的灭亡已经不成为主要问题,开始把民族团结和避免国家分裂问题放到重要位置,因而顺应形势发展接受了五族共和以及保持领土完整的主张。[37]为此,民国初年孙中山多次在有关民族事务的讲演或文件中宣传五族共和、五族一家的理念,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国家。[38]但从1919年以后,孙中山公开批评五族共和,[39]大力主张“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40]“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立一个大民族主义国家”。[40]
中华民国创始之际高举五族共和大旗,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适应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是国内主要思想派别达成的共识。当然,中国的多民族状况不可能用五族来概括,将中国民族划分为5种显然是不科学的。但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分裂活动日益猖獗、边疆局势不稳的背景下,五族共和思想的宣传和提倡是切合实际的,有着积极的意义。五族中的蒙、回、藏,并不尽指单一的民族,所以在较大的程度上可以说五族共和的主张,实质是不分巨细,引导中国各民族在新形势下联合统一的主张,在当时对于协调民族关系、消弭民族冲突、稳定边疆局势和维护国家统一,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不能因为五族这一概念的不清晰,或是因为孙中山后来对于五族共和的批评,就否定或质疑五族共和在当时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
四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就把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主张和实施民族平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在宪法中确立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因此,民族平等成为辛亥革命留下的精神财富之一,为民国初年国内民族关系的改善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现象,由“华夷之辩”和“夷夏之防”等传统民族观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吴贯因说道:
华夏树帜,干戈起于一室,祸乱起于萧墙。种族倾轧之祸,迭为起伏。积数十圣王之力,始能开拓疆土之争,而不能消灭种族之届。……若我黄族,尤为甚焉。故其对于他族,辄字以蛮夷,呼为戎狄,不以平等之道待之,故虽同处禹城之内,而其种族之界,判若鸿沟。[41]
实际上,清末立宪派为了抵制以“排满”为重要特征的革命浪潮,化解国内严重的民族矛盾,曾多次上书朝廷,建议采取措施,消除各民族间不平等界限,尤其是满汉畛域。一些留学日本的满族青年甚至提出“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的民族平等主张。[42]反映20世纪初民族平等的思想和要求在国内已经逐渐形成潮流。而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要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各民族联合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就必须将民族平等包括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倡的“平等”观念之中。
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明确提出了民族平等的观念,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抨击清朝政府实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指出:“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族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43]为此他坚决主张民族之间的平等,特别是政治地位和权利义务的平等,表示:“四万万人一律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别,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44]“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45]在他提倡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决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46]
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五族共和政体的建立,表明资产阶级民族平等的主张在中国初次获得实现,民族平等作为资产阶级平等观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在国内得到宣传和提倡。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47]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民族的平等地位。这是因为这里的“种族”即民族之意,对此孙中山表述得很清楚。1912年2月他在致何宗莲的电文中就指出:“共和民国,系结合汉、满、蒙、回、藏五大种族,同谋幸福,安有自分南北之理,更安有苛遇满族之理。”[43]同年9月他又在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举办的集会上说:“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不平等之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43]
民族平等原则一经在宪法中得到确立,就逐步成为历届政府处理民族事务必须加以考虑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准则。1912年3月25日,袁世凯在《劝谕蒙藏令》指出:“现在政体改革,连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本大总统坚心毅力,誓将一切旧日专制弊政,悉行禁革。……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以期大同而享幸福,是所至望。”[48]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在大总统令中重申: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原系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现在统一政府业已成立,其理藩部事务,著即归并内务部接管。其隶于各部之事,仍规划各部管理。在地方制度未经划一规定以前,蒙藏回疆应办事宜,均各仍照向例办理。[49]
1912年8月,北洋政府在《蒙古待遇条例》中宣布:“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属待遇,应与内地一律。中央对于蒙古行政机关,亦不用理藩、殖民、拓殖等字样。”[50]在其后的各类宪法或宪法草案中,也都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或男女、职业的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民族平等经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在全社会得到广泛响应,最后由国家宪法进行确认,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伦理道德原则,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对进一步改善中国民族关系,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联合,起到了推动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民族平等成为其民族理论和民族思想的重要内容。国民党也在1923年的宣言中说:“我党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消极地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积极地团结各民族实现一大中华民族。”虽然它将民族同化视为实现民族主义的积极方式,而将民族平等视为消极的方式,但仍然说明民族平等是其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
五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的民族关系经历了调整,较之以往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虽然“五族共和”、“五族一家”等反映民族联合思想和民族统一意识的口号得到大力宣传,虽然民族平等原则被写入法律,但这并不说明传统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已经消失,也不说明民国政府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现象,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实际上,无论是在民国政府中还是在社会各界,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仍旧顽固存在并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大民族主义的一个表现是虽然承认五大民族,但不承认其他的民族。他们否认这些民族是单一民族,不承认他们的民族地位。以回族为例,“大汉族主义者的民族压迫政策,不仅在于他对回族实施野蛮的压迫,而更在于基本上就否认回族的存在,不承认回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硬说中国境内没有回回民族”;“大汉族主义者对于满、蒙、回、藏的压迫是在‘五族共和’的欺骗下进行的。但对于回回民族,则根本没有承认其应有的民族地位,抹杀了他是一个民族,因为五族中之回,并不是指的回回,而是指的维吾尔”。[51]大民族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在思想和行为上歧视与压迫少数民族。从民国政府到各个地方政权,一方面都想同化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如民国前期发生的内蒙古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甘肃“河州事件”、青海藏族与马家军的斗争等等,就是大民族主义统治下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
为了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争取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回族争取参加国会的斗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52]由于北洋政府不承认回族是单一民族,没有给予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平等权利,回族人民从1916年开始提出与青海、西藏一样获得国会中专额议员的要求。他们在请愿书中申明,回部八部 (包括回族和维吾尔族)承认中华民国,拥护五族共和,尽管远处边陲,实际却是西北的屏障,因此依据约法有关条款,中央应给予回部专额议员。[53]这个要求得到全国各地回族官员和群众的响应,部分维吾尔人也表示了支持,其请愿活动一直持续了近10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回族人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仍在继续。当时有人撰文呼吁:“民国肇造,五族共和,凡属中华民国国民,皆有享受绝对平等待遇之权。此不特我人之所殷于企求,而亦总理所谆谆昭告于国人者,无论何人均不能加以否认也。然至今日,事实之表现,则往往背道而驰,吾人诚不胜引以为憾。我回民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与蒙、藏族同,而中央各项待遇,独未使回民与蒙、藏平等待之,此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者也。”[54]回族民众要求政治参与的斗争,一方面反映出少数民族对国家事务积极关注及其国民意识逐步增强的现象;一方面也暴露出民国政府在民族平等的口号下漠视少数民族的愿望,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的事实。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实现了中国从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但是,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如何继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基础,怎样构建一个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综观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族事务治理,实际上经历了思想观念方面的彷徨:从“排满”的种族建国到“五族共和”的联邦建国;从国家有“中国本部”和“蒙、藏、回疆”之分,到民族有“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之别;从源流同一的“宗族论”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融合论”。这些变化体现出民国政府一直未能真正把握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未能确立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这一国家民族地位。在民族事务的实践中,仍局限于传统的“蒙藏回疆”,而无视民族众多的现实和民族平等的真实,无法改变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社会实质,所以也未能遏制民族分离主义的活动,未能消除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相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中,把握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实现了从“工农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的转变,最终做出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抉择,开启了中国民族事务的新纪元。中国各民族之间,终于逐步建立起平等、团结、互相、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A].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R].1997年9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杨度.金铁主义说[A].刘晴波.杨度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5]余一.民族主义论[A].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0.
[6]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A].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7.
[7]陈天华.猛回头[A].刘晴波,彭国兴.陈天华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8]邹容.革命军[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9]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32),1975.
[10]杨笃生.新湖南[A].张栴,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C].北京:三联书店,1978.
[11]陈独秀.说国家[A].陈独秀著作选 (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2]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J].北京大学学报,2002,(2).
[13]杨度.金铁主义说[A].刘晴波.杨度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14]孟庆鹏.孙中山文集[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15]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16]政府公报[N].1912-12-18“公文”.
[17]西盟王公招待处.西盟会议始末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3.
[18]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A].辛亥革命回忆录(一)[C].北京:中华书局,1962.
[19]杨霆垣.记鄂军政府的初期外交活动[A].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7集)[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20]黎元洪.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A].阳海清,等.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C].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
[21]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 (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22]李培基.辛亥关外革命始末记[J].近代史资料,1975,(4).
[23]曹亚佰.武昌起义[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 [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4]盛京时报 [N].宣统三年七月四日 (1911-11-24).
[25]郭孝成.东三省革命纪事[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6]辛亥革命回忆录 (一)[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27]吴景濂.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亲身经历[A].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28]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42辑) [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29]中国大事记[J].东方杂志 (第8卷10号),1912-2-12.
[30]潘先林.“七族共和”: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与发展[N].中国民族报,2011-7-29.
[31]西盟王公招待处.西盟会议始末记[M].1913.
[32]陆兴祺.解决藏事说帖[A].拉巴平措,等.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别辑七十种 (第12函《藏事稿本》(一))[C].
[33]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34]班禅致善后会议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35]胡岩.“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J].西藏研究,1995,(1).
[36]王晓秋.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A].海峡两岸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辑要[C].台北:财团法人逸仙文教基金会出版,1995.
[37]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J].北京大学学报,2002,(2).
[38]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J].广东社会科学,2004,(5).
[39]孙中山全集 (第5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0]总理遗教“演讲” [A].张有隽.中国民族政策通论[C].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
[41]吴贯因.五族同化论[A].庸言 (1卷7号)[C].1913.
[42]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EB/OL].浙江社科网,www.zjskw.gov.cn,2004-5.
[43]孙中山全集 (第2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4]胡汉民.总理全集(第1集)[M].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30.
[45]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6]孙中山.在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 (1922年1月4日)[A].孙中山全集 (第6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5.
[47]临时政府公报 (第35号)[N].1912-3-11.
[48]东方杂志 (第8卷第11号) [J].中国大事记,1912,(5).
[49]东方杂志 (第8卷第12号) [J].中国大事记,1912,(6).
[50]东方杂志 (第9卷第4号) [J].中国大事记,1912,(9).
[51]民族问题研究会.回回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
[52]方素梅.从《回部公牍》看民国前期回族的政治参与活动[J].民族研究,2010,(1).
[53]李谦.回部公牍[M].上海:上海中国印刷厂,1924.
[54]突厥(3卷6期)[J].19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