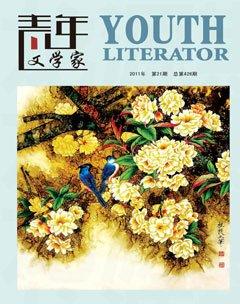我国尚未建立沉默权制度之原因评析
摘要:近年,关于沉默权的讨论一直不断,这几年来学者们对沉默权的讨论渐弱,沉默权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对沉默权的争论并未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不过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并不承认沉默权,这也是无可置疑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沉默权;诉讼模式;辩诉交易;自由心证
作者简介:郝银吾(1986.5-),男,汉族,河北邯郸人,现为四川大学法学院2010级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1-0186-01
沉默权是指被刑事追诉之人对刑事指控保持沉默的权利。这项权利在有关的国际文件和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通常被表述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沉默权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随着世界法治文明的进步、人权保障理念的发展,沉默权制度逐渐被世界很多国家借鉴和吸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但我国一直没有确立沉默权,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原因。
一、人权保障观念缺失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强权社会,传统的社会基础导致个体权利意识的缺失。而且,法在我国封建时期是统治者用来维护自身封建统治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工具,诉讼所要实现的目的则是发现犯罪、惩治犯罪。法律凌驾于人民之上,统治者则凌驾于法律之上,个人的权利意识逐渐淡化,法律被打上深深的义务烙印,导致沉默权没有滋生的土壤。另外,在新中国成立后,法律更多的是强调国家和集体本位主义理念,强调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集体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恢复,法律慢慢地在人民心中重新树立起了威信,但国家本位观的思想仍深刻影响这我们,导致了个体权利保护的弱化。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一直是“国家本位观”。而沉默权的理念背景是市民社会观,沉默权只有在个人本位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生根发芽。在这样的一种理念背景下,个体的权利意识极度缺乏,沉默权的理论的产生则更是没有依托。
二、传统诉讼模式影响
沉默权制度与当今世界司法民主的运动目标和无罪推定诉讼原则紧密相连,无罪推定以及确立沉默权则是近现代法制民主化的必然。在纠问式诉讼模式下,被控人被假设有罪,法官集侦查、控诉与审判职能于一身,主宰全部审判过程,双方当事人只是诉讼的客体,几乎没有诉讼权利,被控人只承担供述义务,成为只能接受审问甚至刑讯的对象。纠问式诉讼模式及其思维模式无疑是专横跋扈的。随着近代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的进步,纠问式诉讼模式及与其相联系的旧有法律制度被历史扬弃。
我国的诉讼模式先后经历了纠问式诉讼模式、职权式诉讼模式、强职权诉讼模式和以强职权诉讼为基础的混合式诉讼模式。从我国诉讼模式的更替过程来看,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并不是原因也不是重点,而是为了维系、强化统治或是适应时局需要,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一直“阴魂不散”,即使我国现在确定的以强职权主义为基调的混合模式,仍然受到纠问式诉讼模式的影响。控审合一的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剥夺了被告人与控方辩论的权利,被告人唯一能做的对其有利的事就是履行供述义务,如果保持沉默,将被认为是对抗法庭,认罪态度不好,构成量刑从重的酌定情节。这些都使得沉默权制度在诸多诉讼环节上难以确立起来,并且使保持沉默失去有可能被作出无罪推定的意义。
三、沉默權与我国“超职权主义”侦查程序的矛盾
沉默权与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无法相容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沉默权与我国“超职权主义”侦查程序的矛盾。
沉默权着眼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方的权利,限制侦查权。而中国的刑事诉讼具有一种“流水作业式”的整体构造,侦查程序中不存在中立的裁判者,这与西方各国“审判中心式”的诉讼构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其中的第一道工序,侦查程序并不与审查起诉、裁判程序居于同等的地位,而经常成为整个诉讼过程的中心。这就无怪乎会出现侦查机关滥用搜查、扣押、窃听等侦查手段的现象,把权力用到极致。
此外,沉默权的享有者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回答问题,保障自己的辩护权,而在中国的侦查程序构造中,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被严重削弱,律师的地位远远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条规定明显限制了律师提供帮助的时间,律师不能及时到场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刑讯逼供或诱供等非法取证情况的出现。不考虑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司法援助问题就根本无法让沉默权得到有效的保障,而我国的侦查程序又是超职权主义的,我国现行的侦查结构,无法全面保障刑事辩护人作用的实现。
四、沉默权副作用的缓解制度的缺失
沉默权之所以先产生于英国,与其有与沉默权相配套的几个重要机制是分不开的,即辩诉交易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
辩诉交易,是指在指控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交易,检察官通过减轻指控、撤销部分指控或者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活动。辩诉交易制度给自愿作有罪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减轻处罚的奖励,以减少其作有罪供述的缺陷。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不存在辩诉交易制度,而有一种与之相类似的简易程序,但仅限于适用于案件性质轻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另外,我国还存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鼓励犯罪嫌疑人做有罪供述,其价值理念与沉默权不同,甚至是相对立。
从证据角度讲,英国、美国的证据制度是自由心证制度,这也是沉默权的制度基础之一。根据自由心证的原则,法律并不要求法官或陪审团在作出判决时所依据的证据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而只要求其根据良心或理性,形成“内心确信”或是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我国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原则强调证明标准的客观性。在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小,法官虽然可以依职权调查取证,但他只能“依法”定罪。因此,在刑事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依赖依然很强,如果因沉默权制度设置不当而导致口供的较大量的减少, 对于犯罪控制将十分不利。在此背景下,要求建立沉默权制度自然很困难。
沉默权不仅是一项权利,更是一项制度,它与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等各方面紧密相连。从以上论述可见,在我国不仅没有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基础,而且还存在与沉默权制度价值追求相异的制度,因此我国并确立沉默权制度也是必然。
参考文献:
[1]卞建林,沉默的权利[N],南方周末,1999-08-06(5)。
[2]苏力,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J],中外法学,2005.5(2):3。
[3]吴延溢、那述宇,沉默权的矛盾分析[J],学术探索,200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