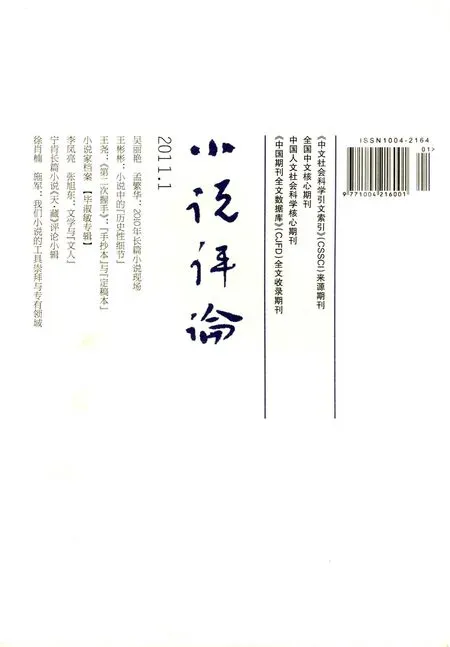我们小说的工具崇拜与专有领域
徐肖楠 施 军
我们小说的工具崇拜与专有领域
徐肖楠 施 军
时尚变幻与工具崇拜中的小说品质
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逐渐演变为时尚文化表演的明星,但被崇尚的是工具的小说,而不是诗性的小说,眼前铺展的是一种罕见的小说的工具崇拜情景。然而,似乎这种小说的工具崇拜被作为小说最新的品质而张扬,它疏离小说诗性的光鲜表现以及对这些表现的赞颂,掩盖了它的工具崇拜特质。
这种小说的工具崇拜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危险性在哪里?如果我们需要对消费化与媒介化時代的小说重新定向,就需要对此加以关注和说明。通过小说的工具性作用与小说专有诗性领域的关系去观察、通过对小说与时尚生活以及人类精神的关系去思考,如果能够进入一些迷惑性现象的更深处,或许会更本质地发现小说理解和表现生活的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生活中时尚而广泛的消费化、商业化、技术化、媒介化进入中国小说时,大都可能是一种工具化表现。在生活中,这些因素既是工具,又是内容和形式,它们改变了生活内容、生活形态、生活结构,形成了不同以往的生活风格和小说风格,但这些改变中的非精神性、泛审美化倾向也试图改变中国生活与小说沿着经典精神前行的方向。
在我们的现实中,利益崇拜已经家常便饭地蔓延,人们把身边生活中的一切都作为工具去谋取利益,把生活变成了一种现成的、以利益为中心的工具性生活,小说也随之变成了一种工具:写作者、批评者、阅读者都把小说当作与生活相接的工具。这种工具性小说尤其与各种时尚的技术因素和文化因素结合紧密,这些因素既作为工具与小说联姻,又以生活为名而进入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并不断成为生活与小说并行的最新表演:它们以个人自由与时尚因素结盟而共谋名利为小说中心,以新技术和新文化为理由和动力而利用小说。
很大程度上,小说本来产生的是诗性的精神崇拜,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本来是为了人的本质解放和心灵净化而存在、为了人的理想主义生存而延续,这是小说的基本精神立场。但中国1990年代后的小说很少为了人性、自由、尊严等诗性核心价值而发生,当人们为了现实需要和欲望满足去看待、去要求小说时,就会任意改写甚至剔除对小说诗性精神的崇拜,从而把小说改造成自己的生活需求和生活资本,为我所用地对小说工具化崇拜。
当主体精神的陷落使小说不断沦为工具崇拜,随心所欲的工具性就使小说的诗性崇拜不断蜕化,人与小说的精神对话就变成了功利主义的时尚互动,小说愈来愈变成便捷地包装利益与分享利益的工具性领域。由于小说软弱地依附于工具化的强大,我们就看到了各种小说尴尬的情景:诗性贫弱、思想空洞、想象萎缩、情趣混乱、审美变态、知识失效等等。
从现象上看,小说的眼花缭乱跟随着小说外部的变幻:技术的、时尚的、商业的、媒介的等等,似乎是生活变迁撬动了小说活动,但细究却不一定真是这样。实际上,这样的小说改变是工具性改变,不是本质性的,但是,需要这些工具性改变的人以及陌生于小说诗性特质的人夸大了时尚工具的作用,并且将这些变化称为小说的本质性更替,试图以此在一定程度上颠覆小说的经典性意义,从而肯定自己需要的小说的实用性意义。
问题不在于小说的内在关系要适应小说的外部变化,也不在于小说的经典性要适应时尚性,而在于小说的核心品质被别有用心地加以工具性替代。一些新兴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的确改变了生活形态和生活模式,被改变的生活习惯与社会心理自然影响着小说,小说也就相应被改变,但小说在不可避免地改变的同时,也有不易改变的核心品质:精神立场和审美意识相融合的诗性品质是小说的核心品质。
1990年代以来小说外部因素对小说的影响,并不能证明小说的诗性精神本质必须被从根本上改变。当圈里圈外一些人以外部的障眼法迷惑他人与自己时,当然要把小说的外部变化宣告为小说的本质性变化,不然他们摇晃小说而让自己花枝招展就会无人理睬。这里被有意忽视的或被有意删去的,就是小说的精神方向、精神立场,没有一种精神方向和立场,就没有一种审美方向和立场,也就会随波逐流地飘离小说的核心价值、核心品质和诗性专有领域。
小说外部活动对小说本质活动的蒙蔽
1990年代以后的时尚变化,尤其是数字化、新媒体等技术文化带来的变化,只是对小说存在的结构和模式发生了影响,并没有对小说的诗性本质产生改变。一方面,小说模式的改变与生活模式的改变具有对应性,但小说模式的改变不意味着小说本质一定改变;另一方面,无论模式如何变化,都需要一种诗性特质来支持变化,没有一种诗性内核也就没有真正有效的小说模式。
新的生活结构和模式对小说的影响主要在于:一是形成了多种文化群落结成的社会关系,改变了以主流文化为主的、线性延续的传统小说的社会关系;二是横向的小说活动模式被改变,小说专门活动被扩散、小说专门领域被打破,传统的小说活动模式因而失效,商业性、媒介化的小说活动取代了精神性和审美化的小说活动;三是小说的知识、写作、阅读的模式和结构产生变化,专门性的、经典性的小说知识领域被瓦解,杂乱无序、无主题、无中心的社会信息、文化信息削弱了小说的精神表现,使小说的诗性与现成信息常常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削弱了诗性精神作为核心资源对小说结构和小说活动的影响。
但是,说到底,这些改变主要是小说外部活动的改变,并不能改变小说的核心品质,它们提供让小说的经典价值有新表现的可能,并不提供消除经典价值的必要。虽然网络、商业、消费等直接地不断改变着小说的传统性延续,使小说的诗性核心不断被遮蔽,但并不是这些外部元素侵入就一定让小说的核心价值难以肯定,而是我们的小说在工具崇拜下放弃了能从内部肯定的价值:人性、自由、平等、尊严、正义、真理等小说的核心价值正在被遗忘。信仰小说就是敬畏人类的这些核心价值,在这样的精神信仰立场上,审美知识就不会失效,就会反对轻狂、发泄、浮躁、谋利、表面的工具性写作。
虽然可以明显地看到,生存风格的刷新改变了小说活动的风格,但与此同时,一系列疑问也应声而出:已有的小说模式被改变了,新的模式是否真正有效地形成了?生活与小说的精神本质是否与以往几千年相比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我们正在看到的对人类精神本质的改变是否是自我欺骗?是否有些人愿意看到这样改变的有效性从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这样,小说对生活模式的记忆所形成的小说模式是否真正有持久存在的可能?小说对生活模式的记忆重要还是对生活精神的记忆更重要?
实际上,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与当代技术和文化结合的各种情景,不过是表明了小说发展变迁最终的精神方向:几千年来的小说一直是在与各阶段历史文化不断结合中发展,但这往往改变的是小说原来的形式和内容,而小说提升生活和人类的精神方向虽百转千迴却仍然不改初衷。中国当代小说也处于这样的历史过程和精神方向中,只不过,科技发展使这样的过程和表现有些特殊,但这种特殊并非是人的精神本性产生了根本改变,那么,作为人的审美性精神记忆的小说也不会产生根本的改变。
如果不从历史和小说的精神方向去看小说的时尚情境,我们的误解就应运而生:媒介文化、消费主义、利己主义、赚钱效应给小说提供了唯一出路,小说只有向新生代、新兴文化靠拢才有前程。在新的生活风格不断形成和改变的过程中,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脚步慌悚、身影纷乱,让许多人迷惑陷落其中,从而形成了小说的诗性品质就该这样衰落的误解。但从本质上看,这种小说与大众文化、公共文化、技术文化结合的方向,不应该是为了迎合依附于身处其境的文化氛围,而更应该是为了增加小说的精神力度的弹性,这种精神弹性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通俗形式装高雅主题,而不是以高贵精神去依附粗俗现实,例如西方作家一直在尝试以侦探、惊险、科幻、艳情等形式去追寻严肃的主题。
我们想要观察到的,是1990年代后中国作家是否也有这样的精神意愿,但可惜他们不但妥协并依附于现实,而且主动利用了媒介化、亚文化等技术和文化来扩张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现实和写作情境,使中国小说在不该被工具化的时刻、在发展人类主题新表现的时刻,重新获得工具性崇拜,也使人们能远离小说的诗性精神和专有审美领域而名正言顺,因为人们宁愿改变小说而不愿改变现实,更不愿改变从现实中获利的自己。
小说对现成生活和工具性写作的依附,其实是人的主体精神对现实欲望的依附。是人的精神疲软直接依附了小说外部的杂乱无章,而不是小说的外部因素主导了小说诗性领域的混乱。放弃诗性精神追求的目的,是获得利益和享受,于是小说变成工具。也就是说,人们正在崇拜的小说表现并不是小说,而是完成小说表现的工具。正是在精神主导缺失而工具崇拜占据上风的情况下,虽然一波波小说后浪推前浪,却总是难以具有上升的诗性力量。
当小说作为工具追随外部现实时,生产与消费就主导了小说。由于诗性精神内核的弱化,小说很容易被小说外部的商业意识和消费主义所控制。没有一种坚定的精神立场以及相伴随的审美立场,与商业行为、消费行为相一致的小说行为就容易失去诗性效应,变成一种工具性效应,也就难以形成独立的小说价值,反而愈来愈具有生产与消费、投资与收益的倾向。
1990年代前的中国小说能对历史有特殊记忆,是因为小说写作和阅读被小说内部的精神内核所主导;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被任意的无中心写作和阅读所主导,写作和阅读又被现实欲望和时尚工具所主导,在缺乏精神主导的情况下,生产与消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小说的品质。
工具领域与诗性领域的疯狂混淆
小说的工具化崇拜已经普遍成熟,小说就很自然地变成一个成熟的获取名利的工具化领域。到2000年代,小说产品的批量生产以及小说的造富效应使小说的大片领域明确沦为生产与消费、投资与收益、生存与获取的名利场,强势地显示出已经不再需要专门的小说领域。
可是,小说的专有领域是美学化的精神领域,它通过精神性与审美性融合的语言而发生想象性的人类记忆,语言表现的诗性特征是小说无法被抹杀的特征。作为美学化的精神记忆,小说既留有人类共同的精神编码印迹,又非人人能无师自通的审美领域。
如果这个时代的中国小说失去了专有领域,那就要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极高级的精神层次,人人具有极高的审美能力;要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小说,人人都可以任意宰割小说。不管哪一种情况,都是疯狂的。
能被迷惑的是,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的工具崇拜完全是个新品种,它极其善于移花接木、假面表演:1990年代后的小说一方面已经不需要小说的精神头脑,一方面却仍然需要小说的身体衣冠,甚至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更加需要夸张小说的效用、更加需要小说的装饰作用,这样就可以在对小说予取予夺、骨子里轻看小说的同时,不是大肆宣称小说的高雅以遮掩自己的粗俗,就是紧紧抱住小说以保障自己的“幸福”生活。
在类似这样的小说发生过程中和小说发挥效力的过程中,虽然针对小说的过程和手段已经透露了这样的小说写作的工具性目的,但在人们的普遍意识中,这些工具性过程和手段现在却似乎倍受推崇。这样的工具化似乎更加具有合法性、有效性和本质性,更加具有写作自由的好名声,并不被承认是个人的工具,这样的工具性表现已经替代了小说的精神本质,蒙蔽了人们对小说专有的诗性领域的想象。
把小说作为一种个人工具还是作为一种专有诗性领域,表明了不同的审美立场和精神立场。不过,不管有意无意,把小说当作个人工具常常是以当作普遍本质为名的。把小说如果仅仅作为个人工具,那就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拿起来任意使用;如果作为一种专有诗性领域,那就不能像野蛮人出没于荒野那样或者像时尚人出没于奢华场所那样随意游荡其中。
小说专有的诗性领域也就是精神培养的领域,它含有两个相互依托的重要元素:一是感受领悟小说表现的诗性能力,二是判断鉴别小说意识的诗性追求,这两方面基本支撑了小说的诗性品质和诗性精神。面对小说的专有领域,需要某种诗性精神和诗性能力,而这是需要培养的。培养小说的专有领域,也就在培养小说的诗性追求和诗性能力,不具备相关的诗性能力,其实是难以自由进出小说领域的。
中国审美文化的流行,使人人都认为自己有很好的小说审美能力、任何事物都可以被看作具有小说审美因素、谁都可以成为小说写作者和小说批评者,这使人们在审美与非审美、小说与非小说之间任意转换、随意跨越。中国小说的日益无中心、无内核、无主题、无界限让小说成为一个眼花缭乱的百货广场,人人都可以走进去买卖,从奢侈享用到日常需要、从妇女儿童到体面人物、从古旧灰暗到时尚光鲜,任何写作都可以无限制地被宣称具有小说效力。
所以,在中国今天泛滥的写作中,人人都可以宣称懂小说、写小说、爱小说,小说写作失去了与小说的诗性特质相应的特殊意义。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在层层推出、目不暇接的文化产品中,要筛选出真正具有诗性品质的小说作品是很难的,而要重建小说的专有领域,就需要一段清理工具化崇拜、重建精神立场的艰难过程。
清理工具崇拜的难点其实就在于:这样的崇尚工具化又不断被工具化改变的小说活动,不但模糊了小说专有审美领域的意义,而且已经在消解小说性精神培养的可能,而小说正是依靠对人类的精神培养来延续小说的专有领域的。为了生成和延续小说的专有领域,就需要相应的诗性精神的培养。每个时代以及后来的小说写作和阅读都需要专门性的、有传统的培养,1990年代前,这种精神培养虽然范围狭小、程度轻浅,但一直在延续;1990年代后,这种精神培养是否还在延续大可置疑。
面对1990年代后小说专有领域的碎片化状态,小说如果要恢复小说自身的专有审美领域,就要注重对诗性精神的培养,培养小说的诗性精神就是在培养小说的专有诗性领域,也是在培养感悟小说的诗性能力。终究,没有一种诗性能力和诗性精神,难以出入小说的专有审美领域,而培养小说的专有领域,也需要培养小说的诗性精神。
与精神立场相伴随的诗性活动始终需要一种专门的精神培养,小说天然要培养自己专有精神领域,也天然有一种精神培养的工具性作用,不过,这与中国目前对小说的工具崇拜完全不同,因为,这始终包含着一种精神立场和精神方向,这是小说的核心资源和核心动机,由此展开的历史和人性活动才可能被赋予自由美好、高贵优雅的气质,并形成专有的诗性活动领域。
小说作用的精神立场与方向
培养一种诗性活动的专有领域以及对其的领悟,就是在培养一种精神立场。一种小说的精神立场,就是一种审美立场,也是一种生存立场,有什么样的精神立场,就有什么样的写作和阅读,就会形成相应的诗性精神活动领域以及审美作用和教育作用。
将1990年代前后中国小说的精神记忆特点相互比较联系,会发现:1990年代以前的小说不论如何刻板保守、如何充满禁忌,其中总有一种自我满足、自我验证的精神方向和精神立场,这样的精神核心推动了那些年代的生活与小说的共同追求。1990年代后的中国小说在扭曲小说的工具作用时,也破坏了小说的精神作用,在疏离小说的精神方向与精神立场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小说发挥作用的诗性能力和小说专有的诗性领域。
如果从精神立场和精神方向的视点出发,对中国1990年代前后小说都发生过的工具化进行比较,其实对认识我们现在小说的工具崇拜颇有意味。在1950年代至2000年代的中国小说中,小说的工具化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于:自195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启动直到1980年代初期,小说的工具化曾强大地影响着小说。陌生在于:199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直到2000年代遍地风流的小说工具化与1990年代以前的小说工具化不同。一方面,1990年代以前的小说工具化是为国家、为理想,为一种革命化的生活伦理;1990年代以后的小说工具化是为个人、为欲望,为一种占有性的生活伦理。另一方面,1990年代前的小说工具化有精神立场和精神方向,1990年代后的小说工具化缺乏精神立场和精神方向。这样两种重要的区别,使1990年代前后的小说工具化有本质的不同。
从诗性角度观察,1990年代前的人生与小说当然存有重大缺陷,但这种缺陷不能推翻与之伴随的精神方向以及非常简朴单纯的小说专有领域。一种小说专有领域的精神核心的核心,是一种精神立场,没有一种精神立场,就难以安放某种精神特质,难以具备小说的诗性价值。至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国小说诗性价值的偏颇,另当别论。
在更大程度上,1990年代前中国小说注重了一种革命化生活伦理的教育性工具作用,但它们真实地存在过并支持了那些年代的生活精神与小说精神。但是,精神的坚强与美学的软弱合并,使1990年代前中国小说的精神活动领域常常太简单、太理念、太生硬,缺乏诗性的柔软、丰盈和弹性。
1990年代前中国当代小说大部分时间成为一种革命化生活伦理的工具,但其中包含的精神方向——为一种理想生存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去鉴别与小说工具化相伴随的精神品性。无论程度深浅以及精神方向朝着哪里,1990年代前的中国小说毕竟保持了一种精神培养作用,与此相伴,无论审美效果怎样以及审美空间是否狭小,也还保持了小说的专有领域,与此同时,也就培养着某种精神方向。
相比而言,1990年代后的小说虽然丰富繁杂,但因为缺乏一种坚定的精神立场,小说深入历史与人性的表现却苍白贫弱,多半复制性地记录生活表面的现象和活动,难以建立深入生活的审美化专有精神领域,也相应逐渐屏蔽了小说的审美和教育的精神培养作用。屏蔽了小说的精神培养作用,与之相连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也随之被败坏了。
如果承认小说的工具性作用,就必须承认小说的工具性伴随着一种精神方向和审美方向,这种方向因为含有一种精神立场,就不会被个人工具化,而没有精神立场的任意工具化的小说只能为我所用、不知所终。一方面,小说是为个人的工具还是为集体的工具使小说有精神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小说的工具性教育作用是小说本来具有的品质和动力,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中国小说不过是延续了这样的传统。问题在于那段小说将工具性作用狭隘化了,而不在于它们具有这样的特性,因为小说本来就具有教育性工具作用。
人类历史中,小说很早就成为人类精神培养的某种工具。古希腊时期的戏剧竞赛就具有普及和倡导古希腊公民伦理的作用,具有健全社会、培养道德的作用。为了让人们愿意去接受戏剧传达的精神和伦理影响,古希腊城邦管理者发放戏剧津贴,补贴人们放下农活去看戏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亚里斯多德提出戏剧以恐怖和怜悯去净化人们的情感、古罗马贺拉斯提出寓教于乐,都表明小说始终有以精神培养为主的教育性工具作用。
从小说的功能意义上说,小说的精神培养作用已经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成为小说本身的某种品质,小说如果不教导人们什么,或者让人们什么也不做,也就不是小说了。小说其实一直成为推动人类前进的某种精神性工具,但不是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这样的实用性工具。
我们这样的工具崇拜,注重的是个人将小说作为工具怎样得到、怎样生存,这与小说的精神培养作用恰恰相反。该注意的,是1990年代后小说常常不问人们为什么生存,而只关心人们怎样生存。当我们时代的小说更多提问为什么生存时,就具有了一种精神立场和精神方向。
徐销楠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施 军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