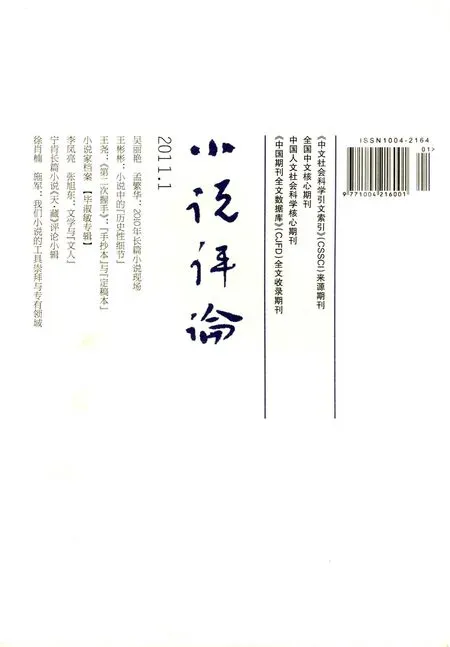西部叙事的古典意蕴与现代追求
——评王新军长篇小说《最后一个穷人》兼及其他
王明博
西部叙事的古典意蕴与现代追求
——评王新军长篇小说《最后一个穷人》兼及其他
王明博
西部是一个地域概念,不同时期地域划分虽然不同,但表现在文学上的美学风格却大体一致,大气、清新、粗犷、浪漫,古道西风的苍凉。在当代文学的书写中,西部代表了封闭、落后、陈旧,西部叙事的特征表现为苦难、底层关怀、厚重、史诗品格,甘肃作家的创作就有较集中的体现。在邵振国的《麦客》中,可以看到吴河东父子在欲望和道德撕咬中的痛苦挣扎;在牛正寰的《风雪茫茫》中,可以听到活的渴求与人的尊严的两难处境中西部女性的滴血呻吟;在雷建政的《西北黑人》中,可以感受到麻哥和尕五舍弃以命相搏的户口证明时的惨烈悲壮;在张存学的笔下,可以触摸到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永远也走不出的贫困和愚昧。还有阎强国的《红色的云雾》《女人秋》,雪漠的《大漠祭》《白虎关》,柏原的《喊会》《背耳子看山》等,无不表现了西北偏僻山村农民生活的沉重与苦难。这些作品往往给人一种逼仄、压抑、沉郁的感受,而王新军的小说却是耳目一新,如沐清风。同样反映的也是西部农民的生活常态,王新军一改当下甘肃小说惯常的沉重风气,用温婉的笔调、诗意的语言,抒写乡村生活,展现底层命运。王新军有意淡化了那种令人唏嘘、令人扼腕的苦情,用看似轻松的调侃、灰色幽默式的笔触,既写出了乡村的纯朴、宁静与诗意,又写出了封闭、落后和荒凉,在给人以清纯、自然感的同时,也给予了人们现代城市文化参照下的忧郁与怅惘。他笔下的苦难是耐人回味的,能勾起读者记忆中的苦涩忧伤,他能把这种苦难“内转”——也即读他的小说,不是从故事情节中接受那些苦难,而是在他故意的轻松中,唤起读者善意的悲悯,涌起一股股生活热情,心中充满了关爱,充满了扎入泥土的踏实的收获感和对纯净生活的向往。王新军不刻意描写人物在苦难中的呻吟与挣扎,不刻意将读者挽留在人物的辛酸中,而是把穷乡僻壤的饥馑病痛作为读者偶尔经过的一条小河,用它的温凉与清澈洗涤着行路人的脚踝,让人生的脚步停下来,体味人性的美好和道德的善良。
王新军被称为“甘肃八骏”之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先后有长、中、短篇小说百余部(篇)作品发表,作品曾获第六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奖,第一届、第二届黄河文学奖中、短篇小说一、二等奖,第四届、第五届敦煌文艺奖等。由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的《最后一个穷人》,是王新军历时八年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力作可以说是王新军乡村叙述的一个突破,他自己曾坦言:“我曾经热衷于精确地表达自己朦胧的心情,但后来还是迷恋上了叙事的长度和难度,我一直盼望写出与前一部不同的小说来。”①
《最后一个穷人》延续了他在“大地上的村庄”系列的美学风格。“大地上的村庄”系列是以他的短篇小说《大地上的村庄》命名的。这一系列的小说有《大地上的村庄》《村庄的开始》《闲话沙洼洼》《吹过村庄的风》《与村庄有关的一头牛》《农民老木》《七彩山鸡》《大草滩》《八个家》等,作品以疏勒河周边的农村为背景,虚拟了一个“沙洼洼”的村庄(其中有的作品并非写这个村庄,但是作品的主题和风格都大致相似),以村庄和“与村庄有关的”事物(牛、狗、风等)为主体,叙写了新时期以来,时代变迁过程中西北偏僻农村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城镇化经济对农村的挤兑,农民生活方式、心理结构发生变化的矛盾和焦虑。作品不是以写实的笔触刻画这种苦焦的生活,而是以小写意的手笔写出了经济大潮冲击下,传统农村所保留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对其小说的审美特征,李建军的评论是极为到位的:“王新军的小说有乔治·桑的温暖的爱意,有汪曾棋小说中的浓厚的人情味,朴实中富含着诗意,平静中包蕴着热烈,将爱情及其他形式的伦理亲情,表现得感人至深,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伦理内容和道德力量。”②这种浓厚的人情味和感人至深的伦理道德,在《最后一个穷人》中表现的更突出。《大草滩》中的许三管,《羊之惑》中的玉根老人,《农民》中的李玉山等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而《最后一个穷人》中的马三多却是普通农民中的下层。他的父亲是个瞎子,他18岁了才读到三年级,还写不上一个“手”字,正是这样一个“头脑像五月的绿麦子”一样的主人公,才去收养一个又一个被人抛弃的女婴,才去一次又一次拯救被宗法社会道德戕害的女人。他的至真至善在于这一系列的行为源自一个人,一个没有受社会规训的人的心底的善良。
《最后一个穷人》的美学特征还在于作品“最后”文学类型的选择上。新时期以来以“最后”命名的较多,形成了文学中“最后”现象。典型的有《最后一个渔佬儿》《最后一个匈奴》《最后那个父亲》等。这一类作品在在审美特色上都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淡淡的忧伤情怀。李继凯教授在谈到“最后”现象时指出:“从作家涉写‘最后’现象所体现出的情感态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侧重于歌项、赞美的,即致力于开掘或发现‘最后’现象中宝贵的东西;其二是侧重于揭露、批判的,即致力于剥露和剖析‘最后’现象中落后的东西或腐朽的东西;其三是侧重于调合、静观的,即对‘最后’现象采取的是通达的多维视角,冷静客观地、全面地观照,其情感态度也最复杂、最隐微。”③我认为《最后一个穷人》属于第三种情形,作者的情感是复杂的,马三多这个在商品经济主导下的最后一个穷人,他身上所呈现出的这种淳朴道德日益在丧失,作者的“最后”情结正是对这温情传统道德异化所唱的挽歌,又是对不能与时俱进被社会所淘汰农民的一种咏叹。从理智上讲,这种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传统精神,传统性格应该被淘汰,但情感上又觉得是美好的、温馨的。作品超出了表层悲剧故事的呈示和浅薄的哀怜悲悯,超出了由一般的心理痛苦转化的审美快适,具有相当的审美深度。
《最后一个穷人》不同于“大地上的村庄”系列小说,关键在于现代性追求上,也即先锋性的探索上。首先,重复的充分运用是最鲜明的特点。米勒指出:“不管是什么样的读者,对小说这样的长篇作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对重复以及因重复而产生意义的识别来达到理解的。”④。米勒所提出的重复并非简单的故事内容的重复,而是通过重复表现一种深层意义。具体说,小说的深层结构经历了一种“圈”的形式,一个主体与回归的循环往复。其关键是透露出的一种为生存而抗争的动力。现代小说中的事件重复通常是主题的意义增殖过程——文本的情感、意义得以积累并进而抽象成为一种象征意义。余华的《现实一种》通过接二连三的家庭内部凶杀凸现了人类生存现状的残酷。海明威《老人与海》中重复出现的同大鱼搏斗的事件则成为了一个恒定的母题,启示了人生的一种永恒意蕴:生生不息的追求。在格非的《褐色鸟群》中,事件的重复表现为三个叙事的怪圈,最终不仅消解了时间还消解了空间。《最后一个穷人》无论在结构还是在语言上都运用了这一策略,形成了喜剧格调,以喜剧的形式建构了悲剧的意味。所以文本阅读时忍俊不禁,充满爆料,但读后却是一股酸楚的滋味。小说的结构简单,就是以收养三个弃婴和二个女人为线索完成文本叙事的。一个连自己都不能保障的主人公——马三多,却在不断重复收养被“公共”认为要遗弃的不道德的女人和被传统封建思想所抛弃的女婴,这在小说环境中就成了一个戏谑的对象,形成了一种反讽距离。小说除了结构的重复之外,在细节和语言上也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小说第一章写的是包干到户,分牲畜的一个情节,马三多兴高采烈从大队里拉回来了一头老牛,第二次拉回了一只独角母羊,第三次拉回一个小驴车,在动作的重复中完成了这个悲剧人物的喜剧道具。他的喜剧事件都是在这三个道具下演绎的,不配套的耕种工具,形成了滑稽的场景。小说从开始到结束,马三多一直重复着一句话:“我想要一头毛驴”,可是奋斗了30年,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一头毛驴,这不是更具有反讽性和悲剧味吗?
悲剧进入现代社会丧失了它的崇高与庄严,代替它的是生活中的平庸与琐屑。希瑟·拉夫(Heather K。Love)就认为,“悲剧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意味着苦难成倍增加,而遭受苦难的原因却变得越来越模糊。”⑤。不断重复既是喜剧的手段,也是形成悲剧的手段。主人公重复犯相同的错误(至少是在别人看来)使马三多的生活越来越窘困,他的生活与现实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愚、拙的性格特征逐渐在加强,反讽的意味也在不断递增,悲剧性也就不断强化了。
其次,《最后一个穷人》的现代性还表现在中心人物的选择上。南帆指出:“文学时常对于‘傻瓜’、‘疯子’、‘白痴’表示特殊的青睐,例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鲁迅的《狂人日记》,或者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个世界的许多异常现象已经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可,以至于只有某些特异的眼光才能发现问题。如果说,那些高踞云端的思想家、哲学家具有一双洞悉一切的慧眼,那么,另一些‘稚拙’的追问也可能甩开种种世俗的成规,返璞归真——许多时候,思想家、哲学家与‘傻瓜’们并没有多少区别。”⑥马三多就是这一画廊中的人物形象之一,他不同于《尘埃落定》中的土司二少爷,土司二少爷带有宗教的神秘色彩,是那种“大智”者的类型;也不同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狂人具有疯癫性和批判性。《最后一个穷人》中的马三多是一种“拙”,是一种不合时宜,是与“聪明人”相对应的“傻子”形象。他不懂社会游戏规则,不圆滑、不世故,敢说敢言,无知者无畏,能够突破世俗的樊篱,做出一些世人看来滑稽的事情,但这正是当下社会所丢失的本真。比如:马三多种洋芋这一事件,本来“沙洼洼”这个地方就干旱少雨,加之生态的破坏,缺水日益严重,马三多没有生产工具,只能把种小麦改为种洋芋,可是这一年别人都绝收了,只有马三多丰收了。这不是因为马三多有“先见”的智慧,而是以他的“拙”质疑了人们习惯于从众思维的“合理性”,顺应了气候的规律。这就是傻子形象的主题意蕴。
再者,马三多形象的多义性还表现在他的批判性上。对他来说,外界变化如清风过耳,丝毫不能撼动他静止凝固的心灵。除了放羊、种地,他不接受任何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这是一个由自然本能、简单常识与淳朴道德组合而成的人物,他或许符合自然人性的理想,却完全不适应现代化的时代。这样,立足于马三多的农民道德与智慧,反思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带来的文明病,就不免有失偏颇,缺乏强有力的历史理性的支持。毕竟,以贫穷自傲并不能成为道德与智慧的强心剂。如果道德与智慧必须付出贫穷的代价,那么,这样的道德与智慧也就完全与现代性绝缘,没有丝毫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雷达在《牧羊人的两个世界——谈谈王新军的小说》一文中指出:“王新军的小说有一定的丰富性和独异的地域色彩,但看多了也会发现,其创作潜藏着某种局限性、封闭性,他的乡村世界我们渐次熟悉,觉得未知因素在减少,审美形态上的重复却多了起来,对象和写法有模式化之虞。王新军面临开拓新境的挑战。”⑦《最后一个穷人》无论在叙事的长度与难度上都应该是一次挑战,是他熟悉领域内创作的一次蜕变,既保持了他审美风格的古典性,又是对小说现代性的成功探索。我们希望王新军走得更远。
王明博 兰州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王新军,《最后一个穷人》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8年版
②李建军: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J].朔方,2004.(4) 第68页
③李继凯:文学视野中的最后景观[J].上海文学,1996(4)
④J.Hillis Miller.Fiction and Repetition[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versity Press,1982.(118)
⑤Heather K.Love.“Spectacular Failure:The Figure of the Lesbian in Mulholland Drive”[J].in New Literary History,2004,(35).
⑥南帆:良知与无知——读范小青的〈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当代作家评论,2008(1),第8页。
⑦雷达:《牧羊人的两个世界——谈谈王新军的小说》,上海文学,2005(9),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