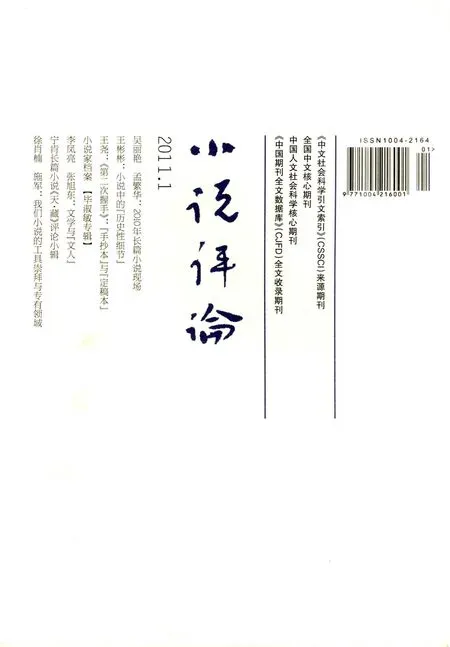感性生活的彰显与理性意义的建构——2010年短篇小说创作巡礼
洪治纲 陈 霄
感性生活的彰显与理性意义的建构
——2010年短篇小说创作巡礼
洪治纲 陈 霄
近些年来,围绕着“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文艺理论界一直在试图重审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其中,让人尤为注意的是,不少学者开始明确强调感性的美学意义,甚至提出“新感性价值本体”,并以此作为“日常生活美学”的核心,其理由是:“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系于生活行动本身的实际发生和满足,而日常生活的美学趣味则决定于这种发生和满足之于人的实际生活的感性意义。对人而言,正是在感性意义的领域,日常生活才有其充分的美学阐释价值——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这一美学阐释价值的具体呈现。”①尽管我们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还存有疑虑,但是,就突出感性本体的美学价值而言,我们觉得颇有意义。
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理性美学,确实无法有效地阐释越来越丰富的艺术发展。尤其是通过理性建构起来的各种自律性理论,正在成为艺术自身发展的羁绊。为此,从实用主义美学出发,重新梳理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审视生活自身的感性价值,不失为一种更加灵活的思维。二是文学艺术的具体实践,也在向日常生活的感性层面不断倾斜,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回避理性意义的深度建构。②尽管这种感性化的创作倾向,也存在着诸多的潜在危机,譬如崇尚后现代式的游戏思维,消解创作主体的自觉意识,推崇时尚化的惯性表达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在本质上取消艺术创作的价值追问,而是将审美价值由原来单一的理性意义,进一步扩充到感性层面上来,即,让我们重新认识艺术作品的价值并非只是建立在作家深邃的思想之上,同样也建立在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把握与精妙传达之中。换言之,捕捉、品味并有效传达生活自身的内在肌理,展示感性生命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亦是艺术的审美价值之所在。
当然,要全面厘清感性本体的审美价值并非易事。因为它在回归生活本身的过程中,很容易滑入世俗主义甚至是庸俗主义的泥淖,使文学艺术越来越忽视对人类理想的关注,对形而上的存在境遇的叩问。因此,就文学而言,确认感性化写作的意义,不是完全回避作家的理性思考,也不是认同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表象化复制,而是通过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种种情境和意味,确认创作主体的审美发现和感知能力,恢复文学应有的艺术灵性——因为太多的作品常常缺乏话语表达上应有的鲜活性和丰富性,只留下所谓的思想意义在“裸奔”。
我们之所以在此强调有关感性化的审美价值,是因为近些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同样越来越重视对感性化生存的审美表达,越来越重视彰显生活本身的丰富肌理,越来越强调普通平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内心感受。如果单纯地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有些作品的内涵可能并不深刻,亦不见得丰厚,但是,它们在叙事上的灵动与鲜活,机智与精巧,以及对细微生活的敏锐捕捉,对生存况味的精心演绎,却让人回味再三。我们认为,这同样体现了作家的审美发现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甚至印证了“感性本体”的某种审美价值。
一
在2010年的短篇创作中,让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这样一批充满了感性化写作意味的作品。如苏童的《香草营》、铁凝的《春风夜》和《1956年的债务》、薛忆沩的《母亲》、洁尘的《酒吧》、迟子建的《五羊岭的万花筒》、王秀梅的《关于那只纸鸽子的后来》等等。这些短篇不见得有多么复杂的思想内涵,也不见得有多么丰富的人物性格,但是,作家在处理人物关系时,常常醉心于描摹各种微妙的心理状态,细腻而又鲜活地凸现那些难以言说的生存况味,从而使叙事在细微处见精神,在平庸中见人性。读这些作品,常让人想起奈保尔笔下的《米格尔大街》,或者汪曾祺笔下的“高邮”,虽然少了些风土人情,但同样的饱满,丰盈,感性,且耐人寻味。
苏童的《香草营》以一个婚外情的故事作为依托,巧妙地演绎了两个不同身份男人之间的内心之战。梁医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主刀医生,又是市政协委员,显赫的社会身份使他和药剂师情人的约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经过一番精心设计,他租下了香草营的一套房子作为约会之地,不料却被住在鸽棚里的房东小马悉知全情。于是梁医生迅速退租房子,引起了小马的高度不满。小马的不满在于,梁医生说好租住一年,结果只租了两个多月,所有房租只够他更换了房内的热水器等设施,对方颇不讲信用;而梁医生的郁闷在于,小马根本没有说清自己会住在窗外的鸽棚里,不仅毁了他与情人的关系,还将自己的隐私落在了小马的手里。所以,当身患绝症的小马频频要求见梁医生,梁医生以为小马的讹诈行动已经开始,其实小马只是希望梁医生帮助自己当上市里的信鸽协会秘书长。小说的精彩之处,并不是梁医生对小马的误解,而是误解里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身份信息和人格差异——它既使梁医生意识到底层人群的精神魅力,亦让他重审了自己卑微的灵魂。
铁凝的《春风夜》叙述了一对常年分居的夫妻短暂的一次晤面,从头至尾都弥漫着某种特殊的温馨。在叙事层面上,作者并没有着力书写俞小荷的生活之苦,而是将沉重的家庭负担分解成若干个信息碎片,有机地置入夫妻相会的过程中。常年开着货车奔波在外的王大学,患有严重的腰椎病;女儿在北京读书,费用不低;婆婆隔三差五地来电话,要为七大姑五大姨“借钱”……这一切,都足以让当保姆的俞小荷不堪重负,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心烦意躁,而是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与丈夫相会的幸福感里。因为种种原因,尽管他们无法相拥而眠一夜,但是围绕着看病、吃饭等庸常事情的交流,那种以沫相濡的体恤和关爱,却始终回荡在人物的心里,也彰显了整个小说如沐春风般的叙事韵味。作者的另一部短篇《1956年的债务》围绕着父亲数十年前的五元钱债务,同样生动地演绎了万宝山父子两代人的丰富心理。
薛忆沩的《母亲》动用了一种极为别致的视角,叙述了一位中年女性隐秘而又无助的情感危机。常年在外工作的丈夫,像时钟般每周回来一次,随着家里铁门的金属撞击声响起,团聚与分别都成了机械性的生活循环。而一次偶然的小区活动,却让“我”看到一对父女异常甜美的场景,尤其是那位温文尔雅的年轻父亲,不仅让“我”心中已消失多年的“羞涩”再度泛起,而且“那种绝望的羞涩令我疲惫的胸脯鼓胀起来,令我窒息”。在这种无法遏止的幻觉冲动下,“我”一次次窥探那位“父亲”,渴望与他擦肩而过,犹如经历了“另一个星球的传奇”。作者以极为细腻的笔触,缓缓呈现了女主人内心深处的情感煎熬,它耽于幻想,止于理智,既是“我”对青春的一次凭吊,也是“我”对幸福的另一种感悟。
与《母亲》不同,洁尘的《酒吧》则生动地再现了一群中年女性对于情感的排遣方式。经历过海誓山盟,也经历过爱恨情仇,所谓的纯洁之爱,对于“我”、林朗和小夏来说,似乎已成为遥远的往事。于是,两性之间的游戏,成了她们打发情感生活的主要手段;于是,酒吧里的嬉闹,成了她们填充内心寂寞的暧昧之地。她们看起来没心没肺,无所顾及,甚至带着些许的放纵。然而,当“我”的前男友汤力为“很有派头地”出现在面前,“我”还是涌起了许多难以言说的酸楚,有眷恋,有感伤,也有隐痛。或许,这就是当代都市人的情感状态,每一个都在拼命寻找“在路上”的新鲜和刺激,却很少顾及由此而带来的绵绵之痛。
迟子建的《五羊岭的万花筒》通过精密而又练达的裁剪,从容地讲述了一个异常繁复的故事。小豆与德顺的情感纠葛、小豆与小猫金霞的依恋、德顺家庭的重负、血缘关系的毁灭……所有这一切僭越伦理的人情世故,像宋翎手里的那只万花筒一样,都被作者轻松地控制在一个小小的饭馆里。从“德顺饭馆”到“小豆饭馆”再到“德翎饭馆”,从马马虎虎到顾客盈门再到日渐衰落,这个小饭馆的变迁,既是德顺命运的写照,也是小豆人生的隐喻。情感和意愿虽然抗不过强大的伦理和吊诡的命运,但终究让他们的生命绽放出一段超越世俗的华彩。迟子建的魅力就在于,她总是能够从那些最为庸常的人物内心深处,不断地析出他们超功利、反世俗的人性光泽。这种光泽,每每附着于尖锐的痛感之上,却又显得无怨无悔,令人敬慕。
张惠雯的《我希望我是美丽的》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道出了一位女性同自卑的艰难抗争,以及对美丽的殉道式追求。“我”因为左脸患有先天性的“血管瘤”,自幼就被人嘲笑为“鬼脸”、“阴阳脸”、“半边脸”,并因歧视而陷入自卑的深渊。辍学,开店,嫁人,育女,“我”看似找到了人生的归宿,然而这一切只是屈辱和伤痛在命运上滑行的结果,“我”的内心依然执着于改变脸面,让女人的美丽获得真正的绽放。在这份艰难的守望中,家庭的破裂和父母的不解,都不曾改变“我”的决心。这种决心,不是单纯的虚荣,而是生命的自我确认;不是僵滞和固执,而是坚韧与反抗。此外,在本年度里,她的短篇《良民周三》对失地农民生存境况的叙述,《墓室与焰火》对反常生活的非理性探讨,也同样别有意味。
王秀梅的《关于那只纸鸽子的后来》看起来是在叙述一次无疾而终的网恋,但作者通过精巧的结构设置,将曾经的游戏与现在的真情、受辱的记忆与漫长的确认揉合在一起,以男女相见不相识的方式,传达了各自隐秘而又酸楚的情感历程。此外,像付秀莹的《花好月圆》、滕肖澜的《星空下跳舞的女人》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与上述作品稍有不同的是,一些更为年轻作家同样也从感性的生存出发,并致力于让人物敲开由理性秩序所构筑的坚硬的现实外壳,追寻那些看似庸常的生活内部所包裹的各种丰富的生命情态。但是,他们似乎完全不在乎对作品思想意义的理性建构,只是确保创作主体对个体生存感受的特殊迷恋,对隐秘生活的特殊敏感。因此,他们常常让叙事辗转于各种无序而又微妙的生存冲突中,着力展示人之为人的某些幽暗的、甚至是非理性的精神冲动。像盛可以的《白草地》、徐则臣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朱日亮的《氓》、朱文颖的《花窗里的余娜》、魏微的《姐姐》、王手的《市场“人物”》、张悦然的《一千零一个夜晚》、高君的《郁达夫的情书》、朱辉的《止痒》、徐东的《叫瓷的女人》等等,都是如此。
在《白草地》中,盛可以讲述了一个职场青年纷乱而又无奈的生存际遇。那个叫武仲冬的外企销售员,终日奔波在客户、家庭和情人之间,像一只迷惘的苍蝇,四处乱飞却又免不了常常撞墙。他与多丽的虚情假意,只是为了福斯公司的那份大笔订单,结果多丽已离开了这家公司;他与玛雅情浓意厚,结果玛雅是个仇恨男人的女权人物,给他长期喂进了雌性激素;妻子对他虽然不错,但更多的是醉心于网店经营……在这些理不清又握不住的生活之网中,他左冲右突,越闯越乱,最终辞了工作,也毁了身体。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很难确定作者要表达什么,所有的叙述,似乎只是在印证这个缭乱的时代对卑微个体的身心侵蚀。
徐则臣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也是如此。旅途中一场难以控制的咳嗽,让他和一个陌生的女人相识,由此牵出了彼此的婚姻生活。在若即若离的叙述中,由“宅男”而变成终日奔波于旅途中的他,时时牵挂着那个等待丈夫归来的她。不料数载之后,她等回了丈夫,婚姻却出现了危机。在最后一次会晤中,他和她同病相怜,把酒互诉,甚至暗生情愫,但最终还是让理智拉开了彼此的距离。这里,作者似乎是探讨脆弱的现代婚姻,又仿佛在寻求生活的稳定感,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永远是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朱日亮的《氓》则叙述了一个极其庸常的情感故事。那个并不招人喜欢的许家乐,虽然心地不坏,但缺少男人的阳刚之气。可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却与漂亮的梅清产生了瓜葛,继而又因嫖娼被抓。从校长到“我”,都满怀希望地帮助他解决个人问题,而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卑微者也有自己的活法,尽管这种“活法”难以适应常人的观念,你却无法轻易地改变,更无法随意地剥夺。
朱文颖的《花窗里的余娜》和魏微的《姐姐》都着重于人物关系的探讨,但在具体的叙述中,作者都没有将这种关系推向一种明确的张力结构中,而是刻意将“关系”进行模糊化处理,让叙事在扯扯拽拽中呈现人物的生存状态。其中,《花窗里的余娜》叙述了两家三代人的关系,但两家之间的正面交流并不多,更多的只是“我家”对余家的观察、猜想和议论。作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鲜活地展示了一代代市民的复杂心绪,有嫉妒也有自足,有向往也有好奇,有平衡也有失落,但终究还是“晃了一晃,就过去了”。《姐姐》叙述了姐弟之间的特殊情感。面对青春四溢的姐姐,懵懂的弟弟常常是“一边要顾着自己玩耍,一边还要照看姐姐,他生怕她上了坏男人的当,被人调戏,诱奸,或是被拐子带走”;当姐姐进入哭笑无常的恋爱季节,弟弟则摆出“小大人”的架势,抬头看着空气说:“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以后少来往,现在合家老小为你操碎了心,你好歹也得替我们想想。”当姐姐出嫁后每次回娘家时,弟弟总会问“他对你还好吗?”这种渗透着血缘亲情的关系,既隐含了某种伦理的意味,又彰显了男儿的血性。它是生活的基石,也是生命的依靠。
张悦然的《一千零一个夜晚》借助了“穿越小说”的某些艺术思维,通过少女“我”与杜仲之间奇特的肉体交流,从而透视了这位与父亲同代且异常委琐的男人失败的一生。它具有强烈的反伦理意味,也颠覆了爱情的神话,肉体的存在对于“我”来说,只是打开别人往事的通道。尽管杜仲的人生像破败的风景一样掠过自己的眼前,但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情感波动。“我”只是沉迷于这种窥探的游戏,而身体仿佛在“我”的意识之外。王手的《市场“人物”》叙述了一个在市场里捡拾垃圾的女人的情感外遇。那个叫李美凤的女人,远离了丈夫和孩子,和一个同样捡垃圾的男人同居于公厕的阁楼上,没有道德伦理的折磨,也没有你死我活的冲突,相互照应,彼此取暖,这就是他们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市场里所有的店主都知道他们的隐情,但大家一律心照不宣,甚至小心翼翼地帮他们遮掩。后来,李凤美的丈夫来了,但战争并没有爆发,一切平安无事。这里,作者试图穿越一种纯粹的价值评断,展示底层人群特有的生存逻辑。
高君的《郁达夫的情书》通过一种分裂性的叙事,让吴克沿着理想的爱情和现实的欲望缓缓滑行。身为文化馆的小干部,吴克每天都在办公室里抄录郁达夫的情书,让那场轰动一时的浪漫情爱沿着自己的灵魂飞翔,而在现实生活里,他却迫不及待地与并不熟悉的董平同居起来,让干渴的身体寻找最大的满足。吴克当然希望理想与现实能够交叉,形成一条完美的轨道,结果董平却掏出了两根当年做三陪时被嫖客使用过的鞋带,这两根似曾相识的鞋带,终于让吴克彻底崩溃。在这个时代,爱情早已被欲望践踏得面目全非,而欲望,也只能靠不断的刺激,才能膨胀起来。这种生命形态,与其说是物欲的必然结果,还不如说是信念沦丧后的代价。
此外,像朱辉的《止痒》、徐东的《叫瓷的女人》等短篇,也都在彰显这种审美趣味。它们极少突出创作主体的某种价值取向,只强调人物“在场”的生命状态,而且这些人物本身,也很少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和目的。面对纷乱无常的现实,他们甚至以更加纷乱的生存方式来对待。
三
与感性生活的极力彰显有所不同,在2010年的短篇中,冉正万的《纯生活》、徯晗的《黎明之刃》、钟求是的《最童话》和《谁是爷呀》、东君的《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范小青的《生于黄昏或清晨》和《接头地点》、张玉清的《地下室里的猫》、周瑄璞的《隐藏的力量》等一批作品,则体现出一种较为浓厚的现代意味。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们不再满足于感性化的生存,而是带着强劲的理性思考,由庸常生活入手,将笔触探入各种复杂的人性内部,层层剥离那些表象化的现实形态,凸现了各种极为独特的生命情态或人性面貌。
冉正万的《纯生活》带有某种明确的寓言性质。它非常巧妙地展示了人对宿命的恐惧。这种恐惧,不只是来自死亡本身的无法抗拒,还来自死亡方式的宿命式轮回。姑父的祖辈意外地拣回一只山魈,养大之后不仅能说各种人语,谙悉人心,而且异常害羞。为了阻止它与野外山魈的交配,主人一次刻意的破坏行为,终于让这只山魈含羞自杀,同时也使主人遭到野山魈的攻击。从此,姑父的祖辈总是因腿痛而死,且代代相传。这种因果报应式的惩罚,给姑父的整个家族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特别是姑父出现腿疾之后,他担心的不只是死亡本身,还有那种永无止境的报应和惩罚。所以,姑父锯掉了病腿之后,并不觉得悲伤,反而欣喜不已,因为他不仅成功地反抗了死亡,还成功地颠覆了宿命式的惩罚。他的儿子和孙子,同样也对这种成功的反抗表现出巨大的乐观。这种乐观,看起来匪夷所思,却是人对“活着”本身的一种特殊注视,也是人对命运的顽强反抗。
《黎明之刃》在直面底层人群的生存境况时,并没有直接书写他们的外在苦难,而是由特殊的工种入手,借助“我”的视角,巧妙地转向对人物精神的探寻。作为屠宰场的杀牛工人,丁勇和李健在每天凌晨踏上公交车之后,从来不坐在座位上,因为担心身上的血腥气带给他人不适;他们不吃牛肉,因为看到太多的牛在死前的绝望挣扎;他们渴望爱情,但屠宰工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无法与异性正常交往。于是,同住一室、面对共同命运的两个青年人,渐渐地有了同性间的暧昧。而这一切,又因为丁勇的意外身亡,使李建陷入一种绝望的回忆。在强悍的命运面前,两个强悍的屠牛青年,最终都败下阵来,却无法诉说,亦无人知晓。
钟求是的《最童话》则动用了极致性的叙述手段,讲述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恋情。它有些凄美,有些感伤,有些“不思量,自难忘”的无望。李约爱上了左岚,正在热恋之中,左岚却因车祸而逝。面对这场绝恋,李约无法从思念中走出来,于是在左岚的孪生妹妹右岚身上一次次寻找回忆,并由此陷入了某种情感的怪圈。不错,它是一次“最童话”的爱情,反衬了现实中早已泯灭的真爱;然而,在这场爱情童话的背后,又分明传达了一个人对既定情感进行反叛的艰难。他的另一个短篇《谁是爷呀》,以一种充满戏谑的叙述语调,展示了一种世俗化的感性生活场景。而这种场景又因为异国朋友的视角,变得更具亢奋意味。
《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是一篇非常别致的短篇。它以一个青年崇拜者作为视角,在漫长的跟踪式采访过程中,缓缓打开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的隐秘生活和内心世界。妻子、保姆、导师、学术对手,组成了一种奇特的生活怪圈和文化怪圈,使终日端坐于书房的苏静安教授并不安静,以至于最终将他逼疯。苏静安渴望拥有一方安静的天地,然而欲望化的世界早已将他的生活肢解得面目全非,随着导师朱仙田的去逝,妻子投到学术对手的怀抱,保姆欲占鹊巢的计谋实施,国学大师在学术上所建构的传统伦理,终于在现实中彻底瓦解了。于是,他将自己幻化成导师“朱仙田”了,因为只有在那个世界里,才没有世俗的纷扰,亦没有吊诡的人群。
近些年来,范小青一直致力于对某些荒诞性生存境遇的表达,且叙事越来越圆熟。2010年,她的《生于黄昏或清晨》和《接头地点》都是颇有意味的短篇。前者以真相的寻找与追问,拷问了作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在真实身份上的不确定性和多重性,以及人对自身终极确认的艰难;后者则通过一个年轻下乡挂职锻炼的经历,展示了乡村干部为了寻找致富门路的乖张行为。张玉清的《地下室里的猫》通过一只受困于地下室里的小猫的死亡,叙述了一个幼小心灵被深深伤害的过程。当女儿一天天听到对面的小猫在无助的哀叫,由同情转向恐惧,又由恐惧而产生幻听,精神几近崩溃。而为了治好女儿的心理创伤,父母却不惜将一只活猫又扔进了无人的地下室,以录下它那绝望的哀叫之音。这种以践踏一个生命来疗救另一个生命的做派,显然违背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周瑄璞的《隐藏的力量》以一种科幻式的思维,通过跟踪定位的方式,揭示了一位都市女性不为人知的隐秘生活。尽管作者在叙述视角的控制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它含蓄地呈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斑驳和诡谲。
应该说,在本年度的短篇创作中,具有一定探索意味的作品还有不少,像于坚的《赤裸着晚餐》、娜彧的《开门》、河西的《渡僧》、李约热的《问魂》、葛亮的《英珠》、吕先觉的《下河打狼》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某种荒诞或尴尬的生存状态,展示了现代人的特殊困境。但是,这些作品或在细节处理上,或在结构设置上,或在意蕴传达中,都多少存在着一些不足。
四
对现实秩序进行必要的思考与反省,展示创作主体对生存现状或历史记忆的审视姿态,一直是很多作家自觉追求的叙事目标。在这个方面,就我们的阅读视野而言,像肖勤的《金宝》、毕亮的《铁风筝》、刘永涛的《银灰色的草原》、王芸的《红袍甲》、于晓威的《天气很好》、晓苏的《暗恋者》、傅博的《城里的猫》、须一瓜的《毛毛虫》、赵本夫的《洛女》、尤凤伟的《空白》、石舒清的《低保》、郭文斌的《寒衣》等等,都是2010年度值得关注的短篇。
肖勤的《金宝》是一篇耐人寻味的短篇。郑老四家的独生子金宝,是整个县城都难觅的英俊青年,不料却得上了痴病。由于金宝意外地卷入一场凶杀案,一时鬼迷心窍的父亲郑老四,便贪婪地讹上了小镇的派出所和政府,继而又被人教唆,迅速陷入一种欲罢不能的怪圈。在一次又一次讹诈成功之后,郑老四并没有洋洋得意。尤其是看到派出所所长李春因此调动成为泡影,不久又被调到更偏远的山区,郑老四的内心很痛苦,以至于“一看到李春就心里打憷”,“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郑老四也有,而且这秤绝对半个星子的误差都没有——但郑老四只能在心头默认这结果,绝不能也不会说出来。”尽管郑老四还想在那个怪圈里死拚硬撑,结果却导致儿子金宝旧病复发,他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而一头栽倒在地。贪婪让他成为别人的黑手,贪婪也剥夺了他的所有希望。小说在一种因果报应的逻辑思维中,生动地再现了山村百姓狭隘、刁钻的心性,同时也对贪婪而无知的人性进行了戏谑性的鞭笞。类似的短篇,还有石舒清的《低保》。它着眼于乡村底层的权力意志,让村长手头的低保名单成为“人治”意愿的法码,从而导致了小集权社会的自觉形成,也反映了当下乡村社会结构中的权力症结。
毕亮的《铁风筝》是一个有关救赎的故事,既包含了他救,亦包含了自救。曾经身为特警的马迟,在一次缉捕银行抢劫犯中射杀了杨沫的丈夫,而杨沫的丈夫之所以打劫,是为了给双目失明的儿子治病。几年之后,无法摆脱伦理重负的马迟,毅然放弃了已有的女友,开始小心翼翼进入这个深受伤害的家庭,实施自己的救赎计划。但在具体的叙述中,作者并没有直接表达救赎的主题,而是通过马迟与杨沫的一次次交往,以及马迟内心的自我纠结,巧妙而含蓄地传达了救赎的双重意愿。刘永涛的《银灰色的草原》也以异常温馨的笔触,通过李尘对弟媳的一次特殊探望,讲述了一对汉人母子在哈萨克牧民中的温暖生活。因为弟弟的猝然离世,李尘希望接回弟媳和侄儿,但遭到他们的拒绝。对于弟媳和侄儿来说,草原是他们灵魂的栖息之地,哈萨克族特有的文化是他们精神的归依。当李尘再度深入草原深处,他所看到的,不只是弟媳和侄子的自由生活,还有哈萨克牧民们善良与诗意的生存方式。
王芸的《红袍甲》通过父子两代人对传统戏剧的不同理解,反映了文化的变迁和审美趣味的变化所导致的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它既是对传统民粹的一次凭吊,也是对物欲现实的一次无奈的抗争。在父亲刘玉声的眼里,演戏是一种神圣的事业,与谋生无关,当儿子要借关公戏服去参加商业庆典时,刘玉声暴跳如雷,认为这是亵渎了“圣人戏”,致使父子冲突加剧。尽管后来病重的父亲与儿子握手言和,但感伤和无奈并没有从父亲的心中消失。于晓威的《天气很好》通过一种心理化的叙事,非常细腻地展现了何锦州被林光不断胁迫而犯罪的挣扎过程。在这种艰难的挣扎中,他不想伤害朋友的义气,不想失去曾经的恋人,不想再陷罪恶的深渊,也不想让关心自己的警察老刘失望,于是,在跟随林光再次打劫之时,他选择了报警。令他意外的是,老刘却因为“嫖娼”被停职审察。生活是如此的无奈,一切都如此的不可掌控,何锦州只好面对寒冷的雪天,一次次重复着“天气很好”,以此来排遣心中的迷惑。
晓苏的《暗恋者》通过大学老师傅理石与进修学生李柔的暧昧关系,讲述了师生之间的不伦之恋。由于李柔太像当年自己的中学老师、暗恋对象温如娟了,所以傅理石总是寻找各种借口,不可遏止地接近李柔,而李柔之所以从南昌来到武汉进修,也完全是因为自己与学生王川之间的师生之恋。傅理石与温如娟、李柔与王川、傅理石与李柔,这三对师生之间的隐秘情感,环环相扣,又纷乱交叉,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叙事结构。傅博的《城里的猫》围绕着一只突出其来的老鼠,对城里的猫与乡村的猫进行了饶有意味的比较式叙述,当然,在叙述的背后,凸现出来的依然是人心。郝嫂的财喜在安娜娜家里所受的屈辱,其实也是当今的底层人在上层社会里常常受到的伤害。
同样值得一读的,还有尤凤伟的《空白》。它围绕着一段录像带中的“空白”,撕开了隐秘的官场秩序,从而让“被录者”局长与“录像者”秘书之间,因信任危机而出现了各种微妙的冲突,尽管这种冲突最终被巧妙的化解,但是,每一个当事人都经历了一次如履薄冰的惊魂体验。须一瓜的《毛毛虫》则以回忆性的笔触,反思了文革时期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就像院子里时常掉落的毛毛虫,让人胆战心惊却又猝不及防。赵本夫的《洛女》通过拾荒老人对捡拾而来的洛女的抚爱,在一种传奇性的叙述中,展示了洛女耐人寻味的个性。鲁敏的《铁血信鸽》试图重审一种肉体与精神的关系,虽然作者在叙述上没能很好地克服理念化的痕迹,但仍然展示了当代人对理想生存的一种向往。
洪治纲 暨南大学中文系
陈 霄 暨南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王德胜:《回归感性意义——日常生活美学论纲之一》,《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②关于此点,本人曾在《增量的文学现场与感性主义的兴起》(《文艺争鸣》2010年第8期)一文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