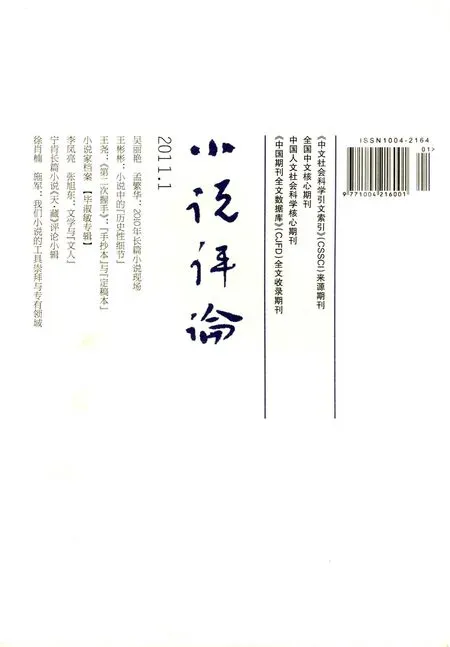蕴藏着一个未来的惊喜
——2010年短篇小说扫描
贺绍俊
蕴藏着一个未来的惊喜
——2010年短篇小说扫描
贺绍俊
2010年的短篇小说从数量上说仍然是高产的,从质量上说似乎让我们很难有自信说出特别硬气的话。也许这符合文学创作的常态。它能够在一个相对的高度上平稳地滑行,这就是很让人欣慰的事情了。相对的高度,自然是相对于以往的年份而言的。因此,翻检2010年的短篇小说,既不会让我们惊喜异常,也不会让我们大失所望。或许它还蕴藏着一个未来的惊喜。
一年下来所收获的短篇小说自然是风格各异,如果要说到它们的共同点的话,当代性也许是最突出的共同点。事实上,当代作家始终就没有辜负“当代”这个称谓,他们对现实问题有着敏锐的触觉,总是站在当代的前沿进行思索,因而他们的故事具有强烈的当代性,他们所表现的情感也同样具有强烈的当代性。作为短篇小说,表现当代性其实难度更大,因为它的当代性不能够靠仅仅呈现当代生活的现象来实现的。短篇小说作家一定要对当代生活有所思索有所领悟,他要凭借自己的独到发现来构思短篇。肖勤的《金宝》(《民族文学》第8期)就是一个例证。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上访的故事,它或许会被批评家归入到底层文学的范围。小说作者的确关注的是底层的问题。底层文学叙述中大致有两种姿态,一种是民粹主义的姿态,将底层神圣化;一种是启蒙主义的姿态,通过底层反省国民性问题。但作者并不是一般化地站在底层立场上为社会的弱势者说话,也不是对底层表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激情。她把视点聚焦在金宝这个人物身上,金宝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伤害。派出所野蛮抓走他,把他吓傻了。他的父亲郑老四为此不断上访,父亲看似是为了儿子,但最终伤害的还是儿子。当已经恢复正常的金宝被一再的上访所刺激又变得不正常时,郑老四的身心也崩溃了。上访是中国的特殊社会现象,上访甚至发展出了上访的中介者和经纪人,说明了上访这种现象的复杂性。卫鸦的《天籁之音》(《山花》第2期)也是写底层的,小说截取的只是两个民工在建筑工地结束最后一天工活的场景。但这场景是如此的令人震栗。范小青的《接头地点》(《北京文学》第7期)所讲述的故事绝对是当代性的,大学生马四季响应政府号召,报名去当村官。我们在新闻里面了解到这一新鲜事物。但范小青却将这一新鲜事物与乡村非法出卖土地的匪夷所思的事件对接了起来。这才是一个思想敏锐的当代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巧妙的“接头”!铁凝的《1956年的债务》(《上海文学》第5期)和刘庆邦的《到处都很干净》(《北京文学》第1期)都涉及到饥饿的问题,但立意各自不同。《1956年的债务》塑造了一个生动的吝啬人形象。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是吝啬人形象的典型,但葛朗台吝啬得让人们憎恶,而铁凝所写的这个吝啬人却是吝啬得让人心酸,因为我们从这种吝啬中读出了时代对人的挤压。但铁凝的立意并不在于写吝啬,她通过一笔债务,对比了两个时代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自然是物质上的,今天的物质丰富程度是当年的饥饿时代完全不可比拟的,然而在铁凝的叙述里却隐含着一个质问,质问今天的时代,虽然物质丰富了,却是不是遗漏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刘庆邦的《到处都很干净》直接写到了饥饿时代的关乎饥饿的故事。但刘庆邦的立意更加诡异,它与饥饿时代无关,而是与人的欲望有关。在饥饿难耐的时刻,女性想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一点挽救生命的食物,但男人告诉她,现在谁还干那事,谁干谁死得快些。于是我们会想到一句古训:“饱暖思淫欲”。一个淫字,意味着中国传统道德把性事看成是不干净的事情,刘庆邦在这篇小说中以一个精彩的故事告诉人们,中国传统道德是饥饿时代的道德,饥饿时代什么都没有,“到处都很干净”,所以连人的欲望也“干净”了。或许作者背后还有话:今天我们到处都不“干净”了,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盛可以的《白草地》(《收获》第2期)应该说是一篇带有强悍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两位受害的女性联合起来,不动声色地惩罚了玩弄她们的男人。故事装置在一个侦探故事的构架里,使得小说更加具有可读性,而作者采用男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叙述中流露出男人的自得和不可一世,这是一种男权中心的叙述,这种叙述恰好与男人最终的落败构成了极大的反讽,于是我们会感到作者盛可以站在背后露出狡黠的微笑。于坚是一位诗人,其实诗人来写短篇小说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短篇小说需要有诗意的滋润。于坚又是一位思想非常敏锐的诗人,他的诗歌直接面对现实发言,如他的成名作《零档案》,具有极强的思想穿透力。《赤裸着晚餐》(《人民文学》第5期)是我读到的于坚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他写小说俟如他写诗歌一样丝毫不掩饰他对现实的咄咄逼人的追问,在这种追问中一个诗人的高贵便显现了出来。于坚从房地产这个最让公众愤怒的社会问题入手,引入到个人生存空间自由的问题,充满了思想的锐利性。我还要特别提到余德庄的《秋勤的蜜月》(《芒种》第6期)。这是一篇平实的小说,没有玩半点花哨和形式,叙述也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述。小说写秋勤与丈夫黎嵩度蜜月的故事,黎嵩是消防特警,这一特殊的职业就决定了他们的蜜月不会是轻松惬意的,一次又一次的突发事件和紧急任务,打破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度蜜月的计划。显然,这是一篇歌颂奉献精神的小说。有人会觉得这样的主题太陈旧,也太“主旋律”。余德庄的这篇小说则告诉了我们,写好“主旋律”并不容易,因为写“主旋律”很容易落入模式化之中。比方说,为了塑造一个人物的奉献精神,就要写这个人物如何牺牲个人的感情。这篇小说却不是这样,黎嵩虽然因执行任务,不得不一再推迟度蜜月的计划。但他同时也在为弥补对妻子的愧疚而重新安排度蜜月的计划,正是在重新安排和打破计划的反复中,把一个人物的精神境界和丰富情感立体式地呈现出来了。
短篇小说更多的是与人心有关。我读到的小说中就有好几篇小说都涉及到诚信问题。当今社会的诚信危机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不能不成为作家心中的疾痛。娜彧的《开门》(《上海文学》第6期)以一个喜剧性的故事来表现诚信的问题。老实头押着一车精神病患者送到另一处地方,车上的“曹主任”几番努力就争取到了老实头的信任,于是一车的精神病患者都逃跑了。老实头被逼得不老实起来,把一群想占便宜的人骗上车,开到目的地交差了。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你老实,你就会被疯子耍弄;你要办成事,你就要变得不老实。于晓威的《天气很好》(《小说界》第3期)则揭示了当今社会在诚信问题上的荒诞性。卧底,首先就涉及到信任的问题,没有对人的信任,是不会把人安排到敌方去卧底的。显然,狱警老刘对何锦州是信任的,他坚持给何锦州办了假释。一个警察能够信任一个罪犯,这种信任应该是建立在道德共识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同样身负卧底重任的老刘却不能得到他的组织的信任。事情的荒诞性就在这里产生了。老刘作为警察,可以信任仍在服刑的何锦州,可他并不知道他本人并不被组织信任。服刑者可以被信任,警察反而不能被信任,这是多么荒诞的事情。于晓威曾经说过,痛苦和荒诞才会显影出立体的真实。这就是于晓威对现实的独到发现,他从来不掩饰现实中的痛苦和荒诞。但于晓威并不是一个荒诞派,他对世界仍然充满着希望,如同这篇小说,他质疑这个社会为什么缺乏信任的道德基础,但他相信,信任这种美好的精神品质并不会消失,因此面对“美丽的大雪”,于晓威说,天气很好。杨遥的《奔跑在世界之外》(《天涯》第2期)不仅关乎诚信,更关乎人心的冷暖。孙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也有不少的毛病,这样的人物在生活中显然是不讨人喜欢的。但难得的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看到谁有了难处,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总是想着要帮上一把。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冷漠,哪怕他拼命救助的对象刘老三,也对他没有半点感激之情。杨遥或许对这个世界感到了悲观绝望,于是他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奔跑在世界之外”,难道说,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就再也容纳不下孙金的善良之心,真的不再需要孙金式的善良之心?读完这篇小说,足可以让人们思索再三。施伟的《逃脱术》(《福建文学》第3期)中的魔术师也是一位孤独的人,他努力营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他的妻子、儿子以及他的同事都不把他当一回事,最终他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心是多么的累,他以极其惨烈的方式从这个世界逃脱了。
乡村叙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具强势的传统。大量的小说仍然可以归入到乡村叙述序列,但在乡村叙述强大传统的笼罩下,作家要有所突破也变得更加艰难。但尽管如此,第一年的乡村叙述,仍然有好作品。我特别要提到尉然的《小荟的菜园》(《中国作家》第9期)和甫跃辉的《守候》(《青年文学·上半月版》第5期。在乡村叙述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也越来越沉重灰暗的时候,这两位作家却以一种清新宁静的笔调讲述乡村的故事。尉然多年前曾有一篇《菜园俱乐部》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写到一个经营菜园的农民,这个菜园是他幸福的来源,他只有与他的蔬菜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滋生出幸福感。但他一离开菜园就无所适从,就成了被人愚弄的对象。陈世清不屑于去计较别人的愚弄,他把菜园当作自己的幸福王国,有了这个幸福王国,世俗的一切烦恼都可以抛之脑后。看来在尉然的文学世界里也有一个能够给他带来幸福感的“菜园”,因此就会有了他的这一篇《小荟的菜园》,这篇小说延续了《菜园俱乐部》的主题,但它显得更加纯粹,纯粹得有些像一篇单纯的儿童文学,何况小说的主角就是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在小小的菜园里获得了那么有意思的精神享受,比如他们有时安静地在菜园边蹲上一会儿,支棱起耳朵听,他们能够听到菜苗喝水的声音,听到菜苗往封里扎根的声音,听到它们在空气里伸展茎儿和叶片的声音,这是真正的天籁之音。菜园对于两个孩子来说,是一个天然的童话世界。然而大人们轻易就摧毁了孩子了童话世界。《守候》同样是以孩子作为主角,同样具有一种童话的意味。从他的叙述中,我能感觉到传统的延续,但他又给乡村叙述带来了新的因素。他写一个孩子不得不牺牲美梦,天没亮就跟着父亲到田头去干活。作者叙述到这里的时候,仿佛一脚就要踏进苦难叙述的窠臼之中,但他轻轻一个跳跃就将叙述引向一个新的空间。他写孩子内心对鬼的恐惧,以及他以装鬼的方式吓走了前来偷水的大人。这篇小说的内涵是丰富的,乡村生存的原生态,乡村伦理法则,儿童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乡村父亲对待儿子的严厉以及严厉下的父爱,这一切融合在一起,充满着开放性,远不是那些自恋封闭的“80后”青春写作可以比拟的,当然也跳出了几近模式化、社会程式化的乡村叙述,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新的乡村图景。
与乡村叙述相对应的是城市叙述。人们一直慨叹当代文学的城市叙述没有传统,至今仍不成熟,与急速扩张的都市化和现代化的现实不相匹配。其实这些年来城市叙述发展迅速,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对城市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并逐渐找到了表达自己切身体验的话语。如前面所述的盛可以和于晓威的小说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经验。另外,须一瓜和邱华栋的两篇小说在讲述城市故事上也各有特点。须一瓜的《海鲜啊海鲜,怎么那么鲜啊》(《小说界》第6期)写了一个城市小保姆的故事,是典型的日常生活叙事。保姆小陶有很多毛病,她被东家辞退也就是迟早的事了。但有意思的是,东家辞掉小陶后,却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保姆,渐渐地,他们才发现小陶的可爱之处,甚至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活离不开小陶,开始思念起小陶来:“距离一拉开,回头看去都是温温润润。”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距离拉开后,才会发现人家的长处和优点呢,我们不是在日常生活也经常犯这样的毛病吗?须一瓜以轻松的方式批评了、调侃了这种日常生活中常犯的毛病。邱华栋的《滋味与颜色》(《广州文艺》第2期)是关于城市伦理的。郑迪与章娇,分明代表着两个时代的伦理原则,不同的伦理原则决定了他们一个是新人,一个是旧人。郑迪属于旧人,他仍是以旧的伦理原则来行事的,这种伦理原则是以乡村精神为基准的,是从过去延续下来的,它强调了血缘关系,维系着家庭的稳定。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这种伦理原则行之有效。但进入到城市社会,这种伦理原则显然有许多与城市精神不谐调之处。郑迪的种种恐慌均缘于他不能摆脱旧的伦理原则的约束,不是他不想摆脱,而是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制度决定了他必须遵循着旧的伦理原则。但是,章娇就比郑迪自由多了,她放弃了旧的生活方式,因此也不必遵循旧的生活制度。章娇无疑是一个另类,她放弃旧的生活方式,也就意味着她没有一个温馨的家庭,也没有古典的爱情,甚至她也没有一个让亲情和身体安妥的避风港。更重要的是,当新的城市伦理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像章娇这样完全摆脱了旧伦理约束的新人类们,却会对那些仍在旧伦理秩序里徘徊的人们既构成极大的诱惑,又构成极大的威胁。邱华栋写了郑迪的无奈,在这种无奈中,其实就包含着一种期待,一种对新的城市伦理原则的期待。
短篇不同于中篇,不在于字数的减少,而在于它不能像中篇那样可以依赖于故事性来藏拙。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它的思想表达必须是含蓄的,内蕴的。收入本集的小说,可以看出作者在艺术性上都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韩东的《呦呦鹿鸣》(《作家》第1期)以诗人的想象讲述了一个超现实的故事。带有某种佛性,神秘性,显然是一种反现代性的姿态。苏童的《香草营》(《小说界》第3期)同样也是一篇让人们想到神秘性的小说。当小说的最后,两只脚上拴着黑布的鸽子停在梁医生的办公室窗台上时,我们会有一种感觉,以为鸽子是一个神秘的精灵,它洞悉人的隐秘内心,它以神秘的方式传递着命运的旨意。神秘性是苏童小说中挥之不去的精灵。苏童的小说极少宏大叙事,他饶有兴趣地描述那些日常生活的世事情事,但在他的叙述中我们隐隐感觉到的是一种少年特有的好奇和迷惑的眼光,他总觉得这些世事情事后面藏着我们不知晓的东西。这种东西也许就是命运。小说中的梁医生与小马完全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却因为香草营而使得他们有了一种命运的牵连。而梁医生冥冥中也觉悟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会多次出现这样的幻觉,他看到女药剂师肩膀上站着两只鸽子。两种神秘的鸽子!神秘性还需要解读吗?也许这就是苏童的小说,我们无法说破它,我们只需要在这种神秘的意蕴中去品咂。葛水平的《月色是谁枕边的灯盏》(《小说界》第6期)则是一篇诗性小说。小说的主题与乡愁有关,乡愁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的诗眼。但在全球化的当代,要从乡愁中写出新意来并不容易。这也是葛水平的这篇小说出彩的地方。她在告诉人们:乡愁之所以煎熬人心,远不是因为背井离乡的痛苦,而是不能回到故乡的文化语境之中。故乡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山山水水都化作了文化的符号。文化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阿银就被故乡这种文化的力量击倒了。这篇小说刚刚阅读时会感到葛水平的温柔一面,但读完之后才发现她的刚烈其实藏得很深,她的刚烈甚至演变为一种残酷,她残酷地将阿银和马克这一对恋人的婚姻和爱情击得粉碎,然而这不是肉体上的残酷,而是一种文化上的残酷,在作者笔下展现的是一种软暴力,一种文化和伦理上的暴力。我猜,葛水平大概是意识到单纯幸福地守着故土是不完整的,于是她写了这篇小说。月色是谁枕边的灯盏,这么诗意绵绵的句子真没想到被葛水平拿来做了小说的标题。这也说明,一个中国作家只要想起故乡,内心就难免不诗情荡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色总是与故乡联在一起的,月色照亮了人们通往故乡的心灵之路。但是,葛水平却发现,月色不是把每一个人通往故乡的心灵之路都照亮了。
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越来越成为主角。在阅读刊物时,我特别留意他们的名字。并非我对他们有偏爱,而是因为他们确实成熟起来,逐渐成为了小说创作的主力。他们的成熟是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齐头并进的。比方说,马笑泉从他步入文坛就有自己鲜明的风格,我很欣赏他正面处理残酷和血腥的方式,因为他不是单纯地呈现残酷和血腥,而是残酷和血腥背后所涌动着的英雄气概。这一特点在《师公》(《红豆》第8期)这篇小说中还保持着,然而我也发现马泰泉的一些变化。他似乎在冷峻的叙述里加进了一些温柔的成分。我想这或许是岁月的作用。岁月就像是绵绵不断的流水,性格这块顽石卧在水中,听凭流水温柔地抚摩,日久天长也会变得圆润起来。或许这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如果说,当年马泰泉写《愤怒青年》《打铁打铁》等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的话,那么《师公》给我的感觉则是他在动笔之际会对前因后果掂量掂量。因此,《师公》的叙述显得要沉稳了一些,这应该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正是因为这种成熟,他能较好地处理妥当这个在文革中发生的故事。张惠雯和付秀莹是这两年冒出的新秀,她们出手不凡,而她们两人的叙述风格却大相迥异。付秀莹的小说让我感到眼睛一亮,这并不是她所讲的故事有多么新鲜,而是因为她叙述的方式非常特别。她真像一位手法熟练的魔术师,但她不玩大型魔术,因此她用短句式来叙述,无论是她有意为之,还是她的语言习惯,总之这种句式构成了她的鲜明风格,在她的小说中一以贯之。比如《火车开往C城》(《广州文艺》第7期)的开头:“夜色慢慢降临了。我看着窗外一掠而过的田野,村庄,树木,河流,心里有一种久违的轻松。我要出趟公差,去B城。”这样的句式难道仅仅给我们提供的是故事元素吗?我们的情绪无形中就被这种句式的节奏牵着上路了。两三个字,停顿一下,让我们喘口气,停下来揣摩揣摩字句里的韵味。付秀莹的叙述似乎与今天的生活节奏不合拍。但是付秀莹的小说却仿佛是要把我们从奔驰在高速路上的车厢里拽出来,要我们在路边的青草地上席地而坐,去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阅读。她的短句式是将生活流程切割成了一个又一个场景,让我们在每一个场景面前停下来琢磨。这有点像电影中的慢镜头。在慢镜头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快节奏中一闪而过的细微变化。付秀莹所要做的事情无非是将这些细微变化定格下来,再让我们去体会这变化中的为什么。《火车开往C城》将镜头对准了一位平时循规蹈矩、生活庸庸碌碌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付秀莹以其慢思维进入到了人物内心的褶皱里,或者说,当我们放慢节奏,就会发现光滑的时间流充满了起起伏伏的褶皱。说到底,叙述不单纯是一种语言技巧,除非一个小说家是在生硬地效颦其他小说家的叙述方式,叙述方式首先体现出小说家的思维方式。付秀莹在这一年里接连发表了好几个短篇,如《花好月圆》(《上海文学》第3期)、《说吧,生活》(《广州文艺》第7期),几乎都是采用的短叙述,她的叙述方式对应着她的慢思维,她如此从容不迫地深入到事物的肌里,或许也证明她一直在波澜不惊的环境中生活。在这种状态下,她非常适合写中短篇,她也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慢思维不断地探幽入微。
读者大概会发现,在我提到的短篇小说中,有好几篇都出自《小说界》这份杂志,这并不是我对这份杂志有什么偏爱,而是因为这几篇小说都是作者为一桩特别有意义的文学活动而写的。这个活动涉及到三个国家,是由中国的《小说界》杂志、日本的《新潮》杂志和韩国的《字音母音》杂志共同举办的“中韩日三国作家作品联展”活动。这三家刊物分别是三个国家的主流文学刊物,他们各自邀约了本国一些重要作家为这次联展创作,并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同时在三家刊物上发表。三家刊物还在年底组织了三国作家和批评家展开了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我从《小说界》上读到三国作家的小说,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逐渐把我们身上的异味冲刷得干干净净,我们的共同性越来越多过了我们之间的差异性。文学对于一个国家的文明建设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加强三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和对话,从而为三国作家资源共享搭建起一个理想的平台。我以为,这一次三个国家的纯文学的出版社和刊物联合举办中韩日三国作家作品联展的行动,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行动,也是搭建这一理想平台的非常具体的行动。为这次活动的苏童、于晓威、葛水平、须一瓜、蒋韵(她为这次活动写的是一个长篇小说),也就是用他们的写作为这个理想平台的搭建作出了努力。
对小说的解读往往是多余的,因为每一个读者从小说中获得的东西不一样,而且在我的阅读中肯定遗漏了很多更精彩的作品。但最后还想说一句的是,如果你不是热衷于读故事的话,那么你最好多读短篇小说,在短篇小说中,你更多地会感受到小说艺术的意蕴。
贺绍俊 沈阳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