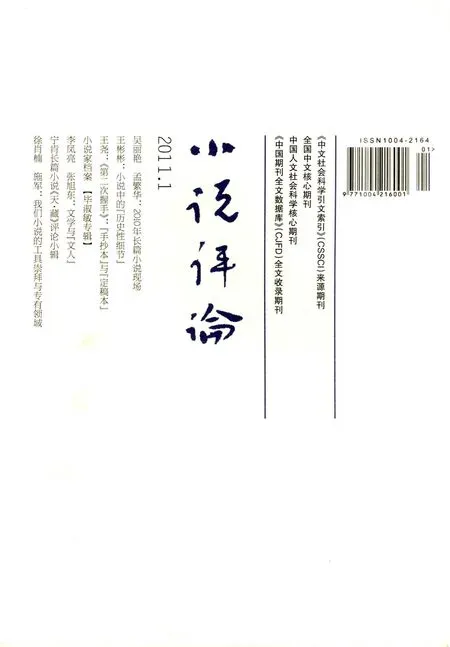文学的纹理层面和精神层面
李洁非
文学的纹理层面和精神层面
李洁非
汉字是精约的文字。尤其古汉语,一字而兼含诸义。所以常读古书的人,通常也养成习惯,以字为单位,逐字地读,而不像读现代书,一目十行也能过得去。比如《论语》有句话:“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这个“文质彬彬”一语,现代人很少不理解为“斯文”、“文弱”之类,其实大乖原意,原因就是没有逐字去读。其原意,绝非君子便有“文人气质”。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文”,一个“质”,要分开来讲。“文”也即“纹”,原本指使视觉愉悦的装饰、修饰,引申出来,指一切美的、华丽的外观。“质”刚好相反,是事物不炫于外、朴实无华于内的质地。所以“文质彬彬”其实是讲,如果人的外表和内心,或者才华与品德,能够保持相和谐、相匹配、相平衡的状态,才比较理想,这样的人,才可以视为优秀的人(“君子”)。有“文”无“质”、有“质”无“文”,或“文”胜于“质”、“质”胜于“文”,都不太好。这跟今人的理解,显然殊异其趣。
这一段开场白,与一部长篇小说有关。那是江西作家熊正良的作品,名为《残》。其实,标题只有一个字的长篇小说,历来倒也不少。单是巴金先生,就有好几部:《家》、《春》、《秋》、《雾》、《雨》、《电》。可是,拿到熊正良这部作品,尚未展开阅读之前,面对它的标题我真是很有些茫然。因为“残”这个字,不像“家”“春”“秋”之类,含义简单或者确切,而是枝枝杈杈地,有多层的意思。试予列举如下——
(一)有损毁意。桓宽《盐铁论》:“残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二)有伤害意。《孟子》:“贼义者谓之残。”(三)有杀戮的意思。《周礼》:“放弑其君,则残之。”(四)有消灭意。《战国策》:“昔智伯瑶残范、中行,围逼晋阳,卒为三家笑。”(五)有暴虐意。《论语》:“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六)有破损、余存、不全等意。毛泽东《十六字令》:“山,刺破青天锷未残。”(七)最奇怪的一个意思,居然是“煮熟的肉”。《文选·张协〈七命〉》有句:“鷰髀猩唇,髦残象白。”李善注:“残、白,盖煮肉之异名也。”不知是否从损毁、伤害等意转来,类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待全部读完,先前的茫然已化为对熊正良的一点小小的惊异——自从1994年与他相识,断断续续交往了十几年。以往对他的认识,主要在于小说叙述上绘画般的笔触,一种富于视觉冲击力的别致的呈现。这一次,忽然发现他颇精于以字存意、以字隐意。这个“残”字之选,显出了心致。这部小说意蕴之繁,本来不易单用一字囊括。可是他却一语搞定,读完小说回头再想,似乎除了这个“残”字,别的也都不合适,或不足以表其气象。
小说写了“文革”中的一段生活。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知青的遭遇,一个家庭的处境……或者,它们的混合体。具体情节就不复述了,大家可以看小说。
单就题材论,写“文革”的作品过去一直就有。“新时期文学”最初的“伤痕”、“反思”文学,一多半与“文革”有关。近年,我阅读不多,但也见过像《英格力士》那样不错的作品,从成长的角度写“文革”。总的来说,文学创作在这个题材上的收获,我个人觉得还有欠缺,或者说,在艺术上还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即便在目前的条件下。
欠缺大概来自深度。这句话好像在别处也适用,但我觉得,对写“文革”的作品来说,可能更关键一点。首先,这段历史幅度大,所谓“轰轰烈烈”、“波澜壮阔”,表面上的东西很多,人们的注意力容易被它的外观吸引,而不大能够静下心来,深入其内部,敛神屏气,细细地观察它的肌里、细胞、神经末梢这样一些方面;而这些方面,我以为才是“文革”的秘密所在,所以我还以为,对“文革”的有力的描写者,可能不是诗人,而是擅长运用薄刃进行解剖的外科手术家。其次,也跟客观条件有关,目前,指望在这个题材上出现全景式的类似于《战争与和平》之于1812年战争那样的巨型作品,还不可能,所以掘进的方向体现在一个“深”字上。深度同样可以带来力度。
比起过去的作品,《残》让人看到了更多皮下组织似的层面。这些内容,主要是通过对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生活的描写而呈现的。应该说,这个家庭在那个年代丝毫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既不是运动猛烈冲击的对象,也不属于在其中叱咤风云、深深卷入的人群。他们相当平庸,以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不论在运动过程之中,还是运动落下帷幕、成为历史之后。我们知道,当时有很多激进分子,表现强劲,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央位置。我们也知道,事后社会的目光则投向了另一些人,受迫害的老干部、名誉扫地的知识分子,甚至是因为有海外关系原来抬不起头来的家庭……这些人在“文革”中遭罪很大,“文革”后便成为俄底修斯式的“归来者”。熊正良介绍给我们的这个家庭,却从没有也不可能被社会注意,且不说“文革”中的默默无闻,即便“文革”结束,这个家庭死于非命的李玖妍以及貌似自生自灭的家庭其他成员,他们的故事也没有向社会讲述的机会。然而我们知道,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群,在中国才是无边无际的海洋。他们无辜地、甚至懵懂而一无所知地被历史、大人物、公共权力播弄着,就像狂风中漫天飞舞的垃圾碎片上下东西,然后不知落到哪个角落。这种飘落,也许不够“典型”、不足以充当修造纪念碑的材料,但是,它们是那时生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存在。
女主人公李玖妍,在“文革”开始时是一个中学生。她被历史裹挟,曾经汇入朝觐的人流。以她的头脑和教养,并不能辨识自己所为和内心。不仅这时,一直到被处决,她所走的每一步实际上都带着盲目,或者说,都是被外力所支配与驱策。生活先把她推往天安门,然后又推往“上山下乡”,继而再推往种种困难处境。她没有做出过任何选择——不单单是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主动的选择意识。她就是这样一个被生活彻底控制起来的十足的小人物。她的身上,只存在最后一点本能:也就是说,尽管不懂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当被逼到绝境时,不幸还在本能中保持着一点抵抗。就是这一点点可怜的生存本能断送了她,当她试图把这种本能表现出来时,生活给予她致命一击。
李玖妍的意义,与其说是在她那个多少与窦娥有几分相似的命运上,不如说是在于她精神的残缺不全。跟自己的弟弟——小说情节叙事人“我”——相比,她作为一个肉体生命尚保持着健全人的外表,但是,在精神上她却明显不能说拥有自我。这种精神上的残缺不全,不是指曾经拥有独立的人格,然后失去了它或交出了它,而是那种东西从不曾降临在身上。一般,人们总是谴责出卖灵魂的现象,将其视为人性的最大悲哀;其实,真正的最大悲哀,是人压根儿并没有自己的灵魂。这种情况,超乎人的本性善恶之外,根本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整体社会环境对个人精神世界加以挤占所造成。李玖妍短促的一生,正可谓如此。她的死固然可叹,但在我看来,更可叹的是直到她死,都并不明晓她的所爱、所恨是什么,她只是本能地抵抗了一下压迫与剥夺,却根本不知道抵抗的真实意义。换句话说,她的抵抗犹如落入蛛网的一只昆虫,却并不含有人的觉醒的意义。在我看来,这样一个李玖妍形象,虽然精致性、充分性与阿Q尚存距离,但其发人深省,或者说她与自己时代精神状态的关系,是可与阿Q相提并论的。
李文兵,也就是“我”,构成相同问题另一侧面的指示。较诸他的姐姐,他的形象更加显明一些——对《残》这个标题,读者首先会想到他;他是肉体上的生而残疾儿,他的双腿犹如豆芽儿,不能自己站立、行走。但正像小说一再出现、描写的“手表”那个意象所暗示的,“时间”给了这个肉体残疾者以更多可能性。他的姐姐的生命,在“手表”的某一刻度上停止了,所幸他的生命指针还继续转动。所以,当他成功穿越时间,来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发现,他成为一个寻访者、追问者,代替他懵懂殒命的姐姐去追索真相,在精神上确认发生了什么悲剧,以及悲剧怎样发生。他是肉体残疾者,也是精神幸存者。
李玖妍殒命之时,也即这个家庭解体之日。在她走向毁灭的途中,她的双亲付出极大努力和挣扎,试图保住女儿的希望。随着女儿的死,希望不再有保留的价值。他们的动物般的对于战胜和逃离恐惧的“热情”,消失了,也耗尽了。一个因为苦难而必须挺住、又因为无边苦难而毫无生趣的家庭,就此可以解散了。这一对夫妇,是一对地地道道的只想“过日子”的平俗的夫妇,他们没有条件奢论什么情意,所以不要用理想主义苛责他们。他们连最起码的“过日子”要求也从未实现,家庭对于他们,只是折磨。于是,解体了;并且在解体后不久,母亲以自尽告别了她无心眷恋下去的生活,我们由此看到“残”的另一注脚。
中国人自古以来观念中,家与国相通。儒家实践“大同”理想的步骤和顺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个人)、家、国、天下(世界)是一个延伸的关系,也是一个回溯或可逆的关系。由个人幸福而达致世界幸福,反过来,如果世界幸福,个人也应该是幸福的。今天,大家脑中都有“国家”这个概念,其实,中国还有一个“家国”的概念。家而不家,则国亦不国。熊正良没有运笔于宏大层面,他只写了一个家庭的残破,一个最最普通的家庭。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对,他观察的是细胞。
小说阅读中,油然想到李九莲案。这是我自己的联想,未向作者求证。此案之于小说,从人物遭遇到内含的情氛,影影绰绰有暗通之处,故不妨在此也有所稽引,以备参较。
此案起于“文革”,发生地正是江西。新华社前资深记者戴煌先生,曾于深入采访之后,为之成文,编入《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我们籍此覈其大要。戴煌于文中写道:
1980年秋天,拨乱反正的急鼓仍在咚咚响,江西鄱阳湖畔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割去双乳。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面此情节,任何人马上会想到张志新——案主都是女人,都被枪决,死前又都遭野蛮对待。然而,令人惊愕处却在于两案的不同:张志新死于“四人帮”倒台前一年,李九莲却在“四人帮”就缚一年多后的1977年底仍惨死如斯。戴煌历数其得罪经过,看来,李氏也是时代造就之人,热衷于政治思考,口诛笔伐,激言高论,妄谈国是,“九一三”前因反林彪入狱,后又于1975年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诸罪名,被正式判刑十五年,而服刑期间,又将矛头指向新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认为后者对毛泽东有“背离”之嫌。戴文说:
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7]六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铁道部于当月中旬下达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李九莲之被杀,正是援引了这一精神。1980年11月,戴煌到赣州采访此事时,当地领导“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代反革命’,‘即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据此不认为杀之有错。此案于1981年经胡耀邦过问后平反。时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的刘复之,在有关座谈会上谈道:
(李九莲)批评华国锋,是因为绝对相信毛主席的缘故。她身陷囹圄多年,不了解外面的实际情况。这当中有些错误,完全应该谅解她……她对小平同志的认识有错误,说了一句不恭的话,这也不算犯法。
虽然戴煌文章有所淡化,但仍看得出李九莲被杀,实以言论偏“左”,这一点应与张志新不同,也是当地领导坚信并未“错杀”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从张志新到李九莲,共同凸显了一点,亦即“因言致死”的问题。且不单如此,对言论乖于世者,恶之至极;张志新割喉,李九莲扦舌,都超乎惩罚必须之外,以示对“反动言论”的惕栗怂兢。
我不能盲言小说《残》取材于李九莲故事,但两相参照着读也不会毫无益处。因为这部作品跟以往涉及“文革”的作品相比,一个好处就在于不单纯从“受害”角度进入,而欲探讨一种全面的残缺的状况;这种状况既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李玖妍也罢,李九莲也罢,都在被残中自残,或在自残中被残。就像“文革”本身,固然摧残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但又何尝不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些残缺?
“文革”一段,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最终来看我以为将着重在于精神方面,虽然它在当时以及现在许多人心眼中是一次“社会”动荡。作为“社会”现象,它可以很快就成为过去,随着历史脚步匆匆向前,而被逾越乃至遗忘,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但恐怕并非如此——“文革”之于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关系,归根结底恐怕在于精神的层面。我们的困惑,不在于“文革”的发生,而在于为什么会发生“文革”以及“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残》是目前所见触及了这一思绪而力图有所解释的长篇小说,它使相关创作深入了不少,而且正确地显示了在“文革”这件事上,文学写作的价值比历史写作的价值来得可能更为重要些。
李洁非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