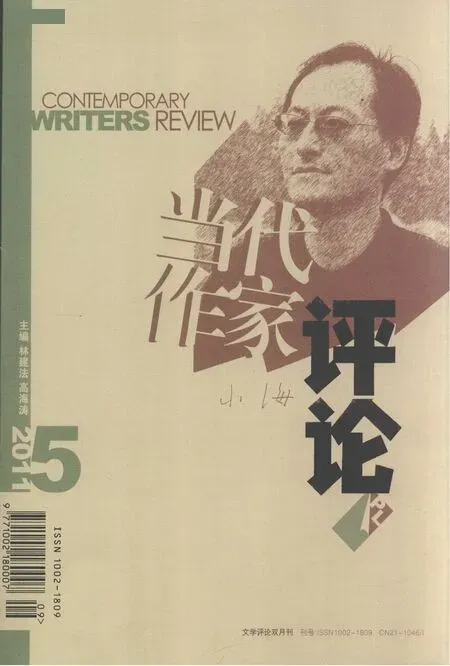两种辛亥革命史的写法
周 云
余英时在其名著《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学术有两种传统:尊德性和道问学,亦即关于价值和关于知识的传统。尊德性注重价值,讲求义理的阐发,但失之于空疏;比如在明代,义理的弘扬与阐发多依靠体悟、冥想,失去了知识的支撑。而道问学则偏重于考证,强调义理的阐发必须依据知识的整理与总结,但往往又失之于琐碎,失去方向。随着历史环境的不同,以及学术内部逻辑的演变,这两种传统交替成为中国学术尤其是经学的主流。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已经经历了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几个轮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热衷于宏大叙事,文化热席卷全国,整个学术空气更偏重于尊德性。九十年代,风气为之一转,学界的注意力逐渐从主义转移到问题,研究日趋精细,同时也渐渐失去方向。进入二十一世纪,各种主义卷土重来,新兴的网络成为主义的竞技平台,尊德性至少在声势上超过了道问学。
具体到历史研究而言,情形也略同。孔子编订《春秋》,明显地偏向于尊德性,一味突出微言大义,甚至不惜牺牲知识的严谨。明明是周天子被诸侯挟持到河阳,孔子却偏偏要叙述为“狩于河阳”,为周天子讳,是为“春秋笔法”。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秉笔直书的良史,如董狐,如司马迁。嗣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撰述,基本上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总体而言,由于学科特点,历史研究总体上更偏重考据。就算是在最为讲求理论指导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仍然存在着“以论代史”还是“论从史出”的争议;尽管“以论代史”在现实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但“论从史出”微弱的声音仍然表明这个学科及其学人对本学科传统的珍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历史专业研究人员渐次远离“主义”的指导,考据越来越成为主流,“论从史出”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先把事情说清楚”,成为专业共识。傅斯年所言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史料主义,成为当今历史专业研究的至上圭臬。但这仅限于专业领域,历史研究是极具魅力的工作,吸引了许多爱好者的研究兴趣。与专业研究人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专业人士的研究多是因为某种价值的影响,进而产生由历史证明或否定该价值的冲动。
这两种不同的对于历史研究、历史撰述的理解与实践,必然会造成相互之间的互存异议。由于非历史专业的研究者,文学或者哲学研究者居多,他们的历史研究,被不太友好地称为“文人论史”。历史学者朱学勤,就非常反对研究学术当然也包括研究历史的“文人思维”:“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这种文学化的哲学或哲学化的文学,构成大陆人文学科的先验氛围,而不是经验氛围。”
但也有人认为历史研究必须要有价值的观照,否则就会陷入烦琐考证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历史研究就会失去意义。已故的学者赵俪生即持此论。他在自传中总结自己的学术风格时说:“其一,原本我就不是个学历史的,学历史是‘跳槽’过来的,我从小喜欢浪漫主义文学,所以一生不愿被枯燥的史料捆绑住。当我读到说某位学者五十年间从头到尾把《廿四史》读过三遍时,我的即刻反映不是钦佩和仰慕,而是认为大可不必。其二,我从一接触史学近著起,就憎恨琐节考据。我看到有人考证了个‘拐子马’,就沾沾自喜得了不得;有人考证了一个浙江士子中的败类谢三宾,就有人出来捧上天;有的老师教给学生考证某人之卒年究竟在某年之十二月抑在次年之正月。我常说,我宁去死,也不做这些‘史学工作’,这没有办法。其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的最终宿营地,怕还是哲学。我爱思维。纵观我的一生,由文学而历史,由历史而哲学,历史学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过渡、一个跳板。让那些琐节考证的史学家去笑骂吧,我并不是你们那里的长驻客,正像鲁迅《野草过客》中所说的:‘我还得走。’一个声音在呼唤我。”
冒昧地揣测一下,伍立杨《中国1911》①伍立杨:《中国1911》,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恐怕也是在“一个声音在呼唤”的状态下写作完成的。当我读完这本书,就不自觉地给这本书排了队,把它排在了尊德性之列。这本关于辛亥革命的著作,创作时值辛亥革命百年之后。辛亥先贤追求的诸多价值,当时还属空谷足音、曲高和寡,但到今天,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普遍的信仰。同时毋庸讳言,在信仰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落差。这既是先贤的遗憾,又是现实的沉痛。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活动,各地声势极大,惊天动地,且都标榜继承与弘扬。但继承什么,弘扬什么,仍然还是个问题。而《中国1911》一书,通篇不提继承与弘扬,但无言以言,书中处处皆是答案。
在《中国1911》这本书中,伍立杨以极为鲜明的立场、犀利的笔锋,几乎用每一个字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重申着这些价值。辛亥革命的意义,在百年来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得到了高度的认可,但近三十年来,对于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党人,不断出现这样那样的非议,比如“告别革命”。对于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论调,伍立杨完全不能同意,甚至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愤怒:“今日常见懵懂文士,纵笔使气,责备孙中山、黄兴,以为他们只要不革命,静待清廷立宪,中国就有明朗前途,以为中国近现代的板荡,尽是孙、黄造成。其实,如此见识,非仅近视、直是瞽者,或为矮人观场,全无见识”。何故?是因为清政府专制之酷烈,“晚清的统治者却是一个从来没有过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度,民众面对的是铁杆专制极权的统治者,而且他们所维护的体制,正是其赖以生存和剥夺的寄生的制度,是一个暴力成性血腥屠杀过民众的朝廷,是一群把暴力看成真理的统治者。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环境下,搬进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那结果只能是不断地将绵羊填进狼群”。作者确信,正是由于清政府专制之苛毒,所以只能用暴力推翻,非暴力的“告别革命”,无疑是痴人说梦。
伍立杨维护辛亥革命,还不仅仅因为其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事实上,以暴力的方式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俯拾皆是。但辛亥革命并不是为了一家一姓的利益,而是为天下苍生谋共福,辛亥革命展现出来的,是共和、民主、自由这些崭新的时代价值,在革命党人身上体现的是责任、无私和牺牲。“辛亥革命,就是要打击专制政治,追求‘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孙中山摩顶放踵,等于是菩萨般的人物。其革命重点在改革,还不是武装的部分。他和他的追随者,秉持为生命求尊严的价值理念,担负起拯救天下的责任,为苍生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可以这样说,《中国1911》这本书,就是在共和、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照下撰写而成的。整本书读下来,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这些价值强烈的感情,可以感受到作者不仅是用笔,更是用心捍卫和维护这些价值。全书基本上就是以这些价值为核心而展开,对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事件的评析,人物的臧否,乃至结构的设置,无一处不渗透着作者的价值关怀。试举一例,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暗杀行为,是全书作者着力最多的段落之一。暗杀是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者使用的重要手段。但一直以来,对于暗杀的认识充满分歧,暗杀对于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被严重低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甚至将革命党人的暗杀行为评价为“小资产阶级的急躁冒进”,显然有失公允。
伍立杨在本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议论暗杀,并冠之以“定点清除”的新名义。他认为暗杀是清末政治环境中,革命者必然采取的手段:“面对专制的恶行(独裁统治、黑箱操作、侵犯人权、控制舆论),坐等其自我改良、良心发现,只能是此路不通。没有外部的推动因素,专制者不会自动‘从良’。辛亥党人并不嗜好暴力,但也绝不否认暴力给统治者造成的外部压力可以变成改良的动力”。对于暗杀行为的意义,伍立杨的评价高得无以复加:“历时十余年的定点清除,它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心部分。武昌起义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定点清除的基础上的推导和推倒。定点清除的效果,较之武昌起义的拖泥带水、民众死伤,不可同日而语”。在作者眼中,暗杀几乎是革命党人能够推翻清政府的决定性因素。这样的高评价,可以说发前人所未发,应该是学界关于辛亥革命暗杀行为的最高肯定了。这一结论想必会有一些人不认同,引发争议。但无论如何,肯定能够引发人们对辛亥革命中暗杀行为的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暗杀这一手段在辛亥革命中的意义。
作者对“定点清除”作如是观,是因为在暗杀者身上,体现了更多的自我牺牲精神,更加彰显了他们所追求理想价值的伟大,理想与牺牲两者交相辉映,产生了极大的情感冲击力,为后来的同道所钦服。伍立杨激赏清末的暗杀行为,既是因为受到这些暗杀志士侠义行为的感染,又是希冀在新的时代,能够唤起人们对于辛亥志士们的孜孜以求的价值的回应。全书中,作者处处渗透着这样的价值关怀,“笔锋常带感情”。因此虽然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著作,却充满了激情。
然而问题也就此出现,历史事实是不是就真的如此黑白分明地指向某种价值,体现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并且做到意义与真实的完美统一呢?恐怕历史研究的专业主义者不会这么认为。他们坚信,过于“尊德性”的历史撰述,经受不住“道问学”的深究。就辛亥革命本身而言,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最终的历史走向,是各方角力的结果。当下关于辛亥革命史的专业研究,就非常注重这“各方”,而非仅仅关注革命派及其对立面清政府这两造人马。而各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又有次一级的各方。甚至具体到个人,也有不同的侧面。这些不同的力量,其思想观念、社会政治参与手段,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对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如果在辛亥革命的研究和撰述中只盯着革命党人,只盯着革命党人中促进革命的一面,会不会对辛亥革命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产生误读?在共和、自由、民主这些价值观照下的辛亥革命史,会不会有所遗漏,会不会对某些阶层的某些活动不公平?
事实上,在专业研究领域,在“道问学”研究范式的主导下,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富,但相应地,分歧与争议也越来越巨大。原有的一些主流研究结论有被颠覆的危险,比如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对于革命派革命活动的评价、对于清政府的评价、对于立宪运动的评价、对于一些“反面人物”诸如袁世凯等人的评价。这样的研究固然更接近于历史之“真”,但也不免令人困惑:如果历史研究淹没或者泯灭了某种价值,而这种价值恰恰是现时代国人所急需,那么这样的历史研究其意义何在?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没有共识的时代,现实的思想纷争必然会折射到学术研究中、历史研究中去。因此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才是正确的,这是个不会有终极答案的问题,也没有必要有终极的答案。因此这也注定《中国1911》是一本充满争议的书。这本书旗帜鲜明地“尊德性”,旗帜鲜明地弘扬辛亥革命所代表的价值,也旗帜鲜明地鄙薄另外一种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撰述。正因为鲜明地高扬了此方的旗帜,那么必然就会引发彼方的非议。不过争议并不能够损害《中国1911》这本书的价值。因为本书所心仪、所坚守、所维护的价值,在中国,由辛亥革命发起开端,历经百年,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不可替代,仍然是实现和维护人民权利、社会正义、国家发展的利器。仅此,《中国1911》的价值就不容争辩。
尊德性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历史研究的善,道问学则体现了历史研究之真。事实上,历史研究还有“美”,罗素就公开宣称,“历史是一门艺术”。这种美,首先就体现在历史叙述上面。在这方面,《中国1911》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全书体例打破时空界限,别具一格。行文文白夹杂,初读起来,并非特别顺畅,但细读之下,却有滋有味。义理与辞章,相得益彰。
——柏拉图《美诺》中的德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