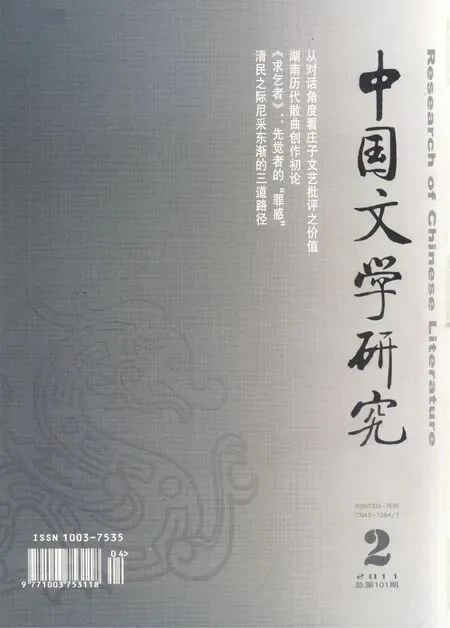《新编五代史平话》的话语形式及其含蕴
李作霖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新编五代史平话》是 20世纪初发现的一部难以归类的著作,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判断它为宋人的“讲史”话本,郑振铎先生认为它应该是后来演义小说的起源,他在《中国小说提要》中认为“‘演义’之传于世者,当以此书为最古。此书虽未如后来诸演义之分回目,然体裁与他们甚相同”〔1〕,直到 20世纪末,尽管此时已发现它和《资治通鉴》的联系,仍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说话的底本”〔2〕。但从 1990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指出它并非说话艺人的底本,而是一部供普通市民阅读的通俗历史读本〔3〕,逐步接近了历史的真实。
《新编五代史平话》作为最早的通俗历史演义,融合了民间说话人和包括《资治通鉴》《五代史》等在内的正史资源,其话语形式十分复杂,迄今未有认真的研究。本文尝试分析其话语形式的构成及其所包含的民间知识人的叙事立场。
一
《新编五代史平话》的叙事话语,首先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两种很不协调的语态的共存。第一种来自民间口头语,第二种则是文人书面语。我们先录两种文字比对一下:
A:朱温整日价只是去四散走马踢球,使枪射箭,怎知他浑家曾被黄巢亲到他军营来相寻,因见张归娘生得形容端正,美貌无双,便使些泼言语,要来奸污他;……朱温听得万事俱休,才听得后,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却不叵耐这黄巢欺负咱每忒甚!”时下间,便带将他的老小、部所属军,不辞黄巢,迤逦向同州路去。〔4〕
B:郭威、王峻入见太后,请立开封府尹刘勋为嗣。太后曰:“刘勋久患羸疾,不能起,何以临朝?”令左右以卧榻升刘勋,以示诸将。诸将信之,乃别议所立。郭威与峻欲立刘赟为嗣,百官表请太后下诰,遣太师冯道诣徐州迎刘赟。初,威在河中讨三叛时分,得朝廷诏书,见其处分军国之事,皆合机宜,问谁为之,使者以范质草诏对,威曰:“此人宰相器也!”直学士当草制诰,威独令范质草诰,令具仪注于仓猝之中,讨论撰定,皆合事宜,威称赏不已。〔5〕
A段是明显的说书人口吻,不仅用了不少口语词汇,而且插入了诗句和套语(“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尹常卖一类的讲史家的说书。然而 B段的语体完全不同,它以文言词汇取代了口语词汇,简洁严整,不再烘托,也没有其他说话的标记,而与史家的叙事话语相一致。事实上,它正是抄自《通鉴》,而且比《通鉴》更简洁。试对比《通鉴》原文: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九)郭威、王峻入见太后于万岁宫,请以勋为嗣。太后曰:“勋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谕诸将,诸将请见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举之示诸将,诸将乃信之。于是郭威与峻议立赟。乙丑,郭威帅百官表请以赟承大统。太后诰所司,择日备法驾迎赟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师冯道及枢密直学士王度、秘书监赵上交诣徐州奉迎。郭威之讨三叛也,每见朝廷诏书,处分军事皆合机宜,问使者:“谁为此诏?”使者以翰林学士范质对。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访求得之,甚喜。时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诰令,迎新君仪注。苍黄之中,讨论撰定,皆得其宜。〔6〕
与《通鉴》相比,平话进行了某些删节,比如郭威入城访求范质,“大雪解袍”等生动的细节(司马光编《通鉴》时“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被删去了;某些句子比原文更简练,如“令左右以卧榻升刘勋”“乃别议所立”等。而且我们还发现,在插叙郭威初识范质这件事时,平话的编者加入了一个为原作省略的“初”字。这样的处理,至少让我们意识到,《新编五代史平话》的编写者并没有如后来的演义小说作者那样明确的意图,即把历史小说化,至少,他在按鉴陈述历史时,还没有从史家意识和小说家意识的矛盾中解脱出来,也许考虑到其读者也有不少是读过《通鉴》的,所以他有时会比史家更像史家(尽管难以达到)。
但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新编五代史平话》“非是一部干枯无味的历史演义”。其趣味不仅表现在讲述黄巢、朱温、刘知远、郭威等人发迹前的故事情节曲折、语言活泼,也表现在它在处理《资治通鉴》、《五代史》等提供的史料时,所体现的创造性的加工。这种创造的艺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新编五代史平话》的叙事语法已与《通鉴》不同。《通鉴》叙“历代君臣事迹”,“年经国纬”、“举撮机要”。所谓“机要”,是“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7〕。凡有益于“资治”,不论是君事还是臣迹,都根据时间顺序铺陈,这就使得事件的叙述没有主轴,比较散漫。而平话首先确定了一个叙述主体,这就是皇帝,如《梁史平话》卷上主要是朱温的故事,《周史平话》上下卷分别是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的故事。主体既明,题材便相对集中。比如朱温与李克用交恶的事件,发生在唐僖宗中和四年,正是朱温归降不久,和李克用并力讨黄巢的时候。《通鉴》在《唐纪七十一》有记载,《新编五代史平话》中,不见于《梁史平话》,而在《唐史平话》中有详述。这便很有讲究。因为这件事是朱温意气用事,放在《梁史》中有损其形象,但放在《唐史》中却为后唐庄宗李存勖为父报仇灭后梁埋下了伏笔。
通观《新编五代史平话》,不仅叙开国皇帝发迹前的故事情节性很强,即使其主人公进入正史后,编写者也常常有意对正史中的材料加以改造敷衍,使前后事件具有一定程度的因果联系,或使某一部分显得突出以彰显人物形象(如李嗣源的体恤民众、郭威的审慎仁厚)。正因如此,这部平话才被理解为通俗历史演义的滥觞,而不是一般性的编年历史读本,尽管其叙述表层是仿照《通鉴》的以年纪事的语法。
其二,尽管该平话有大约七成的内容是按《通鉴》的顺序和文字编写,但它改编的部分并非都如上文 B段所示,是同一种史家语态的陈述,更多的时候,它还是用一种比较粗浅的文言或者文白夹杂的语言在陈述,显示了一种“通俗”的意向。比如:
C:(《汉史平话》)至清泰三年,唐主宣授石敬瑭做天平节度使,敬瑭欲不拜命,朝旨差张敬达做西北都部署,迫胁敬塘赴郓州。敬塘疑惧,与刘知远共谋去就。刘知远道:“哥哥久在兵间,素得士卒心。今据形胜地面,士马又十分精强,若称兵反叛,帝业可成。奈何听命于一纸制书,自投身于虎口乎?”敬塘听得知远这说,心下欣然,应道:“贤弟说的话,使我心下豁然。”〔8〕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天福元年五月)辛卯,以敬塘为天平节度使,以马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甲午,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趣敬塘之郓州。敬塘疑惧,谋于将佐曰:“吾之再来河东也,主上面许终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节与公主所言乎?我不兴乱,朝廷发之,安能束手死于道路乎!……”都押牙刘知远曰:“明公久将兵,得士卒心;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乎?”……敬塘意遂决。〔9〕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平话不仅对于《通鉴》中的一些文言词汇和句法做了通俗化的替换,而且对于人物对话,特别是刘知远、王彦章一类的草莽英雄的语言做了发挥,使其场景或人物形象生动可见。如敬塘“心下欣然,应道:贤弟说的话,使我心下豁然”比起“敬塘意遂决”这样的陈述显然更具小说意味,而这样的处理应该是编写者揣摩一般读者的心理期待而采取的相应策略。
诚然,平话的编创者还没有像后来的通俗历史演义作者那样自觉地运用白话语体,而是杂糅着说话人语言和史家书面语,造成一种不协调和不流畅的语调,但在历史文本中有意地嵌入民间口头语,无疑对后来的演义小说的语言取舍有所启发,因为这些活泼的民间口语,无疑更能带来阅读的欣快感,从而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
其三,插话与诗词。“插话”是指说书人在演说故事时,不时插入一段与正文没有直接联系的小故事。《新编五代史平话》也运用了不少插话。如《周史平话》叙太祖郭威在平定慕容彦超叛乱后,欲尽屠兖州城,谋士范质劝说:“昔高祖围鲁城,怒其不降,欲举兵屠城,闻弦歌之声,以为圣人邹鲁之地,不忍加害。陛下不能为汉高祖之所为耶?”遂引出如下插话:
且说那汉高祖五年十二月,与项羽厮杀,……楚地悉定,独鲁城不下。汉王引兵围之,欲尽屠其城。至城下犹闻弦诵之声,谓其守礼义之国,为主死节,乃持项羽头以示之,鲁城乃降。〔10〕
类似的插话还有很多,如叙李存勖渡黄河恰逢冰合,插入汉光武帝渡滹沱河而冰合的故事;李从珂被谗几乎致死,引出赵高矫杀公子扶苏的故事,等等。这些插话及其连接语,大抵以白话叙述,仿照说话人口气。这样的插话置于史家一般的庄重口吻之间,另有一种不同于说话人书场插话的功能,它不仅活泼了史事陈述造成的平淡气氛,而且具有和史家叙事明显不同的教化立场——一种以民间伦理为准则的立场。
诗词运用的情况。《新编五代史平话》在叙事时加入大量的诗词,这又是不同于正史,而趋向于模拟口头“讲史”的一个特点。正如说话体制,平话有开场诗、散场诗和中间插入诗歌的形式。开场诗一般起提纲挈领的作用,如《梁史平话》开头:
龙争虎战几春秋,五代梁唐晋汉周。
兴废风灯明灭里,易君变国若传邮。
散场诗一般对人物、事件加以评论,以总结历史教训。如《唐史平话》之散场诗揭示后唐灭国的原因乃先王养子的自相残杀:
堪笑鵶儿兴后唐,四君三姓自相戕。
谁知一十四年后,历数依前属石郎。
除了开场诗和散场诗,中间插入的诗句也很多见。这样的诗句大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沿袭了说话人的即兴评说,包括一些套语的插入,如“不向长安看花去,且来落草做英雄”,“手拿三尺龙泉剑,夺却中原四百州”,“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相逢不下马,各自奔前程”等等。另一种却是引用或拟作的诗歌,这些诗句与文中情境较为协调,具有一定的表现力(表现人物的情感、思想或环境氛围)。
《新编五代史平话》引用或拟作的诗句,有雅有俗,有的只是说话艺人似的显示博学,有的却是极具美学意味的创造。这样的情形使人想到,平话的编写者在叙史过程中加入诗歌,一方面受传统的说话艺人的巨大影响,而另一方面,作为供出版的书写文本的书写者,编者也开始注意到了前后文字所需的有机性,从而尽量使一些诗句更高雅含蓄一些,或者使诗句在文中的表现力更强一些。如《晋史平话》的散场诗,陈抟的《归隐》诗及描写黄巢心境的诗句等,均是如此。这样的插入诗句因为在文本中发挥了积极的审美功能,而成为以后明清小说叙事的一种基本成规。
综上所述,《新编五代史平话》杂糅了史家叙事和民间讲史两种叙事形态,如鲁迅先生所言,“全书叙述,繁简颇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俪,证以诗歌,又杂诨词,以博笑噱”〔11〕,既依从正史提供的史料和话语方式,又参以民间传闻和说话人的话语方式,体现出民间历史叙事特有的书写方式,而这种书写方式作为历史小说的开端,或者书面历史叙事由官方向民间的一种过渡,呈现出这种杂糅的特点,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其中所体现的话语含蕴,或者说作为编创者的民间知识人的创作心态,却颇奈玩味,这正是下文将要探讨的。
二
作为一部普通的历史读物,并且是首次出现在文化市场上的通俗历史读本,《新编五代史平话》的编创者在叙述历史时便不得不做多方面的考虑。比如以何种视点来观照这段历史(五代),这本书应有一种怎样的结构,通过哪些情节或叙述手段激发读者的兴趣,以及作为书面文字在讲述历史时怎样修辞才是恰当的,等等。这些设想无疑只有通过借鉴已有的材料和技巧才能付诸实践。而正是在借鉴和改造官方正史和民间说话的实践中,本书叙述者的复杂心态暴露无遗。
以下我们从视点和视域、修辞或者话语两方面来考察本书叙述者的叙事心态。这两方面当然也是一体两面、互相依存的。
视点和视域是点和面的关系,两者的结合构成一个V形聚焦区,它反映出对叙述者而言何者是值得叙述的。而从他所选择的事实中,不管所讲述的话语如何,本身可以看出叙述者的立场。
至少从表面上看,《新编五代史平话》的叙事视点是双重的,即史官似的视点与民间视点的重合。如每当讲述帝王发迹前的行迹,叙事者是从民间立场来“看”的,比如写黄巢出世,先有唐太宗时袁天纲的图谶:“非青非白非红赤,川田十八无人耕(黄巢)”,后有黄巢出生后的种种怪异:其母怀胎十四个月,“生下一物,似肉球相似,中间却是一个紫罗复裹得一个孩儿……”此后写刘知远、郭威等,都是如此。另外如写朱温兄弟与黄巢结拜、石敬瑭牧羊摆阵、郭雀儿(威)买剑杀人等,这些民间流传的故事,正史均不载。正史不载的原因,主要并非这些事件没有真实的发生,而是这些带有传奇性或江湖气的故事与史家观点不合。
而《平话》大部分抄自《通鉴》《五代史》等正史,其视点和视域便有与史家观点重合的地方。如鲁迅先生所言,“史上大事,即无发挥”,“无发挥”,就是对史家记载的这些朝政军国大事无法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而采取承认的立场。如写后唐庄宗因优戏误国丧身,明宗问百姓疾苦而至天下太平,这些典型的史事的陈述与《通鉴》《新五代史》的视点基本重合。
在修辞或话语层面,《平话》的叙述者同样显示出一种选择的矛盾。在表达形式上,他一方面采用了如前所述的诗词、插话、评说等民间话语形式,另一方面也采用史家的编年、实录、奏章等形式。在语体上,一会儿用口语,一会儿是雅驯的文言,更多时候是文白夹杂。但正是在话语的表现上,我们可以看出《平话》的话语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民间话语形态。
所谓“民间话语形态”,有学者认为它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12〕。这里的“非权力”如果界定为“官方权力”当然更准确些,因为话语无任来自哪里,都意味着一种权力诉求。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或知识精英的话语的区别主要在于它在一个等级制的权力体系中它是在低端或底端言说和传播的。它一方面有自己的文化视界和空间,另一方面它又与官方话语和精英话语构成复杂的关系。斯图亚特·霍尔在分析大众文化接受者解读主导-霸权话语时提出三种情况:对霸权话语的认同、协调性的理解(使主导界定适合于“局部条件”和“它本身团体的地位”)和全然相反地解码主导话语。〔13〕这一观点也适合于《平话》对正史的解读。比较特殊的是,《平话》在改编《通鉴》等史书时,同时采用了这三种解码方式。
其一:对主导话语的认同。《平话》全书约四分之三抄自《通鉴》,其话语大部也承袭了正史的简要、雅驯的风格,这已经意味着《平话》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主导话语。但这种认同我们应该理解为民间知识人对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史家的认同式解读,而不应认为它本身也是精英的。在这四分之三的“转抄”中,实际上很少出现连续的照抄,而是在内容上做了很多综合、转换的工作,至少也有措辞和语气的变化。如华莱士·马丁所言,“某种措辞,或者仅仅是某个声调或变音,就使我们留意到视点的转换或混合”〔14〕,由话语产生的变化,意味着表面的认同下包含着协调性的理解。
其二:协调性的理解。《平话》的编者作为沦落社会下层的知识人,其身份本来就不明朗,他在理想中接近文化精英的意识形态,而在现实中却已经深深接受了民间的历史观念、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味。所以他在依据经典来重新解读历史时,就会对主导话语加以协调性的理解和诠释。
这种协调性的理解既表现在抄录正史的间隙穿插诗歌或插话加以评述或敷衍,也表现在对正史的某些话语加以调整或重述。前一种情况前文已有说明,后种情况我们试举例加以分析:
(《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枢密使、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节益狂躁,奏请以端明殿学士颜衎、枢密直学士陈观代范质、李谷为相,帝曰:“进退宰辅,不可仓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论列,语浸不逊。〔15〕
(《周史平话》)峻晚节处事狂躁,一日奏荐颜衎、陈观两个为相,周太祖曰:“进退宰辅,不可仓猝,俟更思之。须有德望者可当相位。公所荐二人,德望如何?”峻骂曰:“陛下以花项纹身为君,又何德望之有?”语颇不逊。〔16〕
这件事是周太祖的重臣王峻命运的转折点。关于君臣之间的冲突,《旧五代史·王峻传》也只说“峻论列其事,奏对不逊”,想必正史对大臣骂君王的事情还是有所忌讳的。而《平话》作者却大胆设想王峻以德望相讥(郭威少时买刀,一语不合便杀人,有何德望?),对君臣关系做了一种平民化的解释,尽管他也承认王峻后来的被贬和忧愤而死有咎由自取的因素。
其三:完全相反的解码。如果不局限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陈述,而从整体理解历史的兴衰和人物的沉浮方面而论,《平话》的许多历史解释与正史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对黄巢起义的演说,对五代各开国皇帝发迹前的描述等。正史对帝王开辟历史的解释往往是仁德与勤政,而《平话》对此的解释却是天命加强力和机谋。而在具体历史事件的修辞上,《平话》作者也有很多与正史完全相反的解释,我们仍以王峻的事情为例加以说明。
在王峻得罪周太祖之后,被贬为商州司马。贬后的情形,《通鉴》的叙述是:“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犹愍之,命其妻往视之,未几而卒”,一方面说明做皇帝的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另一方面暗示王峻是得腹疾而死。而《平话》却全然不理会这种解释,只用一句话交代王峻的结局:“乃贬王峻为商州司马,峻愤恚而死。”联系《平话》对王峻为后周基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铺叙,作者在简短的交代中所蕴含的愤怒和同情已经溢于言表。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平话》的叙事者一方面认同了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某些视点,另一方面又利用民间资源试图对精英的历史解释加以重新诠释。两者的“混合”(而不是有机的“融合”)表明《平话》的叙述者在意识形态立场上处于一种骑墙态势。其中的原因,除了宋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恐怕最主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影响。宋代的科考比以往各朝代规模都大,而且不再有门第限制,因而像范仲淹、欧阳修一类的寒门子弟由科考而至卿相者,屡屡发生,其影响所及,便是宋代的读书人口甚众。但是,科考并非一条现实的道路,有学者考证,“全宋三百余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不过 11万人,平均每年取 360余人。全国举人而待考者,(每年)常常有数十万之多”〔17〕。也就是说,宋朝的绝大多数平民知识分子尽管心怀精英的梦想,而实际的人生道路只能是混迹民间。尽管还不像元代读书人那样发展出一种“游民意识”,但由精英知识人的意识向普通市民意识的转变已经明确发生了。
而从文体的进化来看,《新编五代史平话》的语言不再是单纯的一种历史话语,或者说它不是盲目重复史家话语,而是民间话语和精英话语的“多音齐鸣”(heteroglossia)。巴赫金认为,严格区分不同文体(style,语体)是集权文化的特点,这一文化标出了被认可的语言与任何与之不同的话语之间的界限。而《新编五代史平话》的杂语交糅正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它不仅是平民历史著述的开端,同时也是(长篇)小说的开端。巴赫金认为小说就是这样一种杂交的形式,它是“一个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系统,目的在于使不同的语言相互接触”〔18〕。当我们以历史的同情来翻阅这部不知如何分类的书籍时,我们当可放下我们关于原创性或者语言风格的先入之见,而注意到它在融合多种话语成规方面的努力。而这种努力,进而开启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新时代。
〔1〕郑振铎.郑振铎全集(4)〔C〕.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315.
〔2〕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 〔M〕.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296.
〔3〕参见参见丁锡根.五代史平话成书考述 〔J〕(《复旦学报》,1991年第 5期)和卢世华.并非底本——论五代史平话编写方式 〔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2006年第 1期)等文。
〔4〕〔5〕〔8〕〔10〕〔16〕丁锡根.宋元话本集 〔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4.204.177.213-4.217.
〔6〕〔7〕〔9〕〔15〕司马光.资治通鉴 〔M〕.长沙:岳麓书社,1990:865.935.746.888.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79.
〔12〕陈思和,何清.理想主义与民间话语〔J〕.中山大学学报,1999(5).
〔13〕〔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345-358.
〔14〕〔18〕〔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1.151.
〔17〕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