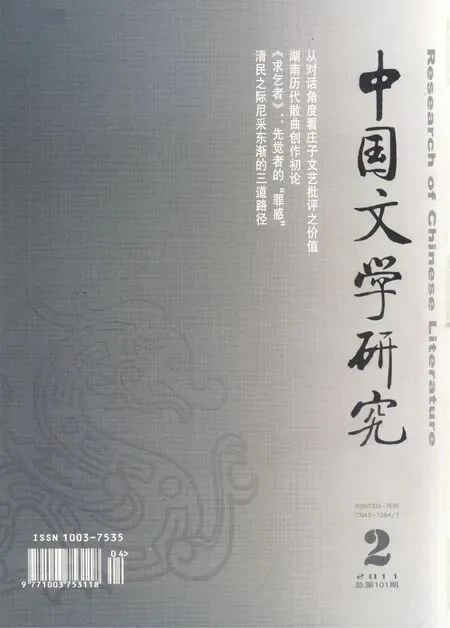视界融合与本土化意识
——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
赖力行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在一次访谈中,叶嘉莹先生指出,多年来,我们热衷于学习西方的新理论,但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古典文化传统却已经相当陌生,这种陌生造成了要将中西新旧的文化加以融会结合时,无法将西方理论和术语在实践中加以适当的运用。〔1〕在建设现代性、民族性的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值得警醒的问题。最近读到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赵炎秋、李作霖、熊江梅等几位学者合作的新作《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丛书(三卷本,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这套丛书立足本土文献,在学术写作上又有明确的问题指向和创新意识,尤其注重中国和西方、现代视野和本土文献的交相融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范例。
简而言之,《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创新意识集中体现在叙事学研究的本土化意识上。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文论的强势话语权威下,中国古代文论似乎缺少应对之术,以至出现所谓“失语症”,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古文论研究的中心话题。中国古代文论能不能转换、如何转换,如何在古今中西对话间挖掘和利用古代文论资源以建构当代文论,这在传统叙事学研究中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叙事学是西方结构主义的分支,其研究立足于西方叙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出现对西方叙事学的介绍热潮,在这一理论视角的刺激下,随后出现了运用西方叙事学原则与方法对中国叙事进行研究的热潮,而且也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既包括通论和专题研究,也不乏大量的单篇论文,这些成果各有其特点和创新之处。其中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在借鉴西方叙事学研究框架的同时,又能突出中国叙事的特点,初步奠定了中国叙事研究的基础;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在熟练运用西方的叙事学理论框架的同时,对之进行中国化改造,抓住小说叙事方式中最基本的元素——时间、视角与结构,尤其突出了适合中国小说特征的叙事结构问题,建立起适合于中国小说叙事研究的工作范式与理论框架,对中国文学至为关键的蜕变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均代表着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实绩。但总体而言,中国关于叙事学及叙事研究的论著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最突出的表现是经验与理论的脱节:研究中国叙事学,多追随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和术语,较少立足于中国叙事的民族性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论著,不顾中国叙事的实际情况,机械套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话语,因而成为西方叙事学的“中国翻版”,得出的结论不免出现偏差。
事实证明,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和移植,终将遭遇一个民族性的问题。文化无国界,但却有民族性。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往往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激活理论研究,对西方理论研究中出现的新思潮、新方法视而不见,势必导致研究的落后和狭隘。但如果不顾具体的民族性特点,不作一番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工作,妄图一劳永逸地机械借用西方的理论进行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研究,很难使研究深入精确,切中肯綮。叙事理论的研究同样如此。本土叙事理论资源的匮乏,使得研究必须依托于西方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叙事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性。如何在叙事研究中具体解决中西文化的视界融合,弥合经验与理论的脱节,建构既充分吸收西方叙事学之长,又内蕴了切身体验而流淌着民族文化血脉的中国叙事学体系,是一个十分重要又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丛书的研究就显得别有新意了。丛书在批判吸取西方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古代叙事的民族性特征对西方叙事学原理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与创造性变形,以适应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的需要,具有鲜明的视界融合和本土化特征。这种本土化修正主要体现为在准确把握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研究体系,初步建立起适合于中国本土叙事研究的学术分析模式,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意识。如丛书在踏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通过与西方叙事学的反复比照与修正,所提出的“诗化”与“史化”两个概念范畴和分析模式,能够提纲挈领地把握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民族性特征,是具有有效阐释力的本土化分析概念和模式。
中西叙事学的不同渊源形成不同的叙事理念。黑格尔说,中国无史诗。浦安迪说,中国没有荷马,却有司马迁,故与西方史诗源头不同,中国古代叙事思想主要渊源于史传,表现出鲜明的“史化”特征。中国古代叙事缺乏史诗性源头,史传充当了古代叙事的源头,由于史传标举“实录”,贬抑虚构,从而导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晚熟,加上其它一些思想文化背景的影响,叙事诗学基本上被排除在传统诗学理论视野之外,抒情诗学则占据了传统诗学主流地位,并对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形成强力渗透和影响,使叙事思想的“诗化”特征突出。《先秦两汉叙事思想研究》一书系统清理了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发生,对中国古代叙事思想“诗化”和“史化”特征的发生学背景、叙事表征、理论表现等予以详尽考析,初步建构了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基本理论体系,从三个方面具体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在叙事结构上,淡化“历时性”事件流程,强化“共时性”场景呈现,逐渐发展出“空间化”叙事结构,在淡化时序和因果律的同时,却通过对事件系列的精心排列与连缀,产生某种“有意味”的组接,借以传达某种认知与情感。在叙事时间上,不注重“时间倒错”等叙事时间操作技巧,而强调经由对时速的操作显示深层用意,构筑“人文化”、“哲理化”叙事时间。在叙事视角上,在保持全知叙事视角的权威性的同时,不斤斤计较于细致描摹,而调动“以无写有”、“以形传神”的高度技巧,达到一种整体的把握和情感的传达。
《魏晋宋元叙事思想研究》扣住中国古代叙事与历史的内在关联,深入阐述了魏晋宋元叙事思想承继、增补和突破历史化叙事的理论轨迹。如著作以志怪为个案,具体分析了志怪叙事的“历史性”及其转化。论述指出:魏晋六朝时代的志怪叙事被目为“史”,其“历史性”不仅表现在写法上“据国史之方策”,秉承历史书写的“其文直、其事核”的“实录”传统,同时也在“历史”的广度和深度上,试图作更有时代性的开掘。这种开掘不是正史意义上的历史性的进化,而是“礼失而求诸野”的语境下的历史的“增补”。志怪叙事对历史书写的承继与增补,表现出志怪书写者的一种特别的历史意识,并由此开拓出虚构性叙事的道路。
《明清近代叙事思想研究》一书研究明清叙事思想,作为一个既有深厚的传统文论功底又有西方文论研究背景的学者,专著对明清小说体制,近代重要文艺思想家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叙事思想,《海上花列传》、《红楼梦》的叙事技巧,以及近代报刊语境的叙事思想等的探讨,均突出了视界融合和本土化转化的理论特色,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观点。
丛书的本土化意识还突出地体现在论述始终强调中西对比的研究视角,这种对比不拘囿于中西叙事思想本身,而且拓展到中西不同的哲学、文化、思维、历史等外部维度,使其理论阐释和体系建构具有了坚实的民族文化土壤。西方经典叙事学将叙事文本视为独立自足、自成一体的艺术品,是典型的形式批评,属于“内部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则表现出一种开阔的理论视野,在借鉴西方叙事学的内部研究范式的同时,引进了诸如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等外部批评维度,这样既符合中国古代叙事的实际,又便于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深入、全面地对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加以把握。如《明清近代叙事思想研究》用西方叙事理论烛照明清近代叙事的理论与实践,既考虑叙事理论基本规定性,又考虑到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传统与独特性,并将文学问题的探讨与时代文化背景结合予以解读,不仅对叙事作品作修辞式的内部研究,而且研究它的外部联系,较好地实现了内部与外部两种研究视角的融合,总结出比较完整富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明清近代叙事思想体系。
总之,《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在借鉴西方叙事学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致力于建构具有民族阐释力的特殊学术模式和分析概念,有力地促进了本土叙事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1〕百年词学的文化反思——叶嘉莹教授访谈录〔J〕.中国社会科学报〔J〕.北京:2010.3.18.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