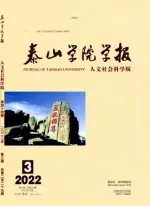泰岳阴司信仰的民间版本——以泰安祝阳总司大帝信仰为例
张萌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 251000)
对生的渴望、对死的恐惧以及对死后世界进行想象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泰山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一个“生死”攸关之地,以泰山为背景形成了泰岳阴司信仰。“泰岳阴司信仰”是指由对泰山的崇拜祭祀生发而来,将泰山 (包括蒿里山、梁父山)视为冥界,将泰山神视为掌管死者魂灵、主管冥界的“司命”之神的一种信仰形态。泰山东麓祝阳镇祝阳村有一座历史悠久的道教庙宇,名曰总司,其中供奉着掌管阴间的神灵——总司大帝,总司庙大殿内绘有十殿阎君①的壁画。在当地民众的信仰观念中,有一个从总司大帝到十殿阎君再到七十五司的阴间秩序。
一、总司庙与蒿里山
要想探寻泰安祝阳的总司大帝信仰与泰岳阴司信仰之间的关系,首先从蒿里山开始。蒿里山位于泰安火车站附近,是泰山脚下的一个小山,也叫亭禅山、高里山。蒿里山作为泰岳阴司文化的一部分,滥觞于汉代,复兴于元代,兴盛于明代。
“汉人不仅相信泰山为鬼魂群聚之处,而且还把和泰山相连的高里山也看作是和幽冥有关的地方。……高里和泰山相连,所以在民间迷信中,它和泰山一样地被涂上了神秘的色彩。汉代人以为人死后到蒿里,蒿里即是从山名的高里演化来的。早在西汉时,人们就用蒿里以代表九泉之下,如汉武帝之子广陵王胥,他在临死前歌曰:‘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师古曰:‘蒿里,死人里。’镇墓文中蒿里一词,经常可见,如‘死人归蒿里’、‘蒿里君’、‘耗(蒿)里父老’,等等。”元人徐世隆《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碑》中称:“今东岳山有地府,府各有官,官各有局,皆所以追生注死,冥冥之中岂无所宰而然耶。其祠距东岳庙之西五里许,建于社首坛之左,自唐至宋,香火不绝,望之者,近则威然,入则肃然,出则怖然。”蒿里山的影响愈来愈大,元初泰山全真道士张志纯发起重建了蒿里山神祠,“‘旧祠百二十楹,近已完缮,次第落成,其塑像辉耀,比旧有加焉’。此次重修中,神祠置有‘七十五司’神房及像设。”明代时期蒿里山成为泰岳阴司文化的中心,“嘉靖《山东通志》卷五《山川》云:‘亭禅山:在泰安州西南五里,一名蒿里山,上有蒿里祠、森罗殿、七十五司官属,管阴府死生,较量人间善恶,有地狱剉烧舂磨之说,虽涉诳诱,亦足为世俗之警励也。’”七十五司信仰也随之盛行民间。
总司庙的住持道长张秀山说:“总司庙与蒿里山是一个系统。”其实,所谓的“系统”指的是泰岳阴司信仰系统,总司信仰的源头则是蒿里山的七十五司信仰。从名称上我们可以看出“总司”与“七十五司”二者之间是一种概括与被概括的逻辑关系。乡村的庙宇不可能有如蒿里山神祠一般宏大的规模,但是又想将蒿里山神祠里的七十五司“神房及像设”都表现出来,于是就采用了一种总括的方式,将“七十五司”概括为一个“总司”。可以说,总司庙是蒿里山神祠的缩微,而总司信仰是对泰岳七十五司信仰的浓缩与提炼。法国学者沙畹在蒿里山考察时拍摄的一张照片可以证明老道长所谓“总司庙与蒿里山是一个系统”的话是真实可信的。这张照片拍摄的是立于蒿里山神祠旁边的一块碑刻②,上面刻有“住持张能纯”的字样,而这位张能纯正是祝阳总司庙的住持。张能纯能够在蒿里山碑刻上以住持的身份留下名字,一方面能够说明总司庙与蒿里山的特殊关系之外,一方面告诉我们总司庙在泰岳阴司信仰系统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据老道长介绍,他的老爷张能纯经常到蒿里山给香客讲七十五司,大概十天去一趟,蒿里山神祠毁于炮火之后才不再去了。
在民间,蒿里山被认为是死后魂魄的聚集地,“自汉以来人们即以为泰山治鬼,蒿里为鬼狱”,除此之外,每一个人死后还要进行“登记注册”,通常情况下,掌管阴间户口簿的神是泰山神,但是在祝阳的总司庙,这个神则变成了总司大帝。总司庙正殿总司神的身边有两位男童侍者,其中一个手拿纸笔,仿佛告诉人们他就是总司大帝手下负责注生录死的“文书”,而他手里拿着的纸张在阴司信仰中通常被称为“鬼簿”或“死人录”,“所谓‘死人录’、‘地下死籍’,是指阴间有一套不同于阳世的户口簿籍,因而有的镇墓文中说:‘生死异簿。’人死后世间的户籍被注销,但幽灵立即又被登上阴间的簿录……”
二、总司大帝信仰的本质
祝阳民众认为总司大帝是阴间的最高统治神灵,并将十殿阎君与七十五司鬼官纳入其统治系统之中,形成一个由“总司大帝”统领“十殿阎君”,“十殿阎君”统领“七十五司鬼官”的阴间统治秩序③。众所周知,泰岳阴司信仰中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是东岳大帝,十殿阎罗 (君)与七十五司判官都是他的下属,“我们看道教里,把十殿阎罗塑在东岳旁的旁殿,阎罗王成了东岳大帝的下属。”“由于东岳大帝主宰幽冥十八层地狱及世人生死贵贱,职务繁重,所以庙中一般还配有七十五司(一说七十二司,或说七十六司),分司众务。”
“东岳大帝”神的出现是泰山神人格化历程中的最后一步,“东岳大帝”由早期的“泰山府君”发展而来,佛教传入后演变为十殿阎王之一的第七殿泰山王④,“从唐代开始,随着对泰山神不断的加封,出现了泰山神的国家化和帝王化的倾向”。唐代出现了“神岳天中王”、“天齐君”、“天齐王”的封号,宋代祥符五年被封为“天齐仁圣帝”,元代至元二十八年加封“天齐大生仁圣帝”,与此同时泰山神由“泰山府君”逐渐演变为民众心目中的“东岳大帝”,“泰山神的人格化,使其具备了中国民俗神灵所具有的一般性质,同时,其安邦定国、通天告地的显赫本领,又使其具有了普通神灵所不具备的威力”,因此,东岳大帝信仰是一个兼具民间与官方双重身份,由民间信仰、佛道势力与统治阶级三方共同参与形成的“既主生又主死”的特殊信仰形态。
总司信仰则不同,总司信仰在其诞生—发展—沉寂—复兴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只具有民间信仰的性质,只属于民间话语体系,体现了民众对泰岳阴司信仰的理解与创造。“总司大帝”的称号没有经过官方“手续”,完全是民间自封;“总司大帝”名号在官方的历史档案中无迹可寻,“总司之神虽祀典所未载而其灵传闻于一方久矣”,其灵应全靠民间“传闻”;祝阳镇百姓习惯称总司庙大殿里的“总司大帝”为“总司老爷”,在封建社会“老爷”是下层民众对士绅阶层的一般性尊称,但从未听说有“东岳老爷”这样的叫法,相比之下更能凸显“总司大帝”的纯民间色彩。
然而,“总司大帝”毕竟脱胎于“七十五司”信仰,属于泰岳阴司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与“东岳大帝”有着剪不断的关系,除了称号与神职体系上的相似之外,在神灵职能上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关联。东岳大帝的职司主要分为两个层次:对于上层统治者而言,泰山是封禅之地,东岳大帝不仅具有“更替王朝、稳定江山”的职能,还具有“延年益寿、长命成仙”的功能;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泰山“主阴阳交代万物生发”,东岳大帝是一位主掌生死的神灵,主管人的贵贱祸福。总司庙碑刻关于总司大帝职能的描述有:“威镇岱左,权司幽冥”,“大抵总簿人间之善恶而隐司其彰瘅,不外福善祸淫者”,“则总统其事、总攝其□、总裁其成,既五刑之阴司,殆百禄之是总者乎”,由此可以概括出总司大帝“主掌幽冥,总理祸福,惩恶扬善”的职能。二者对比,不难看出总司信仰只承继了东岳大帝“主死”的职司,我想这是民众有意识地选择,舍弃那些属于上层社会的职能,只保留属于民间的部分。而同属于民间信仰体系的泰山神“主生”的功能也同样被民众继承与发扬,只是渐渐地被泰山顶的女神“碧霞元君”分担去了。
其实在泰山信仰中一直存在着官方与民间两个系统,“朝野观念的不同就在于:官方认为在泰山祭祀的神明,而民间认为他们祭祀的是些死人,进而把泰山视为死人魂灵的聚集地。参合史书中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泰山地狱的观念就是针对官方祭祀所构造的一种传说,不能视为朝野意识形态在泰山的巧合。”从一开始,泰山主死的功能就是来自民间的想象,“对普通人来说,泰山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死者获得最后宣判的地方”,并且希望死后通过东岳大帝这样一位“聪明正直”的神灵的裁判能够获得一个好去处,最关键的是,在这位神灵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死者在地下无等级差别。对活着的人来说,每个人都面对着死神的召唤,不论贵贱贫富”,包括帝王将相。即使当泰山神进入国家体系、逐渐帝王化的时候,“在民间信仰里,这位泰山岳神,并不是像官方正式祭典中那样一副正襟危坐,不食人间烟火的尊容,而是带上了民间赋予的种种特点,可以说,民间的泰山神信仰,与上层帝王们所崇信的作为与天沟通的中介的泰山神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副面目”。事实上,民间一直有一套自己的信仰解释系统,而“总司信仰”的出现是民间对官方祭祀的又一次“反动”,总司信仰的本质是民众对东岳大帝信仰的改造。
三、在民间阴阳观中探寻总司大帝来历
总司庙为何在祝阳出现,或曰民众为何在祝阳创造了这样一个主管幽冥的总司大帝?其实祝阳之“阳”与总司神灵之“阴”神身份之间构成了一组有趣的组合,而这对阴阳关系或许可以解释总司神灵的来历。
当地人有这样一个传说:过去的时候,往祝阳这边看啊,这里全是很高很大的火,虽是一片旺地、宝地,但火太大,有点压不住。风水先生说只要在这里建个总司庙,就能把火压住。村民听说只有总司庙才能把火镇住,于是就在村东找了一块地方,坐北朝南地建了总司庙。总司庙建成之后,再往这里看就看不见火了,总司庙真的把火镇住了。这是乡民对总司庙来历的解释,是民间对传统阴阳思想的“另类”理解。这个民间传说里的“火”大概与风水所讲的阴阳五行有关。由于“火”属阳性,“祝阳”之“阳”在民众的眼中就变成了“火”的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阳胜于阴的思想,当地人一方面认为祝阳是风水宝地,另一方面又担心阳气过盛(火大)造成风水阴阳失衡。在民间文化里,“阴间”与“阳间”构成一对“阴阳”关系,于是总司庙成为调和祝阳阴阳关系的一种媒介。村民认为之所以在祝阳建庙供奉掌管阴间的神灵,是要用阴气压制、中和祝阳过剩的阳气(火),使风水达到平衡。从字面对民间传说进行解释是比较符合乡民的思维逻辑方式的。祝阳传说中所谓的“火”除了与地名有关之外,可能还与其地理位置“祝山之南”有关。山南往往意味着比山北拥有更充足的阳光,在传统文化中阳光也是火的象征。总之,祝阳民众从这个传说中得到了很多心理满足,既对总司庙的来历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又赞美祝阳是一块风水宝地,同时还可以增加祝阳和总司庙的神秘感,因此村民们至今对此津津乐道。
总司庙碑刻中一块立于咸丰元年的“万古流芳”碑正文记曰:
盖闻一阴一阳之谓道,故道明虽异,其理要可推而通之。祝阳镇有总司庙者,神则灵应、庙亦巍峨,流传至今亦已久矣。
文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出自《周易·系词传》,原文记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 (智)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此语在祝阳总司庙碑刻中得见,所具有的意义殊不一般。第一,从“一阴一阳之谓道”字面含义来看。儒学经典把“一阴一阳”看作并时对立存在的关系,如“天地”、“尊卑”、“男女”等,当地儒生⑤则将其推演到“阳世”与“阴间”的对立存在关系上。儒家传统把“一阴一阳”看作历时交替变化的关系,如“昼夜”、“寒暑”,当然也包括“生死”之间的更替,当地儒士则认为在“阳世”生活的人死后到“阴间”做鬼也是阴阳的更替方式之一。对立与交替两者又是兼具并行的,如“幽明”如果指背阳,向阳则是对立的,如果指黑夜,白天则是交替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阴阳两界。在“阳世”与“阴间”的意义上,它们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对于具体的生命而言,生前属于“阳”,死后属于“阴”,又是一种交替的关系。第二,《周易》的这句话揭示的是“阴阳”与“道”的关系,用理学的观点来说就是“气”与“理”的关系。“阴阳”为“气”,“道”——“一阴一阳”则为理,阴阳的对立迭运不能称为“道”,只有使得阴阳对立迭运的根本道理才是“道”。“盖闻一阴一阳之谓道,故道明虽异,其理要可推而通之”,当地儒生用这样一句话将儒家理学中深刻、难懂的哲学原理与民间信仰结合起来,将其变成可以为民间接受的话语。儒家向来“不语怪力乱神”,撰碑人之所以引经据典,一则为自己参与民间庙宇神灵祭祀找到理论依据,二则为当地的总司信仰找到可以存在的理由。第三,“百姓日用而不知”虽然在碑文中没有提到,但这应该是作者李楠隐而未发的,因为在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中作者挑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样一句话自有其深意,不可能只是孤立的引用。清代祝阳的知识分子看到百姓“日见”的总司庙却不知“一阴一阳”的道理,于是借撰写碑文的机会把“理”传播出去。第四,从当地传说与碑刻文字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到民众与知识阶层之间的互动。《周易》所讲“阴阳”之“阳”在百姓的口中是形象生动的“地火”,总司庙所供奉的神灵在百姓眼中则成了“地火”的克星(或者说压制者)。两种文本与解释体系出现的年代我们已经搞不清楚,哪种出现的更早也无从得知,但是有关“阴阳”的传说与碑刻内容对总司信仰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确是不容置疑的。立于 2006年(总司庙重修后)的《万古流芳》新碑中写道:“泰山东麓,祝山之阳有古剎,一阴一阳,神则灵应,庙亦巍峨,流传至今,亦已久矣。”据碑文作者张永讲,“一阴”指总司庙,“一阳”指祝阳。总之,口述与碑刻的互证揭示了祝阳民众为冥神建庙的原因。在这里,地理位置和区域名称对于总司信仰出现和兴起所起到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四、从庙宇碑刻中解读总司庙的创建年代
祝阳村民不知总司庙的创建年代,庙宇现存碑刻⑥仅有“不知肇造何时”的记载,那么总司庙究竟创建于何时呢?总司庙与蒿里山同属一个系统,总司信仰由七十五司信仰发展而来,因此总司庙的创建年代不可能早于蒿里山森罗殿的七十五司神房。蒿里山三曹六案七十五司的形制创始于元代,“至元二十一年 (1284年)由奉训大夫沂州知州严度 (严实之孙)等人于新修之蒿里神祠构曹案诸司之神房。同时并立《蒿里七十五司碑》及《蒿里七十五司神房志》,备载各案司职名”。蒿里山神祠中气势恢宏的七十五司神房被祝阳民众精简成一个比较简单的庙宇形式——总司庙,庙里供奉的神灵“总司大帝”是对蒿里山七十五司信仰的浓缩与升华。由此观之,总司庙的创建年代当晚于元代至元二十一年 (1284年)。
总司庙碑刻中有两块同时提到了一个人名:“余游总司庙,搜剔古碑,读陈观我先生所撰碑记,总司名□殊少确据”;“至于总司之为神,陈明新尚未确言之,余姑弗深考,何敢妄为附会哉”。“陈明新(观我)”这个人名的出现使总司庙的可考历史提前到了明朝末年。陈明新,字观我,是明末清初莱芜地方名人,他曾为总司庙撰写碑刻,证明在他生活的时代总司信仰已经相当有影响了。
史志资料中没有关于泰安总司庙的信息,但在《济阳县志》和沂水县碑刻资料中,分别载有当地总司庙的创建时间。民国二十三年 (1934)修《济阳县志》卷二《建置志·寺观》记载:“总司庙:在城南十五里 (即金之贤一乡)。明崇祯九年(1636)创修,清康熙六年 (1666)、乾隆五年(1740)、道光三十年 (1850)均有重修。”后又发现了山东沂水总司庙清同治八年 (1869)的碑刻拓片,碑文记载“吾邑龟峰岭总司庙,尤灵应之最著者也。创于前代,永随香火之缘;建自名山,常显庄严之象。”济阳、沂水总司庙都创建于明代,祝阳总司庙的创建年代很可能也创建于明代。
总司庙肇始于明代的原因,与当朝统治者的民间信仰政策关系密切。首先,明代“祀典复古”政策出台后,太祖朱元璋采纳宋儒陈淳、元儒吴澄的部分建议,宣布废除泰山神历代封号,泰山祀典局面为之一变。针对泰山的“祀典复古”政策包括:“恢复泰山山川崇拜的原始意义,淡化泰山神人格色彩,取消泰山神的偶像设置,清除其神作为冥府神之含义;同时认为泰山只宜祀于本土与官府,理应废除各地所建东岳庙,禁止庶民预祭泰山;泰山祭处应去庙宇而复坛壝,其祀典由官方专办;泰山神既淡去其人格色彩,当相应撤去其历代封号。”明廷的“祀典复古”政策对以东岳大帝为主要崇拜对象的泰山民间信仰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官府既严禁民间‘非礼之渎’,不允准民间将东岳神作为生死之神加以祭祀,而作为国家祀典的东岳神又与民生漠不相关,很难得到大众认同与崇拜”。在这种信仰背景下,祝阳民众对东岳大帝信仰稍加改造,选取其“主死”功能,糅合泰岳七十五司信仰,创造了总司大帝之神。其次,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完善了祭祀城隍的制度,提高了城隍在神灵体系中的地位,扩大了城隍神的影响,城隍信仰随之盛行于全国各地。在国家祀典里城隍神是城市的保护神,但是在民众心目中,城隍神是与“人世间地方官相对应的冥间地方官”,民众更看重城隍的“冥神”职司。明代盛行的城隍信仰对总司信仰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祝阳信众心目中的总司大帝也多少带有一些城隍神的影子。统治者之所以推崇城隍神,是因为将城隍神看作一种教化手段,让百姓相信城隍神可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冥举不得幸免”,使其知畏而不敢妄为,民间对城隍神“护佑善者,惩治恶者”的功能却也十分认同。而总司神灵最旗帜鲜明的特点和最重要的职能正是“彰善瘅恶”,这也是其受城隍信仰影响的重要体现。
五、总司大帝信仰与永乐移民
祝阳总司庙创建之初的历史可以从耿、赵两个家族的发展史中寻找线索。耿氏是祝阳村的最早住民,祝阳村曾名耿家庄。而赵氏被誉为泰安东部第一望族,明清以至民国期间出现了包括清代名臣赵弘文在内的一系列官宦名流,在祝阳村镇的发展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泰安赵氏家谱》《赵氏族谱序》记载:“予之始祖直隶枣强野鹊窠人也,自明永乐中迁居于泰山东,至今十余世矣。”《重修赵氏族谱序》亦载:“明永乐中迁枣强之民实泰安,赵氏因居州□东。”又《泰安耿氏家谱》《耿氏创修族谱序》言:“但闻吾耿氏枣强野鹊窠人,前明永乐中迁居岱左。不知始居何地,谱不能及。即后居城东大苏庄,旋移祝阳,亦不知由于何时。”耿氏家谱正文“初来”篇则记录耿氏——“始祖枣强野鹊窠人,传闻自明永乐中迁来山东”。由此可见,无论赵氏或耿氏都是明永乐年间迁居泰安的,具体何时居于祝阳虽是语焉不详,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祝阳居民中当有永乐移民的后代。
明代共有洪武及永乐两次大的移民过程,洪武大移民结束后,“靖难之役”使得华北地区再次变得荒无人烟,“它 (靖难之役)摧毁了华北地区洪武大移民的相当一部分成果,重造了一大批新的无人区,战后不得不展开新一轮的移民运动”。永乐年间泰安地区的人口损失虽然比不上黄河北岸,但是由于泰安与东昌、汶上接壤,在沧州、东昌之役时,必定会受到战争的影响,造成人口锐减,给永乐移民的流入创造了条件。据《泰山通鉴》记载:“因‘靖难之役’中,南北数交兵于山东,兵燹屠戮,居民稀少。本年成祖诏迁山西等处民以实山东。其中迁居泰山附近州县者甚众。迁于泰安者有燕姓、武姓等,迁于肥城者有王姓、尹姓、朱姓、阴姓、安姓、董姓等,迁于新泰有牛姓等,迁于宁阳有黄姓等。在此前后,自直隶枣强、北平及福建莆田、南直淮安等地迁入之姓族亦众。”明代的人口迁移历史在祝阳百姓口中也以故事的形式有所流传:“传说很早以前,大概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夏天,山东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雪,人都被冻死了,山东几乎都没有人了,于是就从山西往这里迁了很多人过来。”另有一个版本则说:“朱元璋做皇帝之后大开杀戒,把山东杀得没有人了,然后山西人就迁到这里来了。”抽出两个版本的共同“母题”,即:“明代山东人少,于是有一部分山西人迁到了山东。”⑦
赵耿家谱都将自己的始祖说成是河北枣强野鹊窠人,同时山东有不少地区的百姓都说来自于河北枣强,然而事实是明代河北真定府东部各县中枣强的人口数量最少 (不足 0.8万),永乐年间真定府又是战争“重灾区”,何以能够从枣强迁出来这么多移民?实际上,明永乐年间迁居祝阳的枣强移民有可能直接来自山西或者是山西移民的再迁移。“从地理上分析,山西娘子关→真定→枣强→山东德州是山西移民进入山东的最便捷的通道,至今仍是横贯河北,连接山西与山东的铁路干线所经之地。在长途跋涉后,山西移民在枣强略作休整再赴山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永乐年间从枣强出发到山东的移民中,小部分人可能直接进入泰安定居祝阳,也有可能来到泰安后,随着子孙的繁衍与家族的不断壮大,其后代进一步扩散迁移到祝阳。永乐移民及其后代在祝阳定居后,逐渐与土著相互融合,移民一方面会“入乡随俗”(一般情况下,“融合”过程应当以移民向土著的靠拢、移民融入土著为主);另一方面,移民也常常希望保留一些对故乡及过去生活的共同记忆。假如某一时期来自同一地域的移民在地方社会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那么这些移民因为“人多势众”势必会有意识地通过某些方式把过去的共同记忆流传后世。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头脑里的记忆变成一种切实的存在,并使之内化成为当地百姓生活的固定模式,即“民俗”。这既可以是一种民俗事项,也可以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
祝阳地方社会的永乐移民选择了民间信仰的方式,他们对泰岳阴司信仰进行了改造,使之独立于泰山阴司系统之外,并通过各种方式使之与老家——山西联系起来。方式一:据老道长说“总司大帝在山东有一个东寺,在山西有一个西寺”。据现有资料看来,山西的西寺有可能是村民的杜撰,其目的是通过总司庙将山东与山西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现在的生活区域与山西老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满足移民的特殊心理要求。方式二:将总司大帝的人格化原型附会为宋代大臣寇准。总司庙碑刻上记曰:“祝山之阳有古剎,其肇造不知何时。问其庙,则曰总司;问其神,则曰莱公。……至其所云莱公,则封号也。应斯称者不少,概见考之宋史,惟有渭南寇平仲。”口述与碑刻都将总司神的原型附会为宋代大臣寇准⑧。在民间,寇准被认为是山西人的代表,民间常常将他亲切地称呼为“寇老西儿”。东岳大帝的原型是黄飞虎的说法在民间流传颇为广泛,而祝阳民众特意选择“寇准”作为总司大帝原型,这种选择应当是别有深意的:一方面借此再次强调总司大帝与东岳大帝的区别,表明总司信仰与东岳大帝信仰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另一方面又借“寇老西儿”山西人的身份来暗示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与山西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
总司神灵是明代永乐移民及其后代与泰山土著之间相互融合、排斥的产物,是祝阳民众对泰山信仰文化有选择、有创新的继承。
[注 释]
①“十殿阎君”即“十殿阎王”,之所以有“君”与“王”称号的不同,是根据其信仰归属的不同,佛教常称“王”,道教常称“君”。总司庙里的老道长一直强调“君”的称呼,以示其特殊的道教身份。但总司信仰的本质仍是民间信仰的一种。
②立于光绪三十二 (丙午)年仲春,为山东省济南府长山县南路孟家堰庄全体信众所立。从沙畹在蒿里山所拍摄的其他照片来看,蒿里山神祠周围碑刻林立,多是人们为已故的历代宗亲所立,说明在民间蒿里山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冥神庙宇。
③总司庙正殿墙壁绘有壁画,内容是十殿阎君审判图,画面看起来完全是世间官府的翻版。
④佛教十殿阎王分别是:第一殿秦广王、第二殿韧江王、第三殿宋帝王、第四殿五官王、第五殿阎罗王、第六殿变成王、第七殿泰山王、第八殿平等王、第九殿都市王、第十殿转轮王。
⑤为总司庙撰写碑刻的大都是泰安或莱芜地区的儒生,有的是地方名人,有的考取了功名。撰碑人的儒生身份对其撰写口吻与内容都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用儒家思想对民间信仰文化进行改造,并试图通过此种改造将民间信仰纳入文化大传统之中。碑文虽出自个人,但其中所反映的思想却往往是属于整个儒生阶层的。
⑥总司庙原有碑刻 130余通,现存 53通,包括 8块新碑和 45块旧碑。新碑的立碑时间集中在 2006至 2007年之间,其中除一块叙述 2006年重修过程的《总司庙重修记》外,其他全部为庙会功德碑。旧碑中有 4块残碑年代不详,其余碑刻的年代分布情况为:乾隆年间 2块,嘉庆年间 9块,道光年间 13块,咸丰年间 3块,光绪年间 9块,宣统年间 1块,民国年间 4块。年代最早的碑刻立于乾隆三十一年,题名《双桥碑记》,记录祝阳村村民募化善款修桥两座的事迹;年代最晚的碑刻立于民国 28年,是一块庙产地契碑;其余碑刻则全部为进香功德碑,碑刻正文大都记录庙会或香社的情况,有的还讨论了总司神灵的来历、职司或功能,正文之后则刻有功德芳名。碑刻大都露天存放,风剥雨蚀,有些古碑风化严重,字迹难辨。有鉴于此,我们在征得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同意之后,将古碑全部制成拓片存档,新碑全部拍照存档。
⑦通过分析这两个故事版本可以了解民间对历史的不同解读。第一个版本流传的年代相对更久远,一方面把人口减少的原因附会成下大雪的自然因素,反映出对统治阶级(皇权)的畏惧,怕说实情惹祸上身;另一方面“夏天的大雪”让人联想到窦娥,隐藏着民众的怨情及对统治者的憎恨。第二个版本则可能出现于明末之后,甚或封建社会结束之后,这时人们已经可以说明朝皇帝甚或皇帝的“坏话”了,只是故事的创造者或传播者对历史知识不甚明了,将移民时间错安到朱元璋时代。
⑧据历史记载,寇准是陕西人,但是随着古代小说和戏剧在民间社会的广泛流传,寇准的籍贯已经被“篡改”成山西。
[1]吴曾荣.先秦两汉史研究 [M].北京:中华书局, 1995:367、368.
[2]姜丰荣.泰山石刻大观 [M].北京:北京线装书局,2002:68-70.
[3]周郢.《<泰山志 >校证》[M].合肥:黄山书社, 2007:94、396.
[4]顾颉刚,钱小柏.顾颉刚民俗学论集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411.
[5]朱宁虹.宗教信仰和戏曲[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85-87.
[6]张仲礼,李荣昌.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7]刘慧.泰山宗教研究 [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4:121、122.
[8]贾二强.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 [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5.
[9]陈梦雷.周易浅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20、21.
[10]郑土有,刘巧林.护城兴市——城隍信仰的人类学考察[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12、19、20.
[11]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7、190、321.
[12]周郢.泰山通鉴[M].济南:齐鲁书社,2005:123.
[13]周郢.泰山与中华文化 [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4.
[14]叶涛.泰山香社研究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26.
[15]沙畹.泰山:中国人的信仰 (日译本)[M].(日本)勉诚出版社,19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