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编年笺证》商榷
○顾 农
《鲁迅诗编年笺证》商榷
○顾 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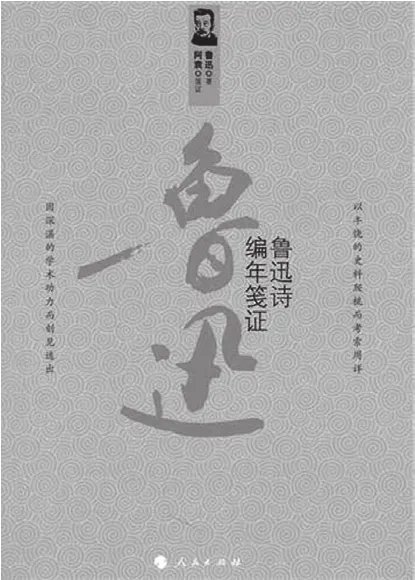
《鲁迅诗编年笺证》,阿袁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
鲁迅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他的小说充满了诗情,杂文则是诗与评论的结合;所以他随手写下的几十首旧体诗以及五四时代的几首新诗,也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学者们写过不少论文和专著。《鲁迅诗编年笺证》(阿袁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是其中最新的成果,并且大有后来居上之意。此书取材丰富,讲究考证,又以唐人李善注释《文选》为榜样,致力于追寻有关文本中语典、事典的出处;据这本书封二介绍,作者就是诗人,怪不得又能体贴入微,时有妙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此,孙郁、熊盛元二先生的序言都给予高度评价。
不过一本书总很难止于至善。智者千虑,容有一失。我读此书除了获得不少知识和启发之外,也不无疑义。姑举三事,以为商榷。
1902年2月的《祭书神文》
关于此篇的“版本源流”,阿袁先生就其中的两句有如下说明——
按,1958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作“香焰絪緼兮烛焰赤”与“君之来兮毋徐徐”,而2005年版《鲁迅全集》则据《周作人日记》手稿影印本改作“香焰氤氲兮烛焰赤”与“君之来兮毋除除”。窃谓前者意义本相通而可改,盖并不有碍于诗意之确切表达也,具见下文注解。而后者虽据《周作人日记》挖改,实则未必稳妥,故仍以1958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及前此有关版本——亦即作“君之来兮毋徐徐”为当,并见该条目之“笺注”。(P28)
按旧版《鲁迅全集》收入之《祭书神文》的文本依据,是周作人解放后以自己的日记为原始材料的回忆录,但他态度不尽严谨,工作不够过细,与原件有些出入;但由于他所拿出来的乃是独家材料,无从校勘,人们只好以此为依据,也就那么收到《全集》里去了。等到《周作人日记》的原件公开了一部分以后,则自然应当直接采用有关日记中的文本来过录。按传统的校勘学手法,这里的一句正文仍应作“君之来兮毋除除”,另加校勘记说明“除除”应作“徐徐”,或疑当作“徐徐”。
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2005年版《全集》以及由此而来《鲁迅诗编年笺证》的文本校勘做得不尽到位。“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句,《周作人日记》在“樨香”下原有一“峕”(“时”)字(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P300),《全集》以及《鲁迅诗编年笺证》皆脱去,应补入。
顺便说说,周作人1902年日记中抄录存稿的那一部分称为《柑酒听鹂笔记》,用的是晋、宋间著名艺术家戴颙(378-441)的典故。戴氏世居会稽剡县,后来迁居吴中,宋衡阳王刘义季迎居于京口黄鹄山、招隐山(今江苏镇江南山)一带。他常常携双柑斗酒,外出听黄鹂声,并说“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冯贽《云仙杂记》卷二);今镇江南山招隐寺有听鹂山房。周作人早年羡慕隐士,尤重乡贤,所以有这样风雅的名目。
1928年4月的《吊卢骚》
1928年4月10日,鲁迅作杂文《头》(后收入《三闲集》),文末活剥清人王士禛《咏史小乐府•杀田丰》“长揖横刀出,将军盖(原诗作“一”)代雄。头颅行万里,失计杀田丰”,作五绝一首以吊法国大思想家卢骚(现在通译为卢梭)云:
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
这首比较难以理解的是最后一句。阿袁先生的解释是——
【造儿童】谓造就儿童教育也。卢梭于1762年出版教育小说《爱弥儿》,提倡儿童身心之健康自由发展,批评封建贵族与教会之教育制度。其时法国当局竟下令焚毁卢梭书籍并欲逮捕之;于是卢梭只得被迫亡命瑞士、英国等地,直到1770年方得重返法国巴黎。(P105)
可是卢梭的这些经历同《吊卢骚》诗,同《头》的全文,又有什么关系呢?鲁迅这篇杂文本来是说,梁实秋新近在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卢骚——答郁达夫先生》一文之大力攻击卢骚,多有影射之意,可谓“借头示众”,其本意在于打击中国进步的新文学家(梁先生称之为“浪漫派”,详见其《浪漫的与古典的》一书),其手法颇近于国民党反动派在“清党”之际把共产党人郭亮的头割下来示众,“遍历长(沙)岳(阳)”,以恐吓群众。
在论争中将文学问题文化问题勉强地同政治事件挂钩,现在看去并不甚可取;但鲁迅在这里也只是涉笔成趣提出的一个类比而已。鲁迅的这首诗其实婉而多讽,他的意思是说,卢骚之倒霉不仅在于生前遭到法国当局的迫害,更在于死后又遭到梁实秋先生如此的攻击,简直弄得无路可走。这里的“穷”就是“日暮途穷”之“穷”——所以要写一首诗来凭吊他。
“头颅行万里”一句迳用《咏史小乐府》的原句,这是有典的。《鲁迅诗编年笺证》引用《后汉书•袁绍传》,当然也可以,而更早则见于《三国志》及裴注所引的材料。汉末大军阀袁绍不听谋士田丰的劝告,反而把他关押起来,结果在官渡一战中被曹操打得大败。“绍军既败,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袁绍死后,其长子袁谭和少子袁尚内讧,分别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建安十二年(207)袁尚、袁熙(袁绍之中子)败走至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诱杀之。《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典略》云:
(公孙康)乃先置其精勇于厩中,然后请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缚之,坐于冻地。尚寒,求席,熙曰:“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
《后汉书•袁绍传》的有关记载当源出于此,但将最后这两句话安在公孙康名下;后来《三国演义》也是如此。据《典略》,袁熙是个明白人,他知道他们弟兄两个的头颅将被公孙康砍下来送给曹操,事既至此,屁股冷一点何足挂齿。按照李善注《文选》的原则,有关资料应引用最早出现者,所以这里应主要引用成书早于《后汉书》的《三国志》。
《杀田丰》诗认为,袁熙 、袁尚兄弟之死,根子还在袁绍不听田丰之计反把他杀了。鲁迅诗中借用这一句仅仅是取其字面上的意思,指出卢骚的头被不远万里地挂到中国来,也是有其现实的原因的。所以接下来的“失计造儿童”一句,是指卢骚之“失计”在于他影响了后来的大批作家,这就是文章中所说的“他现在所受的罚,是因为影响罪,不是本罪了”。诗中之“造”固然是“造就”之“造”,而实乃指其影响而言。正如鲁迅在文章中所说:“假使他(卢梭)没有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就不至于路远迢迢,将他的头挂给中国人看。一般浪漫文人,总算害了遥拜的祖师,给了他一个死后也不安静。”鲁迅诗中的“儿童”当是借指被认为是受到卢骚影响的后代作家。这当然是一个隐喻,用“童”字收尾也有押韵方面的考虑。2005年版《鲁迅全集》沿着过去注释的老路,以“卢梭于1762年出版教育小说《爱弥儿》,提倡儿童身心的自由发展,批评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教育制度”因此遭到迫害来解释“失计造儿童”(第4卷,P94),似失之粘着,离开了鲁迅《头》一文的思路,颇近于古人之所谓“释事而忘义”;《鲁迅诗编年笺证》照录此说,照我看恐怕也是不大中肯的。
1933年的《教授杂咏》其四
诗云:
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
阿袁先生解释道:
此诗系影射谢六逸者。谢氏曾编选过一本《模范小说选》,其中选录鲁迅、茅盾、叶绍钧(即叶圣陶)、冰心、郁达夫等五人之作品,于1933年3月由上海黎民书局出版发行。谢氏先曾将该书序言发表于1932年12月21日《申报•自由谈》,其序言称自身并不是近视眼,而有所谓“匠人”之“墨线”者,亦即能入其法眼者故属难得矣。然则其人固难逃攘窃他人劳动成果为己有之讥。加以谢氏其他方面之奸恶,故作者特作此诗予以讽刺也。(P236)
这些话未免言之过重了。编一部小说选怎么会就是“攘窃他人劳动成果为己有”呢?这部《模范小说选》(上海黎明书局1933年3月版),照我看选得还是比较好的,其中共选短篇小说22篇:鲁迅12篇、茅盾两篇、叶绍钧三篇、冰心两篇、郁达夫三篇,鲁迅一人占了一半以上。书前列有编选凡例四条:
一、本书的目的:(一)供欣赏作品之用或作研究小说理论之参考。(二)作学生的教本或课外读物。
二、每篇作品后面,附有“解说”,此为编者鉴赏原作的所得;希望阅者从“解说”里得到鉴赏其他作品的暗示。
三、我们能够从各种观点去欣赏一篇作品,或是指摘它的缺点。教师如采用本书作为教本,我想不致因为我的“解说”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其次,本书不是“文章病院”,缺点恕不指摘。
四、每个作者的来历,都有简约的介绍。每篇作品的后面,附有参考资料,必须注释或需要习题的地方也附上注释和习题。正文后面有附录数篇,此为研究近代小说的重要论著,读者互相印证,自多趣味。
这个体例应当说是相当好的;中外有不少选家采用类似的办法(例如美国布鲁克斯、华伦合编的《小说鉴赏》,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一般都很受欢迎,特别是年轻读者的欢迎。
谢氏所选的鲁迅的12篇小说是:《故乡》、《在酒楼上》、《风波》、《祝福》、《孔乙己》、《示众》、《鸭的喜剧》、《社戏》、《端午节》、《孤独者》、《伤逝》、《狂人日记》,这里不按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列,大约是考虑到这书可能被作为教材吧,所以取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顺序。
为了便于指称,谢先生给所选文章的每个自然段编上数码;解说的部分先就全文作出简要的提示,然后按自然段的顺序择要地提出若干分析,其中颇有精彩而发人深省者。例如关于《在酒楼上》的第四自然段,谢先生分析解说道:
描写冬天的景色,阅者看了仿佛展开绘卷,简直是一幅活鲜鲜的“雪园沽饮”。注意“老梅……斗雪……满树繁花”,“山茶花……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诸句。作者又比较南方的雪和北方的雪不同的地方,“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这一段描写,非懂得南画趣味的人写不出。西欧的作品里面,很不容易看到这样的表现。这点足见作者艺术修养的湛深。
要言不烦,深中肯綮。编选者注意各门艺术之间的“横通”,分析鲁迅小说中景物描写富于文人画的韵味,提醒读者做中外小说的比较。这样的意见很富于启发性。
这本书中注释很少,大抵只注那些最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例如《狂人日记》中有一句道“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给桀纣吃”,显然于史不合,难以理解。谢先生遂出一注道:“易牙为春秋时人,此为狂人联想的结合。”读者可能会有的困惑立刻得到化解。该书的练习也不多,但设计得很精巧,如《孤独者》后面的一条练习是“将本篇和《在酒楼上》作比较的研究(注意主人公的性格,环境描写,结构诸点)”。这样的题目是有意思的。
各家作品之后附有参考资料,鲁迅的十二篇后所附的是《呐喊•自序》和方璧(茅盾)的《鲁迅论》。全书之末又有八篇参考文章,它们是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论短篇小说》、俞平伯《中国小说谈》、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夏丏尊《评现今小说家的文字》、锦明《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陈勺水《论新写实主义》,虽然稍微杂乱一点,但确有参考价值,足以启发读者作多方面的思考。
鲁迅这首《教授杂咏》固然有些讽刺谢六逸(1896—1945)的意味——这位选家陈义甚高,而且也太自信了——但态度是和善的。《教授杂咏》的其他几首也都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据当年接受鲁迅手书之《教授杂咏》前二首的梦禅先生说,“当时鲁迅诗兴书兴兼浓,挥毫为乐,了无拘束,两首(按指其一、其二)随手而出,看情况没有其他意图”(转引自胡今虚《鲁迅〈教授杂咏〉字幅的受赠者——记梦禅与白萍》,《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其三其四两首应当也是如此。许寿裳先生在《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的游戏文章》中称这一组《教授杂咏》为鲁迅的游戏文章,自是确论。
可是后来的研究者或有求之过深者,以为被鲁迅讽刺过一下的就一定是反面人物。这样的意见似不足取。而阿袁的立言尤为严厉,甚至斥为“奸恶”,不知道有什么根据。谢先生决非什么坏人。已故著名鲁研专家林辰先生对他的这位同乡前辈相当尊重,曾有一篇《忆谢六逸先生》,收在《林辰文集》第三册中(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6月版,P237—241),很容易找到,最宜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