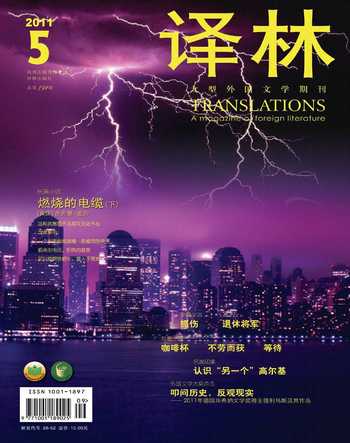古鲁比村庄的孩子们
(英国〕 佩尼洛普•莱夫利 著 郭国良 译
佩尼洛普•莱夫利(1933—),英国女小说家。生于埃及开罗,曾就读于牛津圣安学院现代史专业。莱夫利是位多产作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出版近40部著作。她写了一系列少儿读物,如《星笼》(1970)、《托马斯•肯普的鬼魂》(1973),深受读者欢迎。主要作品有:《通往利希菲尔德之路》(1977)、《时间的财富》(1979)、《最后审判日》(1980)、《根据马克所说》(1984)、《月亮虎》(1987)、《热浪》(1995)、《照片》(2003)以及短篇小说集《只有茶饮失踪了》(1978)、《不请自来的鬼魂》(1984)、《一堆卡片》(1986)等。《月亮虎》夺得布克奖。
当特弗雷•卡特赖特第一眼看见美杜莎喷泉时,他就被喷泉中的仙女塑像吸引住了。这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他停下手推车,仔细地观赏了好一会儿。那些用大理石雕刻的女子姿势优雅,令人赏心悦目。他参加了青年机会项目,来到了洛克韦尔庄园里当园艺学徒,这是第二天了。特弗雷十七岁了。他宁愿自己在别的地方,希望能干些农活,能开开机器,而不是成天与修建篱笆墙和清扫落叶之类的杂活打交道。
洛克韦尔别墅的花园以园艺和雕塑闻名,而位于著名的耶沃克街道尽头的美杜莎喷泉,理所当然的要算是件象征抵抗的作品。美杜莎塑像矗立于滴水的洞穴中,周围长满了蕨类植物。她掌管着这个巨大的喷水池。在喷泉的基部,一群美丽迷人的天仙造型各异,静立凝固。水池的边缘上或坐着或斜倚着富有青春活力的裸体雕塑,有精美的阿波罗,还有纤弱的小仙女。特弗雷完全被吸引住了。美杜莎自身被苔藓和地衣覆盖着,因而无法辨认出她的脸。她的蛇发也早就隐没在岩石和绿色植物的背景中了,以致特弗雷在第一眼时没有看见她。但无论如何,他不想在这里呆太长时间,否则弗莱彻会像一吨重的砖块把他压垮。弗莱彻是花园主管,一个十足的讨厌鬼。他虽然事实上是第一个从特弗雷家族里搬出的侄子,但这并不足以让他有权利粗鲁地对待这位青年机会项目的新成员。因此,在观赏过这些仙女和俊男的雕像以及所有在清凉碧水边嬉戏的石孩后——在八月这样一个酷热的下午,这绝不是个坏地方——他拉起手推车,开始他的下一项工作。
当然,对这个花园他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就出生在一英里外的地方,并在那儿长大。古鲁比村庄集中为数不多的几座相连的茅屋,尽管有些死气沉沉,但它历来为洛克韦尔别墅和那里的花园提供劳动力,并且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对公众开放了。特弗雷的祖父在那里干过活,他的曾祖父以前在那儿也干过。他的父亲则因日子稍好后进入建筑行业得以解脱。现在,经济状况又迫使特弗雷回到那片土地上了。令他极为不满的是,他原已在村公所谋得一职了。他的母亲是属于那种逆来顺受、很少发牢骚的一代人,她责备儿子的不安守本分。“古鲁比村和庄园之间总会有交往。塞克斯比家族的人是有些怪异,但他们为这个村子做过好事。在你祖父那个年代,他们每年为孩子们举行村庄聚会,让他们在喷泉池水中游泳嬉戏,还在马场里开设撞柱戏的场地呢。”可是特弗雷却听不进去。
现在的庄园主是塞克斯比上校,他隐居此地。当地有流言,毫无根据的夸大其辞,说他隐隐地看上去像个邪恶之徒。外边的世界发现他的确是很难相处。艺术史学家对园中的雕塑很感兴趣,但他们都被一纸告示拒之门外,以致关于园中各种东西的起源无任何记录,连拍照也不允许。塑像的年代无法确定,大多数仿佛建于十九世纪,虽然某些巍然耸立在耶沃克街的古典女士或许年代更为久远。美杜莎喷泉简直是一个谜团——那些有幸能仔细观察一番的专家们认为,它作为一组群雕,并不是一致而和谐的:雕塑似乎是在不同时间添加上去的。即使那些天使——位于喷泉脚下的、翻滚嬉笑的可爱孩子们——在老练的目光看来,似乎也有些不相协调,一些经过时间的磨蚀,几乎面容、酒窝消失殆尽,而另一些的笑容以及大理石头发依然线条分明。
事实上,这些花园并没有吸引大批的来访者。广告做得漫不经心,开放的时间也没有准儿,谁也说不清。在那些已经去过的人中,大多数会被那个地方阴郁的气氛所震惊。那种气氛似乎真的要扩散到周围的乡村地区,这样,黑色的灌木树篱和低小的矮树灌木成了别墅花园阴沉的骑马道和抑郁压人的林地的延伸。那些不明就里的人说,开辟些好看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花坛也许会让此地显得生机勃勃;而另一些对早期园艺传统更有经验者,则评论说它风景如画,但即便如此,在他们艰难行走于阴湿篱笆墙之间,看着狭长的远景时,从篱笆两侧射出的、来自狄安娜、丘比特和阿波罗雕像的无神目光,也总会使他们不寒而栗。在开车离开停车场时,如果他们走错路无法转回到主干道上,突然发现被困在古鲁比村子时,那种阴郁感和遗弃感将会愈加强烈。村庄显出一副沉闷的样子,那里既无商店又无酒吧。外表的感知总会因其声誉而加强,这一点是肯定的。据说古鲁比村民从不与外人交往,甚至有传言说他们近亲繁殖,毫无进取之心。可以肯定地说,如今这个村庄充满了几乎被遗弃的氛围,有几间茅屋已经废弃不用了。一些来自伯明翰或伦敦的购房者有心买下它们,却在村公所遭到断然拒绝,因为村里的茅屋决不投放市场。一个人口史学家注意到这个村子的高婴儿死亡率,对此很感兴趣,但却被村民们冷眼相对,吃了好些“闭门羹”。
特弗雷,一位克鲁比村子里长大的孩子,只知道他渴望有一份适合男人从事的活儿,能开开机器——比如拖拉机、翻土机和联合收割机——而不被囚困在花园里,摆弄手推车和耙子,还要忍受因稍稍背离弗莱彻的命令而遭他破口大骂之苦。他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是在孤寂地劳作着,在花园里偏僻的地方跪着双膝拔草,枯燥乏味地耙着草坪,将一车又一车的碎土块推到肥料堆上。这个夏天酷热湿闷,洛克韦尔的雇工们却要求穿着端庄稳重。第一天,特弗雷脱光了上衣,赤裸到腰部,被弗莱彻狠狠地训骂了一顿;后来他穿着衬衫汗流浃背,不禁对他周围的大理石雕裸体——那泛光的躯体,模糊的臀部和胸部轮廓,还有赤裸的纤细四肢——投去羡慕的眼神。毫无疑问,这一切有些许性感,当你独个儿和她们在一起时,看着树林中隐隐地现出她们的臀部,你会情绪高昂起来。
第一眼瞟过美杜莎喷泉后,特弗雷发现自己无可抗拒地被那个地方深深吸引住了。那天,为了体验撩动水中的脸蛋和小手的快感,他还是偷偷转道从那儿经过了好几次。无可否认,这地方确实有些阴森,但那清水似的凉爽和喷泉飞溅出的银白色水珠,足以弥补那阴郁的氛围,而特弗雷也渐渐感觉到那些雕塑是十分友善的。他对某一个仙女情有独钟。只见她蜷曲着坐在池边,害羞得用手遮住她的胸部,好像是在私自裸泳时被人瞅见了似的。初次与她相识,他发现她楚楚动人,可现在,在几次往来之后,他有了不同的看法。特弗雷觉得她的动人凝固有些伤感和脆弱。她那无光彩的石眼里似乎有一种表情,一种永恒的惊愕与讶异。她的脸部也有令他熟识的特征。老实说,她有着玛丽亚姨妈的面容,甚至有点像他自己的母亲。
他变得更胆大了。到喷泉那儿,他逗留的时间更长了。他时而将双手和肩臂浸入水中,时而坐在池边一两分钟,懒洋洋地拍溅着池水。他渴望得到神灵的眷顾,而且神灵不可避免地降临了。他将脸浸入水中,奋力地将水泼在头发上,忽然一个声音令他深感惭愧地站立起来。“游个泳吧,孩子。去吧。脱下衣服。不要害羞自己的身体。你看上去完全能够与它们相媲美。”
是上校——不可能是其他人。他站在那儿,就在美杜莎头部的下方。他矮小粗壮,身穿粗花呢西装,从充满岩石和蕨类植物的洞穴里冲着他咧嘴一笑。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冒了出来,真够令人毛骨悚然的。
“我们——不允许——这样的,”特弗雷支支吾吾地说,“我们甚至不许脱去衬衫。”
“就你和我知道。”上校说,“还会有谁知道?老弗莱彻正在温室里忙着呢。去吧,孩子。别傻了。”他露出牙齿,分明是在对特弗雷微笑,然后就突然消失了。难怪人们说他是一个行为古怪的老混蛋。
特弗雷环顾四周。是真的,弗莱彻在其他地方忙着呢。今天花园不对外开放。这里就他一个人。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就解开了衬衫,脱下工作裤和内裤,一脚踏进池水中。
感觉棒极了,水透心的凉,比想象中的要深一些。他把自己蜷在一起。在水里蹚来蹚去,嬉戏了一番。他游划了几下,然后翻过身来仰面浮在水面上,美美地凝视着淡蓝色天空下摇动着的树叶穹顶。他真想永远呆在那儿。
但是,为了减小风险,最好现在就离开。特弗雷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走到池边,拖着身子爬上池沿,但仍然把双腿浸在水里,以回味最后一刻的欢愉时光。周围的石像映出他年轻淡红色的身体轮廓。他瞥了一眼,略为得意地触摸着自己瘦削的躯体,扁平的胁腹部和长长的双腿。那个老家伙刚才说他什么地方能与那些雕塑相媲美呢?
他看着喷池那边的穴洞,只见满头蛇发、苔藓斑斑的美杜莎直直地瞪着他。光线似乎暗了下来,仿佛太阳被遮住了似的。那些嬉戏的仙女们渐渐地褪去了金色的光彩,变成了灰色。天也不太热了。他想把腿抽出水面。奇怪的是,他感到双腿僵硬,而且沉重无比。也许他的腿抽筋了。他坐在那儿,试图弯曲他的脚趾,但它们似乎一点知觉都没有。他在淡绿色的水中能够看到它们,但那好像是别人的一样。
他伸手去拿放在身后手推车上的衬衫,想用它将自己全身擦干。至少,他试图伸出双手,可是此时他的手臂也麻木了,重得几乎无法抬起来。他用力拖动了一两英寸,但它似乎又僵硬在腿上了。一阵恐慌袭上心头。“我得病了!”他想,“和爷爷一样,我有心脏病——我会死的,就像这样,坐在这里。”他拼命呼叫,但他的下巴却不能动弹。特弗雷使劲全力拖动手掌,将它移到脸部;他触摸嘴巴,看见他的拳头贴着它,却毫无知觉。
他一寸一寸地移动着头部,与自己的僵化搏斗;他竭尽全力朝耶沃克那儿张望,看看是否有人。特弗雷看不了那么远,但他现在正望着喷泉池边的邻伴,望着那个仙女,那个他情有独钟的少女,那个永远羞怯地用手掩着胸部的蛇女。小仙女的石眼与他的目光相碰,似乎不再是惊愕或讶异,而是极度的悲伤。
特弗雷看见自己身体的颜色渐渐隐去,大腿披上了一层精致的大理石。他看见自己变得像仙女们、像阿波罗、美人鱼、森林之神萨特,还有那些天使、那些凝固在喷泉基部嬉戏着的胖孩子们一样。他们那大理石形成的鬈发上布满了金色的地衣。片刻之后,所有的感觉都消失了,特弗雷知道他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而是一个其深处潜藏着某种可怕意识的物体——他意识到,过去的某个时光,他曾听到过或见到过上校。此时,他看见上校又来了,就站在洞穴下,凝视着他的所有一切。可是,特弗雷那时已失去了一切感知。或许已是第二天,或下个月,或是下一年了。对特弗雷而言,时光将停滞:春去秋来,四季交替,而他仍然禁锢在他年轻的身体中。道道雪脊会积聚在他的手臂上,然后堆满他的大腿,最后充斥他的膝部。夏日的阳光会灼热地照在他身上。秋叶会堆砌在他周围,然后慢慢地飘落到水面。他可以听到游客们的嘈杂声。他那一片空茫的大眼睛见证着过往的游人——所有明亮的色彩都随着他那僵硬的身躯而失去光泽。所有的一切都被禁锢在这个永远可怕的记忆中。在那里,俊朗潇洒的小伙子,仪态万千的俏姑娘,天真活泼的小儿童……或端坐着或斜倚。啊,可是一想到这些古鲁比村庄的孩子们,就永远无法释怀。
(郭国良: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邮编:31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