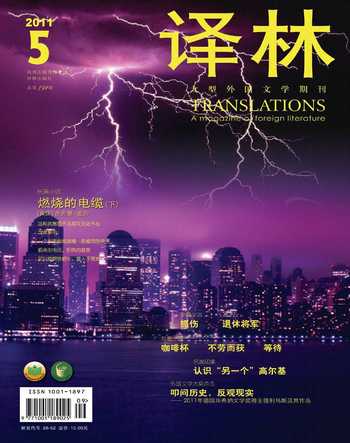《格林词语》: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
宋健飞 王学博
步入耄耋之年的德语文坛名宿格拉斯,2006年曾借“洋葱”之名,不顾自己的声誉受损,层层剥开污点往事,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本人也曾于一夜之间从巅峰跌至谷底,以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备受争议,陷于沉寂。然而格拉斯毕竟不是凡夫俗子,在两年远离社会政治的“潜伏”中依旧笔耕不辍,于2008年又抛出了黑“匣子”,将一幅幅自家的老照片晾晒在世人面前,让人与其一起重温旧梦。如今又是两载似水流年,沉浸在抚今思昔中不能自拔的语言大师,最终在畅游了一辈子的词语海洋里找到了自传三部曲的归宿,这不能不说是作者为自己文学生涯精心设计的一个结局。无论格拉斯本人还是德国媒体及文学评论界,都将《格林词语》视为这位辛勤耕耘并收获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巨匠的封笔之作,对这部2010年问世的深沉厚重的新书,尽管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它毕竟凝聚了格拉斯晚年文学思想的精华,宛如这位世纪老人辉煌一生的一曲夕阳晚唱。
与前两部自传相比,《格林词语》有着自己的独特构思和叙事侧重点。如果说在《剥洋葱》中,格拉斯把洋葱这种西餐配菜佳品作为统领作品的意象,抽丝剥茧般由表及里地暴露出历史的真相,那么在《盒式相机》中,一架能留住人生瞬间影像的爱克发老相机,则恰似童话里的“魔盒”,闪现在故事情节的各个场景,呈现出作者不同阶段的历史图片。但在新作《格林词语》中,格拉斯没有像以往一样把小说的主题用寓意丰富的美术手段形象化,而是选取了格林兄弟编纂《德语大词典》这一德国文化的史实为红线来贯穿全书,于语言词汇的纵横捭阖里,让历史伟人的际遇与自己本人的经历交相辉映。再看其近作的叙事重点,《剥洋葱》的故事情节始于少年时代,经青年从军时期一直写到1959年格拉斯成名作《铁皮鼓》的发表,是作者对三十岁之前的人生的一个总结;《盒式相机》则描写了1960年以来的风风雨雨,笔触涉及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个人情感与家庭生活,倾诉了对家庭的爱与依赖;而《格林词语》巧借史实为索引,笔触的重点则落在陈述格拉斯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
书名引发的争议
新书面世后,有德国媒体批评说,格拉斯虽然将此书冠以《格林词语》之名,但是其中涉及格林兄弟的故事,基本上是众所周知的陈年旧事,毫无新意。此外,在叙述格林兄弟往事的过程中,格拉斯经常穿插自己的故事,从而使书名显得与内容有些脱节,给人一种“名不副实”的感觉。但亦有舆论认为,格拉斯的新书是一部“双重传记”,内容一方面围绕格林兄弟的生平展开,另一方面则铺叙作者的自传。更为准确地说,书中自传的成分占据了主要篇幅,而格林兄弟的那些事儿仅为作者匠心独运的情节导线,貌似主调,实为陪衬。格拉斯在书中力图平行叙述格林兄弟的生平与自己的人生,但总体来讲,他是以名人的故事为作品真正情节展开的背景,从而描述自己的文学、政治生涯。诚然,为了突出二者的共同点,格拉斯在创作中不得不有所取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书评曾指出,格拉斯没有提到格林兄弟作为德语语言学鼻祖这一最重要的史实。不过,既然新作是格拉斯的自传,要求他面面俱到地详尽介绍别人的平描,就显得有些苛求。那么为什么格拉斯要把书名定为《格林词语》而非《格拉斯词语》呢?
或许在名家辈出、各领风骚数载的当今之世,人们已经逐渐淡忘了格林兄弟对德语语言和儿童文学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但是中国读者大都读过《格林童话》中那些脍炙人口的精彩故事,如《小红帽》、《睡美人》、《青蛙王子》等,每一篇都想象丰富,引人入胜。《格林童话》作为德国文化的宝藏,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格拉斯在谈到他与格林兄弟的关系时说道,格林童话故事伴随着他长大,故乡的剧院曾上演的《拇指人》,至今让他难以忘怀。格林兄弟的作品给予他丰富的文化熏陶,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比如《铁皮鼓》中的主角奥斯卡•马策拉特,三岁生日时摔了一跤后便不再长个,塑造这一角色的灵感便来自于《格林童话》中“拇指人”的侏儒形象。另外,格拉斯的其他作品《母鼠》、《比目鱼》等也都带有相当明显的童话色彩,所以《法兰克福汇报》评论说,《格林词语》让人很自然的联想到《格林童话》。
格拉斯在新作中主要叙述了格林兄弟编纂《德语大词典》这一丰功伟绩。格林兄弟所处的时代正值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衰落崩溃之阶段,德意志土地上出现了三十九个各自独立的邦国,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要想统一,首先需要的就是统一的民族语言。在这个背景下,心系统一的格林兄弟开始了“探寻词语的漫长旅程”。 1938年格林兄弟受命编纂德语词典时,本以为数年后就可完成这一任务,不料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一远比其想象的要艰巨百倍的工作,直到他们的生命走到终点也只刚刚开了个头,完成了以德文字母表最初几个字母起首的词汇的收集。1859年弟弟威廉•格林(WilhelmGrimm)去世时,正在编纂“Durst”(饥渴)这一词条;四年之后,哥哥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离开人世,词条“Frucht”(果实)才刚刚完成。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又有数百名语言学家前赴后继地投入到这一宏伟的世纪工程中,甚至在冷战时期,分处东、西德两大意识形态迥异地域的语言文字专家也求同存异,鼎力合作。1960年,总共八十卷的《德语大词典》终于完成,前后历经一百二十二年,透过百年沧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语大词典》是一部德国历史的侧记。
《德语大词典》成书的历史及其在德国语言史上的地位,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格拉斯要选取格林兄弟编纂《德语大词典》这样一个史实来承载其封笔之作的文化意象。在《格林词语》的书名下,格拉斯还添了一个副标题——爱的表白,以示自己对语言学前辈的无限敬仰,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给予他温暖与力量的德语语言的挚爱。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格林词语”是每个德国人的词语。而作为德语语言大师的格拉斯,对与之文学创作密不可分的词语更是情深意长,因为正是通过对千万德文词语的纯熟驾驭和运用,让这位文豪大家得以随心所欲地直抒胸臆,畅抒喜怒哀乐,尽书悲欢离合,这种如同相濡以沫般的挚爱绝非一般人所能拥有。格拉斯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格林的词语”在他的笔下也就不言而喻地成了“格拉斯的词语”。
穿越历史的反思
在新作中,格拉斯娴熟地运用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的写作手法,以跨越时空的生动想象,让格林兄弟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并驾齐驱,其用意就在于通过两者间的对比,制造出某种鲜明的碰撞并从中产生深刻的反思。例如,《格林词语》第一章的标题为“政治避难”,叙述了德国历史上“哥廷根七君子”反抗强权的故事。1829年起,格林兄弟在哥廷根大学担任教授;1837年,新上任的汉诺威国王废除新宪法,复辟旧制度,引起民众不满。格林兄弟联合另外五位哥廷根大学教授,起草了一份抗议书,以示其忠于宪法誓言的决心。文书发表之后,七君子立即被剥夺教授职位,同时雅各布•格林和另外两位教授被判限期离境。雅各布•格林不得不离开哥廷根,前往卡塞尔避难,后来威廉•格林追随其兄也去了卡塞尔。“在格林兄弟看来,国王肆意废除宪法就意味着自己发出的誓言遭到亵渎。”格拉斯在书中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同时也讲述了自己与“誓言”有关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这就是他在第一部自传《剥洋葱》中提到的那段参加党卫军的历史。
在《格林词语》中,格拉斯再次回忆并反思了他年少时的失足。“那是一个冬天清冷的夜晚。我刚好十七岁。我们在林中空地上列队完毕,发誓效忠元首、人民和国家。……战争的结束把我从盲目的誓言中解救出来,我却并没有立刻意识到,那天夜里发出的誓言背后掩盖着多少罪恶。我将永远不会再发什么誓!”加入党卫军无疑是格拉斯人生一个难以洗清的污点,同样都是“誓言”这个词语,可在相隔百年的不同时代的语境中,一个是为了捍卫民主与自由,一个却意味着去戕害民主与自由。相形之下,格拉斯老人不能不感慨万千。
也许正是由于这段经历,格拉斯对作家的认识就多了一层政治内涵。他认为一个作家要敢于对政治社会问题表态,不仅要“妙手著文章”,更要“铁肩担道义”,不能像希特勒统治时期采取“内心流亡”的作家那样,逃避现实,明哲保身。基于这样的信念,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开始积极参加政治社会活动。在《格林词语》中,格拉斯回顾既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指责德国的第一任总理阿登纳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虚伪;回顾他当年不惜搁置手头的文学创作,积极帮助勃兰特参加联邦总理竞选的情景;他批评德国人任意践踏宪法,使宪法失去了格林兄弟眼中的神圣地位;他始终坚定地反对德国的“统一”,认为这不过是西德对东德的吞并;他叹息当下德国作家对于政治的漠不关心;他痛批德国社会的物质化,讥讽其为“享乐社会”。格拉斯在个人政见上毫不妥协,在政治批判上言辞犀利,虽到暮年,也未偃旗息鼓,仍旧仗义执言。
黄昏夕照亦辉煌
在《格林词语》中,八十三岁高龄的格拉斯也谈到了衰老和死亡,其叙述方式仍旧是与格林兄弟互为对照,相伴而侃。面对这一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后生”格拉斯也得向前辈格林兄弟请教。格林兄弟中的弟弟威廉•格林于1859年去世,这对哥哥雅各布•格林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也很自然地促使他思考死亡这一话题。1860年,他写下了《论衰老》一文,并在当时的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宣读。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一般能活到七十岁,多活一点的话就是八十岁。如果人生是美妙的,那是因为我们付出了辛勤的工作。” 七十五岁的雅各布•格林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出这句话,他们兄弟二人晚年致力于《德语大词典》的编纂,将全部心血倾注到这一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之中,虽经重重困难,但却义不容辞,决心要为德意志民族统一奠定语言的基石。雅各布•格林在文中还说道:“我们离坟墓的距离越近,就要越不害怕,越不畏惧,勇敢地说出真话。”这一番话不禁让人想起格林兄弟在哥廷根大学面对强权,挺身而出的风采。格拉斯在自传中引用了文中的这两句话,视其为格林兄弟对自己的教诲——身体可衰,心不能老。正如他在书中所写:“最后的稻穗正摇曳在枝头。” 虽然人生已近末路,但硕果累累的晚年让人欣慰淡定,不再有任何遗憾。
自传中,格拉斯写到自己饱受重听的困扰,而且越来越难以入睡,这一切都让他感觉到死亡的迫近。《明镜周刊》采访格拉斯时曾问他是否害怕生命的终结,格拉斯回答说,一方面他已经成熟到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另一方面,他对未来还保持着一份好奇心:“当然,我还是好奇地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那时芦笋和草莓就会上市。奥古斯特—贝波尔基金会的计划还有待付诸实施;我所写的也许是最后一本书(笔者按:即《格林词语》)还要完成排版打印前的工作;另外,我也不愿离开我的妻子、儿女、孙子孙女;我还想与这个混乱的社会一同前行;我还想周末坐坐过山车,看看足球赛。但是,我身边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只有死亡确定无疑。我要像雅各布•格林那样,把死亡作为一个不请自来,不可回避的客人来接待……” 书中的这段话写出了格拉斯晚年的心境,虽有些怅惘,但更多的则是从容坦然面对生活的幽默与乐观。他在采访中说,自己眷恋的其实都是一些“平庸俗气之事”。作为一名作家,格拉斯在面对死亡时也如同凡夫俗子,透着一股人间烟火的气息。也许这正是生活的真实面,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能阻止死亡的脚步,在死神的面前,一切名利权势都黯然失色,一切绚烂都归于平淡。
然而,平淡并非平庸,也非虚无。作为三部曲的终结篇,为了给自己的自传文学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在《格林词语》整个出版过程中,格拉斯付出了大量心血。《格林词语》的装帧朴实高雅,古拙的字体,经典的色调,凝重的构图,质地甚佳的纸张,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格拉斯的精心构思。酷爱美术的大师亲自操刀设计封面,让简单的字母串连排列,极富创意地传达出作品的主旨。显然,格拉斯追求的不仅仅是留下一部书,而是要留下一个永恒的艺术创作。
书的结尾,格拉斯想象了这样一个场景:夕阳的余晖中,他与格林兄弟泛舟湖面,侃侃而谈。读罢全书,人们眼前也仿佛浮现出三个历经风雨沧桑的老人的背影,其中两个肩并肩走在前头,嘴里时不时蹦出几个德语单词;后面紧跟着一个老人,呼唤着前面两个老人的名字,蹒跚向前追赶。夕阳西下,他们最终并肩而行,缓缓踱着步子,走进落日的余晖,走进属于他们的历史。
以往每部重要作品面世后,格拉斯都要举办一次“译者学习班”,其目的是在各国高手动笔翻译其新作之前先作一自我解读,和与会者共同探讨迻译的难点。2011年3月中旬,格拉斯借在德国北威州小镇施特拉棱举行的欧洲译者研讨会之机,畅谈了与此书翻译的有关问题。当有译者质疑《格林词语》的可译性时,一向对己作的迻译要求严格甚至苛刻的格拉斯破天荒地发话称,鉴于《格林词语》内容涉及复杂的词语元素,该书在传统意义上的确是不可译的。正因为如此,他极力鼓励译者打破成规,摆脱束缚,解放思想,采用自由、开放的翻译策略来处理书中的难点,甚至可以而且也应该将译者自己与德语的不解之缘以及同本民族语言打交道的经验写进译文,并坦言道:“当然,这么做可能会有所失,但更能有所得。”深谙词语之玄机与奥妙的格拉斯诙谐地调侃,说恰恰这种“不可译”是对译者的挑战,会激发他们的斗志,“或许当中文的译本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了”。
此语抑或真能产生激将法的效果。诚愿中文版的《格林词语》能够早日问世。
(宋健飞:上海同济大学德语系教授,王学博:上海同济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邮编:20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