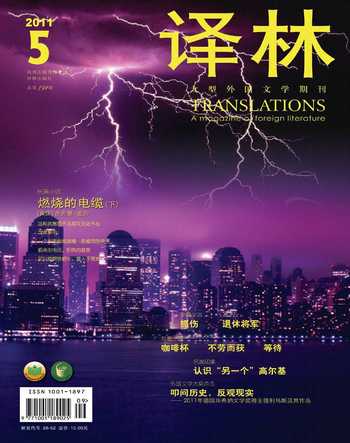退休将军
〔越南〕阮辉涉 著
阮辉涉在2008年1月以本篇小说获意大利第33届诺尼诺文学奖。小说中的越南正处在革新开放初期。在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几经硝烟战火的越南人到底会以一种什么状态来迎接这场变革?让我们静静聆听作者讲述那年身边的故事吧。
1
提笔写这些故事时,我才意识到,那些强烈的情感经过岁月的洗涤已经在熟知的人群中慢慢远去。是我不得已而为之,扰乱了父亲在地下宁静的生活,也希望读者能接受我拙劣的文笔和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我对父亲的偏袒。
父亲名椿,是阮氏家族的长子。阮家在村里是个大家族,男丁的数量仅次于吴家。爷爷曾经学过儒学,后来在村里教书,有两房夫人。大房生了父亲不久后便去世了。爷爷又娶了做染布活儿的二奶奶。我没有亲眼见过她,只听说是个极其刻薄的人。年幼的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尝尽了人间苦辣。十二岁,父亲离开家乡,进入部队。从此就很少回家。
几年后,父亲回家娶了媳妇。当然,这样的婚姻是没有爱情可言的。繁忙的工作间隙,他请了十天假就办完了婚事。爱情是讲求条件的,而时间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条件。
随后,我慢慢地长大,对父亲却知之甚少。而母亲也一定与我有相似的感受。总的来说,父亲的一生,是在枪林弹雨中战斗的一生。
后来,我参加工作,娶妻生子。母亲越发老了,而父亲仍在外奔波。有时他也会顺路回来看看,但每次时间都不长。就连寄来的信也是很短的,可是我看得出,其中蕴藏的都是父亲的关爱。
因为是独子,我享受了父亲带来的一切优待:获得学习机会,到国外深造,就连建房也是父亲帮忙办的。我们的房子是父亲退休前修建的一栋别墅,它外观漂亮,住起来却不太方便。房屋图纸是一位著名建筑专家设计的,他是父亲的朋友。这位专家是大校军官,只熟悉营房建设。
父亲七十岁时以少将军衔退休。
尽管早已提前知道了这事,但当父亲真实地站在面前时,我却仍感到非常地生疏。母亲已经神志不清(母亲长父亲六岁),因此家里也就只有我对父亲回家怀有特殊的情感。我的孩子还小。而妻子同我结婚时正赶上打仗,父亲在外杳无音信,因此也不怎么认识他。但在我们家,父亲一直是荣耀和自豪的象征。甚至在家族和村子里,也是这样。
父亲回来的时候,只带了简单的行李。他身体仍很健康,感叹地说:“人生的大事算是完成了!”“是呀。”我应声。父亲笑笑。全家人因为父亲的回家显得很激动,半个月都没能平静下来。生活作息乱作一团。有一天到晚上12点大家才吃晚饭。客人也纷至沓来。妻子感叹地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杀了猪,请来邻里乡亲一同庆祝。我们村尽管在郊区,却仍保留着农村的习惯。
一个月后,我才有时间同父亲坐下来聊聊家常。
2
在继续讲故事前,我先来介绍一下家庭情况:
我是物理研究院的一名技术员,今年三十七岁。阿水是我的妻子,她是妇产医院的医生。我们有两个小孩,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我的母亲已经有些神志不清,每天只是呆呆地坐着。
除了上面介绍的以外,家里还住着基叔和他的女儿茉莉。
基叔有六十岁,老家在清化。一场大火把他家烧得精光。妻子见他们父女俩善良又可怜,就安排住进了我家。他们单独住在下面的平房里,生活上得到妻子的救济。因为没有户口,他们不能像城里人那样领取粮食补助。
基叔勤劳、能吃苦,照料着家里的菜园子、牲畜和种狗。我家养了狼狗,竟没料到收益颇丰,是家中最赚钱的行当。茉莉虽然性情乖张,却很勤快,是家里的好帮手。妻子教她做油炸猪皮,炒蘑菇,焖鸡肉。茉莉说:“我从不这样吃。”她真的就没这样吃过。
我们夫妻和两个孩子都不用操劳家务,吃穿用洗都归基叔父女俩管。妻子掌握着家中财政大权。我忙着工作,目前正在搞一个电解应用的工程项目。
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我们夫妻感情稳定。阿水是个有文化的人,生活新潮。我们思想独立,看待社会问题相对简单。阿水一边掌管经济事务,一边照顾着孩子。而我呢,看上去愚笨,反应迟钝。
3
重新回到我们父子俩唠家常的那一段。父亲问:“退休了,能做些什么?”我说:“写写回忆录。”父亲说:“不!”妻子说:“您老试着养养鹦鹉吧。”现在街坊很多人养画眉、鹦鹉。父亲说:“赚钱啊?”妻子没说话。父亲说:“再看看吧!”
父亲送给家里每人四米的军用布匹。基叔和茉莉也有。我笑着说:“您真公道啊!”父亲说:“这是生活之道。”妻子说:“全家人都穿上这衣服,就成小连队了。”大家都笑起来。
父亲想跟母亲一起住在下边的平房。让母亲单独吃住的事使他很不高兴。妻子不同意,说:“母亲神志不清。”父亲沉思不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孩子不去亲近爷爷。我让他们学外语、学音乐,很多时候都忙得很。父亲说:“孩子们有什么书吗,拿给我读读。”小眉笑了。小薇接着说:“爷爷喜欢读什么?”父亲说:“容易读懂的。”两个孩子齐声说:“没有。”我给父亲订了报纸。他不喜欢读文学作品。现在的一些艺术性文章很难读懂。
一天下班回家,我看见父亲正站在妻子饲养狗和肉鸡的屋子前,满脸不悦。“什么事情?”我问。父亲说:“老基和茉莉太辛苦了,没日没夜地干活。我能不能帮帮他们?”我说:“让我问问阿水吧。”妻子听了不同意:“父亲是将军。退休了也是将军。他是指挥官,当小兵岂不是乱了套。”父亲没有再说什么。
虽说父亲已经退休,但来家里的客人仍然很多。这让我很吃惊,甚至感到有些欢喜。妻子说:“别高兴……他们只是来求爸办事的。爸,别太往自己身上揽事。”父亲笑了:“这有什么,我只是写封信。像这样:军区司令,这是五十年来我第一次在家过三月初三的节日。打仗那会儿,咱俩是多么期盼这个日子。你还记得在那个路边小村子,慧嫂做的汤圆吗……顺便跟你提一提,M是我的一个熟人,想去你手下工作,云云。我这样写,可以吧?”我说:“可以。”妻子却说:“不行!”父亲托着下巴说:“别人求我帮忙啊。”
父亲总是把写好的信放进20×30规格的公文硬纸信封里,上面写着“国防部”,然后才让人带走。三个月后,信封用完了。他用牛皮纸自制了信封,也是20×30的大小。一年后,父亲改用邮局卖的普通信封,一个五盾。
那年七月,也就是父亲退休后的第三个月,赶上了我的叔叔阮俸娶媳妇。
4
俸叔和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儿子阿尊拉黄包车。父子俩长相吓人,壮如护法,声大如雷。这次是阿尊第二次结婚了。前妻因为家庭暴力离家出走。阿尊到法院告她跟男人跑了,法院也只得作罢。这一次结婚,对方名叫金枝,做幼教工作,有点文化。听说是因为怀上了小孩才闹出结婚这档子事儿。金枝长得漂亮,做阿尊的媳妇等于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尽管我们不喜欢俸叔一家人,但所谓 “血浓于水”,逢年过节仍然有来往。俸叔常说:“臭书生!看不起劳动人民!不是看在他父亲面子上,我早就把门锁起来了!”尽管这样说,俸叔还是照样过来借钱。妻子是个苛刻的人,每次都让俸叔打欠条。俸叔很恶,说:“我还他叔呢,借钱跟个地主似的。”很多次俸叔借了钱都没有还。
俸叔娶媳妇,邀请父亲当主婚人:“金枝的父亲是副局长,你是将军,门当户对。以后孩子们就靠你罩着了,我一个车夫,不值啥钱!”父亲同意了。
婚礼办得怪里怪气,十分庸俗。包了三辆汽车。宴席快结束的时候,过滤嘴香烟已经抽完,只得换成了卷烟。五十桌酒席有十二桌都空着。新郎穿黑色西服,系红色领带。这是我衣柜里最漂亮的一条领带,虽说是借,但肯定是有去无还了。六位伴郎打扮一致,都穿着肥大的裤子,剃着吓人的胡子。婚礼开始时,由乐队演奏《万福马利亚》。接着一个男子登台独唱了一首极其恐怖的歌曲,他跟阿尊是同一个黄包车合作社的:
“啊,啊,啊。鸡回头吧。
我们行走江湖,找钱。
钱啊,赶快跑进我们的口袋。
啊,啊,啊。颓然的鸡。”
轮到父亲说话了。他很慌张,不知所措。准备好的发言稿言辞过于华丽。每句话结束时单簧管总是胡乱地应和着。鞭炮闹翻了天。小孩们随便说着话。父亲略过了整段话。他拿着稿子,气得全身发抖。这群乌合之众让他惊骇、难过。副局长亲家也是惊慌失措,把酒洒到了新娘的裙子上。乐队演奏着披头士、ABBA乐队的歌曲,欢快熟悉的音乐将这一切掩盖起来。
很快,让父亲烦扰的事情发生了。新娘婚后十多天生下小孩。俸叔很难堪,慌乱不知所措。于是,喝醉酒时把媳妇赶出了家门。阿尊很生气,拿刀差点砍死俸叔。
没有办法,父亲只得让金枝住进了我家。家里多了两口人。妻子没说什么。只是茉莉又多了一个活儿。好在她不介意,又喜欢小孩。
5
一天晚上,我正读着苏联杂志《伴侣》,父亲悄悄地走进来说:“我想跟你聊聊。”我给他冲咖啡,他不喝。父亲问:“你留意过阿水的工作吗?我想起来就全身哆嗦。”
妻子在一家妇产医院工作,专给人打胎。她每天都把医院里剩下的胎盘装在瓶子里带回家,由基叔做给猪和狗吃。其实我知道这事,但也没在意。父亲把我领到厨房,指着食槽,里面全是快成人形的胎盘。我悄悄地走开。父亲哭了起来。他把装胎盘的瓶子扔到狗堆里:“死东西!老子不需要这样赚钱!”狗群叫了起来。父亲回到屋里。妻子进来跟基叔说:“为什么不放进碾碎机里?为什么让父亲知道了?”基叔说:“我忘记了。对不起。”
12月,妻子叫人把狼狗卖掉了。妻子对我说:“你别再吸印度烟了。今年咱家少赚2.7万,乱花掉1.8万,总共是4.5万。”
金枝休完了产假。她说:“谢谢大家,我准备带孩子回家。”我问:“回哪里?”阿尊因为流氓罪进了监狱。金枝带着孩子回了娘家。父亲租了出租车,亲自把金枝送回家,并留下来玩了一天。金枝的父亲刚从印度出差回来,送给父亲一块花绸子和半两综合膏药。父亲把绸子送给了茉莉,把半两综合膏药送给了基叔。
6
春节前,基叔对我们夫妻俩说:“我有事相求。”妻子问:“什么事?”基叔回答得含含糊糊。大意是想回老家看看。基叔跟我们住在一起已经六年,有了点积蓄,希望回家重新把妻子的坟墓修缮一下。放了这么久,棺材都陷下去了。“尽生者之义”。况且住在城里,也想衣锦还乡回老家看看亲戚朋友。妻子打断了他的话:“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基叔挠挠脑袋说:“去十天,农历12月23日前回来。”妻子想了想说:“好的。阿纯啊(纯是我的名字),你可以请假吗?”我说:“可以。”基叔说:“我们想请老先生一块去乡下玩玩。就当旅游了。”妻子说:“我不喜欢。父亲怎么说?”基叔说:“老先生已经同意了。没有老先生的提醒,我也想不到迁葬这事。”妻子问:“你们父女俩有多少钱?”基叔说:“我们有三千盾,老先生给了两千盾。一共是五千盾。”妻子说:“算了,别用父亲那两千了,他那份我补给你们,再多给五千。这样你们有一万盾,可以回家了。”
出发前一天,妻子做了饭。全家人,包括基叔和茉莉在内,坐在一起。茉莉很高兴,穿着父亲拿回家的布匹做成的新衣服。小眉和小薇跟她逗趣:“茉莉姐最美了。”茉莉不好意思地笑笑:“才不是呢。你们妈妈最漂亮。”妻子说:“坐火车时多照顾下老先生。”父亲说:“我还是不去了。”基叔不高兴了:“不行!我已经给老家打过电话。这样不是坏了名声吗?”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有啥名声?”
7
星期天的早上,父亲和基叔、茉莉一起回了清化。星期一晚上,我正在看电视,听到“扑通”一声,忙跑出去看个究竟。母亲摔倒在院子边。她老人家神志不清已经有四年,给吃的知道吃,给喝的知道喝,就是要人提醒着上厕所。每天由茉莉照顾着倒是没什么问题。今天由于我的疏忽,给她吃了东西却忘记提醒她上厕所。我把母亲扶进屋。她一直埋着头,没看到什么伤痕。半夜起身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全身冰凉,双目无神。我有些害怕了,叫来妻子。妻子说:“母亲快走了。”第二天,母亲没有吃饭。第三天,母亲还没有吃饭,大小便也失禁了。母亲的床单由我换下来洗。有一天换洗了十二次。我知道阿水和孩子们爱干净,所以每次换下来就马上拿去洗。母亲把喝下去的药全都吐了出来。
第七天,母亲突然坐了起来。一个人能蹒跚地走到院子里,也能吃下饭了。我说:“已经好了。”妻子没说什么。下午的时候,看见她拿回十多米白布,又叫来了木工。我问:“准备后事啊?”妻子说:“不。”
两天后,母亲又瘫在床上,像以前那样,不吃不喝,大小便失禁。她身子一斜,吐出一摊发臭的棕色黏稠液体。我给她倒补药,妻子说:“不要倒。难为母亲了。”我大哭起来。我很久都没这样哭过了。妻子让我忍住,过了一会说:“随你。”
俸叔来看望母亲。他说:“就这样翻来覆去地躺着,真是难为她了。”接着又问:“姐姐,能认出我吗?”母亲说:“能。”“那我是谁?”俸叔又问。“是人。”母亲答道。俸叔哇地大哭起来:“还是姐姐最疼我。全村、全家族的人都叫我狗崽子。妻子叫我无赖。阿尊那小子叫我混蛋。只有姐姐叫我人啊。”
干尽坏事且性情粗暴、鲁莽的叔叔,第一次在我眼里变成了一个小孩。
8
母亲走后六个小时,父亲赶回了家。基叔和茉莉说:“是我们不好。如果我们在家,老夫人就不会走了。”妻子说:“胡说。”茉莉哭着说:“老夫人,您是骗我的吧?为什么不让我跟您一起走,好伺候您呢?”俸叔笑了:“你想跟姐姐一起走,就一起走吧。我替你做棺材。”母亲入殓的时候,父亲哭了,他问:“为什么走得这么快?是不是每个老人都死得这么难受?”俸叔说:“你是糊涂了。我们国家每天都有上千人这样难受地死去。你手下那些士兵,能挨一子弹就归西的,那才叫爽呢。”
我去布置灵堂,吩咐木工把棺材做好。基叔一直守在做棺材的木堆旁。木匠吼着说:“怕我们偷木料啊?”俸叔问:“几厘米的木板?”我说:“四厘米。”俸叔说:“做椅子的木料。现在谁还在用塌榔木做棺材?等迁葬的时候,把这口棺材给我吧。”父亲忧郁地坐着,看起来很痛苦。
俸叔说:“阿水,给我做点白煮鸡和米饭吧。”妻子问:“叔叔,煮多少米?”俸叔说:“天哪,怎么今天这么客气?三公斤。”妻子跟我说:“你家亲戚太恐怖了。”
俸叔问我:“家里谁掌管经济?”我说:“媳妇。”俸叔说:“这是平常。我问的是,这次的丧事谁管钱?”我说:“还是我媳妇。”俸叔说:“不行啊!外人总是外人。我去告诉你父亲。”我说:“叔叔别说啊。”俸叔说:“给我四千盾。你打算办多少桌?”我说:“十桌。”俸叔说:“还不够杠夫吃呢。你再跟你媳妇商量一下。四十桌。”我给了他四千盾,然后进了屋。妻子说:“我全听见了。我打算摆三十桌,八百盾一桌,三八二十四。二万四千盾。六千盾用来备用。买东西的事由我来操持。菜交给茉莉来做。别听俸叔的。他是个无赖。”我说:“他已经拿了四千盾。”妻子说:“真是气死我了。”我说:“他过来要的。”妻子说:“算了,就当作工钱。他人不坏,就是太穷了。”
吹鼓队来了四人。父亲跟在后面。下午四点,开始入殓。俸叔在母亲的嘴里放上钱,说着:“拿去渡河吧。”接着又放了纸牌。解释说:“没事。以前姐姐经常玩纸牌。”
那天晚上,我守着母亲的棺材,静静地想了很多事。死亡终会到来,每个人都不例外。
院子里,俸叔和几个杠夫在打牌。每次赢了钱,他都跑到母亲棺材前说:“给姐姐磕头,保佑我赢他们口袋里的钱。”
小眉和小薇陪着我,也没有去睡。小眉问:“为什么人死了,坐渡船还要给钱?为什么把钱放进奶奶嘴里?”小薇说:“爸爸,这是不是缄口费?”我哭着说:“你们不理解,爸爸也不理解。这是迷信。”小薇说:“我知道了。人生来就需要很多钱。死了也一样。”
我觉得很孤单。孩子们也很孤单。一群人都在打牌。父亲也在其中。
9
从我家到墓地,走近路只有五百米。可是走大路,穿过村子的大门,足足有两公里路程。道路不宽,不能开灵车,只得用肩膀扛着棺材。杠夫换了三十人,有许多人我们夫妻俩连名字都不知道。他们像扛柱子一样抬着棺材,一边走一边嚼槟榔、吸烟、聊天。休息时,全都横七竖八地靠在棺材边。有人躺在棺材上说:“太凉爽了。要是不忙,就在这睡到晚上。”俸叔说:“各位大爷,快点走,还要回去吃饭呢。”杠夫们这才又动起来。我按照送葬习俗,拄着棍子在棺材前面倒着走。俸叔说:“哪天我死了,杠夫们随便打牌,丧宴不是猪肉就是狗肉。”父亲说:“你啊,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开玩笑!”俸叔不说话,又哭了起来:“姐姐啊,你骗我,怎么就抛下我走了呢……”我心想:“难道死人都在骗活人?”
把母亲安葬好后,大家都回去了。二十八桌饭菜很快端上了桌。看到这些,我不由佩服起茉莉。每一桌的人都在问:“茉莉呢?”茉莉急匆匆地应声,跑过去上酒、上菜。晚上,茉莉洗完澡,穿上新衣服,站在供台前哭起来:“老夫人啊,我对不起您,没带您去田边看看……之前您说想喝蟹粥,我胆小怕螃蟹,不敢做,您没能喝上……现在去市场,我都不知道给谁买零食吃了……”我看着心里难受。我已经有十年没给母亲买过一块饼或一袋糖了。茉莉哭着说:“要是我在家,您就不会走了。”妻子说:“不要哭了。”我有些发火:“让她哭去。葬礼是该有人哭的。家里还有谁能这样哭?”妻子说:“三十二桌。你帮我算准确了吗?”我说:“算准确了。”
俸叔说:“我看了看时辰。依姐姐走的时间来看,她会入殓一次,家中有两人重丧,迁葬一次按照迷信的说法,如果死的时间不好,家中亲属当年还会有人过世(重丧),还会遇到迁葬的情况。。需要掩符镇邪吗?”父亲说:“屁的符。我一辈子埋了三千人,从没用过这玩意。”俸叔说:“这才叫爽呢。一颗子弹了事。”他弯弯手指,做出扳动机枪的样子。
10
那年春节,家里没有买桃花,也没有包粽子。初二下午,父亲单位派人过来悼念,送来五百盾。父亲以前的副手章叔现在已经是将军。他专门到母亲的坟前上了香。勤务大尉阿清跟在后面,朝天上开了三枪。这之后,村里的小孩都私下议论部队放了二十一发大炮悼念母亲。章叔问父亲:“想回部队看看了却心愿吗?5月演习。单位派车来接你。”父亲说:“好。”
基叔领着章叔参观了我家。章叔对父亲说:“你家真是厉害。花园,鱼池,猪圈,鸡窝,一应俱全。”父亲说:“儿子弄的。”我说:“妻子弄的。”妻子说:“茉莉的功劳。”茉莉不好意思地笑了,头跟拨浪鼓似的摇着:“不是这样的。”父亲开玩笑地说:“这是紧跟菜园—池塘—猪圈模式啊。越南革新开放后,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大年初三早上,金枝坐着三轮车抱着孩子来拜年。妻子给了一千盾压岁钱。父亲问:“阿尊有没啥消息?”金枝说:“没有。”父亲说:“是伯父的错啊。我不知道你有小孩了。”妻子说:“这不是什么稀奇事。现在哪还有处女。我在妇产医院工作,这些都知道。”弄得金枝很难堪。我说:“别这样说。当处女真的不容易。”金枝哭起来:“我们这些女人很屈辱。生了个女儿,我都伤心死了。”妻子说:“我还有两个女儿呢。”我说:“那你们想想,男人难道不屈辱啊?”父亲说:“有良心的男人就会觉得屈辱。良心越多,越屈辱。”妻子说:“我老公发神经了。别理他,吃饭去。今天有金枝,我专门做了莲子炖鸡。管他什么良心,吃饭才是大事。”
11
我家附近住着一位孔先生,小孩都管他叫孔子。孔先生在鱼露公司上班,却喜欢作诗往《文艺报》投稿。他经常到我家来玩,说:“诗歌是美妙的。”他把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美国诗人惠特曼等人的作品读给我听。我不喜欢孔先生,认为他来家里玩更多的是扮潇洒。有一次,我在床上发现了妻子的一本手抄诗集。她问我:“孔先生的诗你读过吗?”我摇摇头。妻子说:“你老了。”我的内心突然害怕起来。
有一天,我忙着单位的事回家晚了点。父亲在门口等着我,说:“傍晚那个姓孔的小子过来玩。他跟阿水一直开着玩笑,两人现在都还没回来。太过分了。”我说:“去睡吧。留意这些干吗?”父亲摇着头,上了楼。我骑着摩托车,去街上乱转,直到最后车没了油。我架好车,像无业游民一样坐在一个花园的角落里。一个脸上涂着粉的女人过来问我:“想玩玩吗?”我摇摇头。
孔先生故意回避我。基叔很生气,有一天,他跟我说:“你揍他嘛!”我差点就点头了。又一想:“还是算了吧。”
我去图书馆借了点书,试着读了读洛尔迦、惠特曼这些文人的作品。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优秀的作家内心都是极其孤单的。突然,我有点理解孔先生了。只是对他的无赖行为又感到气愤。为什么他不把自己的诗给别人看,要给我媳妇看?
父亲说:“你太软弱了。难道真想一个人过?”我说:“不是这样的。人生如戏。”父亲说:“你说这是在演戏啊?”我说:“不是演戏,但也没那么严重。”
父亲说:“为什么我总是格格不入?”
单位打算派我去南方工作。我问妻子:“我去吗?”妻子说:“别去。明天你把浴室的门修一修,门坏了。那天小眉正在洗澡,我看见姓孔的经过打算占小眉的便宜。那个畜生,我把他锁门外了。”妻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我难受地背了过去。如果小薇在,她肯定要问:“爸爸,这是不是鳄鱼的眼泪?”
12
5月,父亲以前单位派车来接他回去。阿清大尉还拿着一封章叔的来信。父亲双手颤抖地握着信。信上说:“我们需要你,希望你……但能来就来,我们不强迫。”我认为父亲不应该再回去了,但这样说出口又不太好。父亲退休后,身体完全不行了。今天拿信的时候,见他又恢复活力,我也很高兴。妻子把准备好的生活用品放进行李箱。父亲说:“放背包里。”
父亲一一地同乡亲告别,又去了母亲坟前,让阿清朝天上开了三枪。晚上,父亲叫来基叔,给了他两千盾,让他刻一块妻子的墓碑寄回清化。然后又叫来茉莉:“你要嫁人啊。”茉莉哭了起来:“我不好看,没人娶我。况且我又容易轻信别人。”父亲哽咽着说:“孩子啊,难道你不知道容易相信别人正是活下来的力量吗?”我没有料到,这些恰恰是父亲此行不再回来的预兆。
上车前,父亲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学生练习本,给了我。父亲说:“我在里面记了些东西,你试着读读。”小眉和小薇跟爷爷告别。小眉问:“爷爷,您去战场吗?”父亲说:“是的。”小薇问:“这个季节,去战场的路上风景很美吧?”父亲批评道:“太放肆了啊!”
13
父亲走后十多天,家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基叔和俸叔在池塘里打捞垃圾的时候突然发现池底露出一个瓦罐底(妻子付给俸叔两千盾一天的工钱,管饭)。两人卖力地挖,不料又发现一个罐子底。俸叔认为这肯定是以前老人埋的东西。两人把事情告诉了阿水。阿水过来看了看,也跑下去挖。接着茉莉、小眉、小薇也跳进池塘里开始挖瓦罐。家里脏得全是泥。妻子只得把池塘拦住,租了个水泵来抽水。大家都屏气凝视。俸叔最好笑,说:“我是最先看到的。一定要分给我一个瓦罐。”忙乎了一整天,挖出来两个破空罐子。俸叔说:“一定还有。”又开始挖。于是又多挖出一个罐子,也是破的。全家人都累了。肚子咕咕地叫着。妻子派人买了面包,补充气力继续挖罐子。挖了快十米,终于挖到一个小瓦瓶。大家都很高兴,认为里面装的是金子。打开来看,是一串生锈的“保大通宝”铜钱和一枚已经被腐蚀了的勋章。俸叔说:“哎呀,我想起来了。以前和阿仁到韩信家偷东西,被发现了,阿仁那家伙就把这个小瓦瓶扔到了池子里。”全家人肚子都笑疼了。阿仁是郊区这一带有名的大盗。韩信之前是法国殖民军队的士兵,参加了“南龙喷银,驱逐德寇”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遭德国侵略,越南的官僚和资本家捐钱、捐物、出人,帮法国驱赶德寇。 两人很早前就死了。俸叔说:“没事。现在就算全村的人死了,我都有足够的铜钱往他们嘴里放了。”
第二天上午,我起床时听见有人叫门。原来是孔先生站在外面。我想:“妈的,这混蛋是我命里最不祥的征兆。”他说:“阿纯啊,有你的电报。你父亲去世了。”
14
章叔在电报中说:“阮椿少将在×日×时执行任务时牺牲。明日×时在烈士陵园举行葬礼。”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妻子很快把所有的事安排好了。我出去租车,回家发现一切都办妥当了。妻子说:“门锁在楼上的房间里。基叔留下来。”
汽车从第一公路去高平。当我们赶到的时候,父亲的葬礼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
章叔说:“我们愧对你家呀。”我说:“不是这样的。人都有命。”章叔说:“你父亲是位值得敬佩的人。”
我哭了。从没有像这样痛苦地哭过。现在我才知道了“像死了父亲一样地哭”是个什么哭法。似乎这是人一辈子最痛苦的一次哭泣。
父亲的墓建在了烈士陵园。妻子带着相机拍了很多照片。第二天我就要求回去了。尽管章叔挽留,可我还是坚持要回家。
回去的路上,妻子让把车开慢点。俸叔第一次出远门,很新鲜。他说:“我们国家真是如画般美丽呢。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要爱国。要是在老家,尽管河内文化根基深,却不能体会到这种热爱。”妻子说:“因为你习惯了。其他地方的人也这样,他们喜欢河内。”俸叔说:“嗯,住在这个地方喜欢那个地方,这里的人喜欢那里的人。都是祖国的地方,祖国的人民。祖国万岁!人民万岁!”
15
我的故事到这里就快结束了。日子又恢复到父亲退休前的样子。妻子继续忙着工作。我也完成了电解应用的工程项目。基叔变得不爱说话,部分原因是茉莉的坏毛病更严重了。闲暇之时,我会翻翻父亲写下的东西。我更加了解他了。
以上就是父亲退休一年多来的一些琐碎小事。我将此看作是对父亲的怀念。如有不妥之处,请见谅。谢谢。
(白洁: 北京海淀区5102信箱80号,邮编:10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