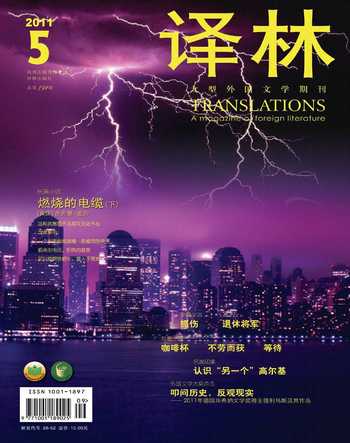抓伤〔英国〕
乔尔•莱恩 著 杨露萍 译
乔尔•莱恩,英国小说家、诗人、评论家、编辑。1963年出生于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埃克塞特,目前在伯明翰南部从事商业出版工作,而伯明翰这座城市也常常成为他笔下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他曾于1993年获得英国青年诗歌艾瑞克•格里高利奖(Eric Gregory Award),并于1994年和2008年两次荣膺英国奇幻文学界最高荣誉英伦奇幻奖(British Fantasy Award)。
他的短篇小说主要属于恐怖、黑暗、奇幻类型,长篇小说则多倾向于主流文学。目前已经出版的短篇小说有奇幻小说集《地线及其他》(The Earth Wire and Other Stories,1994)和《迷失之地及其他》(The Lost District and Other Stories,2006);长篇小说有《从蓝到黑》(From Blue to Black,2000)和《蓝色面具》(The Blue Mask,2003);诗歌集有《屏幕边缘》(The Edge of the Screen,1998)和《腹地之患》(Trouble in the Heartland,2004);编辑出版物有都市犯罪及悬疑小说集《黑暗伯明翰》(Birmingham Noir,2002,与史蒂夫•毕肖普合编)以及超自然恐怖小说集《地下》(Beneath the Ground,2003)。
本文《抓伤》(Scratch)被选入作者的小说集《迷失之地及其他》中,也被选入了由美国著名的推理奇幻小说编辑艾伦•达特罗(Ellen Datlow)所编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曲折:关于猫的恐怖小说》(Twists of the Tale: Cat Horror Stories,1996)中。
你知道吗?我忘记妈给她取的名字了。只记得我暗地里叫她萨拉。是萨,不是莎。我姐的名字。别冤枉我,拿她当亲姐可不是装出来的。除非发生了所谓的世事巨变。但我可不信。我只觉得一切事情皆有规律。如同音乐、报复或爱情。
我没见过我爸。即使见过,我也认不出。我妈和他相识也不过几个钟头。他没留下电话号码,所以我妈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也无法联系他。我妈对我说的唯一一件关于他的事是没有戴避孕套意识的人不配做父亲。我听后大笑。萨拉的父亲和我们住的时间稍长一些,大概有几个月吧。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同母异父。她一直喊我弟弟,她比我大十八个月。
①题目“scratch”在英文中语意双关,一方面取“抓伤、擦伤、刮伤”之意,暗示主人公所受身体、心灵上的伤害;一方面取“以牙还牙(Scratch me and Ill scratch you)”之意,暗示主人公将对不公的命运予以回击。
我们住在奥尔德伯里英格兰西米德兰兹郡一镇名。的政府统建房里。奥尔德伯里是个好地方,但这些统建房突兀地竖立在各种工厂和发电站之间,实在不算好。这里交通可以直达,但是商店、民宅一概全无。统建房主要有两处,一处是一条街两边盖的三四层方方正正、一模一样的房子,像幼儿园里的某些东西。但现在这些房子不是倒了就是烧了,基本没人在住。另一处盖在一块荒地的斜坡上,一栋栋塔楼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九楼。所有窗户玻璃都用金属丝箍得严严实实。一年四季,房子都是冷冰冰的。
生下我之后,妈就患了抑郁症,必须接受治疗。邻居帮忙照看了我们一段时间。后来,妈又做了绝育手术。人和猫的一个不同点就在于,人才不管能不能生出孩子,他们想操就操。我和萨拉很小的时候,家里便有形形色色的男人来往不断。有时只过一夜,有时好几个星期。有个男人断断续续地呆了近一年。我知道他结过婚,因为他和我妈经常为着他要不要离婚而吵个不停。最终他还是没离。
有些男人会带些东西给妈。但妈却从不卖肉做妓。有些人则拿东西走,我是指除了所有男人都拿走的东西。对于我们的这些爸爸,我只能说他们通常比较识相,知道什么时候该走人。但有一个例外。那时萨拉八岁,因得了流感没去上课。我刚上小学,和她念同一所学校。我放学到家,却见有警察在。妈脸色惨白,端茶水的双手颤抖不止。说起话来嗓音嘶哑,仿佛已经哭了很久很久。不记得她当时说过什么了。正要往我和萨拉的房间里面进时,我被警察拦住了。
让他跑掉了。妈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因为忙工作而托他照顾萨拉。我以前还挺喜欢他:他对我和萨拉都很好。还以为他会一直如此。葬礼过后我回到学校,发现似乎所有人都比我更了解内情。我学会两个新词:强暴和勒死。没人愿意和我多说句话。一贯看我不顺眼的小子们不愿趁人之危,一贯拿我当朋友的同学又怕说错话。或者他们觉得我就是扫把星。妈也不怎么和我讲话。她念叨的全都是怎么找机会逮住他,而后收拾他。她还开始搜集各种刀子、刀片、碎玻璃碴等等。她时不时把这些东西摊开在桌上看,并拿起来划划胳膊试试它们够不够锋利。而我能想到的一切只有萨拉。每天,无论我身在何处,我总能看到她在微笑,听到她在讲笑话,感觉到她的双手,像以往每天早上一样,将我从睡梦中摇醒。这些情景无比清晰,正如你发高烧时眼前所见的一切。
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再没有男人上门。有个社工每周二都过来找我妈谈话。有几次还单独和我谈,问我愿不愿意去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妈以前说过,如果被送到孤儿院,八成要挨打被使唤。有段时间我也上了收养名单,但没人要。后来我才明白,如果你倒过大霉,人们就不会再喜欢你,因为你不再天真了。很多人想要天真,因为他们喜欢无知。有些人想要天真,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天真。我既不无知也不天真,而是自闭。回头想想,三年来,我几乎没开口和别人说过话。
除了萨拉——这是只猫。妈买来给我们做伴的。地方政府想重新安置我们,但安排的新住处只会更差更烂。离开这里的话,妈很难保住工作并同时照看我。尽管她只是在流水线上给产品上包装,但在黑乡英格兰西米德兰兹郡一工业区名。失业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
这是只小母猫。几乎浑身黑色,只有上半边脸、前爪和尾巴上点缀着几处白色。双眼狭长,透着灰绿色,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你。我妈在楼梯口给她放了只碎石盘子。该死的塔楼根本不是养宠物的地方。但萨拉却总能绕开禁止一切外来者进入的安防系统,自由出入。她常在附近来回踱步,时而把死麻雀、死老鼠衔回家,后来被我妈制止,她才不这样。在家时,她就卧在离电暖炉几英尺的地方,一动不动。绝育后的猫大都这样。我想,她永远不会原谅人类使她丧失了性别。
人们常说猫怎么喂都成不了家猫,确实如此。特别是母猫。无论喂什么,她们依旧在外捕食。带回来的战利品可不是送你的礼物,而是在教你。把你当作小猫咪来训练。她们蹭你亲近你,可不是出于爱:是留下气味,说明你已成为她们的地盘了。猫的世界里就满是这些东西,地盘、朋友和敌人、安全的路和危险的路。这是规律。
我不知道起先为何叫她萨拉,也不知道为何她对我这样亲昵。她会跟着我在房子里转悠,跟着我出去散步、买东西。晚上,她蜷成一团,伏在我床边。我习惯了她的静默无声,习惯了她走路时小心翼翼的步伐。没有她,我感到的不是孤单,因为我一直孤身一人;而是觉得我整个人都反常了。妈很高兴让我来养萨拉。她有其他的事要操心。男友照旧来来去去,只是深夜时常传来尖叫声、打斗声和摔东西声。有时走廊上还留有被打伤的男人的鲜血。也有人还手打我妈——她因此住了两次院。我已习惯用枕头捂住头,全当没听见,萨拉则蜷在被子另一头,天使般静静地守护着我。妈在别人眼里一定是得了神经病,因为到家来的男人越来越少了。
日子一年年过去,一切几乎还是老样子。对于我和妈两个人,似乎只要糊口就已足够。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直接当受害者比当旁观者还容易些。
自打去沃利读中学,我在家的时间更少了。常去伯明翰四处闲晃,看看橱窗,逛逛音像店,口袋里装着的几个子儿只够买罐可乐。晚上好一点。我可以带着萨拉——公交车上不行——去找朋友或在市中心晃悠,看路上来往的行人,就像在看有线电视:形形色色的面孔和声音,应有尽有。在校外很难交到朋友。我年龄太小,令许多人望而止步,却招来一些我不喜欢的人。但我适应力强,也善于隐藏。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脑海中总浮现的一个场景是:一大家子人不分你我,欢聚一堂。
妈习惯了我的周末不归。我有时睡在朋友家的地板或空床上。同龄的女孩子喜欢我是由于我较为沉静,外表成熟。我不怎么经常和女孩子上床。十三岁的感觉很不一样,像是和着全新的音乐起舞。我喜欢淹没在人群中,大家坐在一起,睡在一起,我感觉自己仿佛能挨个地滑进别人的头脑中去。上学纯属浪费时间。老师叫我“隐身人”,因为他从来没见我上过课。我不是叛逆,我只是不在乎。但他们派训导员几次到家来,我妈大发一通脾气后,我不得不学乖点,让他们高兴。其实他们对我才不抱任何期望。他们是在教室地板上铺好木屑,让我演马戏做样子而已。
我真正喜欢的是晚上在镇上漫步。或是去镇间的工业区、外环路或是引水渠上晃悠。和萨拉一起。她使我看到了我自己无法看到的东西。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在高楼大厦之间四处伸展。空窗户上插着碎玻璃片。发电机的废零件生锈发黑。地面上有东西不停在动,只有下雨才能把它们老实钉住。银色的,红色的。我常常是找个门槛,倒下就睡,醒来时下半身勃起,满嘴是灰。我放声就哭。我拾到过一包香烟,为取暖一口气全部抽光。这些夜晚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我恨它们,却又不希望它们结束。
有天晚上在雪山伯明翰商业区一地名。,我站在哈姆利大型儿童玩具店外面。这个店几年前就关门停业了,那栋楼现在也不在了。但当时还有个巨大橱窗,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玩具,张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街道很静。只有几个看得入迷的孩子在等夜班公交车,还有个乞丐在垃圾箱里翻找个不停。忽然我看见窗边有一排老鼠在爬。妈妈带着六个孩子。接着只听见尖利的一声怪叫,像有人在远处哭喊。老鼠立马钻到墙后不见了。过了会,鼠妈妈从街面的通风口溜出身来。孩子们紧跟其后。
尖利的叫声是从我背后传出的,是萨拉。她蹲在地铁口路旁草坪的一面矮墙上。张着大口,双肩紧张地颤抖着。目光紧随着老鼠,看它们缓缓向自己靠近,像是正一步步走入暴风雪的旋涡。她猛地一跃而下,跳上草坪,趴在紧贴墙面的排水道端口静候着。鼠妈妈费力地爬了出来,落在草坪上。萨拉一下子扑上去。一只,两只……小老鼠尾随妈妈,接踵而至。我突然想到,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萨拉捕杀。当老鼠一家全都在爪下丧命,她才开始吃。高亢而尖利的声音这才停止。
萨拉留了只小老鼠给我。当然,我没吃。我将这事讲给米基听,她说萨拉是“哈姆利的彩衣吹笛手”语出童话故事《哈默尔恩的彩衣吹笛手》,他的神秘笛声能吸引并驱除老鼠。。但那是许久之后的事情了。当时我一心想回到之前我曾逃离的那个世界。
哈姆利事件过去不久,我同一个陌生人在伯明翰过了一夜。和妈的关系实在糟糕,我不愿回家。当时身无分文,也饿了一整天了。夜幕渐渐降临,我坐在停车场的围墙上,看萨拉正扑捉一只椋鸟。当鸟儿扑翅飞向一家中国餐馆的屋顶时,我发觉这个人正盯着我看。他正准备上车——一辆白色的罗孚汽车。我困窘至极,开口问他是否能救济我一块钱。他走过来,看起来有些发慌。实际是害怕,但不是因为我。他四十岁上下的年纪,黑色短发,戴着眼镜。
“饿吗?”他问。顿了一下。“要不,吃披萨去?”我抛下萨拉,跟他走了。他没问我的年纪,我也不想说,以免吓到他。我那时才十四岁,但却比实际年龄显老多了,因为流浪街头的时间太长了。我贪婪地将披萨(火腿、腊肠和黑橄榄)全部消灭。接着他问我要不要回家喝一杯。在车上,我告诉他我晚上无处过夜。他立刻面露喜色。
和女孩子上床感觉不一样。倒不是因为他是个男人,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分享——实际上是我驾驭他,他驾驭我。对此,我有本能的反应。到最后我仿佛从镜中看到自己的样子:趴在他身上,两手紧抓他的腰侧,指甲戳入他的肉里,深埋着头,像一只正在舔食牛奶的猫。我醒来时,他在我身边睡得正香。天还没亮,但能隐约看见。地板上我的衣服窝成一团。旁边是他的牛仔裤,另一半在床底下。我掏了他所有口袋:总共二十五块,还有些零钱。我拿了张十块的,心想他也许不会发觉自己的钱被抢了。发觉的话,他会认为这是出于需求,而不是贪婪。抬起头,我能看见他正在看我。我装好钱,转身走人。我大致知道回去的路。不到一小时萨拉就找到了我。那天,无论我吃什么喝什么,那股味道总无法去除。打那以后,我就一直开价要钱了。
是我发现的她。三月,寒冷寂静的一天。天快亮时,我才到家,径直倒头睡觉去了。三点钟起床时,四周没一点动静。我开着暖炉,看着电视,琢磨着妈到哪里去了。一般周日她都在家。最近她一直吓唬说不要我了,说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了。家里一片狼藉。我想,要是用吸尘器打扫一遍,她心情可能会好一点。最后打扫到她的卧室。她躺在床上,已无知觉。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感到她浑身已是那么冰冷,我不再奢望还能将她重新唤醒。
他们告诉我,妈死于过量吸食吗啡。问我她是不是有毒瘾。我说没有,但实际上我不知道。警察联系了她在布隆斯格罗夫英格兰中西部伍斯特郡一镇名。生活的姐姐。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她,她像妈的翻版,不过更苍老、更肥胖。她和丈夫住在一间狭小平房里,没有孩子。他们照顾了我和萨拉一段时间。葬礼上我没哭。几天后,我自己去了墓地。我突然想起姐死前这里最起初的样子。她也埋在这里。找到她的坟墓后,我开始痛哭,放声哀嚎,一种惨白的麻木意识在我脑中蔓延开来,像伤疤一样。我跪倒在地上。一个劲地狠抽自己的脸,直到墓碑在眼前模糊。我恳求妈原谅自己没能救她。天地间唯一的回应只有我脑子里的尖声哭喊。这是个静寂的清晨,阳光明媚,却冰冷刺骨。
一星期后,我搬到伯明翰北部的一家私人招待所,这里住着的都是“问题”少年。房间清一色漆成蛙绿色,墙上霉湿的斑点像皮肤上生的瘤子。窗户极小。垃圾没人收拾,乱丢在楼梯上。厨房、卫生间,所有设施统统坏掉,不能使用。这家招待所是三个胖男人开的,他们整天无所事事,闲坐在办公室装有铁栏的玻璃墙后面,兴致勃勃地夸耀自己以前打架如何勇猛,搞女人如何成功。
至少我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摆了几张旧相片和我读书时画的画。我喜欢在屋子里点上便宜的蜡烛,幻想自己身处在地下室里,而外面是一片被轰炸后的世界。因为我还只有十五岁,有个社工每周都过来检查我有没有逃学。她也讨厌这儿。这里大多数孩子年龄都比我大,但都是十足的笨蛋。我是指反应迟钝。也许是无聊的生活已使他们变得麻木了。也许是他们惧怕直面世界。有些是危险分子。曾有人拿刀逼我口交。我和他们无论谁混在一起,结果不是染梅毒,就是生疥疮,或者被有意打伤。我像别人收捡空瓶子一样收捡着道歉。晚间去拖船牵道上走走还不错。那里有座大石桥,下面的凹地上一半堆着碎砖头,一半空着。警察从不会去。有些是喝得东倒西歪的醉鬼;另外的人大多还充满无穷的幻想。我就常常盯着漆黑的水面,想象自己游过隧道,游向红光四射的灿烂黎明。
这里最让我痛恨的是他们不让我养萨拉。我只好托学校同学米基照顾她。米基是我唯一信得过能谈论萨拉的人。她们很合得来。萨拉对除我之外的任何人都十分警惕,但却老实地在米基的房里安了家。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我想。我和米基一直亲近要好,但该死的命运硬生生不让我们在一起。她喜欢跟着有工作、有摩托车的大男孩一起混。可这些人不是把她甩了,就是把她的肚子搞大。米基比我大一岁,头发乌黑,颧骨高耸,脖子一侧文着蜘蛛网。我知道她和她爸妈关系很僵。十四岁时,她砸烂了家里所有的玻璃。是为了让真理进来,她说。她妈骂她“迟早会进精神病院!”她立马还嘴,“先让我离开这个精神病院吧!”她爸动手揍了她。从那以后,她再也没砸过家里东西了。
十六岁时,我开始盘算着找份工作,搬出去住。就等毕业了。一天,米基带着萨拉,拉着一只大箱子出现在我门前。告诉我她被家里撵出来了。我从一个欠我人情的邻居那要来几罐陈年啤酒。喝着酒,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也睡在了一起,第一次。早上醒来时,萨拉蜷着身子,躺在我俩中间。仿佛标志着,这是一个家。
但我俩都没工作。只好和米基的几个朋友在巴萨尔希斯伯明翰中心贫民区一地名。一间房子的顶楼上凑合住了几个星期。我在牛环市场 伯明翰商业区一地名。找到份活,每天晚上打扫卖摊。我们陷入了常见的两难困境:没有房子就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也找不到房子。不过至少不用上学了。一旦满十六岁,他们就不管了。社会救济没你的份。你不再是无辜小孩,而是问题青年了。春天已经快过完了,我们不太担心会挨冻。萨拉也早已习惯自己找吃的了。
对于我们,要找个属于自己的家,只有一个办法。在巴萨尔希斯红灯区靠近城边的后街上,有些用木板封起来的旧平房闲着。也许是主人卖不出去,也懒得费劲装修再出租。后面的混凝土院子松松散散堆着半满的砖块,我们就从那钻进其中的一间。房里地板已腐烂,油漆从霉迹斑斑的墙纸上一块块剥落下来。我们把蜡烛、床垫、被褥、行李箱等搬进来。水还通。电不通。但米基带了电池,收音机还能用。从前面看,你一定以为房子是空的。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一段时光。好是因为这里如此地与众不同。终于来到我早已梦想的猫的世界。无需说话、无需花钱、无需阳光。洗澡我们就去当地的游泳馆。好多流浪汉都来这里。米基找来些便宜的油画,贴在房间四壁。画上的树木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几座楼房掩映其中,破败而空荡。地上落叶成堆。晚上是最好的时光。我们裹在毯中,在黑暗中温存。或者手牵着手去城里散步,萨拉默默跟在后面。市中心边上有一处组合统建房,是围着一个空停车场和儿童游乐场建的一圈塔楼。再远一点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旧房子几乎全部被推倒,新建筑正准备动工。起先工地上只有很多木头桩子和泥沟,后来他们运来了金属槽,装上了新砖块和沙子。这楼群只住了一半,另一半空着。窗户是烂的烂,封的封。我们结识了几个在那蹭住的人,晚上他们都在附近。我和米基常在半夜跑到那个小的混凝土游乐场去玩。像一部黑白电影。我们荡秋千,压跷跷板,倒挂在攀缘架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最坏的时光是早晨。晚上看似神秘的一切都变得肮脏不堪。灰尘折射着阳光,闪闪发亮,给所有东西蒙上外衣。萨拉要么睡着了,要么出去了,我无法借助她的眼睛。如果是我一个人,也还能凑合着过;但我和米基经常对彼此互发脾气,都忘记如何好好说话了。这是我们唯一需要借酒才能度过的时光,每天早晨。阳光威胁着我们。不只是阳光。每次和外界的接触,都使我们的处境更加糟糕。社会保障部告知我们,我们的福利救济金只应由家人承担。也就是说,你不用在莫斯利伯明翰一郊区名。的办公室里填上固定住址。我和米基只得靠皮肉生意来过活。我还比较适应,但米基太辛苦了。巴萨尔希斯这里未成年妓女遍地都是,好几百人。她们三三两两站在那里,穿着T恤衫,紧身裤或超短裙。我教米基尽量躲开那些喝醉的嫖客。但她还是被强暴了好几次,有次还是警察干的。有个家伙把她痛打一顿,却连一个多余的子儿也没出。每当米基伤心难过时,我都极力安慰她,可却始终无力说出“我带你离开这里”这句话。好像暴力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你不可能摆脱。小时候我就这么想了。已经麻木了。如果很小的年纪就明白这一切,你不需要吗啡。
有天早上,米基告诉我,她遇到一个人,想让她搬过去住。“我去了。”她说。我笑了,但米基只是看着我,我突然意识到她是说真的。我们在垫子上坐下来,她双手搂住我。“我在这儿呆不下去了,”她说,“生活没意思,就像在等死。冬天我们会冻死的。肖恩,你一个人过会好一点。你可以在招待所里找间房,没问题的。这个人——他很好,有钱,要我。我没办法,肖恩。实在没办法。”她想吻我,我推开了。她开始收拾箱子,而我则在想她说的“你一个人过”。米基知道我在想什么,她一直知道的。“我把萨拉带着。”她说,“我可以照顾——”
“带萨拉?混蛋。萨拉是我的。她不是东西,可以随便带走。”那时,我只觉得浑身瘫软,孤独无助。萨拉蜷在房间角落,睡着了。像个孩子,又像个已目睹过世间所有背叛的女长者。我穿上外衣。“再见。”走到外面,我几乎无法相信有阳光在照耀。整个城市黑暗一片,空旷一片,死寂一片。我连续走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在亚德利伍德伯明翰一地名。的公园长椅上睡着了。回到家,米基和萨拉都已不见。我用头天晚上接客的钱买了四罐特酿啤酒,一饮而尽。黑暗中房间里似乎空无一物。连我自己都不在其中。
第二天,萨拉回来了。她在房后的院里等我,眼神古怪而不安,和那天在玩具店外流露的一模一样。我把她搂起来,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以前她从没这样过。我抚去她黑色毛发上沾的落叶碎片。又过了几天,我看到米基正在巴萨尔希斯的大街上等人。她自己。当时已接近午夜。我走近时,看见她左边脸颊上有道刚刚愈合的抓伤。她拥抱了我。“很高兴见到你,”她说,“我在这里呆不长了,他要送我去伦敦。”
“送你走?”我打量着她的脸。新的化妆品。新的香水。抓伤。
“是的,我为他干活。世上只有两种人,肖恩。混蛋,还有更混的混蛋。”
我握紧她的手。和她吻别——轻轻地,是那种亲吻你喜欢的人的感觉。我伸手摸摸她脸颊。“是萨拉干的吗?”
“什么?”她笑了。“天哪,不是。是他。詹姆斯。”她忽然紧张起来。“他来了。好好看着我。”
他是个略微发福、留着短发的中年男子,颇像电视剧《舍伍德的罗宾汉》中的塔克教士。我迎上去,对他说:“看来这星期你又抱上新大腿了。”他没听懂。这是我和米基的最后一面。几天后,房主找人把我的家当扔了出来,还将窗户和后门用砖全部砌住。
我在街头过了几夜。即使是夏天,还是很冷。四周的混凝土建筑像巨大的冰库,积聚着逼人的寒气。我不禁想起妈,想起她死去的情形。我真的想找个安全的地方容身,不是蹭在别人地盘上。我只好去城里的救世军招待所,他们给了我一间房。规矩简单:不喝酒、不吸毒、不养宠物。所有人都违背前两条,却都不受追究,安然无事。
我想萨拉自己可以再坚持几天,容我找个人来照顾她。但我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往事像落叶一样,被风吹进我的脑海。我姐。我妈。所有那些男人。米基。我拿日常用品和住在招待所的同伴换了些安定。眼前昏沉沉的一片。当我再次回到和米基一开始住的那座房子时,看到两张新面孔,但米基的朋友珍妮丝仍在那里。我说服她帮我暂时照看一下萨拉,并留给她一些买猫粮的钱。一切安排好。但萨拉却连影子也没见着。
我整日整夜四处找她。有天天刚亮,路上来往车辆刚开始喧闹,我终于找到了她。她想让我找到她。是在内奇尔斯伯明翰中心贫民区一地名。,那个有儿童游乐场的统建住宅区。我一到那里,看到清冷的日光正从塔楼的顶层窗户上照射过来,仿佛闪烁着遇难信号时,我就知道了。萨拉被钉在停车场一侧低矮的木围栏上。脖子和爪子被钉子穿透。围栏上还留着被风干了的血迹,黑乎乎的。乱糟糟的毛发早已僵硬,上面爬满苍蝇。眼睛不见了。但我能在脑海中看到。走上前去,只觉得臭气熏天,无法忍受。我憋不住吐了出来,不得不先走开。停车场空无一人。正常人不会把车停在这里。
过了一会儿,我才平静下来,回到原处,把钉子一个个拔出来。她的腿还在,仿佛在飞一样向两边伸展开来。浑身冰凉。有个布绒玩具躺在柜子后。苍蝇爬上了我的双手,我想哭喊,却张不开嘴。我把她带到住宅区外面的建筑工地上,放在一条沟里,埋上泥土。然后回到游乐场,坐在长凳上,等着。那天早上天气阴沉。太阳时不时露个脸出来,照得一切通亮无比,街道仿佛都成了幻觉。
傍晚的某个时刻,一群孩子从最近的一栋塔楼出来,在停车场上玩足球。我数了数,共八个。最小的差不多五岁,最大的九岁、十岁。天色渐暗,有一个回了家。又新来了两个。基本上都是大孩子在踢。这群孩子都脏兮兮的。全是白人。有些身上贴着膏药,有些脸上带着瘀伤。我猜,他们当中不知有多少人挨过打,有多少人被同住的大人操过,这一张张无血色、无表情的脸上又淌过多少没用的眼泪。我站了起来,走向游乐场和停车场之间的那堵墙,爬了上去。孩子们停下来,转过头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然后我开始用以前只听过一次的那种尖利而高亢的嗓音哼唱起来。像远处有人在哭喊。那里哭声不绝于耳。
他们向我走来。步伐很慢,仿佛在水下行走。我沿着墙走了一段,跳下来,往后退,口中仍哼唱不停。他们紧跟着我,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塔楼。表情全无。眼神空洞,像在看电视。我把他们领到建筑工地上,带头跳进最近的那道沟。沟的另一边是一堆堆的沙土,还有码得松松散散的砖头。我站在那里,嘴里念念有声。孩子们直视我的眼睛。最小的那个先跳进来。我已挪开了木头围桩。他们毫无声响。九个孩子。九条生命。
当孩子们一个个全跳进去,我开始往他们身上扔砖头。他们没有挣扎,好多被砸中后还纹丝不动。我想哭,但没哭,和他们一样没哭。我只是继续哼唱。后来我开始填土填沙,把他们全身都盖住。感觉自己的一部分也和他们埋在了一起。我埋头不停地填啊填,直到将沟填平。走回招待所,睡了一整天。
一切事情都有规律。一旦开始,就要做完。互相扯平。两不相欠。抓伤对手,以牙还牙。
之后,我离开了米德兰。一路搭便车来到伦敦。这里满大街都是孤儿,但我能勉强过活。你知道北美印第安人是如何把动物当作精神图腾的吗?有的是一家人崇拜同一个图腾,有的是整个宗族。我身体里有多少条生命?我会被人在脖子后捅一刀,四仰八叉地死在床上或车顶上吗?我可以照顾自己的吃穿。我喜欢人,但我不需要他们。我不会再信任任何人。我的利爪已准备好。深藏在心。
(杨露萍: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务处,邮编:2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