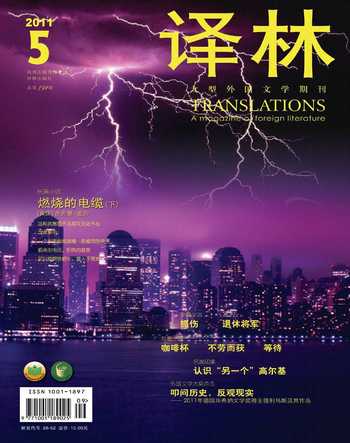咖啡杯
〔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 著 毕井凌 译
马里奥•贝内德蒂,乌拉圭著名作家、诗人,1920年出生于巴索德洛斯多罗斯市。1938年至1941年期间居住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年回到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进入《前进》周报编辑部工作。1949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今晨》,一年后发表诗集《仅仅与此同时》。1953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之中的谁》收录于1959年出版的小说集《蒙得维的亚人》,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形成了他独特的“都市概念”叙事手法。1960年停战期间,贝内德蒂的作品开始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小说有一百多种不同的版本,被翻译成十九种文字。
2009年5月17日,贝内德蒂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这套咖啡杯共有六只:两红、两黑和两绿。它们价格不菲,质量上乘,而且款式时髦,是恩里克塔送给玛丽安娜的生日礼物。恩里克塔建议每种颜色的咖啡杯应当与另一色的碟子搭配。比如,黑色配红色简直妙极了,这就是她的美学观点。但是玛丽安娜有自己的想法,她认为咖啡杯必须和同一种颜色的碟子才能搭配成套。
“咖啡快煮好了,你要吗?”玛丽安娜一边询问丈夫何塞•克劳迪奥,一边盯着小叔子阿尔贝托,但他只是冲她眨了眨眼睛,没出声。这时何塞回答道:“现在不要,待会儿吧。我想先抽根烟。”玛丽安娜的目光转向丈夫,并冒出一个已经想过一千次的念头:何塞的眼睛一点也不像是瞎了。
何塞的手开始在沙发上不停地摸索。“你找什么?”玛丽安娜问道。“打火机。”“在你右边。”他的手改变了方向,终于摸到了打火机,哆嗦着打着开关,试了许多次都没有成功,左手夹着的那支烟只能徒劳地等待着火苗的出现。见此情景,阿尔贝托划了一根火柴帮他把烟点着了。“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没用的打火机给扔了?”阿尔贝托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微笑着问道,那是一种常见的对盲人的微笑。“这个打火机对我很重要,是玛丽安娜送给我的礼物。”何塞淡淡地回答。
她微微张开嘴,舌尖舔了一下嘴唇,这是开始回忆的标志。那是1953年3月的一天,当时何塞才三十五岁,眼睛还能看得见东西。他俩在何塞父母位于格尔达角的家中共进午餐,吃的是贻贝海鲜饭,饭后两人一起去海边散步。他的一只胳膊自然地搭在她的肩头,让她有一种安全感,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感觉。回到公寓后,何塞就像以前那样吻了她,轻轻地,缓缓地。他们还一起用那只打火机点燃了一支抽了一半的香烟。
现在这只打火机点不着火了。她本来是不相信这类预兆的,但是现在不得不信了。一切都过去了,回忆再美好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月你又没去看医生。”阿尔贝托对他哥哥说道。
“是的。”
“你就不能和善一点吗?”
“当然可以。”
“我觉得你的做法很愚蠢。”
“可我为什么要去看医生?难道就为了听他告诉我身体很健康,肝脏情况良好,心率正常,肠子也没问题吗?难道你要我去听这些蠢话?难道我应该庆幸虽然瞎了眼但是有一副好身板吗?”
在失明之前,何塞从来不会这样发泄他的感情,玛丽安娜永远无法忘记这张充满紧张、气忿的脸上以前的那些可爱的表情。他们的婚姻有过美好的时光,她不能也不愿否认这一点。但当不幸降临的时候,他拒绝她的照顾,甚至还故意躲着她。他所有的自尊都浓缩成一种可怕而固执的沉默,一种即使被话语包围仍旧保持冷漠的沉默。何塞已经拒绝说“同意”了。
“不管怎么说,你都应该去看医生,”玛丽安娜是站在阿尔贝托这一边的,“你可别忘了梅内德斯先生反复跟你强调的话。”
“我怎么不记得:‘对您来说失明并不意味着失去了一切。还有一句更经典的:‘科学不相信奇迹。我也不相信奇迹。”
“可你为什么不抱希望呢?每个人都应该有希望啊。”
“真的吗?”他冷冷地反问道。这时香烟恰好熄灭了。
他总是这样把自己包裹起来。玛丽安娜并不准备陪伴——仅仅陪伴——这样一个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的人。她渴望的是被人重视和需要。何塞的失明是一种不幸,但不是最大的不幸。最大的不幸在于他一直回避所有的帮助,特别是玛丽安娜的帮助。他忽视她的保护,而玛丽安娜本来是很愿意保护他的,而且是温柔地、充满爱意和慈悲地去保护他。
好吧,这些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不一样了,事情在慢慢起着变化。首先是温柔在逐渐消退。一开始被爱情光环笼罩着的那种照料现在慢慢变成机械式的了。她做事还是那么有效率,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并不像从前那么充满热情了。然后是可能随时面临吵架的危险。何塞现在变得十分好斗,爱惹是生非,随时准备伤害别人,经常说一些难听的话。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算在最不恰当的场合,他也经常能准确无误地说出直插人心底的伤害性的话语,发表一些包含怒火的评论。他总是把自己的失明作为一堵挑衅的高墙来引起他人的不安。
阿尔贝托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
“真是一个糟糕的秋天,”他说,“你注意到了吗?”显然,他问的是玛丽安娜。
“没有。”何塞回答道,“你帮我注意到了就行。”
阿尔贝托看着她。沉默中,两人相视一笑。这开心当然没何塞的份,虽然是由他的回答引起的。这个时候,玛丽安娜意识到自己很美。每次只要看着阿尔贝托的时候,她都会变得很美。他第一次告诉她这个秘密是在去年4月23日的晚上,整整一年零八天之前。那天晚上何塞用最恶毒的语言羞辱她,她哭了,哭得很伤心,整整哭了几个小时,直到靠在阿尔贝托温暖的肩头,她才感觉到安全和理解。阿尔贝托是那么的善解人意!她向他倾诉,或者只是简单地看着他,她知道他正在把她从困境中拯救出来。“谢谢。”那时她对他说,即使现在,这句话也到了嘴边,这是她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她对阿尔贝托的爱是出于报答,这并不有损于这份她认为十分纯洁的爱情。对她来说,爱情一方面是感谢,另一方面是报答。她感谢何塞,那个阳光、青春、聪明的何塞,感谢他在过去的美好时光中对她这个丑小鸭的追求。但是那根本谈不上报答,就算他失明后那么需要她的时候也谈不上。
然而,一开始她就感谢阿尔贝托,感谢他慷慨无私地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特别是帮助她变得坚强。从这一层面上说,她在报答阿尔贝托,这毋庸置疑。阿尔贝托是一个很文静,尊重兄长,崇尚公平的人,而且一直保持单身。很多年以来,他和玛丽安娜之间保持着恰如其分的亲密,他们相处时很谨慎,甚至都不用“你”而用敬语来称呼对方。只是在有限的几次机会中才能隐约感觉到两人之间那种深深的密切关系。或许阿尔贝托有一点妒忌哥哥的幸福,因为哥哥幸运地拥有一个他认为完美的女人。事实上没过多久,玛丽安娜就亲耳听到阿尔贝托的坦白:他一直过着平静的单身生活是因为在他眼中,所有的姑娘都无法与她比拟。
“昨天特雷耶斯来看我,”何塞说道,“还说了一大堆拍马屁的话,说厂里的职工都很关心我。我敢肯定,他们一定是抽签决定哪个倒霉蛋来看我,拿我当笑话。”
“也很可能是他们真的很尊敬你呀。”阿尔贝托说道,“也许他们真的很担心你的健康。不要总站在你自己的角度把人都想得那么卑鄙。”
“好吧。每天我都能学到不同的做人的道理。”何塞没好气地笑了笑,明显带着一丝讽刺的意味。
当玛丽安娜向阿尔贝托寻求保护甚至爱情的时候,她很快就确信其实自己正在保护着他,确信他像她一样都需要保护,确信他还有一丝顾虑和羞怯。她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保护他。她对他的爱情是一种报答。无须过多的言语,仅仅只需要他用温柔包裹着她,一起度过以后的美好时光。她对他的“报答之情”已经无法控制。四目相对时她忘记了辛劳和痛楚。几天以后他们就互相表白了,然后一直偷偷摸摸地见面。玛丽安娜的心舒展开来,仿佛全世界就只剩下两个人:阿尔贝托和她。
“现在给我热杯咖啡,”这时何塞说道。玛丽安娜走到桌子跟前,点燃了酒精灯。她漫不经心地盯着那套咖啡杯。她只拿出了其中的三只,每种颜色一只。她喜欢看着那些漂亮的杯子排列成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随后她往沙发上一躺,脖子碰到了她所渴望的阿尔贝托温暖的手,已经做好准备等待着她的手。上帝啊,真是甜蜜!那只手开始轻轻地移动,修长的手指在她的秀发中摩娑。这是阿尔贝托第一次鼓起勇气这么做。玛丽安娜感到很紧张,紧张得让她无法好好享受这份爱抚。好了,现在好了,现在她平静下来了。现在对她而言,何塞的失明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
这时何塞正惬意地喘着气坐在这对情人的面前。慢慢地,阿尔贝托的爱抚变成一种仪式,玛丽安娜可以预见他下一步的行动。就像每个下午做的一样,那只手充满爱意地抚摸她的脖子、右耳,缓缓滑过脸颊、下巴,最后停留在她微微张开的双唇上。她呢,也像每天下午做的那样,闭上眼睛静静地亲吻那只手掌……当她睁开双眼的时候,何塞的表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还是一副事不关己、沉默寡言的样子。尽管如此,她还是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害怕,虽然在进行这场带点羞怯、风险甚至轻佻的爱抚练习时两人的“技术”都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安静的境界。
“别煮糊了。”何塞提醒道。
阿尔贝托的手立刻停了下来,玛丽安娜重新走到桌子跟前,撤下酒精灯,熄灭火焰,向杯中倒满了咖啡。
每天咖啡杯的颜色都会变换。今天绿色的是为何塞准备的,黑色的是阿尔贝托的,红色的是留给自己的。当她拿起绿色的咖啡杯准备递给何塞的时候,她发现何塞紧绷的脸上出现了奇怪的表情,并听到了大致这样的一句话:“不,亲爱的。今天我要红色的咖啡杯。”
(本文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毕井凌: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