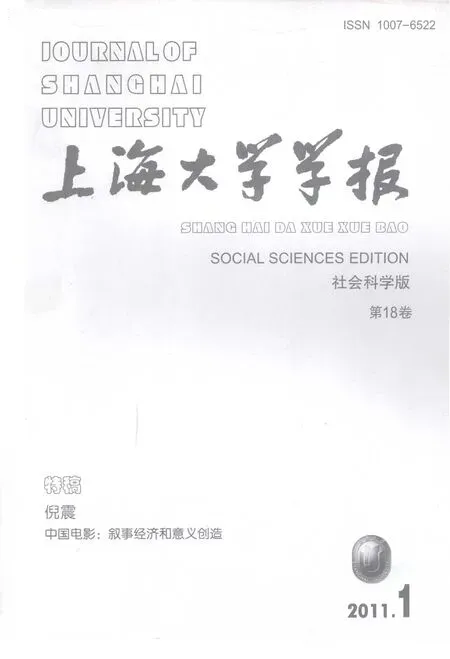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
朱立元,栗永清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
——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
朱立元,栗永清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将“实践存在论”理解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拼凑的观点源自对“存在论”(ontology)理解的片面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的割裂。在马克思那里,“物质”、“自然界”仅是“本原”意义上的“第一性”,而非“本体”。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于“存在”(on、being、Sein)问题的追问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对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古典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革命性超越在于他同“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而非所谓的“物质本体论”。
实践存在论;实践;存在论;马克思主义
从去年,董学文等先生先后发表十多篇文章批评笔者提出的“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设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颠覆”、“消解”至今,仅据笔者所知,同“实践存在论”相关的学术会议就开了三次之多。在美学已相当程度地远离了“热点”的当代学术语境中,实践存在论美学能引起如此的关注,应当说,这是值得学界,特别是笔者为之欣喜的。然而,让笔者深感遗憾的是,在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以及对笔者回应的再批评文章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些不断的重复和莫名的指责,而董文中概念使用的前后矛盾乃至随意则更令笔者感到失望。在前面数篇文章中,我们已就董先生的一些批评做了具有针对性的回应,本文尝试在此前论述的基础上,对董先生的质疑以及我们的观点做一初步总结。
一、矛盾的“本体论”和武断的批评
对于论辩对象的理解,是有效的学术论争之展开的基本前提,然而,董先生却根据自己的想像,凭空架构起一个完全不符合我们本意,而又充满矛盾的“实践存在论”,并以这个自己虚构出来的靶子作为批评的对象:
“实践存在论美学”是先把“实践本体论”变成“实践存在论”,然后再将“实践存在论”中的“存在”换成存在主义的“存在”,这样就完成了从唯物论到唯心论、从唯物史观到非唯物史观的蜕化与演变。这一美学理论,诚如提倡者自己所说的,“虽然仍然以实践作为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却已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转移到了存在论的新的哲学根基上了”。[1]
在董先生看来,“实践存在论”等于“实践”加“存在”再加“论”,而且各个部分可以如积木般进行替换,于是,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到存在主义,从“本体论”到“存在论”,再到“存在”,这些哲学基础概念就在这种拼贴中构成了一个“颠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这个“实践存在论”同笔者的主张其实风马牛不相及,而董先生不惟将其“发明权”强加于笔者,更以此为据,对笔者进行了严厉的有政治化意味的批评,这是笔者对此次论争最感失望的地方。
“实践存在论”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拼凑”,这是董文的基本立论,想来无需引证,董先生也不会否认。然而,董文所以认为这是笔者的主张,迄今所作的唯一正面论证即是上文所引文字中,援引了笔者的那句话,而后得出“既然‘哲学根基’已经‘转移’,从‘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变成‘新的’存在主义的存在论,那么这种美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也就需要怀疑了”。董先生还说,“无庸讳言,这个理论结果未必是‘实践存在论’坚持者所希望看到的”,[2]46自然,他又确认“但它又确乎是明摆着的事实。”①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文字以及证明在董文中数次出现,不一一列举了。[2]47此外,几乎都是斩钉截铁的断言。
笔者以为这句话并不费解,所谓“转移”是指从“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移,而董先生却将之释读为从“辩证唯物主义”向“存在主义”的转移。所以如此,在笔者看来,是董先生将“存在论”视作“存在主义”,准确地说是视作海德格尔的“专利”,且绝不容马克思染指。因为只有这样,如此推论方可成立。
然而,董先生却不仅以“物质本体论”概括马克思主义的ontology,且又分明说“客观地说,无论是英语的ontology,还是德语的Ontologie,译介为‘存在论’都未尝不可”。[3]45又以“实践”不是“本体”来批评所谓“实践存在论”的“另一个说法”“实践本体论”。这样看,董先生不惟承认马克思有ontology的理论维度,且对学界之于ontology的翻译和理解的学术史也颇有了解。但如此一来,则又势必与“存在论”是海德格尔“专利”的“前理解”发生矛盾,董先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的解决之途却非躬身自问,而是将这个矛盾归之于笔者,更生发了用“存在主义”的“存在”替换“存在论”中的“存在”的妙论。
也正在这里,我们意识到,董先生之于“存在论”、“本体论”、ontology的理解实大有值得商榷之处,虽然他主张对ontology的理解“不能不充分顾及‘本体论’的西方语言习惯,不能不考虑西方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实际特点”,但从董文对ontology、“本体论”的一系列正面立论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姑且勿论董先生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是否足够深刻和透彻,仅就“西方语言习惯”,董文似都还谈不上准确的程度。
Ontology是关于on的学问,这一点中外学界几无异议,主要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on。不过,on是古希腊语EIMI的现在分词中性单数主格和宾格形式的ον的拉丁拼法,这一点上,许是笔者孤陋,似也未见多少歧见。董先生却别有新解:“从词源学上来考察,它们(指 ontology的英、德文形式——引者)都是关于on的学说或学问。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拉丁语,后来进入古希腊语,即ον,也就是英语中的 being,即‘存在’或‘存在物’。”笔者非常希望能够拜读到董先生对于ov的拉丁词源的“词源学”考证这一新见的根据。可惜一如对实践存在论的批评一般,我们读到的只有这一权威式的断言,却毫无细密乃至起码的论证。董文还指出“同时,这个词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用法,就是作为系词‘是’来使用,因此有学者主张将其译为‘是’,将ontology或Ontologie译为‘是论’”,更指明“在西方语言中,on作为系词的用法占据了一个很重的位置,或者也可以说,占据了大部分的用法”。[3]45放开这里的“西方语言”其实应当是“古希腊语”及“拉丁文”的疏漏不说,这些关于on的阐述同董先生对“本体论”的界说之间却毫无联系:
所谓“本体论”,指的是探究天地万物本原的学说,或者说是探究世间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根本动因和依据的学说。换一种通俗讲法,“本体论”是关于“是”(Being)的学说,而这里的“是”,指的是事物的始基,是事物最普遍、最原始、最基本的实在。所以,它是对事物存在方式及其宇宙实体问题的探讨。再说得浅白些,“本体论”探讨的是世界的终极本原到底是什么,是物质还是精神,只有从这个角度解释问题,才具有本体论的真谛。我们不管如何转换思维方式和提问方向,但“本体”的规定是不能随意改动和编造的。[4]56
从这一界说看,可以说,董先生固然知道on的系词用法,甚至承认它“占据了大部分的用法”的事实,但他对作为系词的on在ontology的理论谱系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实毫无领会。上述界定实质上完全脱离了他所说的“充分顾及”“西方语言习惯”的“本体论”理解之途。这样说可能会让董先生难于接受,其实这也是笔者最感沮丧,也是让我们对论争的有效性产生怀疑,并终归失望的重要原因所在。而更让笔者难以接受的是董先生的武断乃至独断的论辩方式。以下略举两例。
其一,董先生从笔者所说“当代中国美学要实现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要首先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单纯认识论思维方式和框架”,居然可以看出:
这里,隐含着两个问题,一是它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在超越二元论思维模式上起码是不够力度的,或者本身就存在二元分立问题,故难以实现“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二是它认为只要实现了“实践”概念的存在论化,超越和冲破二元论思维和二元对立就可以完成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实践存在论美学”竭力将“实践”说成是“存在”,并借助于“存在论”来完成对主客二元对立的克服。[5]10
先不说“实践存在论”压根不是什么“实践”的“存在论化”(后文将予以说明)。董先生大概认为“物质本体论”就是将“物质”“说成是”“本体”(当然,在董先生看来,“物质是本体”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不是“说成是”就“是”的,但应该用什么词,笔者斟酌良久,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姑且沿用董文),所以觉得“实践存在论”就是将“实践”说成是“存在”。我们想请教一下,董先生有没有想过“将实践说成是存在”该怎么理解,按照董先生对“存在”的理解:“存在”就是being,就是“存在物”,也就是要将“实践”这种人类活动“说成是”一种“存在物”,这未免太低估学界的智商了吧。而如果把“存在”理解为表状态的动词,“实践存在(着)”,这还用“竭力”么?难道董先生认为实践“不存在”,实践存在论非要说它“存在”,所以错了?当然,董先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实践存在论是要把“实践”说成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那海德格尔的“存在”又是什么呢?董先生如是说:“‘存在’在海德格尔那里,处于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之域,当你想要抓住它的时候,它巧妙地逃脱了,而就在它逃脱的一瞬间,却又显示了其‘存在’。”[2]44先不说这么理解海德格尔对不对,请董先生找一找,我们在什么时候,又怎样把“实践”说成是如此“神秘”的“存在”的。
除了这种武断,还有莫名其妙的推论,我们实在想不出“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同“马克思的实践观”在这一超越上的“起码是不够力度的”之间何以建立起了如此清晰简明的逻辑联系。董先生追问:“为什么‘实践存在论美学’特别不赞成‘认识论思维模式’和‘主客二分’呢?”似乎对实践存在论之于“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特别不赞成”颇有保留,且又认为这种“不赞成”的原因在于“这还是受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4]59但他却又分明指出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实现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互动与互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和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纯粹理性思维”。[6]4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董先生可以不赞成“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和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纯粹理性思维”而赞同马克思对其“超越”,实践存在论就不能呢?又为什么实践存在论不能受到马克思超越“二元论”的影响,而非要假道海德格尔和“西方现代哲学”呢?
再举一例: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学观主张从人的存在出发探寻存在的意义,这就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从人的存在出发的。[6]2
这里,董先生的逻辑十分清楚:“实践存在论”主张什么,就“隐含着”马克思主义不主张什么,换言之,先将“实践存在论”放置在非马克思,乃至反马克思的立场上,而后对其展开批判,于是乎“顺理成章”地得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颠覆”和“消解”的所谓“结论”。显然,这是典型的先入为主、循环论证的“有罪推定”。套用董先生的话,“无庸讳言,这个理论结果未必是‘实践存在论’的批评者所希望看到的,但它又确乎是明摆着的事实”。[2]44
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董先生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发现马克思的实践观超越了主客二分的对立,且认为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我们却不仅被排除在“周知”的“众”之外,只能“受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才可以“特别不赞成主客二分”,更要命的是,董先生批评主客二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而实践存在论“不赞成主客二分”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董先生的逻辑依据又在哪里呢?
对于马克思的理解不等于马克思,董先生当也赞成这样的区分,实践存在论突破“认识论”而且是近代以来“单纯认识论”的思维模式,它所针对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对马克思的实践观只局限于单纯认识论的范围,而忽视其“存在论”(马克思主义的ontology,而非董先生所理解的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维度的片面理解,这不仅不是对马克思实践观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超越的怀疑和否认,恰恰相反,它首先是对马克思的这一超越的坚持,而且在我们看来,也是对深入和全面理解这一超越的彻底性的必由之路。
二、怎样“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同认定“实践存在论”的“存在论”来自海德格尔、来自存在主义一样,董先生还认定“实践存在论”是“唯心主义”的,而正面论证同样只是对笔者的一句话“没有人,自然界充其量只是一种存在而已”的分析。①关于这句话,笔者在前面曾做过一些说明,后文将在阐述笔者的“存在论”究竟何所指,“实践存在论”的理论诉求和理论基础究竟何在的时候进行专门讨论,这里姑且暂存。此外,便是基于“实践存在论”的“存在论来自存在主义”的基本判断,展开对海德格尔“此在存在论”的高调批判。
董先生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对马克思的“实践”和海德格尔的“此在”以及“存在”概念的“不相容”进行了论证,姑且不说这些说法是否构成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两位大师级思想家的误读,就算这些结论成立,其实也丝毫不影响笔者主张的“实践存在论”的理论合法性。原因很简单,我们所主张的“实践存在论”不是董先生创造出来的可以随意替换的“实践”加“存在”再加“论”,而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概念。“实践存在论”不是主张“实践”是所谓“事物最普遍、最原始、最基本的实在”的“本体”,它的理论基础不是海德格尔的“此在”,甚至不是海氏的“存在论”,而是马克思的“存在论”。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对于“实践”范畴的发展,乃是马克思“存在论”理论维度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实现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革命的重要途径,所以称之为“实践存在论”。这也是笔者所以说董文持论与笔者的主张风马牛不相及的原因所在。
由于董先生对于“存在论”理解的有限,在他的行文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判断。董文说“既然马克思已经用‘实践’范畴来揭示‘此在’的在世,而且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始终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实践论’的高度,那么,何需多此一举地在马克思的‘实践论’上再加个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呢?不是只要进一步阐明马克思的‘实践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3]50对于这一发现,董先生显然颇为得意,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更为这一立论找到了重要的理论根据:“根据‘奥卡姆剃刀’定律,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原则,倘若‘存在论’维度果真是‘实践’概念所固有的,那么‘实践存在论’也就仍然是‘实践论’。所以,在‘实践存在论’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海德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存在论化’之后,势必也就同时完成了对自身的消解。”[5]10
我们只想反问一句,按照董先生的说法,马克思的“物质观”岂非已经阐明了“本体论”,在“物质观”上再加上一个“本体论”,是否也是“多此一举”呢?用奥卡姆剃刀,是否也可以把“物质本体论”剃为“物质论”,将“主观唯心主义”剃为“主观论”(既然主观,怎么可能“唯物”),再将“机械唯物主义”剃为“机械论”、“直观的唯物主义”剃为“直观论”……这把剃刀在董先生那里未免太过锋利了一些吧。“实践存在论”尝试表明的是,“实践”在马克思那里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更是一个基本的“存在论”(ontology)范畴;海德格尔以“此在”为基础的“此在存在论”没有达到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存在论的高度。试问,“实践存在论”究竟增加了怎样的“实体”需要剃去呢(姑且不说笔者根本不同意把存在、是简单地理解为“实体”)?如此立论除了证明董先生将“存在论”视作海德格尔的“专利”和对存在论理解的有限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而董先生推论更让人困惑:“显然它表明,‘实践本体论’经过多年的探讨和争论,已经被认定为是一种站不住脚的‘非本体论’思想,那么,如果再加上海德格尔的‘存在’,或许可以弥补‘实践本体论’的缺陷,形成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这大概就是‘实践存在论’的初衷吧。”[3]50而就在不久之后的另一篇文章中,董先生又说“直到今天,围绕‘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的争论仍在继续”,[5]11甚至还说“把‘实践’作为本体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来规定和界说,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既然“已被认定”,怎么又“仍在继续”?究竟是谁认定它“站不住脚”呢?这个被“认定站不住脚”的观点,又居然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如此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董先生是不是该先反省一下自己的“认定”到底对不对呢?
让人彻底无语的是董先生对“实践”的界定,我们在董文中找到了他对实践的两个界定:
实践是什么呢?实践是人的活动的总称,是外在客观自然界向人的生成的途径和方式,是人改造自然世界和建立社会关系的基础。实践是一种变革的力量,它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变迁。[2]40
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2]42
两个定义出于同一篇文章,想来董先生不会释以“思想的发展”。董先生善用举例,我们也举例来看。读书看报、听歌赏画这样的活动是“实践”么,如果以第一个定义看,当无疑问,毕竟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人的活动”;而以第二个定义看,则未必然,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一些活动是不是董先生所理解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这些活动不是董先生所说的“人的活动”。也许董先生认为,这些活动都是人受到外在的刺激,在其感官以及大脑皮层中发生了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变化的“物质劳动”,而如果这样,睡觉打盹、吃饭做梦乃至董先生所说和尚念经、单相思何尝不复也是“物质劳动”?吃饭睡觉难道不是“人改造自然界”的基础?释之为“推动社会和历史变迁的”“变革的力量”可能都不为过吧,和尚念经、单相思何尝不可理解为客观的“经文”、“相思的对象”“向人生成”的途径,何尝不可理解为“建立社会关系”?难道僧人念经这样最基本的、重要的宗教修行活动与“实践”与“社会”绝缘么?
更让人惊讶的是,董先生一方面屡以实践存在论将艺术、审美等活动纳入“实践”范畴批评我们将实践“泛化”,更由此生发“颠覆”马克思主义的耸人之论,另一方面却不惟高扬“实践是人的活动的总称”的大旗,更指出:“‘艺术生产’论与‘艺术精神掌握世界方式’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具有内在的同构性,可以通称之为‘艺术实践论’,这是一种与一般的物质实践既有相同性又有差异性的实践活动。”[6]5抛开这里的“这”的指代不明(究竟是指“‘艺术生产’论”和“‘艺术精神掌握世界方式’论”这两种理论观点,还是指“艺术生产”和“艺术精神掌握世界”两种活动)不说,董先生主张艺术虽则“特殊”,却仍是“实践”,当无疑问。读至此处,我们除却无奈,还能奈何?
董先生否认实践存在论的另一理由是认为“曾一度信奉”“实践本体论或劳动本体论”的只是早期的“非马克思主义”时期的马克思,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是“反对”这种本体论的,转而“坚持的事实上是一种具有客观物质前提和制约性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能动的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对人自身生产——的本体论”。[4]55-56
对此,我们想问的有四点,其一,董先生不是说“实践存在论”是“实践本体论”的另一种说法么?不是说这是马克思同海德格尔的“拼凑”么?这么一来,马克思曾经信奉过的“实践本体论”岂非是海德格尔跨越时空影响了“非马克思”的马克思?董先生还不至于如此吧,那“拼凑”又从何说起?其二,董文虽然加了一系列试图凸显“物质”的定语,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成熟的马克思所坚持的本体论是“社会生产本体论”,这样,既是“物质本体论”又是“社会生产本体论”,岂非是“双本体论”吗?但是董先生说“双本体论”会“取消了本体论的科学的陈述”,[2]46“本体论具有一元论的特征,双本体或多本体现象的存在,事实上是取消了本体论自身的意义”,[5]12墨痕未干,声犹在耳,岂非自相矛盾?其三,“实践”同“社会生产”两个范畴之间难道是如董先生所说的“反对”关系吗?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社会生产”难道不正是我们所主张的“实践”范畴的“另一种说法”吗,“反对”之说又从何而来?其四,“社会生产本体论”是不是把“社会生产”“说成是”“事物最原始、最基本”的“实在”,这个“不能随意改动和编造的”“规定”的“本体”,这么一来,“自然界”岂非也派生于这个“最原始”的“实在”?董先生不是坚持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么?难道董先生主张成熟的马克思最后坚持的居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本体论”?!
显然,通过论争,董先生事实上已经或者说不得不承认:“实践存在论”的真正来源是《手稿》,而不是海德格尔,同样也承认“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而是一个“存在论”(ontology)的范畴的事实。董文总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给我们以惊喜,这是颇为典型的一处。
而董文所以陷入矛盾无法自拔,除了前文言及的对ontology本身理解的单薄之外,以一种割裂而非整体的视角看待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董文说:“马克思早期的一些著作虽包含了日益增长的超越前人的思想成果,但确也带有不应忽视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痕迹,不同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14并指出,“19 世纪 50 年代之后”,“马克思基本上已经告别了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的问题性和提问方式,在他的思考中也很少再使用‘实践’、‘存在’这类古典哲学概念”,[4]64这样看来,董先生认为马克思著作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痕迹”,也就是残留着“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的问题性和提问方式”,而具体表现则是“使用‘实践’、‘存在’这类古典哲学概念”,这样理解当符合董先生的本意吧。
我们想追问的是,按照这一分期,董先生又是从哪里得出了“在物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方面,马克思的‘实践’的内涵是一以贯之的”,[3]47而且这一“实践观”实现了对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突破,这一“不容置疑”、“众所周知”的“真理”呢?从残存着“资产阶级的问题性和提问方式”的早期呢?还是从很少使用这些古典哲学概念的“成熟期”呢?
其实,没有多少人会将马克思同“马克思主义”混淆起来,原因很简单,即便天才如马克思,在其咿呀学语时也不可能就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判断,甚至连马克思自己都有“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类似的表达在《全集》中至少有五次之多,熟读马克思文献的董先生想来不会陌生。这里不想对马克思如是说的原委,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同对“马克思”的研究之间当如何区分进行讨论,但至少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应以对马克思的经典文献研究为基础,董先生想必也能同意。但是,衡量马克思思想的成熟与否不能仅以“使用古典哲学概念”这样大而化之毫无说服力的根据来加以判断,更不能把“前期”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仍然局限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性和提问方式”,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荒唐的。更何况,以1850年代作为马克思“告别资产阶级”的分界,无疑太过武断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哲学的贫困》(1847年)、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共产党宣言》(1847年)等著作是否都不能看作马克思主义“成熟”的著作?这怕也不是董先生能“说了算”的吧。
将1850年代作为马克思成熟与否的划界的根据,董先生习惯性地没有给出证明,我们姑做揣度: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立论根据,至少在董先生看来,主要是《手稿》、《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这样,一旦这些文本都被划归为残留着“资产阶级的问题性和提问方式”的“不成熟”的马克思时期的“非马克思主义”(至少是有非马克思主义实质在内的)的著作,而“成熟期”的马克思又“很少使用”“实践”、“存在”这些概念,“实践存在论”的根据自然坍塌,董先生的批评自可一路通达,畅行无碍。但董先生大概没有想过,这样一来,自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究竟从哪儿来,也随之成了问题,希望董先生能够证明我们的揣测是错误的。
在此,我们还不得不指出,上面这些引文无须多加说明就充分证明,董先生以自己最清楚的语言在一再制造前后期“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然而,董先生却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责笔者一方面把马克思存在论化或存在主义化,另一方面说马克思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从而制造了“两个马克思的神话”。[1]14这样来理解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笔者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似乎是董先生的“独创”,但恐怕难以成立。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的,主要是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围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评价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两个马克思”的主张:一种是竭力抬高青年马克思《手稿》的思想意义,而贬低和否定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就制造了青年时期和成熟时期“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另一种恰恰相反,竭力贬低《手稿》,否定《手稿》思想与马克思后来著作思想的连续性,认为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指责《手稿》仍未超越唯心主义,并认为马克思后期完全抛弃了《手稿》的基本思想,这实际上又从相反的方向制造了“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这两种主张虽然观点针锋相对,但在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方面却异曲同工——其含义非常明确,就是指把前期或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后期成熟期的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对立起来,或者贬低前期而抬高后期,或者相反,贬低后期而抬高前期,虽然在前后期的时间划分上,不同的神话制造者并不相同。这样理解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的含义,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普遍认可并约定俗成的。不是哪个个人可以不加论证、随意推翻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像董先生那样自说自话另立“新”说的。其实,不用多说,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董先生的观点与上述后一种“认识论的断裂”如出一辙。所以,制造前后期“两个马克思”对立神话的不是我们,恰恰是董先生自己。
此外,董先生反对“实践存在论”还有一个重要依据,即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这里不想对这一立论是否成立再进行具体论证,我们只想说即便马克思没有用过,也毫不妨害我们如此去理解和概括他。就像时常征引马恩的德、俄、英诸种版本,对马克思的经典文献当烂熟胸中的董先生,也没有拿出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中曾经使用过“物质本体论”所对应的德、英、俄等欧洲诸种语言的概念,并用以指称和概括他们的哲学思考的例证出来。而更有学者注意到,马恩的经典文献中甚至“从来没有出现过‘唯物主义哲学’(德文die materialistische Philosophie,即英文 the materialistic philosophy)一词。”[7]难道,就此能推论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唯物主义哲学”么?
用以界定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意义的理论概念,不能也不应仅拘泥于马克思所使用的文字,在马克思的文献中甚至有大量对“哲学”、“哲学家”的贬义性使用,这也不妨碍我们用哲学的视角并在哲学史的脉络中寻找马克思的功绩。就算否认马克思作为“哲学家”的身份,也不能否认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在哲学史上以及他对哲学家们的影响。实践本体论、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能否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概括,其合法性基础不在于马克思是否使用了这些概念,而在于“实践”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一种地位,想来这一点应当能够得到董先生的认同。
为避免董先生又生发“将一顶帽子扣将过来”的联想,我们姑且借用董文中的用语来对董先生之于我们的批评做以总结,引号所引词句散见董先生数篇大作,恕不一一作注。董文中所说汉语以“存在论”、“本体论”、“是论”、“有论”等翻译ontology“都未尝不可”云云,其实“不过是论者所使用的障眼法”,其对“存在论”、“是论”、“有论”等概念中所包蕴着的中国学界之于ontology的深入理解的陌生抑或选择性无视“则是一目了然的”。董文将存在论视作海德格尔抑或存在主义的专利,乃至作为“本体论”的“替换”,“无疑是将”“存在论”大大地“狭隘化”了,而将“实践存在论”理解为“实践本体论”的“另一种说法”,并将之同所谓“实践一元论”、“实践唯物主义”等目为一体,更将南斯拉夫“实践派”、“赫斯主义”、“实践人道主义”等等强加在“实践存在论”的理论“来源”之中,则又是将“实践存在论”过于“泛化”了。而作者行文中大量似是而非的矛盾提法和不加论证即武断结论的论辩方式,则“实在是有点说不通的”。
笔者从来没有也不敢狂妄到将“实践存在论”视作所谓不可置疑的“真理”,直到今天,也还依然是说“走向实践存在论”,换言之,这是一个未完成,甚至远未完成的目标,我们试图用这样的思考为当代美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我们也不敢以“真理”自居随意去“认定”什么,更没有权力允许或者不允许“不同的声音”的存在,我们希望也欢迎有建设意义的、具有学术含量的批评,但我们不欢迎非学术的、不摆事实、不讲道理的政治化批评。对于董先生这样以不断的重复、武断,且敢于“认定”的“权威”的批评,我们除了澄清对方的误解,并希望对方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实事求是的、在理解的基础上再进行讨论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而这种希望却被说成是“将一顶帽子先扣过来”。要说到“帽子”,董先生所说的“颠覆和消解”马克思主义又当做怎样的解释?
试问,“on最早出现在拉丁文,后来进入古希腊语”,这是“摆事实”么?建立在对“存在论”如此单薄的理解的基础上,即对“实践存在论”横加指责,是在“讲道理”么?对自己立论中的自相矛盾视而不见,凡自己出即为真理,凡自他出则为谬误,宽以待己,苛以求人,这是“以理服人”么?经过如此“初步分析”即给实践存在论戴上“消解”、“颠覆”马克思主义等一顶顶大“帽子”,岂非骇人听闻?
这样的“帽子”,董先生最近又“发明”了一顶:实践存在论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旗号,完成的却是‘去中国化’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消解与置换”。[5]10我们实在想问问董先生是从哪里发现我们“打着”这一“旗号”,又怎么样“去中国化”了?不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么?事实是,我们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只是尝试在现有的实践美学基础上对之有所拓展和深化,确实还没有想到要把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探讨当作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努力。即使偶尔提到过“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也主要是强调马克思的实践观、人学理论等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既然我们还没有这种意图(也许是觉悟、水平不高吧)又何来什么“打着”中国化“旗号”,更何来什么“去中国化”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消解与置换”呢?前提不存在,结论必荒谬。而且,作出上述不无政治意味的结论总要作一些论证、分析吧,哪怕是“初步”的分析,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批评“实践存在论”是“唯心主义”、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拼凑,虽则是董先生基于自己的想像,但却还没忘引上笔者的两句话,然后再做歪曲;而对“去中国化”,董先生则干干脆脆地不加分析,直接作判断,下结论,这才是真正的“将一顶帽子先扣过来”!这难道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态度吗?
综上,董文说“一种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转移’没‘转移’,‘转移’之后的‘根基’性质是什么,是不能由论者自己说了算的”,[4]60我们也想说,这也不是由董先生说了就“算的”。实践存在论哲学基础的“转移”,是从对因为时代和历史的原因仅仅从认识论层面对于马克思的片面理解所形成的“哲学基础”,转移到已经为当代学者所认识和把握的、内蕴于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思想的根基之上。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根基不是什么存在主义的存在论,而是马克思的ontology,是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是马克思与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
三、“存在论”和“物质本体论”
从这一部分开始,我们拟对实践存在论的基本理论取向及其基础进行说明,由于相关的问题在前面以及更早的论文中,笔者均有了较多的征引、阐发,这里则尝试用尽量简单和通俗的文字对我们的诉求进行一种诠释。
首先还是关于“存在论”,其实是关于on的理解问题。对此问题的澄清远非董先生所理解的那样,仅是“主要存在于中西方两种语言习惯的差异和由此引起的两种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上面”[3]45那般轻松,而是需要面对一个由从古希腊语(“古希腊语”是古希腊多种方言的一个总称,它本身即足够复杂,更况这种讨论还有可能涉及更为古老的梵文及其他上古语言)到拉丁文、到古代欧洲语言再到现代欧美主要语言承载的西方哲学史的整体,笔者学有所限,实无信心能做到全面把握且又条分缕析。但中外学界前辈同仁在这个问题上已有了相当的研究,可视作本文的基础,这里仅尝试从逻辑角度对此问题做一个简单的陈述,疏漏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由于董先生了解并承认on作为系词的用法在古希腊文中占据着重要乃至“大部分用法”的地位的事实,我们可省去对此的铺陈征引,直接进入对于作为系词的on何以影响到ontology的理论谱系,我们又在何种意义和尺度上来使用和界定“存在论”的问题。为求通俗,兹以一简单例证勾连论证。
“……是……”是ontology问题的基本语言形式,想来董先生不会否认。由此,不妨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判断:“石头是……”。显然,这一命题乃至提问之成立的前提在于“石头”的“存在”(这个“存在”是动词性的“存在”,相当于on及英文中的being,也即董先生所谓“系词”的on,而非名词性的“存在物”),而且这个“存在”还不是一个作为总称的“石头”的存在,而是具体“存在”的这一块和那一块的“石头”的“存在”,也就是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物是存在的,是不可能不存在的,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它通向真理”[8]51中的那个“存在”,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存在论”(ontology)中的“存在”(on)。有了具体的一块块石头的“存在”,才会有“石头”这一概念的存在,才会有“是‘石头’”这样的判断的存在,也才会有对“石头”的“始基”、“本原”、“最初实体”的追问和澄清。
这样来看,在对存在(on)的追问,也即ontology的论域中至少包含着“如何存在”、“因何存在”和“是什么”这样三个基本问题:“因何存在”即寻求存在物之存在的“根据”、“本原”的理论向度,也即董先生所理解的“本体论”;“是什么”追问的是某一具体的存在物所以如其所是而非他是的那个“是”,也即通常所说的“本质论”。①这样概括仅是为了理解的方便,其实“是……”的追问不仅包含“本质论”,同时也是“本体论”追问的基本方式,对此,亚里士多德对“是”的意谓进行了澄清,并由此得出了质、量、本体等“十范畴”。董先生所理解的“本原”意义上的“本体”,其实直接源自“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同亚里士多德对于“本体”的讨论虽有关联,但其中的演变也极为复杂,下文将做简单分析。这两个理论向度在中国学界得到了相当的理解,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配了我们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ontology,乃至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本领悟。然而,从逻辑上说,“如何存在”其实是更为源初和根本的问题。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意识到,不管是作为“本体论”的“存在物之存在的根据和本原”,还是作为“本质论”的“如其所是”的“是”的追问和理解其实都先在地包含着对于“存在物”之“如何存在”的某种程度的领悟,反过来,对于存在物存在之根据以及其如其所是的“是”的回答其实也构成了对于“如何存在”的一种道说。
也正因如此,在我们看来,这个以追问“如何存在”作为根本的“存在论”才是“作为系词的on”之于ontology的理论谱系之影响的真意所在,也是我们所主张将ontology理解为“存在论”而非“本体论”的根本缘由。“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提出的初衷,也在于尝试在这一意义下的“存在论”的理论视野之下,以“生成论”反思“现成论”,以“存在论”反思和超越单纯“认识论”思维下的“主客二分”,将美学大讨论中的主要提问方式:“美是什么”转化为“美如何生成”,由此突破美学研究中过度拘泥于对“美”的本原、本质的抽象讨论,而相对忽视现实世界中美的生成和创造问题的关注的局面,以便对现代主义以来诸如行为艺术、荒诞、丑、惊颤等一系列新的审美现象和审美范畴的出现作出新的美学释读。而绝不像董先生所臆测的那样,由于“‘本体论’(英文为ontology,德语为Ontologie)真正的中文译法应该为‘存在论’。相应而言,如果‘实践本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实践存在论’或许更是一个合适的译名,因而,正式地将‘实践存在论’纳入美学研究的视野。从这个层面来说,‘实践存在论’不过是‘实践本体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3]45①需要说明的是当代学界不少学者仍然出于习惯以及其它学理上的原因仍然坚持“本体论”的译法,但其中不少学者所理解的“本体论”已经超越了董先生所主张的那种“本体论”的理论视野,其在理论诉求上同“存在论”实质上是一致的。在ontology理论谱系中,也的确存在着董先生所理解的那种“本体论”,不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这种“本体论”其实恰恰是为马克思所批评和超越的旧哲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用这样的本体论观来概括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将马克思拉回到了近代形而上学的水平之上了。仍借用董文的表述,“坦率地说”,董先生对于“存在论”的理解实是对于ontology和“实践存在论”的“歪曲”和“随意改动和编造”,“未免太强词夺理,太不负责任了”。
汉语学界究竟是谁最早将ontology译作“本体论”,甚至这个概念是直接译自西方语言甚或古希腊语,还是同许多哲学基础概念一样转道日文而来,这个概念在进入中国学界之后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种诠释和演变似乎尚待详考。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存在论”上。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的“海德格尔热”,特别是围绕着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等著作的翻译无疑为“存在论”这一概念的流行并最终为学界所广泛采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这也或许是董先生将“存在论”误作为海德格尔甚至“存在主义”的“专利”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对笔者而言,所以承认并多次强调海德格尔之于“实践存在论”的启发意义,原因也并不复杂。大陆学界同笔者年龄相近的一辈人,可以说几乎没有人不受到董先生所主张的那种“本体论”思维的影响,笔者亦不例外。但新时期以来,在哲学界对海德格尔研究所取得的许多重要成果的影响和启示下,我们也开始研读海德格尔,并逐步意识到,恰如海氏所说,我们过去对于ontology的理解,存在着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下,片面强调对客观存在物的“本原”、“本质”、“本质属性”的追问,而对更为根本的“存在”问题反倒遭遇“存在的遗忘”的现象。而当我们意识到这样一点的时候,再回过头来重新阅读马克思,我们发现,其实马克思早在海德格尔之前就已经向我们敞开了这样的“存在论”的理论维度,只是由于我们原有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视野遮蔽了这个客观存在的维度,因而无法对此获得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我们从“存在论”的视野切入马克思,此前之于马克思的一些理解中的疑惑也可迎刃而解,这也是我们最终提出“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将实践观与存在论有机结合为一体,也是马克思在西方哲学史ontology领域的真正革命所在。这里何来“拉存在主义”的“虎皮”之说?实际上,把马克思客观存在的现代存在论思想与存在主义混为一谈,进而降低为“存在主义”的,不是我们,恰恰是董先生本人。
董先生以“物质本体论”批判“实践本体论”,说“实践”不是“最普遍、最原始、最基本的实在”意义上的“本体”,这实在是张冠李戴、文不对题:因为他心目中的“本体”乃是物质性的“实体”,然而,这样一种“本体”即“实体”的“本体论观”同“实践存在论”、“实践本体论”并无关系,因为“实践存在论”认为实践是一种“活动”的、“关系”的存在,从来未曾主张“实践”是董先生所谓的那种“实体”。而董先生这种“实体观”的“本体论”恰恰是为马克思所批评和扬弃的对象。
由于马恩的经典文献中很少直接使用ontology及其西方语言的相应概念的表达,甚至由此在国内学界引发了关于马克思是否存在“本体论”(存在论,ontology)理论维度的讨论。不过由于董先生新近的文章似乎接受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也至少承认马克思的《手稿》中有实践本体论、劳动本体论的思想,只不过是在歪曲的意义上称之为“抽象的”罢了。所以这里对这个问题不做讨论。于是问题就在于马克思的ontology究竟是什么,是“本原实体”意义上的“本体论”,还是以“如何存在”为基本提问方式的“存在论”,这也就涉及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出发点的判断了。
1845年,马克思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9]213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10]24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即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57董先生认为此时的马克思尚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提问方式”中,显然他对恩格斯的这一判断是颇有保留的,或者他认为“萌芽”、“起源”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本身,而“历史唯物主义”和“新世界观”究竟又在马克思的1850年代之后的哪部著作中出现,董先生没有详述,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以“改变世界”作为其哲学乃至整个理论体系的展开的根本诉求,正是马克思超越一切旧形而上学乃至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们的重要根由,对于这一点,董先生应当也不会否认吧。
次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更提出了时常为人引用的以下两个命题:
意识[das BewuB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B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11]72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像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像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1]73
从以上的命题看,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也即“人们的存在”(董先生难道认为这个“存在”还是所谓“存在物”或“实体”么?)去描绘“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难道这还不足以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已然彻底扬弃了从抽象的概念、范畴的逻辑推演抵达所谓的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掌握(即“从天国降到人间”)的一切旧哲学方法论和形而上学么?而正是这一颠倒,马克思事实上已经彻底超越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而开始在“存在物”的“存在”的视野中去进行讨论。而人的“现实生活”也就是“人们的”“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改变世界”的新理论体系的最终归宿。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存在”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或更准确地说革命性地提出了“现代存在论”问题么?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追问并非仅仅是所谓“早期马克思”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同样根源于对这一问题的追问。
由于种种原因,在目前的教学乃至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被划分为三个独立的体系进行独立的研究。应当承认,这在事实上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人为割裂。这种局面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和反思。①该处有关内容可参见仰海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该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哲学著作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存在”问题在马克思那里的关注是持续的。
从《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已然将自己同“旧哲学”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将从“改造世界”和“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来追问包括“物质”和“人”在内的所有存在物的“存在”视作自己的事业。而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中,他发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2]32的“结果”,并在此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寻找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也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提出了自己“得到、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即可被视作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总纲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2]32
显然,对于“人的社会存在”,也即“现实人的生活”而非抽象的世界的“本质”、“本体”的追问,构成了马克思毕生思考的基本出发点,而澄清社会的人是“如何存在”的问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的“存在论”。对此,已有学者指出“《资本论》不仅是关于‘资本’的‘资本论’,而且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13]马克思“存在论”维度的存在,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基本的、客观的历史和学理事实,决不是什么“歪曲”、“颠覆”、“解构”,更不是什么“拉存在主义的‘虎皮’”。其实,恰恰是董先生“拉存在主义”为棍子,在批判实践存在论的同时,轻率地抹杀和否定了马克思的与实践观结合为一体的存在论思想及其在建构唯物史观中的关键作用。
四、“物质本体论”及其矛盾
那么,董先生所说的“物质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其实,从上引的几段马克思经典文献中的字句即可发现,“法的关系”的“根源”不是“物质”,而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决定人们的意识(Bewu tsein)的是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s Sein),也非抽象的“物质”。诚如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物质’在绝大多数场合都是表示人的社会实践的行为和结果的外在特征的形容词(material,materiell,materialistisch,等),如‘物质生产’、‘物质力量’、‘人的物质关系’、‘物质生活条件’,等等。他没有把‘物质’当作本体。……马克思没有、也无意要建立一个物质本体论。如果把马克思关于物质本身的零星论述加以发挥,使之成为系统的物质本体论,那就可能会淡化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独创性,既不能与以前的唯物主义有本质上的不同,也不能在学理上有效地抵御历史上对‘物质本体’的种种质疑。”[14]5
“物质”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不仅没有被赋予“本体论”的地位,而且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物质”和“人”一样,都是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确立其“存在”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说:“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5]52诚如有的学者所言,“这里的‘实物’(Ding)、‘定在’(Dasein),相当于物质存在,但马克思没有把它当作不依赖于人的存在,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14]5联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56的命题,可以发现,不管是对“物质”还是“人”,马克思的理论出发点都是一致的:破除古典哲学由抽象理论概念的纯逻辑推演来抵达对现实世界的把握这一形而上学的理性预设,并将这一被颠倒了的哲学之思重新颠倒过来,还原出被形而上学所抽象化、概念化了的“物质”和“人”的现实性。
虽然同前文提到的“存在论”、“本体论”一样,是谁最早使用“物质本体论”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似乎同样需要小心求证,不过,至迟在建国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观点就逐渐被广泛接受,并渐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乃至“唯一”的理解。也以此为基础,衍生出被董先生视作“不可超越”的以唯物、唯心为标尺对西方哲学、中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史乃至自然科学史进行区分划界,乃至将“唯心主义”同“落后”、“腐朽”、“资产阶级学说”等负面判断紧密联系起来,甚至上升至政治批判、人身攻击的地步。经历过那样一个不正常的学术生态的学者,大概很少有人对此不表示一种反思乃至反悔吧。
从学理而言,“物质本体论”的确立,以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进行的划分为重要依据的。然而,回到恩格斯的原文,我们将会发现,其实从这段文字中同样不仅难以直接推导出所谓的“物质本体论”,恰恰相反,我们更可清楚地意识到马恩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亦即这种“实体论”的“本体论观”的超越的彻底性。
在《终结》一文中,恩格斯不仅将“思维和存在”同“精神和自然界”并提,而且说“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9]224显然,这里“存在(Sein)”和“自然界”(Natur)的含义是基本一致的。而将“自然界”视作“第一性”的观点其实也并非始自马恩,费尔巴哈在其《宗教本质讲演录》中即指出“从我的观点看来,那个做人的前提,为人的原因或根据,为人的产生和生存所依赖的东西,不是也不叫做神(这是一个神秘的、含糊的、多义的词),而是并且叫做自然界(这是一个明确的、可捉摸的、不含糊的名词和实体),……自然界这个无意义的实体,是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16]523费尔巴哈更进一步指出,所谓的“第一性”“不过是时间上的第一性,而不是地位上的第一性,是物理上的第一性,而不是道德上的第一性;有意识、属人的实体,则在其发生的时间上是第二性的,但在地位上说来则是第一性的”。[16]523①文中所涉及德文原文,参见 Bolin,F.Jodl,Ludwig Feaer bachs Sämmtciche werke,由stuttgart于1908 年出版。显然,即使是在费尔巴哈那里,“自然界”(Natur)的“第一性”也主要从时间和物理意义的“本原”角度立论的。
尽管马、恩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都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但在“自然界”的“第一性”问题上,马、恩对费尔巴哈的继承还是显然的,问题在于,马、恩之于费尔巴哈在这一维度的真正超越却没有被董先生所了悟。在上引恩格斯的原文中,费尔巴哈用来描述“自然界”的“第一性”含义的“实体”,被恩格斯代以“本原(的)”。在汉语中很难看到这一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回到德文和马恩的哲学整体,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一词语的替换绝非偶然。
在费尔巴哈那里,第一性的“实体”的原文是Wesen(通译作“本质”),这个概念是由德文的系词sein的过去分词gewesen去掉前缀ge-演化而来的,它同源自希腊文的作为系词的on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同时也构成了ontology理论演化谱系中的重要一环。而恩格斯则扬弃了这个表达,转而使用Ursprüngliche来描述“自然界”(存在)对于精神(思维)的“本原”意义。联系前文提及的马克思对于旧哲学、形而上学的超越,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概念使用的转变绝非简单的用词习惯,而正是马恩对旧“形而上学”“实体”思维和“实体”意义上的“本体论观”之扬弃的彻底性的表现。
再看一段被董先生视作“再明白不过地讲明了物质本体论在说明和解释历史时的作用”[4]59的马克思的一段文字。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1]67
董先生能够将赋予这段在他看来是马克思尚未成熟的写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文字如此高的评价,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不过,这里依然无法推导出董先生的结论。
首先,“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中“存在”的原文是Existenz,汉语一般翻译作“存在”,日语译作“实存”,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翻译中,一些学者主张译作“生存”,“这个词来自拉丁语existentia(exsistentia),一般用来表示事物的存在,据说首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E·J·司各脱(810-877)。从语源上说,exsistentia是ex-sisto(在外站立)的名词化……因此,exsistentia所表示的概念是:现实地具体地存在着的东西或者这种东西的成立、现存、生存”。[18]显然,这里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说的是“存在”这种状态,同样不是董先生所理解的“存在物”,也即,这里不是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作为“物质的”“存在物”的人,而恰恰是个人的“存在”,同时,“第一个确认的事实”不仅包括个人的“肉体组织”,也包括“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肉体组织”是个人存在的“物质性”,而“关系”则是个人存在的“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个人的“存在”的内涵。顺便指出,作为系词的on、being、sein所包含的“存在”的含义,其实同Existenz有着极为密切的语源和逻辑联系。试问,这如何可以解释为“物质本体论”在说明历史时的“作用”呢?
至此,可以说,董先生所理解的“物质”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始基”和最初的“实体”的“物质本体论”,至多只能概括从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至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以及其他旧唯物主义的实体论的“本体论”思想,但用以概括马克思主义在ontology领域的真正贡献,则显然不但难称准确,而且实际上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降低到一般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的水平。恩格斯只是从“本原”的意义上肯定了“自然界”(不等于“物质”)的“第一性”,但这个第一性并非“本体论”(ontology)。而将“物质”视作实体性的“本体”则必然面临着一系列无可克服的逻辑矛盾。
矛盾首先来自“物质”概念本身,如果“物质”是对客观世界(自然界)一切存在物的理论抽象的话,那么,诚如董先生批评笔者将艺术、审美活动纳入到“实践”,导致实践概念的外延太广时所说“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广,其内涵就越狭窄”,当“概念包罗万有、无所不及的时候,其实它也就等于‘无’”这一“一般的常识”[5]6所指出的那样,“物质”概念的外延的广延,势必使这个“物质”概念“等于‘无’”。
更关键的是,如果“物质”仅仅是一种“理论抽象”,那么,它同诸如“上帝”、“神”、“理念”等唯心主义对于“本体”的预设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而如果“物质”并非“抽象”,而是现实的一切自然界的“存在物”(包括作为高级动物的“自然人”在内)的总称的话,一方面,“物质本体论”远未终结“最初的本原”意义上的“本体论”追问:在“物质”的外延所指中,同样存在着从无生命到生命,从低等生命到高等动物到人的演化,那么,究竟何种“物质”才是那个“本原”呢?另一方面,一切“存在物”的“本体”都是“物质”,也就意味着一切存在物的本体即是它自身,“石头”的“本体”就是“石头”,“人”的“本体”就是“人”,这样一来,对所谓“本原”的追问,实质上回到了问题本身的起点。用“物质本体论”概括马克思主义的ontology,无疑是将马克思在本体论领域的革命贡献彻底抹杀,而将之等同于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
在“本原”的意义上,在时间和物理的意义上,世界是物质的,自然存在物意义上的人也是物质的,人的精神、思维都派生于“物质”,这一点,我们不但从未否认过,而且也是我们所一贯坚持的,诚如恩格斯所说,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分野,但董先生却忘记了恩格斯紧接着所说的“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9]224-225一旦跨过“本原”的含义,而视之为“本体”,并将这一主张贯彻于认识论,则必然陷入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预设。
如果“物质”是“本体”,则“物质”无疑构成一切哲学追问的前提和基础,人的所有精神活动的解释最终也必然只能落实于物质性的生物活动,方才可以得到解答。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只能被理解和掌握为一种物质运动的结果,我们又何以澄清其同动物的“条件反射”之间的区别?仅仅用所谓“高级动物”的“高级、复杂的精神活动”区分,无疑太过空泛,而如果认为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即可发现人同动物之间在生物构造方面所存在的“本质差异”,由此,人无疑将彻底沦为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的对象。而这一点不但遭到马克思一贯的、深刻的批判,而且也遭到了近代哲学的猛烈批评,无需多做理论证明。
同时,“物质本体论”对于“认识论”的优先性的坚持同样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从而回到了笛卡尔主客二分的近代认识论思维的框架中。一方面,物质本体论的本体观之形成的基础本身就源自一个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方式的追问:“世界是什么”;另一方面,由于“物质本体论”无法澄清具有主体性的物质存在物“人”的主体性的哲学根源,人同自然界的所有的关系也就成为两个“物质存在物”的相对和照面,由此,设立逻辑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也就成为必需,唯其如此,“物质存在物”之间的关系的达成方才具有可能,否则人同自然界的关系也就只能成为两种“物质体”间不具有任何意义的“共同存在”了。
综上,“物质本体论”的理论失误在于将“自然界”在时间和物理意义上先于精神、思维的“本原”性夸大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不仅抹杀了马克思在西方哲学史上之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扬弃和超越,同时也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旧唯物主义哲学之于“物质”概念的理论扬弃和超越。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董先生批评“既然论者已经先期承认了自然界先于人的存在性,那么,又如何能够说在‘没有人的时候,有没有自然界都值得怀疑’呢?显然,论者是将世界存在的意义与世界存在本身弄混淆了”[3]49的批评再做些说明。
首先,“自然界”是相对于社会性的人而言的,如果没有人,没有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人,即人产生之前,我们现在称之为人以外的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充其量不过是种种存在物而已,而不具有相对于人而言的“自然界”的含义。这就是上面这句话的本意。请注意,这段话中的一个前提是“没有人的时候”亦即人类形成或产生以前,比如在2.5亿年前的恐龙时代,现在被我们称之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存在物都只不过存在着而已,它们不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或作为相对于人而言、与人相互作用和相互生成的对象世界而存在的,更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人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世界),正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没有人,也就没有相对于人而言的自然界,它们存在着,也只是存在着而已,但是不是真正作为与人相关的世界(自然界)而存在的,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现实的、人(生活、实践于其中)的自然界。这丝毫不涉及自然界相对于人的意识而言的先在性、客观性问题,因为在人还没有的时候,哪里来人的意识?没有人的(主观)意识,又哪来什么“客观存在”?所以,董文所谓“典型的唯心主义”的指责不但毫无道理,而且恰恰暴露出他们主张的物质本体论是游离于人和人的社会实践的抽象的自然主义的本体论。
诚然,马、恩明确肯定相对于人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存着”(这就是自然界第一性的含义),但是他们紧接着强调,“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这就是说,这种外部自然界的优先性只有在人已经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时才有意义。如果自然界还没有作为与人发生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对象时,这种优先性就毫无意义。在人类产生之前,这种优先性(客观性)更加无从谈起,因为它的前提都不存在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9]178由此可见,当我们在相对于人而言的自然界的意义上说“没有人的时候,有没有自然界都值得怀疑”完全正确,因为马恩说得更加透澈:这种意义上的自然界不仅值得怀疑,而且干脆“对人说来也是无”。更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句话里的“自然界”替换为“物质”也完全适用。这显然是对物质本体论一针见血的批评。
五、余论
前文论及,无论是对“人”还是“物质”,马克思实质上都是放置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予以审视,由此追问其“如何存在”的。而“社会关系”的达成也只能源自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关系”同样不是一个逻辑的抽象,它是人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也即人的社会性活动之中具体生成、发展的。由此,“实践”在马克思那里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更为根本的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是澄清一切存在物之存在的基础。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实践存在论”的基本理论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董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一方面强调,“哲学上的物质本体论,是不能被所谓‘实践本体论’替代的;美学上的实践观,也是不能被所谓抽象超然的存在观替代的”。却又同时强调马克思“最后坚持的事实上是一种具有客观物质前提和制约性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能动的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对人自身生产——的本体论”。[4]55-56我们不知道,董先生是否真正理解了“社会生产本体论”同“物质本体论”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因为,按照他对“本体论”的解释,“社会生产本体论”也就意味着“社会生产”(不就是“社会实践”的另一种说法吗?)是最初的“实体”和“本原”。显然,“社会生产本体论”实际上“颠覆”和“解构”了他自己对“本体论”的实体性解释,从而也“颠覆”和“解构”了他自己的“物质本体论”。同时,如果董先生承认“社会生产本体论”,那么为什么又对“实践存在论”的成立如此难以理解呢?既然社会生产可以包括“精神生产”,为什么“实践”就不可以包括“精神实践”呢?我们相信,董先生对于“社会生产本体论”的理解,可以视作此次论争对于董先生的一种影响,我们也希望,董先生能够通过“社会生产本体论”,来达到对“实践存在论”的真正理解。
对于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董先生和我们的论争的焦点似乎在艺术、审美这样一些活动是否是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的外延,然而,前文已然指出,董先生本人同样不仅主张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而且也从开始不赞同、后来羞答答地承认“实践”是“人的全部社会生活”的理论命题,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法找到同董先生的真正区别所在。而对于“实践”何以可以包括艺术、审美这样一些精神性的活动在内,我们在前面数篇文章中都已经做过论证,这里也不拟再做过多的说明。在这一部分,我们想对董先生对于实践存在论关于“实践”范畴的一些说明的误解加以澄清,也对董先生对我们的反批评的回应中的质疑做一些简单的回应。
在董先生那里,似乎认为我们将精神性的实践活动纳入“实践”范畴,就是要用这种精神性的实践替代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并作为“本体”,说什么“如果仅仅把‘实践’视为人的一般的感性活动,如审美、生存、人伦、欣赏等,并以此为美学实践观的阐释基础,那么就仍然可能是在抽象的逻辑中进行演绎”。[4]56这里要说明的是,首先,这种理解也属董先生随心所欲的联想,实非我们的主张,这一点上文已及。“实践”范畴的核心规定是“社会性”的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换言之,在我们看来,除去诸如饥饿时的胃部痉挛等这样一些纯粹动物性意义上的人的生物性活动之外,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人的全部生活,亦即“社会生活”都是“实践”;其次,将非物质活动之外的精神活动纳入到“实践”范畴中,更不意味着我们在逻辑上将“精神活动”提升到“物质活动”之上,这一点我们已做过说明,此处不赘。①在《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一文中,我们即指明:“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对实践作广义的理解和应用,他把物质生产劳动看成实践概念最基本、最基础的含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从来没有将实践的含义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是认为实践还包含了政治、伦理、宗教等人的现实活动,以及艺术、审美和科学研究等精神生产劳动。”
董先生还曾列举了数个“不能说是实践活动”的例子,其中包括“僧人念经”、“单相思”、“瞬间的审美感受”、“患臆想狂症”、“形而上学的思辨”,[20]最近又举出“婴儿吃奶”、“老人躺在病床上输液”、“懒虫奥勃洛摩夫每天遐思冥想”。[4]57在董先生看来,前面几个例子所以不是实践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是“革命实践”,而后面的几个例子是用来批评“实践是人在世的基本方式”的命题的。对这两组例子我们略做辨析。
我们不知道董先生是否意识到第一组例子的随意,简单说,“形而上学的思辨”不是实践,那么马克思的哲学沉思是实践么?僧人念经不是实践,那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是实践么?如果只有前者是而后者不是,原因何在?如果说这些都不是“实践”,实践仅仅指称所谓的具体的“物质劳动”,譬如,一个人一边思考哲学问题,一边打扫厨房甚至锄禾插秧,或者一个人一面思考,一面用笔在纸上书写(不知董先生是否认为这样的活动也不是“物质活动”)构思的结果,在董先生看来,这两个人同时既“实践”着,又“不实践”着,这是否是对具体的人的现实生活的“抽象”呢?这岂非与马克思主张从具体的现实生活过程、生活关系中把握人、把握物质、把握实践的思路的正好相反?!“瞬间的”审美感受不是实践,“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深沉的审美感受是实践么?“瞬间的感受”是一个完整的审美活动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董先生是将瞬间的审美感受理解为瞬间的单纯的感官刺激,如此一来,“审美活动”岂非都要随之土崩瓦解?“僧人念经”应该是佛教出家人修行的基本方式,是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怎么能排除在实践之外呢?而至于“患臆想狂症”则更让人啼笑皆非,且不说这种提法本身依然是对于具体的人的活动的抽象,我们主张实践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总称,而董先生非举出一个(暂时、部分)丧失了人的社会性和意识的生物性病理现象,这对“实践”范畴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说后面一组例子,董先生举出老人、婴儿和奥勃洛摩夫,认为他们的“在世方式”不是“实践”,所以为“实践是人在世的基本方式”的命题不成立。首先,“实践是人在世的基本方式”的命题不能反过来是“人的在世的所有方式都是‘实践’”。原因有三,其一,原命题中的“人”是社会的人,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其二,这个“人”是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逐渐展开和完成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断形成和完善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完整的“人”,不能割裂成婴儿的人、青年的人、老人的人;其三,“基本”本就不是“全部”。所以,举出不是“实践”的“人的在世方式”,特别是自然意义上的人的在世方式的例子来否定这一命题本身就是文不对题。打个比方,马克思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有人举例说先天性失明的盲人没有视觉的原因是生物原因,不是世界历史的原因,所以这个命题错了。董先生的逻辑即与此仿佛。具体到“婴儿吃奶”,如果是与哺乳动物一样的无意识的生命活动,当然不算实践;而“老人躺在病床上输液”,则是人生(生老病死)的一个环节,如果他积极治疗躺在病床上输液,与病魔抗争,怎么能不算实践的一部分呢?顺便说一下,奥勃洛摩夫的“遐思冥想”,我们看不出为什么不能将之视作是一种实践,作为一个正常人,他在他所生活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活中主动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在世”的方式,他通过这样的一种冥想完成自己的“本质力量”,虽则消极、无聊,但却无法否认这就是他作为一个“多余的人”的“实践”。
至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做一个总结,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是社会的人的全部社会活动的总和,这种社会活动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主体性的投入的属人的活动。这样的回答不知能否得到董先生的认同。
此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①主要是《“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实质与思想渊源》中关于“实践”部分,本节不注出处均出自该文。董先生对笔者《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一文中对于“实践”的范畴史梳理提出了一些质疑,这里一并回答如下。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董先生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不是物质劳动和生产实践,根本上是一种道德的形而上学”。对于这一判断,我们表示惊讶,难道仅仅因为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这种“活动”就成了一种“形而上学”?试问追求社会公正的这一“行为”、“活动”怎么就成了一种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呢?难道说董先生所理解的“物质实践”就是以“实践”本身为目的的,还是“无目的的”,难道“目的”可以成为某一活动的“本质规定”?我们没有否认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是一个伦理学范畴,我们强调的仅仅是,他的“实践”范畴从外延上存在着广、狭两义,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抽象固然是形而上学的基本运思方式,但总不能说形而上学家所说吃饭、睡觉这样的活动都是“形而上学”吧。
对于康德,我们说康德自己认为“道德实践”才是真正的实践,并以此用来批评“按照(遵循)广义的自然概念的实践”这种在他看来是需要予以纠正的、“流俗理解和误解”。由此证明,近代以来,“把实践主要理解为物质性的技术生产的这一‘流俗’见解已经相当普遍”,我们不是要用康德来纠正这种“流俗”的见解,只是要用康德证明他所尝试“纠正”的这种观点已经流行开来。有什么“内在矛盾”呢?
对于黑格尔,董先生大谈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本质,问题是,我们仅仅指出黑格尔的“实践”概念“就范围而言”,也就是说,所涵盖的具体的内容在外延上同马克思的“实践”基本吻合,我们没有说马克思的“实践观”同黑格尔是一致的,两者之间的哲学基础的差异实在无需多做论证。这就好像同是点头这样的一个动作,外延范围一致,但是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却可以分别表示同意和不同意两种意义。总不能因为它们的文化传统(哲学基础)不一致,就否认两个动作在“行为”这个层面上是一样的吧。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董先生也“以很大的篇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很遗憾,这些分析实在同我们的主张无关。
对于费尔巴哈,董先生对我们将“不贬低那种‘自然需要’或‘感性需要’,即‘饥,渴,倦,吃,喝,饱,睡眠’等比较低级的‘实践’”,视作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却“否定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实际的、现实的、自然的生活的实践观”表示“奇怪”。并最终回到“肯定唯心论的实践观,这无疑不能说是一种进步”。我们仅仅希望董先生能够看一看我们在怎样的意义上说黑格尔的伟大,又在怎样的意义上说费尔巴哈的“退步”:
在黑格尔那里,吃和喝还具有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延续的基础性地位,他天才地猜测到人首先要吃喝、生存,然后才有可能从事各种各样的精神活动,包括艺术和审美,因而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因素;而费尔巴哈的吃和喝只不过是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生理活动而已。[20]
黑格尔的“伟大”在于在其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天才地猜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费尔巴哈的“退步”(不是否定)是因为他虽然是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审视“吃”、“喝”这样一些“基础性”的“低级的”人生实践活动,却仅只将之视作“自然需要的满足”,退步与否非一目了然?有什么好“奇怪”呢?对此,我们只能将之归之于在董先生那里根深蒂固的“唯物论”必然“进步于”“唯心论”的偏见了。
这次围绕“实践存在论”的论争持续已一年了,然而,在面对一次次的重复性和无针对性的揣测式批评中,我们已从最初的看到批评时因实践存在论美学受到关注而生发的兴奋转为疲倦。如果非要找到我们从此次论争中所得到的收获的话,我们也很茫然,似乎除了意识到我们一度认为已经成为历史的陈旧思维方式依然如此根深蒂固之外,除了为了回应批评而不得不一次次重申我们认为已经表述得足够清楚的概念之外,真的难以谈得上什么收获。当然,为了回应批评,我们也较此前更为系统地重新阅读了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和新时期以来学界关于本体论、本体、存在论、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等相关的研究文献,这对于继续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自然是一件好事,然而这些同论争所涉及的数个议题似已无甚关联。我们依然真诚地欢迎并期待严肃的、真正学术的而非政治化的批评,然而,对于本文和我们此前几篇反批评文章所涉及到的有关议题,如果看不到董先生像样的新的批评意见,我们就不准备继续回答了。
[1]董学文.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辨析[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1):9-15.
[2]董学文.“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37-50.
[3]董学文.“实践存在论”美学何以可能[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9,(2):45-50.
[4]董学文.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再辨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3-65.
[5]董学文,陈诚.“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实质与思想渊源[J].中南大学学报,2010,(1):5-12.
[6]董学文,陈诚.超越“二元对立”与“存在论”思维模式[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3):1-6.
[7]刘立群.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没有用过“唯物主义哲学”一词?[J].泰山学院学报,2005,(2):1-6.
[8]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195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0,(2):4-14.
[14]赵敦华.“物质”的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嬗变[J].社会科学战线,2004,(3):1-7.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2.
[1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23.
[17]王炳文.名词解释[J].国外社会科学,1983,(4):80-81,36.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8.
[19]董学文.“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缺陷在哪?[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9,(4),5-8.
[20]朱立元.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76-95.
(责任编辑:李孝弟)
A Counter-Criticism of the Recent Criticism about Practical Ontology——An Initial Summary of the Criticism by Mr.Dong Xue-wen and Others
ZHU Li-yuan,LI Yong-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The argument about"practical ontology"as being the patchwork of Marx's view of practice and Heidegger'ontology derives from a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ontology"and a separa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Marxist ideology.In view of Marx,"matter"and"nature"are merely"primary"in the sense of"origin"rather than"ontology."From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to his later critiques of political economy,Marx constantly inquiries into the question of"existence"(on,being,sein).His true revolutionary transcendence,beyond all classical philosophies and metaphysics including old materialism,is his ontological thinking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view of practice,"rather than the so-called"substantial ontology."
practical ontology;practice;ontology;Marxism
B04
A
1007-6522(2011)01-0056-23
2010-06-23
朱立元(1945- ),男,上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