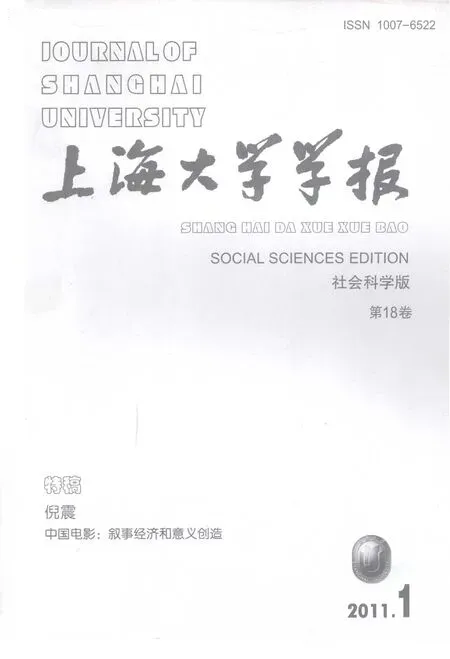“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陆绍阳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871)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陆绍阳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871)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十七年”电影;“影戏”传统;故事;冲突
一、中国电影的“影戏”传统
“十七年”电影承接的是将近五十年的中国电影传统,在中国电影前50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中国风格,但中国电影在利用影像手段讲述故事上已经比较成熟,已有《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电影精品问世。作为一个艺术文本,它讲述故事的能力,表现社会政治的宽广度和观众的接受度,都使后来者感受到了电影这门年轻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度。可以确认的是,当时的电影并没有偏离世界电影发展的主航道,也就是在叙事层面上,它更多地契合了观众的审美期待,在营造“银幕幻象”这一点上并没有要疏离的倾向,相反把它看成是可资利用的元素,这就保证了电影这门诞生在大众娱乐场所的艺术,并没有放弃和观众亲近的努力。同时,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生成的中国电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些是潜移默化的,有些是电影艺术家有意识的吸收,从这个“舶来品”进入中国起,就不由自主地被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
理解中国电影,或者说进入中国电影的通道在哪里?有学者认为蒙太奇和长镜头这两个概念是西方人认识电影的关键词,至少在爱森斯坦和巴赞眼里,这两个概念分别构成了他们各自电影观的基础,那中国人认识电影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以陈犀禾、钟大丰、陆弘石为代表的电影史学家明确把“影戏”认定为是中国人认识电影的核心概念。①陈犀禾的《中国电影美学的再认识》和钟大丰的《“影戏”理论历史溯源》两篇论文是思考“影戏”学说的重要文献,均收入了罗艺军主编的、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一书。2001年,钟大丰又发表了《中国电影的历史及其根源——再论“影戏”》一文,对“影戏”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应该说这个观点是具有洞察力和有创新价值的,虽然中国电影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这个论点是在芜杂的各类言说中及时做出的有说服力的总结,在中国电影的创作界和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确实,“影戏”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它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学者戴锦华把“影戏”传统表述为是中国戏曲与古代小说的叙事方法与“五四”以后“文明戏”三者的融合。②顾肯夫、陆洁、张光宇于1921年4月在上海创办的《影戏杂志》,现已成为上海图书馆珍藏电影文献中的“镇馆之宝”。1924年12月3日至24日,上海《大公报》连载郑正秋的谈中国电影草创时期轶事的文章,题目叫《说中国影戏》;理论家侯曜把它的著作命名为《影戏剧本作法》;主演过《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的郑鹧鸪刊登在《民国日报》(1925年3月21日)上的介绍自己演艺生活的文章,题目叫《我之影戏回顾录》。商务印书馆还在1918年专门成立了“活动影戏部”,拍摄新剧和古装剧,这是民族资产阶级不依靠外资自制影片的开始,由此可见“影戏”的名称在20世纪20年代是有相当普遍性的。《定军山》只能说是一部不完整的戏曲纪录片,但它毕竟将“影”和“戏”做了最直接的结合,并开创了戏曲纪录片这一片种。中国电影的几个第一部都多少与戏曲有关,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描写戏曲艺人的悲欢离合,片中还穿插了4段戏曲演唱;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也是根据同名京剧改编并由戏曲大师梅兰芳主演。戴锦华强调了“影戏”这个概念的生成是有历史渊源的,尤其是它和中国戏曲以及当时流行的“文明戏”的关联,从中可以寻找到影响中国电影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电影刚在中国放映时,中国人给这个科学和艺术结合的新鲜事物命名为“西洋影戏”、“电光影戏”、“美国影戏”等,巧合的是不管怎样命名,后面总是带着一个“影戏”的后缀,后来就干脆简化为“影戏”,它成了中国人早年称呼电影的通用名称,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把这个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和“戏”联系在一起,只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影”字,说明是带影子的戏,也曾有学者相当肯定地指出,“影”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识别标志,“戏”才是其基本内涵,把电影命名为“影戏”反映出当时电影工作者对电影的基本认识,在他们眼中,电影既不是对生活形态的简单实录,也不是和内容无关的形式实验,而认定为是戏剧的另一种样式。比如徐卓呆在《影戏者戏也》一文中非常肯定地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新兴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包天笑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续篇)》中写道,电影初来中国时,大家只说去看影戏,可知其出发点原是从戏剧而来的。早年中国电影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周剑云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影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不开口的、有色无声的戏。虽然也有零星的文字讨论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它的独特性,但总体而言,从当时的报章文献看,占主导的观点还是认为电影就其本性来说是戏剧,至多是戏剧的一种变奏。
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物传入中国,为什么一开始不叫它“电影”,或者其它什么名称呢?而是起名为“影戏”?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影戏”说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且深远地影响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走向,它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首先,电影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如何让“西洋镜”在这个拥有悠久文化的古国扎下根来,这是摆在当时从业者面前的一个问题,从对“影戏”的命名看,他们采取的是一种相对稳妥的方式。“戏”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已经根深蒂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戏剧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已经被时间证明它受到中国人的万千宠爱,因此在对电影这个新的艺术形式,带有明显商业目的的艺术没有足够的认识前,但又需要给它命名的时候,当事人就认为是找到了两全其美的方式,把电影和戏联系在一起,这样既有“新”的东西,又保留了吸引观众的核心内容,既可以满足一些新潮观众的好奇心,又不会疏离那些喜欢传统的观众,可以说是很有策略的举动。
其次,电影进入中国后,很快就与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联结在一起,打上了社会和时代的烙印,在西洋艺术本土化方面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这里面也不排除因为对这门新艺术太陌生而采取的无奈和权宜之举,但那些中国电影的先驱者们却在这门艺术中注入了他们的艺术理想,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心得贯注在新的艺术之中,这当中包含了电影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信念。与此同时,当他们自己有机会拍摄电影时,并没有编创新剧,而是直接搬演现成的戏曲片,比如首先吃“螃蟹”的任庆泰,虽然他拍的第一部电影最初的动机是为了给京剧大师谭鑫培祝寿,选取了当时谭鑫培先生最受百姓喜爱的题材和形式拍出了《定军山》,实际上就是一部戏曲纪录片。但此后任庆泰一发而不可收,接连拍摄了谭鑫培的《长板坡》,俞菊笙的《艳阳楼》和《青石山》,许德义的《收关胜》,小麻姑的《纺棉花》等剧目片段,这些所谓的电影全是清一色的对传统京剧的搬演,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戏曲有着当时庞大的观众群,拍摄戏曲片是最保险的商业行为。中国的戏曲(剧)虽然发展历史没有西方的戏剧久远,但它的民族特色、成熟度又不亚于西方戏剧,这也给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块具有东方风格的坚硬基石。
再次,正因为最初的电影人多是从文明戏、话剧界转行来的,如田汉、沈西苓、郑君里、金焰、白杨、赵丹都是先从事话剧工作的,他们又习惯性地拿戏剧表现手法、美学要求来衡量、规范电影。中国最早出版的电影专著之一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年)就明确指出:“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1]因为是“拍‘影戏’,自然就很快联想到中国固有的旧戏上去。我的朋友郑正秋先生,一切兴趣正集中在戏剧上面,每天出入剧场,每天在报上发表‘丽丽所剧评’”。[2]郑正秋等电影人是演文明戏出身,所以电影中大段的说教和他的这一背景是有关系的。我们从张石川在《一束陈旧的断片》一文中的具体描述中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电影制作和戏剧的瓜葛有多深:“亚细亚(1909年)公司成立了一年才拍戏。演员多数是‘新剧家’,就是演话剧的,或者说是演文明戏的。全都是男演员,没有女的,‘男扮女装’不但是中国旧小说中最常见的浪漫故事,在中国的戏剧艺术(旧剧、新剧)上,也是最出色的本领。连近代科学宠儿的电影,到了中国,也未能免俗,亚细亚拍电影,剧中的女角,都由男人演。我们‘发明’的拍戏方法是这样的:正秋教演员做动作,我指挥摄影师选择机位。摄影机一开,演员做起戏来:哭哭笑笑,跑跑跳跳,跟舞台上一样。直做下去,一直到摄影机的胶片完了才停止,加了胶片,然后再接着来,刚才在哪儿断,现在就从哪儿起。”而吴永刚在回忆当时的创作时说得十分明白,当时电影剧本的来源就是“文明戏”的照搬,①“文明戏”是我国话剧的前身,1900年,留学日本的王钟声观看了日本的话剧表演,他被这种崭新的舞台样式打动,于是潜心研究,回国后首创了中国话剧的前身:“新剧”,后期又称“文明戏”。随后,王钟声、马相伯等人在上海白克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社团“春阳社”,1928年由戏剧家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文明戏”作为话剧的前身,也不乏进步思想,比如反封建思想,反对裹脚、纳妾、买卖妓女等。无所谓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一切掌握在导演手里,间或有像“文明戏”式的幕表分场剧本。[3]虽然“影戏”这个概念没有多久就被“电影”所取代,②1905年6月16日,上海《大公报》首次使用“电影”这个词取代“电光影戏”,但另有一观点认为它到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兴起之后,才逐渐被“电影”一词所取代。“影戏”的痕迹并没有随着词语的弃用而消失,相反,作为一种创作主张和美学原则渗透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影戏”说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第一,故事是第一位的。电影作为一种通俗文化,和任何一种通俗文化一样,消费者充满着对故事的渴望。作家毛姆说,听故事的愿望在人类身上,同财产观念一样是根深蒂固的。观众在千奇百怪的故事与情感宣泄中获得世俗生活的愉悦、幻想和趣味。在电影发明阶段,一些电影发明家就产生了将电影首先用于讲述故事的想法,当时的专利书可以为证,W·保罗和G·韦尔斯的专利书上就提到:“用放映的活动画面讲述故事。”[4]这样的表述清晰地规定了电影的主要功能,也抓住了这门艺术的核心。
电影诞生之初有两条影响未来电影发展的源流,一条是由卢米埃尔兄弟开辟的,他们的电影注重对生活的模仿,是以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为立身之本的,卢米埃尔兄弟出于照相师的本能,将电影引向纪实美学的道路。后来的法国诗意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德国新电影、伊朗新电影都是沿着这条路往前走,把对真实性的追求放在首位。而另一个先驱者梅里爱走了一条和卢米埃尔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用电影来继续他的魔术和木偶神话剧的表演,梅里爱开掘了电影的戏剧美学,他是把戏剧美学运用到电影中的第一人,他在电影中增加了戏剧性,提高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观赏性,创造了一个魅力无比、奇异的世界。而早期的中国电影创作者显然和梅里爱的趣味更相近,他们绞尽脑汁希冀满足人们对故事的渴望,观众看电影就是去看戏,是不是有戏,意味着是不是有故事,好故事的标准就是引人入胜,情节跌宕起伏。中国人传统的戏剧审美习惯,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形成一种牢固的审美心理定势,即希望看到表现人生悲欢离合的“有头有尾,层次分明”的呈线性发展的故事,而排斥“时空交错”的放弃逻辑顺序的作品,观众不希望情节游离开去,宁愿跟着导演的安排往前走。他们把“讲故事”,即情节的曲折生动作为衡量影片叙事成功的基本标准,注重影片叙事中的传奇、巧合等因素的应用。这些要点在当时郑正秋、张石川等人为代表的电影创作主潮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是“形式活泼、颇受观众欢迎的文明戏的编剧与表演方式,影响了初创时期的中国电影;而中国戏剧与故事的传统,特别是通俗文学一面,包括民间故事与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则多融会于早期电影当中,成为其活的有生命力的关键性元素”。[5]郑正秋、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把传统的舞台艺术中的许多表现方法运用到影片拍摄之中,由于郑正秋、张石川等人的影片在商业上的成功,使不少创作人员竞相模仿。1933年,郑正秋编导的《姐妹花》能在上海连映两个多月,曲折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悲剧性的命运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一年后,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在上海的酷暑天里连映84天,影片中小猫、小猴两个孤儿的凄惨命运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同情。14年后,蔡楚生又一次将自己影片的票房记录刷新,《一江春水向东流》(和郑君里联合导演)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1月,在上海连映三个多月,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连映时间最长的纪录,观众达70余万。这部影片采取的也是典型的戏剧式叙事结构,导演把社会、历史和人物性格因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家庭的遭遇和时代的变迁融合在一起,使影片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而钟惦棐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当时的创作者采用这种创作手法的缘由,他说解放前的进步电影艺术家迫于政治的需要,把明明是“简单的道理通过曲折的情节表现出来,这在我们,无疑是一种痛苦。但也应看出,从中锻炼了他们在电影艺术上的表现能力”。[6]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外力的因素,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电影的“戏剧性”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第二,注重矛盾冲突,讲究情节的曲折。戏剧主要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冲突的关系美,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一出戏记流水账似的铺排生活是很难吸引观众的,冲突是矛盾在文艺作品中一种尖锐的表现形态。按照黑格尔对“冲突”的解释,冲突是对本来和谐情况的一种改变,要有一种破坏力量作为冲突的基础。戏剧中人物性格的开掘和故事情节的推进,都要靠戏剧冲突来实现。由于戏剧在舞台上演出,虽然也用分幕和分场来转换时间与空间,但分幕总是有限的,时空受到限制,因此,戏剧所表现的时空要相对集中,不能拖泥带水,这就要求艺术家在一定时间的舞台演出中要有集中性和概括性,这也是“三一律”总是大有市场的原因。早期的创作者认为电影也可以概括为是主要反映现实生活冲突的关系美的。在剧作上,“影戏”电影借鉴了冲突律、情节结构方式和人物塑造等大量戏剧剧作经验,在双方的冲突和撞击中展开情节,冲突越集中,越尖锐,效果就越好,冲突双方壁垒分明,常常明显地分为善恶两方,观众在伦理上也容易区隔,其结局则大多是以善良战胜邪恶而告终。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一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叙事上的冲突容易和现实中的矛盾相对应,有大量现成的冲突资源,这样“中国式的家庭伦理和民族使命纠合起了复杂的人物关系,使中国电影的情节组织能力大大提升”。[7]在《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丽人行》等影片中,冲突的各种形式都表现得相当充分。
第三,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在文艺功能上,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早就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说,认为诗具有教益和娱乐双重功能,既劝谕读者,又使他们喜爱,是一种既重视摹仿又重视受众快感和教益的文艺观。这种劝善惩恶,颂扬正义,通过对人心的潜移默化,达到促使社会进步目的的理念和中国人倡导的“文以载道”有很多相通之处。在中国第一部内容全面、系统介绍影戏知识的著作《影戏概论》中,作者周剑云、汪煦昌就认为影戏具有“开通风气,指导社会”的功能,[8]22而侯曜说得更直接:“影戏是教育的工具。”[8]50郑正秋、洪深等也有诸如此类的表述。
电影从业人员不仅在观念上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在实践活动中也主动向它靠拢。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理念作为大众意识形态,是中国普通百姓最为关注的民间生活层面,呼应了观众的审美取向,同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同构。这一切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内化为创作者的自觉行为和自我要求。电影理论家尼克·布朗认为,最复杂、最有力的流行形式总包含传统伦理体系和新国族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妥协,这种形式能整合这两者之间情感冲突的范围和力量。因此,有学者提出,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经过历史和文化的长期积淀与筛选,创作者就试图把观众烂熟于心的故事模式与特殊的历史语境挂钩,以民族气节的表现为目的,机智巧妙地完成了影像的隐喻性叙述和传统价值中的叛逆性想像。[9]20世纪20年代,邵醉翁创办的“天一”公司的制片主张是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而郑正秋明确指出:“我做导演,往往喜欢在戏里面把感化人心的善意穿插进去。”[10]1913年,郑正秋编剧并参与导演了中国故事片的开山之作《难夫难妻》,他以辛辣的笔触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对人的戕害;“明星”公司成立后,郑正秋坚持以艺术形式进行社会教化的方针,由他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1923年)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封建因果报应思想和主张平民教育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混合体;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第一部“左翼”影片《狂流》则有意识地把个人感情纠葛与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一江春水向东流》在社会批判的基础上,以特定故事类型表现传统的忠孝伦理、道德判断。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们都把电影作为表达自己社会政治理想的工具,这种明确的社会功利目的决定了中国电影创作不允许暧昧的,带有非理性色彩的东西存在。
第四,影像的辅助作用。由于对电影的教育宣传作用的强调,以第二代导演为主体的电影人对影像本体的思考明显滞后,加上“戏剧性”的“正统观念”,影像的伸展空间就受到挤压,电影语言是围绕着情节叙事展开的,出于服务的目的,处于辅助地位。创作者对情节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影像和镜头处理的探索。当然,为了真正有效地达到教化作用,只有借“副以背景”、“辅以音韵”的艺术创造,才能确保叙事的“调和”与“流畅”。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电影也逐渐形成一套以叙事蒙太奇为主要特征的时空组合体系。1925年,侯曜拍影片《弃妇》的高潮段落时,主人公采莲在山中打柴的镜头和芷芳被抢劫的镜头交替组接在一起,当采莲得知芷芳处于危急之中,立即赶下山去救助,这已经是典型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的交叉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了,明显地受到《一个国家的诞生》中经典段落的影响,对紧张气氛的营造效果已比较明显。时隔两年后,侯曜导演了《西厢记》,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一只正在绣花的手的特写,这种镜头处理方式在当时的影片中是罕见的,导演突出了单镜头的表意功能。而且这部电影动用了约5000个群众演员,用6台摄影机同时拍摄,影片基本上摆脱了以“场”为叙事单元的局限,发展成为以镜头为基本叙事元素的新的结构处理方式,“影戏”结构中“影”的成分在增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电影意识觉醒的表现。重视“场”(段落)还是从镜头出发,基本可以判断出导演受戏剧影响的程度。
学者杜庆春特意指出,在1930年代的电影中,尽管当时主导中国电影修辞体系的“三镜头”(先是交待性的双人关系镜头,然后是谈话双方的对切镜头)处理方式和最常用的全景、中近景、特写镜头构成的“三景别”修辞法则已经出现,但从当时的影片中可以观察到,能够促进人物之间情感交流的正反打镜头运用得并不多,即便有类似的处理,也没有有意识地将摄影机和人物视点统一起来,不能形成恰当的人物之间的情感交流。[11]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电影中,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力加大,更加强化了技巧服从并服务于叙事关系的基本原则。著名摄影师吴印咸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拍摄纪录片,他在战火硝烟中拍摄的《白求恩大夫》已经成为中国文献中的珍品,但以他为代表的延安纪录学派那种鲜活的,甚至随性的拍摄手法,建国后只是在少数影片中“冒了一下头”,并没有更多实践的机会。真正从“影戏”传统中摆脱出来,走向视觉化表达的,那是在新时期电影中,特别是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张军钊、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等导演都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实践。
二、“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在钟大丰、舒晓鸣等电影史研究专家看来,中国“影戏”传统的基本原则为新中国电影创作奠定了基础,中国早期电影所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从政治社会的功能出发,以戏剧性叙事为核心,使电影视听构成服从和服务于叙事,这与几十年来在中国电影中占主流地位的电影主张是一脉相承的。[12]1949—1966年间的中国电影并没有因为社会制度的改变而产生本质的变化,事实上,“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延续了对好故事的追求
一直以来,在中国电影人眼里,好电影的标准就是好故事基础上的人物性格化。在大部分影片中,故事的叙述是电影最根本的目的,在影片的结构构成中占核心地位。杰姆逊在总结故事的特点时,认为它必须给人一种新的事情就要发生的幻觉,讲故事就是要制造出一个事件的幻觉,即历时性的幻觉,这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光有时间的流逝并不成其为故事,必须给人带来新鲜感。[13]“十七年”电影对故事性的追逐一如既往。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期,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号召电影要创“四好”,即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好,“故事好”是着重强调的一个方面。因为面对新的服务对象——工农兵阶层,戏剧式的叙事方式最能有效地吸引和引导观众。因此在绝大多数影片中,各种大同小异的戏剧式叙事方式、结构和技巧被普遍地采用,并达到了娴熟的程度。我们可以在“十七年”电影中找到大量的实例,比如表现清末农民起义的影片《宋景诗》采用了话本传奇小说中的“官逼民反”、“兄弟结义”、“单刀赴会”等叙事元素和说书式的表达方式。导演郑君里感觉这样表现自然贴切,容易被观众接受。而何其芳认为《青春之歌》里面最能吸引受众的是那些关于当时革命斗争的描写:“紧张的地下工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英勇的监狱斗争。这些斗争都是能够激动人心的。”[14]
(二)延续了对戏剧冲突的爱好
“十七年”电影在把矛盾冲突作为结构的基础这一点上没有改变。茅盾曾经指出,“我们必须反对创作上那种‘无冲突论’或类似‘无冲突论’的倾向,必须把从表现生活矛盾中去创造人物,作为现实主义的重要课题”,[15]这种以“冲突律”为核心的戏剧式叙述架构,有些史学家在讨论“冲突律”之所以会成为本时期电影结构形态的主流时,借用恩格斯“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来形容,即它并不是某个文艺政策单方面规定的缘故,而是多种力量“合围”的结果,诸如“影戏”传统的审美习惯、某些深层的社会文化需求、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也许暗合了当时流行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考察“十七年”电影,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像《我这一辈子》、《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董存瑞》、《中华女儿》、《青春之歌》等影片,创作者在组织矛盾冲突时,并没有像某些学者想像的那样,是机械的、空洞的、完全是为了配合政治的需要。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些作品就会是应景之作,没有长久的生命力。但事实上,这些作品不但吸引了观众,而且留存了下来。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影片通过一些基本的冲突和克服、对抗与解决的模式,表现了真实的社会矛盾冲突,比如革命与反革命、压迫与反抗、个人与集体、进步与落后、新与旧的冲突,这些矛盾冲突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创作者凭空想像的,有些干脆是创作者亲身的经历,即便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基本上都是有原型,是以社会真实作为基础的,体现了真实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的切肤之痛,所以并不让人觉得矫揉造作,反而是富有质感和力度。
(三)更加突出教化功能
可以说,在中国电影的初创时期,电影人的创作目的比较单纯,就是让大众爱看电影,让电影这颗幼苗从根上开始就有充足的养分。解放后,主旋律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把电影的“教化”功能推到极致,因此“十七年”电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再现。创作者把政策宣传放在重要的地位,周恩来总理重提“寓教于乐”,显得温和得多,这个主张其实是他一贯的看法,周恩来早年在一篇关于戏剧的文章中曾这样表述他的艺术观,寄希望于它“纵之影响后世,横之感化今人”。建国后,领导人认识到电影的娱乐功能,并不是对电影的功能有新的认识,也不是为了给电影“减压”,更不是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大方向唱反调,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寓教于乐”的观点反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政治,通过这方银幕影响和教育观众、改造世界才是终极目的。
(四)忽视影像的表现功能
在对叙事技法和具体影像表现手段的学习和应用时,中国影人的学习成果集中于对“影戏”传统中叙事方式的继承和改良上,而对电影修辞的理解还比较浅显,花费的精力不多,在影像的呈现上带有明显的舞台剧痕迹。比如,在场面调度时,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人物和摄影机调度的有机结合。但实际上运用得最多的是分切镜头加摇镜头,而移镜头以及其他运动镜头则凤毛麟角。如果一个场面中有两个或多个演员,导演就会把他们安排成程式化的“八”字形,构图刻板、机械,而机位就设在演员的正前方,摄影机像是被“钉”在地面上,人物缺少调度,摄影机完全没有得到解放,画面上就缺乏机动灵活的变化;构图上求完整,鲜有对画外空间的追求。摄影机的高度多与常人的视线相近,镜头的角度是平视居多,俯视和仰视的镜头很少见,出来的效果像舞台剧照一样单调,缺少镜头角度变化带来的视觉上的新鲜感;镜头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虽然也有一些变化,但老是缩手缩脚、中规中矩,缺乏镜头调度所特有的灵活性;除《小兵张嘎》《风暴》等少数影片外,表演与场面调度上多在横向上挪移,缺乏纵向调度的能力,使得呈现出的银幕效果多是二维的、平面的,缺少立体感;由于受“影戏”观念的影响太深,在镜头结构上多采用与舞台剧幕场结构相似的戏剧性段落场面作为基本叙事单元。
因此,当时的创作者在影像表现力的探索上,首先还是把精力放在破舞台习气上,以及如何妥帖地用影像反映叙事内容上,至于如何展现影像本身的表意性,则存在认识上的差距。
[1]侯曜.影戏剧本作法[C].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47-65.
[2]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J].明星,1935,(3):13-15.
[3]吴永刚.银海拾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2.
[4]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6.
[5]丁亚平.论20世纪中国电影与通俗文化传统[J].电影艺术,2003,(6):45-53.
[6]钟惦棐.为了前进[N].文汇报,1957-01-04(4).
[7]杜庆春.影在中国:中国电影回顾[EB/OL].(2006-03-12)[2010-11-10].http://www.ilf.cn/Mate/3503_5.html.
[8]罗艺军.中国电影理论文选[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22.
[9]段运冬.《木兰从军》:隐喻与想像交融的影像坐标[J].当代电影,2005,(3):59-61.
[10]郑正秋.自我导演以来[J].明星,1935,(4):11-16.
[11]杜庆春.无梦过百年:写给中国电影百年[EB/OL].(2005-10-30)[2010-11-20].http://www. zgyspp. com/Article/y5/y52/200510/13.html.
[12]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71.
[13]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5.
[14]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J].中国青年,1959,(5):30-33.
[15]茅盾.茅盾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68.
(责任编辑:魏 琼)
The Influence of the"Dramatic Film"Tradition on the"17 years"Film Narrative
LU Shao-y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lthough the"17 years"film(1949—1966)draws nourishment from the multifarious cultures of both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thus producing a phenomena that can be said to comprise multiple resources,the"dramatic film",as a concept of the film,gives a deep,extensive influence on the creation of the film in new China,which can not compare with other concepts of the film.The tradition of the"dramatic film"can be described as the follows:the story narrative is primary,and a great 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the contradictory confliction,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film,and to the auxiliary role of the image,all of which can be found a specific parallelism in the"17 years"film.While the"17 years"film has a little change in the aspect of detailed expressions,the main body comes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dramatic film".
the"17 years"film;the"dramatic film"tradition;narration;confliction
J902
A
1007-6522(2011)01-0027-09
2010-11-20
陆绍阳(1966-),男,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影视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