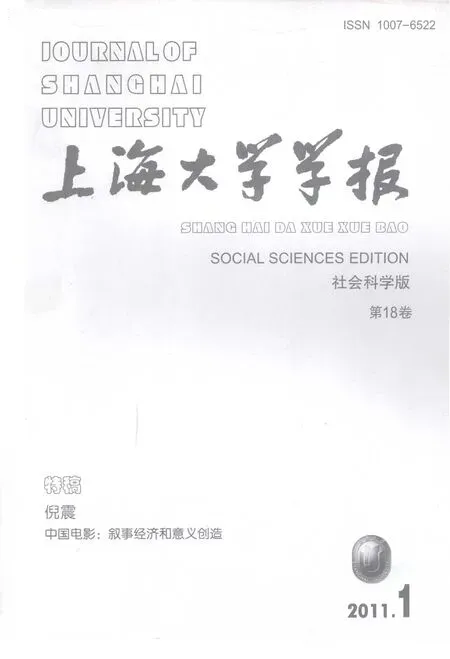“宗教生态”,还是“权力生态”——从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态论”思潮谈起
李向平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宗教生态”,还是“权力生态”
——从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态论”思潮谈起
李向平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社会实质,不仅仅是宗教生态问题,而是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其问题的深层,则是当代中国的权力生态问题,而非局限于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及其宗教信仰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生态、社会生态问题。就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来看,重祭“华夷之辩”的旗帜,急于引申华夏传统以建构正统的信仰方法,实际上是忽略了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之公共性与社会性。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要给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一个发展的空间,不如说,如果要解决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存在与发展的矛盾关系,关键在于开放宗教关系,还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实践自由,给宗教信仰一个公共实践、公开交往的社会空间。从当代中国宗教信仰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权力生态及其国家定义的信仰等社会学问题。
宗教生态;权力生态;社会结构;信仰关系;国家形态
目前中国宗教学术界流行的“宗教生态论”,表面上是基督教与正统信仰、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关系问题,但实质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教关系、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关系如何平衡的问题。其讨论对象并不局限于民间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合法性问题,其中某些论点的倾向甚至内涵有“华夷之辩”、“礼仪之争”的现代版本。因此,宗教生态论的社会学本质,源自于对当代中国宗教发展原因的解释,涉及当代中国信仰与宗教信仰的重大理论问题,值得关注和认真讨论。
因此,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动力?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较快的现象?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正统信仰或安身立命的价值底线究竟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会涉及到如何定义中国是传统国家还是现代国家的方法论,都将涉及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形态及其与宗教信仰的重大关系。
一、宗教生态论诸论点及其相关问题
所谓“宗教生态”,指的是社会中各种宗教的存在状况。在正常情况下,各种宗教之间应该是互相制约的、自由自发地达到一个彼此的平衡状态,即各类宗教各得其所,都有它们的市场,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但是,如果不适当地加以人为的干预,或者是因为政教关系的畸形发展,方才会破坏宗教信仰间的互动与平衡,造成有的宗教发展极其迅速,有些则凋零了,有的被压制了。
然而,如果把这些论点放在讨论中国宗教特别是中国基督教的发展问题中,就会呈现为一种“宗教生态失衡论”的思潮。其主要论点是,基督教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其他宗教信仰形式特别是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衰落或发展不足。
基于这种宗教生态关系的论述,一种普遍的意见是,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迅猛发展,其主要表现为1949年以来,政府对于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管理过严,甚至是大力铲除民间宗教,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政府防范基督教,没想到却让基督教发展了。
此类观念的始作俑者,乃香港基督教界的一位学人。该观点认为,基督教在文革之后的农村蓬勃增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立国之后,一直不遗余力地铲除民间宗教,将基督教在基层社会的农村中传播的最大障碍除去了,从而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此角度看,中共的宗教政策是协助基督教发展的一大助力。因为,民间宗教在农村遭到全面取缔后,妨碍民众接受基督教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均告去除,于是,农民便将自己的感情投向基督教,基督教成为了原有宗教的替代品。[1]12
不过,上述这一观念多年以来一直不太受关注,却在近年来成为学界议论的一个热点。①参看段琦:《宗教生态失衡是当今中国基督教发展快的主要原因》,载甘肃省委统战部《2008年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交流资料》(内部交流资料)。[2]230-264与此相应,宗教学界部分学者沿袭了这一分析路径。这些观点认为,既然基督教的发展是起因于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发展不足,这就说明了基督教的发展,十分不利于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至于有学人给政府建议,发展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以抵制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发展和渗透,以平衡或完善现有的宗教生态。其中,还有部分论点更有意思,他们主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宗教与信仰;中国社会经济落后的时候,信仰基督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而今中国发展了、强大了,自然就不应该再信基督教。这种说法,其要害是把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结合在一起,构成宗教民族主义倾向、汉民族信仰主义特征。其以汉民族认同的宗教信仰作为正当、正统的宗教信仰,否则就不是正当性的民族宗教信仰。
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关系,早在1990年代初就有学人指出,基督教的发展(尤其在农村的发展),“实际上是鬼神观念极普遍的中国老百姓在信仰对象上的一种转移或移情”。[3]因此,广大群众中普遍存在的鬼神观念是基督教发展的沃土。[4]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土教”实际上受的冲击超过“洋教”,特别是在人们心理上,对“土教”的排拒也超过了“洋教”。这种宗教生态的失衡,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5]6
很明显,现有的宗教生态说诸种论点,实质上是把一直存在着的“基督教是洋教”和“基督教非洋教”的对抗性认识再度激活了。这种认识,表面上是“既不能忽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的悠久传统,以及它与中华文化的核心基本价值的密切联系,更不能漠视文化全球化处境下各种外来宗教形态在中国的快速传递和冲击的现实”,而在内地里却内涵了一种对政府固有宗教政策的批评,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政治期待,希望国家权力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大力推动,希望“国家应该将‘宗教安全’纳入中远期的‘国家文化安全’规划中”,特别是“将宗教软实力(包括中国传统宗教文明的普世价值及时代特色)的有效展示和提升,纳入到国家文化战略安全体系当中,从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确保国家的战略安全”。[2]230-264
大致说来,宗教生态论代表性论点有:
(1)宗教生态失衡是基督教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或是根本原因。[6]具体而言,民间信仰的衰落才使基督教的发展成为可能;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关系成为反向关系。
(2)基督教在乡村社会的发展,挑战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破坏或颠覆了一向借民间信仰活动得以维系的社群关系。
(3)国家宗教战略出现偏差,导致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发展不足,基督教一教独大。因此,宗教生态论者大力呼吁国家调整宗教发展战略。
(4)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只能在传统宗教信仰之中才能找到。传统宗教、民间信仰是正统信仰,外来基督教并非正统,同时也是西方文化霸权、宗教殖民主义的象征。
实际上,“宗教生态失衡说”本来内涵了一种对政府固有宗教政策的批评,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政治期待,希望国家权力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大力推动,甚至把它们视为当代中国合法性的宗教信仰方式,以宗教信仰的民族性来满足宗教信仰的现代性;以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或本土民间宗教来抵制来自西方社会的外来宗教特别是基督宗教。加之,国家政府对于传统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暗中青睐,常常就会给当代中国人一种暗示:传统宗教更利于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此类论点的发展,自然会以宗教民族主义、汉民族信仰主义来建构当代中国宗教信仰结构,最后将走向另一种宗教生态关系的严重失衡。[7]
显然,这些宗教生态论者,往往还藏有一组潜在的话题:基督教的较快发展,应当引起当代中国人的忧虑;基督教与传统民间信仰对立;甚至暗示着——基督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或正统信仰。其中,最为严峻的观念是,当代中国基督教的较快发展,对中国国家社会构成了三大挑战。一是挑战了传统信仰的底线,二是挑战了意识形态的底线,三是挑战了社会控制的底线。由此观之,传统信仰与意识形态成为了社会控制的底线;什么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底线,不是传统信仰,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能够进行社会控制的、权力维稳的传统信仰与意识形态。这可能是宗教生态论的最大话语背景,最实在的真实内涵。
二、“宗教生态论”的严重失衡
“宗教生态论”提出了当代中国宗教与中国国家权力、社会建设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大多数论者的论述方向走偏了。真正失衡的不是宗教,而是国家权力及其对宗教信仰的控制方式,导致了宗教信仰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失衡。
大多数宗教生态论者有一个致命弱点,大多以乡村社会、民间底层为论述对象,集中于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发展却不仅仅是集中在乡村社会。这就是问题提出方式的偏颇。一个宗教的发展快慢,本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但宗教生态论者为什么单挑基督教?三十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很快,信徒与活动场所绝对多于基督教。一教独大的并非基督教,而是佛教。①依据北京零点公司2007年的全国问卷数据,佛教徒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是18%,为18500万人,而基督教徒所占比例2.5%,只有3300万人。至于民间信仰在城市中的存在,除了财神信仰和节日习俗信仰之外,几无更多的影响。所以基督教在城市中的发展几乎与民间信仰没有关系。至于传统佛教、道教与基督教的互动关系,均在政府的宗教管理架构中方才得以建构起来的。甚至可以说,基督教在城市中的发展,远远比不上佛教、道教那样的发展。佛教、道教能够做的公益事业,基督教常常无法去做。
基督教从进入中国始,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其中尤其是民间信仰对于基督教的渗透与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主要在广大的基层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中。各地城市中基督教的发展比较正常,所以这种影响并不多见。[8]50-55由此可见,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关系,主要是在乡村社会,而非城市。如此观察,基于为民间信仰立论的宗教生态观念,大多局限于中国乡村社会。这就限制了宗教生态论的论述空间。
其次,人们很难得出结论,基督教是在政府宗教政策的支持下而得以发展的,因为很难说传统宗教或传统信仰就没有政府的支持。就近年来的深度观察,基督教的发展,往往是在外在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才得以发展的,而非传统宗教那样,常常是在地方政府经营旅游经济、香火经济,以利益交换的情况下得以发展的。这就是说,当代中国宗教关系的开放或者封闭,不是传统或非传统的信仰特征所能够决定的。
因此,当代中国基督教较快发展,并非与政府的宗教政策直接相关。诚然,就当代中国宗教的管理特点,即集中于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方式来说,佛教信仰的社会发展反而不如基督教的信仰实践方式。基督教的信仰实践,可以不在教堂里面进行,而佛教的信仰活动往往要集中在寺庙或佛堂才能举行。它被局限于寺庙或佛堂之中。因此,这种“围墙式”的管理方法或“空间化”的管理方式,对于寺庙佛教的发展更有具体效果。但这是当代佛教发展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同时,这一问题恰好是佛教信仰之制度性不强所造成的,此与基督教内向认同的团契风格及其封闭性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佛教与道教、民间宗教一样,能够有所参与,能够发挥功能,所以在地方权力主持的各种经济活动之中,地方政治精英往往很喜欢参与佛教协会类等各种组织,参与各种佛教经济活动的规划与进行。至于宗教活动与宗教活动场所中的“三定”:定人、定点、定时,进行各种宗教仪式活动的时候,主要就是针对基督教等制度性较强的宗教而设计的制度安排。但相当于佛教、道教及民间宗教而言,好像就没有类似的要求和制约。从此层面而言,佛教是最能从中受益的宗教。[9]
以佛教为例,佛教与基督教在交往关系层面上的差异,利益交换的可能性不同,从而构成了作为宗教团体在维护各自宗教质量上的关系结构。而基督教常有的小组聚会、教会信仰及其人际互动方式,虽然其目的是在于建构一种社区型教会或地方性教会,但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参与者及其社会关系的弱小,不得不构成了社会交往关系的相对封闭。而这种封闭性宗教团体特征,又使得基督教在相对性自我封闭的情况下,使其内部的信仰认同关系更为紧密、牢固,能够承担外在的压力——甚至是外在压力越大,其内部的信仰认同就越稳定,从而以信徒抱团的形式在体制之外继续发展。如此看来,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并非是与传统宗教、传统信仰的矛盾关系所造成的,其中有着更加深层的社会、政治原因。①其实,让官方不满的不只是基督教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合,常要脱离他们的领导。更实际的是,集会频繁,影响工作、劳动生产。冉云飞:《1957年的一则基督教史料》,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70812849.html。史料说明的是1957年的情况,但历史最能说明问题。当代基督教的问题,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权力顾虑在内?而佛教与社会间的利益交往关系,则使佛教信仰者内部的信仰认同更加开放,同时也更有扩散性特征。
实际上,此乃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宗教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利益功能、政府利益与宗教利益之间实行相对交换的结果。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最近参与地方政府一个宗教服务与法制建设的课题。在该课题的开题研讨会上,地方政府负责宗教工作的领导介绍该地方各宗教及其社会服务多项业绩的时候,他对于佛教的社会公益事业,包括捐款有多少,做了多少好事等,一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其介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社会服务情况的时候,则话锋一转,说基督教是个外来的宗教,虽然也捐钱去救灾服务,但是就弄不懂,怎么也会有人去信这个宗教。
在权力—信仰之生态关系如此失衡的前提下,中国宗教关系无疑也会呈现一种特别复杂的互动局面。比如,活跃在宗教管理体制外的佛教发展现象,为什么就很少被人提及?政府造寺庙、和尚被招聘、经济利益再分红的现象,为什么就没有使用“地下佛教”或“非法佛教”的概念来进行批评?一方面,这是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依旧是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一厢情愿,在东南沿海地区自造寺庙,发展地方旅游经济及地方佛教势力,以抵制基督教在当地的发展。这种佛教发展方式,无形中就经由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合作,建构了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合法性。
很明显,这是权力经济与正统信仰的整合模式。如果这种整合恰好是地方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宗教精英的结合,那么,这就正好证实了一种特别值得忧虑的现象:权贵资本与传统信仰之间所可能具有的某种整合及其相互利用。权贵资本的财富经营,经过传统信仰的神圣性符号和神圣性证明,似能给中国人表态,权贵尽管权贵,但还具有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以获取民心国情;权贵既是权贵,但这是中国特色、具有中国信仰传统的权贵。此当为中国政教关系常常失衡的最要紧之处。
汉民族信仰主义+宗教民粹主义,乃传统信仰“华夷之辩”的现代版本。对于其地位和功能的讨论的确应该引起极大的注意。其中还有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民族信仰、文化信仰以及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此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影响中国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涉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现代社会中,公平、公正、和谐、正义才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底线。所以,不是单纯的信仰,不是正统的宗教,即能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根基的。我们关心宗教与信仰的认同与实践,我们更关注我们的社会及其交往互动是否公开、公正、可信、可爱。不同信仰共同体的信仰及其认同方式,其中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价值内涵,但无疑要从中衍生出一个社会共同体公共的价值内涵,方才是一个社会的信仰及其认同。一个乡村信仰、一个地域的神灵,诚然可以具有地域信仰、乡村信仰的价值认同意义,但它们与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一样,唯有其中蕴含的公共意义或公共信仰方式,才是所有中国人的信仰内容。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才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中国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
所以,不是宗教生态的失衡才会造成基督教的发展;而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才构成了基督教的一定发展。正是因为乡村社会底层人际交往关系的失衡、失序诸现象,人们急需精神团契和社会交往,才使具有精神团契和信仰共同体等社会交往特点的基督教得以发展较快。在一个秩序真空的环境之中,制度性强的宗教信仰体系,会很快适应和满足社会的信仰需求。这本不是什么坏事情。信仰关系之间的竞争,本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不是宗教生态的原因,而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这才是基督教得以较快发展的缘故。
因此,宗教生态平衡有几大指标。第一,各个宗教与社会环境有良好的关系;各宗教之间能够和平共处。第二,各个宗教在时间、空间上是有序而稳定的活动与发展。第三,宗教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和自由调节功能能够正常发挥。如果只认为中国宗教生态失衡促成了中国基督教的较快发展,此论很难成立。当代佛教发展也很快,为什么就不是宗教生态发展失衡的结果呢?实际上,当代中国宗教生态关系如果有一定失衡的话,它肯定是在于宗教和它的社会环境关系间的失衡。就此而言,基督教方面的社会压力较大;而其他某些宗教则与政界、商界的合作关系过于紧密;而社会环境对五大宗教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于传统宗教宽容得多,而对于基督教、天主教则相对而言要严紧得多。[10]
如借助于国家公共权力,以宗教信仰平衡宗教信仰关系,无疑会建构新的不平衡。宗教信仰间的关系,只能在宗教信仰体系与公民社会的互动中去寻找、去建构。它们将依赖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权力独大,社会缺席,宗教信仰关系如何得以平衡?!依靠一些宗教信仰来维护宗教信仰关系间的平衡,这无疑是缘木求鱼,宗教信仰之间良性的竞争关系如何得以构成?!宗教信仰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在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之中,既是互动交往的关系,同时也是彼此间的良性竞争关系。它们不是谁来维护谁的问题。谁来维护?谁来做主?有主有从,有维护者与被维护者,这种关系很难平衡。
实际上,社会、宗教、文化与信仰的多元发展,宗教生态的真正平衡,关键在于权力生态的平衡,政教关系的平衡,社会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平衡。需要调整的,不是“宗教文化战略”,而是国家权力、社会信仰结构及宗教信仰在社会中的实践关系与运作机制。宗教生态论的似是而非,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些问题是:(1)把共同体与非共同体的信仰方式,以排他性与本土性的概念来对待。(2)把社会结构上的开放或封闭的问题,转换为片面、单一的信仰关系。(3)以宗教信仰问题替代了国家权力、社会变迁问题。(4)把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单纯定义在本土而传统的宗教信仰之中,以传统国家意识替代了现代公民的国家意识。
这种试图用信仰关系来定义国家形态、证明权力合法性的想像力,用涂尔干的话来说,真正的争论是他们对神圣的概念认知不同。涂尔干认为,神圣不只体现在神的或超自然的存在之中,凡是“引起注意的”或是“崇高的”,都是神圣的。要了解每个道德社群的宗教本质,就要了解他们热爱的来源与热情的泉源。涂尔干指出,事实是各社群不会也不愿任由神圣被亵渎。问题就在这里,不仅文化分裂双方对神圣的概念相异,单是一方的存在,就是对另一方的亵渎。[11]147
三、民间宗教—信仰的合法性问题
宗教生态论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宗教信仰关系的要求,这就是为传统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直接张本,争取在当代中国五大宗教之外的合法性发展空间。此论本来没有问题。然而,鉴于目前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不足,有些学者的主要论点则认为中国宗教的制度安排基于来自西方的宗教定义,排斥了类似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这样的分散性宗教,从而造成宗教生态关系的失衡,[5]6进而把批评的方向指向了制度宗教,而不是宗教制度。
源自西方的宗教定义,无疑会偏重于制度宗教,但当代中国的宗教管理,却是以宗教场所的管理作为基本方法的,而非以宗教信仰的制度化形式。出自于这种场所的管理方式,配合以“三定”即定时、定点、定人的管理理念,以及把宗教信仰空间化,再加上合法与非法的宗教活动概念,及其对宗教信仰结社的意识形态恐惧,恰好与来自西方的制度化宗教定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中国五大宗教均须出自于这种由“宗教制度”转换为“空间化”的管理模式,所有的宗教信仰活动,必须局限在正常的合法性活动场所,这些宗教信仰才能具有合法性,概莫能外。“宗教制度”被建构为“宗教空间”。[12]宗教活动空间成为了宗教信仰合法性的象征与符号。因此,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理所当然也无法出离这一空间化的合法性框架。
在此管理模式之中,宗教信仰及其社会实践往往被局限于场所、空间的“围墙式”管理原则之中,而非宗教信仰的社会性制度实践的结果。如果是制度性的信仰实践方式,任何宗教信仰、包括民间信仰都会使自己的信仰体系社团化、制度化,即便是扩散性的民间信仰,也能够从中获得制度化的实践空间,或许也能够以社团化、村社化的实践形式获得其合法性。宗教制度化,乃信仰共同体的制度建构,信仰结社的合法性。所以,如果说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平衡现象,恰好也是宗教信仰的认同与实践的制度化不强所造成的。而排斥扩散性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恰好也不是制度宗教,而是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对于宗教信仰的垄断性定义方式所决定的。这说明,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发展现状与基督教并非直接的反向关系。可见,许多宗教生态论者,实如关公战秦琼,不得要领。
宗教生态论者的主要论点是,政府以“迷信”的政策对待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使基督教得以大肆发展,从而提出政府要开放、认可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以抵制基督教以及西方文化霸权的发展。[13]1
实际上,此类政策及其意识形态话语的偏向强化,不仅是对民间宗教信仰的压制,几乎对所有宗教都异曲同工,无法出离其外。比如对基督教,同样也使用迷信的符号进行意识形态控制,认为基督教传布迷信思想。[14]似乎不存在因为“迷信”的概念,基督教能够超越其外而自由发展的。因为迷信不是宗教,亦非信仰的术语,而是一个权力的符号。
“迷信”一词,在19世纪末,经日语转译进入中国本土语汇,并成为早期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之一。迷信与知识进步、专制主义以及国民道德的关系是初期“反迷信”知识氛围的主体内容。所以,“迷信”是一个权力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形式,而非宗教学术语,在其诞生之初并不具有统一的内涵,其不同的概念和指向,恰恰构成了现代中国人对面临的政治、文化冲突的反省。而有关迷信的论述,却能从中窥探出现代民族国家被建构的复杂过程。[15]
宗教学意义上的迷信如同民间信仰,即非制度宗教的信仰方式与实践;扩散式的民间信仰主要是关注直接的、细小的问题以及特殊的现存个案和个人的问题,而宗教信仰体系则能够覆盖更长的时间跨度,涉及更一般领域的精神问题,因为它处理的是普遍性价值认同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层面所强调的所谓迷信,乃与国家权力认可的正常信仰(正信)与非合法的信仰方式(淫祀)相比较而言的,是与正统信仰相对立的价值体系,从而才有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坚决取缔“封建迷信”的管理模式。很明显,宗教与迷信的关系,不是宗教信仰体系与民间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而是国家权力、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为此,宗教生态论强调的仅仅是宗教学意义上的迷信及其话语表达结构对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制约功能,而忽略了后一种迷信话语的控制功能。
即便如此,国家权力、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地方政府与民间宗教信仰的关系历来就非常复杂。自古迄今,民间信仰的传统实践方式大多依附于现实社会、世俗权力关系,民间宗教信仰从来就不是国家权力的一块“飞地”,地方宗族、官府、信众、行会、士绅等多个利益集团及其关系,在这一领域中交织着。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权力话语,从而可以视为从民间信仰理解中国社会权力运作的学术进路。因为,民间信仰中庙宇的重建、庙会的举行,几乎处处体现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利益的共谋与协商。这一问题,根本就不限于当代,因为,自古以来的民间信仰就一直在寻求国家意识形态的承认。[16]161-180
但是,民间信仰对于合法性的要求,也内涵有一种宗教自由的诉求。就此方面而言,争取民间信仰的合法性及其发展无疑是有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它能通过祛迷信化而产生去意识形态化的某种现代功能。
然而,民间信仰在祛迷信化而争取获得制度宗教发展空间的同时,却又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权力化、利益化了。它们在面对迷信化、宗教化的矛盾的同时,却又同时进行国家化的权力诉求。在此背景之下,原来局限于局部和零星的民间信仰活动,牵涉了国家、社会制度、交通、商业、地域文化等问题。以申请“非遗”的文化身份来表达民间信仰,而民间庙宇甚至可以绕开宗教管理机构,直接挂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所以,民间信仰与国家意识形态更趋和谐。[16]161-180为此,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的发展,似乎不存在什么合法性问题了。
那么,民间信仰合法性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现行宗教制度的管理方法,表面上是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合法性的障碍,但新兴宗教、民间宗教的概念一直不为中国宗教管理原则所采纳。这不是五大宗教或基督教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关系,而是国家权力如何面对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政教关系问题。可是,民间信仰的合法性关系,甚至成为国家权力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共谋结构了。它不似宗教,却胜似宗教。由此观之,除了国家权力之外,当代中国社会之中,并没有任何其他宗教的发展能够在制度层面上制约民间信仰的合法性、制约民间宗教的发展。
另一方面,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的发展,其间还有深厚的实际利益包含其中。由此不得不使人怀疑,在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的发展过程之中,人们追求的是信仰的合法性,还是实际利益的合法性?
实际上,学术界在最初提出有关“宗教生态失衡”的论点时,其中一些论述却是被现在的宗教生态论者所忽略。这就是说,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单性群体,其社会结构对宗教的延续与拓展非常有利。[1]229正是那种制度性较强的基督教,对于中国农村这种同质群体原则的作用比较明显。这一特点,其他学人也有相近的发现。因为,近些年来,农村地区的宗教热除了因为其人际传播的特殊方式之外,亦与其它教派的退守相关,再加上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非充分性、村庄社会保障机制的残缺性,以及许多地区农耕方式的脆弱性和别有用心者的逐利性,地下非正式宗教团体在许多农村地区的乘虚而入不可避免。[17]
在一个传统社会关系占据整个社会结构核心的时候,人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或行动空间时,往往是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群体为单位行动的。因此,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中,宗教信仰的行动者往往就会是个人,而不是信仰群体。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信仰群体能够表达所在地区人们的利益和社会要求的话,那么,这一信仰群体就会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近期在网上看到一则资料,说安徽省太和县李兴镇程寨村一位85岁的老人,在儿子今年1月死后,无人照料,被活活饿死在自己栖身的废墟里。面对村民们对村干部不履行救助责任的指责,村干部的回答是:“谁让他没有儿子。”
此则信息,读来使人不寒而栗。这就是民间中国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之一。底层空虚,关系沦陷。这是明明白白的社会结构问题,而非宗教信仰问题。如果乡村生活多一些有信仰的共同体支持和社会互助团体,人们可以相信,这个老人无疑会获得来自信仰共同体之救助的。无论是哪一种宗教信仰,都将会为他们的精神与生命带来关怀。
对此,即便是代表了当代中国“非基思潮”的一份研究,也表明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社会的结构性紧张,是基督教在乡村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因。该报告认为,“在整个农村社会各个方面的大转型、大变革中,社会结构的转换和重新调整是基础性的变量,而社会结构中家庭结构和村庄阶层结构的转变和重组又是最为基础的。在转变过程中,某些人群或阶层会从较高的位置上摔下来,掉入低层,失去了原来的权力、荣耀和面子,无疑他们会不甘心失势,会进行反扑,企图维持其原来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而新的阶层和人群则要巩固自己的位置,从而造成新旧阶层和人群的对立,构成结构性的紧张。要达到社会结构的重新稳固,就必须对社会结构进行重组,消除失势的低层人群、阶层的反抗心理,固化社会结构。在此背景中,基督教趁势进来,扮演着固化社会结构镇静剂的角色。基督教在两个方面起到了固化社会结构的作用,一是为低层人群和阶层提供一整套对当前状态安之若素的说法,使他们放弃反抗的念头,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他们地位和角色的安排,承认当前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合理性;二是提供一套新的关系网络、评价机制和行为模式,给人们一种全新的实践和盼头,从而使人们退出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性竞争,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不争与不吭,在当前社会结构中无所作为就是对它的承认与合作”。[13]1
因此,表面上的宗教生态现象,实质上却是社会生态、社会结构的稳定问题。可以想像,在一个社会责任无人担当的社会底层,信仰共同体的组织互助是多么的重要和必须!何必去分别那种无聊的华夷之辩,正统与非正统。几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社会缺席,宗教安在?》,时人不解其意。如前正好呈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当代中国民间乡村社会结构的散乱,宗教存在和信仰表达的社会空间混乱不堪,才出现了如此所谓的宗教生态现象。如果社会归位,宗教自然安定,各种信仰就能彼此尊重,理性互动,关怀人群。
不可否认,民族民间的宗教信仰是当代中国多元民族文化、多元宗教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宗教生态的平衡,关键就在于民间信仰的正当维护吗?如果民间信仰发展了,基督教就不发展了;而基督教不发展了,宗教生态的失衡问题就能够解决吗?基督教在农村较快发展的原因,不仅仅是宗教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所谓宗教生态的问题多发生在农村,而非城市之中?为什么基督教在乡村的发展,大多能够替代底层社会秩序,能够填补乡村居民日常生活、公共交往乃至利益表达等方面的功能?
在此方面,应该强调的是,信仰与“宗教并不是个人与超自然力的任意关联,而是一个团体的所有成员与一种力量的关联,这种力量从最深处有利于该团体,它保护该团体的法律与道德秩序”。[18]于是,就其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理论关怀而言,中国人当下的信仰自觉或宗教自觉,应该包括对信仰的社会实践方式的自觉,包含有对宗教认同社会建构的自觉。其要点不在制度宗教及其迷信的界定方法,而是乡村、地域的信仰与公共、社群或社团的信仰方式及其与现代社会公共理性的互动交往。倘若宗教不开放,信仰限于私人利益,即便乡村有信仰,其实践关系也必然会失衡。
因此,民间信仰局限于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局限,当然也是目前宗教生态论者以民间信仰立论的一个局限。它说明了传统信仰需要一个社会化和社团化的过程。开放社团比宗教自由更加重要。民间信仰的社团化或社会化的发展形式才是民间宗教发展的正常路径与关键问题。如果一味地从政府利益和国家权力之中寻求信仰的合法性基础,这始终不会是值得肯定的发展模式。如果采用“荆轲刺孔”的方法,为了吸引国家权力的兴趣,必欲建立、针对一个信仰的对手,在对抗基督教的立场上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及其合法性基础,这就更不是信仰与宗教的生态问题了,而是宗教信仰的政治学问题了。
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合法性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宗教制度的相关设置及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制约,难以归咎于制度宗教在当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因为许多民间信仰的仪式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单元,于是在宗教上也就保留了传统的活力。但经由近年来的城镇化,家庭在承担民间信仰的表达功能方面却大大减弱了。同时,也因为现代化教育的作用及其影响,尤其是对扩散性的宗教,会使得教义不成完整体系的民间信仰产生负面的冲击,促成民间信仰者的大量减少。[19]虽然民间信仰依然为台湾地区大部分居民所信奉,但此论乃能说明现代社会中民间信仰的衰落,并非基督教的发展直接造成的。这对于一些好以台湾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关系作比较的宗教生态论者,是值得去认真思考。
值得指出的是,基督教与民间信仰也并非处于对立、对抗的关系之中。中国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一方面继续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得不与迅速复苏的民间信仰争夺信众。这种事实说明,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现象的存在,是今天中国农村的现实和广大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所决定的,它的存在顺应了中国特定的历史与环境,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换言之,这也许是中国农村基督教发展中的必然过程。[8]50-55
可以认为,当代中国宗教信仰的变迁与发展,不仅仅是宗教信仰关系的变迁与发展。宗教信仰关系的变迁与发展,首先需要改革和变化的是权力结构与社会结构,需要政教关系的与时俱进。所以,宗教生态关系的优化,绝不能把问题局限于宗教信仰层面。其要害是权力生态,而非单纯的宗教信仰关系及其表达问题。
四、信仰与权力,谁的毛病?
宗教的本质不仅是信仰上帝而已,它还是一种“基本的关怀”,存在于个人生活的内心深处,是大家认真看待的问题。总之,宗教可以定义为“建立在权力、人、信心之上的所有的信念”。[11]282于是,国家权力与宗教信仰,均可被视为一种合理性的象征,而在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竞争关系,其目的也就是要“独占合理性的象征”。[11]168这说明,权力与信仰始终具有不解之缘,而权力却也可能被视为“人类行动的一种转换能力”。[20]在合理性象征关系的争夺之中,权力关系有可能去支配或应用于当代社会中主要的宗教信仰类型。这就使我们在讨论宗教信仰或民间信仰的合法性问题之时,有必要梳理权力关系与信仰类型的互动关系。
无论是民间信仰,还是其他宗教信仰,它们要回答与面对的问题,无疑还是两个经典性的社会理论命题:一个是社会秩序是如何构成的?另一个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把握了这两大命题,实际上就能够呈现一种超越所有宗教信仰关系的学术立场。因此,与其以民间信仰、传统信仰、外来宗教来对其问题进行分别与处理,还不如仔细梳理不同信仰表达与宗教实践中,能否承担上述两大社会理论命题的解读功能。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关系,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构建过程。这种宗教信仰关系,大多是国家强力干预且被国家认定或对国家的自我认同。它们表明了国家规定的宗教信仰及其宗教信仰上面的分类。而在此分类关系之后,却是一整套知识体系,其后有国家规定的内容,你的信仰是什么、谁隶属于哪个宗教?这就是说,中国人的信仰与宗教,好像很自由,但在其后又蕴涵有一套国家话语或知识体系,使中国人都在沿袭着这一套信仰体系及其建构的逻辑,在信仰、在选择、在困惑。应当指出的是,这套神圣的符号系统,自上而下,而不是仅仅每个信仰者的自身表达。与此相关,信仰关系的建构与表达,常常就是一种国家权力或精英主义的构建。
此前各地方政府都在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且通过“非遗”的申请与保护互动,绕开了宗教信仰的相关管理制度,使其在宗教管理的体制之外,各地民间信仰、民间宗教获取了政府认可的合法性。其与固有体制中的宗教信仰比较而言,它们的空间更大,功能更强,不似宗教,胜似宗教;不似信仰,却强似信仰。这就是以宗教信仰之功能建构起来的权力—经济合法性结构。而在相应的学术领域,亦蔚然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一股政治与宗教的文化思潮。
由此可见,公共权力、经济发展、民间信仰,大致已整合为一种以宗教信仰加上经济发展的国家想像,从而构成了一套新型的知识信仰再生产体系。如同已有的研究展示的那样,当国家以民族成份作为政治身份时,民间的文化制度会对这个族群身份进行更深一步的识别。因为中国社会中的民族身份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不仅包含了正式的、政府规定的身份系统,也包含了许多民间的创造。[21]而当国家以民族信仰视为权力表达关系的时候,民间的信仰关系就会对这一民族国家进行更深一步的识别与合法性证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中的民族身份及其信仰关系,实乃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它不仅包含了国家权力规定的民族身份信仰系统,同时也包含了许多民族民间的信仰创造。既有自下而上的许多民间社会的自我创造,同时也有自上而下的来自国家权力的话语表达。
在《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沃尔德曾对中国城市单位中的某种庇护主义关系进行过富有理解力的分析。而奥伊在《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一书中也对中国农村中存在的这种庇护主义关系进行过分析。
按照沃尔德的看法,那种存在于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之间的庇护主义关系并不是纯粹的“非正式组织”或“个人性”的关系网络。相反,它是不能离开正式组织而独立存在的,这种关系是受到官方支持的,是其组织角色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关系,过去人们往往从领导方法的角度加以分析,但同时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是一种包含着社会结构核心要素的稳定关系。无论是在物质的层面上,还是在精神的层面上,这种关系都有极深的社会含义。正是这种关系网络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它是当时那种社会能够正常运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机制。这种庇护主义关系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将公共的因素与私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22][23]
以此方法分析现有的民间信仰通过地方政府申请打造“非遗”项目、以及参与地方旅游经济的实际行动,我们不难发现,地方信仰与民间宗教在此类“非遗”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是将对一种地方政府组织及其意识形态的公共效忠与对领导者个人的私人效忠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这无疑就构成了一种“信仰型庇护主义”或“依附型信仰关系”及其实践方式。既在公共领域中表达,同时也是私人利益的要求,更体现了一种公私领域彼此结合的权力—信仰生态结构。更准确地说,此乃公私领域之间、宗教信仰领域与地方政府权力界限不清的合作结果。
由于这种“信仰型庇护主义”或“依附型信仰关系”自然呈现了所谓宗教生态严重失衡的现状。它们已经是地方政府权力发展经济利益之要求、公共信仰群体与私人信仰各个层面的多层矛盾。在此基础之上,各种利益、社会关系、民间信仰、地方关系的整合,构成了这种不似宗教、胜似宗教的权力—信仰庇护结构,进而在庇护之中孕育了矛盾。
无独有偶,在乡村政权研究的相关论著之中,同样也发现了这种作为公共关系变体的新庇护关系,即使用个人关系的理念——亲疏或内外——来建造公共关系的权力模式。由此而通行的行为规则,不是对等、独立、价值导向和普遍主义,而是远近区分、依赖、利益导向和特殊主义。[24]于是乎,在民间信仰通过地方“非遗”项目的申请及其建设之中,个人关系、宗教信仰事务与公共权力、地方利益,都能得到应有的整合与表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关系,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是地方权力及其利益而复兴、重建的民间信仰,的确发挥了地方利益与地方文化认同的整合功能。但这种基于地方利益与政府权力认同的信仰复兴方式本身就是非信仰的。它们要求的不仅是信仰,更是权力与利益关系。正是因为这种权力与利益关系,它们与国家利益及其地方政府权力本身就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与互惠功能。它们所整合、建构的,必定是一种独特的“信仰庇护关系”,甚至是一种“依附型信仰关系”,而非现代社会宪政中的政教关系、权力与信仰关系。与其说是信仰关系,不如说是对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高度认同,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利益关系庇护下的另一种信仰方式。
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关系与国家权力关系,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新宗教传统基础上的信仰庇护关系。信仰“关系”成为在神圣资源的再分配权力体制中,不同的信仰者争取自己信仰及其利益的一种行动策略。表面上,这是定义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理论方法,本质上却是混淆了对于宗教信仰与公共权力的定义规则。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地方乡村社会中已有不少从“迷信”到“宗教”、从“民间宗教”到“佛教道教”的社会事实。它们的确是在说明当代中国信仰与权力的一种同构与合谋的复杂关系,也同时呈现了一种宗教信仰与国家权力间的各种变迁倾向。其中,既有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迷信与宗教的关系;迷信或宗教的定义方式及其与地方党政的关系;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与传统信仰的复兴诸种关系。
地方社会的民间信仰活动,本可为一种反对国家权力垄断的表达形式,同时也可视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形式。它们是一个既能与权力合作,亦能批判权力不公的乡村“公共领域”。然而,民间经验告诉人们,尽管是地方宗教与民间迷信活动,它们一旦被置于地方政府的领导之下,并且能够为地方旅游经济服务,这种“挣钱”新伦理就能够实现从“迷信”到“宗教”、从“封建文化”到“民俗文化”的合法性转换,呈现一个合法身份的华丽转身。因此,封建与民间、迷信与宗教之间的分类与冲突,地方信仰试图重建权威、声明其地方身份以反对国家文化界定的努力,大多能够被消除、减弱,最后转换为与地方政府、权力经济的合作。[25]
地方政府权力由此具有了一种合法性转换能力,而民间信仰也因此获得了转换的合法性可能与发展的空间。信仰与权力的合作,甚至会使权力成为被信仰的社会关系之一。然而,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疑惑是:为什么伴随着近年来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的大量复兴与发展,依旧会出现以基督教作为对立面的不同论述?其中是否内涵有提倡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主观情愿,作为复兴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的一种行动策略,以再次争取国家权力、经济发展的认可与合作、挤入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的正当性过程之中?倘若如此,这就已经超出了宗教信仰的范围,已被建构为民间宗教信仰的国家想象力了,想象由国家权力与民间宗教及其信仰的再度合作与意义共享。
在此基础之上,其“信仰自觉”很可能就成为国家权力的自由恣肆,而民间、乡村、老百姓似乎会再度“被信仰”,排斥在国家权力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之外,难在社会底层而获自觉,更难有神圣的关怀。
五、权力—信仰关系的现代性要求
被信仰的权力关系,在定义宗教信仰及其民族国家的想像力层面,举足轻重。一旦权力形态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组织、信仰类型也都会发生变化。
按照马歇尔·福柯的论述,权力关系分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权力存在于关系之中,存在于任何的差异性关系之中。“权力关系普遍存在于人类关系之中。这并不是说政治权力无处不在,而是说,在人类关系中存在一个权力关系领域,它会在个人之间、家庭之中、教育关系之中以及政治生活领域中发挥作用。”“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努力去控制他人的行为。”[26]
所以,权力不仅仅是国家主权形式、法律形式或统治的统一性。这些大多是权力的最终形式。权力应当是众多的力的关系,这些关系存在于它们发生作用的那个领域。权力的实施乃是通过无数的点、通过不均等的、运动的力的关系的变化而得到实现的。[27]在此类差异关系之中,福柯界定了个体化权力与总体化权力。个体化权力即牧师权力,总体化权力即是国家权力。福柯的“牧人—羊群游戏”或“城邦—公民游戏”,也大致体现了这两种权力关系。前者更多地与信仰、宗教与伦理相关,后者更多地与理性、科学、法律相关。前者是拯救性的,个体化的,其目的是要保证个体得救;后者是总体性的、压抑性的,其目的只要别人为他献身。
福柯说的这两种权力,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形态之中,存有不同的表达形式。依据福柯的权力观,我们就能够看到,现代国家是如何整合了这两种权力,特别是整合了牧师权力——个体化的权力,使之进入总体化的权力结构之中。诚然,福柯所论述的权力关系,在当代中国宗教信仰中的具体渗透,却有很多不同。中国传统的“人王兼教主”的信仰方式和权力运作方式,早已把羊群的游戏与臣民的游戏整合为一体。因为中国有没有公民或公民社会,尚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为此,总体化权力与个人化权力是合二为一的,同时也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信仰关系及其控制方式,实际上就成为了总体化权力行使及其对宗教信仰进行控制的权力技术。
这就是一种特殊的现代权力—信仰模式。其行动策略就如杨美惠教授所论,它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训戒的技巧,或者说是一种权力技术,它把人们安置在一个空间里,促使或限制他们的运动和活动,以及他们的发展和再生产;二是规范化的技巧,即通过构造一种单方面的关于正确与错误的话语,通过依据一种统一的、而又是普遍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和调节人们的行为,通过以这种特定的话语为基础,以界定人们的身份和位置并行使他们的权力。[28]
承受着这种权力—信仰结构的制约与影响,中国宗教信仰之基本关系,同样也存在着与此相应的两种宗教信仰的国家想像力。一个是自上而下由国家规训所规定并控制,另外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民间信仰策略。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各自都依据自己的信仰特征,来建构不同的实践路径和行动策略,进而在不同的方向上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信仰方式。然而,它们均为不完整的信仰体系,隔离了社会、公民社会所建构的制度空间及其信仰实践方式。国家建构的信仰体系,需要民主化的实践方式;民间信仰的行动体系,需要社会化的团体表达方式。它们都与福柯讲的两种权力极为近似。
所以,应当摆脱国家权力与宗教信仰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及其与国家权力间的交往互动,更应该通过信仰类型和宗教信仰关系的研究,最终建立一种新的权力治理模式和新型的宗教信仰模式。
显然,当代中国社会之中,国家信仰、民间信仰,宗教信仰,不一而足。当然,我们也应当明确,国家权力可以分为传统与现代两大形态,而信仰关系也同样能够分出两大形态。至于民族信仰主义,在本质上提供一种归属感,即归属于具有某种共同文化特征的共同体的感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许多民族国家甚至扭曲历史,使用国家的力量创造出某种虚拟的历史。[29]而近乎为神圣的民族国家,特别擅长“发明传统”,当然也特别爱好复兴传统信仰。在这里,“传统”总是包含了特定的内容:表现为特定类型的信仰与实践,深深嵌入在“由来已久”的合法性之中。[20]164不过,依照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传统的信仰关系,往往以个人关系为中心,具有工具性、非正式制度性、特殊主义的、私下的、等级式的、忠诚于个人等特征,意味着涂尔干提出的“机械团结”;而现代信仰关系,则以非个人关系为中心,具有价值型、正式制度化、普遍主义的、公开的、职位分工式的、忠诚于法律等特征,建构为涂尔干提出的社会“有机团结”。
问题在于,今日我们所讨论的民间信仰,究竟是公民信仰方式,还是传统信仰方式?而民间信仰如宗教生态论者多强调的那样,其所希望的国家权力及其对民间信仰的青睐,究竟是传统国家及其信仰方式,还是现代国家权力及其信仰的期待。
中国人现在所缺失的,不仅仅是信仰,更不是那种所谓中国人的本土信仰或外来信仰,而是那种能够与现代国家意识与现代公民意识紧密契合的公民信仰。无论哪种信仰,能够于此契合者,必然复兴发展;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就此而言,宗教生态论的真正价值,应该是通过具体而真实的宗教信仰关系的梳理,使当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能够从国家与国家权力相关联的信仰类型中解放出来,进而能够建构一种新的信仰类型。如果要说真正的“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一方面,是“要恢复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宗教生态”;另一方面,则是“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包括各种健康的宗教文化,使之各得其所”。[30]其中,这个新的历史条件,我体会就是民主的、现代的国家形态及其权力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合法性关系建构,以及各得其所、良性互动、社会交往的宗教信仰关系。
梁漱溟曾经指出,现在的读书人,以为社会像一团面粉,“染苍则苍,着黄则黄”,这个书本上比较容易,而要在实践层面让中国社会真的能朝理论设想的方向演变,才是百年大计。……究极而言,人是不可信的,指望人去做好事,是在希望没指望的事。[31]
梁漱溟说的人是不可信的,犹如权力—信仰关系也不可信。这就是说,宗教及其信仰不是灵丹妙药,无法包医百病。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也不会完全依靠宗教信仰而得以治理。宗教信仰如何进入公民社会,把宗教信仰建构为公民社会的公共宗教与公民信仰,这才是解决宗教生态问题的基本方法。在政教关系法制化的问题没能最后解决之前,宗教信仰都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宗教信仰如果始终停留在国家权力的监控与控制的领域之中,无论任何信仰、任何宗教,都无法真正解决宗教与信仰的生态关系难题。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中国宗教信仰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去改变人们的信仰,也不在于去区分何为正祀、正统的宗教信仰,何为非正宗的外来宗教信仰。最要紧的,是在于如何去改变中国人固有的信仰条件、宗教实践的规则以及信仰与社会认同的权力关系。一句话说来,宗教及其信仰的真正自由,根本在于宗教与信仰条件的社会化与民主化。
[1]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M].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12.
[2]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赣、湘、云三省基督教现状调查报告[C]//金泽,邱永辉.中国宗教报告(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30-264.
[3]汪维藩.谈基督教的现状问题[EB/OL].(2008-10-17)[2010-08-14].http://wangweifan.bokee.com/6821281.html.
[4]萧志恬.四十年来基督教宗教活动框架的变迁[J].宗教,1991,(1):70-75.
[5]段琦.宗教生态失衡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以江西余干县的宗教调查为例[N].中国民族报·宗教专刊,2010-01-19(6).
[6]王爱国.民族民间宗教信仰对于宗教生态平衡机制的维系[N].中国民族报·宗教专刊,2010-01-12(6).
[7]李向平.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512-513.
[8]高师宁.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J].浙江学刊,2005,(2):50-55.
[9]李向平.当代中国宗教格局的关系建构[EB/OL].(2010-07-08)[2010-08-15].http://lxp0711.blog.hexun.com/53063031_d.html.
[10]高师宁.基督教信仰在今日中国[EB/OL].(2009-05-06)[2010-08-15].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ab150b0100d8g1.html.
[11]J·D·亨特.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2]李向平.“场所”为中心的“宗教活动空间”——变迁中的中国“宗教制度”[C]//基督教文化评论,2007,(26):93-113.
[13]孙冶方基金会.基督教传入农村的社会背景和发生机制[EB/OL].(2010-01-20)[2010-08-17].http://new.21ccom.net/plus/view.php?aid=5279.
[14]冉云飞.1957年的一则基督教史料[EB/OL].(2010-07-08)[2010-08-17].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70812849.html.
[15]沈洁.“反迷信”话语及其现代起源[J].史林,2006,(2):30-42.
[16]吴真.从封建迷信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信仰的合法性历程[C]//金泽,邱永辉.中国宗教报告(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61-180.
[17]陈潭,陆云球.非正式嵌入、蓄水式成长与村庄宗教传输镜像——以皖南H县非正式宗教团体的生存状况为研究个案[J].南京社会科学,2008,(1):55-64.
[18]罗伯特·希普里阿尼,等.宗教社会学史[M].高师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0,57.
[19]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一)[M].台北:台湾桂冠图书公司,2006:11,34.
[20]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M].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51.
[21]关凯.当代中国社会的民族想象[EB/OL].(2010-06-25)[2010-08-18].http://new.21ccom.net/plus/view.php?aid=12041.
[22]Andrew G 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23]Jean C 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24]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52.
[25]约翰·弗洛尔,帕米拉·利奥纳.中国乡村的文化生活:以川主庙为例[C]//张敏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西方学者看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01-322.
[26]米歇尔·福柯.福柯读本[M].汪民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51,358.
[27]米歇尔·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344-346.
[28]Mayfair Yang.The Gift Economy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89,31(1):25-54.
[29]安东尼·吉登斯,郭忠华.民族国家理论的悖论性发展[N].社会科学报,2010-01-21(3).
[30]牟钟鉴.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EB/OL](2010-04-02) [2010-08-19].http://www.mzb.com.cn/html/node/122313-1.htm.
[31]吴子桐,艾恺,许章润.艾恺、许章润、吴子桐:“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梁漱溟与中国的现代化(中)[N].中华读书报,2010-06-16(17).
(责任编辑:周成璐)
"Religious Ecology"or"Power Ecology"——To Begin with the Trend of the Theory of"Religious Ecology"
LI Xiang-ping
(Research Center for Values and Cuctur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Center on Religion and Societ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The social essence of China'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is not only the issue of religious ecology,but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faith and social power,that's to say,its deep problem being the problem of China's contemporary power ecology,not being the proble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folk religion faith.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temporary religion and its religious faith,or the contradiction or even conflict between them,in fact,concerns power ecology or social ecology.As far as China's current trend of social change,it is actually a neglect of commonality and sociality of modern country and modern society to re-wield the flag of the"Chinese tribes in the east",or to be exact,to use anxiously the Chinese tradition to construct orthodox faiths.In regard to its essence,than saying to give a space of development to folk faith or folk religion,we would rather say to open a religious relation to return a freedom of the social practice of religion and faith,if we want to settl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s contemporary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faith.This essay,from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 of China's contemporary religious faith,tries to sort out such issues of sociology as power ecology and the faith in the level of the nation.
religious ecology;power ecology;social structure;faith relation;nation formation
B911
A
1007-6522(2011)01-0124-16
2010-07-21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20005)
李向平(1958- ),男,湖南邵东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