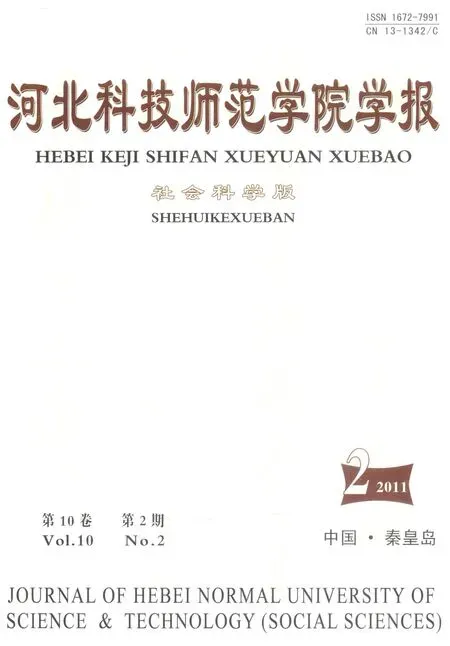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原因探析
杨卫宏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政法教学部,安徽 芜湖 241002)
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原因探析
杨卫宏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政法教学部,安徽 芜湖 241002)
从国家法律与社会民意、规范思维与普通理性、法律事实与民意认定的事实之间的冲突详细论述了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司法判决违背民意的情形,正确认识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的原因,也是提高司法权威性和司法判决社会认同度的基础。
司法;民意;规范思维;普通理性
民意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民心、公意,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民意多为社会基本道义的常见表现形式。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以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规范,司法正是以维护社会的基本道义为己任。在法治社会,司法与民意在维护社会基本道义上一般情况下应是一致的,两者存在维护社会道义的共同价值取向,司法所维护的社会基本道义即为民意所在,民心所向。
但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也会出现司法判决违背民意的情况,即法官严格依法判决,结果却与民意不相符合,甚至完全相左。探寻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的原因是提高司法判决社会认同度的基础,是发挥司法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保障作用的关键。为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探寻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的原因。
一、国家法律与社会民意的冲突
司法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驭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1]。在人类历史中,国家从来就是一种与社会相对的合法性暴力。因此,作为国家职能的司法必须体现的不是社会大众的意志,而是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律。“司法都离不开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它以社会关系上的纠纷为对象,司法是化解纷争的;二是由第三者出面解决纠纷,即主要由法院的法官来解决;三是解决纠纷的尺度是法律,即以成文法律、判例、习惯为解决争议的是非标准。”[2]任何情况下,司法机关都不能超越法律,而只能是受法律约束的法律适用机关。即使是在倡导司法独立的西方国家,司法以及法官服从法律甚至只服从法律仍然是其独立性的底线。民意则代表了大众诉求,是广大民众伦理道德观念、人情、风俗习惯等的一个综合载体,是社会基本道义以及广大民众伦理价值观的体现。它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也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当然也就不完全体现国家意志,它是在一定范围内俗定的或通过交流讨论而形成的共识性理念。民意不是一种制度性要素,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效力更多地来源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广大民众对传统道义的认同。
国家法律与社会民意的冲突集中表现为法意与民意涵盖下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社会道义以及人情等的冲突。它们在价值标准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如道德的价值标准是“利他”,而法律的价值标准是“利己”,伦理学信奉的是“人性善”,而法学推崇的是“人性恶”,它们之间不可避免产生冲突。著名的许霆案以及张学英案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许霆案中,首先撇开法律问题不谈,单从民众的日常经验出发,许霆的行为可谓非抢非盗,只是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一块从天而降的“馅饼”时的一念之差。也就是说,许霆当时当地的行为,换上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对于这样的行为,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来说,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显得过于严厉,甚至不近乎人情,法律与道义、法理与人情之间产生了巨大裂缝。张学英案中,有妇之夫黄永彬发现自己患上了癌症后,立下了遗嘱,决定在自己死后将自己房屋的一半及其他财产赠予和自己共同生活并长期照顾自己的情妇张学英,并到公证机关对这份遗嘱进行了公证,但在黄永彬死后,其结发妻子拒绝张学英参与遗产分配。从法律上来说,这是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但法院最后还是判张学英败诉,张学英没能根据合法有效的遗嘱获得遗产。但法院的判决却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支持,以至于一审判决作出后,庭审现场的旁听群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法院最终依据“公序良俗原则”这一概括性条款作出了判决,这明显违背了继承法作为特别法优先于民法的效力冲突原则,但却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可以说法官的最终判决迎合了以广大民众为代表的社会道义。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因为关系到法律是否应保护“二奶”的权益这一当下中国最关注的道德问题而变得复杂,“二奶”的权益是否应给予平等保护的争论的本质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法律规范的难以融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深深根植于民众的心中,如果法院判处二奶获得继承权必将会引起民意的不满,司法机关在舆论压力之下作出了保护原配妻子的司法裁判,巧妙地化解了法意与民意的冲突。但在这场法意与的民意较量中,民意却成为了实际上的获胜方。
法律与民意冲突除了前面介绍的各自自身因素外,还有其他原因。首先,民意的不周延性以及语言的模糊性,往往使得民意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而法律相对稳定,社会情势变迁的日新月异,思想道德文化发展日趋多元化,又使得法律在吸收民意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一般情形下,一元化的法律规范很难吸收多元化的民意。而普通百姓却习惯于将问题纠纷道德化,总是用好人和坏人的标准来看待纠纷,并按照这一思维模式要求司法做出回应,在道德观念支配着社会的传统下,道义、民意成了民众衡量司法正义与否的标准,如此一来,司法判决违背民意的现象就极易发生。其次,从近现代以来的立法史来看,我国的立法对外国法律的借鉴远甚于对本土风俗习惯、惯例的考察,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法律制度、规则、概念和术语,而缺少了对现实国情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总结,由此逐渐形成了一副立法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尴尬社会图景。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与运作模式与人们日常生活场景之间的整合出现断裂[3]。这种断裂正是司法与民意冲突的真实写照。
法律与民意的冲突体现了民众对司法根本价值的质疑,如不予以正确认识和积极解决,势必会导致民众对法律的认同危机,影响司法救济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当人们认为司法救济导致不公正、不经济的后果时,当法律无法在民众中取得应有的认可和信任时,司法也便丧失了调控社会关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尤其是当前我国尚未摆脱“差序格局”的乡土本色,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纠纷并非只有国家司法一种途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民间法仍发挥着巨大作用,且这些地方性规则更契合民众社会心理和生活习惯,更易为人们所接受[4]。因此,随着法律和司法正统性危机的日益加重和法律权威性的日益消解,当纠纷再次发生时,人们可能会选择民间法、私力救济从而规避法律的适用。
二、规范思维与普通理性的冲突
司法是以法律规范为判案依据的,与广大民众依据普通理性与个人感受追求理想、公正与效率不同,司法表现出极强的规范思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谈到法律家的显贵时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有人问我,美国的贵族在哪里,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们不在富人中间,因为富人没有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纽带。美国的贵族是那些从事律师职业和坐在法官席位上的人。他认为在法律家的身上潜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如同贵族那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由衷热爱规范,对观念之间的规律联系有一种本能的爱好。[5]这种规范思维不仅体现在实体法律方面,更体现在程序法律方面。司法活动十分注重程序和形式,法官对程序和形式正义往往有着特有的偏好,他们习惯于按照某种固定的、甚至在普通人看来有些呆板的程序审理案件。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与宗教活动非常相似,他们最大的相似性就在于按照某种呆板僵化的形式来处理事件[6]。司法的程式化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价值,马克斯·韦伯对此曾说过,司法裁判的形式主义使得法律体系如同机器一样有序运行,这既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又极大地提高了预言他们行为法律后果的可能性[7]。在日复一日地司法审判程序中,法官们形成了独特的法律逻辑思维方式,这种法律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于一般的生活逻辑,它严谨程度高,比较深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甚至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从前提到结论,推理严密,环环相扣,其中又蕴含着独特的法律理性。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言,在司法程序中,法官必须抑制自己的情感,泯灭自己的个性,就是要像自动售货机那样——一边是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的入口,一边是输出司法判决的出口,机械运行,不逾雷池半步[8]。
民意不大在乎法律体系的内在秩序,更注重朴素的道德感和正义观,正如苏力所言:“普通人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律做出回应。”[9]民众的这种普通理性使他们坚持认为当法律与外在的社会价值发生对立冲突时,应以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来作为规范要求的最终依据,即强调“法律应当是什么”这一命题,以法律的外在价值——正当化为基点。对于司法,民众则始终站在一个外部的立场上,虽然他们不参与司法审判,却会针对司法机关提出许多不同的道德主张,亦或是直接给予某种情绪化的是非评价,以希望司法机关能体现其基本意志,这种普遍理性与追求合法性的规范思维之间存在很大距离。
再回到许霆案,为什么广州中院会作出一个连普通民众都能感知的明显畸重的判决呢?难道真的是法官素质不高,不懂法律,或不通人情吗?或者干脆如某些网民所称的“枉法裁判”吗?事实上,就在许霆案一审判决一年前,广州某区法院就曾另案以盗窃罪判处参与许霆案的郭安山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但这一判决并没有引发任何社会非议、争论,与许霆案一审判决后民众反应差别巨大。尽管没有证据,但是相信,作为郭安山案二审法院的广州中院在审理许霆案时,不可能不参考郭安山案,也许一审法官也有难言之隐。刑法学者都认为,一审判决定性盗窃罪,从犯罪构成或法理上看,似乎没有大错,只是“量刑重了些”。量刑是法定的,一审法官在判决裁量时已经选择了最低的法定刑。有理由作出猜测,一审法官是被迫判了一个在他们看来也不合情理的刑期。但当代中国司法强调的不正是“罪刑法定”、“有法必依”、以及“程序正义”而非仅仅“实质正义”吗?不能仅因为许霆的具体身份、案件情节而随意从轻呀?严格的规则主义、法条主义、罪刑法定因此成为中国当代法学界、法律界和法律教育界的主流和主导法治意识形态[10]。所以,许霆案中的一审法官宁愿违背民意甚至也违背了自己内心意愿也要规范甚至是机械的依照法律规则运用三段论推理作出判决,这样的判决所形成的裁判文书一定是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简单、机械的安装与对接。一审判决没有考虑或是为了恪守法律而有意忽略的东西,忽略了每个案件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个性特征,忽略了法社会学或伦理学给予的有益启示,而这些正是广大民众期待司法所作出的回应,这无形中加大了民众与司法之间的距离感,自然也就无法赢得民众的内心认同。法律具有社会相关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当案件在法律技术上、社会结构上都相似的时候,案件的处理方式才会相似[11]。那些曾经深深影响中国司法进程的典型案例,如王余斌案件、刘涌案件、许霆案件,大部分原因就在于法院作出判决时,没有充分考虑甚至忽略了案件所包含的社会信息或民意所传达的社会道义。由于缺乏代表民意的普通理性的传输机制,司法审判过程中,普通理性难以得到合理的表达,这也直接导致了司法裁判在民意的旋涡里徘徊难以前行,衍生出按照法律标准得出的司法裁判与代表社会公正的民意之间冲突的现象。
在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中,传统的司法裁判者常常凭借自己的良心,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运用朴素的平民化而非职业化语言作出判决。他们没有系统学习一套与“权利命题”相对应的法律规则,不能像现代的法官那样借用缜密的逻辑思维观察、思考与法律推理。他们经常超出文字的拘囿,以一种平民观念,通过通俗的语言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在法条字义与法律目的之间,他们一般不会拘泥于法条的字面意思,而是侧重于裁判活动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并根据目的需要进行裁量。法官在做出判决时首先考虑的不仅仅是判决的合法性,同时还包括社会公众的认可度,纠纷的处理结果是否符合社会大众在长期的生活中所形成的正义观念,是否符合普通百姓的行为习惯或道德价值观念。这种传统的裁判方式必然要求司法裁判要充分考虑民意以符合社会道义,所以形式推论或是论证在司法审判过程中的作用显得非常微弱。对于规范思维与普通理性易于发生冲突的导致司法违背民意的道义相背案件,传统的司法裁判者审理案件的逻辑思维方式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法律事实与民意认定的事实的冲突
这里对法律事实的理解与法理学上的理解不同,法学理论上认为:法律事实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它包括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12]。这里法律事实主要是从法律规范中作为制度的法律事实来理解。而本文所说的法律事实是指司法审判中所需要查明的案件法律事实,是司法人员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证据规则等所认定的案件事实。通过司法审判程序查明的法律事实,反映了案件的“法律真实”,“法律真实”证明要求也被越来越多的法律专业人士所接受。所谓“法律真实”,是指人民法院在司法裁判中遵循法定的证据规则,按照诉讼的证明标准对事实的认定,从其所依据的证据来看已经达到可视为真实的程度。从现代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来看,也已不再一味追求案件法律事实是否符合客观的真实,而只要符合法律上的真实,即便这种真实有可能与客观真实不符,法官也应当将其作为定案的事实,并以此为依据作出法律上认定为正确的判决。
然而,在日益强调公开透明的信息化社会里,通过法律事实所呈现的“法律真实”与社会的主流判断标准以及广大社会民众对司法审判的预期显然有差距,老百姓从心理上难以认同。社会民众期望司法机关所认定的事实能与客观实际所发生的事实完全吻合,确定无疑,完全做到“客观真实”。并且在此过程中,广大民众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即民意认定的事实。民意是民主基础上的社会大多数人意志的理性表达,因此,民意认定的事实可以理解为民众通过媒介等各种途径的了解对案件客观情况所做出的理性判断。民意认定的事实与法律事实都是对案件客观情况做出的一定程度判断。但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以及认知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司法人员与民众对案件事实完全可能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认定。由于法官、当事人以及社会民众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关系存在认识方面的较大差异甚至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民众对司法判决的质疑。尤其是在案件审判程序结束而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时,法官根据举证责任规则,依据“法律真实”标准作出判决,而且无法详尽解释为什么这样判决。当事人以及社会民众势必会产生疑问:法官凭什么糊里糊涂就把案子给判了?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其中的“事实”正是根据规定程序和证据规则所认定的法律事实,只要司法审判人员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审查符合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就可假定它已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案件客观事实,并可依此来定案,但这种假定并不能保证绝对正确。民众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并不受法律的限制,他们通过各种媒介的介绍做出自己对案件事实的判断,通过媒介汇集的民意认定的“事实”与法官根据依据证据规则认定的案件事实可能大相径庭。有时甚至会出现法官查明的案件事实背离客观事实,而民意认定的事实却与客观事实一致的尴尬局面,例如某被告客观上确已偿还原告债务,但忘记索回欠条,而原告却凭借此欠条起诉被告索要欠款,法官却只能依据法律事实判令被告败诉并偿还债务,这与民意期望、预想的判决结果截然相反,由此导致民众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由此可见,法律事实与民意认定的事实的冲突并非民意与司法本身的冲突,实质是法官与民众由于对事实认知的不一致而产生的一种误解、一种隔阂,这属于事实层面的问题。其实,民众对司法行为以及法律本身的价值可能并不存在质疑,而只是根据由报纸、网络等媒介提供的信息作出某种与司法不同的事实判断罢了。在此情形下,司法对于此种民意的态度应当是明确的,即在案件裁判过程中不予过多考虑。因为没有任何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民众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介提供信息掌握的事实就具有客观真实性,就比法官通过诉讼程序确认的“事实”更符合事实的本来面目。基于此,法官应秉承法律的基本理性,遵循法定程序来认定事实并作出裁判。否则,如果法官盲从了民意的诉求,放弃了查明的案件事实,不仅丧失了法律的严肃性,冲击了法律应有的理性,而且极易造成错案,佘祥林案件已给带来了这方面的沉痛教训。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94.
[2]夏锦文.社会变迁与中国司法改革:从传统走向现代[J].法学评论,2003(1):72-74.
[3]谢新竹.论判决的公众认同[J].法律适用,2007(1):32-37.
[4]喻 中.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3.
[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02-303.
[6]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1-22.
[7]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227-228.
[8]贺卫方.许霆案:法官何以说理[N].南方周末,2008-01-24(A5).
[9]苏 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C]//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53-354.
[10]苏 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J].中外法学,2009(1):93-111.
[11]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M].郭星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07-108.
[1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65.
Exploration on Causes of Conflicts between Judicial Judgments and Public Opinions
Yang Weih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Anhui Business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Wuhu Anhui 241002,China)
From the conflicts between national law and social public opinions,regular thoughts and normal rationality,legal facts and the facts confirmed by public opinion,the situation in which judicial judgments infringe public opinions sometimes occurs during judicial practices is illustrated in details.Understanding the reason caus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judicial judgments and public opinions is the foundation to enhance judicial authority and the social recognition of adjudication.
judicature;public opinion;regular thoughts;normal rationality
DF84
A
1672-7991(2011)02-0051-05
2011-05-10;
2011-05-30
杨卫宏(1980-),男,安徽省桐城市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宪法与行政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