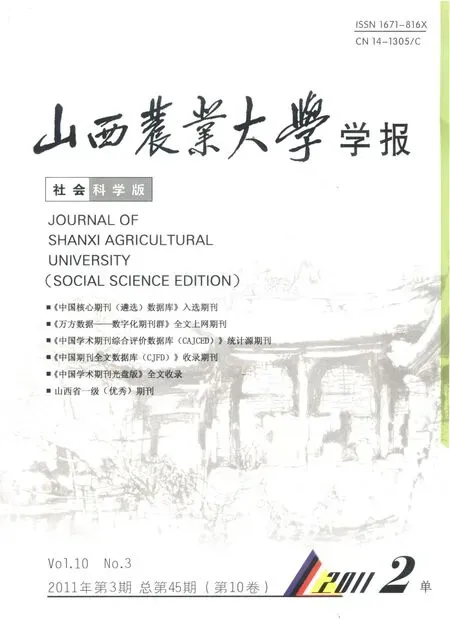从文湖的湮没看汾河流域中部水环境的变迁
白美云,杨昌杰
(1.山西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山西太谷030801;2.山西省太谷中学,山西太谷030800)
由王玉德、张全明等著的 《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一书中这样写到:“山西古今县名有560多个、其中88个是以河川为名,21个是以泉为名,4个是以山水为名。此133个县名反映了古代山西曾经有过湿润多水、植被厚密的历史。与晚近以来山西严重缺水形成鲜明对照。”[1]纵观山西省水环境的变迁,多角度地分析水环境恶化的要因,摸索防止、改善的方法已成为当今的紧急课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河流湖泊的变迁,对于我们今天水环境的综合治理亦不无裨益。
关于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六、七十年代起、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水患,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学术界将研究重点转向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环境复原,如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状况等方面。近年来,相关研究又注重了人类活动、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探讨。然而,以上研究大多立足于古都长安及相邻地区的生态变迁,对于山西省汾河流域中部地区,特别是其水文环境变迁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因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湖的变迁,利用 《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制》《读史方舆纪要》等文献,并结合实地调查,想就山西晋中地区水文环境的实态和变迁做一考察,并祈行家指正。
一、《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文湖
北魏郦道元撰注的 《水经注》,对汾河流域的河流、湖泽有较详细的记述,其中对湖泊的地理位置、规模记载尤为详尽,为认识当时该地区的水环境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据 《水经注》记载:当时汾河流域中部,即现在山西省中部大的湖泊有介休县的昭余祁 (汾陂或邬城泊)、汾阳县的文湖、榆次县的洞渦泽 (淳湖)、太原的晋泽等。本研究主要以文湖为对象,来考察汾河流域中部水环境的变迁。
《水经注》卷6《汾水》记载:
“文水又南,右会隐泉口,水出隐泉山之上顶。……其山石崖绝险、层松饰严、列柏相望。
文水又南,经茲氏县故城东为文湖。东西一十五里,南北三十里。湖在县直东一十里。湖之西侧,临湖又有一城,谓之豬城。水泽所聚,谓之 ‘都’、亦曰 ‘豬’。盖即水以名城也。
又南,经汾州府东,原公水自城北来注之,豬为文湖。”
依上所述,文水向南流,与隐泉水汇合,隐泉水发源于隐泉山,这一带 “层松饰严、列柏相望”,是森林非常茂密之地。这些森林的存在,一方面与这里的地下水条件好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又对这里的水文状况有调节作用。文水在茲氏县 (今汾阳县三泉镇巩村)正东十里处,潴为东西十五里、南北三十里,方圆近百里的文湖。原公水源源不断地注入,补给着文湖的水量。临湖有一城,谓之豬城。 “豬”意为水积聚之地。现在汾阳县东南的潴城村,其名大概源于此吧。由此可推测,在六朝时期,汾河流域中部的水环境是非常优越的。
唐代汾河流域中部水环境与前代相比,有了一定的变化。
《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记载:
“文水城中种水田。
文水县城甚宽,大约三十里。汾水经县东十五里。文水自交城县界流入,经县西,又南入隰城县界。西河县:隰城县,上元元年改为西河县。文湖,一名西河泊,在县东十里,多蒲魚之利。”
由此可知,文水县城在当时已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县城周围的农民以种水田为生,文湖在与文水县相邻的西河县东十里,也叫西河泊,水产资源丰富。据竺可桢的研究,隋唐时期是5000年来的第三个温暖期,气温约高于现今温度1~2℃。[2]暖湿气候必然带来丰沛的雨量,有利于森林和一般植物的生长,也有助于改善当地的水环境。总体上来看,唐代文湖周边的水环境还是比较优越的。但是也不是说毫无变化的。唐朝初期,随着突厥的不断南下,唐王朝与突厥的关系日益紧张。《读史方舆纪要》卷4《山西二》记载:
“唐武德五年,突厥冠并州,襄邑王神符破之于汾东。
阳邑故城……隋曰太谷。唐武德八年,李高迁屯太谷以拒突厥,既而并州揔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
唐开元五年,突厥九姓内属者,皆散居太原。”
由此可见,唐创业初期,由于突厥势力强盛,其侵攻范围达到太谷;开元年间,伴随其势力的衰弱,一部分人落户于太原。据以往研究考证,直到唐代中期太原以北的广大地区几乎都是突厥的活动范围。[3]为此,太原作为 “王业所基,国之根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太原被称为 “北都”“北京”,与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并称为 “三京”。据 《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记载:
“唐高祖武德初,窦静为并州大总管府长吏。时突厥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足。静上表,请于太原多置屯田,以省馈用……竟从静议。岁收十万斛,高祖嘉之。六年 (六二三),秦王又奏请益置屯田于并州界,高祖从之。”
可见,唐王朝把发展农业作为防卫突厥南侵的重要一环。在太原屯田事业积极地展开,考虑到农业与水利的关系,也足以想象出水利兴修事业的发展。《新唐书》卷39《地理志》记载:
“并州文水县西十里有常渠,西北二十里有柵城渠。高祖武德二年汾州刺史萧头引文水南流入汾州。贞观三年 (六二九),民相率引文谷水溉田数百顷。东北五十里有甘泉渠,二十五里有荡沙渠,二十里有灵长渠,千亩渠倶引文谷,灌田数千顷,皆开元二年 (七一四)令戴谦所凿。”
这里所看到的 “渠”,是战国时期开始修建,与沟洫相比可以说是大规模的人工水路,被使用于灌溉、排水、交通,迄今在华北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代开凿灌溉数百顷乃至数千顷的常渠、柵城渠、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的水源,都是源于文水,这不能不考虑由文水积聚而成的文湖,也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农业生产的发展势必也会对周边地区的森林植被构成破坏。再加上唐代封建统治者大兴土木,肆意砍伐,唐代中叶以后,秦岭、陇山一带的树木已砍伐殆尽,不能够满足建筑宫殿的需要。[4,5]《新唐书》卷137《裴延龄传》记载:“近山无巨木,求之岚胜间。”这里的 “岚”指今山西省岚县;柳宗元 《晋问》中则载 “晋之北山有异材,梓匠工师为宫室求木者,天下皆归”。山西因为距长安、洛阳较近兼有黄河、汾河及陆运之便,成为宫廷使用木材的供给之地。可见尽管当时山西的植被破坏没有国都长安那么严重,但在吕梁山脉一线滥砍滥伐现象已经出现了。所以,唐代汾河流域中部的水环境与之前相比,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
二、宋元时期文湖的缩小
北宋河东路人口密度较高的仍集中分布于汾河谷地一线,宋人 “导汾水,兴水利,置屯田”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山西通志》卷41《山川考》记载:
“《宋史河渠书》:煕宁元年正月,复汾州西河泺,泺旧在城东,围四十里,岁旱以溉民田,雨则瀦水,兼有茭菱蒲鱼之利,可给贫民。”依上所述,干旱之季可以引水灌溉农田,洪涝之季吞吐汛期洪水,文湖对农业生产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可以说,文湖在调节、改善当地水环境方面至关重要。但是,从其所记载的面积来看,“围四十里”表明六朝时期方圆近百里的大湖,再经过约五百年以后已缩小了一多半。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名称也不断发生变化,六朝时期称为文湖,唐代称西河泊,宋代则称为西河泺。从湖→泊→泺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该地域水环境的变化。[6]
宋代文湖的变化还可以从以下史料体现出来。《读史方舆纪要》卷4《山西二》记载:
“宋煕宁初,前转运使王沿废为田。人不以为便。至是知杂,御使刘述请复之、即文湖也。”
由此得知,在宋神宗煕宁初年 (1068~1078),转运使王沿围湖造田,发展农业。当地人民认为这样做于生产生活诸多不便,御使刘述请求割田造湖,恢复文湖为原有状态。我们不难判断,宋代统治者的错误政策直接导致该地域水环境进一步恶化,结果招致水患频繁发生。《读史方舆纪要》卷4《山西二》记载:
“大陵城,汉置。晋时为南单于所居。永兴初东瀛公腾主遣将聂玄击刘渊于大陵,为渊所败。后魏治于城西南十里,改曰受阳。隋曰文水,今县东十里故文水城是也。子城周二十里有奇,宋元丰间,因水患徙至南漳蛇村,高阜处即今县地。”
这则史料中提到的文水城,隋代以前也称大陵城,为匈奴所占领。宋元丰年间 (1078~1086),因水患频繁,影响了人民的生活、生产,迁到地势较高的南漳蛇村。同样,光绪 《山西通志》卷41《山川考》记载:
“《一統志》曰:文水故城在今县东十里。宋元符间,因水患徙。 (即水皆入田,故道之湮,或由此矣)”
这两则史料关于文水城的迁移时间,记载虽有所不同,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一则史料的记载是以迁移开始为基准,另一则是以迁移结束为基准而形成的差异。但是文水城在宋代因水患而被迁移是无可非议的。第二则史料进一步说明了造成水灾的原因是由于大量引河水灌溉,旧有水道湮废,失去了防洪、抗洪的作用。此外,北宋大中祥年间(1010~1016)为修筑宫殿,在岚县、离石、汾阳一带采伐柏木,伐木工多达三四万人,砍伐的大量木材 ,“先沿支流漂入汾河,后束为木筏顺汾河而下,至河津入黄河,沿河东下至于开封 ”。[5]因此,当时就出现了万筏下河汾的情景。汾河流域历经唐宋各代垦殖、采伐,以前林草茂密的青山绿水之地已逐渐变貌,当然也影响到当地的水环境。 《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汾河谷地的情形:“本路多土山,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水浊如黄河。”由此可见,宋代汾河流域中部的水环境已严重恶化了。到金大定年间,文湖的变迁从 《汾阳县志》卷1《山川》中反映出来:
“瀦城一带,旧系文湖,深一丈,长十五里,阔八里。……金大定间,滨湖居民浚渠入汾,太守公傅慎徽,力为严禁。守去,终引而注之,耕以为田。无论傍田膏腴,多旱暵之虞,皆变石田,即此地也。亦惟旱年可熟,略有淫霖,辄致漂沒。但知窪地可田,而不知余田失也,但知低田可耕,而不知凶年赔累也。今欲全濬为泽,势必不能,当法割田为湖之意,规其半以瀦水,导上流会纳,而勿使通于汾。”
这里记载的文湖 “深一丈,长十五里,阔八里”,其宽度虽比 《水经注》的记载缩小了一半,但与宋代的 “围四十里”相比,变化还是不大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首次出现了关于文湖深度的记载,“深一丈”也就是10尺,宋元时一尺合今30.72厘米,[7]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文湖已变得非常浅了。到金大定年间,文湖沿岸居民开渠引湖水入汾河,围湖造田,盲目发展农业生产。太守傅慎徽极力严禁,他离任后,沿岸居民大规模围湖造田,致使文湖进一步缩小,水患增加。在寻求防治水患对策之时,把农地扩大导致湖泊等低洼地的消失看作是水患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主张废田为湖,蓄水造湖,以调节当地的水环境,减少水旱灾害。可见宋元时期汾河流域中部的水环境已严重恶化。
三、明清时期文湖的湮没
光绪 《山西通志》卷41《山川考》记载:
“而乾、嘉以来,文湖多湮为田,井庐相望,由文水自上游決渠,东流入汾也。道光初,遂北夺瓷窰河道。于是,清源、交城之水,旧入汾者徙而入文。山潦涨时,冲突不常,決而东则灾及文水,決而南则滨湖诸村悉成泽国,疾苦墊隘,无岁不闻。乃议三县合修,济以库款,濬故渎之淤滞,复文湖之瀦蓄,凿渠建闸,经营岁余,水始畅行。其湖身久为村落所占,施功所及,仅得古昔之三四也。”
由此得知,文湖在乾嘉时期已经湮为民田,昔日的汪洋大泽变貌为农田、庐舍,完全失去了调节地表径流的作用。以致于该地域水害频繁,洪灾不断。故而建议交城、清源、文水三县合力疏通淤滞,凿渠建闸,以恢复文湖蓄水功能,发挥其湖泊效应,但因湖身久已成为村落,故而收效甚微。
据史念海先生丰厚的研究可知,明清两朝是黄土高原的森林植被遭受毁灭性破坏时期。其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推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政策,人口急速增长,必然加剧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全国人口在乾隆年间己突破四亿。清代山西人口在清初顺治十八年451万人,乾隆二十七年增为1024万人。到光绪三年大旱前,己增至l643万人。由于人口的压力,乱采滥伐森林,垦荒屯植的现象有增无减,到光绪前,山西“总计田亩51 120 098亩”,几乎接近于现在全省的耕地面积,可见森林面积己所存无几了。[8]由于森林受到摧残,水土流失日益剧烈,汾河水量大减。到清代,河道常有决溢之患,这就导致了灾害的频发和河道的改徙。
乾隆23年3月29日刘慥上奏曰:“窃查晋省汾州府属之汾阳、介休二县,地临汾河,常遭水患。”《汾州府志》卷32《艺文志》载〈治汾说〉:
“汾水上至太原府之文水县,下至府属之介休县,百余里间,每遇夏秋水涨,近河居民田庐,屡被淹没。乾隆二十一年,曾议于河身两岸修筑夹板堤堰,……保护麦田。”
以上史料,我们不难看出,清代汾河中游地带水患频繁,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沿岸居民于汾河两岸筑堤以保护麦田。“保护麦田”与之前所言 “文水城中种水田”相比,可以说该地区土壤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臆测其地水环境变化巨大。
究其原因,与该地域居民将陂泽改为民田聚为村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古曰,九泽既陂,陂即堤也。联系唐代以后洞渦泽 (淳湖)不再被史书记载,元代昭余祁 (汾陂)被改称为昭余池、清代晋泽改称为臺骀驿,湮为民田,以及文湖的消失,不能不给我们以很深的启示。
四、结语
六朝时代,文湖是山西汾河流域一个大面积的淡水湖泊,唐代的文湖与汉魏相比略有不同,但无巨大变化,汾河流域的水患记载很少;宋代文湖缩小,且汾河水颜色开始变黄,水患增多;明清时期文湖消失,汾河流域水患严重,由此看出汾河流域的水患与文湖由丰变枯的历史是相联系的。联系唐代以后洞渦泽 (淳湖)不再被史书记载,故而臆测唐代是汾河流域中部水环境变化的开始,宋代则是转折点。
河流泛滥、水患频繁、湖泊干涸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过度砍伐森林,致使原始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进而引起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紊乱。因此,应把植树种草作为保持水土资源的一项长远国策和治本之策来抓。另一方面更在于随着军事需要或人口增加,农业生产高速发展,引湖水以及湖水源来灌溉大面积的农地,进而围湖造田,故导致湖泊消失,洪水泛滥。因此,制定水环境的改善措施时应考虑农牧业更替等生产方式的转换。
目前山西省依靠大量采掘地下水补给地上水的不足,但地下水的过度采掘会造成地面下沉、坍塌。还有时下汾河流域的污染已相当严重,如何合理的利用、保护现有的水资源,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深思的问题。
[1]王玉德,张全明.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 [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
[2]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古代史卷下 [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449-483.
[3]石见清裕.唐の北方問題と国際秩序[M].东京:汲古書院,1998:273.
[4]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河山集三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55-75.
[5]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卷二[M].北京:三联书店,1981:232-313.
[6]村松弘一.澤から見た黄河下流の環境史―鉅野澤から梁山泊へ―,黄河下流域の生態環境と東アジア海文明 [C].东京:国際シンポジウム,2005:95.
[7]卢嘉锡,丘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352-358.
[8]山西水土保持编委会.山西水土保持志 [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