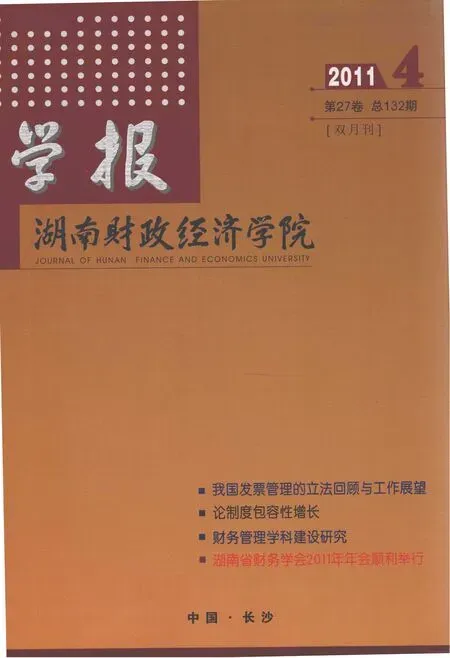道家治世 “三步曲”
徐良根
(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湖南长沙 410004)
道家政治学说的核心主张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内涵是什么?或曰无所作为,或曰顺其自然,或曰清静无为。这些解释,或者不正确,或者不完整。笔者以为,“无为而治”起码包含三层意思,即清静无为、顺势而为、无为而无不为。
一、清静无为
道家从其最高哲学范畴“道”那里引申出“道”的基本特性,从“道”的基本特性那里引申出他们的政治主张。“道”的基本特性是什么?自然无为。“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①,以自然为效法的榜样。自然养育万物而不施加干预,任万物自由生长。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第五章)。天地无所偏爱,对待万物就像对待祭祀的草狗,顺其自然,任其自生自成。既如此,“道”也应该表现出自然无为。“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五十一章)。“道”之所以受尊崇,德之所以被珍贵,就在于它不干涉万物,让万物顺其自然;庄子更是明确指出:“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庄子·内篇·齐物论》)②任由它这样就是了,已经如此而又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这就是“道”。
“道”的这种基本特性体现在社会生活领域,要求统治者“无为而治”,不干涉老百姓的生活。“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老子》第二章)。统治者以“无为”的态度处理世事,不发号施令,不随意指导。“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辅助万物自然发展而不加人为干扰。庄子也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外篇·知北游》)圣人效法天地的美德,融通万物的本性,保持“无为、不作”,这就叫做向天地看齐。总之,“为无为,事无为,味无为”(《老子》第六十三章)——无为而治,是道家政治学说的核心主张。
笔者认为,“无为而治”的内涵分若干个层次,其初始层次的内涵是清静无为。清静是指心神宁静,清虚纯一,没有心境扰动、焦虑多思、私欲旺盛。无为是指随顺自然,心志专一,没有苛烦多为、盲目妄为、主观强为。
对于清静无为,道家创始人做了充分阐述。老子认为,“言有宗,事有君”(《老子》第七十章)。言论有主旨,即清静自然。做事有根据,即清静无为。所以,修“道”的人务必“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十六章),使心灵达到极度空虚,保持极端安静,不带任何主观妄想。因为“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老子》第四十五章)。清静克服扰动,寒冷克服炎热,清静无为是治理天下的要诀。老子还打比方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烹煎小鱼不能随意频繁扰动,否则鱼烂味败。治理国家也是同一个道理。“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第二十九章)。想要治理天下却强作妄为,那就达不到目的。出于强力,终究会失败;把持不放,一定会失去。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既然政令苛烦加速败亡,那就不如持守虚静了。
庄子对清静无为阐述得更透彻。《庄子·内篇·人间世》中,庄子假借颜回和仲尼的对话,谈了一番清虚纯一的道理。颜回要去卫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出发前向仲尼辞行。仲尼说,卫君年轻气盛,喜怒无常,独断专行,气势嚣张,这一去必定凶多吉少。颜回赶紧问仲尼有什么好办法。仲尼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就是说,你心志纯一,不要用耳听而要用心听,不要用心听而要用气听。外界的声音对耳朵毫无触动,外界的事物对心灵毫无干扰。只有空虚的气才能容纳万物,而“道”就是集结在空虚之中。空明清虚的心境,就是心斋。实际上是说,有道的人内心清虚纯一,忘却名利,随顺自然,不主观强为。《庄子·内篇·应帝王》中,庄子虚拟一个名叫天根的人在外游山玩水,遇到无名人,于是请问治理天下的妙道。无名人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保持心境平和恬淡,虚寂安宁,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而不夹杂私欲,天下就治理好了。《庄子·外篇·天地》中,庄子想象远古的至德之世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君主如同树梢的枝叶,安静地看着百姓,不加任何干扰;老百姓如同树下的野鹿,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反之,如果主观多为甚至强作妄为,其结果是把事情搞糟。庄子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内篇·应帝王》)本来是好心,但违反自然而强作妄为,结果办成了坏事。所以,明白天道,通晓圣道,完全懂得帝王之道的,都是任其自为,自然清静。任世间万物如何变化,都不能扰动他的心境。“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外篇·天道》)。圣人做到清静无为,就能成为天地的明鉴、万物的明镜。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是天地的根本和道德的极致,帝王圣人安心于这种境界。
清静与无为相辅相成。内心清静才能做到无为,无为又反过来促进清静。 《庄子·内篇·人间世》中,庄子假借仲尼的口说:“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意为修道不能心杂,心杂就会多事,多事就会扰攘,扰攘就要引起忧患,这样连自己也不能自救。在《庄子·杂篇·庚桑楚》中,有一大段话论述富贵名利、声色好恶、喜怒哀乐拖累德性,蔽塞心志,接着就说,这些东西“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从这些引述可以看出,纯一到宁静,宁静到空明,空明到无为,盖缘于宁静则不妄想,不妄想则无扰动,无扰动则心志纯一,心志纯一则顺任自然,顺任自然则无为。
道家是很重视清静无为的,将清静无为推崇到非常高的位置。老子说,车轮的辐条汇集到车毂上,有了车毂中的空虚处才有车的作用;揉合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皿中的空虚处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和四壁中的空虚处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实有给人带来器物的便利,空虚发挥器物的作用,“无”的作用大于“有”。老子还感慨道,“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第四十三章)。无言的教化,无为的益处,天下很少有能比得上的。庄子认为,“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庄子·外篇·天道》)。清静无为是帝王之德的基本准则。无为施政,治理天下轻松有余;有为施政,治理天下忙碌无功。因此, “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庄子·外篇·刻意》)。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是天地的准则和道德的本质。清静无为何其崇高乎!
二、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是“无为而治”中间层次的内涵,比清静无为上升了一个档次。清静无为侧重从否定面回答问题,显得消极保守;顺势而为则是从肯定面回答问题,是由消极向积极转化。何为顺势而为?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和发展趋势而作为,不做违逆事物的自然本性和发展趋势的事情;进一步,努力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按规律办事,不胡作非为;更进一步,适应历史潮流,顺应天下百姓意志,按天下百姓意志办事,不做违背天下百姓意志的事情。
对于顺物自然而作为,老子有自己的论述。《老子》第二十七章中,老子以隐喻的口吻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善于行走的,不留下痕迹;善于言谈的,不留下破绽;善于计算的,不需要筹码;善于关闭的,不用栓梢别人也打不开;善于捆扎的,不用绳索别人也解不开。这段话实际上是说,有道者治国,根本不需有形的作为,只要顺任自然以待人接物就可以了。老子还说:“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二十九章)世人的情况不同,有的前行,有的后随,有的嘘暖,有的嘘寒,有的强健,有的羸弱,有的安定,有的危险。所以有道的人要去掉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措施。这就是说,世人的秉性不同,不能主观强求,只能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庄子则用大量寓言故事阐述顺势而为的道理。在《庄子·内篇·齐物论》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养猴子的老翁去给猴子喂橡粒,他对猴子说:“朝三而暮四。”早晨喂三升,傍晚喂四升。猴子听后发怒了。他又说:“然则朝四而暮三。”那就早晨喂四升,傍晚喂三升吧。猴子听后高兴了。在这里,名和实都没有改变,只不过顺应了猴子的喜怒心理而已,这就叫做顺势而为。在《庄子·外篇·达生》中,讲了三个寓言故事,从正反两面说明要顺势而为。孔子到吕梁观赏山间飞瀑,只见那瀑布高悬三千丈,飞流溅沫四十里,连大鳖都无法游过。这时忽见一男子游入激流,孔子以为他有痛苦的事而要自杀,连忙叫弟子顺流去救他。没想到那男子潜入水中数百步后浮出来,披发唱歌游到了岸边。孔子满怀钦佩地上前说:“我还以为你是鬼呢,仔细看才知道是人。请问,你游水有什么道术?”那人回答说,没有什么道术,只不过从小就游水,慢慢地摸到了水的习性,“我随漩涡一起没入,随涌流同时浮出,顺着水势自然而为,这就是我的游水之道”。有个叫做梓庆的人砍削木头制作悬挂钟乐的鐻,做成后,美轮美奂,看到的人惊叹为鬼斧神工。鲁侯看见后问,这是用什么道术做成的?梓庆回答说,作为一个工匠,能有什么道术!只不过独自斋戒,平心静气,专心致志,忘却名利。然后进入山林,观察树木的天性,见到形态极其符合的材料,一个成形的鐻就呈现在眼前,然后顺势加以雕制;如果不是这样,就放弃不做。心性自然和外界自然相结合,就成了完美的鐻。顺任事物的自然天性加以作为,就能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如果违逆事物的自然天性强求妄为,只能走向失败。有个叫东野稷的人在鲁庄公面前炫耀驾御马车的本领,进退往来象用绳墨划线一样直,左右旋转象用圆规画圈一样圆。鲁庄公认为驾车能手造父也不过如此,叫他兜上一百个圈然后回来。颜阖在一旁说,东野稷的马肯定要垮掉。没过多久,马果然垮掉了。鲁庄公问其中的道理,颜阖回答说:“马都筋疲力尽了,他还在强迫马奔跑,所以必然要垮。”这就是逆势强为的后果。
对于顺势而为,道家后学《淮南子》做过很好的概括。“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淮南子·修务训》)。那种违背自然本性、背离事物发展趋势的行为叫做“有为”,那种“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的行为不叫做“有为”。叫做什么呢?当然是叫做“无为”。显然,《淮南子》将“无为”理解成顺势而为——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和发展趋势而作为。
如何更好做到顺势而为呢?这就要求研究客观事物,探索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按规律办事。“从事于道者同于道”(《老子》第二十三章),追求道的就要按道的规律办事。“从事于道”,既是追求那最高的本体,也是探求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老子还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明察常理的人善于认识和把握变动不居的事物中不变的准则,即事物的内在必然性,或规律。如果单凭主观愿望,不懂得、不尊重事物变化规律,轻举妄动,其后果是可怕的。庄子认为,人们受心外之物的牵累太多,难以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但“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庄子·内篇·逍遥游》)!如果能够顺应天地本性,驾驭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那就无所依赖,可以进入无边无际、自由自在的境界。“天地之正”,既是指天地自然无为的本性,也是指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可见,依循规律,才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庄子·内篇·养生主》中,这个道理讲得更清楚。庖丁替文惠君宰牛,动作娴熟优美,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文惠君佩服地五体投地,连连叫道:“妙呀!你的技术怎么会达到如此高超的地步呢?”庖丁回答说,他爱好的是“道”,对“道”的追求远远超过技术,经过多年历练,他宰牛时完全能够做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于是, “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进入了“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境界。在这里,追求的“道”当然是指老、庄们说的天地万物的本性,但又何尝不是事物运动的规律呢?正因为对事物运动规律有深刻认识,且能“依乎天理”,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因其固然”,顺应事物的必然趋势,最终达到“游刃有余”的境地,进入自由王国。
顺势而为具体到社会治理层面,就是要顺应天下百姓意志,按天下百姓意志办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做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事情。老子认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得道的人总是没有私心,以百姓的心为心,即老百姓怎么想,统治者就应该怎么想。老百姓想过“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第八十章)的日子,那就要“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老子》第七十二章),不得逼迫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不得压榨老百姓的生活。更应该“物形之,势成之”, “养之覆之”(《老子》第五十一章),顺应百姓的意志,促成百姓愿望的实现,对百姓加以调养爱护。
庄子认为,“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庄子·外篇·在宥》)。老百姓虽然地位卑微,但他们的意见不可不听从,他们的愿望不可不顺应。所以,“智者之为,故动以百姓,不违其度”(《庄子·杂篇·盗跖》)。高明的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以百姓的意志为转移,不违反法度。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治理好。《庄子·杂篇·说剑》中,庄子和赵文王谈论剑术,提出剑术分: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三类。前两类实际上是治理天下和国家的方法。其中诸侯之剑“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方”。意即诸侯治理国家,上效法苍天以顺应日月星辰,下效法大地以顺应春夏秋冬,中顺和民意以安定四方。如能做到这一点,则“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反之,如果只顾一己私欲而漠视民意,“以己出经式义度”(《庄子·内篇·应帝王》),凭自己的意志制定颁布法律制度,就是“欺德”,即虚伪的道德。这样去治理国家,无异于在大海里凿河,让蚊虫负山,是不会取得任何效果的。庄子感慨地说:“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庄子·外篇·秋水》)违逆时代、社会和民意的人,是可恶的篡夺之人;顺应时代、社会和民意的人,才是高尚的大义之人。
三、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而无不为”是“无为而治”最高层次的内涵,是顺势而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道家治世主张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道家政治学说追求的完美结局。无为,不是消极保守、无所作为,而是没有苛烦多为、主观强为,是一种顺应事物发展趋势、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为”。无不为,是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办不好的。无为而无不为,是说摒除苛烦多为、主观强为,不需要刻意作为,只要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和发展趋势,按照事物发展规律去作为,就能把一切事情办好,将社会治理得井然有序、安顺祥和。
道家代表人对“无为而无不为”非常神往。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庄子说:“天地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外篇·至乐》)“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杂篇·庚桑楚》)“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杂篇·则阳》)
“无为”如何才能达到“无不为”呢?
首先,无为则简政,简政则不扰民,不扰民则各安其事。庄子指出:“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庄子·外篇·马蹄》)民众的天性就是渴望过宽松安宁的日子,不希望统治者来打扰他们。顺应这种天性,统治者要摒除苛烦多为、盲目妄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以清静之道治国,以诡奇的方法用兵,以不生事扰民来治理天下。如能做到这一点,则民众“织而衣,耕而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国家祥和。反之,如果统治者政令繁多,苛求妄取,不断搅扰民众,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国家就难于治理了。“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四十八章)。治理天下就是要顺其自然,不扰攘生事。到了政令苛烦、惹是生非的时候,就不配治理天下了。所以,老子讲: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第二十三章)少发号施令才合乎自然,如果政令烦多,国家就会象狂风骤雨那样,终究难以维持长久。事实上,在老、庄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统治者巧取豪夺、妄作非为,才致社会多难、民生疾苦。“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第七十五章)。统治者贪得无厌,制定各种各样的规矩来盘剥、束缚民众,弄得民众手足无措、颠沛流离,于是铤而走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第五十八章)政治宽厚,人民就淳朴;政治苛严,人民就狡黠。
其次,无为则任下,任下则因民自主,因民自主则“民自正”。道家认为,民众有安居乐业的天性和自我管理的潜能。无为而治,要求顺应这种天性,不干扰民众的生活,同时顺势而为,充分挖掘民众的潜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相信民众,任由民众自我管理,以达到社会自治的目的。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老子》第三十七章)侯王如能坚守“无为而治”的准则,万物就会自我化育。在这个过程中有欲望萌发,要用“道”的真朴来镇住它、引导它。“道”的真朴是什么?就是统治者做好清静无为的表率。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统治者不强做妄为、不生事扰民、爱好清静、节制欲望,老百姓就会自然归化、走上正道、自然富足、自然朴实。庄子说:“古之蓄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外篇·天地》)治理天下,君王无贪欲而天下富足,无为而万物自我化育,清静而百姓自然安定。在《庄子·外篇·在宥》中,庄子虚构一个叫做云将的人,往东方游玩,巧遇鸿蒙,求问“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的办法,三问而三不得答。问急了,鸿蒙回答说: “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意即只要心处无为,万物就会自然化育。庄子还认为:“静则无为,无为则任事者责矣。”(《庄子·外篇·天道》)君主清静无为,属下百官才会各司其责。这是社会管理的一条规律。“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庄子·外篇·天道》)。如果君主过于有为,管得太宽太细,属下百官就会偷懒取巧,推诿职责,事情反倒越搞越糟。道家后学《吕氏春秋》总结说:“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无以则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君守》)意即君主喜欢亲自做事,属下百官就会放弃自己的职责去曲从君主所做的事。曲从君主所做的事,即便出现错误也无法责备。这样,君主就会一天天受损害,臣子就会一天天得志,社会动乱也就为期不远了。
再次,无为则察微,察微则“治于未乱”,“治于未乱”则“取天下”。事物的发展趋势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顺应这种趋势,统治者治理天下,必须察微观细,注意事物发展的各种趋象,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事情刚一露出苗头就处理好,也就用不着事后的忙碌和补救,这样治理天下当然轻松有余。所以,老子说“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老子》第五十九章)。早做准备,就叫做不断积德。不断积德,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因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老子》第六十四章)。局面安稳时容易持守,事变还没有迹象时容易图谋;事物脆弱时容易消解,事物细微时容易散去。故“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六十四章)。处理事情最好在问题还没发生的时候,治理国家要抢先在动乱产生之前。
怎样才能“为之于未有”呢?就是要从根源上杜绝各种张扬的“有为”的行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一句话,“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治理天下,收敛自己的私欲,使人们的心灵归于浑朴。统治者做到清静无为,天下则太平无事。
总之,“无为而治”内含清静无为、顺势而为、无为而无不为三层含义,“无为”是出发点,“无不为”是最终目的,“顺势而为”是由“无为”过渡到“无不为”的关键环节,它们是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构成道家治世理论逻辑进程“三步曲”。这种“无为”的实质是“有为”,并且是“大有为”;只不过这种“有为”以“无为”为表现形式,“入世”以“出世”为行进途径。实现天下太平、百姓幸福安乐,是道家和其他诸子百家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