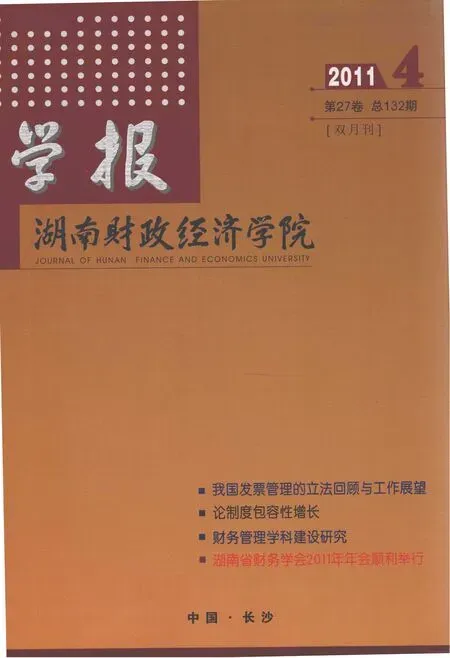体大思精 探原扬新——《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简论
黄胜江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中国古代戏曲文化形态丰富、源远流长。囿于雅俗之辨的文化偏见与史料散碎,现代意义的古代戏曲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指出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特质才正式开启古代戏曲研究大幕。此后戏曲文化研究大致侧重于文献整理、戏曲文本内容、舞台演述体制、戏曲文物、东西戏剧形态比较等方面,专门从编剧创作角度进行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此前理论界尚无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的著述。刘奇玉著述的《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对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充溢着较强的思辨性与创新性,体现了较高的理论水准与学术品位。
一、开阔的文化视野
戏剧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地域环境、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等诸多因素影响。作者以大戏剧文化理论视野,“从文化史层面探求戏曲创作理论所蕴含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轨迹及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流转变化和深厚的民族精神内涵”[1],从传统文化、时代精神、跨文化戏剧参照等向度立体阐释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理论的文化品性与特质。首先是传统文化心理的引证。作者从雅俗之辨的传统文化心理出发,探寻传统文人对创作主体的辨认;从“发愤说”传统梳理“抒幽愤”的戏曲创作动机;从“重史征实”的史官文化诉求解释历史题材剧创作的发达。其次,时代精神的互释。“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时代精神是影响文艺创作发展的重要因素。作者分析了明初强化道德伦理的思潮,晚明心学解放的主情思潮,清初经世致用思潮深深影响了爱情题材剧作中情理激荡的产生与发展。再次,西方戏剧文化的参照。“人类不同的戏剧形态之间又有着彼此不断的交汇与影响,其表现或隐或显地体现在一部戏剧历史的发展过程中。”[3]该书虽立足于本土戏曲文化理论与批评,但没有抛弃西方戏剧文化这一参照系。关于戏剧结构理论,作者梳理了西方亚里斯多德开始就形成的明确系统的重叙事结构的创作理念;而受抒情写意的直觉思维模式影响,中国古代戏曲创作中有关戏曲结构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艰难的孕育过程后,才明晰了“结构第一”的创作理念。通过亚里斯多德悲剧整体性思想与儒家天人合一完美和谐文艺审美趣味的比较,指出东西方戏剧创作均有重视结构整体性的美学原则。
二、稳称的理论构架
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理论形态繁杂而零散,此前的研究多将其体系性和独立性悬置,该书以创作主体和方法论为切入点,论述了创作理论的相关内容。全书理论架构分两大层次,主体论、动机论是创作主体的探讨,题材论、语言论、人物论和结构论是戏曲创作方法论。该书采用考证与艺术概括结合的论述方式,以专题形式,从理论发展史的维度,纵横立体阐释了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的理论范畴,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架构工整谨严。如论述文辞与声律的戏曲语言元素关系时,既梳理了二者在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发展,同时总结出对二者关系的探讨体现了古代剧作家对戏曲特征的不懈探求。“结构论”中,以神龙戏珠法、草里眠蛇法、移堂就树法、羯鼓解秽法、郑五歇后法、错认巧合法等六种技法概括戏曲结构技法论,“余论”又从七个方面对散金碎玉般的不常见的技法予以补充,不但信而有征、准确周详,而且不琐碎、不勉强,得其大体,融通不偏。总体看,著作条分缕析,层次清晰,既有面上的概括,亦多细部的实证,具备了学术史与批评史的通论性架构。
三、丰赡的支撑材料
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主要散见于戏曲序跋、理论专著、评点、杂论、选本等多种理论形态中。人们所忽视的戏曲序跋(包括序、跋、叙、题词、小引、总评、弁言、凡例等)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资料,序跋作者往往从创作主体、戏曲本体、创作方法等层面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全面反映了人们对戏曲艺术的认识过程,是古代戏曲创作理论批评的核心构件,对研究戏曲的文学、美学、理论、批评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充分研究戏曲序跋是对已有戏曲创作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和必要完善。但由于其零散而缺乏系统性,加之不少文献不易见到,作者不畏艰难,多方搜罗,从剧本评点、文集史料、方志杂乘、随笔序跋等材料中发掘新的理论资料。作者特别重视戏曲序跋蕴含的创作理论,在蔡毅编著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集》与吴毓华编著的《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基础上,发掘百余条此前相关著作未收的序跋史料和其它文献资料,给论述以丰实的素材支撑,每一立论,均语有所本。
四、迭出的新见卓识
作者立足于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理论的客观建构和深度阐释,也注重西方戏剧及戏剧理论、小说理论的参照、对比,对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作了全景式、多角度探讨,就其研究视角的多项开掘、对中国古代戏曲创作论的全面把握、对戏曲理论材料的分析和运用而言都具有理论意义和创新价值,取得了颇具启发性的进展。扎实的文献资料和稳称系统的理论架构组织下,全书新见迭出。论述主体创作动机时,作者借鉴文艺心理学的缺失性动机与丰富性动机分别阐释抒幽愤与尚娱乐的动机深层学理,新人耳目。对“本色”的探讨中,作者认为古代戏曲学家纷纭复杂的戏曲本色理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既指戏曲语言的滑稽机趣风格,也指音律的“合律依腔”和文辞的雅俗旨趣,既是对复合曲体审美特征的概括,也是对表达的内容和情感的艺术要求,全面反映了戏曲理论批评家对戏曲本体特征和艺术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肯定东西方戏剧创作寓教于乐的诉求后,作者认为西方创作批评更重美的本体,中国文人阶层对政治的依附性与认同感导致其戏曲创作理论更强调善的伦理道德灌注,于区别中见真知。“题材论”中,作者从审美特征这一角度,认为戏曲创作题材可分为历史、伦理、爱情、宗教四大类,避免了此前诸多论著交叉重复的分类问题。作者指出由于缺乏与当今相对应的历史剧概念,历史剧的创作是否必须严格遵循历史事实,是明清戏曲理论家的重要批评话语,他们从不同视角总结了诸如依史实录、写意虚构、真幻结合等创作观念。这种传统的重出处、讲征实的史学理念,运用于戏曲创作理论中,形成了戏曲家以曲传史、以曲补史、以曲运史三种不同的叙事策略,是理论家们创作实践中以戏曲艺术再现或表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反映,体现了他们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审美认知。对宗教题材的探讨中,强调想象力超凡的宗教故事和奇特的宗教人物为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题材,宗教神学思想如灵魂不灭、阴阳两界、因果报应、普度众生和羽化登仙等观念同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相结合,对戏曲作品内容和戏曲理论学家的审美价值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再如作者从曲体、叙事、剧场三个体系层次的交融角度,总结了古典戏曲创作追求整体性、曲折性、新奇性、自然性的美学原则,认为其最终体现了开放性叙事特点与内敛型叙事要求的调和,颇具识断眼光。
《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作为一部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的专门性研究著作,其意义是众多的,对当下戏剧创作势必产生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对盲目追求大制作、追求矫饰空洞的视觉效果而忽视编剧工作的错误做法将起到理论示范意义。
[1]刘奇玉.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2]刘 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M].济南:齐鲁书社,1995.542.
[3]刘彦君.东西方戏剧进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