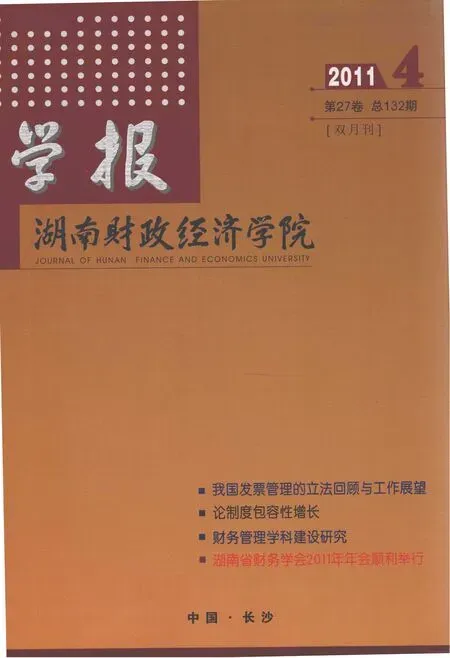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以《水浒传》中人物绰号的翻译为例
吴静
(东莞理工学院,广东东莞 523808)
传统翻译理论将译者和译作置于“仆人”的位置,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忠实于原作者和原文本,甚至将译本比作“不忠的美人”,认为译者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向原作靠拢。随着翻译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既是原文的读者、阐释者,也是译文的创造者。作者在作品完成时就已经抽身离去,他把阅读、理解的任务留给了读者,作品的思想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可以得到新的升华,读者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而获得对作品不同的认识。作为特殊读者的译者在创造译文的过程中,更会因其主体性而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原著新的生命。对于文化归属性较强的作品,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更是要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才能使译文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也能熠熠生辉,闪现出其应有的光芒。
一、译者主体性及表现形式
1、主体与主体性
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第一次将思维与存在相区分,开创了主客二元论的先河。社会是由人组成,人是社会的主体,客观存在的世界和社会则是客体。马克思认为人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特性,是人作为认识主体的主体性内涵。然而,主体性并不仅仅意味着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还包含着受动性和为我性。受动性揭示的是人对自然对象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是人之所以要发挥能动性的客观依据。福柯是这样定义主体性的,[1]“subjectivity is subjugation(subjection);subjugated is being made subject to,being governed by institutional forces that control and frame.”(主体性是一种屈从、服从;屈从则是指被迫服从于、被辖制于具有控制性和制约性的一些社会习俗制度)。可见,人对客体有依赖,客体对人有制约,并不存在真正的、完全的主体性,主体性中必然存在着受动性。为我性揭示的是主体性发挥的方向和目的。主体性中能动性占主导、支配地位,受动性对能动性是起制约的作用。因此,人的主体性必须遵循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2、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
I.A.Richards曾说过,翻译活动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复杂的活动。究竟谁才是这个最复杂活动的主体呢?许钧通过总结国内各方的观点,得出四种答案,[2]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的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是翻译的主体。可见,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其翻译主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身兼数职,他既是原文的读者,也是语言的转换者,更是译文的创作者。
第一,阅读原著的主体性。译者首先是原著的读者,具有阅读的主体性,他拥有自己的文化素养、知识结构、审美心态、人生阅历,这些构成他的互文记忆。所有的读者都需在自己互文记忆的基础上解读作品,读者阅读作品即是对作者互文记忆的识别,也是与作者、原著之间的对话交流。[3]读者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他有着与作者不同的互文记忆,因此阅读原著时自然会包含一些自身的主观性,也可能会读出自己的理解与新意。特别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征就是想象性和艺术性。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可以启迪人的思想、激发人的想象、唤起人的某种情感,而这些思想、想象和情感往往又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说一千个不同的读者眼中会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当然,作为译者的读者不同于普通读者,普通读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甚至曲解原著,而作为译者的读者则必须受到受动性的制约。他必须深入理解原著的灵魂思想,并充分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情感,以及与原作相关的大量注释和评论。在此基础上,译者再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个对原作的较为全面的理解。
第二,语言转换的主体性。如果说分析理解原著的过程可以体现译者的主体性,那么,将原著用另一种语言阐述出来更是译者的主体行为。传统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充当一个语言转换器,完全忠实地将原文复制到译语语言系统,要求译者有高超的复制技巧,绝对服从原文。这无疑是对译者主体性的极力掩饰和抹煞。事实上,语言的转换过程本身就是译者的一种主体性行为,即使是一对一的直译,也会因为译者的外文水平、文化环境、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个人理解能力等的差异而不同,可见,译者不可能充当简单的语言转换器角色,作为独立的主体行为必然体现其主体性,这也是传统翻译理论无法形成统一的“忠实”标准的原因,也是机器翻译无法取代人为翻译的关键所在。
第三,译文创作的主体性。翻译不是对原著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原著语言转换的简单堆积,而是在语言转换过程中融入了译者痕迹的创作性活动。原著作者是在其互文记忆的基础上创造作品,译者在创作译文的过程中,也会不由自主的加入自身互文记忆的元素。一部优秀的译著,必然会充分考虑不同文化环境所导致的思想意识、文化形态的差异,从而将原著所体现的灵魂与宗旨转换为自身所处环境下的表现形式,使译本的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原著的思想和意境。这本身就是译者的一种主体创作性行为,可见,真正“忠实”于原著的译本,需要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的文体形式,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具有较强的艺术本质和区域文化特性。“‘虚构性’、‘创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学的突出特征。”[4]因此,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同一部文学著作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故而翻译过程中,需要译者积极发挥主体性,最大可能地保持原著的真实思想。
二、《水浒传》两个译本简介
《水浒传》是我国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施耐庵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农民起义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和一段段精彩绝伦的英雄故事,为老百姓耳熟能详。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Pearl Buck)将它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赛珍珠出生于美国传教士家庭,小时候就随父母来到中国,在双语环境下长大,对汉、英两种语言文化都有很深入的了解和掌握,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她将《水浒传》意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取自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充分体现了书中绿林好汉的侠义精神和兄弟豪情。这个译本成为《水浒传》的第一个英译本,译者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向外国读者呈现了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底蕴的精彩世界,故问世后在美国盛行一时,至今还流传甚广。遗憾的是这个译本是根据金圣叹七十回本翻译,故事情节不够完整。
另一个更为完整的一百回全译本出自沙博理(Sidney Shapiro),他是一位精通汉语的中国籍犹太人,生于美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二战时被美军派去学习汉语,从而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1947年来到中国,娶了上海演员凤子为妻,定居中国并投身翻译事业。沙伯理一生译著颇多,最为著名的就是《水浒传》,他的译本被认为是“信、达、雅”皆备的绝妙译作,也因此赢得中国文联最高翻译奖。沙译本《水浒传》的书名是《Outlaws of the Marsh》,outlaws在英语中可以用来指反抗当权者而触犯法律的人,与梁山好汉的形象十分贴切。
三、译者主体性在《水浒传》绰号翻译中的体现
文学作品中,给人物取绰号是一种常用的艺术手段,可以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施耐庵的《水浒传》将这种艺术手段发挥到了极致,给每个人物都安排了极为贴合的绰号,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这些绰号简短而蕴含深意,却为翻译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一般而言,越是简洁寓意深奥之处就越需要译者发挥主体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创造。 《水浒传》的两个译本中,赛珍珠和沙博理充分发挥自己的译者主体性,对原文进行理解、判断与再创造,从而翻译出为广大读者接受和认同的作品。我们可以通过对本小说两位译者对绰号的翻译来窥见两人不同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意识形态的取向
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被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所接受的、有观念和态度组成的概念网格 (conceptual grid),而读者和译者正是通过对这个概念网格来进行文本处理的。[5]意识形态主要是某一个人或群体对世界的系统认识,具体表现可以是哲学、政治、宗教、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从宏观上来看,译者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为译著树立怎样的形象;而微观上译者的选词用字也会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
赛珍珠出生于传教士家庭,基督教已经溶入她的血液,成为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在她翻译的绰号中多用到基督教的词汇。如“花和尚”鲁智深,她翻译成The Tattooed Priest;“行者”武松翻译为The Hairy Priest。“和尚”和“行者”都是佛教语言,鲁智深为避祸曾出家为僧,武松逃亡时曾假扮带发修行的行者,故而得此绰号。赛珍珠将它们都译为基督教的“priest”(牧师、神父),显然是受她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她在绰号翻译中使用基督教词汇之处颇多,如“操刀鬼”曹正——The Dagger Devil;“鬼脸儿”杜兴——The Devil Faced;“赤发鬼”刘唐——The Redheaded Devil;“活阎罗”阮小七——The Fierce King of Devils;“催命判官”李立——The Pursuing God of Death; “井木犴”郝思文——The Guardian Star God;“神算子”蒋敬——The God of Accounting;“立地太岁”阮小二——The God of Swift Death; “云里金刚”宋万——The Guardian God in the Clouds等等。可见,赛译本中几乎所有的“鬼”都译为“devil”,“神”都译为“god”。Devil本是宗教用词,在基督教中指撒旦、魔鬼,意为邪恶的诱惑者、上帝的敌人;God则是神、上帝。
沙博理虽然也是美国人,但他从1947年开始就长期定居中国,深爱中国文化,并加入中国籍。而且他翻译《水浒传》是在新中国成立多年以后,那时整个社会阶层都排斥西方意识形态,受此制约,基督教思想在他的个人意识形态中尚未十分深入。因此沙博理的译本中,“花和尚”译为The Tattooed Monk,“行者”译为The Pilgrim,“鬼”多用demon,god则曾未出现过。
2、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策略即为翻译的方法、技巧、手段。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主要体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与译者的翻译目的密切相关。德国古典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指出,翻译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居安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居安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将前者定义为“异化法”(foreignizingmethod),后者称之为“归化法” (domestication method)。
赛珍珠版《水浒传》的译序中谈及她的翻译目的,[6]“因为它生动地讲述了美妙的民间传说……我觉得汉语的语言风格与该书的题材极为相称,因此我惟一要做的,就是尽己所能使译本逼似原著,因为我希望不懂汉语的读者至少能产生一种幻觉,即感到自己是在读原本。”同时她也说明了自己的翻译策略,“我尽可能做到直译……保留原作的内容及写作风格,即使对那些原文读者看来较为平淡的部分也未做任何改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她为了贯彻“异化”的翻译策略,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尽量保持原文的真实面貌,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从而去欣赏独特的汉语文化,领略异国情调。
与赛珍珠偏向异化的翻译策略不同,沙博理致力于向西方推介中国文化,采取的是归化翻译策略。方法上,他努力克服直译的困难和意译的不准确,力求达到“意译、准确”的效果。二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从人物的绰号翻译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玉麒麟”卢俊义,赛珍珠采用直译,将汉文化中独有的神兽麒麟直接音译为Ch’i Lin;沙博理则选择归化法译为unicorn,即英文中的独角兽。另如“锦毛虎”燕顺、“锦豹子”杨林,赛译为The Five-Hued Tiger,The Five-Hued Leopard,“锦”字直接译为“Five-Hued”(五种颜色),与汉语意思保持一致,对英语读者而言却稍显生硬。沙博理则译为The Elegant Tiger,The Elegant Panther,用elegant来翻译“锦”字,在意思上略有差池,却更易为英文读者接受。 “毛头星”孔明,赛译为The Curly Haired,直译“毛头”而得;沙译为The Comet,古代中国“毛头星”的一种解释是“彗星”,这里采用了这种更为西方读者接受的解释。“母夜叉”孙二娘,赛译为The Female Savage,显然是根据汉语字面直译;沙译为The Witch,依然采用英语中相对等的词语意译。“没面目”焦挺,赛珍珠直译为The Faceless,而沙博理则认为没面目即没面子、不讲交情之意,翻译成The Merciless。
3、创造性的介入
翻译的过程是译者运用译入语进行再创造的过程,特别是在文化因素较多的文学翻译中,既要传达原文的意义,又要确保译文符合译语的语言规范,没有创造性的译者不可能很好地将原文移植到译语语言文化中。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多多少少都保留着译者苦心孤诣的创造。这种创造,有时候表现为对原文的取舍,有时候甚至是对原文的叛逆。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特点,《水浒传》的两位译者在翻译绰号时也不时地进行了创造性地介入。如翻译“摸着天”杜迁时,赛译是The Skyscraper,沙译为EaglesWho Flutters Against the Sky,两人分别创造性地选用了不同的形象“摩天大楼”和“鹰”来形容杜迁高大的身材。这两种比喻形象都是原文所没有的,但都十分恰当地表达出“摸着天”所体现的视觉效果,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另外,沙博理将“病关索”杨雄译为The Pallid,描绘出他苍白的病容,而摒弃了原文中提及的关索这个人物,以及杨雄和关索的比较。他还把“拼命三郎”石秀译为The Rash,充分体现石秀的性格特点。在这两个绰号中,沙博理都选用简短的词语来描绘人物的特征,而舍弃了原著的字面含义。这样也完全实现了原著绰号所达到的效果,有利于译文读者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相对于赛珍珠的译本而言,沙博理在翻译绰号时运用的创造性介入更多一些,因为赛珍珠是推崇直译,强调字面和结构与原文一致,为此宁愿牺牲译文的流畅和地道,可见译者对创造性介入的使用也与其翻译策略的选择息息相关。
总之,文学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译者不是复印机、不是语言转换器,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翻译活动的主体。从以上对英译《水浒传》赛、沙两个译本中人物绰号翻译的分析可以看出,译者意识形态的取向、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创造性介入都必然作为主体性的一部分在译作中体现出来。两个译本虽然体现着不同的主体性,却都为译语读者所接受,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姿态在译语文化中表现出原作的丰姿,都无愧为优秀的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