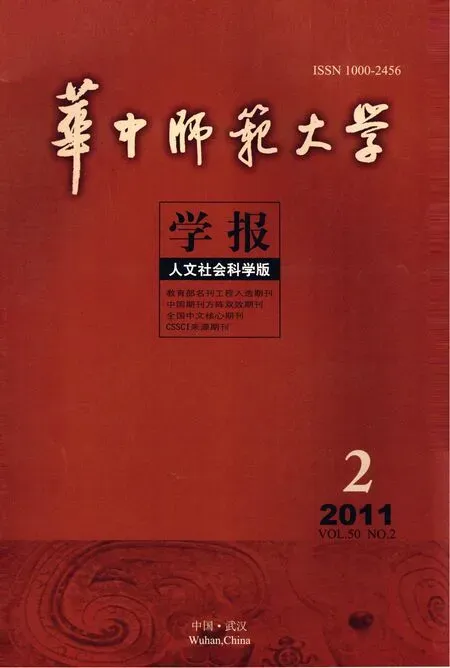消解易代:从《同郡五君咏》看清初士人的身份认同
冯玉荣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消解易代:从《同郡五君咏》看清初士人的身份认同
冯玉荣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明清易代造成士人出处与认同上的混乱,这种焦虑不仅存在遗民,也存在清入仕之士。清初松江士人利用咏史诗《五君咏》这一体裁,吟咏本郡名士,将晚明地方乡贤与易代之际的名士一起吟咏,以“文人”身份认同来逃避易代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偏见、道德上的臧否,以此消解自身对易代问题的焦虑。并且随着清政权对“忠”的提倡,士人的私怀与国家的赐谥逐渐纠葛在一起。清初士人的吟咏,一方面是对已故者的追思,以此解怀;另一方面则在评定同郡士人易代之际的表现时,重塑他们认可的地方乡贤,以确立一个重建秩序的规范,给自己的安身立命一个合理的诠释。由此整合与重朔易代之际的身份认同,为动荡的文化秩序提供一个稳定的观念性基础与支撑。而这种地方认同最终被国家所操纵,成为新王朝统治秩序的一部分。
易代;《五君咏》;士人;身份认同
明清易代打破了士人们原有的生存方式,故国不在,友人已逝,如何自处?面对“异族”与“异质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便成为明遗民之隐衷”①。即使对于“无数衣冠拜马前”,已入仕为清,成为清“顺民”的士人,也始终存在未死而生甚至入仕的愧疚,这已成为清初士人普遍的焦虑。如何在煎熬中寻求心理上的宽慰,正视易代,这是活着的士人势必面临的问题。
我们经常把目光投向王朝大背景下士人在易代之际出与处的身份选择②,而较少关注清初士人自身营造的身份认同。一方面在于刚经易代,士人对新政权还处在观望中,形势未明,何以自处难以决断,对于同乡、同僚的评判则更是难以取舍。另一方面在战乱与动荡中,能保全生命已属不易,更遑谈营造认同。朝代鼎革给地方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但松江从明清之际的兵燹中复甦之后,一直居于全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地位,使得当地士人尚有能力营造乡贤的崇拜。③清初在松江出现了《同郡五君咏》、《五君咏》,对易代之际的本郡士人进行吟咏,或许可以从中窥豹一斑。
《五君咏》最初为东晋南朝颜延之所创,对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进行了歌咏。竹林七贤本是优游清谈的玄学家,“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④。当时颜延之被贬为永嘉太守,“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⑤。五君在政治上皆不甚得意,颜延之借述五君以抒发自己的不平。故《五君咏》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是加入了吟咏者的主观判定,表现出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对于所咏对象是有所选择的,将其认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歌咏。后世受《五君咏》的影响,出现了很多咏史诗。鲍照《蜀四贤咏》、萧统《咏山涛王戎》、张说《五君咏》、高适《三君咏》、张居正《七贤吟》、杜浚《三君咏》等,都是规模颜诗的传体咏史作品。⑥自颜延之创《五君咏》后,这一咏史诗的体裁基本固定,主要歌咏历史人物,尤其是以竹林七贤为主,所咏对象为远离政治、具有竹林精神、注重个体的名士,“五君”形象逐渐程式化、符号化。
但有趣的是,到了清初,《五君咏》这种带有历史话题的咏史诗,却注入新的元素。吟咏的对象发生很大的变化,出现非竹林七贤的人物,对创作者曾相识甚至相知的本郡人士加以吟咏,并以《同郡五君咏》命名。清初顺治时期是士人较为迷茫的时期,一方面士人在追忆旧朝,另一方面又与新朝未完全融入。我们无法全部了解清初士人的世界,但从《同郡五君咏》所选择取舍的人物形象,大致可以判断出其价值的基本取向,从心理方面窥测时人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所认同的标准。并且这组诗并非出自政权的压力,收在文集中,纯属私人的悼怀,这可能更足以反映出其中所蕴含的意义。
一、逃避易代:顺治年间的《同郡五君咏》
清初《五君咏》注入了新的内容,并命名为《同郡五君咏》⑦,由松江人宋征舆所撰写。
《董尚书玄宰》(董其昌)
尚书学无生,早岁依哲匠,偃蹇卧玉堂,超然临濠想。子敬规遗章,恺之?幽赏,翰墨寄远纵,终焉却尘網。
《陈徴君仲醇》(陈继儒)
徴君岩壑才,隐约人间世,鸥舞朱门间,鹄举云中志。卫生守谷神,微言类卜筮,庶几季主伦,何为不居肆。
《夏考功彝仲》(夏允彝)
夏子守风概,泰华当衝河,抗此五尺躯,宁顾三军多。月旦垂汝南,离忧归泪罗,回风弭灵驾,吾将陈楚歌。
《陈给谏卧子》(陈子龙)
卧子诚不羁,其来每惊坐,零露期美人,云雷想王佐。慷慨北海尊,意气元龙队,一成薇蕨吟,清音邈难和。
《李内翰舒章》(李雯)
舒章好奇节,逢蒿自水矜,文王如可待,豪士仍特兴。吞舟徙江海,青冥辞弋矰,归为河梁别,苏李良可称。
宋征舆(1617-1667),字直方,一字辕文。宋氏为松江望族,先世为开封人,靖康之难南渡,迁到松江。入明科名鼎盛,到晚明宋征舆这一代时,已是“膏梁世族”,其家族的文学非常显赫。⑧宋征舆负雅才,工诗赋,诗以博赡见长,与从兄徵璧有大小宋之目,又与同里陈子龙、李雯并称“云间三子”。中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至御史中丞。⑨这一年宋征舆金榜题名,而友人陈子龙殉难,李雯抑郁而死。曾经叱咤文坛的云间三子,仅剩下宋征舆一人,如何悼念友人,又如何自处,这一直是宋征舆萦绕于怀的。
为何写《同郡五君咏》,据宋征舆自己的叙述,因为宋征舆曾受教于夏允彝、陈子龙、李雯,三人皆有文名,夏允彝长于简牍、陈子龙才气盛人、李雯书写自然。三君子又出自同里,为松江盛事。董其昌擅书画,陈继儒道德言论皆佳,二老均登高寿,宋征舆有幸都亲眼目睹。随后夏、陈遇国难,而李雯病逝,皆未益养终年。因此“用怀五君,仿延年之制”,表彰郡中先贤,并倡导郡中之人与他一起同赋。
五君中两位先贤董其昌、陈继儒,代表晚明士人的两种生活状态,“一显一隐”。董其昌万历进士,身为显宦,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擅长书画,身名俱保。⑩陈继儒二十九岁焚儒服,放弃生员的资格和身份,却能自如地周旋于山林与济世中,虽不为官却交游广泛,成为地方名士。(11)两位均以高寿而卒,得以给养天年。“崇祯初,礼部尚书董其昌、征君陈继儒为一代风流之冠”(12)。晚明,虽然国家制度松懈,政治黑暗,败亡日近,但松江地处一隅,没有受战火的侵扰,经济的繁荣,富足的生活,国家对地方控制的松弛,士人反而怡然自得,或显或隐,皆能优游足岁,并且名节俱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应是士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五君中三位友人经历了王朝鼎革,并且代表了易代之际士人的三种选择:
夏允彝选择了“死”,以身殉国。顺治二年(1645),松江城破,夏允彝拒绝清的劝降,作绝命词投松塘殉节而死。夏允彝“才致宏敞,海内文章领袖”(13),在松江几社中,无论在年龄还是资历上,都是长辈,享有为人师表的崇高声望,是当时高山仰止的人物。因而夏允彝的一言一行都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在“中兴杳然”,又不能事二主的情势下,惟有死为万世法。正是他在绝命词中所说的,要“修身俟命,欲励后人。”(14)夏允彝的投渊报国,乃是出于个人自主的选择与坚持,并非时势逼迫下的无奈之举,也不是一时意气所激,是一种非常高难度的道德实践。(15)
陈子龙先隐于山林,后投水而逝。陈子龙为几社名士,名重一时。明亡后,曾在南明谋事,受马阮结党排挤,回松江。(16)参加吴胜兆起义,失败后,因年迈的祖母尚在,隐姓埋名,着僧服居广富林。(17)后被清军捕获,投水自尽。陈子龙在明亡以后,从未间断过努力于中兴的大业,可以说是屡败屡起,以顽强不屈的意志从事复明运动,最后终于与夏允彝白首同归,实践了自己“顾成败则不计”的诺言。(18)
李雯则入仕新朝。作为云间三子之一的李雯,“以文望倾动士林”(19)。甲申李自成攻破京师,其父李逢甲殉国。随后清军进入京城,李雯为尽孝葬父,滞留在京师。由于文名,被龚鼎孳荐授为内阁中书舍人,“一时诏诰书檄,多出其手”。尤其是致史可法的檄文,最为著名。虽然做了官,但李雯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鼎革后的诗词“眷念平生,摧抑不堪卒读”(20),无不流露出强烈的故国之思和失节之恨。顺治四年(1647)陈子龙逝,这一年,李雯也忧伤憔悴以卒。
宋征舆吟咏的五君,皆以“文名”享誉松江,然而朝代更替却造成了他们在出处选择上的差异。宋征舆将夏允彝投水自沉,誉为“屈原”,宁死不屈,舍生取义;陈子龙不仕新朝,视为“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但曲高和寡,难容与世。对于李雯,则认为“文王如可待,豪士仍特兴”,如同姜子牙遇到周文王,如果恰逢明君,是可以出来为官。将身份出处的选择转化为是否遇到“明主”、“贤君”。既然苏武、李陵在异族下尚可生存,为尽孝道的陈子龙、李雯也是值得称道。易代时士人出处的身份选择都有它所存在的特定环境和理由。
无独有偶,松江府华亭县人周茂源也作了《同郡五君咏》(21),吟诵的还是这五君。
《董尚书玄宰》:
宗伯扬清晖,德劭身亦固,微言洞元始,云物丽旧□。龙见无常仪,凤举有恒度,乘石匪足荣,千龄宝缣素。
《陈徴君仲醇》:
徵君达者流,早岁谢尘鞅,东菑协耦耕,束帛非所尚。雅抱敦薄夫,清言亦沆瀁,磊磊白石间,海山存逸响。
《夏考功瑗公》:
夏子执亮节,荣名善自保,举身赴清渊,大勇存怀抱。虚室有遗经,扬乌乃速夭,我行昆山阴,西州起悲悼。
《陈黄门卧子》:
黄门好奇计,文采为国琛,骨鲠终见弃,离忧思难任。精卫穷木石,冲波一何深,九京不可作,同怀愧药簪。
《李舍人舒章》:
李生乃数奇,途穷每瞻顾,萧骚梁父吟,踯躅金门步。飘然返故丘,悲鸣恋俦伍,吹箎良有因,税冕更何慕。
周茂源虽未述其著《同郡五君咏》的缘由,但恐是与宋征舆相唱和,也盛赞董其昌年高德劭,陈继儒“海山存逸响”;夏允彝则“荣名善自保”;叹陈子龙,“文采为国琛,骨鲠终见弃”,有心用世,却不能施展;将李雯比作诸葛亮卧龙作梁父吟,期待明君以用世。
对于易代,想逃避不敢面对,却又无法回避。亲历易代的松江士人曹家驹就曾羡慕先贤董其昌、陈继儒不经朝代鼎革这一突然变故,不须经过其中的考量,“若使谢世稍迟,身逢鼎革,彼长枪大剑者,方将狎而侮之矣。真所谓来亦得时,去亦得时,第一有福人,亦第一凑巧人”(22)。没有朝代的变更,士人们皆可悠游足岁,这是士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生活状态。但朝代更替改变了这种状况,友人殉国,而自己却入仕为官,那么如何去看待士人出处的选择呢?宋征舆曾对于自己的行为做过辩解,他认为出处之道“非可尽责士也,时为之也”,是时代的变化导致士人出处态度的改变。(23)恰如晚明董其昌、陈继儒,可以一显一隐,悠游足岁。那么易代时,士人也可选择或殉道、或归隐、或入仕,每一种选择都可接受,君子“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宋征舆、周茂源将易代不同选择的士人与晚明名士一起吟咏,实际希望淡化易代所带来的政治归属的差异。
二、直面易代:康熙年间的《五君咏》
而稍后王鸿绪这位曾经参与《明史稿》撰写,对明朝人物烂熟于心的儒者官员,对本郡之士,也加以歌咏。
《陈黄门(子龙)》
给事天人姿,藻采何挺拔,响发必金声,弩末可穿札。遭乱登谏垣,颇为奸党轧,不作褚渊生,伤哉鸾翮铩。
《夏考功(允彝)》
考功本儒者,雅负经济才,厦倾嗟一木,沉渊乃自裁,哲兄泮林秀,蹈义何雍哉,更痛无完卵,千秋赋大哀。
《张少保(肯堂)》
少保始入台,谏草已谔谔,及秉入闽节,将骄主愈弱,度势不可为,全家泛大壑,仿佛厓山事,忠魂并寥廓。
《李舍人(待问)》
舍人工染翰,下笔迥有神,一官犹未达,顿际世运屯,王师数万至,溅血东城闉,亦知倒戈是,未敢遗君亲。
《徐孝廉(孚远)》
孝廉司寇裔,相国传簪缨,声华振兰錡,蔚然三代英,风尘猝澒洞,万里航蓬瀛,埋生鳄岛中,长逝无还情。
王鸿绪(1645-1723),字季友,号俨斋,又号横云山人,王广心幼子。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官至户部尚书。为人重文章,敦气谊。曾充任《明史》总裁官。(24)
王鸿绪的《五君咏》(25)保留三君夏允彝、陈子龙、李雯,舍弃明代先贤董其昌、陈继儒,增加了徐孚远、张肯堂。两君均是参与抗清的志士,一为名士,一为显宦。徐孚远为人通达,负救世之志,鼎革前,松江几社的社稿几乎都是由徐孚远主持,月旦亦多以其为宗师。鼎革后,松江城破,曾参与太湖义军,失败后,辗转东南沿海一带,跟随过唐王、鲁王、桂王三个南明政权,参加复明运动,至死方休。(26)张肯堂在明崇祯年间曾任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明亡后,曾跟随唐王政权,授为尚书。顺治十八年大兵破舟山城,肯堂衣蟒玉,南明向坐,从容赋诗自经死,妾周氏、方氏、毕氏,子妇沈氏、女茂漪同死。(27)
此五君均经历了朝代的鼎革,其中徐孚远逝世最晚,于康熙四年(1665)卒。王鸿绪作《五君咏》时当在康熙四年以后,此时离明清鼎革已有数十年,南明小政权均被平定,尘埃落定,复明的希望已全无,士人的选择至此可以清晰判定。王鸿绪并没有更多的去赞誉五君的“文”名,而是肯定他们的“经国济世才”以及道德气节。赞陈子龙经世之“才”,“响发必金声,弩末可穿札”,但是未遇治世,不能一展报负。赞夏允彝之“义”,视为儒者,雅负经济才,死得大义凛然,“哲兄泮林秀,蹈义何雍哉”。赞张肯堂之“忠”,将其与“厓山事”比拟,举家自沉,誉为“忠魂”。赞李雯之“孝”,为尽孝道,不得已出仕为官。赞徐孚远之百折不回之精神。“忠、孝、节、义”在五君中得以体现,五君的出处选择都蕴含了极深的道德气节。
王鸿绪生于顺治二年(1645),并未亲历朝代鼎革,也没有经历家破人亡的切肤之痛,王家的显赫反而是在清朝。王鸿绪的父亲王广心,鼎革之后,中顺治六年(1649)进士,走向仕途。王广心生有三子,长子王顼龄,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授太常博士,康熙十八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获一等第六名,补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次子王九龄,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官至左都御史。王氏“一家父子,四登科,三入词林,亦吾郡近来科名之最盛者”。(28)此时,清政权统治已稳定,康熙帝也以明朝继承者的身份出现,在历次南巡中,参谒孔庙,给各地学府颁发匾额,并一再亲诣明太祖陵祭祀、拜谒,以示对明太祖的赞许仰慕之情,并安抚明末遗民。在南巡时特别宣扬忠清朝的南人事迹,接见新进之士,以示优宠。王氏兄弟深得康熙宠幸,康熙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康熙帝两次巡幸松江,都临幸了王鸿绪的赐金园及兄长王顼龄的秀甲园,并赐御书匾额。(29)入清后成长起来的松江士人,在清笼络之下,逐渐树立对清政权的忠。
王鸿绪以存信史、辨兴衰、述往事、思来者为宗旨,摆脱易代因素的困扰,不受政治立场所左右,回归到士人的本来面目,给予士人身份以独立的评价。如认为五君中陈子龙“遭乱登谏垣,颇为奸党轧”,直述明代党争的现象及南明政权的权力争夺。南明“将骄主愈弱”,导致南明政权的覆亡,机锋直指昏君奸臣之误国。虽然张肯堂“度势不可为”,却仍以高度的道德气节以身殉国。王鸿绪的咏怀更为强调对于道德的践履以及对“忠”的肯定,而非强调反清复明的事业。
《五君咏》所咏五位均遭逢易代,有投降效忠之人、有奔走抗清之士、有百折不回之士、亦有无奈变节而又忏悔之人,将这些易代之际不同选择的士人放在五君的地位,不再彰显同郡,使得五君不仅在松江,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通过此举,对易代作出合理的解释,整合与重塑易代之际的身份认同,为动荡的文化秩序提供一个稳定的观念性基础与支撑,逐步构筑起整个社会的认同意识。这是人心与文化由动荡走向安定的关键一环。另一方面,在吟咏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自处之道和生存状态,本身就是秩序重整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这意味着士人找到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意味着包括清代秩序的逐渐稳定与成熟。易代在此不再是困挠士人的问题。
三、文人与国殇
从顺治年间到康熙年间,一直有《五君咏》的传颂,这种吟咏一方面为缅怀故人,另一面也为活着的士人树立一种典范。
除《同郡五君咏》外,宋征舆的文集里还保留了《云间五文人祠记》(30),希图对五君以“文人”的身份立祠以祀。宋征舆称以文人的方式来祭祀,为五君子的愿望,“夫五君子者与从事于翰墨者,举得至而致敬焉,宜五君子者之所许也”。入明以来,松江文风甚盛,至“崇祯之末,主持文教者,首推云间”,宋氏家族也是以“文学”享誉松江,(31)可能宋征舆希望借此举延续明末这种风气。宋征舆没有表达的另一层意思,可能也希望通过文人的身份,来弥补自己入仕新朝与友人已逝的鸿沟。
五君作为乡贤,本可祭于社(学宫之侧),但宋征舆认为乡贤祠“名美而实滥”,(32)恐有辱五君,“我惧夫五君子之避席也”,故另择一地。所选地为南郊张氏废圃,方圆十五亩,中有七亩池,上植有竹木,池之阴,有祠堂三楹,“高深相临,水木交错”,“深山大泽神灵之所棲托”,此圃“几近矣”。祠建成后,准备上书地方官(有司),揭为公所。园圃容易易主,若改为祠,则可常存。宋征舆欲托五君子之灵,常存此圃,实也希望此五人祠也能长存于郡。
《云间五文人祠记》作于顺治庚子十七年(1660)正月十五日,时距夏允彝殉国已十五年,两位友人陈子龙、李雯已逝十三年,元宵佳节时,宋征舆还在缅怀友人。七年以后(1667)宋征舆年仅五十岁卒。可见终其一生,友人在易代之际的死难始终萦绕于怀,无以排解。当夏允彝自沉以殉明,“名节俱保”时,宋征舆就被寄予后望。等夏允彝子夏完淳被捕入狱后,宋征舆却已科举登第,夏完淳讥讽他为“裘马客”(33),想必宋征舆背负了不少骂名。宋征舆虽未提夏完淳,可见也是愧对晚生,倒是周茂源在吟诵时加入了夏完淳,“虚室有遗经,扬乌乃速夭”。虽然宋征舆曾辩解“归为河梁别,苏李良可称”,但是同郡名士杜登春却咏到:“大樽既永诀,宋公登天衢。河梁苏李交,五言非同途”(34),极尽嘲讽。吴伟业把陈子龙、宋征舆比做魏晋的嵇康和山涛,他说:“大樽即前死,舒章得一官,又不究其用。直方乃以名位大发闻于时,既跻显要,进卿贰,为天子之大臣矣,复不幸早没……士君子处于抢攘之际,其生而同心,死而相恤,百世而下,未有及山巨源之于嵇中散也。今以观吾直方,何其类巨源之风乎!”(35)吴伟业把他比做山涛,未免有些抬高。大概吴伟业也应了清廷的召,借古人替宋征舆开脱,也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但这可能也恰好道出了宋征舆《同郡五君咏》的弦外之意,自己的境地恰似那排在七贤之外的山涛,虽非“五君”,但为“七贤”,还是在名士中,以此解脱。
周茂源与宋征舆一样,与陈子龙、李雯等相善。鼎革后,中顺治二年(1645)举人,与宋征舆为同榜举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授刑部主事,擢郎中,官浙江处州知府。(36)友人已故,而自己应了清朝的召,虽入仕但内心又有煎熬。周茂源受到奏销案的影响,落职回到松江,不久便归田,常与僧道之人相交往。周茂源虽然落职归田,但是已没有了晚明士人悠游隐逸的环境。清政府虽然屡开科举以笼络江南士人,同时又兴哭庙案、科场案,怀柔与迫害相结合,士人或隐或仕都不甚得意。“萧条卧北楼,寒雨逼帘钩。纵有登高赋,还添去国愁。饮冰差共信,熏穴竟谁求。远愧陶彭泽,家园得自由”,黍离之悲与身世之感黯然流露。(37)
明亡之后,书写“故明之思、明亡之恨”成为当时一般文人的普遍精神取向,而决不仅仅限于那些遗老遗少,甚至在那些失节投降者那里,也可以读到似乎更为深切而动人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恨。显然,书写者的政治态度和处世观并不能完全决定其文字表述的情感取向,在这里,共同的审美思维和感受使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截然不同的文人,有着几乎一致的人生体验并都可以转化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文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内部的那些失节分子,可以表示出有限的宽容乃至理解。(38)易代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是那些从旧政权而来的人如何面对新政权。忠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伦理规范之一,无疑就成为考验人心动向的一个敏感问题。一方面忠的规范要遵守,这就要求不能明确或公开地站在明朝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势的发展要面对,这就要求对新政权的态度要灵活变通。也就是说,需要一种处世的办法,使得易代之际的人们可以打破矛盾处境,消解由易代所带来的思想与情感焦虑。
采取的办法是问题置换,即通过对明代地方乡贤与易代之际的地方名士一起吟咏。对这五君而言,其成就最高者当然还推文名,甚至夏完淳虽年幼但也是文名甚高。在松江社会,能跨越易代,为士人所普遍接受、甚至效仿的,还是文名出众的士人,故立“文人”祠以祀,来超越易代。
如果说《同郡五郡咏》更多的还是文人为文人歌,那么到王鸿绪的《五君咏》则更为强调易代之际死难者的道德伦理,有君臣之义、还有父子之情。王鸿绪作《五君咏》时,离易代时的动荡已有若干年,宋征舆也已逝。王鸿绪在《挽中丞宋直方先生》中咏到:“兰台风赋旧知名,执法光沉返苧城,白马素车惟故友,寒烟细雨又清明,顿令七子芳华歇,相继三君宿草平,泉路若还逢仲举,衣冠今古两含情。”(39)作为同入仕清朝的士人,对宋征舆还是抱有了解及同情。他自己在康熙时官位显赫,已无宋征舆、周茂源内心的彷徨,可以坦然为官,因而能正视易代,坦然对易代之士进行悼怀。并且随着清政权的稳定,入清以后成长的松江士人,已经自觉的加入到清的“忠”的观念中。松江士人叶映榴,顺治十八年进士,于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任湖广粮储道、暂摄布政使时,遇武昌兵变,不屈自刎。康熙皇帝获悉叶映榴的死讯后,特封工部右侍郎衔给予祭葬。次年南巡,又亲书“忠节”匾赐其家,以表彰其对朝廷的“忠”。(40)
康熙二十二年(1683)创修、乾隆元年成书的《江南通志》中,董其昌、陈继儒、夏允彝、陈子龙、徐孚远、李雯、宋征舆均列在“文苑”中(41),只有张肯堂列在“忠节”(42),陈继儒未归入“隐逸”。王鸿绪的父亲王广心参与编纂了《江南通志》(43),王广心等人还是遵循了宋征舆、周茂源等人的看法,仍是把他们视为“文人”,只有张肯堂为“忠节”。而顺治二年请修,至乾隆四年成书的《明史》,董其昌列在“文苑”,陈继儒归在“隐逸”。张肯堂、陈子龙、夏允彝专列传,而徐孚远附其后。至清朝乾隆四十一年奉敕撰《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对于易代之际的松江名士,专谥诸臣有:陈子龙“学问淹通,猷为练达,贞心可谅,大节无亏”,谥“忠裕”;张肯堂“大义能明,忠谋素蕴,崎岖渡海,慷慨捐生”,谥“忠穆”;(44)夏允彝则列在通谥忠节诸臣中(45)。对忠臣的表彰,更多的强调的是忠节。随着对“忠”的强化,故《明史》及《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均将李雯排除其外。《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对“忠孝节义的评价”直承《明史》,而《明史》则以王鸿绪删定的《明史稿》为基础,王鸿绪个人的私怀与国祀逐渐契合。
徐孚远逝世后,徐孚远的弟子李延昰,曾将其师与陈子龙、夏允彝并提,而李雯则不提,“徐孝廉孚远、夏考功允彝、陈黄门子龙各言其志,孝廉慨然流涕曰:百折不回,死而后已。考功曰:吾仅安于无用,守其不夺。黄门曰:吾无闇公之才,而志则过于彝仲,顾成败则不计也。终各如其言。”(46)陈、夏逐渐成为文人与国殇的完美结合,进而也成为地方士人私怀和国谥统一的象征。“国朝定鼎容顽民,吾乡抗节夏与陈”。(47)地方士人的私怀与国家的赐谥,最终纠葛在一起,成为新王朝统一的新秩序。
四、结语
对于朝代更替,陈寅恪先生曾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言论: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新旧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48)
清初士人的吟咏,一方面是对已故者的追思,以此解怀;另一方面则在评定同郡士人易代之际的表现时,重塑他们认可的地方乡贤,以确立一个重建秩序的规范,为自己安身立命得一个合理的诠释。能贯穿调和两代之间差异的还是“文人”身份,以“文人”身份认同来代替政治上的偏见、道德上的臧否。同时以文人身份自处,希望身后仍当以文人来论,以避免政治归属上的定性,弥补与已逝友人的鸿沟。通过对明代地方乡贤与易代之际的地方名士一起吟咏,将忠的内涵和践行方式丰富化与多样化,从而将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转换为文人之间的学术和文化问题,运用自己熟悉的文化方式和包容的态度,有效地消解自身对易代问题的焦虑。
宋征舆虽然借《同郡五君咏》使自己作为一个文人仍能安身立命,但他年仅五十岁而逝,终其一生还是活在自责中。故吴伟业希望身后以“诗人吴梅村”自居(49),也是要模糊易代所带来的政治归属的差异性。
穿越历史的《五君咏》被同郡士人所认同,所以继宋征舆、周茂源后,又有王鸿绪,加以吟咏。康熙时期,政权已稳定,易代的纷扰至此已尘埃落定,故王鸿绪可以直面易代,直抒胸意,并且作为《明史》的总裁官,他个人的私怀实际上与官方话语某种程度下得以契合。如果说“五君”中,张肯堂的加入,代表了忠臣名宦,那么陈子龙、夏允彝则是文人与气节的完美结合,所以后世再提易代之际的松江士人形象必提陈、夏。而随着清朝对忠臣表彰的确立,入仕新朝的李雯则逐渐淡出。
在社会变动时期,原有的社会理念并不重要,如何做能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才是士人真正关心的事情。而这种地方认同最终被国家所操纵,成为新王朝统治秩序的一部分。
注释
①孔定芳:《清初明遗民的身份认同与意义寻求》,《历史档案》2006年第2期。
②有关明清之际士人研究代表性著作: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孔定芳:《清初遗民社会》,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15)孙慧敏:《书写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节故事的形成与流传》,《台大历史学报》第26期,1990年。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8《魏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⑤《宋书》卷73《颜延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⑥于溯:《略论颜延之〈五君咏〉对早期咏史诗的变革》,《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⑦宋征舆:《林屋文稿》卷4《同郡五君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5册),第496-497页。
⑧(31)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1页,第228页。
⑨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16《宋征舆传》。
⑩《明史》卷288《董其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1)《明史》卷298《陈继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2)徐枋《居易堂集》卷12《杨无补传》,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04册),第238页。
(13)查继佐:《国寿录:行取知县夏公传》。见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107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63页。
(14)陈田:《明诗纪事·辛籤》卷5《夏允彝》。见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第15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481页;杨泽君:《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晚明几社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2年5月。
(16)宋征舆《林屋文稿》卷8《於陵孟公传》,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5册),第334页。
(17)李雯:《蓼斋后集》卷2《初春四日与张郡伯冷石、陈黄门大樽小饮柯上人息庵,时两君已受僧具矣》,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1册),第666-667页。
(18)(46)李延昰:《南吴旧话录》(瓜蒂庵明清掌故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19)(28)叶梦珠:《阅世编》卷5《门祚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0)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4《李雯》,见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第20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498页。
(21)周茂源:《鹤静堂集》卷1《同郡五君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9册),第3-4页。
(22)曹家驹:《说梦》,《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12册),第265页。
(23)宋征舆:《林屋文稿》卷16《报曹鲁元书》,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5册),第438页。
(24)嘉庆《松江府志》卷57《王鸿绪传》。
(25)王鸿绪:《横云山人集·山晖集》卷4《五君咏》,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16册),第649页。
(26)有关徐孚远的生平,可参考陈乃乾、陈洙编《明徐闇公先生孚远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
(27)(44)《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1,见《四库全书》(第456册),第412-413页。
(29)王鸿绪《横云山人集》卷22《乙酉三月二十九日,圣驾幸臣小园,赐松竹匾额并对联二幅,御制诗扇一柄,时臣鸿绪在京遥受恩荣,喜溢望外,恭纪八首》,卷23《丁亥三月二十五日驾幸,臣鸿绪赐金园恭纪八首》,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17册)。王项龄:《世恩堂集》卷23《康熙四十六年春二月,圣驾阅河南巡;三月二十四日驻跸松江,二十五日幸臣项龄秀甲园》,见《四库存目丛书补编》(第5册)。
(30)宋征舆:《林屋文稿》卷7《云间五文人祠记》,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5册),第331页。
(32)对于乡贤祠“名美实滥”,松江人董含也提到:“士大夫有功于国,有德于桑梓,殁而祀诸瞽宗,礼也。迩来乡贤一路,竟为藏垢纳污之地,真有不敢言、不忍言者。犹忆明罗念庵、郑淡泉两先生,望重朝野,父皆耆儒,后见滥觞,不忍父混列其间,各抱其主以归。闻二公之风,可以愧矣。”董含:《三冈识略》卷10《乡贤祠滥觞》,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29册),第776页。
(33)白坚笺校:《夏完淳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夏完淳《毘陵遇辕文》:“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灑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1647年七月被执押解途中作)。此书第95页还载,夏允彝有《练川五哀诗》,哀《侯峒曾、黄淳耀、张锡眉、侯玄演、侯玄洁》,完淳效之,有《六哀》,哀《徐石麒、侯峒曾、黄蜚、吴志葵、鲁之玙及允彝》,皆共举义师者;又有《六君咏》,赞《史可法、黄道周、刘宗周、徐汧、金声、祁彪佳》,皆负天下重望而先后殉国者。郭沫若认为“六哀亲亲,六君尊尊”。夏氏父子以忠节终,故吟咏对象都为殉国者,与宋征舆志趣大异。
(34)杜登春:《尺五楼诗集》,转引自白坚笺校:《夏完淳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
(35)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28《宋直方林屋诗草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72页。
(36)嘉庆《松江府志》卷57《周茂源传》。
(37)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0-111页。
(38)刘克敌:《从〈柳如是别传〉看明清易代之际江南文人风貌》,《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39)王鸿绪:《横云山人集·山晖集》卷2《挽中丞宋直方先生》,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6册),第633页。
(40)叶映榴:《叶忠节公遗稿》,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32册),第284页。
(41)乾隆《江南通志》卷166《文苑》。
(42)乾隆《江南通志》卷153《忠节》。
(43)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1页。
(45)《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3,见《四库全书》(第456册)。
(47)夏完淳:《夏节愍公全集》卷末《题辞》,转引自孙慧敏:《书写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节故事的形成与流传》,载《台大历史学报》第26期,1990年。
(48)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5页。
(49)吴伟业临终时,“自叙事略曰: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殓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 ‘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见吴伟业:《吴梅村全集》附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06页)
责任编辑梅莉
2010-02-2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
“变动时期地方秩序的重整:以明末清初的江南为中心考察”(08JC770007);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群体与社会变迁——多学科视域下的前近代社会群体研究”(CCNU09C02004)
——松江二中(集团)初级中学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