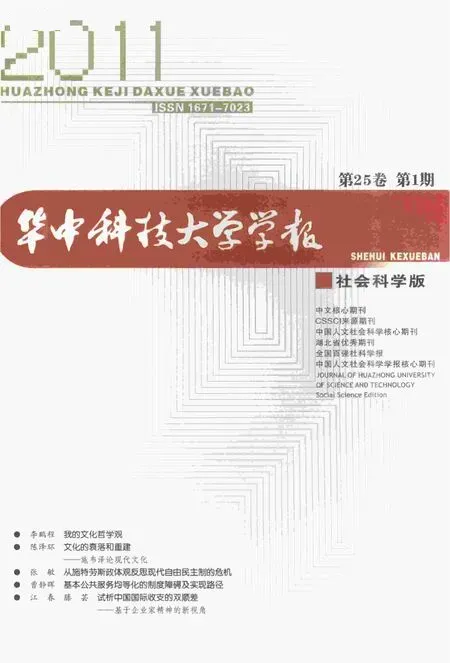回顾、反思与重构:近百年来中国社区研究
崔应令,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 430072
回顾、反思与重构:近百年来中国社区研究
崔应令,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 430072
社区研究有社会学和人类学两种传统: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在文明社会内部进行个案调查,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在异文化社会中研究封闭社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中国的社区研究同时在这两种传统的影响下得到确定和应用。人类学传统的社区研究在中国遭遇“代表性”的质疑,这导致了两种回应结果:一是通过将社区与国家、大社会的时空结合,丰富并拓展了人类学社区研究的内涵。二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在反思过程中,既肯定社区作为完整个案本身的人类学意义,又提出从社区个案到区域类型再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扩展社区的社会学研究思路。对社区与外界联系的强调既是学术本身内在的发展逻辑所致,也是一代学人重建国家、社会的责任感的体现。未来的社区研究要承袭此前将社区与外界联系起来的研究脉络,但更应该重视社区作为一个独特世界所具有的地方性意义和对多元社会文化所具有的贡献,这是新时期学术与时代共同赋予的主题。
社区研究;国家;社会
一、社区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传统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区研究有来自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两种传统。
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是对文明社会内部的个案研究,它从一开始就强调单个社区与文明社会的联系,其开创源自美国芝加哥学派。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社会学者们展开了对人文区位、人口、种族、邻里关系、贫民窟、犯罪等问题的社会调查。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人积极的关注城市社区,提倡通过参与观察法展开对城市社区的调查活动,1926年,帕克出版他的《都市社区》一书,奠定了社会学领域社区研究的基本理念。沃斯的《贫民区》(1928)、左布夫的《黄金海岸和贫民区》(1929)、路易斯·沃斯的《城市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1938)也是芝加哥社区研究的代表性作品。此后学者们又将社会学的理论引入到社区研究之中,丰富、发展了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传统。1958年桑德斯在《社区论》一书中提出社区研究三种模式:社会体系论、社会冲突论、社会场域论,三种模式都是将社会学流行理论应用到社区研究中的体现[1]。
严格来说,人类学并没有直接用社区这个概念,但学界一般认为以马林诺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的作品代表了人类学的社区研究传统。在人类学的社区理念中,社区因其相对封闭性而具有了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它重视的不是其与外界的联系,而是其自身的特点。同时它关注的不是文明社会内部的社区,而是非西方社会中的土著部落。其成果多建立在对“原始”部落与小型社区进行参与观察的基础之上。马林诺斯基通过对特罗布里恩德岛的考察,完成其关于此地库拉交换、性生活等一系列现象的研究。布朗的《安达曼岛人》[2],普里查德的《努尔人》[3]和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4],都是功能主义民族志作品。
功能主义社区研究的特点是强调整体性,这种整体是指功能整体,正如马氏所说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而对每一方面“取得的一致性、法则与秩序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5]8。在社区整体结构中,亲属制度、经济生产、政治制度、巫术、神话、宗族仪式等各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的,把具体问题放到整体社会中才能真正认识此问题,这是功能主义社区研究的基本要义。功能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布朗也曾明确指出社区研究的功能整体视角:“一个特殊社区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系密切地相互关联着,或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或体系中的各部分。……任何活动的功能,任何风俗和信仰的功能,就是把社区看作一个统一的体系,来定它在这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6]181-182功能主义对社区研究的开创性阐释直接决定了后来对于社区研究特点的认识:“整体的眼光、参与观察的方法与相对较小的地域范围”[7],社区研究就是“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研究方法[8]91-92。这一思路在西方人类学界持续发展并产生影响,成为之后的研究者基本认可的一种研究取向,解释学派、后现代民族志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批判和反思功能主义民族志的科学性,他们依然大部分坚持这种社区取向的田野调查。
中国的社区研究同时在社会学与人类学这两种传统的影响下得到确定和应用。它直接受惠于吴文藻先生对社会学学科的指导方针:“请进来”和“送出去”。前者主要是指访问中国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和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 -布朗。后者则是指吴文藻先生将学生送往英美等国系统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知识,并最终因学生在国外所学的理念而影响到之后的社区研究,代表性人物则是费孝通先生。
1931-1932年帕克在来华采访期间,指导了燕京大学学生及老师如何进行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他鼓励学生到户外去研究北京的城市生活,这启发了中国人类学者[9]55。而就在 1935年,布朗也来华讲学,社区研究范式自此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整整一代学人。布朗在发表于《社会学界》第 9卷名为《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足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6]182-183他说的乡村,显然不是抽象意义上与都市相对应的农村,而应该说是单个的村庄更为贴切。在此文中他还详细的指明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三方面:横的共时性结构研究、社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研究、纵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动态关系的变迁研究。
就在两位社区研究的领军人物访华后不久,吴文藻先生开始阐述他的社区研究认识。在 1935年至 1936年间,他曾多次撰文阐述社区研究的意义与相关理论和方法[10][11][12]。后来又在给费孝通与王同惠合著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作序时专门择要介绍他的社区研究相关学说[13]。他还培养和推动了一大批学生从事社区研究:在他的指导或安排下,燕京大学的很多青年社会学者都开始了积极的社区调查活动。比如林耀华于 1934-1937年间在燕大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期间回老家做调查,后来写成了《金翼》[14];燕大毕业生蒋旨昂 1940-1941年间在四川重庆调查了两个乡,完成《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15]一书。此外,还有费孝通与张子毅合作完成的云南三村的调查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16]。杨懋春对山东台头村的研究,许烺光对喜州的调查、李安宅、杨庆堃、李有义等人的调查等等。在 20世纪 30-40年代,中国人类学者们的社区调研成果蔚为大观,为世界所瞩目,并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传统。潘乃谷后来总结道:“社区研究在当时被认为是这个学派的特色。在社会学学科里可以说是偏于应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社会的一派,在社会人类学里可以说是偏于以现代微型社区为研究对象的一派,即马林诺斯基称之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17]53。
从吴文藻先生对社区的阐述以及其后辈们的实际研究来看,中国的社区研究同时融合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两个传统,有的研究本文化所在的汉族社区,有的研究异文化的少数民族社区。有的重视社区与中国社会的联系,有的则强调孤立社区的解释力。有时则是连研究者自己都弄不清楚究竟是人类学的传统还是社会学的传统,从一开始,这两个传统就是模糊难辨,互相影响的。
二、汉学人类学对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法的质疑
中国社区研究两种传统模糊不分的状况因为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18]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而在外界看来更倾向于人类学的研究传统。这一本中国社区研究的代表性作品,通过对开弦弓村从政治到家庭到经济到仪式全方面探讨,作者完成了对小型社区的全方位功能主义考察。也正是《江村经济》引起的巨大反响,直接催生了学界对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在中国可行性和有效性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声音来自人类学内部。
问题由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提出。1962年,在题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一文中,他指出,中国社会是“有历史的文明社会”,它与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原始部落存在根本的不同。在这样的复杂社会里,社区不是社会的简单缩影,功能的整体分析不足以反映其整体社会事实和特点[19]。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所引以自豪的对某种社会文化整体性的分析无法达成,自然,这一方法本身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也被广泛质疑。弗里德曼强调,在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必须要借鉴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和成果,走出社区,在较广阔的空间跨度和深远的时间深度探讨社会运作机制。他同时提出已有社区研究在与大社会的空间及时间联系上的缺失。
如果说弗里德曼还只是指出中国社区研究存在的问题,则在他之后的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干脆就否定了中国的社区研究。他用他1949-1950年间在四川实地调查的资料写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系列论文,于1964-1965年间发表。他指出,村庄 (社区)根本就不是中国社会的单位,因为农民的生活圈是由基层市场的范围决定的: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20]40而英国人类学家埃蒙德·利奇又着重从社区与国家的关系的角度继续否定了以往中国社区研究作品的典型性,在 1982年出版的《社会人类学》一书中他提出“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他本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说“费 (即费孝通)虽称他那本书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他并不冒称他所描述的社会体系是整个国家的典型。……这种研究并不或不应当自称是任何个别事物的典型”①利奇语,转引自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载《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3、25页)。。
来自弗里德曼的质疑最终导致了对社区研究的反思与推进,从某种层面来看,这种质疑其实是针对人类学功能主义式的社区研究传统,它揭示了传统人类学研究的某些局限,而并非说明了中国社区研究的真实现状。在两种传统影响下的中国社区研究,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抛开社区与国家、大社会的历史性、社会性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还处于不自觉的应用之中。比如林耀华的《金翼》,就对村庄家族的命运与国家、时代的命运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作出了说明,但从方法上作者却并没有自觉的对社区研究做出深入说明。无论怎样,因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中断,来自异国的质疑直接统领了学科的话语权,国外对于社区研究的反思所提出的问题也直接成为国内学科重建时中国学界直面的问题,促使国内对社区研究的使用走向自觉与反思。
三、被拓展的社区与作为个案的社区
对弗里德曼的回应同时催生了两种现象:一是功能主义社区研究的含义得到拓展,二是社区研究被当做个案,作为其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前者由一些汉学家完成,后者则来自费孝通先生在新时代下对于种种质疑的回应。
(一)对功能主义社区研究从学理和实际操作上的拓展
一些汉学人类学研究者试图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之下重新研究社区,他们本质上并不将社区当作孤立的独特的存在,而是把社区放置于更广大的时空网络之中进行考察,并由此扩展了社区研究的内涵。
其一,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分析社区的地方性及所具有的整体社会共同性特征。这种论点受吉登斯 1985年出版的《民族 -国家与暴力》[21]观念的影响,他认为民族 -国家的成长史是以社区内部的人民不断地被从地方性的制约“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它区别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对地方社会的直接侵入。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国家权力无处不在,地方性社区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地方社会,而是整个国家之下的地方,具有整体社会的共性特征。现代国家建立后,民族国家与社会是高度融合的,地方性知识虽然常常别具特点,但它实际上又蕴藏了整体社会的东西,因此,即使不能说村庄代表了整个社会,通过它也至少可以窥视到社会的部分特征。地方社会在民族国家制约之下的特点恰好可以揭示国家力量与地方文化复杂的互动,于我们的研究有积极的价值。这一认识对现代国家建立后的中国尤其是适合的,为很多学者所接受。这成为汉学者们对社区研究价值的肯定的理由,“国家 -社会”成为汉学界对社区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
其二,将共时性的社区结构研究与历史性探讨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关注小社区的历史,也关注更大的社会环境的历史,将传统与现代同时纳入对社区的考察视野中。将弗里德曼所说的历史性引入到了社区研究中,从此社区研究本身的意义得到扩展,即社区研究的整体性不仅仅是共时结构的整体,更是包括传统和现代的历史整体。自此中国的社区研究开始强调一种“传统 -现代”的分析框架,力图在“小地方”的社会场域中涵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社区研究从单纯的共时结构走向与历史的结合,这是研究者们对社区研究本身的推进。代表著作有《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农民社区的现代史》(1984)、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桑格瑞(P.Steven Sangren)《一个汉人社区的历史与魔法》(1987)和马德生:《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与权力》(1984)等等。
当然很多作品同时包含这两种视角,真正的完成了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要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应用到社区研究的思路。当代的一些作品多半同时包含了以上两种路径:即在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看社区与国家的关系,社区的发展与变化。比如于建嵘的《岳村政治》[22]、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23],等等。
(二)作为个案的社区:两种思维下的两种认识
对社区研究的内涵进行拓展是人类学界学术上的自我发展,其话语还在人类学内部。而当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经历三十年沉寂恢复重建以后,费孝通重新回应来自利奇的批评时,他在两种思维下对社区研究做出了重新认识。
第一种是以利奇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认为个案的意义在于找出人文世界的共相,在于理论上的对话和思考。
利奇说:“费著的优点在于他的功能主义风格。与社会人类学者的所有优秀作品一样,它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关系网络如何在一个单一的小型社区运作的细致研究。这种研究没有,或者不应自称代表人和意义上的典型。它们也不是为了证明某种一般的论点和假设的。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本身。虽然这种作品以小范围的人类行动为焦点,但是它们所能告诉我们的是有关人类学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其内容远比称为‘文化人类学导论’的普遍教育丰富博大。”[24]而费孝通本人也曾据此对《江村经济》研究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从村落社会入手只能观察到全村几十户人家。这能说得上是个整体么?中国农民何止这几十家人。我所观察到的连中国农民的几十万分之一都不到,离开中国农民的整体太远了。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却可以说是个整体。那就是说这些农村的居民生活在这个社区的人文世界里,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人文世界却是个整体,因为它满足了这个村子居民的全部生活。它包括了马老师所讲的文化的诸方面和所有的社会制度。这些方面和这些制度又是密切地有机联系成的一个体系。我们在这几本书里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生活在其中的具有整体性的人文世界。
……社会人类学所要求的就是解剖一个文化的整体。江村经济描绘出了一个各部分复合的经济体系,可以说满足了整体观点的要求。……社会人类学就是要把人文世界从对个别的观察里把共相说出来。……各个民族文化尽管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有了本质上的一致才能比较,才能沟通,最后才能融合。[25]140
社区研究对人文世界共相的概括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类行为的一般特点,提供一种对人类文化与行动认知的基础。从这个层面出发,支持社区研究的学者认为,村庄研究本不是为了代表社会,而是“为了通过个案的验证 (case test)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流行观念加以评论和反思”[26]。或者说,个案研究仅仅是要为理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案例,如吴毅的《小镇喧嚣》[27]。
如果费先生对社区作为个案的认识仅仅到此就结束了,那么在人类学学术话语下,他已经不用再对利奇批评他的《江村经济》只是个案,而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做出回应,利奇本人也已经代他做出了回答。然而,他继续前行了,于是有了对社区作为个案研究意义的另一种诠释。
第二种是费孝通先生进一步的回应策略:社区研究只是开始的第一步,是基础,经由它,我们要找到类型或模式,最终了解大中国社会。
他指出江村的调查只是他调查中国农村的开始,他后来提出了“类型”的概念,他认为江村虽然不能代表中国,但江村毕竟是中国农村一隅,它可以在某些方面代表中国的一些农村,也许它构成了某一种类型,而通过各种不同农村类型的比较,我们是可以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比如江村和云南内地农村就有区别。而事实上,费孝通先生正是将中国几十万个农村划分为各种模式,以适应整体中国农村研究的需要,他认为这是对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论的充实。这是他 20世纪 40年代在云南所进行的农村调查中捉摸到的研究方法,后来他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推广到了全国各省的农村调查,并将调查的脚步从中国的沿海带到中部再到西部,以此试图完成他“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并证明“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28]26结论。当代一些学者对社区研究的再肯定有的继续沿着费孝通的路径前行,比如华中学者贺雪峰在其博士论文《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就讨论了“由个案调查上升到区域比较,及如何由村庄类型研究上升到区域比较研究途径”[29]。
这种从个案到区域类型再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扩展模式,某种意义上是将社区与外部环境之间横向的关系联系起来,是进行结构要素的一般性特点的归纳与综合,期待逐步扩大研究单位:“乡村只是使用社区研究法的第一步,在理想中,社区研究法不仅可以应用于村庄,而且可以应用于县、省,乃至整个中国。”[30]这样的分析思路是将社区研究作为最基础性的工作,社区研究的意义不在其自身,而在其对于类型提供的素材。
至此,费孝通先生对社区研究的认识从人类学的思维范畴走到了社会学的话语之中,某种意义上,他将社区作为研究“类型”的基础,也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基础工作,对社区研究自身原有的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的意义进行了降级处理,自此,社区研究只是作为一种基础性前提工作,其本身不再是目的。通过这第二种回应,费先生将自己陷于混乱之中。
四、学术情结与国家意识:强调社区与大社会联系的原因解读
无论是将历史和国家视角纳入社区研究之中的做法,还是费孝通从个案扩展到区域类型再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思考路径,都是试图找寻社区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他们共同的关注点是社区研究作为时空网络中的点所具备的意义,强调社区与外界的联系性,重视的是社区研究对中国社会认识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思路要么在意的是用社区证实或证伪当前流行的理论,要么在意社区与周边环境的互动过程和变迁,无论是回到社区还是扩展社区的内涵其目的都不是单独的社区本身,而在社区之外。社区的特殊性或地方性是作为与外界的关系的意义而存在的,而不是其本身具备的意义。
当然在所有强调社区与大社会的联系时,不同的学者其根本出发点是不同的。回应弗里德曼宗族理论的很多学者都重新回到村庄做研究,这是一种学理上的取向,其目的是为了理论本身的推进。比如巴博德就对弗里德曼的“边陲社区论提出质疑,并在 1964-1969年之间到台湾屏东和台南两个社区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最终得出了与弗里德曼不同的结论”①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68-71页)。。这是一种学术情结,是对学术理论本身的发展与延伸思考。
而对于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学人而言,强调社区与中国大社会的联系并不单是为了适应这种学术场域的规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时代的使命感和作为中国人的责任感。这种差异从社区研究在中国诞生之初就已经呈现: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相互影响,互相融合;对社区独立性的研究,又无时不在的试图从中认识中国社会的努力是几乎所有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者所做的事情。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情结必须要让位于国家重建的使命:救亡图存,振兴国家,富裕人民。这是自 1840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主题,从曾国藩面对赵烈文 1867年预言这个国家“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时长叹“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31]4,5的悲叹,到戊戌君子的以身殉变革;从以严复为代表的学者翻译西学到“师从日本”、“以敌为师”,大量翻译并介绍转引自日本的西学;从辛亥革命掀起的武力救国浪潮到民主人士各种改良之策,这一代知识分子两肩不仅仅担当着道义,还扛起了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社区是一种他们认为可以了解中国的良方,故而在日本轰炸的命且不保的年代,令世界人类学、社会学界难以置信的中国学界涌出大量的经典调查之作,造就了当时世界学界一大奇观。
这种时代主题促使费孝通等人的社区研究一定要与了解中国社会并为之做一点什么相联系,他从学医转向学社会学,其目的正在于此。1993年,近过七十的费孝通这样说:“我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体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于是我改学社会学。学一门学科总是有个目的。我是想通过学社会学来认识社会,然后改革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我这一生的经历中根本的目的并没有动摇,就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年到七十了时,我还是本着‘志在富民’的目标,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到实地去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的少数民族,凡是贫困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富起来。”[32]10-11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以致用”的思想情怀在国家危难之时在费孝通等人身上得以深刻体现。乡村工业化、小城镇理论的提出无不是在对社区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探索性途径。
也正是这种意识,使得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从开始到现在始终是纠缠不清的,既然都是为了了解中国社会,严格区分两种传统和话语的相异自然不是重点,且有时融合,有时分离,有时用社会学的方式回应人类学的质问,有时错把西方人类学世界的问题当成了中国人类学界的问题等等。这便是学习社会学又学人类学的费孝通先生自己对社区研究价值的思考上互相冲突的原因所在。
五、重构一个“分离的世界”:新时代社区研究主题
如果说强调社区和中国大社会的时空联系既是学术内在拓展的需要,更是时代赋予那一代中国学人的责任和重担所造就的,那么今天中国学人所面对的时代主题已经变了。中国已经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站立起来,国家开始复兴,人民开始富裕,当世界都在以一种新的眼光思考“中国模式”所具有的启示时,我们需要重新开始关注统一国家内部所具有的多样性,重新思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地方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这将为我们找寻内部的多元性提供契机。这既是对社区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学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思考,同样也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和主题。
而事实上,任何一个社区都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场域”,有其内部的结构和资源分配、有其自身的权力关系和角色扮演,因此仅仅将某一社区放在“环境”、“上下文”、或“社会背景”下分析其“同构性”是不够的,因为其内部采取了“完全特殊的形式”。社区作为“一个独特而分离的世界”[33]11所具有的研究意义,犹如民俗中的“标志性文化”,它“深刻地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体现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生命力”,且“能反映这一地方的特殊历史进程和贡献”[34]。社区的特殊性和地方集体性格的整合性,促使对每一个具体社区的关注都具有了独特和地方整合之双重含义。作为一个地方社会的小型集合体,社区既作为整体国家之下的个体而存在,也作为地方社会的小集体而存在。
我们重新肯定社区独立性、分离性、整体性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回到人类学功能主义的孤立社区研究中,而是强调在复杂时空网络中个别社区所具有的特殊性。我们并不否定对社区的研究应该关注其与国家、与传统的联系(事实上已有的研究都是这么做的),而是要在这种联系的背景下思考:社区何以特殊?其起源在哪里?其特殊的形式体现在何处?为何会特殊?具体来说,重新强调社区独立性、特殊性所具有的意义出于以下的思考。
其一,在国家无所不在侵入社会,在全球化、市场、都市化、工业化无不影响到社区的大背景下,对社区以特殊的关注有助于我们进行更大的理论思考,这种理论不完全是人类学流行理论(如利奇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辩护),更重要的是当前更宏大的理论思考,包括对各种宏大话语进行反思。
其二,从实践上说,我们已经走进一个应该开发多元、保护多元、找寻我们国家发展的内在生命力和多样的地方形态的时代里,不同社区内在的发展状况、发展模式、文化事项的独特魅力为我们探寻内部的多元模式奠定了基础。今天的时代,无所不在的相同性和互动固然为一种重要的方面,然而,在国家稳定发展的背景下,对地方独特性的强调也是另一种思路,至少我们还要保护和重新肯定社区独特性所具有的意义。
为此,我们不仅要重新解读并重视已有社区研究作品中所呈现的特殊性,还要在更宏大的视野下思考其独特的意义。除此以外,未来的社区研究不仅仅要承袭此前将社区与外界联系起来的研究脉络,还要重新在时空坐标下看到社区自身作为一个分离世界所具有的地方性意义和对多元社会文化案例所具有的贡献。社区研究也要经历一个从强调封闭、独立性到强调与大社会及历史的联系最终在大社会、历史的网络体系中重新发现其特殊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这一道路既是时代主题所赋予的,也是学科理论反思与创新本身所需要的。在新的时代,我们要重新将社区研究中社会学、人类学的传统融合起来,又要因时代的需要而有所侧重。
[1](美)桑德斯:《社区论》,徐震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2年版。
[2](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英)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年版。
[4]Leach,Edmund.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 land Burm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Cambrida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5](英)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年版。
[6](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载《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7]张雄:《论社区研究的三大特点》,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1999年第 1期。
[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9](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毛泽东》,胡鸿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0]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载《北平晨报》副刊《社会研究》,1935年 1月 9日。
[11]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社会学刊》1936年第 5卷第 1期。
[12]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载《益世报》副刊《社会研究》第 1期,1936年 5月 6日。
[13]吴文藻:《导言》,载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1936),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14]Lin Yueh-hwa.The Golem Wing,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London:K.Paul,Trench,Trubner, 1948.
[15]蒋旨昂:《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16]Fei Hsiao-tung,Chang Chi-I.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45.
[17]潘乃谷:《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访谈》,载《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18]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19]Maurice Freedman.“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4,No. 1,1-19.Mar.,1963.
[20](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2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版。
[22]于建嵘:《岳村整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23]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24]Edmund Leach.Social Anthropology.Glasgow:Fontana, 1982.
[25]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载王铭铭编选:《西方与非西方》,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6]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 1期。
[27]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三联书店 2007年版。
[28]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载《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年版。
[29]贺雪峰:《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年。
[30]刘雪婷:《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1935-1936》,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1期。
[31]雷颐:《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32]费孝通:《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载《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年版。
[33]布迪厄:《知识场域——一个分离的世界》,载 (美)佐亚·科库尔、梁硕恩编:《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王春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年版。
[34]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 蔡虹
Review,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Chinese Community Study in One Century
CUI Ying-ling
(Sociology Depart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There are socio 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s in comm unity study:sociologists did case study within civil society,while anthropologists emphasized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of closed small comm unity in different cultures.Comm unity study in China was established and appli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oth traditions.Anthropological study encountered question of“representative”,which led to two responses:First, Western sinologists enriched and expand the meaning of anthropological comm unity study by establishing temporal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 unity and State and larger society.Second,Chinese scholars, such as Fei Xiao tong,on the one hand,affirm ed the comm unity′s significance as an integr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unit,on the other hand,they also put forward socio logical research route:from community to the zone type,finally to thew hole China.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rebuilding our country were reasons why importance was attach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 unity and larger society.We should value the comm unity′s link with outside,and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m unity′s local significance as a separ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pluralistic society,which is the academic subjectgiven by new era.
comm unity research;state;comm unity
崔应令 (1981-),女,湖北恩施人,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史、女性人类学。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07JZD0040);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 (人文社会科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2010-10-15
C91-06
A
1671-7023(2011)01-009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