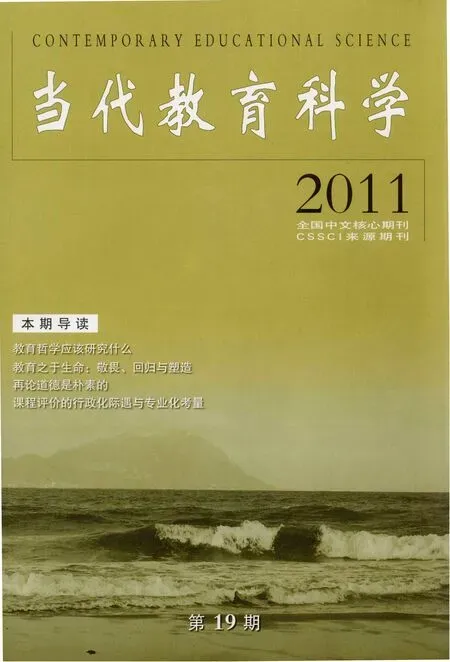再论道德是朴素的
● 李长伟
再论道德是朴素的
● 李长伟
长期以来,中国的道德教育忽视道德的朴素特性,强调道德神圣化的政治运动,由此导致了今日的道德滑坡和道德失范。为了回归道德的朴素本性,建设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有必要从几个方面加以努力:国家要反思并避免建国后长期的政党伦理社会化的政治运动;国家要以适当的行动承担起一定的责任;重视公共领域的建设。
道德;朴素;神圣;公共空间
一
“那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年代,那是糟得不能再糟的年代;那是闪烁着智慧的岁月,那是充斥着愚蠢的岁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夜沉沉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绝望的冬日。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大家都在升天堂,大家都在下地狱。”[1]这是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之语。之所以引用它,是因为它也可以视为对我们时代状况的最好把握。当下中国,人们追逐并享受着种种的物质生活,这是一个物质发达时代;但彭宇事件、范美忠事件、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也明白地告诉人们,这也是一个道德败坏时代。这个时代,人们对私人利益和自我保存精打细算甚至陷入疯狂,而对他人的不幸遭遇则示以冷漠、麻木和旁观。友爱、同情、仁慈、正义、勇敢等德性似乎只在书本之中,冷酷的现实中没有它们的位置。
德性,或者对他人的善,显露着美好的人性之光。可人性之光难道真得在这个糟糕的时代中荡然无存吗?不尽然。政治哲人阿伦特说:“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些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2]实际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时常有着这样的人性之光,或许他们并不是阿伦特笔下的精神贵族,但作为普通人的他们同样用自己的爱心点亮着这个世界,给糟糕时代的人们以希望和慰籍。刚刚被人们知晓的15位普通大学毕业生的行为就显露着这样的人性之光(详见《光明日报》2011年4月1日相关报道),透过光亮,人们看到了人性复苏的希望。
二
15年前,河北农大15位大学生的同学李宝元因病去世,其父母陷入贫困和孤苦之中,未来似乎一片黑暗。让人感动的是,大学生用他们的爱心支撑起了这个贫苦之家,给与了宝元父母生存的希望和勇气。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关爱行动不是来自短暂的心血来潮而是来自持久的道德信念,他们用15年的时间实践着他们立下的道德承诺——“宝元的父母咱们得管”,15年中15张汇款单和56封信是其道德信念的极好体现。亚里士多德曾言:“一只燕子或一个好天气造不成春天,一天的或短时间的善也不能使一个人享得福祉。”[3]15位毕业生15年的德性实践,可以看作是对亚里士多德言论的最好注脚。
对于15位大学毕业生的爱心行动,深化了人们对“朴素道德”的理解,或者说深化了人们对道德来源于并指向日常生活的思考。毫无疑问,大学毕业生的道德行动是自发的而非被道德的;是日常的而非神圣的;是基于内在道德感的而非基于外在政治灌输的;是单纯的而非功利的。总之,他们的道德实践是朴素的、自然的,常人的,而正因为朴素、自然、普通,他们的道德实践才是默默无闻但又持久不断的。朴素的、自然的东西最有生命的活力,外在的修饰和过分的拔高往往会造就外表道德但内里反道德的虚伪之人和分裂之人。坚持同情是人之自然本性的卢梭说:装饰对于德性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就是灵魂的力量和生气。[4]
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国家忽视了道德的朴素和自然,将本来朴素的生活化的道德神圣化和政治化,由此导致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实践因缺乏来自人之自然本性与日常伦理资源的支持而异化为反道德的观念和实践。做一个纯粹的无私的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刻准备着为人民献身,这些我们熟悉且曾实践的道德口号固然无比神圣和高贵,但它们实际只适合“圣徒”而不适合广大的普通人。须知,人是有血有肉的,有情有感的,将人彻底地纯化,将德性无限拔高,脱离日常生活而与纯粹的神圣和至高的彼岸世界相连,必定会扭曲普通大众的自然本性和德性,将其变成“伪善之人”,或者将其变成以善之名行恶之事的人。进言之,当普通人无法达到但又必须达到高标准时,自然只能伪善了。
学者包利民提出的两阶价值结构——一阶的生活价值、二阶的道德价值——也有助于我们分析这一问题。在本体论上,生活的价值是本源,道德价值低于并最终指向生活价值,为后者所操作;但在价值论上,道德价值高于生活价值,“因为它能提供比日常生活强烈的、浓郁、惊心动魄、富于超越、神圣性、英雄性的意义。”但也因为如此,“历史上一直有一种不顾生活价值而将道德价值本身作为终极目标追求的倾向(二阶价值的自指倾向)。这实际上是十分危险的。多少‘小民’的生命财产的惨遭牺牲,并不完全是因为‘大人’们争权夺利,也有的是因为‘伟人’们热衷于道德神圣化运动。”[5]回到我们的现实,文化大革命就是道德神圣化运动的最好体现,它对个体和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可谓触目惊心,并且这种恶劣影响在今日许多地方仍然明显可见。
当然,不管怎样,在道德神圣化的政治运动中,人们或是迫于压力而不敢做出反道德的行动,或者人们因陶醉在“神圣的氛围”中而掩盖了自己的“伪善”,社会的伦理秩序由此得以建立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建国后尽管传统伦理被破除,灵魂被革命,但社会生活仍然存有伦理规范的原因所在。但是,一旦道德神圣化的政治运动成为过去,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成为生活主导,道德失序就成为一种必然,因为人的自然本性以及涵养人之自然本性的伦理资源在道德神圣化的政治运动被破坏和被扭曲,而它们恰恰构成了心性秩序以及社会伦理秩序的内在支持。由此可说,当下的时代之所以是糟糕的时代,原因与其有关。
对于当前社会伦理失范,学者刘小枫有过这样的解释:“从建国至今,政党国家从未停止过道德化的全民运动,它也曾达到过看似全民一致的道德团结。但这一情形的可能反面是:整个国家或全民式的道德沦丧。因为政党伦理是大众动员的媒介,也是大众参与政治的媒介,‘人民’的大众伦理并没有得到传统社会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反而使社会共同体中的自性组织及其伦理功能萎缩。一旦政党伦理萎缩,社会中个体的伦理归属就找不到可属的社会机体,社会伦理秩序的瓦解就不可避免。”[6]毫无疑问,政党伦理是神圣的、至高的、纯粹的,但它起初只是用来规范政党成员的,但后来却通过历次的政治运动成为规范所有人的“社会化的伦理”。这样的社会伦理的确高贵,但却因为不是来源于日常生活和人的内在良知而必然失去规范社会成员的效力。孔子所倡的儒家伦理的确也与政治结合而成了社会伦理,但它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固。一方面是儒家伦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但更重要的是儒家伦理的“生活化”取向,即儒家伦理是建立在家庭亲情的基础之上,这种对自然和日常生活的关怀使其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历代的统治者也因认识到这一点而将孔子视为先师。遗憾的是,自五四开始,高调的反传统的革命不断破坏着这一朴素的伦理观念和实践,直至作为革命顶峰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儒家伦理也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孔子提倡的父子互隐虽然符合古代家庭伦理,但却有违现代的普遍伦理和法律规范。但孔子的伦理学说对日常生活的关照却具有启示性的价值,或者说,如何建立一种来源于生活但又提升和引导生活的伦理规范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三
如果我们承认道德的败坏与道德神圣化的政治运动有密切的关联,那么面对15位大学毕业生的源自自然本性的道德实践,还有李宝元父母一直坚持的朴素的道德信心——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无论生活多么苦难,我想我们应该好好思考如何保护发自人性的道德之光,换言之,该思考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去养护朴素德性。由此,微弱的人性之光才能渐变为普照大地的人性之光。
一方面,国家应该反思并避免建国后长期的政党伦理社会化的政治运动,这样的道德运动违背了个体的道德本性,破坏了长期涵养这种道德本性的传统环境,导致了社会伦理失序。也就是说,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道德的本来面目:道德是朴素的,是日常的,养育道德之人的道德环境是习俗性的。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德性就是一种在良好的习俗环境形成的习惯,而习惯无非就是在持续的道德实践中形成的持久的内在的情感体验模式。这决定了德性的形成不可能靠外在的高调的政治灌输和宣传,而只能靠良好风俗的潜移默化式的教化。在中国古代,道德也是朴素的,培养道德人就是从培养他的日常习惯开始的。朱熹有言:“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当下之所以出现道德滑坡和败坏,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扎根于民间的传统的日常的伦理资源在历次的大规模政党伦理社会化的运动中被破坏殆尽,失去了约束人的行为的力量,而随着政党伦理或者国家主导的神圣伦理失效以及人的物欲的解放,人的行为必然处于失范状态。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做深刻的检审和反思,以回复道德本来面目。
另一方面,国家在反思政党伦理社会化的前提下,也应该以适当的行动承担起一定的责任,以保护恢复中的美好的德性之光。反思政党伦理社会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在今天社会伦理建设中毫无作为。实际上,国家可以通过法律与制度等力量保护(而不是直接介入和指导)源自社会个体的道德行动。的确,随着现代性的兴起,古典时代的法律与道德的内在关联逐渐被剥离,但在道德环境尚未正常以及人的道德感还很脆弱的今天,强调法律等制度力量的保障尤为必要。进言之,15位大学毕业生的感人行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糟糕的时代实际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法律与制度的保护。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长期的道德神圣化运动以及市场经济对私利的强调,歪曲了人们的道德判断,好人流血又流泪,好人遭恶意中伤和讥讽的事情时常出现。进言之,我们应该抛弃传统的“好人是不会受到伤害的”观念,认识到好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是会受到伤害的。而当好人受到伤害时,国家应该通过法律等力量对好人的行为予以公正保护,为道德环境的确立提供必须的法律支持。南京的彭宇事件之所以导致很多人不敢也不愿做好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没有尽到保护好人的义务。由该事件可以看出,司法公正在构建良好道德环境方面发挥着多么强大的作用。
第三,重视公共领域的建设。道德神圣化的政治运动以及随后的人们物欲的解放和膨胀占据了公共领域,导致社会自发形成的“公共领域”的消失,而公共领域的消失意味着自由的消失,而没有自由就一定没有道德,这是一个不需要过多论证的观点。依阿伦特的观点,公共领域充满着自由人与自由人之间的交流与言说,显露着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承诺和团结,如此,美好社会才成为可能。陈家琪说,汶川地震中让人感动的事有太多,但有一点特别显眼,这就是突然有了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中的人们表现出长久未见的让人感动不已的道德行动。他引用刘莘的话说:“你想想,地动山摇,瓢泼大雨,没有人组织安排,没有警察指挥交通,更没有红绿灯,但成百上千辆出租车都奔向了同一个地方:都江堰。道路之崎岖,危险之大早已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但这也正是那些有着非凡胆量和高超技艺的人表现自己的时候。”[7]这意味着,公共空间的建设对良好道德环境的建设至关重要。而且,它也是对中国传统伦理资源的一种重要的提升,因为如梁启超所言,中国向来有私民和私德,而无公民和公德。所以,公共空间的建立有助于超越狭隘的传统伦理而建立一种普遍的公民伦理。15位大学生救助与自己非亲非故的同学父亲,多少已经显现了这一点。
最后想说的,教育部与光明日报在评论这一感人事迹时,都提到了他们行为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毫无疑问,这是重要的。但我想补充的是,他们的行为也体现了“普世价值”。同情他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宝元父母的欠债还钱,显然具有一定的普世性。陈家琪对普世价值问题有这样的论说:“哪怕学习马克思,也应该想到应该努力揭示那种人类社会中普遍的、深层次的共同问题,比如社会结构、分配原则、交换原则、利益博弈、道德与法律、权力与权利、个人与共同体、人性中的本能与教育、文化的传承等等方面的问题。世界上的主流话语掌握在西方人手中,普世价值都是由他们定义的,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普世价值,就不能给我们的价值以普世性而走向世界。”[8]对这一论说,笔者深表赞同。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民族国家的独特性而忘记了人所共有的普世价值,除非你否定中国人不是人类。
道德建设非一日之功,希望大学毕业生群体所显露的人性之光能够渐变为普照大地的人性之光。我们期待着。
[1][英]狄更斯.双城记[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1.
[2][德]阿伦特.王凌云译.黑暗时代的人们[A].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封底.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
[4][法]卢梭.何兆武译.论科学与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2.
[5]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39.
[6]刘智峰主编.道德中国[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1.
[7][8]陈家琪.三十年间有与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7,65.
李长伟/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