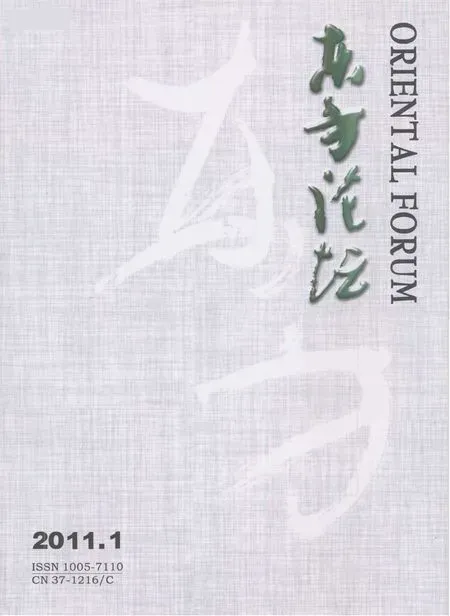“自然观”与生态困境的道德哲学演绎
牛庆燕
“自然观”与生态困境的道德哲学演绎
牛庆燕
(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210037)
生态难题日益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问题。以系统论思维方式全面考察人类“自然观”的生态演化历程,历经远古文明时期“自然为人立法”、近代工业文明时期“人为自然立法”,应当寻归生态文明时期有机契合的系统“生态自然观”,是谓“人为自身立法”。其中,现代“生态自然观”的确立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现时代的内在要求,为缓解生态危机并破解生态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应当成为绿色文明时代的伦理共识和文明期待。
自然观;生态困境;道德哲学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生态难题日益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的全球性问题,直面生态威胁,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自然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它在思想观念深层影响着人们的生态道德认知,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历经远古文明时期的本体论“自然观”——“自然为人立法”、近代文明时期的认识论和工具论“自然观”——“人为自然立法”,应当寻归生态文明时期“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有机契合的系统“生态自然观”,是谓“人为自身立法”。其中,现代生态自然观的确立为缓解生态危机并破解生态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
系统考察人类“自然观”的生态演化历程,以系统思维方式尝试探究走出生态困境的有效路径,对于全面完整地探析生态困境、积极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自然为人立法”
早在远古时期,随着人类意识逐渐趋向成熟,从原始神话、自然宗教和早期图腾崇拜中逐渐分化出属于人类自身的世界观和自然观,把自然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寻求自然和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逻辑。古希腊所强调的宇宙整体秩序性以及西方中世纪神权统治时期的上帝预置万物理论,都肯定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共同体的一体相关、混沌未分,属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自然观”。慑于自然的威力,当早期先民运用自身的力量无法与自然相对抗时,便不得不顺从自然、顺天而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实际上在没有人类明确的自我意识关照下是一体未分的融合状态,是谓“自然为人立法”。
(一)主客一体的原始本体思维
远古时代,人类整体处于蒙昧和未开化的状态,人类的主体意识在尚未完全呈现出来时,人只是作为自在和自然状态的主体而存在,并且不能完整辨别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人类源于自然、依赖自然,人与自然是原始直接、混沌朦胧的统一关系,这种主客一体的原始本体思维模式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注入了更多神秘一体的感性因子。建基于自然本体论之上的对自然与生俱来的膜拜信念,通过原始宗教和“图腾”神物的缔造,以一种发自生命深层的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表达着远古先民的自然情怀。如此,远古先民能够“克服”人类主体意识和主体力量的有限性,化解人类在强大冷漠的自然面前无助,从而在潜在和自发的层面上直面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矛盾,维系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远古文明时期主客混一的原始本体思维把自然看作是具有生命和灵性的有机体,这是一种潜在的有机论生态伦理思想。
(二)朴素的“天人合一”有机论自然观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东方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性命题。在远古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在面向自然的生产实践活动中逐渐增强着对自然的体认过程。人类“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萌发开始区分作为认识与实践对象的客体自然与主体人类,但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和归依自然却作为一种深层的价值理念印刻在远古先民的思想深处,在主客一体的本体思维的激发下,逐步确立起朴素直观的“天人合一”有机论自然观。
“天”是至高的权威和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人类在具体的生态实践中要“惧天”、“畏天命”,进而在“尊天命”的基础上顺天而动,遵循自然规律,以确保农业生产和生活的稳定。“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具备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是远古文明中主客一体的原始本体思维的延伸,这不仅是一个哲学存在论的命题。更是价值论的命题,它认为自然是一个统一性的有机整体生命系统,肯定自然存在的价值及其自然规律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制约调节作用,并且认为人作为自然中具有能动意识的生灵,理应关爱自然、尊重自然的价值,扩展道德关怀的范围。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传统儒家文化中作为一种世界观、宇宙观和普遍的思维方式,体现着人生最高的精神追求境界。作为儒家生态智慧的精髓,彰显着和谐的人生态度,不仅是东方传统自然观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展现,也是“天人合一”形上精神旨归的理念体现。其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旨归、“民胞物与”的文化关怀与“取物限量,取物以时”的道德规范,彰显着天人合其德、天人合其性、人之性与天之性合其类的宇宙情怀。“天人合一”的古朴有机自然观在道家生态思想中主要体现为“道法自然”。“道”作为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和主导理念,是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的辩证统一,“道”是万物的始基、本源和万有之根,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道”是向“自然”的理念认同与价值合一,“自然”是“道”的皈依,“道”是“自然”的彰显,“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佛教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自然观的生态理念,但却以宗教信念的形式潜在地契合了“天人合一”。它站在生命关怀的高度主张应当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类、生物与非生物,因为“众生平等”、“万物皆有佛性”。个体依靠道德修行的努力能够向佛的本体境界迈进,从而获得“内在价值”,因而具有平等的生命本质,所以应当以平等慈悲的心态关怀宇宙众生,体现了佛教生态伦理自然观的道德情怀。
(三)混沌直观的“生态印记”
“天人合一”的朴素有机论自然观,是东方传统文化自然观的基本生态理念。自然是人的生命之源和价值之基,人在创生并实现着万物和自然的“价值”的生态实践过程中,不断实现着自身的“内在价值”,在人与自然主客合一的本体思维模式下,达成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同一。在“天人合一”自然观的熏陶影响下,中国古代文明的实现过程蕴含了天、地、人的有机协调与统一,生态伦理思想初露端倪,五帝时代设置了专门管理草木鸟兽和山林川泽的机构,东汉时意识到水旱自然灾害与乱砍滥伐息息相关,到晋代时已把人口数量的暴增与生态环境问题相关考虑。
东方传统的“天人合一”自然观是中国远古先民顺天而动,维系自身生存和生活的深层指导理念。作为创生万物的自然是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生命始基和价值源泉,所谓之“天道流行”、“生生不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对于今天生态伦理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囿于时代的局限,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缺乏对自然规律的科学体认。这种建基于“主客一体”的经验直觉思维基础上的生态理念具有直观混沌的总体特性,并过多地强调了人对自然的先天依附性,对主体人类的能动创造性突出不足,但毕竟是远古文明时代“自然观”的生态印记,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二、“人为自然立法”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近代自然科学得到迅速发展。新兴资产阶级以人权反对神权,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尊严,追求俗世的舒适享乐和现世的实用幸福。当把自然看作一种“纯粹的有用性”[1](P535)的时候,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便成为社会进步的唯一价值依据和终极目的。人类开始过度关注经济发展速度,漠视和排斥发展的目的性和价值性问题,过分追求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无视自然生产力的同步增长。由此,人类过度乐观的经济实践在打破了自然生态平衡之后所获取的物质增长,实际上是抛弃了生态效益的经济效益。当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充斥社会,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不负责任的毁坏和无节制的浪费也便愈演愈烈。因此,近代工业文明彰显的是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形成的认识论和工具论“自然观”,是“人为自然立法”的生态悖论。
(一)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与工具论思维
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使神权统治造就的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分裂状况有所改观。在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意识的基础之上,注重哲学思维的微观分析和细节描述。然而,机械论思维的“自然观”把整体的宇宙、自然与万物看作静止、孤立和永恒不变的僵化的“物质世界”,人类成为认识和实践的绝对主体和对自然进行任意宰割和鞭笞的主人,自然成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性的工具存在,在工具性的意义上,只能被人类无限地占有、使用和消费,自然本身的精神审美属性和价值被无限放逐,人类开始“从事着推翻自然界的平衡以利自己的活动”[2](P125)。机械论“自然观”以单纯的认识和实践关系看待人与自然,把科学认知与道德理念截然分开,认为伦理与道德的原素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生态伦理观念在文化体系中被抽离,生存困境与生态危机便难以避免。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提出,奠定了西方哲学史上“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基础,人类相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起来;康德在强调人类主体认识能动性的基础上突出了人类的理性主体地位,并把理性自我提升到先验自我的高度,要求“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把人类的主体意识继续推向前进,认为人类即理性自由与绝对精神。在“主客二分”的机械论自然观影响下,培根的经验主义、笛卡尔的科学分析以及牛顿机械力学充斥整个西方世界,它们共同把作为整体存在的自然生命系统经过分析和还原的方法拆卸、分解为各自孤立的、静止的原子和单个个体,这是一种数学化和物理论中的“自然观”图景:“我们在认识了火、水、空气、诸星、诸天,和周围一切其他物体的力量和作用以后(正如我们知道各行工匠的各种技艺一样清楚),我们就可以在同样方式下把它们应用在它们所适宜的一切用途下,因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所有者。”[3](P593)
因此,“主客二分”最终落实为“人类中心”。人类是唯一具有价值意识的存在者,同时也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性存在,客体的价值属性成为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性,而这种“有用性”只是相对于主体人类而言的“工具价值”。如此,当以人类物种为尺度衡量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顾及的是自然对人类的短期效用,自然被降格为向人类提供生存环境和物质资源的工具性存在和没有灵性的客观存在,狭隘有限的视角漠视了生命自然系统整体的生态价值以及对人类和其他自然物种的终极性的价值意义,从而进一步消解了人类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
(二)“天人相分”的机械论自然观
“天人相分”的机械论自然观是“主客二分”的工具论思维方式的具体展现。西方社会自普罗泰格拉明确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以后,人类主体性的基调便基本奠定。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神权的枷锁后,整个社会开始推崇人类的理性和主体能动性,满足主体人类的欲求和实现人类的幸福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推动了人类运用科技手段统治自然的实践行为,折射出人与自然相抗争和对立的“自然观”的认知意蕴;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以人类理性的普遍怀疑精神,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统治权威和神权信仰,黑格尔以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视角把自然置于人类理性和“绝对精神”的统治之下,人类主体意识最高层面的“绝对精神”是自然演化的至高目的和动力源泉。因此,主体人类的理性意识和能动意识高于自然存在,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自然是认知对象,二者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
“天人相分”的机械论自然观在推动人们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实际上不断地张扬着人类生命物种的个性,增强着人类的主体性,带来了人类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飞跃,又反向强化着人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强权意志,为人类向自然索取找到了合理化的证明和依据。建基于此种“自然观”的认知理念基础上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经济理念,被打上“征服”和“占有”的烙印,人类与自然逐渐背道而驰,能源枯竭、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一系列的生态难题接踵而至。由此可见,“天人相分”的机械论自然观在高扬人类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创造的优势的同时,也在不断毁弃着对自然的人文理念和生态精神。
(三)人与自然的疏离与生态灾难
“天人相分”的机械论自然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的积极意义。它在高扬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同时,增强了人类对自然世界探索的勇气,并拓展了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广度、深度以及进一步改造自然世界的力度,促进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推进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是,“天人相分”的机械论自然观以对自然的认识论和工具论思维取代自然本体论思维,以机械论取代有机论,以“天人相分”代替“天人合一”,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人与自然的一体相依性,背离了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层底蕴,也暴露了人类生命物种个体的狭隘性,引发严峻的生态灾难。
首先,人的“类本质”的遗忘和生态理念的缺失。如果说,“远古文明时期“天人合一”的有机论自然观的认知理念统一于德性论,那么,“天人相分”的机械论自然观则是以认知论消解价值观,把道德认知从人与自然关系当中抽离出来,彻底颠覆了自然本体论的价值认知。而脱离了人性的道德束缚的实践行为必定在充分张扬人类的占有欲和物欲的基础上对自然开战,特别是关注主体人类利益并对自然进行机械分割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从道德认知的深层遮蔽了人类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忽视了对自然生态规律的体认,遗忘了人类与自然共在平等的价值关系和自然本身不可替代的“系统价值”,遗忘了人在“类”的本真状态下所应当担负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使命,引发难以预计的“生态灾难”。殊不知,人类是自然之子,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在否定自然的实践行动中实际上又在不断地否定人类自身,当人类本质力量的呈现片面化和碎片化,那么,人类在追寻自由的同时也便日益陷入不自由的境地。
其次,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和背驰。人类成为控制自然机器并统摄万有的至高存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线性还原和简化,遮蔽了自然的价值和人与自然的丰富和多样性的联系,自然生命主体地位的缺失使得人类原本应当对自然具有的“敬畏之情”消解,对其他自然生命物种的道德关怀弱化甚至不复存在。这里,人类所谓本质力量的实现历程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过程,即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掠夺和对生命尊严的摧残和践踏,使得自然的生命本性和存在状态遭受严峻的冲击,并且,自然已经向人类发起了反击,接踵而至的生态困境已经逐渐发展成为蔓延整个地球生命系统的生态灾难,痛定思痛,人类有足够的理由进行自我反省。
因此,近代工业文明时期“天人相分”的机械论自然观摧垮了自然本体论的神话,确立起人类主体能动性的理性神话。远古文明时期对自然的敬畏和敬重之情被近代工业文明时期对科技理性的崇拜所替代,人类与自然相脱离,自然成为工具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象性存在被征服和占有,“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使得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联系分崩离析。实际上,自然是充满生机和活力并不断演进和进化着的生命系统,其本身并非是毫无价值意义的“荒野”之地,而是趋向完整、稳定与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这是现时代应当重新确立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自然观”。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应当以生态的道德认知理念和思维方式看待自然万物,以发自内心“爱”的情感关涉自然,以生态、有机、系统、整体和互利的文化理念和思维视角实现对“天人相分”的机械论自然观的变革与更新,在对自身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为自身设定行动的域界,即“人为自身立法”,从而探寻生态文明时代“共生和谐”的生态自然观,替代“天人相分”的机械论自然观。
三、“人为自身立法”
生态文明时代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上,不同于远古时期原始混沌的“天人合一”,也不同于近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天人相分”,它认为宇宙万物与自然中的单个生命在生命系统中存在彼此相依的内部关联,其价值的展现通过自然整体生命系统而获得生态意义,是“主客统一”思维模式的辩证复归。因而,重新建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有机契合的系统“生态自然观”,是人类依靠自身价值观念的反省,不断地向内追索,为合理“自然观”的确立及时地补充生态价值的合理因子的路径,是“人为自身立法”。
(一)“主—客—主”的辩证复归
走出生态困境,就要在充分考量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建构人对自然的新认知模式,以生态的思维理念超越旧的机械论范式,建构系统、整体、有机的生态自然观,进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世界观的革命,这是深生态学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主客统一”的思维模式。
不同于旧的孤立、还原的机械论自然观,系统有机的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把整个自然生命系统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内部的生命要素相互作用、彼此联系,作为相互关联的动态整体中的有机构成,共同维系着整体的生命系统的持续稳定运转。因此,“主客统一”的思维模式是以自然生命整体的存在为依托的“主—客—主”的关系模式。主体人类能动地作用于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命过程,折射出的是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有道德的原素渗透其中。生态有机论自然观关注“人——自然”生态共同体的协调运作,其间涵摄了主体“人——人”之间的道德关联,在生态世界中主要以“人——自然——人”的生态相关性体现出来。通过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之上谋求“人——自然”生命系统的和谐发展,在尊重和维系地球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同时,尊重自然价值和生命物质的生存权利,在遵循客体生态规律的前提下辩证看待主体人类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与受动性和依附性的关系,达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为一,实现“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和谐统一。
“主客统一”的思维模式下,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自然中介建立起来的“主——客——主”的关系范式,既融汇着人类与自然生态共同体的伦理意蕴,同时也渗透着主体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切和道德内涵,是人——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也是生态文明时代正确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自然观的思维体现。人类的思维从机械式的理性、分析、还原的线性模式下解放出来,向生态文明时期系统有机的综合、整体的非线性模式转化,能够融入更多的知觉情感和人文关切的因素,由支配控制自然的欲望的无限膨胀,转换为在全人类共同保护自然实践行动基础上的理解、宽容、信任和支持,承认生态系统整体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机联系,这是生态时代的伦理意蕴和“主客统一”思维模式的辩证复归。
(二)系统有机的“生态”自然观
“主客统一”的思维模式把自然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有机地整合为一体,使自然认知论融会了主体人类特有的道德认知的因子,把近代工业文明时期的机械论的自然认知观转换为生态文明时期的科学、系统、整体和有机的自然价值观,是作为“类”的存在的人的生态伦理意识的深层觉醒与道德自觉。
人类——自然——社会的整体有机系统是生态的存在系统和价值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内在的生命个体,不仅具有相对于人类生存的需要和意义而言的工具价值,而且具有自身存在的固有的内在价值。作为“价值主体”,生命本身的自组织活动必须紧紧依赖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和能量,利用其他系统物质的工具价值维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是本身固有的“内在价值”。作为“价值客体”,自身在生态系统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又不断地为生命系统整体的维系与协调运转和其他生命个体提供着不可或缺的“工具价值”。作为整体的自然生态系统在系统运作过程中是一个自组织、自协调、自进化、自选择、自平衡的生态过程,在自然周期性的运转过程中不断孕生、养育和发展着丰富多样的生命目的中心与价值中心,在系统进化与价值增值的过程中维系着自然生命整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这是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的“系统价值”。因此,生命个体之间、生命个体与种群、生命个体、生命种群与自然生命系统整体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价值关联,个体的生命存在具有“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价值属性,而自然生命系统整体却具有至高的“系统价值”属性,它们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中的“价值”整体。
因此,“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系统整合的生态自然观认为,人类作为自然之子,产生于自然生命系统,是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生命组成部分。人类的生存维系和发展,必须紧紧依赖自然生命系统的稳定和进化。同时,人类的主体价值也必须归依自然生命系统的整体性的存在价值才能够得以展现,主体人类在自觉意识到自身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存在价值的基础上,应当尊重其他生命存在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的“系统价值”,发挥生命主体的调控作用,维护自然生命系统乃至整个生物圈的稳定与和谐,促进人类与自然生命系统的协同进化。
(三)反思与审视
“生态”自然观不仅是系统论自然观在人类生态社会的具体彰显,也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现时代的内在要求。生态自然观把人类对自然的科学理性认知和对待自然的伦理关怀与道德关切统一起来,把自然“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系统整合起来,在科学认识自然因果律的基础上注重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的维系,在合理运用自然工具价值的基础上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尊重自然的“系统价值”,把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和共生和谐作为生态实践主体的道德价值诉求,在具体的生态实践中充分发挥人类主体的意识能动性,维护、恢复并优化自然生命系统的动态平衡。因为人类——自然——社会是动态有机的复合生态系统,人类的自然性、社会性以及精神性的生命存在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样态,这是系统有机的生态世界观和自然观的内在规定和价值含义。
因此,人类“自卑——自负——自省”的思想成长历程,也是现代人类在“类本质”觉醒的基础上不断地向内追索的道德哲学生长过程。道德哲学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思考中得以“深化”,人类自身在“类本质”意境的不断彰显中得以“进化”。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和谐共生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和对话关系的建构,是生态自然观的本质内涵,为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应当成为绿色文明时代的伦理共识和文明期待。
[1] (英)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责任编辑:郭泮溪
“View of Nature” and the Ecological Dilemma in Light of Philosophy
NIU Qing-yan
(Dept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
The ecological dilemma is becoming a major global problem threatening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human race. By inspecting the ec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view of nature” with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it is found that after “legislation for man by nature” of ancient times and “artificial legislation for nature” of modern industrial times, it is time for “legislation by man for himself”. Moreover, the “ecological view of nature” is not only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 of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t the present time, but also th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basis to alleviate and even to re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which should become the ethic mutual recognition and the civilized anticipation in times of green civilization.
view of nature; ecological dilemma; moral philosophy
B82
A
1005-7110(2011)01-0032-06
2010-12-30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09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9SJB720007)阶段性成果。
牛庆燕(1978-),女,山东泰安人,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道德哲学、生态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