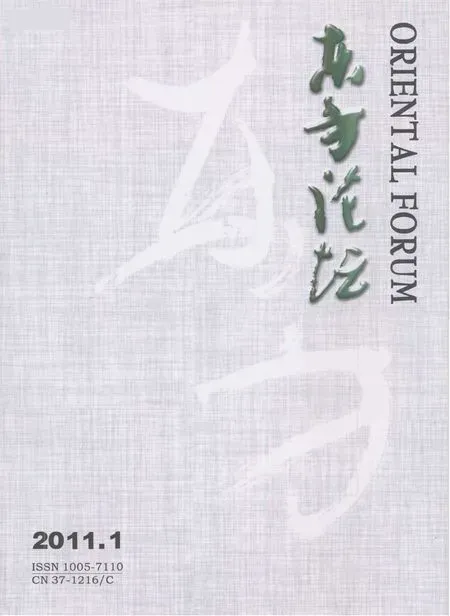论作为世界文学学科依据的文际交往
王钦峰
论作为世界文学学科依据的文际交往
王钦峰
(湛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为准确地描述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历史趋势,应以民族文学间的“文际交往”作为世界文学的学科依据。文际交往是世界文学的实际运动过程和具体呈现形式,它应当成为我们理解民族文学关联网络和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内在支撑点,同时应当成为我们重构世界总体文学发展史的出发点。
世界文学;民族文学;文际交往;学科依据
世界总体文学史撰写的一个根本的学术目的,是对世界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内在关联作出准确的描述与勾勒。而在国内学术界,从理论上对世界文学学科史、学科现状及其存在的弱点一直缺乏研究和反思,这使得学科本身形成不了自身的特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虽已开始在实际的编史过程中把文际关联的视野纳入考虑,酝酿着某种学术转型,但理论界对文际关联这一学科前提仍缺乏最起码的理论建构。本文重在提出和阐述以下两个问题:一、世界总体文学是如何在民族文学相关互联的网络中展开自身的,现有的世界文学发展状态的各种理论描述和认识能否满足我们的理论需求,它们有哪些长处和不足;二、“文际交往”应当成为我们理解民族文学关联网络和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内在支撑点,同时应当成为我们重构世界总体文学发展史的出发点。
一、学科史的不足
世界文学概念是在发现以往民族文学研究局限性后提出的,它的任务是遵循比较文学的“信仰文学现象的整体、拒绝民族文化经济学的自给自足”的原则,[1](P29)构筑民族文学间的“关系”和以此为基础的“世界”文学叙事,正如基亚所说:“关系,这个词在‘世界’方面划出了一条界线”。[2](P119)如果在超越狭隘民族立场的前提下去看待世界文学进程,就会发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整个文学发展系统是由全人类各民族文学共同交织而成的网络,是一个文学共同体或文学时空联合体。这个网络决不是静态作品的偶然的空间分布,而是民族文学发展动态过程及民族文学之间的文际交往关系在纵和横两个向度上的伸展,具体说就是,“一国民族的文学总是处在(垂直方向上)连续的历史传统的前后联系之中,同时又处在(水平方向上)与别国文学不间断的地区性交流之中,这种交流除非使用强制手段,否则是地理或政治界限所不能阻止的”。[3](P98)
交往中的人类总体文学的描述,认定(而非假设)世界各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文学发展史,同时认定各具特点的民族文学历史之间存在实质性交叉关系。站在这个高度上对现有的总体文学研究加以观照,就会感到,缺失其中任何一个向度的所谓的文学研究,要么就是看不到自身或其他民族文学文化的独立历史,只承认某种单一历史型构的存在,要么就是看不到不同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乃至权力关系,从而对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不真实的描述和判断,这两种缺失都势必导致总体文学研究的失真。我们认为,指出并强调世界文学交往结构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我们将无法正确判断和弥补当下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乃至国别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不足,也不可能正确认识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内在理路,把世界文学学科建立在可靠的理论基础上。
世界总体文学发展状态研究已有两百多年历史,其中数德国学者最早、也最热心于尝试对全人类文学史进行构想和描述。赫尔德是世界文学的第一位发端者①韦勒克说,赫尔德“是世界文学史方面最明显可见的一位发端者”,见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第243页,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他在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编的《民歌: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1777-1778)是第一部完备的世界文学选集,他也是第一位构想了世界文学史和写出了它的提要的人。数十年后,赫尔德的学生歌德,以及马克思都提出了“世界文学”概念,但遗憾的是二者都没有专门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各民族文学及其关联进行总体把握。与歌德同时,黑格尔完成了赫尔德的夙愿,应当说写出了第一部世界总体文学史,这部历史内含于他的《美学》第三卷中(该书1828年即在大学讲授,黑格尔死后出版于1835年)。在法国,克劳德•弗里埃类似于赫尔德在德国的角色,他在《近代希腊通俗歌谣•译序》(1823)中“宣布了全球性的民间诗歌理论纲领”,甚至勾画出一部史诗通史的轮廓,展望过一个包揽梵文史诗在内的“全球文学史”理想[4](P6-7)。在法国人维尔曼于1828年在巴黎大学首次开设比较文学课以后的整个比较文学时代,对世界总体文学发展状况的研究越来越走向自觉,其中在欧美诸国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1886)、尤利乌斯•哈特的《世界文学史》(1894)、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自滥觞至二十世纪》(1903)、卡尔•博塞的《世界文学史》(1910)、保尔•维格莱的《世界文学史:外国民族的诗歌》(1914)、约翰•马西的《世界文学史话》(1925、1936)、吉阿科莫•普朗波里尼的《文学的世界史》(1938、1953)等,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的这类著作更多,难以尽数。其中,早期较著名的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虽不是单纯的世界总体文学发展研究,但却把东方文化圈中的中国、印度、希伯莱、阿拉伯乃至美洲印第安在内的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学纳入视野,加以总体探讨。约翰•马西的《世界文学史话》在认识上达到了歌德的高度②该书作者谈论中国文明的语气与歌德类似:“现在的中国人能够读到他们古代祖先的智慧,……但在那时,我们的祖先还在野森林中相互撕杀”。见John Macy,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New York: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1936,pp.23-38.,但仅在第三章以“神秘的东方”为名简单概述了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文学,所以基本上仍是一部欧洲文学史。
为了全面认识西方国家在世界总体文学研究领域所存在的根本弱点和特点,我们认为最好从分析黑格尔和洛里哀这两个个案入手。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史的追溯中,自称为歌德儿子的黑格尔一直被人忽略。③黑格尔于1825年曾致函歌德:“我要自称是你的一个儿子”。《黑格尔生平和著作年表》,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2页。他的《美学》第三卷(下册)虽然并非严格的史学著作,但却体现了在当时来说非常宽广的世界胸怀。该书视野开阔,编入了包括东方的中国、印度、希伯来、阿拉伯、波斯在内的东西方许多国家的文学简史,方法上根据“理想”或“心灵”这种主体自由的体现程度,依次把文学分为史诗、抒情诗、戏剧三类,继而把文学史分成相应的三阶段来布局谋篇。与之相应,这部世界文学史的根本弱点表现为:一、东方文学史部分很不完备,尤其是中国和巴比伦的文学史最为薄弱,几沦为西方文学史的陪衬或可有可无的插曲;二、它根据西方人主体精神的追求这一固定不变的标准来衡量世界文学的价值,把中国乃至东方文学定格在西方主体精神(而决非真正世界精神)的浮士德式追求的逻辑框架中,把它们安排在最低级、最原始的发展阶段上;三、缺乏真实的、历史的联系和交往,这在交往的时代里分明是无视交往的事实,不及歌德和马克思的鲜活;四、精神的和真实的两种历史并存,真实史依附、内含于精神史,独立的民族文学史、世界文学史虽有雏形但尚未从后者中脱出。洛里哀可谓文学总体研究的转折点。他作于1903年的《比较文学史》应当说是早期世界文学史撰著的典范,④关于洛里哀《比较文学史》一书的性质,傅东华在译序中告诫读者,洛里哀的这部“由系统的——或统合的——方法见出的文学”与后来的摩尔顿(R.G.Moulton)所称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名虽不同,实际则一,是一部跨国别的、统合性的世界文学史著作。见洛里哀《比较文学史》,傅东华译序,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2页。该书的优点主要表现于:一、涵盖面空前广泛,主要涵盖了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在内数十个民族国家的文学成就,充分显示了比较文学的发起所提供的世界范围的大视野;二、刻画了文明的流动和文学的频繁交往这一世界性的进程,把全书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了各国文化有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三、在意识上给予世界上每一个有着自身悠久历史和文化上成熟的民族以平等地位,把欧洲以外的民族文学当作真正的自成维度的历史来抒写,超越了黑格尔。同时,洛里哀首次在文学史范围内对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的某些表现,如西班牙对于曾受其滋养的境内阿拉伯文化以及美洲文明的摧残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不过该书的弱点也不可忽视,如后半部几乎没能再涉及欧洲以外的亚、非、美等洲,改变不了欧美比较文学、总体文学研究存在的普遍弱点。
迄今为止的总体文学研究在对世界文学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存在着一系列不足,有意味的是,这些不足往往是在文学世界主义的名义下产生的。除了早期洛里哀的某些可贵努力以及当代斯洛伐克学者久里申等极少数学者所进行的有意义尝试之外,西方国家的世界总体文学研究多局限于欧美文学范围,难以将触角延伸到东方①强调影响研究的法国早期实证派比较学者布吕纳介认为,东西方文学之间不存在事实联系,因而应将西方文化圈以外的文学排除在比较文学和文学总体研究之外,这种看法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上述结果。,即使打着文学世界主义的名义把东方国家文学拉入,也很难在这方面取得理想进展,因而他们所刻画的世界文学是不全面的。主要表现于:将东方国家的文学变成西方文学史的插曲或附注,难以写出其相对独立的历史;对东方文学中的名家名著不甚了解,难以写出能够真正代表东方文学成就的内容;在描述西方文学演进或建立西方文学现代性话语的时候,潜在地假定西方文学及思想进展的独立性,不能够在东西方文学文化之间进行横向的勾连,找到来自东方国家的影响;纯粹以西方的文论规范分析解释东方作品,从而使东方文学失去自性,以至贬低、脱漏东方文学的价值;多数关于世界整体文学发展的著述变成了各民族文学的堆砌,文际的交往过程被忽略。②比如布律内尔等所说的普朗波里尼的《文学的世界史》一书,只是无关地平行罗列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并不是世界文学史本身。但埃尔温•拉特的《世界文学史》在重视作品影响和传播等文际方面稍有改观。见皮埃尔•布律内尔、安德烈•米歇尔•卢梭、克洛德•皮舒瓦《何谓比较文学》,黄慧珍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9页。我国的世界总体文学发展研究虽然能够基本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平等对待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但也难免处理上的粗疏和方法使用上的稚嫩,以至于:多数关于世界整体文学发展的著述变成了各民族国别文学的简单相加或堆砌,缺乏把文学的总体发展确立在文际过程上的方法的自觉;人为地划分出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孤立的两大块,而在两大板块之间,以及在各板块内部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上缺乏勾连;将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各自板块的特征凝固化,在板块内部过于强化某国思想文化范式的普遍性,简单地以统一代差异,以放送国的影响代替接受国本土历史的自性和选择的歧向性;有意识地在世界文学总体的发展中拿掉中国这一本地维度,使中国文学独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把世界文学变成外国文学,并将世界关怀变为域外认知③缺失中国一极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不是完整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季羡林先生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特点,应是“把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没有东方文学,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季羡林《前言》,《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我国近年的世界总体文学史研究也有一定改观,较早有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蔡茂松主编的《世界文学发展纲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近期则有陈惇、刘象愚等主编的《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上中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三书在意图和写法上打破了东西方文学的人为划分,系统地把握了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并将中国文学纳入其中,阐述了世界总体文学的多元发展和相互交往关系。。综上,中西方世界总体文学发展研究中的根本失误,在于没有摆脱著者的文化心理障碍和狭隘视界,不能将世界文学的总体发展当作平等共行、相关互联的多维文学整体来描述。
早期的总体文学是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内容之一,他们是不可能做到对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都很公正的。在论及早期比较文学是否曾作为一种摆脱了一切政治及体制的羁绊而向所有语言和文化开放自身的学术努力而出现的时候,加拿大比较学者伊娃•库什纳说:“认为比较文学缺乏意识形态和先在的成见是不真实的。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是在理解各民族文学及其多重历史的根本特征的基础上,或者在以暧昧的精英式国际主义取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希望中蓬勃生长出来的。那时这种研究最多作为民族文学的补充而发挥作用”。[5](P71)在这种背景之下,再加上学者们对于域外文学知识的欠缺,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研究要做到平等对待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把世界文学当作一个相关互联的有机整体来看是不可能的。不过,象法国人布吕纳介那样认为东西方文学之间缺少比较理由的人毕竟越来越少。当代一些学者正在逐渐倡导冲出国别文学和西欧文学中心论的空间,虽然落到实处是很难兑现的。艾金伯勒(Etiemble)、基亚、康拉德、韦勒克、奥尔德里奇、雷马克等人也基本上在这一点上获得了共识。不过我们同时也认为,尽管某些美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西方以外其它文化圈文学的重要性,但他们决意排除掉影响研究的意见,对于当代学者有机地勾勒总体文学内部各民族文学间的文际交往关系将是极为不利的,也就是说,正确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正确的方法。
二、文际交往与“世界文学”的内在肌理
世界文学之作为整体,其内在支撑点是文际交往,换言之,文际交往乃是世界文学的实际运动过程和具体呈现形式。这必然使我们由民族文学关系的形象化描写过渡到“世界文学”概念的本质上来,以便清理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一些论争。我以为,目前比较文学界普遍流行的几种关于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如世界文学是指“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超越各民族和各个时代之上的、广为流传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世界经典作品”,或是“各民族文学的大一统或者融为一体的伟大理想”等)都与文学文际交往的基本精神相冲突,也有违于歌德的本意。如果我们联系上文对世界文学发展基本状态的初步描述,并依据、结合从歌德到久里申等人的思考,就可以对这几种理解中的歪曲成分作出鉴别。
可以说上述几种理解均掐断了世界文学内在历史和动态结构中的纵横关联,或说中断了其内在有机结构中的诸种联系,把“世界文学”当成了僵死的以及虚无飘渺之物来看待。其中,通过“民族文学的总和”或“具有普遍价值的世界经典作品”所作的理解很显然将“世界文学”处理成了各民族文学作品的原子论的堆积和静态的并列物,而所谓“大一统”的理想说则把它当作某种尚未诉诸经验的未来幻想状态,总而言之,这三种理解都是反联系和反历史的。它们长期以来一直主宰世界各国的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研究,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世界文学”无法在有机的动态过程和历史的流动网络中得到体现,并且使人们忽略或遗忘它的真正属于历史和当下的存在形态。首先让我们带着这种怀疑回到歌德。
歌德的“世界文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沿着以上几种理解的顺序加以搜索。非历史的韦勒克找到了歌德提出“世界文学”这个词的历史出发点,同时指出了上述前面两种理解实为误解,其原话是:“‘世界文学’这个术语是歌德首创的。它提出从历史的角度来设想民族文学的演进:它们将彼此混合,最终融汇成一个宏伟的混合总体。如今人们运用这个术语时所赋予的意义是歌德始料未及的。现在它指的是从爱尔兰到新西兰的所有文学;或者是已经成为各个民族的一份共同遗产的古典作品”。[6](P291)这个评论一方面关注到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是着眼于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这一视角的,一方面指出关于这个概念的“所有文学”集合说和“古典作品”说都背离了歌德的原意。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背景是拿破仑战争、民族间的争斗和当时已经形成的民族文学间的频繁交往,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歌德于1827年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一种全球性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其中为我们德国人保留着一个光荣的地位”。杨武能先生认为,歌德前后至少在五种场合谈及“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另外他还有诸如“全人类的文学”这样的提法)。①详见杨武能《歌德与比较文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综合其语境和创作实践,它当含有以下规定:一、世界文学具有将来时态,包含在歌德说过的“未来的世界文学”这样的话中;二、世界文学也是一个具有正在进行时态的概念,比如,歌德说:“一种全球性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这种认识表明“世界文学” 决不是一种非经验的文学形态;三、歌德所感受到的只是他那个时代的“世界文学” 的萌动,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对于世界文学的自觉意识,这种情况表明,世界文学的进程应该是早于歌德的自觉而存在的,因而这种进程非话语地包含着过去时态的存在;四、世界文学的进程已越来越清晰地形成了加速度的态势,人们为此应当淡化民族文学的认同;五、民族文学虽然算不了太大的一回事,但并不是说应当放弃民族文学和民族个性的追求,而是强调各民族文学应当相互交流、“相互宽容”,在世界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归纳上述要点,我们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正是一种已经存在的民族文学间的交往过程;而把“世界文学”理解为原子论的民族文学或其经典的集合的观点,以及把它仅理解为未来时态的观点均遗漏了这一过程。
“世界文学”概念引起的最大误解,莫过于把它抽象化为某种只属于未来的、人们经验不到的文学乌托邦(即上述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第三种理解:所谓的民族文学的“大一统”或者“融为一体”的伟大理想),然而歌德经验地感受到世界文学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对这一理解的有力反驳,因为恰是文际交往过程和语境,规定并赋予这个概念以历史意义。韦勒克明白歌德对于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过渡的说法立足于历史的视角,然而韦勒克毕竟是非历史的,所以他从自己的立场上误解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否定了该概念的民族文学交往性和历史内涵:“文学思想和形式的不断互相交流就酝酿着世界文学;但是这种交流并非是世界文学本身。无宁说它是一种将所有文学合而为一的理想,在这种统一的文学中每个民族都将在一个世界性的音乐会上串演自己的角色”。[6](P291)不难看出,韦勒克把歌德的“世界文学”理解成了“统一的文学”,而且强说这是歌德的意思,这实际上是韦勒克从新批评的形式普遍主义立场上对歌德的误读,在这一理解中,民族文学因融合而消失,似乎越过了语言、国家、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等众多界限(韦勒克的几跨变成了反历史的纯诗符号)而融合为一国,这显然是对文学理想国的一种追求。退一步说,假使这种文学的理想国确能实现,它也必须以民族国家的消亡为前提,但这件事又如何可能?歌德实际上很明白这种尽失个性的跨界融合无异于说胡话,因而说道:“我们重申一遍,这种看法并不是说各民族应当思想一致,而是说他们应该学会互相了解;倘若他们不愿彼此友爱至少也要学会互相宽容”,然而韦勒克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却不顾歌德如此明确申明的意见,仍然牵强附会地评论说,歌德希望德国文学“在统一的世界文学中失去自己的个性”。[6](P292)韦勒克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解释?其目的无疑在于,希望通过所谓的全人类共通的抽象的“文学性”这个概念,来占领“世界文学”的内部空间,悬置文学研究中所有的外部联系,冷冰冰地把交流、交往、历史、世界历史、欧洲的文化历史传统、民族间的殖民关系,乃至于能够让法国人便利地从事影响研究的一切现实历史因素,统统从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中排除出去。
因而,我们有必要在此重申:“世界文学”除了是一种已经存在的民族文学间的交往及其过程,或一种文际过程、一种历史过程以外,并非指别的什么东西。一旦形成这种历史化的意见,“世界文学”多维的内部组织就显现出来了,然而韦勒克所误解的那种“世界文学”的未来大一统却是没有内在维度和张力的,因为民族文学一旦消失,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就无从谈起,或者说是名存实亡,即便存在也无法构成由继承和革新、亲和力和抵抗力辩证交织着的纵横力度关系。
布律内尔、卢梭等人也曾明确反对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总和的观点:“一幢房屋绝不可能只是一堆准备用来建造的砖块,世界文学也绝不会是许多民族文学的并列;或者,换一种说法,因素的总和不等于它们的综合”。[7](P67)前苏联科学院在组织撰写九卷本《全世界文学史》时也明确提出,不应把世界文学看成是各国民族文学的总和,而应看作是初级文学单位所形成的历史流动现象,它们相互制约,在世界历史过程的系统内获得发展,其中,某个民族文学采取与其它民族文学结成发生学、接触学和类型学的关系的方式进入世界文学,这种强调文际过程的意识令人赞赏,但遗憾的是它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8]只有更加有机整合的文学发展观才足以抗拒并压倒上述对于“世界文学”概念的失根的理解。斯洛伐克著名学者季奥尼斯•久里申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了惊人的胆识,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他的一系列论著和编纂如《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1975)、《文际过程分类法》(1988)、《文际过程理论》(1988)、《文际过程是全世界文学规律的表现》(1988)、《什么是世界文学?》(1992)、《独特的文际共同体》 (1993)等,从文学联系和影响规律入手,建立了世界文学的新观念和大容量的文际共同体的内结构。久里申把文学过程分为“民族文学过程”和“文际过程”两部分,这两个过程其实把我们所说的文学发展的网络形态动态化了,其中,“文际过程” 代表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和交往、交际的过程。他提出的“独特的文际共同体”颇类似于布律内尔等人所提出的“文学大群体”的概念,意指受不同情况制约的、内部充满紧密而直接的相互作用的民族文学间的联合体,它的形成条件包括种族、语言、地理、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而且具有为其他的文际共同体所没有的某些规律和异质性、另类性,由于受到各种历史决定因素的影响,这一独特文际共同体具有阶段性变化的特点。从构成上来看,有的文际共同体是在单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的则形成于多语的基础上,但一般是由多民族文学形成的系统,它“既保留各别的民族文学成分的个性特点,又具有得以相连的共同特性”,从级次上说,“民族文学”只是合成文际共同体的初级单位,而“世界文学”作为更开放的系统则是文际共同体中的终极共同体。[8]久里申充分地考虑到了世界文学进程内部可能存在的多种关系,尤其是共同体内部民族文学之间、整合、分化、互补等复杂关系。另外,布律内尔等人提出的“文学大群体”的概念也很有意义,他分出西欧和美国、中欧和东欧、远东、伊斯兰、非洲以及太平洋岛国民族等的文学群体。如果这个级别的、内部充满“相互作用”的群体文学史能够完成,那么世界文学史的描述基础应当说可以得到更好地建立,其结果将会是,“人们从部分综合到部分综合,终于作出全面的综合,写出一部人类文学史”[7](P68-69)。
文学史是一个世界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的进程,但不应理解为民族文学在某一个时刻被世界文学取代了,导致了民族文学的消失。我们认为,在那些表面上看来各民族文学相互隔绝的时代里也同样存在一个文学世界化的过程,总的趋势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和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学世界化的程度越来越加深。有的学者根据文学的交流方式与总体结构的演变,对世界范围内人类文学的发展分成民族文学、近现代文学、总体文学和一体化世界文学四个时代。①参阅曾逸《论世界文学时代》,见他编的《走向世界文学时代: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4、25、71页。这个分类的主要问题在于将“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个时代相互隔绝和对立起来,没有认识到挺进的过程并非是一个诸时代依次被否定的过程,而是一种悖论性的推演。在这一问题上,亚历山大•迪马、康拉德、基亚、霍斯特•吕迪格等人的认识是客观的,他们认为文学的世界化进程自古希腊以来一直都在发生着,至于象歌德那样对“世界文学”有所意识只是后来才有的事。[9](P15)这种认识为我们把世界总体文学的历史当作自古以来就已存在的民族文学的关联运动史和交往过程提供了依据。
[1] Francois Jost,"A Philosophy of Letters",i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74.
[2] 马•法•基亚.比较文学[M].颜保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 霍斯特•吕迪格.比较文学的内容、研究方法和目的[A].比较文学研究资料[C].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5] Eva Kushner,"Comparative Literary History among the Human Sciences",in Comparative Literary History as Discourse:In Honor of Anna Balakian,edited by Mario J.Valdes, Daniel Javitch, A.Owen Aldridge,Bern and New York:Peter Lang,Inc.,European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6]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M].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7] 皮埃尔•布律内尔,安德烈•米歇尔•卢梭,克洛德•皮舒瓦.何谓比较文学[M].黄慧珍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8] 陆肇明.“世界文学” 与久里申的“文际共同体”[J].中国比较文学,1997,(3).
[9] 亚历山大•迪马.比较文学引论[M].谢天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冯济平
On the Literary Intercourse as the Disciplinary Basis of World Literature
WANG Qin-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China)
To describe accurately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ion of literary intercourse between nations as the disciplinary basis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past, many researchers from home and abroad were divorced from the basis, and described “World Literature” as a non-historical, non-interactional and static collection of literary works or a utopia that does not exist. The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ary, points out its fundamental weaknesses, establishes the conception of literary intercourse as its basis, shows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national literature; literary intercourse; disciplinary basis
I1-1
A
1005-7110(2011)01-0043-06
2010-09-26
王钦峰(1965-),男,安徽砀山人,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