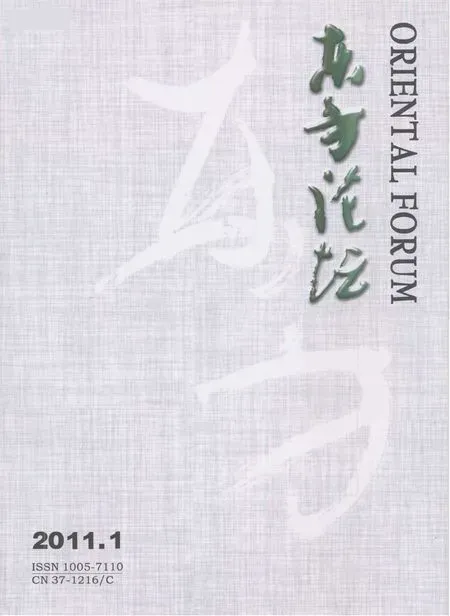《史记》编纂学中的破例问题
舒习龙
《史记》编纂学中的破例问题
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 政法系,广东潮州 521041)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破例问题是中国史学进程紧密关联的重要问题,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史记》立例而又破例,开创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破例现象的先河,解读《史记》破例背后所体现的司马迁的历史编纂思想,必须要从《史记》的撰书宗旨和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用开放的眼光来解读司马迁在史书编纂方面的创造力。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长河中,强调史书体例纯粹性、抨击史家史法乖迁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史学家在评论史书体例破例与否,一定要从历史编纂的实际出发,从历史编纂的指导思想出发,唯有此,对史书编纂破例与否的讨论才“名”、“实”相符,才更有积极的意义。
《史记》;历史编纂学;破例问题;编纂思想;历史情境
史书的体裁体例是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史书的得失成败。杜预在阐释《春秋》之例时,特别强调体例的重要性,他说:“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1]。刘知几更是把史之例视如国之法,指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2](序例第十)。清代学者姚永朴则认为:“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二曰例。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3](P11)由此可见,体裁体例在史书编纂中非常重要。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历史编纂学中的“破例”问题,确实值得仔细考察和探究。古来的史学家将史书体例视为国之大法,坚守史书体例的纯粹性,在前人设计的史书体例的范围内记载历史,固然是史学家珍视历史编纂传统的一种表现,但却不利于启导方来,引领历史编纂的新潮流。而有些史学家不顾客观历史实践和已有历史编纂的原则和经验,不尊重既有历史编纂的传统,根据一己之私创成新例,其“破例”由于不能反映客观真实,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历史编纂中的“严体例之规”和尊重传统、尊重客观实践基础上的“破例”,恰如钱币的“正”、“反”两面,既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正确的态度是既要提倡史书体例严谨完密,反对散漫乖迁;又要鼓励在史书体例上勇于变革创新,在尊重传统、尊重客观实践基础上允许“破例”,鼓励“破例”。
一
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的“破例”问题可以追溯到司马迁所撰的《史记》,最早指出《史记》编纂中存在“破例”问题的是唐朝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刘知几评析史书体例的通常方法是,先追溯该体例之渊源,然后述其流变,再归纳一个简洁的定义,接着便用此定义去检讨相关史书的违例之处。刘氏认为,《史记》“破例”以《本纪》和《世家》最明显。刘氏评论《本纪》之体时,指出:“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又说:“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2](本纪第四)。刘氏评论《世家》时亦指出:“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2](世家第五)以此衡量,《史记》就有乱例问题,因为陈胜起义称王仅六个月就兵败身死,子孙未嗣,封地亦无,“无世可传,无家可宅”,因而《史记》列陈胜于世家,是“名实无准”。另外,《世家》之作应区别诸侯和大夫,“家国本别”,但《史记》竟将一些大夫记入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他还认为,世家应记“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者,而汉代的诸侯王和古代诸侯有很大不同,“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应入列传。而《史记》将汉代诸侯与先秦诸侯并列世家,“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2](世家第五)刘知几对司马迁《史记》首创的“本纪”和“世家”体例不纯问题的分析和评论,引发了后世学者对于《史记》“破例”问题的论争。通过学者之间的争论,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所谓《史记》“破例”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实现“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撰述宗旨的结果,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纪事实录”的必然反映。正如《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指出的:“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品格创新精神的反映。无例,述史无规范,必将流于泛滥。死守成例,不能曲尽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势将流于呆板。因此立例而又破例,是客观情势使然。司马迁恰好是最善于把握情势的历史家,故所创五体能容纳大量的历史素材,有无限的蕴藏力”[4](P167)。这一观点很是精当,《史记》的“破例”是司马迁历史编纂学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历史的客观情势本来就是丰富多彩、变化万端的,史书的体例只有同客观情势相契合,同史学家历史编纂的指导思想相吻合,才能更好地反映客观实际。
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结构均有破例,其中以《本纪》和《世家》最为明显。《本纪》是纪传体史书中的编年体,以帝王为经,按时间顺序记载国家大事。刘知几认为只可为名实相副的帝王立本纪以显国统,只可包举大端,不必载入细节和小事。按照刘氏的观点,司马迁撰写的《本纪》自乱其例。实际上,《本纪》的破例有三:其一,夏、殷、周三《本纪》包括了三代的先公先王,更有《秦本纪》乃是诸侯入《本纪》。其二,《史记》立《吕太后本纪》,而不立《惠帝纪》,竟把帝王逸出了《本纪》。其三,《史记》立《项羽本纪》,却不纪西楚之年,而用“汉之元年”、“汉之二年”记正朔,且记事章法为传体。并且,司马迁写的是一篇《项羽列传》,只不过定名《项羽本纪》而已。要想客观、准确地体味司马迁“破例”的个中真谛,就必须从司马迁的《史记》编纂思想入手,同时结合司马迁所处时代的历史情境,方可收“了解之同情”的历史效果。
关于撰述宗旨,司马迁自己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5](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从《本纪》编纂的主旨、编纂的形式、时间断限上规定了《本纪》记载的内容和范围,着重表明要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考察“王迹所兴”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所谓“王迹所兴”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王”则可以包括帝王、天子,但司马迁决不是仅仅局限于帝王和天子。因此,从实质上来说,裴松之所说“天子称本纪”,刘知几所说“以天子为本纪”,直到清代学者所说的“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等等,都不完全符合司马迁的原意,特别是刘知几指责司马迁“求名责实,再三乖谬”,更是以己意强加于司马迁,从总体上讲,十二本纪的任何一篇都不存在所谓“破例”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决不可拿《汉书》以后对本纪的正统解释来范围司马迁。从历史编纂原则的角度看,学界亦曾对《本纪》“破例”提出过富有价值的看法。宋人林駉就认为:“尝考迁之纪传世家矣,子长以事之系于天下则谓之纪。秦始皇已并六国,事异于前,则始皇可纪也。项羽政由己出,且封汉王,则项羽可纪也。孝惠、高后之时,政出房闻,君道不立,虽纪吕后亦可也。”[6](P294)并认定这是司马迁的撰史原则。与此同时,还特别指出:司马迁为秦始皇、项羽、吕后立纪,正是依据了这个原则,因而是完全合体的。林駉由于摆脱了“以天子为本纪”的思想羁绊,就得出了与裴松之、刘知几不同的结论,这种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另一学者张照则指出说:“马迁之意,并非以本纪非天子不可用也。特以天下之权之所在,则其人系天下之本,即谓之本纪。若《秦本纪》,言秦未得天下之先,天下之势已在秦也;《吕后本纪》,吕后固亦未若武氏之篡也,而天下之势固在吕后,则亦曰本纪也。后世史官以君为本纪,臣为列传,固亦无可议者”[7]。在这里,张照提出应视实际的权、势以立本纪,不以是否为天子以议本纪,辨析了《秦本纪》、《吕太后本纪》之宜立纪的合理性。此外,刘咸炘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本纪之所以能成“一书之纲”,是因为 “本纪……惟一时势之所集,无择于王、伯、帝、后。故太史创例,项羽、吕后皆作纪。刘知几诃之,非也。……司马迁作纪,以项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历年不可中废,年不可阔,故书也。”[8]。刘咸炘的论说破除了正统观念,在深化的基础上揣摩了司马迂的原意,并视项羽、吕后二纪为创例,堪称历史之识见。朱东润则就有争议的《史记》三篇本纪进行了辩论,他认为立《秦本纪》,是企图通过记述秦之先世以明秦及其帝业之所由来,然后才有始皇的成功,突出了“王迹所兴”的事势发展;之所以立《项羽本纪》,是因为秦亡之后,项羽为诸侯之长,以见政由羽出。不为惠帝立纪而立《吕太后本纪》,是因为自惠帝元年始,吕后就是实际的“纲纪天下者”。这三纪都符合司马迁确定的立纪宗旨,而不是以天子为标准的[9](P27)。近人吕思勉也表示了与刘知几等的歧议,认为:“必天子而后可称纪;纪必编年,只记大事;每事又止以简严之笔,记其大纲:此乃后世史体,不可追议古人。……正统、倍伪之别,亦后世始有。项籍虽仅号霸王,然秦已灭,汉未王,义帝又废,斯时号令天下之权,固在于籍;即名号亦以霸王为最尊,编之本纪,宜也;此亦犹崇重名号之世,天子虽已失位,犹不没其纪之名尔。”[10](P14)。吕氏认为所谓天子入“本纪”是后世的标准,后世在正统观念的束缚下所得出的本纪记载天子的原则是不符合司马迁设立本纪的原则的,其观点颇有见地。司马迁的意思是要通过本纪,将王迹兴衰的原始,根据行事的实际,详略有致地区分不同的时代加以条理,进而突出、记述某一历史阶段时势主宰者的事迹,并以此作为认识整个历史的一个纲要。因此,《史记》的本纪是从根本的政治性质上来表现其“通变”思想的。
欲得探求《史记》“破例为体”的真正原因,就必须从司马迁创立本纪体例的目的及其所要完成的使命入手。在司马迁看来,无论五帝和三代先公先王的“积善累功”和“修仁行义”,还是秦之先公相对于中原诸侯的后继勃发,以及秦楚之际的陈涉发难和项羽称霸,无一不是夏、商、周、秦、汉帝王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据实载录这些先公先王的历史,才充分揭示出了他们统一天下的艰难;同样,正是通过秦楚之际的历史大变动的载录,才充分反映出这一特殊时段完成一统、成就帝业的迅疾和猛烈。有鉴于此,司马迁的这些“破例”实则传达了隐没在帝王统绪背后的宝贵历史信息,他促使后来者将眼光投向所谓“先公先王”的历史,并逐渐认识到对先商、先周和秦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种群雄竞立的多元文化格局中,中国古代文化才最终完成了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一个由尧、舜、禹至商汤、周武的古代圣王统绪,逐渐沉淀为华夏诸族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心理的基础结构。所述这些,正是司马迁写作《史记》和创立本纪体例的基础和前提。
二
“世家”是《史记》五体中比较复杂的一种。它是用编年兼纪传的形式,记载捍卫天子的诸侯、有功于国家的勋贵、于民族有杰出贡献的先贤、于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俊杰的家族或个人的历史和事迹。《世家》的破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楚王熊心应立《世家》。项梁所立楚王熊心,曾统兵遣将,号令一方。刘邦入关,项羽北救赵,均为楚王熊心所遣。项羽杀宋义自号上将军犹假号楚王之令,入关后尊楚王为义帝。司马迁既不为之立“本纪”,亦不为之立“世家”。其二,汉初诸侯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刘安,衡山王刘赐,均因叛逆而降为“列传”,而西周诸侯管叔叛逆,宗庙不守,却有《管蔡世家》。其三,汉初功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爵禄不过封侯而立“世家”,但其他侯国不立“世家”,而且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封为诸侯,又历传数代,亦不立“世家”。其四,三十《世家》中有孔子、陈涉、外戚三《世家》。孔子为布衣,陈涉称王不终,汉帝后妃无世可传,但均立“世家”,其例云何?《史记》世家的人物、侯国的构成可谓林林总总,但在哪些人可以入“世家”的问题上,司马迁有其明确标准,这就是“非天下所以存亡”者不著[5](留侯世家)。司马迁遵循这一原则而确定可入世家的人物和侯王:列入世家的个人必须是对天下兴亡有特别影响之人;列人世家的侯王必须是对历史的发展、王朝的兴衰发挥了重要作用者。据此不难看出:要评判 “世家”体例是否“破例”,其重要依据只能是《史记》本身所提供的内容。如果撇开《史记》,先在头脑里勾勒出某种定义或观念,并据此来评论《史记》破例,则往往很难得出与事实相符合的正确结论。
以往的学者在探讨世家体例时,不乏强调世家专指“王侯传国”、“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之论。刘知几曰:“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欧抑被诸侯,异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5](留侯世家)浦起龙曰:“由周而来,五等相仍。当子长时,汉封犹在,故立此名目,以处夫臣人而亦君人者。”王若虚曰:“迁史之例,唯世家最无谓。颜师古曰:‘世家者,子孙为大官不绝也;诸侯有国称君,降天子一等耳。’虽不可同乎帝纪亦岂可谓之世家?且既以诸侯为世家,则孔子、陈涉、将相、宗室、外戚等复何预也?”[12](卷十一)这些学者以自己理解的“世家”概念来框定《史记》世家的含义,造成对于《史记》世家的解读与司马迁创制世家的本意的大相违背。比如在《陈涉世家》和《孔子世家》的解读方面,他们的观点在现在看来确有可资商榷之处。刘知几就明言司马迁将陈涉的事迹列入世家不当。在其所著《史通•世家》篇中谈及:“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程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从刘知几指责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所持的理由来看,刘知几并没有窥见司马迁作《陈涉世家》的意旨。章学诚对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与刘知几持着相同的看法,认为是“名实不正”[11](驳张符理论文)。陈涉之所以被列入世家,司马迁说得很清楚:“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5](太史公自序)。在《陈涉世家》结尾处,司马迁说得更为透彻:“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显然,司马迁作《陈涉世家》的主旨在于肯定陈涉的首事亡秦之举。司马迁看重与推崇的是陈涉对历史进程、历史发展所起的重大的推崇动作用。对于《孔子世家》,学者们亦陈述过自己的观点。王安石说:“其列孔子为世家,奚其进退无所据耶?孔子,旅人也,栖栖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以传宜矣,曷为世家哉?岂以仲尼躬将圣之资,其教化之盛,舄奕万世,故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极挚之论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所谓多所抵牾者也。”[14](P359)王安石认为孔子无王侯之位而入世家,不合世家体例,因而《史记》列《孔子世家》为破例。理解《孔子世家》非破例的关键是从《孔子世家》原文中找到答案。《孔子世家》赞语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司马贞曰:“孔子教化之主,吾之师也,为帝王之仪表,示人伦之准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继代象贤,诚可仰同列国。前史既定,吾无间然。”张守节曰:“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於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正因为 孔子是圣人、教化之主,列诸世家之目的是为了尊崇孔子,由此观之,其体例是非常精良的。盖列之本纪无所系,侧于列传非所伦,以布衣而上同列国,尊圣之心。《史记》中有《仲尼弟子列传》,载孔门弟子七十七人,又有《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说:“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儒林列传》还详尽记载了从春秋到汉代的儒学传授情况,以显示和强调孔子开创儒学统纪垂范后世。郭嵩焘曰:“高帝始以太牢祠孔子,太史公适鲁得观孔子庙堂,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儒林传》亦称:‘陵夷至秦,天下并争于战国,然齐、鲁间学者独不废。’是孔子之道因是以自世其家,不待后世之追崇也。史公列孔子于世家,自纪其实而已。”[15](卷四)。《儒林列传》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太史公自序》更将孔子作《春秋》与汤、武革命并称,都可见孔子学说对后世影响至巨。《自序》云:“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迫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正是从孔子关天下治乱盛衰这一角度,申述了作《孔子世家》的理由,而《史记》全书,始终贯穿的就是这样一种认识。
显而易见,研究《史记》世家的概念一定要从司马迁撰书宗旨和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用开放的眼光来解读司马迁在史书编纂方面的创造力。朱东润和刘咸炘对世家的解读就很切合司马迁撰述世家的本旨。朱东润曰:“周汉之间,凡能拱辰共毂,为社稷之臣,效股肱辅弼之任者,则史迁入世家;开国可也,不开国可也;世代相续可也,不能相续亦可也。乃至身在草莽,或不旋踵而亡,亦无不可也。”[9]刘咸炘曰:“世家二字,本不可泥。若必泥于其字,则既已传国,何以无家?既已数世,何为无世?后之传国固有及十数世者,岂遂可为世家邪?”[8]这就是说,王侯传国未必就符合世家的要求。司马迁之所以撰写《史记》,是因为他要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来探求治国之道。“世家”一体,之所以多载王侯贵族,是因为他们对历史发展、国家治乱的影响不仅巨大,而且久远。从世家的创作宗旨到各世家的具体写法,均可看出,作者注重社会治乱,留意“成败兴坏”,用心良苦。世家所表现的“通变”特点,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所主张的大一统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其载录的内容看,三十世家并不存在“破例”的问题。
三
自刘知几抨击《史记》体例开始,有关《史记》破例问题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从自身的立场、观点出发,按照自己对历史编纂的理解来诠释《史记》的体例,所得出的结论往往相左。如何看待《史记》破例与否,实则关系到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司马迁的不朽名著《史记》之所以成为传统史学的楷模,其重要原因即在于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主要包括:司马迁自觉地构建规模宏伟的史著,“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配合,构成社会的“全史”,可谓容量广阔,博大精深;其重视记载人物的活动,多方面地、深刻地表明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它并非停留于单纯记述史实,而是勇于提出对于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并通过撰史来表达独立的思想体系。每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的创立,和历史编纂的每一项改进,都是通过历史思想领域取得新的创获而实现的,都是编纂思想的更加进步、更加合理、更加严密而带来的成果,都是历史学家在哲理上获得新的灵感的生动体现。在历史编纂领域内,探讨历史学家编纂思想的成就是关键的环节,研究其在体裁运用、体例处理上的具体做法,也必须结合其思想上和观点上的创获,才能有恰当的理解和合理的解读。因此,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考察,就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以历史编纂思想研究《史记》的破例问题,实际上是个伪问题,产生这样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从《史记》本身所提供的内容来解读《史记》的编纂思想,没有探索《史记》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而是先在头脑里形成某个定义或观念,并据此来评论《史记》破例,因而很难得出与事实相符的正确的结论。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长河中,强调史书体例纯粹性、抨击史家史法乖迁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史学家在评论史书体例破例与否,一定要从历史编纂的实际出发,从历史编纂的指导思想出发,唯有此,对史书编纂破例与否的讨论才“名”、“实”相符,才更有积极的意义。
[1] 杜预.春秋左氏传•序[M].皕忍堂刊兰印本,1926.
[2] 刘知几.史通[M].张之象刻本,1577.
[3] 姚永朴.史学研究法[M].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38.
[4]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5] 司马迁.史记[M].冯梦祯本,1596.
[6] 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后集[M].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 张照.殿本史记考证[M]. 武英殿校刊本,1739.
[8] 刘咸炘.史学述林•史学体[M].成都尚友书塾,1929.
[9] 朱东润.史记考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0] 吕思勉.史通评[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1] 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世界书局,1935.
[12]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M]山阴祁氏淡生堂抄本.
[13] 章学诚.文史通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4]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 郭嵩焘.史记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责任编辑:侯德彤
Rule Breaking in the Compilation of Shih Chi
SHU Xi-long
(Dept of Politics and Law,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41, China)
The issue of rule breaking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important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and has exerted huge influence over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examples of breaking rules must be studied from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at period, and Sima Qian’s creativity in compiling historical books must be interpreted with an open mind.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discussion of breaking rules in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be of significance.
Shih Chi; historiography; issue of breaking rules; compiling guidelines; historical context
K092
A
1005-7110(2011)01-0009-05
2010-11-09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历史编纂的演变路径、主要成就与当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A770043。
舒习龙(1968-),男,安徽巢湖人,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