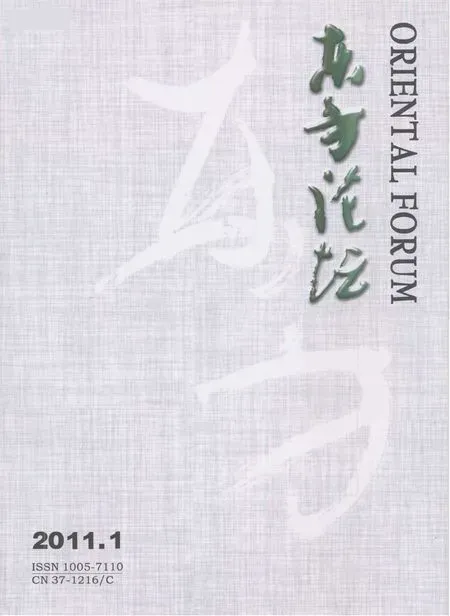殖民地时期及建国初期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
崔丽芳
殖民地时期及建国初期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
崔丽芳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71)
殖民地时期及建国初期,美国人中国观形成的基础是传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和来自欧洲的关于中国的文字叙述。前者将一个想象中的精致、优美、光亮的中国形象直观地呈现于美国人面前,成为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之一。后者则使美国启蒙学者承袭了欧洲思想巨擘们的中国观,从观念和理论上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古老、文明、智慧、富庶的中国形象。早期美国人在继承欧洲人所塑造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的同时,也曾利用这一形象构筑美国精神,建设自己的新家园。
中国形象;早期美国人;启蒙运动
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曾风靡欧洲社会的“中国风”并未全面波及到北美大陆。而十八世纪中叶之后,随着中国商品的不断输入,早期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有了直观印象。与此同时,大量耶稣会士和欧洲思想家们有关中国的著作的译介更使美国人从思想上承袭了不少欧洲人对中国的见识。总的来说,在早期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个古老、智慧、富庶的文明礼仪之邦,这种对中国文化羡慕和推崇的态度尤其体现在以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托马斯•佩恩(Thomas Paine)、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代表的美国开国元勋兼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议论之中。他们的中国观既师承于欧洲,又突出地反映了美国启蒙时期的时代特征。本文在考察殖民地时期及建国初期美国人中国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的基础上,试图从北美大陆对中国的初步印象和美国思想家议论中国的文字中找寻出较清晰的线索,从而论证早期美国人在继承欧洲人所塑造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的同时,也曾利用这一形象构筑美国精神,建设自己的新家园。
一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正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其商业殖民势力开始向东方及世界各地大肆扩张,而随之而至的是各种身份的旅行家或冒险家,他们在各自的游记作品中向欧洲人传达着有关中国的有形信息。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们开始在中西交流的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由于“受他们所接触的有文化的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观念”的影响,同时出于“传教团为自己鼓劲以应付艰巨的使命和刺激其身在欧洲的基督教同胞支持他们的努力、相信他们的努力会取得成功的需要”,[1](P64)耶稣会士们对中国进行了更加丰富、全面和深刻的描述,他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又给正在为处于变革前夜而前途未卜的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和宗教的发展而苦思冥想的的欧洲思想家们提供了一种证据,后者戴上理性的眼镜,将纳入自己视域的中国文化同欧洲现实社会进行比较,由此出现了对中国的或褒或贬的种种议论。由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观念两种因素所导致的席卷整个欧洲的“中国热”,使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有关中国的各种书籍出版蔚然成风。根据约翰•勒斯特(John Lust)所辑的《及至1850年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记载,考迪耶(Henri Cordier)在《汉学目录》中收录的1600至1799年间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作品就多达1489条。虽然许多条目是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但这也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在十七、十八世纪曾激发了不少欧洲人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产生了难以比拟的深远和持久的影响。[2] (P98)
当处在社会制度和运行机制变革之中的欧洲人正在努力打通通向东方的道路,并由此翻开与东方关系的新的一页时,位于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大陆则迎来了自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来自欧洲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移民热潮。远涉重洋的大部分普通移民移居美洲的主要动机是对财富的追求,而新大陆的创业生活一开始必然是艰苦的。学者莫里森在考察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历程时,曾试图为当代读者再现十七世纪弗吉尼亚殖民区移民们的生活环境:
当我们想到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时,首先应当从我们头脑里清除掉情男美妇、穿绸裹缎、终日悠闲的骑士生活神话,那都是十九世纪的政治家和浪漫主义小说家们臆造出来的。我们必须这样想象:沿着詹姆斯河、约克河和拉帕哈那克河直到瀑布线,两岸分布着一连串田庄和种植园。……一般田庄面积不超过三、四百英亩,由庄主及其家人和一些男女白人契约佣工耕种。住房是一所带矮阁的木造农舍。冬天燃烧大段圆木取暖;农舍四周是菜地和果园;外面就是种玉米和烟草的大田,用劈开的木条编成曲折的栅栏圈围起来;栅栏以外是林地,放养着牛群和猪群。……直到1650年,在詹姆斯敦以外马是很少见的,车辆更少。[3](P57-58)
北美生活条件的艰苦以及它所包含的开发的潜在可能性同时展现在移民者面前,及至十八世纪中叶以前,他们一直坚持以务实奋斗的精神忙于建设自己的新家园,而根本无暇顾及太多的享乐,更不消说去享用只有欧洲贵族闲适阶层才有可能拥有的来自中国的诸如丝绸、瓷器、家具等奢侈品了。因此,对于刚刚开始创业的早期北美人来说,中国无疑是个陌生的异域之国。即使极少数显赫之家能摆出几件通过间接贸易购进的精美的中国商品以炫耀邻里,中国充其量也只是作为一种由淡雅纤细的瓷器和雾绡轻裾的丝绸反映出来的海市蜃楼般幻象存在于北美人的印象之中。
造成殖民地时期北美人对中国的隔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美国曾起了非常普遍而持久的影响的清教信仰。虽然北美移民中清教徒只占少数,但清教传统却在美国历史、文化和国民性格等各方面留下了它的烙印。“清教徒前辈移民”移居美洲的最初动机与大多数普通移民无异都是为了谋生,为了过更好的生活。但不同于后者的是,他们同时具有相当明确的宗教目的。正如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区总督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在他专门为自己于1630年率领的著名的“大迁移”所写的《基督教博爱的典范》布道文中所宣称的,清教徒们去新世界的目的不是积财致富,而是为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宗教社会,“修身养性,为上帝,为我们身为其成员的基督教的加强和发展而尽更大的力量,以保证我们自己和后代更能免受罪恶的今世里普遍堕落现象的侵蚀,为主服务,在主的圣示的威力和圣洁的感召下争取得到拯救”。[4](P2)北美的清教徒们是曾在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所创立的神学教义的忠实信徒。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强调上帝是一切,而人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教民必须按照上帝的诫命和律法生活,遵守严格的宗教和道德原则,外御堕落和罪过,内防任何异端分裂,以使后世永享上帝的恩赐和慈悲。不可否认的是,清教主义具有某种严刻、偏激的因素,但作为一种宗教和一种社会势力,清教在北美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殖民地时期和清教徒定居的新英格兰地区。
当然,十七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徒并不可能都是清教教义中所宣扬的那种戒酒禁欲、不苟言笑的苦行僧,但神学家们对上帝律例和诫命的竭诚恪守和对衣粗食淡的简朴生活的大力推崇,必然会遏止清教徒们享受包括中国瓷器、丝绸、家具、装饰品在内的生活奢侈品的欲望。此外,务实的清教领袖们在北美殖民地初建时期更关注的是自己教区内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建设与完善问题。加之清教徒本来就与虽主张在天主教内进行改革、但仍坚决反对新教的的耶稣会格格不入,因此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兴趣去步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们的后尘,派教士亲赴中国传教。即使进入十八世纪,当耶稣会士们被禁止在华传教,与此同时,殖民地的人口和财富在不断地增长,北美新教各教会仍没有对派遣教徒赴华传教表现出任何兴趣,而是坚持固守家园,致力于历史上被称为“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旨在重申加尔文信仰立场,重新激起北美人自己的宗教热情。“大觉醒”的核心人物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就曾明确表示:“上帝更让我们眷顾我们自己国家的人民,而不是那些中国人”。[5](P45)当然,爱德华兹的言论并无对中国的毁誉之词,他的态度只是说明了中国在十八世纪确实还没能激起北美新教教士们的兴致。也许在这些虔诚的神学家们的印象中,中国至多是一个由不信上帝的异教徒们组成的遥远国度。
二
鉴于上述所分析的历史和宗教方面的原因,我们不难看出曾风靡欧洲的“中国热”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未能全面波及到北美殖民地。不过,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情形则大不相同了。首先,经过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建设,北美人物质生活水准日益提高。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世俗兴趣使他们对中国商品有了更强烈的需求。虽然在北美十三州独立之前,中美之间并无直接贸易往来,但转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进的中国货已成为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人家庭中的必需品。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之一“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因英国政府的《茶叶法案》所引发的。[6](P1-2)除对茶叶的大量需求外,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不少美国人对其它中国商品和中国式风格也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十九世纪初期,波士顿和塞勒姆地区的住宅里陈设的瓷制茶具约有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是从中国来的。在费城地区,不限于上等人家,普通人家一般都有几件中国瓷制茶具和餐具。还有一位曾出使过中国的荷兰人万•布拉姆(Van Braam Houckgeest)①万•布拉姆(Van Braam Houckgeest)曾于1794至1795年代表荷兰出使大清帝国,后加入美国国籍。他根据自己的出使经历写了《1794至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行记》(Voyage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4& 1795)一书。在定居美国费城后,于1796年仿照中国的建筑风格建造了一幢房子,取名为“中国退隐园”(Chinese Retreat),屋内全是古色古香的中国情调的立体布置,四周陈设着种类繁多的中国古玩、诗、画等艺术品。[7](P76)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物品和文化如此喜爱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清教传统所提倡的务实精神,而并不完全像某些学者所推断的是由于人们“对占支配地位的古典模式感到不满,”因此“希望通过引进新颖奇特的中国商品和风俗习惯来排遣他们胸中那种古典主义的单调乏味感”[8](P20)。北美独立战争中的活跃分子之一、建国后担任美国国会秘书的查尔斯•汤姆森(Charles Thomson)就曾在为费城的《美国哲学学会报》第一卷所作的前言中指出:“引进古老的东方国家的产物,特别是中国的物产,我们这个国家将可以获得期望已久的空前发展。我们如能有幸引进中国的工业、生活艺术、进步的管理以及当地的植物,美国终将有一天会成为像中国那样人口兴旺的国家”。[7](P77)可见,虽然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在风靡欧洲的“中国风”逐渐波及到了北美殖民地以后仍相当有限,但他们对中国产品的青睐充分说明了通过有形物质传播到美国的中国形象大体上是积极和美好的。
美国人对中国的初步印象不仅仅是通过中国商品获得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受了欧洲中国观的影响。构成十八世纪欧洲人认识中国的主要来源包括旅行家或冒险家的游记、耶稣会士的介绍和描述以及思想家们提及中国的著作。学者米勒(Stuart Creighton Miller)在他的专著《不受欢迎的移民:美国的中国形象,1785-1882》的引论部分中曾谈到,中美贸易开始之前,即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北美殖民地所建的图书馆中关于中国的书籍寥寥无几,……即使像富兰克林和杰斐逊这样见多识广的大人物们也只是在他们人生历程的后期才偶尔碰到中国这个题目的”,而“殖民地时期的出版商与那些开国元勋们所表现出来的一样,无一例外地都对中国缺乏兴趣”。[9](P13)然而,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826年以前,在费城和其它地方出版的涉及到中国的书籍至少不下三十几种。另外,报刊、杂志也登载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因此,另一位学者奥尔德里奇(Alfred Owen Aldridge)在考察了这些文献后,得出了与米勒相异的结论:“到十八世纪末,在伦敦或巴黎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文字中所囊括的每一种思想或每一项内容都曾在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美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过”。[5](P8)
毋庸置疑的是,欧洲著作的大量译介对当时启蒙思潮在北美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北美启蒙运动的兴起虽然较之欧洲要晚半个世纪,但这却有益于它直接师承于后者,并使北美人有充分时间考虑选择这一运动中最有助于解决他们自身问题的思想和理论。从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文献和思想家的著作中不难发现,对美国启蒙运动影响较大、人们引用频率较高的首先是英国思想和法国思想,这其中就包括英法哲学家们的中国观。[10]前面谈到,耶稣会士所介绍和塑造的中国形象曾为启蒙时代的欧洲学者们思考自身社会的现状和弊端提供了一种参照,他们在各自的视界中立足于自身需要,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发表了见仁见智的各种评述。虽然其中不乏囿于文化成见的批评之声,但大多数人则对中国持有基本肯定的态度,如伏尔泰(Voltaire)就极为赞赏中国的道德和理性宗教,他曾在《自然法赋》中阐明要以儒家的理性道德来挽救欧洲的时弊。他还十分推崇中国的开明君主制和中国以官吏选拔制和谏议制度为基础的完善的行政组织,并且赞美中国4000年一贯充满“仁爱”观念的法律;赞美中国从印刷术、陶瓷、玻璃、养蚕术、纺织术到农业和建筑的物质文明。霍尔巴赫(Baron d'Holbach)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也曾分别在各自的著作中称赞过中国政治思想的合理性和儒家的道德哲学,如前者在《社会之体系》中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理性对于中国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后者在为《百科全书》写作“中国”和“中国人的哲学“条目时称赞孔子学说简洁可爱,其中的理性教和实践哲学尤其值得敬佩。向来被划入“贬华”派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也格外看重中国的礼治之术和孔子的道德教义,他甚至认为中国专制之弊可以用孔子的教义来补救。[2](P123-124)
欧洲学者对中国儒教和政治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无疑感染了正被启蒙和理性观念充盈着的美国思想界。当译成欧洲文字的有关中国文化和宗教的书籍被传到北美时,人们争相阅读的热忱不亚于欧洲人。仅就孔子经书而言,到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在美国就已出现六七种译本。[11]其中英译本中最为著名的是马士曼(Joshua Marshman)的《论语》,它是英语世界中第一部直接译自汉语的译本。该译本不仅成为半个世纪后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中国经典》时的重要参考,也是日后美国超验主义思想家爱默生和梭罗东方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梭罗还从中选取了21段格言发表在了1848年4月的《日冕》上[12]。除对儒家经典的引介外,中国文化的影响还见诸于美国启蒙思想家们的笔端。他们通过在公开场合或发表的文字中提及中国时,表达了对心目中这个值得效仿的大国的景仰之情。
三
与思想积淀深厚的欧洲文化巨擘们相比,美国早期学者对中国的认识不免显得有些单薄和零乱。但中国国强民富、道德高尚、实行开明政治的美好形象确实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了十分清晰的痕迹。美国开国三杰之一、被称为美利坚民族之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对中国文化钦羡备至。他的好友、英国外交官本杰明•沃恩(Benjamin Vaughan)对他的“亲中国情结”似乎有相当的了解。沃恩曾对最早出版《富兰克林作品集》的其中一位编者说过:“富兰克林很喜欢读关于中国的书,他甚至表示如果能年轻几岁,他必定要亲赴中国”。[5](P25)的确,有证据表明富兰克林可以算作美国颂华派的领军人物。早在1738年,富兰克林就曾在他自己创办的《宾夕法尼亚报》上连续3期刊载了《孔子的道德》一书的部分内容。该书原是法国新教教士拉•布律纳(Jean De La Brune)译自拉丁文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法译本,在伦敦出版的是这本书的英译本①该译本是将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的法文节译本La Morale de Confucius (Amsterdam, 1688)转译成英文,出版于1691年。该译本因属间接翻译,并不为欧洲知识阶层所看重,但却成为当时英语世界普通读者了解孔子和中国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参见王辉、叶拉美《马里逊与马士曼的〈大学〉译本》。。富兰克林摘录的正是英译本中有关《大学》的一小段内容。事实上,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报》是以刊载陆海战事、宫闱秘闻、民族习俗等方面的文章而赢得北美人极大欢迎的一份报纸,“下至平民百姓、上至总督、议员和各级官吏,都为费城有了这样一份出色的报纸而感到欣喜和自豪,他们毫不掩饰对这份报纸的偏爱,年轻有为的办报人富兰克林的名望也因此大大提高”。[13](P63)在这样一份使自己名利双收的报纸中专门登载中国儒家经典的教义,富兰克林对中国的兴趣和青睐由此可见一斑。
富兰克林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的肯定和推崇无疑是受了欧洲思想家们的中国观的浸染,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生坚持奉行的道德原则和生活信条与儒家教义中所提倡的与人为善、修身养性的思想有明显的契合之处。富兰克林在年轻时就已注意培养自己的品德,他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充分体现在他著名的《自传》中,如他在其中的第二部分列出的修身表格中就为自己规定了十三条要培养的美德,包括节制、沉默寡言、生活秩序、决心、俭朴、勤勉、诚恳、公正、适度、清洁、贞节、谦虚等,每周着重于一条,每年循环四次,如此不懈地努力修身,以使自己完善,并由此可以证明人是可以达到完善境地的。[14](P126-127)不难看出。富兰克林的道德修养准则与儒家的道德人本主义思想如出一辙。根据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人生来是善的,但要保持先天的善,他必须进行自我修养,犹如美玉须经雕琢方可成器,因而,人的终生学业就是学做人,学会与人为善。正如孟子的这段话: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①出自《孟子•告子上》。
由此可见,儒家推崇的自我修养和富兰克林提出的道德自修所依据的都是人的可完善性,注重现世和乐观主义也是二者共同具有的特征。当然我们目前尚无证据证明富兰克林是否直接从儒家教义中受益因而形成自己的人本主义的道德观,但可以推断的是,他至少在其中发现了能够利用的现成的观念和思想,这就难怪他为什么会在自己创办的颇有影响的报纸上连续三期刊载有关孔子学说的内容了。总之,朴素的人本思想和踏实的务实精神使富兰克林青睐于儒家学说中最能适用的部分,即自立和自修,而开创这样一种理想道德哲学的孔夫子在他的心目中自然就是一位伟大的道德伦理思想家了。
中国圣贤之师的美好形象寄寓着西方启蒙哲学家的一种政治理想与道德教育理想,成为他们改造社会历史的思想工具。与此同时,这个“乌托邦”的形象还被欧洲当时的一些自然神论者们赋予了一种理性宗教的色彩。这些人自称为“自由思想家”,他们并不否定宗教的存在,但反对天启论,反对超自然的、神秘的东西,主张一种“自然的”、合理的宗教。他们从耶稣会士对儒教的描述中发现中国人所说的“天”与“天道”与他们所称的“自然”在精神上大体相近。所以孔子学说给这些自然神论者们一个有力的佐证,使他们得以用“中国人的议论”来向传统的天启宗教进攻。[2](P125)出生在英国,曾先后投身于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思想家兼作家托马斯•佩恩就是这样一位视孔子为精神导师的热忱的自然神论者。他曾在《理性的时代》这部杰作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宗教观,旨在借助理性,拨开“基督教神话家”所散播的迷雾。佩恩指出,理性——而不是神启——为人的正确向导,而基督教的圣子之说和古代神话家们的偶像崇拜毫无二致,都是为权力和金钱的目的服务的,应当通过理性和哲学消除这种迷信。佩恩的宗教观并没有否认上帝的存在,但《理性的时代》仍激怒了欧美圣坛,甚至有人将曾出版过这本书的一位伦敦书商告上了法庭。针对宗教保守主义者们的攻击,佩恩给予了驳斥。他在致这场官司中的控方律师托马斯•厄斯金的一封公开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基督教的源头——犹太信仰本身充满了迷信之说,同时又缺乏道德约束,基督教因而已丧失了其原来具有的权威性。而相比之下,中国儒教则是富于理性、道德纯洁的宗教哲学。犹太信仰与中国宗教同是源远流长,且中国历史与犹太历史相较更为古老悠久,但为什么二者之间存在着如此本质性的差异呢?佩恩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两个民族性格的不同,“中国人温文尔雅,道德高尚,犹太人则是急躁好动,顽梗不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有着良好修养和性情的民族的宗教置若罔闻,却将毫无理性的犹太人奉如神明”。[15](P805)佩恩还在他发表于自然神论者的专门刊物《前景》中的一篇文章中说道:“作为一部道德哲学方面的作品,《圣经新约》中有几部分还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早于耶稣出生的好几百年前,东方世界就已经有这样的思想了。比耶稣早出生五百年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就曾说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②出自《论语•宪问篇》。这样的话”。[15](P805)可见,在佩恩的心目中,中国儒教文化就是理性和智慧的代名词,而其开创者孔子不仅是精神导师,也是伟大的宗教启蒙者。
美国思想家所继承的欧洲启蒙哲学家们的中国观不仅仅包括对儒学的尊重和美化,还体现为对中国农业社会经济模式的推崇。对中国农业的赞美声,早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tz)和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那里就能听到。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人物波维尔(Poivre)更为欧美启蒙思想家们直接提供了关于中国农业的情况。其著作曾在巴黎出版多次,受到了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魁奈(Franscois Quesnay)的关注。魁奈生活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当时法国推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而农业却日益衰落,大量农民破产,整个国家的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魁奈对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创立了比较完整的重农主义思想体系,而中国以农为本的社会生活模式恰为这一体系提供了一种现实证据,他因此指出,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自然秩序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样一条真理,“只有中国是个例外”。[16](P221-222)他还在《中国专制制度》一书第二章的两节中专门谈了“中国的农业”和“附属于农业的商业”,并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合法专制政治”可算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形式了,中国的重农主义使之成为农业国的典范。[2](P124)当然,魁奈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绝对拥护者,如在经济政策上,他笃信不干涉主义和流通自由,即将贸易从政府的制约下解放出来,这与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大相径庭。魁奈还指出过一系列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落后之处。这种亦褒亦贬的中国文化观自然影响到了正在从欧洲哲人那里尽情汲取精神食粮的美国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认识。但与贬抑之言相较,重农学派对中国的褒扬之词似乎给后者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如富兰克林,他除了对中国儒教文化颇有好感外,还对中国的现实社会模式产生了兴趣。他购买了关于中国的书籍,甚至认真地打算派使者到中国,以使“年轻”的美国可以学习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生活组织。[17](P5)富兰克林还希望美国能在较短时间内拥有同中国一样的资源和财富,他曾在自己于1768年创办的美国哲学学会会刊第一卷的致意引言中提到:“假使我们非常幸运地能够引进中国的工业、他们的生活艺术和畜牧业的改良方法……,在将来的某一天,美国可能会变得像中国一样人口众多”。[18](P124-125)
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中,对中国的农业立国政策最为推崇的当属曾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而杰斐逊的中国观又和他的社会理想和治国策略密不可分。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杰斐逊就反对发展工业,主张把美国变成一个农业国家,并且勾画出他的农业理想国的蓝图。在这个理想国中,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是农民,他们可以享受经济上的独立、自由的地位;人人有文化知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爱关系代替了金钱关系;人人可以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过一种悠闲幸福、安居乐业的生活;禁绝投机、赌博等歪风,人人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19](P481-482)杰斐逊的这种以农立国、以农民为主体的美好社会理想显然受到了重农学派的极大影响,而这种影响自然使他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赞赏有加。他曾直言道:“我不希望我国去发展贸易或航海业,而应与欧洲一起去效仿中国,使我们的社会保持中国那样的状况,这样,我们就能避免战争,所有的公民就都能过上农民的日子了”。[5](P45)由此可见,杰斐逊把中国作为他在美国建立农业理想国的楷模。此外,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采取的超然孤立的态度也为他坚持美国建国伊始就已开始推行的政治孤立主义政策提供了一种参照,他因此认为美国也应像中国那样孤立于欧洲之外,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纷争。也可以避免美国沾染欧洲的邪恶、动乱和腐败,以保持美国农业文明的纯洁性。[5](P45)
综观殖民地时期及建国初期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美国人的中国观形成基础是传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和来自欧洲的关于中国的文字叙述。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并不完全是欧洲中国观的翻版。这是因为,北美殖民地文化虽然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尚未独立于欧洲文化,但拓殖者所笃信的清教主义使美国文明从本质上既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又致力于务实的世俗追求。这种看似矛盾而实则统一的文化传统影响了早期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使他们有选择性地继承了欧洲人的中国观,如富兰克林青睐的是中国儒家学说中有关道德自修和情操培养的部分。此外,欧洲人所描述的中国人崇尚劳动与节俭、家庭观念强以及以农立国的传统则契合了清教传统中反对奢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责任等信条,同时也为美国民主思想的杰出代表杰斐逊所设想的农业社会提供了一种现实证据。当然,中国形象无论是表现为富兰克林所景仰的德行之邦,还是杰斐逊所推崇的农业乐园,都是西方文化中乌托邦从文学描述到历史现实的一座“美丽的栈桥”。[20]第一次利用中国形象将传统的理想国引入的是声势浩大的西方启蒙运动。美国启蒙运动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继续,也是西方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美国思想家们一方面师承欧洲哲人在道德政治期望中塑造“美好的中国形象”,并试图将具有乌托邦特征的中国形象当作社会批判与变革的武器;另一方面,美国启蒙学者面临着欧洲人不曾遭遇的艰巨任务,即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而中国形象恰恰为美国开国元勋们构筑美国精神,建设美国民主提供了某些灵感和参照。虽然这一异域乌托邦的理想状态仅仅是美好的幻想,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但他们效仿中国的愿望和努力,对当时的现实变革还是有启迪作用的。(本文系笔者2005年博士论文《被俯视的异邦——19世纪美国传教士著作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第一章第一节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为笔者原创,特此声明)
参考文献:
[1] 雷蒙•道森. 中国变色龙[M]. 常绍民等译.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2] 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M].纪琨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4] 常耀信. 美国文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5] Alfred Owen Aldridge. 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M].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李定一. 中美早期外交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 梁碧莹.早期美国商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介绍[A].陶文钊.中美文化交流论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 Jonathan Goldstein. 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1682-1846[M].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9] Stuart Creighton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1785-1882[M].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10] 李永清.略论美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渊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
[11] 常耀信.中国文化在美国文学中的影响[J].外国文学研究,1989,(1).
[12] 邸爱英.马殊曼与世界第一个〈论语〉英译本[J].读书,2009,(5) . [13] 刘文涛.民族之父富兰克林[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4] 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自传[M].姚善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
[15] Thomas Paine. Complete Writings[M].Philip S. Foner (ed). New York: Garden City Press, 1945.
[16]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17] 史景迁.16世纪后期至今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A].罗溥洛.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M].包伟民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18] 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M].于殿利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19] 刘祚昌.杰斐逊[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0] 周宁.东风西渐:从孔教乌托邦到红色圣地[J].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3,(1).
责任编辑:郭泮溪
Early Americans’ Notion of China in th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Initial Stag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USA
CUI Li-f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Nankai 300071, China)
In th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initial stag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USA, early Americans’ notions of China were based on Chinese goods and Europeans’ recounting of China. The former presented an exquisite and brilliant image of China to the eyes of early Americans, thus becoming a mirror through which an imaginary China was reflected. The Europeans’ views of China were inherited by American enlighteners who made use of this image to cultivate typically American spirit and establish their own new homeland.
image of China;early Americans;Enlightenment Movement
G04
A
1005-7110(2011)01-0025-07
2010-12-30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资助项目(TJ05-YW0406)阶段性成果。
崔丽芳(1971-),女,汉族,河北蠡县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中西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