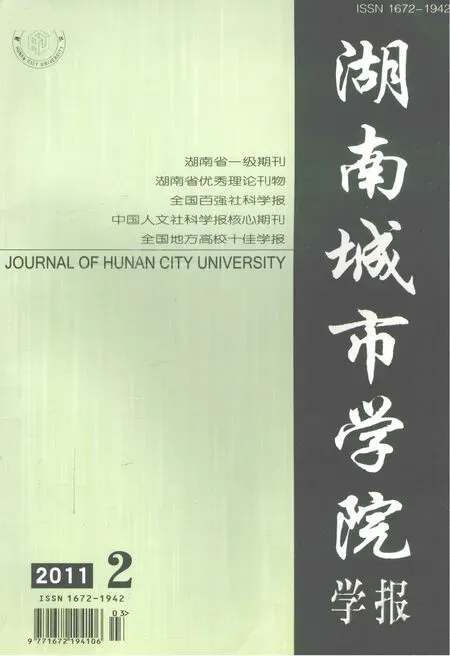茨维坦·托多罗夫:作为结构的阅读
熊海英,李异辉
(湖南理工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湖南 岳阳 414006)
茨维坦·托多罗夫:作为结构的阅读
熊海英,李异辉
(湖南理工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湖南 岳阳 414006)
法国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作为结构的阅读”等理论概念的脉络是从注重文本结构分析到注重读者阅读体验,从结构主义到对话批评。运用“作为结构的阅读”这一理论指导可以使读者认识到,作品人物通过不同读者、不同时期的阅读建构呈现为变动不居的人物形象,从而赋予文本材料这一客观事物以鲜活的生命。
茨维坦·托多罗夫;作为结构的阅读;读者;文本
一
茨维坦·托多罗夫(Tzetan Todorov)是法国著名的符号学家,思想史家,哲学家。他与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一起创办《诗学》(Poétique)杂志,并确定叙述学的基本概念。托多罗夫的重要著作包括:《文学与意指》《言语类型》《脆弱的幸福》《我们和其他人》《面对极端》《不完美的花园》《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邦雅曼·贡斯当》《民主主义热情》《恶的记忆,善的向往》《世纪调查》《个人赞:责任与乐趣,一种艄公生活》《艺术中个人主义的诞生》等。
托多罗夫认为,基于人们审美疲劳的原因,无所不在的事物会使人们因习以为常而失去了对它们的兴趣,变得没有什么感觉了。乍一看,阅读似乎没什么可谈的,因为没有什么比阅读体验更为平常的了。在文学研究中,人们经常从读者和读者意象两个方面来考虑阅读问题。对读者的社会、历史、个体多样性等方面的研究和把读者意象化为作品中的人物或被述对象之间存在一个批评空间。托多罗夫把这个空间定义为“阅读逻辑空间”,并分析了对所谓的代表性作品的阅读情况。根据托多罗夫的观点,这种阅读方式是作为一种结构展开的,因为读者倾向于把文本视作对现实的复制并据此想象性地创造出一个自认为合情合理的真实世界。托多罗夫关心的不是文本和现实之间关系的争论,而是对这样问题的回答:“文本如何使我们建构一个想象世界?”他运用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首先对指涉句和无指涉句进行了区分,认为读者只是把指涉句作为结构内容。然后,托多罗夫又指出了一些叙事手段如时间、视点、语气等如何服务于不同的结构功能,它们的作用如何靠重复得以加强,从而使读者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叙事中建构出一件事情来。
至于建构起“作为结构的阅读”这一概念的重要性问题,托多罗夫认为,在对一本小说的阅读中,每次的阅读体验都是不相同的,因为每一位读者并没有从小说中得到对世界的看法,相反,他是从小说支离破碎的信息中建构起自己对世界的意象的。读者阅读之间的差异部分原因在于指称(signification)与象征(symbolization)间的差别。在指称中,也就是在符号秩序中,读者被告知一件事情;在象征中,我们得到事件的情节和需要解释的含义。稍加思索,我们就会发现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不断对前面的阅读体验进行修正。正如读者建构不同的阅读体验一样,文本也在通过读者对文本人物或叙述者的阅读来对其自身进行建构。托多罗夫称之为“作为主题的建构”。但是不是所有的建构都是有益的建构,有些文本在有意地误导读者,如一些侦探小说故意为读者设置迷局。这样的区分可以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没有那一次阅读得到的体验是“正确的”,不是所有的阅读都能完全或正确地建构起它们的意义。从以上托多罗夫的观点可以看出,他的理论脉络是从注重文本结构分析到注重读者阅读体验,从结构主义到对话批评。
二
托多罗夫辨析了叙事的三个方面:语义、句法和词语。语义指的是叙事所表达或隐含的具体内容,即作品的“主题”;句法指的是叙事单位的组合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词语指的是构成一个叙事的具体的句子。当然,叙事的这三个方面在作品中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在对作品进行分析时,才将它们区别对待。[1]托多罗夫从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两方面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这一学术流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采用的方法受到了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研究者普洛普以及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的启发,不过,他的方法更偏重于语言形式。他先将每个故事简化成纯粹的句法结构后再作分析,换言之,也就是将每个作品看成一种扩充后的句子结构。托多罗夫的《诗学》以其简练清晰的文笔系统地阐述了结构主义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托多罗夫而言,建立新的诗学意味着对文学的功能和意义的再认识。他将历史上对文学的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归结为两种:第一种是将文学作品本身视为认识的对象;第二种则认为每一部个别作品都是某种抽象结构的具体表现。他称第一种态度为“阐释”(interprétation),即任何作品都具有一个结构,它由文学话语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因素交织而成;这个结构同时也是意义的所在之地。托多罗夫认为诗学的任务只限于建立起这种结构而无需顾及作品的意义。在他看来,体裁体现了某种结构,是一些文学特征的总括,因此在体裁研究中,应该采取的是诗学而非阐释的态度。他进一步指出,在对文学作品语义方面的研究中,如同在词语方面和句法方面的研究中一样,意义与形式是可以分离的:我们并没有试图去阐释主题,而只是考察它们在作品中的出现。[2]
托多罗夫借助于语言学术语和语法分析模式建立起来的这种叙事语法,向我们清楚地展示出了作品最基本的叙述结构。与以前那些只局限于诠释作品意义或进行修辞分析的批评方法相比,叙事语法更注重作品的系统性,即作品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观察角度无疑为文学研究引入了新的内容。此外,叙事语法力图在复杂多样的叙事话语中寻求普遍性的规律,这对于我们把握叙事的本质以及认识个别作品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是不无裨益。但是,叙事语法剥离了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将作品简化为一个纯粹的语法框架,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构成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极为重要的细节部分,从而妨碍了对作品的正确审美估价。其次,叙事语法将作品的结构看作一个自足的体系,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不考虑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样做不但忽视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而且排斥了文学作品情感、想象诸层面上的意义,使任何价值判断成为多余。
文学作品不仅有结构,还有内容,对作品的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强调不应以放弃作品具体内容为代价,单纯追求文学的“内在性”和“抽象性”,无异于将文学看作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然远离文学中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和情感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等于抹杀了文学的魅力。[3]因此,避开文学作品具体内容的批评难免枯燥乏味,其诞生时具有的生命力终将在单调的批评模式的多次重复中渐渐丧失。
三
托多罗夫指出:幻想存在于悬而未决之中,一旦人们选择了这样或那样的答案,就不再是幻想作品,而是相近的另一种体裁志怪或神话了。幻想是一个了解自然规律的人,面对一个超自然事件时感到的犹豫不定。在大部分幻想作品中,是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了犹豫,也有少数作品,其中的人物并未产生犹豫。但无论哪种情况,幻想作品都要求读者加入到人物的世界中去,要让读者也感到模棱两可,读者的犹豫是幻想作品的首要条件。在一些非幻想作品中也存在着超自然事件,但它们并不能引起读者的疑问,例如寓言故事中动物说话以及诗歌中的某些修辞手法。幻想作品不但意味着要有一个离奇事件以引起读者和作品主人公的犹豫,它还意味着一种阅读方式。托多罗夫指出,幻想作品包含三个条件。首先,作品要求读者将人物的世界看作一个真实的世界,要求读者在解释发生的事件时在合乎自然和超自然的解释之间产生犹豫。其次,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要产生同样的犹豫,读者的角色由一个人物担当起来,犹豫因此在作品中得以表现并从而成为作品的主题之一。最后,读者的阅读方式至关重要:读者不能对作品进行“寓言式”或“诗意”的理解。这三个条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第一和第三个条件是构成这一体裁的真正条件;第二个条件可以不满足。但大多数幻想作品都具备所有这三个条件。
从注重作品的内在结构到在读者的活动中去寻找理论基础,托多罗夫已经在有意无意之间打破了文学话语的封闭系统,这种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是对结构主义一贯强调的“内在性”的反拨。
托多罗夫关注读者的阅读体验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在读者和作品人物之间建立“对话关系”,通过对话互相从对方发现自己的存在。这种对话关系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巴赫金的理论关注小说语言的对话性,以期通过对话引起人们倾听和追忆。因此,他的理论更注意语词的所指,利用所指的“差异性”造成一种对话不可终结的过程。他关注的中心问题不是一般语言学的语音、语汇、语法和修辞问题,而是各种语言材料按照不同的对话角度组成的语言类型即对话类型。巴赫金在《小说话语》中指出,个人是一种不相关的范畴,在小说中,讲话者主要是历史上一个具体特定的社会个体。他的话语是一种社会语言(尽管还是雏形的),而不是一种个体语言。对话性话语是不断冲突着的画面:社会语言多元化。巴赫金侧重于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来考虑问题。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关系体现人的社会存在,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对话关系就是个人同社会和环境的关系,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在巴赫金的思维中,始终关注人的自我建构问题,他认为主体建构只能在自我和他人的对话交际中实现。任何话语都体现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在说话者与他者的关系中表达意义的。
托多罗夫对阅读体验的强调也表达了文本与读者互为镜像的关系,即读者通过作品人物及事件构成一个虚拟的镜像世界来反观自己对阅读体验的认同,阅读就成了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沟通的桥梁。作品人物通过不同读者、不同时期的阅读建构呈现为变动不居的人物形象,从而赋予了文本材料这一客观事物以鲜活的生命。正如人们所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品人物和读者之间构成了五彩绚丽的镜像空间,并进一步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1] 程锡麟. 叙事理论概述[J]. 外语研究, 2002(3): 10-15.
[2] 段映虹.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托多罗夫——从结构主义到对话批评[J]. 外国文学评论, 1997(4): 15-16.
[3] 祁晓冰. 对话:人的存在特性——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 广西社会科学[J]. 2008(9): 65-68.
[4] 托多罗夫. 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Tzetan Todorov: Reading as a Structure
XIONG Hai-ying; LI Yi-hui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Hunan 414006, China)
The article summarizes and comments on Tzetan Todorov's views of “reading as a structure”. His ideas remove from emphasis on structure of the text to reader's reading experiences, from structuralism to dialogue criticism. The theory makes us aware that the characters in the text could become rather changeable than static through various readers' construction in reading in different period, which could endow the text with vitality.
Tzetan Todorov; reading as a structure; reader; text
I 109.9
A
1672–1942(2011)02–0084–03
(责任编校:彭 萍)
2011-02-28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YBB241)
熊海英(1974-),女,湖南湘潭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