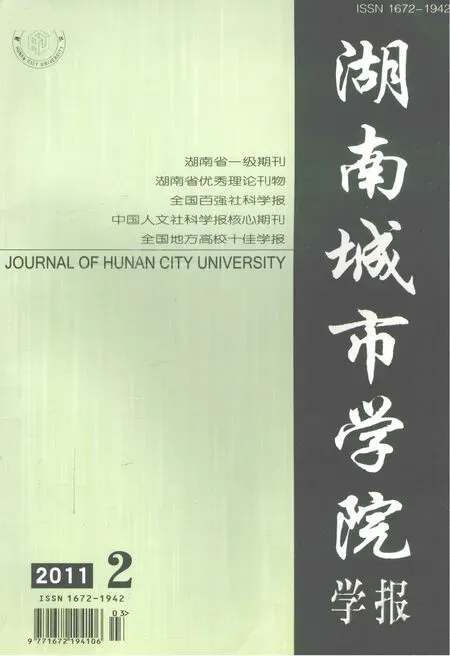论《我的丁一之旅》的叙事艺术
赖力行,杨志君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论《我的丁一之旅》的叙事艺术
赖力行,杨志君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史铁生近年来对小说叙事艺术进行了新的探索,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的叙事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叙述者的虚化,让限知叙事的“我”具有了全知叙事的功能;二是图像的介入,为说理与辩难提供了便利;三是碎片化的写作,淡化了故事性,甚至颠覆了传统的情节结构。
叙事艺术;灵魂;图像;碎片
史铁生是当代很有特色的优秀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充满着对人的根本处境的终极关怀,带有鲜明的思辨色彩。而在小说文体与叙事的创新上,他也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1996年),再到2006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他的小说离常见的小说形态越来越远,甚至打破了小说与散文、杂文之间的界限。叙述者的虚化(即“我”是一个永远的行魂),让限知叙事的“我”具有了上帝的功能;图像的介入,既符合读图时代人们的审美需求,又为说理与辩难提供了便利。而碎片化的写作,让故事性逐渐淡化,甚至颠覆了传统的情节结构。这种种叙事方式的并用,无疑拓展了《我的丁一之旅》的叙事空间。
一、灵魂叙事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到处都充斥着欲望叙事与身体叙事,甚至沦为下半身写作,而对人心与灵魂关注的作品很少。对这种现象,青年评论家谢有顺批评说:“我的确以为,文学光写身体和欲望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应该是人心的呢喃;文学不能只写私人经验、只写隐私,文学还应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叙事,这是文学写作最为重要的精神维度,遗憾的是,它被多数作家所遗忘,或者藐视。”[1]然而幸运的是,在谢有顺为当代作品灵魂缺失感到遗憾的同时,我们还有史铁生这样关注人心与灵魂的作家,还有灵魂叙事的佳作——《我的丁一之旅》。
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叙述者“我”不同于一般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史铁生笔下的这个“我”是一个“永远的行魂”,不具备人的形体,是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灵魂。在“我”漫长的旅行中,到过的生命不计其数,曾有一回是在丁一。如今“我”已远在史铁生,张望时间之浩瀚,逝去的时光历历在目,常仿佛又处丁一,于是有了追忆曾在丁一之旅沿途上所见的风景。
“我”的丁一之旅起始于伊甸园。那时“我”在亚当,“我”和夏娃共同居住于那座美丽的园子。后来因为蛇的引诱,“我”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并以亚当和夏娃之名分头起程。从此,“我”伴随着丁一踏上了寻找的征途。寻找什么呢?寻找分散的夏娃,寻找生命的另一半,寻找爱。爱被史铁生认为是生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说:“我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主要探讨的就是爱的问题”。[2]爱的问题的确困扰了丁一的一生,他一辈子在探求什么是真爱、以及爱与性、爱情与自由、性爱与自私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的丁一之旅可看做一次寻爱之旅。
“什么是真爱”这个问题落实在小说中,便成了“我”与丁一如何确定哪一个女子就是夏娃。丁一是一个情种,从小就喜欢混在女孩群中,永远追在女孩屁股后头甘做仆从。年纪不大就在阿秋、阿春、泠泠、何依身上便萌发出朦胧的性意识。但与其说那就是爱,毋宁说是欲望。史铁生曾说,人的名字就叫欲望,生命就是欲望。但欲望不是爱情,或说性不等于爱。只是在遇到夏娃之前,性欲往往会蒙蔽丁一的眼睛,误以为一切欲望的对象都是夏娃。
丁一继续寻找,又遇到了秦娥、吕萨。在他们的交往、对话及共演丁一自创的戏剧《空墙之夜》中,着重探讨了爱情与自由的问题,即那个困惑了秦汉,也困惑了丁一、吕萨和“我”的问题:爱情,既然是人间最美好的一种情感,为什么一定要限制在尽量小的范围里呢?为什么不该让它尽量地扩大?因为缩小、限制、防范,只许它老老实实不许它乱说乱动,不像是对待什么美好事物,而是对瘟疫与洪水猛兽。丁一想要扩大爱情的范围,不让爱情局限在两个人之间。他在《空墙之夜》中虚构了一种自由的爱,那是他心中理想的爱。但那毕竟只是无墙之夜的戏剧,一旦遭遇冷峻白天的现实,丁一的理想便败下阵来:秦娥跟前夫商周走了,因为问问必须得有一个父亲,问问必须得上学,问问必须得过一种所谓的正常生活——这些都是丁一不能给或不愿给的。事实上,丹青岛诗人与画家丹、画家青的悲剧也正标志了丁一“多向爱情”的理想的破产。说到底,现实中的爱情是自私的,它只能局限在两人之间。爱情的自由也仅仅存在于相爱的两人之间,一旦超出了界限,赢得了自由却丧失了爱情。丁一因为爱情理想的破灭而回归西天,标志着“我”的丁一之旅在失望中结束。
“我”,作为叙述者,因为是一具超时空的灵魂,便可以驰骋于文本内外,游荡于事理前后,从所有角度观察被叙述的故事,并且可以任意从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这便突破了传统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限制,获得全知叙事的功能,因而作者能以最充分的叙述自由,写出他想象中的多样人生,写出他的梦想,及他对生与死、性与爱、爱与自由等重大问题的思考。这无疑拓展了文本叙事的空间,使限知叙述达到了最大的自由。
二、图像叙事
尼古拉·米尔佐夫说:“新的视觉文化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视像化。”[3]随着“图像转向”(米歇尔语)及读图时代的到来,文学这一语言艺术,也逐渐走向视像化。具体到小说中,视像化就体现于图像叙事的渗透。
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图像叙事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且不说文中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单是戏剧场景的多次涌现,就在我们脑海中呈现出一幕幕生动形象的画面。在第103、107、109、117、121节中,丁一与秦娥、吕萨自导自演,或改写往事的情节,或即兴去诠释陌生与冷漠,或上演丁一自创的剧本《空墙之夜》,或表演两场意蕴截然相反的戏——“近而远”与“远而近”。而在第126节“丁一的理想生活”中,丁一与秦娥,已经不满足于《空墙之夜》了,他们去改编戏剧、电影甚至小说,并将之搬上他们的三色舞台。这些章节中的戏剧场景,画面性都很强,几乎可以直接搬上现实的舞台。
相比戏剧场景的设置,对索德伯格的电影《性·谎言·录像带》的借用是一种更明显的图像叙事。史铁生花了一整节的篇幅(即第84节)描述了《性·谎言·录像带》中的一些主要场景。虽然短短的9页纸不能代替一部长达90多分钟的电影,但它却涵括了整部剧情的精华。全剧总共四个人物:詹和彼得是分别多年的老同学,彼得和安是夫妻,安是劳拉的姐姐。詹喜欢给女人录像,录的都是女人关于性的问题。在安发现了丈夫与自己妹妹的私通之后,她找到詹,让詹录了像,并要求与彼得离婚。彼得一气之下,跑到詹那里找出安的录像,看完之后出于报复之心,彼得把他曾跟伊莉莎白上过床的事告诉了詹——那是在詹和伊莉莎白分手以前的事。
这部电影,正如其名,探讨的是“性与谎言”的问题,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性”的问题。人们往往会因为性的吸引走进婚姻,而在无爱的婚姻中又彼此欺骗,甚至背叛,如彼得背着安与自己的小姨子私通。这正如后来秦汉说的:“以性为引诱的爱,注定的,从始至终包含着欺骗。”因为性压根儿是要挑好的,挑美的,挑酷的、靓的,挑健康的、聪明的、有能力的,或者是有思想、有抱负的,有作为的。总之,性挑的都是优势群体。而爱是要人平等地善待一切,一切他者,一切上帝的造物。对优势群体的亲睐与对平等的追求,这两者的矛盾必然导致这样一种后果:过于看重性,爱情便不可能发生。史铁生借用《性·谎言·录像带》,更深入地探究了性与爱,及爱与自由的关系问题——这正是他在《我的丁一之旅》中要表达的主题。
因小说改编成影视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家海岩说:“我认为我们已经从阅读时代进入电视时代,原来的文字读者不停地被瓦解。有很多人不看小说,但很难说有人不看电视。小说读者的阅读习惯被电视媒体的特点改造了,文字给视觉补充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讲故事必须适应这种欣赏习惯的变化。在这个时代写小说,必须在写作方法上做出调整,来适应这种新的思维习惯和欣赏习惯。这不是取悦读者,而是因为时代不同文本的特点和风格也必然不同。”[4]应当说,图像叙事中包含有文学叙事内在的美学更新诉求。新世纪文学在图像文化的排挤之下逐渐处于文化市场的边缘位置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文学与电子传媒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文学完全可以尝试吸收电媒文本的叙事手法来丰富自身的表现手段。
史铁生对图像叙事的运用,或许是无意为之,但无疑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段,使《我的丁一之旅》既符合读图时代的人们的审美心理,又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
三、碎片叙事
诗人约翰·多恩说:“一切皆支离破碎,所有的一致性均已不复存在。”这句话正好可用来形容后现代世界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博德里拉宣称:“玩弄碎片,就是后现代”。碎片化是现代社会存在的一个特征,反映在意识形态的文学小说中,便是碎片叙事的广泛运用。
《我的丁一之旅》是一部由156个散文式片段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每一个片段有一个小标题。片段篇幅远不如一般长篇小说中的章节,平均1个片段也就3页左右,加上片段之多,所以书的前面连目录都没有。片段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小标题而写,或者可以说,几乎每一片段都是对标题进行释义,就像史铁生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多次写的“标题释义”一样。每一个片段可以单独成篇,或是随笔,或是杂文,或是散文,或是戏剧,是一个意义完整的实体。但片段与片段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显得随意、散漫,如文中多次以“引文”为题的片段(第2节,第67节,第91节,第92节,第110节,第111节,第139节)、“史铁生插话”(第13节,第52节,第61节,第106节)、梦境(第69节,第88节,第98节,第100节,第127节),及以“无题”为题的片段(第108节,第118节),就鲜明地体现了文本之间的散漫与无序。而对《圣经》《参考消息》、诗歌、戏剧、电影及之前小说文本的大量引入,“在叙事上彻底改变了小说对故事的依赖,以一种精神漫游者和灵魂审视者的姿态,在零散化的情节拼缀中打开了人物隐秘的内心情境”。[5]
《我的丁一之旅》中的碎片叙事,尽管使文本显得散乱与无序,但那只是表面的,因为它遵循的不是客观逻辑,而是史铁生记忆中的印象——印象虽不具备相对稳定的客观时空结构,但它在主体的内心世界里通常会不断地获得某种重新编码,因而具有内在的逻辑与统一。
碎片叙事打破了常规小说情节的连贯与完整,也突破了宏大叙事的话语霸权。作者只要根据自己脑海中的印象,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只要是作者能想到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纳入笔端。在叙述的同时,他可以随时对某一话题发一翻议论,对某一个场景抒一通情怀。甚至是虚无缥缈的梦,与漫无边际的幻想,只要与作者表达的东西关联,都可以纳入文本中。作者无须精心去构思、布局,因为看似随心写下的片段,自有一条内在的理路。这样,史铁生的小说创作便是一种无拘无碍的自由表达,并在文体、结构、布局等形式上,有很大的突破,为当代文学长篇小说的写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1] 谢有顺. 谢有顺专栏:文学伦理[J]. 小说评论, 2007(1): 15-17.
[2] 站在人的疑难之处[N]. 南方周末, 2006-03-30(6).
[3] 尼古拉·米尔佐夫. 什么是视觉文化[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5.
[4] 海岩. 电视剧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N]. 新京报, 2004-09-17(4).
[5] 洪治纲. “心魂”之思与想象之舞[J]. 南方文坛, 2007(5): 67-69.
The Narrative Art in My Ding Yi Trip
LAI Li-xing, YANG Zhi-j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In recent years, Shi Tie-sheng carried out a new exploration in the narrative art, there are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ovel “A trip of my Ding Yi”: Firstly, the virtual narrator, makes the limited knowledge narrator “I” with an omniscient narration Function; secondly, images involved, provides a convenient for the arguments and reasoning; Thirdly, pieces of writing, it weakened the tale, or even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plot structure. From the soul of narrative, images of narrative, pieces of narrative, they are to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vel's narrative and artistic effect.
the narrative art; soul; images; pieces
I 206.7
A
1672–1942(2011)02–0074–03
(责任编校:彭 萍)
2010-10-25
赖力行(1948-),男,湖南南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杨志君(1984-),男,湖南安仁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