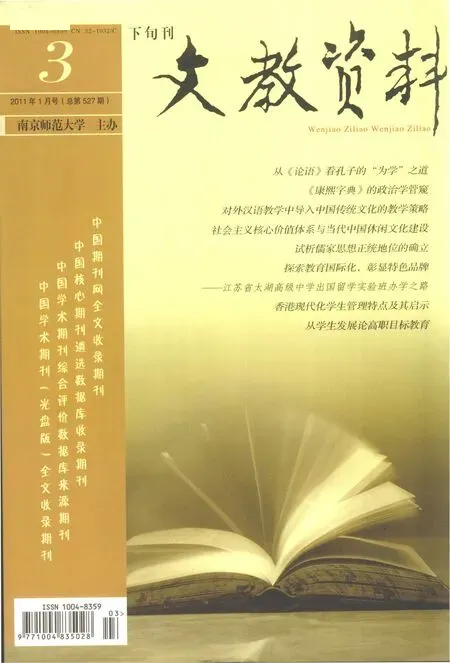《康熙字典》的政治学管窥
邓 莹 陆丽明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三月下达上谕,诏令张玉书、陈廷敬等人,组织了当时翰林院的学士、编修三十人,按照字典编撰式例编撰而成的一部划时代的字书。该书前后用了五年多时间,至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乃成。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康熙字典》的文字、体例、编撰过程等方面的考证,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问题是,《康熙字典》既然是皇帝亲自下诏书编撰,便和民间私人著述不同,它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典籍,仅仅关注其学术意义,未免会对学术背后的政治语境有所忽略。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政治、学术的角度,着重分析以下两个问题。
一、从“上谕”和“序言”看《康熙字典》的现实政治意图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九,上谕南书房侍直大学士陈廷敬等,康熙皇帝说:“朕留意典籍,编定羣书。”连年以来,编订了《朱子全书》、《佩文韻府》、《渊鑑类函》、《广羣芳谱》等各种典籍,因此,理解《康熙字典》的政治学意义,不应孤立地瞄准这一本书,而应将其和其它典籍并列齐观,即放在康熙何以要编撰书籍这一文化背景下加以勘察。康熙御定可《朱子全书》,朱熹乃是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皇帝编撰此书,本是鉴于此书本指隐没,因此“表彰朱子之学,而睿鉴高深,独洞烛语录文集之得失”,才命令大学士李光地等汰其榛芜,存其精粹,以类排比,“奉此一编为指南,庶几可不惑于多岐矣”。
1.所谓“惑于多歧”,就是流于怪力乱神之道,也就是说思想上走上异端。因此,康熙下令编撰此书,本来有统一思想的目的。清朝制度规定讲解儒家经典,必须以宋儒朱熹的诠释范本为依据。科举考试必须按照宋儒的传注,用八股文取士,钳制思想。所以说“凡可以禆世敎、励民风者,脩眀补正”。
2.就是要有助于世间教化,使民风归于王化的雅正而不要犯上作乱。从这些话头看来,康熙的文治政策带有相当明确的政治意图,而不像我们现在学人对待《康熙字典》时那样,一味追求纯粹的学术“真知”。这里附带指出一点,从古典文教看来,其学术与现代人的理解虽有相似之处,但却有根本的区别。相同的一点是,古今学术都是追求真知,古人讲究“信”,鄙视“曲学”。但不同之处在于,古人的学问 “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经传和孔子是其衡量的标准,而学术则以是否合乎科学为皈依。
在古今之争的视野下考察《康熙字典》,则会获得新的理解。宋明理学到清代已经渐趋末流,沦为政治的附庸,这才有清代朴学的兴盛矫正宋学的流弊,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宋之争成为学界的主要思想分歧,最后以朴学的获胜暂告一段落。这意味着,当政治强权压制思想的时候,儒生便会采取纯粹学术的手段。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康熙字典》的编撰不应仅仅看作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更应该将其放到政治—思想的大背景下予以理解,从这个视角看,其学术的政治意味就凸显出来。因此,与诸家关注《康熙字典》本身的纯粹学术价值不同,本文关注的重心是该书所承载的教化意义和伦理价值。
文治是以政治大一统为其前提,从秦始皇的 “书同文”到汉代撰述《说文解字》《方言》等书籍,其中都以统一为其背景。比如说,《方言》撰述本来属于周秦一种制度,“周秦常以嵗八月遣輶轩之使,求異代方言,还奏籍之,蔵于祕室”。这个制度类似于后世的民间采风,是从民间搜集资料,但目的还是为“流化于民”和“王教”。
3.从王教的角度理解字学之书,就不会单单将其归于学术研究,而有着甚广的社会政治目的,康熙在上谕中说:“兼之各方风土不同,南北音声各異。”对儒生而言这是个整理文字的学术工作,但对雄才大略的康熙来说,未始没有同文的政治目的。所以,在《钦定四库全书御制康熈字典序》就揭示了其政治教化的文教意图,如:
易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周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保氏养国子教以六书,而考文列于三重、盖以其为万事百物之统纪,而足以助流政教也。”
在古典时代,经学是民族文化价值的源泉,是政治教化的归宿和标尺,所以序言首先引述经学,这个叫做“考信于六艺”,然后说明编撰的目的,一则是出于学术需要,毕竟以前的书籍不够完善,有遗漏和缺失,最后归结到教化意图上来,这话也说得明明白白:
凡五阅岁而其书始成,命曰字典,于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学稽古者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
康熙的文治当然是古典政治时代文治的延续,但不同的是清代文字狱的兴盛,因此这便在其文治中凸显出自己的特点。
二、《康熙字典》编纂过程中的政治案件
《康熙字典》由皇帝钦定,这自然赋予其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联系当时的政治现实,满清入关之后,为强化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大搞文字狱,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康熙字典》产生了许多政治案件。
王锡侯 《字贯》案是涉及这本字典权威的一桩文字狱。其得罪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对《康熙字典》纠谬;其二,对清廷皇帝没有避讳。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江西新昌县(今宜丰)棠浦镇沐溪村举人王锡侯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学者查此遣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字犹散钱”,他便想出“以义贯字”的方法,把音或义相同的字,汇萃一处,编写出了一部名为《字贯》的新书。《字贯》出版后,江西巡抚海成报告乾隆帝,说有人揭发江西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并据以另刻《字贯》,海成建议革去其举人。乾隆皇帝原来并不以为意,但看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后,发现“凡例”未避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和他的“御名”,这大大触怒了皇帝,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并且迁怒海成,给军机大臣的“谕旨”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地附和幕僚的意见,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开卷就可以看见。乾隆皇帝责问:“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抑见之而毫不为异,视为漠然耶?所谓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安在?”
十二月,王锡侯被满门抄斩,“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凡为王锡侯的诗文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一律予以制裁。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或“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的官员都予以处分。乾隆认为,江西巡抚海成只将王锡侯“仅革去举人审似,实大错谬”,判以斩刑。而王锡侯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贯》,各种书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诗别裁》、《古学指南》九种五十二本藏书全部销毁,王锡侯也成了封建专制的牺牲品。案件还牵连到地方上下官员、士人近百人受到惩处。这起残忍的文字狱,更加凸显了《康熙字典》的神圣地位,这种杀一儆百的极端专制手段强化了其权威性。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四库全书》纂辑成书,总纂官纪昀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收录的书籍都要摘举要点,考其源流得失,进行褒贬评价,而对《康熙字典》,只是以溢美之词大加恭维:“无一义之不详,无一言之不备。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
这个案件说明,《康熙字典》并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从传统的小学理解只是其一种角度,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理解角度。从文字狱来理解固然不错,但是应该注意到文字狱是古典文教传统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只有在“先王之教”的古典政治语境中,文字狱这种思想控制手段才会得到理解。
上文已经提及这个问题,文化事业绝不是仅仅脱离政治环境的、象牙塔式的、纯学术的东西,而是与现实政治密切关联。但问题在于,随着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输入,学术脱离政治而独立,现代学者将此看作文化进步的产物。在此观念影响下,《康熙字典》的现代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纯粹学术的色彩,纯粹学术兴趣使我们遗忘了本是 “王化”事业组成的古典学术方式。而古典学术方式和现代学术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以某种所谓客观的、科学的“真理”为其前提,而是着眼于现实之价值意义关怀。一言以蔽之,古典学术的学术目的是当下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勘察《康熙字典》的政治学问题,就不能单单以进步或是落后为标准,而应考虑王化之教的古典背景。
安徽师大已故教授张涤华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长达三万多字的题为《论〈康熙字典〉》的论文,全面论述了该书。1983年,张涤华先生编选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张涤华语文论稿》,也把这篇《论〈康熙字典〉》编选了进去。该论文的贡献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此书进行了一个圆照的分析。其论编纂这部字典的原因或目的归为三点:第一,玩弄过去封建王朝的老圈套,借修书来笼络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怀柔手段;第二,采用过去封建王朝的又一骗人手法,在武力大肆镇压之后,来一套稽古右文的把戏,借以点缀升平,炫耀新朝的文治;第三,通过修书,检查并销毁一切不利于清朝的文献记录,借以加强封建统治。
张先生的议论虽然批评多了一些,但是足以启发我们,《康熙字典》是一种政教手段,只有“怀柔”,知识分子才会服膺现实政权,这对于国家是有益的。古人说,骑马打天下,而治理天下要靠儒生,“稽古右文”、点缀生平、销毁禁书,正是高明的政治策略,这无可厚非。“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食古不化的腐儒理当受到查处。不过,统治者应当采取更为宽厚的手段,动辄满门抄斩的封建做法只能招来更多反抗。
[1]《朱子全书》提要.
[2]《佩文韵府》序.
[3]《四库提要》“经部十·小学类一”.
[4]许冲.上说文解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