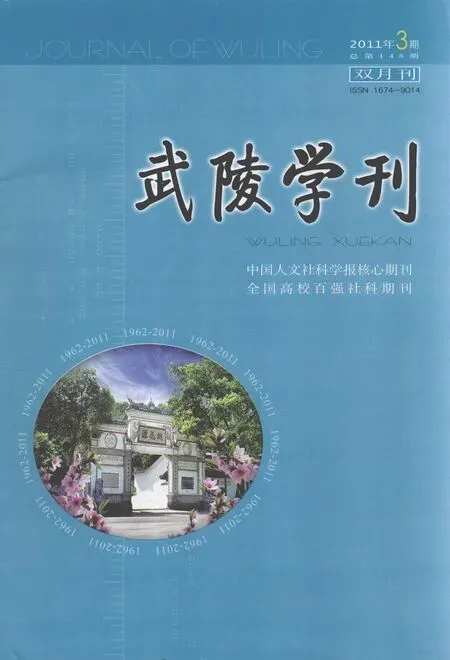论因时通变与历史盛衰
庞天佑
(湛江师范学院 历史系,广东 湛江 524048)
论因时通变与历史盛衰
庞天佑
(湛江师范学院 历史系,广东 湛江 524048)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变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既是华夏哲人对于宇宙万物存在形式的认识,又是他们因应环境变化行为处事的方法与原则;既是有作为的政治家治国兴邦的施政理念,又是思想家、史学家反思历史、考察盛衰的史学思想。因为一切事物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人的行为必须顺应时代,人的思想应该随时变通,所以治国施政要随着时间推移并顺应环境变化而变化,探讨历史应该运用通变思维揭示出盛衰转化的必然性。通变思想与历史盛衰考察密切相关,蕴涵深刻的辩证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因时通变;施政理念;史学思想;历史盛衰
中国古代通变思想的最初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华夏先民认识到,宇宙自然,变动不居,天下万物,生生不已,萌发了初始的通变意识;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华夏先民意识到,社会现象,日新月异,国家盛衰,不断变化,形成了通变的思想观念。因为中国古代史学承担着独特的政治功能,特别重视人的行为与活动,尤其关注君主的行为与天下盛衰的关系,蕴涵着鲜明的人文主义特色与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注意考察盛衰成败,总结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为统治者治国兴邦服务,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与重要特点。华夏哲人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出发,根据不同时期社会的现实需要,将历史盛衰总结与治国兴邦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主张“读古人之书,以揣当今之务”[1]626。他们强调考察历史要有通变思维,不仅将历史作为伦理教科书与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而且通过历史总结表达因时通变的施政理念,寄托治国兴邦的政治理想,为未来发展开辟道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变既是华夏哲人对于宇宙万物存在形式的看法与认识,又是人们因应环境变化的方法与原则;既是有作为的政治家治国兴邦的施政理念,又是思想家、史学家反思历史、考察盛衰的史学思想。这种历史盛衰总结的传统,使华夏民族积淀了因应时势、随时通变的意识,培育了勇敢坚毅、不屈不挠的性格,形成了以史为鉴、瞩目未来的精神。
一 “通其所穷,疏其所壅”
“通其所穷,疏其所壅”, 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于王夫之的《宋论》,但反映出华夏哲人对于通变普遍性的深刻认识,揭示出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通变的永恒性。《周易》经传表现出先民对于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考察中,包含着极为深刻的通变趋时的思想理念。人们面对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必须不断破除迷信,冲破传统观念束缚,牢固树立通变思想。所谓通变思想,蕴涵以下四层含义:一是从客观世界到主观世界、从宇宙自然到人类社会、从思想认识到思维方式,一切都在变化,时时都在变化,永远不会停止。二是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新的情况时时产生,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必须经常关注新情况,应该及时解决新问题。人的认识要与时俱进,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世而权行”[2]5,一切施政举措随着具体情况而定,各种制度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三是穷则思变,锐意进取,突破陈规,冲破禁锢。每当国家陷入困境,社会积弊深重之际,必须“遗其小利,惩其大害,通其所穷,疏其所壅”[3]10,变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转机,于困境中求发展。四是人的社会实践,必须随机应变,灵活处置,敢为人先,不断创新,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敢于超越。通变不仅是宇宙万物的存在形式,而且是华夏先民永恒的思想主题。华夏哲人强调宇宙万物,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时时在变,不断在变;人的认识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随着社会实践不断接受检验而走向完善,必须抛弃那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陈腐观念;任何制度只是一定环境下的产物,没有固定不变的、永远适应的制度,应该在治国兴邦的实践中实现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人们考察历史的发展,必须看到盛衰转化的必然性。一切现象既是历史的产物,也将随着历史的延续而改变。因此面对不断变化、无限发展的世界,只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随时通变,顺应潮流,才能把握变革先机,因应时代趋势,掌握发展主动权,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国家的繁荣。我认为,通变既是先民的宇宙观与自然观,又是他们的社会历史观。通变思想建立在对过去、现在、未来永无止境向前延续的认识的基础上,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应该不断突破陈规,勇于弃旧图新,务实应对变局,顺时开创新局,从而将总结历史盛衰,考察社会现实,因应未来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通变思想将一切事物置于永恒运动、无限延续的长河中进行考察,反对陈腐的意识与过时的观念,否定永恒的教条与僵化的模式,反映出一种深刻的批判性思维。
华夏哲人指出宇宙万物随时随地在变,没有不变的人与不变的事。他们思考“天地之经,治乱之理”[1]110,总结历史盛衰,强调因时通变的必要性。欧阳修将通变说成天理,他指出:“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4]在欧阳修看来,通变代表天理,天理就是通变,既贯穿于宇宙万物之中,又是永远存在而不可改变的。二程强调变革的永恒性,宣称:“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明理之如是,惧人之泥于常也。”“往来变化,生成万物。”这就是“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5]862。二程阐发《易传》关于因时通变的思想,指出:“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天地阴阳推迁改易而成四时,万物于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时成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新,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天道变改,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故赞之曰:革之时大矣哉!”又说:“夫变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迹之至著,莫如四时,观四时而顺变革,则与天地合其序也。”[5]952在二程看来,事物运动体现宇宙万物之理,“时极道穷,理当必变”[5]1018。人们应该“随时变易以从道”[5]689。顾炎武则将变易视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属性,有如白天黑夜,寒来暑往一样,因时而变是遵循《周易》的原则[6]22。人类社会无限延续与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后代因袭并继承前代的过程,一方面又是后代对前代通变的过程,因袭与通变构成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他强调后代对前代的继承:“‘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6]246;概括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6]680的规律。顾炎武提出,“天下之变无穷”,因此“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无穷”[7]46,必须做到“过中而变”,在“将变之时”适时而变[6]16,顺乎时代潮流,因应历史趋势,为未来发展开辟道路。王夫之强调,一代之制,各因其时,事随势迁,因时制法。君主治理国家,把握“时之所兴,势之所凑”[1]134,遵循“因时制宜”的原则施政[1]650。这些论述充斥于中国古代典籍中,说明华夏哲人运用通变宇宙观与通变自然观,以及通变的社会历史观,看待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锐意进取的政治家总是以通变思想作为施政理念,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变法图强,协调社会关系,完善各种制度,勇敢地抛弃过时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提倡与推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制度;而许多思想家与史学家则以通变思想为理论依据,深入考察历代的盛衰兴亡,认真总结治国安民的经验教训,为人们顺应时代要求,推动社会发展,承担历史责任,提供启示与借鉴。在我看来,政治家的通变与思想家及史学家的通变,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从相同点来说,两者都建立在通变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之上,都把社会看成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都要求人的行为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都主张通过考察历史上的通变为现实的实践活动提供借鉴。从不同点来说,前者主要是追求摆脱现实困境的功利目的,对现实的关注使之考察历史的经验教训,侧重探讨那些与现实相关的具体问题,从历史盛衰思考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施政实践中表现为突破传统进行变法;后者主要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8]2597,注意探讨与实现长治久安有关的理论问题,对长远目标的关注使之总结历代的盛衰,侧重概括与治国兴邦相关的一般原则,为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前者的通变主要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在施政实践与社会活动中因时制变,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创新改革活动;后者的通变则是在前人的政治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历代盛衰兴亡对创新改革作出思想总结与理论概括。前者的通变为后者的通变奠定了基础,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材料;后者的通变则是在前者通变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创造活动。华夏民族不仅注意从盛世中总结经验,而且重视从灾难中得出教训。通变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治国施政与历史总结,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总之,华夏民族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形成了通变的思想观念。人们考察盛衰兴替,必须巨眼深识,把握古今沿革,“洞察在历史演变的持续过程中,过去如何影响现在,现在又如何导引未来,并导绎出其演变的脉络,了解其始终不歇的究极的意义和价值”[9]。
二 “与时迁徙,与世偃仰”
中国古代思想家、史学家总结历史盛衰,考察古今沿革,目的是认识现实,顺乎时势,适时通变,治国兴邦。管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应该“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0]。在管子看来,治国施政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必须根据情况变化而变化。荀子曾言:“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11]荀子认识到,把握时机,顺应社会,随时而变,灵活处置,一切施政行为与治国措施,应该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其所体现的就是因时通变的道理。《吕氏春秋》考察历史盛衰,提出“因时而化”的主张,宣称:“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为什么“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因为人类社会不断地变化,施政举措必须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不应固守先王之法而不能变通。这种情况如同“病万变,药亦万变”。在《吕氏春秋》的作者看来,“变法者,因时而化”,“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12]177。君主不能墨守成规,应该随时而变。二程强调:“虽二帝、三王不无随时因革。”[5]452又说:“君子之道,随时而动,从宜适变。”“君子现象,以随时而动。”人的行为不能脱离时空环境,必然随着环境变化,随时变化适应形势发展,这就是“随时之义”[5]784。“人能识时知变,则可以言《易》矣。”[5]1019朱熹指出:“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易也,时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则谓之易;自其推迁无常而言之,则谓之时;而其所以然之理,则谓之道。时之古今乃道之古今,时之盛衰乃道之盛衰。人徒见其变动之无穷,而不知其时之运也;徒见其时之运也,而不知其道之为也。”[13]在朱熹看来,易、时、运、道四者是一致的。因时通变应该紧紧把握时机,把握时机必须顺应盛衰之运,而顺应盛衰之运就是遵循天道。
中国古代历史的盛衰兴亡,说明了因时通变、顺乎潮流的极端重要性。君主因时通变,必须认识时势,才能与时俯仰,作出正确的施政决策。时势体现复杂的因果联系,反映社会的发展方向,显示历史趋势与时代潮流。君主洞察与分析时势,判断并顺应时势,才能觉察机遇,进而把握机遇,实现创业守成的目标。贾谊总结秦的盛衰兴亡,指出秦的君主因为顺应时势,把握了统一天下的机遇,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帝国。然秦实现统一以后却违背时势,秦皇“遂过而不变”,秦二世“因而不改”,不知适时通变,逆历史潮流而动,失去创建盛世的机遇,导致二世而亡。秦皇“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14]11。在贾谊看来,统一天下与治理国家,应该采用不同方法。君主治国安邦,必须“去就有序,变化因时”[14]21,顺势而为,适时通变。唐太宗考察晋代盛衰,强调“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15]。所谓“顺理而举”,指因应盛衰兴亡之运;所谓“背时而动”,则指逆时代潮流而动。顾炎武将因时通变与顺应民心结合起来,提出通变宜民,“唯变所适”的观点[7]47。通变必须符合民心,不可悖逆民意。王夫之从中国古代盛衰考察中认识到,因时通变不是一意孤行,不能随意乱变,不可胡作非为,而是根据“得天之时则不逆,应人以其时则志定”,遵循“圣人之所不能违也”的客观必然性[1]571,顺应时势而革故鼎新。隋炀帝横征暴敛,穷奢极欲,“虐民已亟”,引起“怨深盗起”,最后“天下鼎沸而以亡国”[1]560。这是其悖逆民心、恣意妄为所致。
中国古代思想家、史学家关注着民族的命运,谋求国家的富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从历史盛衰总结中,引出革除弊政,通变创新的结论。杜佑审视典章制度的变迁,反思天下盛衰成败,阐发顺应时势、通变创新的治国理念。他强调治理国家要“随时立制,遇弊则变,何必因循惮改作耶”[16],君主应该“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17]71,做到“便俗适时”,不能“非今是古”[17]403。《通典》记载从上古到唐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揭示数千年来典制的发展变化,寓含因时立制、适时变通的深刻意蕴。顾炎武认识到有关的制度,如果“居不得不变之势,而犹讳其变之实,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7]128。这就是说只有因时而变,才能兴利除弊。他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封建制与郡县制,指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7]12王夫之指出:“政之善者,一再传而弊生,其不善者,亦可知矣。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弊也,必至于厉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国受其益,人受其赐。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宽以便其弛,假其所严以售其苛,则弊生于其间,而民且困矣。”[3]147他以通变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制度,指出这些制度都是特定时代环境下的产物,即使是最好的典章制度与施政措施,在实行中也会出现各种弊端,“传之数世而弊且生矣”[3]77。典章制度与施政举措存在弊端的必然性,决定了损益变通、改革创新的必要性。在王夫之看来,“所患者,法弊以极,习相沿而难革,虽与更张,害犹相袭”[1]662。国家各种弊端相沿积累、不断加深之际,正是因时通变、革故鼎新之时。如果不能兴利除弊,绝处求生,就会贻害无穷,在困境中越陷越深,甚至走向灭亡。通变是清除各种积弊,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因时通变史,改革创新史。那些创业守成的统治者建树的业绩,是顺应潮流、通变图强的结果。
总之,通变思想强调人们的一切活动,因时制宜,适时而变,根据时间推移与环境改变而变化。如果拘泥陈规,思想僵化,盲目守旧,不知变通,必然为历史发展的洪流所淘汰。君主治理国家,必须革故鼎新,兴利除弊。
三 审时度势,建功立业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锐意进取、奋发图强的君主,高瞻远瞩,把握机遇,适时通变,建功立业。他们的通变不是主观臆断、蛮干胡来,不是恣意妄为、倒行逆施,而是审时度势,顺势而行。审时度势指对客观时势作出正确判断,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因时通变的前提。其关键是抓住“天时”,把握机遇,“上瞻天文,下察人心”[2]11,因势利导,实现目标。孟子将“天时”作为人的活动能否成功的条件,寓含着顺应时势、把握机遇的思想。我认为,“天时”与机遇都强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都指出时机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切实把握有利时机;都重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都主张因天因人,顺势而行,通变创新,弃旧图新,在这些方面二者具有共性。然从内涵上考察,二者又存在某些差别:“天时”虽然指从事社会活动的最佳时机,但侧重指人的某些具体的行为或活动恰逢时机,这类行为与活动涉及的时间比较短暂;机遇则指成就事业的最好时期,侧重利用有利的时期建树历史性的重大业绩,涉及的时间通常比较长。因为“天时”指从事某一具体活动的时间,抓住“天时”只需短暂的决策,通常是战术性的,只在一念之间当机立断;机遇则指较长时间之内创建历史性的业绩,通常是战略性的,把握机遇要正确判断时势,应该冷静观察,需要深思熟虑,做到趋利避害。“天时”强调天赐良机,即从事各种具体活动的最佳时机,或者说是决定人的活动取得成功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刻。王夫之指出:“难得而易失者,时也”,因此要“知时以审势,因势而求合于理”[3]106,才能成就事业。时机未到,条件未备,盲目行动,必遭失败而不能成功;时机已到,条件具备,不能抓住时机,必失良机而贻误大事。“天时”与机遇,彼此交织、相互联系:“天时”体现机遇,机遇包含“天时”;众多具体活动的“天时”,汇聚为建树历史业绩的机遇。那些不能够抓住具体的“天时”的人,更不可能把握建树历史业绩的机遇。如隋末生灵涂炭,群盗蜂起,天下大乱,国家崩溃。如果抓住天时,顺势而起,或能创建新朝,甚至取而代之;如果拘泥臣节,丧失机遇,就会在乱世洪流中被淹没,还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李世民敏锐地意识到,隋朝天下大乱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把握这一机遇具有重要意义。他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使裴寂言于其父李渊曰:“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8]2286裴寂之言说明,李世民站在时代的高处,有着超越常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远见。王夫之认为根据具体情况,把握有利时机,才能“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务”[1]581。他说:“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规取天下者,夺之于群盗,非夺之于隋也。隋已亡于群盗,唐自关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1]572李渊父子起兵兴唐,是从群盗手中夺取天下。如果不能当机立断,顺势而兴,因时通变,错失机遇,就不能削平群雄,创建一代盛世。
中国古代那些胸怀大志的君主创业守成的过程,与顺应时势并把握机遇有着直接的关系。时势代表社会潮流与历史方向,顺应时势与把握机遇是一致的。在奔腾向前的历史潮流中,尤其是在新旧转折的关头,必然出现建功立业的机遇。人们虽然生活于具体的时代环境中,人的社会实践总是受到时代环境的制约,但是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如果把握历史提供的机遇,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可以进行各种创造活动,建树辉煌的历史业绩。朱熹总结历史盛衰,强调“酌今之宜而损益之”[18]2188,又说“审微于未形,御变于将来”[18]2644,把握机遇而建功立业。王夫之言:“禹乘治水之功,因天下之动而劳之,以是声教暨四海,此圣人善因人以成天也。”[1]60禹之所以能传位于子而建立夏朝,是因为把握治水有功而形成极大声望的机遇。历史盛衰反复说明,把握机遇必须顺应时势,违背时势不可能有任何机遇,倒行逆施则必然被时势所抛弃。机遇蕴涵在时势之中,具有稍纵即逝的特点,往往与人擦肩而过。因为时势是向前发展、不可逆转的,所以错过了的机遇永远不可能重新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机不可失而时不再来,一旦失去必然铸成无法挽救的损失,故把握机遇对君主建功立业关系极大。殷商后期,君主荒淫残暴。商纣王帝辛,“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诸侯多畔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19]。周文王在位的四十年时间里,利用殷商后期政治腐败、渐趋衰落的有利时机,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不断增强自己的国力,做好灭商准备工作。北魏张衮对太祖拓跋珪言:“盖命世难可期,千载不易遇。”“夫遭风云之会,不建腾躍之功者,非人豪也。”[20]鲜卑族的拓跋珪紧紧把握苻坚败于淝水之后,前秦政权崩溃、北方陷入分裂的历史机遇,建立北魏并逐渐统一了北方。令狐德棻总结历史盛衰有言:“因时制宜者,为政之上务也;观民立教者,经国之长策也。”[21]如果说时势代表历史的必然性,机遇代表历史的偶然性,那么时势总是蕴涵机遇,机遇则必然反映时势。因为历史必然性通过历史偶然性表现出来,所以机遇的出现与时势的发展是一致的。
审时度势才能顺应时势,通变创新,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进退取舍。《吕氏春秋》将桀、纣的倒行逆施与汤、武的顺势而王结合起来考察,指出:“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故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12]148。桀、纣的荒淫昏暴,大大加速了夏、商的没落,为汤、武取而代之提供了机遇。如果汤、武不是生当桀、纣之时,不逢于衰乱之世,就未必能王而创建一代盛世。新莽末年,天下大乱,分崩离析,寇盗趁乱而起,称雄问鼎者不计其数,为刘汉王朝的重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一机遇虽然首先降临到更始身上,但更始因为主观条件差,不能把握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成为昙花一现的政治小丑。王夫之将更始与光武进行比较,“更始所任为大臣者,类皆群盗之长,贪长安之富盛,而藉口于复高帝之旧业以为廓清”;“光武得士于崛起之中而任之,既无盗贼之习气,及天下甫定,复不以任三公,而别用深识之士。虚建西都,而定宅洛阳,以靖东方之寇”。光武的行为“皆惩更始之失而反其道”,“更始之失,光武之资也”[1]126。光武因为有效地利用更始之失,所以把握其所丧失的机遇,顺势重建了汉朝。在王夫之看来,汉高祖刘邦利用“群天下而起亡秦”以兴,汉光武帝则“乘思汉之民心以兴”[1]134,这是顺应时势、把握机遇的结果。满清入关以前,明朝已经腐朽不堪,危机四伏,濒临崩溃。熹宗时期,“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22]307。崇祯在位,“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22]7948。在“人怨已极,天怒已甚,灾害并至,民不聊生”[22]6827的情况下,李自成虽然攻占北京推翻了明朝,但无法把握建立新王朝的机遇,却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提供了机遇。满洲贵族紧紧抓住机遇挥师入关,取而代之建立了清王朝。王夫之指出:“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1]127其所言“天”,不是指天神的意志,而是指社会发展的时势。人只能决定得失,时势却可以决定存亡。
把握机遇需要抢占先机,因时而变。抢占先机可以引导社会潮流,占据时代的制高点,成为号令天下的旗帜。机遇对于同一时代的人虽然是公平的,但能否把握机遇却因人而异。这是因为人的政治理念、品德素质、知识水平、智慧韬略、性格气质等主观条件千差万别。那些识见非凡、能力超群者,对时势发展有正确的判断,对事态演变有充分的估计,不断积聚逐渐壮大力量,才能在机遇到来之际,洞察并把握它,实现建功立业的目标;那些胸无大志、鼠目寸光、能力平庸、见识短浅的人,即使机遇降临身上,也必然被错失,最终事业无成,甚至贻笑千古。战国后期,齐国、楚国虽然都是大国,但因君主昏庸无能,缺乏政治远见,国势日渐衰落,失去统一天下的机遇。秦国的孝公、惠王、武王、昭王等君主,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国势渐趋强大,赢得了实现统一的大好机遇;最后秦王嬴政紧紧把握这一机遇,灭六国而实现了天下的统一,创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中国古代每当旧的王朝腐朽黑暗、摇摇欲坠、众叛亲离、走向崩溃之际,虽然群雄并起,天下纷争,称孤道寡,战乱不已,但只有那些站在历史高处,胸怀韬略与能力卓越的人,能够抓住天时,把握历史机遇,成就创建新朝的大业。秦朝末年,陈涉、吴广首举义旗,对唤起民众推翻暴秦作出了重要贡献;六国之后纷纷称王自立,对秦朝政权的崩溃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人都因个人的智慧谋略与主观能力等方面的局限,先后失去了创建新朝的历史机遇。楚汉战争开始之际,项羽虽然号称数十万军队,声势浩大,称雄天下,摧枯拉朽,气壮山河,但只是逞匹夫之勇,并没有深谋远虑,不可能把握机遇。刘邦虽然军队远远少于项羽,但勇敢坚毅,富于谋略,把握项羽丧失的机遇。这些事例说明,把握机遇是主观顺应客观、主体与客体有机结合的结果。人们能否把握建功立业的机遇,总是与其主体素质直接相关。
总之,历史运动有着内在的逻辑,历史延续存在客观的时势。人们顺乎时势发展、因应盛衰之运,必然有着施展才能、实现自我、成就理想、建功立业的机遇。那些既能审时度势,又能把握机遇的君主,有可能建功立业,开创辉煌的未来,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地位。
四 因时通变,开创未来
中国古代的通变思想,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精神支柱,不断奋起、开创未来的强大动力。在中国近代这一社会转型时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各种矛盾不断加深,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从世界大势与中国现实出发,继承与发展传统的通变思想,提出改革变法的主张与建议,探索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道路。因时顺势,变法创新,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旋律。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使中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千古未有的奇变。龚自珍阐发《春秋》公羊学的变易思想,说明古今历史不断变迁之势。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23]在龚自珍看来,历史在后代不断革除前代之弊的过程中前进。魏源在鸦片战争失败与《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认识到古今时代的巨大变化,强调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他指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在魏源看来,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是走向进步的,“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他主张,“变古愈尽,便民愈甚”[24]。龚自珍、魏源的历史通变思想,虽然还没有突破循环论的桎梏,但已经隐含某些新的思想因素,显示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
19世纪60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深,制造兵器、开办工厂、学习洋文、操练军队、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逐渐兴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产生。冯桂芬认为英法联军对北京的侵略,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25]48。他认为“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提出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主张[25]57。在冯桂芬看来,中国如果不学习西方,不谋求自强之道,不惟无法雪耻,且不能自立于天下,终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25]51。郑观应阐发中国传统的通变思想,指出:“夫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参诸上古,历数千年以降,积群圣人之经营缔造,而文明以启,封建以成。自唐、虞迄夏、商、周,阅二千年莫之或易。洎秦始并六国,废诸侯,改井田,不因先王之法,遂一变而为郡县之天下矣。秦以后虽盛衰屡变,分合不常,然所谓外患者,不过匈奴、契丹西北之塞外耳。至于今,则欧洲各国兵日强,技日巧,鲸吞蚕食,虎踞狼贪,环地球九万里之中,无不周游贩运。中国亦广开海禁,与之立约通商,又一变而为华夷联属之天下矣。是知物极则变,变久则通。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的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26]郑观应主张顺应时代的要求,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学习西方建立议院,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19世纪末,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继承传统的通变思想,将其与西方传入的社会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指出:“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27]260在康有为看来,医生给病人治病,应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开出处方,病变方亦变;君主治理国家,应根据天下的具体情况,及时灵活地变通。他指出:“若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哉?”[27]292他又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敝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27]342-343康有为意识到,“若泥守不变,非独久而生弊,亦且滞而难行”。“故能变则秦用商鞅而亦强,不能变则建文用方孝孺而亦败。当变不变,鲜不为害。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27]313维新变法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途径,笃守弊端丛生的祖宗旧法必然灭亡。梁启超认为,古法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因为社会发展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必须顺时变法。他指出:“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28]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立足于新的时代环境,看到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先进,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严重的危机,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与重大意义。在郑观应等早期改良主义者维新主张的基础上,他们的通变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新的思想高度。汪荣祖指出:“晚清变法家为求中国之富强,倡论新型国家体制,对军人与商人之尊重,以及对立宪政府之向往,皆可谓已突破传统思想模式。他们虽未抛弃固有文化,但对固有文化已作重新之评鉴,并作若干取舍。毋庸置疑者,西方之影响于传统文化之重估有决定性之效果。”[29]19世纪末年的中国,变法图强、挽救危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总之,在人类历史奔腾向前的长河中,新的情况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新的问题随着时代进步不断产生,历史演变的无限性决定了因时通变的永恒性,国家有盛必有衰,通变与国家的盛衰联系在一起。我们生活于全球化时代,科学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广泛的交往,使全人类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在全球化环境下,各个国家与各个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速度空前加快。我们考察历史盛衰,必须有广阔的视野,树立全局的观念,从全球整体意识出发,看到“一个国
家的盛衰,与整个世界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兴亡,是和其它国家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兴盛是与殖民地国家的苦难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兴盛与另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盛衰变动又是相互关联的”[30]。我们既要深刻思考中国古代的盛衰兴亡,深入总结数千年来治国施政的经验教训;又要认真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盛衰兴亡的新变化,考察其内在联系与演变规律,将历史的总结与现实的探讨结合起来,不断研究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顺应历史的潮流,推动时代的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陆贾.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54.
[3]王夫之.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上[M].北京:中国书店,1986:.131.
[5]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 黄汝成,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
[7]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方东美.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473.
[10]戴望.管子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54:260.
[11]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54:87.
[12]高诱,注.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54.
[13]朱喜.答范伯崇[M]//朱熹.晦庵集:卷三十九.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重印本).
[14]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
[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087.
[17]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8]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05,107.
[20]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3.
[21]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209.
[22]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59:6.
[24]魏源.魏源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6:47,48.
[2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6]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66.
[27]谢遐龄.康有为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28]龚书铎.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98.
[29]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39-40.
[30]吴怀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203.
K092
A
1674-9014(2011)03-0056-07
2011-03-01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历史盛衰思想研究”(06GI-03)。
庞天佑(1952-),男,湖南益阳人,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和中国历史文献学。
(责任编辑:田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