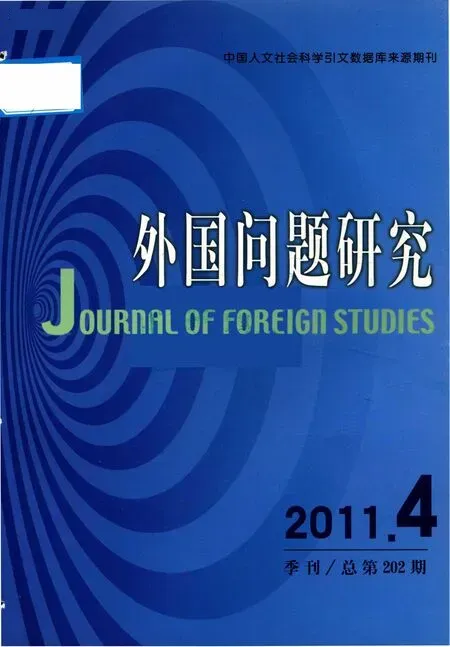日本古代小说的佛学烙印与文化成因
勾艳军
(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072)
佛教早在公元6世纪前半叶便已由中国经百济传入日本,因被赋予镇护国家、除病消灾等现世功能而逐渐得到统治者的扶植以及民众的认可,作为大陆先进文化的复合型代表,到江户时代(1603~1867)以前一直居于日本思想文化史的主导地位。佛学意识和谐地融入日本人内心深处,成为其思维方式和文艺审美无法抽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文学领域,与同样受佛教影响的中国和韩国相比,日本文学的佛学色彩表现得更为普遍和强烈,“不论是汉诗和歌,还是物语、随笔,无一不隐现着一抹佛光佛影,字里行间仿佛可以听到寺院的钟磬和僧侣诵经之声。”[1]
中国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界对佛学烙印的考察,大多集中在无常观对中世随笔及战记物语的影响,对小说领域的其他佛学意识尚未展开充分研究。其实,小说的兼容性特征使它能够囊括更加丰富的佛学内涵,如普遍涉及无常、净土往生、轮回、宿命等佛学主题。同时,日本对佛教的接受多是通过汉译佛典进行的间接接受,古代物语也始终受到六朝志怪、唐代传奇、明清小说的浸润,因此通过日本古代小说佛学烙印的考察,还能进一步了解汉译佛教故事及志怪传奇在日本的影响状况,在明确两国文学某些共同发展路径的同时,探寻一些日本小说佛学主题独特的发展轨迹。以下,笔者将细致考察镌刻于日本古代小说的佛学烙印,并深入解析其背后隐藏的宗教、信仰、风俗、艺术等文化成因。
一、净土往生:现世救赎·来世关怀
净土教是日本佛教的主流。净土思想的核心是厌离秽土、欣求净土,通过念诵阿弥陀佛实现极乐往生。经过南北朝时期的隆盛和唐代的日益发展后,净土教经高句丽传入日本。平安(794年~1183或1185年)中期到末期,藤原贵族的专政体制濒临崩溃,饥馑与盗窃使社会生活中的不安感迅速蔓延,此时,作为“救济”佛教的净土教思想,成为人们借以摆脱现世苦难的精神支柱。“塑造了日本文学特质的思想原动力,就是源信(惠心僧都)的净土教思想。”[2]的确,天台宗僧人源信(942~1017)的《往生要集》是平安时代净土信仰的基础,对平安朝乃至以后的整个日本文学史都具有决定性影响。《往生要集》对净土经典和中国的净土著作做了分类摘编,并提出以观想念佛为重点的净土理论。后来,净土宗创始人法然(1133~1212)进一步简化了净土念佛的程序,提出只要在死前念诵十遍南无阿弥陀佛,便可极乐往生,这使得净土信仰不再局限于少数的僧侣和贵族,而是逐渐渗透到日本民间,甚至有日本国民全部成为净土教徒的说法。
净土教的盛行根源于它同日本原始神道教中“彼岸”信仰的一致性。日本文化学者梅原猛指出:“日本人从绳文时代就有着对彼世的深深的信仰,正是这种对彼世的信仰,使得日本人从佛教的许多宗派中选择和吸收了最接近自己的净土教作为日本的佛教”[3]。净土信仰对平安贵族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10世纪中叶以后,天皇以及藤原贵族中出现很多热衷于念经理佛、祈求净土往生者,还有很多人选择在晚年出家,出家隐遁似乎成为贵族男女的一种惯例,日本历史上削发为僧尼的天皇就有约40位。历史物语《荣华物语》记录了平安中期太政大臣藤原道长(966~1027)极尽荣华的生涯,其中就有净土往生情景的详细描写。藤原道长是紫式部所侍奉的中宫皇后彰子的父亲,他十分信奉净土往生思想,在因病出家后建立了法成寺,并按照源信《往生要集》的方法虔诚念佛万遍,最后手牵阿弥陀如来的五彩丝线,在众僧念佛声中实现了极乐往生。
平安时代《源氏物语》的核心佛学主题便是净土思想,作者紫式部(约973~1014)因饱有才学而遭到宫中女官的嫉妒和排挤,她在《紫式部日记》中就表达了诵经出家、皈依阿弥陀佛、等候极乐之云来迎的愿望,同时流露出罪孽深重之人恐不能实现净土往生的忧虑。“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观念在《源氏物语》中常有表露,例如,藤壶中宫担心光源氏对自己的妄念一直不断,若关系败露必将招致世人耻笑,同时又担心弘徽殿太后对自己僭越的责难,唯恐遭受戚夫人般的悲惨命运,因此感觉人世可厌,决心遁入空门。在为先帝辞世一周年举办的法会上,藤壶邀请高僧开讲《法华经》,并在法会的最后一天宣布落发出家,众人无不悲伤涕泣。“帘内兰麝氤氲,佛前茗香缭绕,加之源氏大将身上衣香扑鼻,其夜景有如极乐净土。”[4]主人公光源氏在最爱的紫姬死后备感痛苦迷茫,他在周年法会上悬挂起紫姬生前主持绘制的“净土曼陀罗”,并在安排好各种俗事后选择了出家。
从藤壶中宫和源氏公子的出家不难看出,佛教在日本早期传播的过程中,体现出典型的“现世化”特征。飞鸟奈良时代(约552~794年)最初引进佛教时,就是本着镇护国家的现实目的,把原本超越国家的佛教作为护国教加以吸收的。佛教的核心是人生极苦、涅槃极乐,经过修行来世超脱轮回,最终臻于极乐。“但佛教这种来世主义,在日本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被现世主义所置换。现实主义的日本人,固然想得到彼岸的快乐,但更重要的是得到今世的幸福。”[5]的确,佛教在日本更像一种祈祷现世幸福的宗教,驱除病魔、祈祷安产、降服怨灵、追思亲人等都是其现实愿望的表现。前述《源氏物语》虽然将欣求净土作为构思的基础,但真正的用意并非宣扬佛法,而多是出于现实的考虑皈依佛门,并试图以念佛修行来超脱人间的痛苦。总之,净土思想在平安时代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信仰,不如说是救赎人们解脱人间诸苦的现世途径。
中世镰仓时代(1183或1185~1333年)的《平家物语》同样贯穿着净土信仰,与《源氏物语》中注重现世救赎的净土信仰不同,《平家物语》中的净土信仰几乎都与惨烈的死亡联系在一起,像僧都死去、新院御崩、入道死去、小宰相投水、重衡被斩、六代被斩等,死亡无疑能令人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世间无常。在20余处关于死亡的描写中,结尾《醍醐卷》中平清盛之女建礼门院的极乐往生最震撼人心。曾贵为天皇母亲的建礼门院,栖身在荒凉简陋的山间草舍念经礼佛,感觉性命犹如朝露,满目所及无不悲怆凄凉,她期待“在弥陀如来的引导下,摆脱五障三从之苦,清静三时六根之垢,一心向往九品净土,虔诚祈求一门冥福。”[6]最后,建礼门院在哀伤愁叹中手牵五彩丝溘然长逝,实现了永归净土的夙愿。
顾名思义,战记物语体现的大都是武家社会的净土信仰。实际上,前述净土宗开创者法然就出身于豪族即武士家庭,他在传播教义时也常以武士为比喻。例如,他认为念佛行者在皈依阿弥陀佛后继续过俗世生活,这正像武士在保持对主君忠诚的基础上过日常生活一样。武士在沙场上即将战死之际,只要念诵十遍阿弥陀佛,那么即使是为了名誉而进行的杀戮行为,也不会成为极乐往生的障碍[7]。经法然简化后的净土往生思想,就这样迅速渗透到驰骋于沙场、无暇诵经礼佛的武士中间,并成为武士赴死时强大的精神支柱。
镰仓时代是日本民族佛教的形成时期,与佛教初传时期(平安时代结束之前)的“现世”主义倾向不同,镰仓佛教大都否认现世救济的可能性,像《平治物语》、《太平记》、《义经记》等战记物语,更加关注自己和家人“来世”的幸福。动荡不安的社会使人们对现世安稳的追求很难实现,因此试图超越死亡来寻找来生的极乐,净土信仰成为对人们渴求来世的终极关怀,而这也发展为镰仓佛教的特点之一。正如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所说的:“十三世纪的所谓镰仓佛教,与现世利益型的、咒术式的平安时代佛教尖锐对立,它强调佛教的彼岸性、超越性的一面。”[8]其实,这也正回归了佛典的本来面貌,佛教最初就是强调人生极苦、涅槃极乐的出世哲学,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使中世人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更加深刻和纯粹。
二、无常:感性叹息·理性解释·生死观
佛教思想在中世文学表现得最为明显,以致人们常将佛学色彩视为“中世色”,中世色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无常”。无常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生和社会体验,也是佛教经常提及的基本概念。佛家认为世间一切时刻处于消灭流转之中,没有什么能永恒存在,人或物终将走向毁灭。无常观往往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消极影响,认为人生只是一个虚幻短暂的时间过程而已。日本是一个地震、台风、海啸、火山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岛国,因此其民族意识中早就潜藏着一种生死、兴衰皆无常的感觉,所以很容易与佛教揭示人生虚幻感的无常观相契合。
进入平安时代末期,随着武士地方势力的崛起,维护国家的传统律令制已接近崩溃,因保元之乱(1156年)和平治之乱(1159年)而引发的社会危机意识,使“末法”思想在僧俗之间传播开来。以藤原氏为中心的宫廷贵族因自身没落而深感人世无常,饱经战乱的武士及庶民也具有普遍的悲观厌世倾向。从保元之乱的导火索即近卫天皇驾崩(1155年)开始,“无常”一词频繁出现在文艺作品中。镰仓时代的随笔和战记物语中更是随处可见无常的字眼。例如,鸭长明(1155?~1216)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约1283~1352以后)的随笔《徒然草》,都流露出一切都在生灭变化、万物不能长久的无常心态。
在中世以无常观为底色的文学作品中,《平家物语》是最杰出的一部,它以极度惨烈的形式展现着人们所无法逃脱的宿命,开篇“祗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沙罗双树花失色,盛者必衰若沧桑。骄奢主人不长久,好似春夜梦一场;强梁霸道终殄灭,恰似风前尘土扬”[6]1的语句,充满了盛者必衰、诸行无常的悲观色彩,既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广为渗透的无常思潮,又因其影响而使无常感更加深刻地蔓延开来。
通常认为,日本人首先对“无常感”产生共鸣,之后逐渐发展为“无常观”。《平家物语》对此便有浓缩的展现,其中既有对人世无常的感性接受,同时也将无常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用来解释盛者必衰的人间规律。也就是说,《平家物语》中的无常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无常感:对人间悲剧的感性叹息,作者持同情心态;(二)无常观:对物盛者必衰的理论解释,具有一定的批判色彩。两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处于时而平行时而交织的融合状态。
一方面,作者对世事无常、生命无常、恋爱无常等发出感性的叹息。主人公平清盛虽然一度权倾朝野,子孙高官厚禄,财宝堆积如山,但在短暂的50余年间,其统治便土崩瓦解,家人也大都惨遭屠戮。平清盛的死亡是其家族命运的转折点,他在经历了一场离奇病症的折磨后,体热如焚气绝而亡,那个曾经“闻名全国威震一世的人,他的躯体顷刻间化为烟尘,升到京城上空;他的骨骸暂留岛上,不会太久,便与海边的砂相混,化成虚空的泥土了。”[6]247作者对平清盛的无辜子孙表现出悲悯情怀,虽然他们曾因平清盛的权势而享受过至高无上的荣华,但随着平氏家族的衰败,都纷纷遭遇到枭首示众、投海自尽等重大不幸,而这自始至终都是他们自身所无法把握的宿命,因此只好将一切都归咎于命运的无常。恋情同样不能长久,像平清盛看到歌女阿佛后便无情驱逐了曾经无比宠爱的祗王,而阿佛通过众多女性的悲惨遭遇也预见到了盛衰的无常,因此毅然选择了弃绝尘缘,与祇王一同修行并期待着极乐往生。
另一方面,作者以佛教的无常观来解释因战乱而起的荣枯盛衰、生者必灭的历史事实。《平家物语》批判性地展现了平清盛及其家族的极端兴盛与最终灭亡,意在表明残暴的统治必然不能长久。作者开篇即以赵高、王莽、安禄山等人走向灭亡的史实来暗示平清盛的结局。虽然作为新兴武士阶级推翻了腐朽的贵族统治,但平清盛很快便重蹈覆辙,因为骄奢淫逸而使百姓怨声载道,所以终究无法避免盛者必衰的无常宿命。平清盛在临终前却并不安于无常宿命的安排,唯一的遗愿竟是斩下伊豆流亡之人源赖朝的首级以供孝养。作者在此冷静地揭示出,与无常抗争是徒劳无益的,暴虐不仁者终究无法逃脱死亡的残酷和统治的土崩瓦解。作为一部面向庶民的说唱文学,《平家物语》似乎在传达一种“无常史观”,同时替百姓表达了对于无道当权者及混乱社会现状的不满。
死亡是无常最典型的体现,战记物语中的无常体验也大都与死亡观紧密相连。战乱频仍的时代,对武士而言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甚至有“死亡乃意料之中,活着乃意料之外”的说法。此刻,无常已经不仅仅是佛教术语,而是战场上武士们真实的生死体验或曰死亡观,它与贵族世界因朝露易逝或飞花落叶而引发的无常感有显著不同。无常观激发了武士阶层深深的共鸣,同时也成为麻醉自身灵魂、能够毅然赴死的思想武器。众所周知,根据变化速度的不同,佛教将无常分为“念念无常”与“一期无常”。念念无常指精神或物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一期无常指人或事物终将走向毁灭,一期无常是念念无常的累积和最终爆发。日本传统和歌物语中的无常大都表现为念念无常,重在抒发因四季轮回、花开花落、月圆月缺、物换星移、悲欢离合等引发的瞬息万变的情感体验。与此相对,战记物语中的无常表现为一期无常,当死亡不可避免地降临时,人们的无常感受才格外地强烈。
无常感已经深深融入日本民族的内心深处,并渗透为全民族的审美意识。日本学者唐木顺三说过:“自古以来就有‘无常美感’的说法,说到无常时,日本人的心灵琴弦,就会拨动出悲哀的、奇妙的音响。”[9]的确,日本的文艺作品常以优雅华丽的笔触来抒发无常感受,日本读者欣赏和品味着这份无常之美;无常美感往往伴随着沉重的感伤,物哀审美意识的发生便与无常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方丈记》、《平家物语》因出色展现了无常美感而被尊奉为国民文学,中世世阿弥的谣曲、近世松尾芭蕉的俳句、近松门左卫门的殉情净琉璃等,也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无常的生死观和审美意识,从而构成了日本文学史上绵延不绝的无常审美潮流。
三、因果报应:怪奇趣味·儒佛融合
因果报应是传统佛教影响最广泛也是最通俗的理论。在佛教因果报应思想传入之前,日本的传统意识是以集团的方式遭受惩罚,个人的错误往往会给所属部族乃至国家带来灾难,这与佛教宣讲的恶报只会降临作恶者本人有所不同,而且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轮回转生概念。平安时代很多人并不接受因果报应观念,还曾经对讲述因果报应的人加以迫害。但随着佛教在统治者支持下的不断传播,以及《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等众多佛教故事集对百姓的诱导,人们开始熟悉并接受因果报应的思维方式。
日本最早的佛教故事集《日本灵异记》(约822~824年)开始向民众普及因果报应思想,所收录的116篇奇闻异事大多为因果报应和灵验故事。作者是奈良药师寺僧人景戒,其职责即向俗众通俗易懂地讲解佛家真理,并诱导其皈依佛教。《日本灵异记》在编纂思想和题材方面受到中国佛教故事集《冥报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等的重要启示,但辑录的重点转向日本国的现世报应。景戒在上卷开头强调:“匪呈善恶之状,何以直于曲执,而定是非。叵示因果之报,何由改于恶心而修善道乎。”并在结尾处进一步提出期望:“祈览奇记者,却邪入正。诸恶莫做,诸善奉行。”[10]
《日本灵异记》基本分为善报故事和恶报故事两大类。善报故事大都与菩萨或经典的灵验谭交织在一起,如信敬三宝得官位与长寿、信仰妙见菩萨盗品失而复得、信仰方丈经治愈疾病和耳聋等,总之善报的前因是建造寺院佛像、抄写经卷、布施、放生、悔过、诵经等。而且,正如题名中“现报”二字所提示的,这些善报故事都属于现世现报类型,没有轮回或冥报的事例,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佛教传入日本之初便具有现世倾向。《日本灵异记》的重点在于恶报故事,像生剥兔皮得皮肤病痛苦而死、嘲笑法华持经僧口角歪斜而死、因淫邪或不孝而堕入地狱等,总之恶报的前因在于杀生、不孝、淫邪、破坏佛像、污蔑僧侣等。惨烈的恶报故事无疑会给人以更加强烈的震撼和警示,中国的佛教典籍及早期小说对善恶两报的宣传也大都偏向于后者。
正如其全称《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所显示的,善恶果报往往与“灵异”故事联系在一起,这同时也开创了日本小说崇尚怪异的先河。因果报应与宿世、轮回、转生等概念互为表里,极大扩展了日本文艺的思维空间;地狱、阎罗、狱卒、鬼魂等描写,也为怪异小说的叙事提供了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怪异性成为日本古代小说不可或缺的叙事因素,在为数众多的怪异情节中,“怨灵作祟”无疑是最常出现且最具日本特色的一笔。《大镜》、《荣华物语》、《源平盛衰记》等描写了引发疫病和天变地异的“御灵”,《源氏物语》、《好色一代女》、《雨月物语》等描写了“物の怪”即活人的灵魂作祟。六条妃子、崇德上皇、菅原道真等都是死后或生时化为怨灵的经典人物。
笔者认为,怨灵作祟既是日本原始神道教的概念,也是佛教引进后因果报应观的一种变形体现,可谓“神佛融合”的产物。以万物有灵、祖先崇拜为中心的神道教认为,人死后灵魂会继续穿梭于现实之间,灾难或疫病流行的起因是怨灵作祟。“平安时代是一个怨灵跳梁跋扈的时代,平安京到处都飘荡着死于非命的皇族、贵族、僧侣的怨灵。”[11]引进佛教后,人们吸纳了中国众僧念佛驱逐恶灵的仪式,并将怨灵作祟理解为因为眷恋或仇恨而难以极乐成佛。其实,怨灵作祟的本质是一种复仇,化为恶灵的大都是阴谋的牺牲者或者含冤负罪之人,曾经的施恶者仍然活在世间安然无恙或逍遥自在,恶有恶报的定律没有及时反映到这些人身上。于是怨灵只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惩罚恶人,使其自身或家人等遭受恶报。此时的恶有恶报与佛教教义有了较大距离,也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日本式的、个人复仇似的报应观,人们以此种方式为弱者伸张正义,并抚慰那些游荡在人间无法成佛的怨灵。
在中国文化及文学的综合影响下,日本小说中因果报应的重要特征,也体现为与儒家“劝善惩恶”观念的结合。善恶有报的标准,不再是早期的是否尊敬佛典僧侣或是否杀生淫邪等,而是逐渐被儒家道德条目所取代。众所周知,日本并非直接承袭印度佛典,而是通过汉译佛典或中国高僧亲授等方式进行的间接引进,而后汉至东晋的早期佛典本身,其实就已经掺杂了少量的儒教或道教思想。为使佛教能在中国立足和发展,佛学家总是尽力寻找儒佛伦理道德的契合点,这种援儒入佛的趋势,通过佛家故事、六朝志怪、唐代传奇、明清小说等传播途径,影响到了隔海相望的日本。
因果报应思想向儒家靠拢的趋势典型体现在近世(即江户时代,1603~1867年)。德川幕府将儒学提升为“官学”,佛教不再是涵盖一切的意识形态,甚至还出现以朱子学者为中心的排佛思潮。佛家在近世后期积极向儒家接近或妥协,提出神儒佛三教一致理论,认为三者皆“劝善惩恶”,儒佛皆能“辅翼吾神袛,益吾灵国。”在通俗小说领域,读本小说家曲亭马琴(1767~1848)是劝善惩恶小说观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南总里见八犬传》是参照《水浒传》等中国小说并融合日本史实完成的鸿篇巨制。马琴在序言和卷首附录中反复申明自己的“劝善惩恶”主旨,如“虽是痴人荒唐事,然欲劝善惩恶,以教诫世间愚顽之女子、童蒙、翁媪,以作迷津之一筏,故始握戏墨之笔。”(第九辑序言)[12]。他在《月冰奇缘》自序中,还明确传输了自己借用佛教的因果报应之理、来弘扬劝善惩恶主旨的良苦用心:“聊借释氏刀山剑树之喻,以寓化人解脱之微意,虽未免捞水弄月之诮,些可以惩恶奖善,读者镜焉,庶几迷津之一筏矣。”[13]
因果报应的观念往往也是充满矛盾的,善良之人遭遇厄运的例子不在少数,穷凶极恶之人也经常尽享荣华富贵,所以说因果报应只是人们憧憬中的理想状态,是对现实世界的绝望和逃避。尽管如此,因为善恶有报的美好结局能够满足民众朴素善良的愿望,所以因果报应一直是备受小说家青睐的主题之一。较之于宣传佛教教义的功能,因果报应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叙事手段,日本古代物语往往存在无固定主题、结构松散凌乱、缺乏逻辑联系的缺陷,因果报应观念伴随佛教故事和志怪传奇传入日本后,日本小说家开始尝试依照因果报应的链条来连缀情节。到了明治维新以后,受西方写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因果报应、劝善惩恶为核心的旧小说观念开始遭受抨击,以1885年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为契机,小说家开始将写实的笔触延伸向现实世界普通男女的喜怒哀乐,小说领域的因果报应观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结语
上述佛学思想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循环交织,一部小说往往融入多种佛学内涵,《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等小说就综合体现出无常感、净土往生和因果报应思想的深刻影响,佛教思想与小说创作已经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佛学意识在经历了最初的传播阶段后,到15世纪后成为艺术被广泛接受,有时甚至成为一种非自觉的抑或装饰性的存在,因此很多小说在佛学的叙事氛围中,其实还蕴含着更加深广的内涵,如对人类情感的描摹、对社会万象的展现、对历史的反思或对现实的质疑等,佛学意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的创作主旨,只是切不可将佛学主题完全等同于整部作品的创作核心。
[1]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96.
[2][日]久松潜一.增补新版日本文学史2中古[M].东京:至文堂,1975:11.
[3]梅原猛著.卞立强,李力译.世界中的日本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218-219.
[4][日]紫氏部著.丰子恺译.源氏物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04-205.
[5][日]武安隆.浅议佛教的日本化[J].日本问题.1990 (2):75-76.
[6]作者未详.周启明,申非译.平家物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20.
[7][日]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M].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1994:119-120.
[8][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M].东京:筑摩书房,1981:210.
[9][日]唐木顺三.无常[M].东京:筑摩书房,1964: 196.
[10][日]景戒著.远藤嘉基,春日和男校注著.日本灵异记[M].东京:岩波书店,1978:54、56.
[11][日]须永朝彦.日本幻想文学史[M].东京:白水社,1993:31.
[12][日]曲亭马琴著.小池藤五郎校订.南总里见八犬传(九)[M].东京:岩波书店,1985:5.
[13][日]曲亭马琴.曲亭马琴集(上)[M].东京:国民图书株式会社,19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