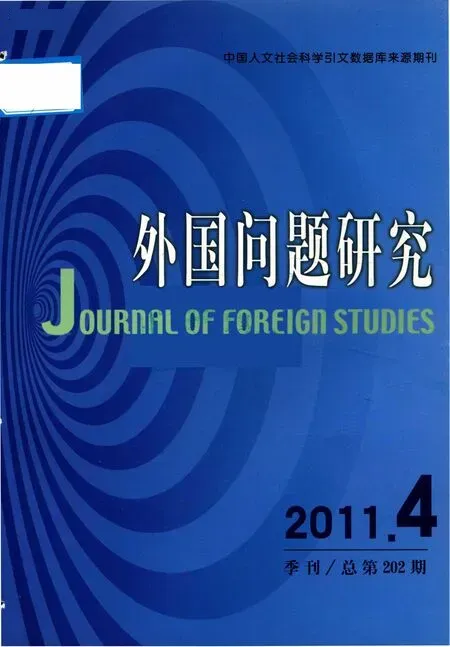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地方自治——以莫塞的地方自治理论为中心
郭冬梅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24)
阿尔伯特·莫塞(Albert Mosse1846-1925)作为当时德国乃至欧洲都极具影响力的国法学和行政法学者格奈斯特的高徒,1886年受日本聘请,偕妻子远渡重洋,成为日本内阁的一名法律顾问。在直到1890年的共计3年零11个月的顾问生活中,莫塞得到时任内务卿的山县有朋的极大信任,受托全面负责近代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创设工作,承担了《地方制度编纂纲领》和《市制町村制》等的起草工作,是构筑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灵魂人物。不唯如此,对于明治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他亦多有建言,由此成为近代日本在国家建设上选择普鲁士道路的最直接责任者之一。
莫塞的地方自治理论承袭于其师格奈斯特,在其政治学和行政学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一理论被全面地贯彻到了近代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中,对近代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系统考察其地方自治理论,不仅是解读近代日本地方自治特性的一把最为便捷的钥匙,同时也会为深入理解近代日本宪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提供某些启示。笔者通过对莫塞的相关讲义及意见等资料的解读发现,莫塞的地方自治理论的核心内容,总结起来便是:以法治国为目标,强调地方自治之于国家与社会的调和的重要作用。他的这一理论,不仅征服了当时为近代国家建设所迷惘的明治官僚,即便是今天,通过对其理论中某些合理成分的吸收,或可为我国的地方制度建设提供某些借鉴。
一
关于莫塞的地方自治理论,日本学者在战前已经开始了考察,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如龟卦川浩在《自治五十年史制度篇》(良书普及会,1940年)中即对其理论进行了阐述,此外还有其发表的文章《莫塞对町村制草案修正的意见》(《都市问题》28卷1号)等等。战后初期吉川末次郎在论文《日本地方自治制的创案者阿尔伯特·莫塞的思想及其批判1、2》(《同志社法学》第9号和11号,1951年7月和12月)中对莫塞的国家观、君主观、地方自治观和政党观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居石正和在《明治地方制度的成立及其特征2——以莫塞的自治论为中心——》(《岛大法学》38卷4号)中则从分权论、名誉职制度、参事会制度三个角度论述了莫塞的自治理论。笔者通过研读这些文章发现,学者们在撰写文章时,在阅读资料上往往各有侧重,未能做到全面。而如果对莫塞的地方自治理论进行总体的研究,必须全面地对所有有关莫塞的讲义及意见资料等进行考察。因此,笔者通过在日期间的收集整理,将莫塞的有关地方自治资料归纳为如下:
(1)伊东巳代治文书中的莫塞讲义笔记,是1882年伊藤博文赴欧进行宪法考察时的莫塞讲义笔记,但遗憾的是,共计44回的讲义遗失了21回,特别是关于地方自治内容的部分基本上都遗失了。此讲义后收录于清水伸著《在德奥伊藤博文的宪法调查和日本宪法》(岩波书店,昭和14年)中。
(2)东京大学法学部近代立法过程研究会编集的《大森钟一关系文书2-4莫塞氏讲义》,发表于《国家学会杂志》84卷7·8、9·10、11·12 (1971年)三期上。是1885年10月21日到1886年2月10日,莫塞对伏见宫贞爱亲王一行进行的国法学和行政法学的讲义,共42回。当时大森钟一作为陪同进行了笔记。
(3)《自治论纂》(德逸学协会,1888年5月发行)中的《国法论讲义笔记》,据说是莫塞仍为德意志地方裁判所判事时对日本有关人士的讲义,是野村靖的听讲笔记。
(4)从1886年12月14日到28日共四次的讲义和回答提问。这是莫塞来日后不久,在内阁法制局所进行的讲义及答疑,伊东巳代治笔记,后题为《自治论》收入到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 法制关系资料下卷》(秘书类纂刊行会1934年,原书房1965年复刻)中;另题为《莫塞氏自治论》,由国学院大学日本研究所整理收入到《近代日本法制史料集第十》(国学院大学,昭和63年)中。
(5)东京市政调查会市政专门图书馆所藏《大森钟一文书》49“关于府县郡自治的山县大臣、野村、青木诸氏和莫塞的问答”以及50“莫塞氏关于设立立宪政体的意见书、莫塞氏、劳斯雷鲁氏关于地方制度的意见书”。后都收入到内务省地方局编纂的《府县制度资料(上卷)》(历史图书社,1973年)中。
(6)莫塞于1887年2月1日提出的《地方官政及共同行政组织的要领》(包括《共同区行政的监督》、《官政事务上参事会的合议厅职权》和《行政裁判》三个大纲),经过地方制度编纂委员审议后形成《地方制度编纂纲领》,7月起草完成的市制町村制的草案《自治部落制草案》等收入到东京市政调查会编纂的《自治五十年史第一卷制度篇》(良书普及会,1940年)中。此外,1888年与《市制町村制》同时发布的《市制町村制理由》是由莫塞起草的,反映了莫塞的自治主张。
(7)《市制町村制》发布后莫塞进行了三次题为《町村制度》的演说。其内容分别在1888年7月15日、8月15日和10月15日出版的《国家学会杂志》第2卷第17号、18号和20号上发表。
(8)1888年10月19日到1889年3月29日,莫塞和兰道根(Karl Rathgen1856-1921)两人在自治政研究会交互进行讲义,两人的讲义笔记以《自治政讲义录》(上下二册)为名于1888~1889年公开发表,而后单把莫塞的讲述部分共十次名为《自治制讲义》,1889年10月由日本书籍会社刊行。
从以上的资料的时间上看,(1)(2)和(3)是莫塞来日前的讲义;(4)为来日后不久的讲义; (5)为法案制定过程中的意见书;(6)(7)(8)为莫塞起草的草案及《市制町村制》发布后进行的说明和讲义。从特征上来看,(1)(2)和(3)是内容较长而系统的国法学和行政法学的讲义,自治制度只是其讲义的一部分内容;(4)是比较简洁的自治制讲义;(5)(6)(7)(8)是意见、草案及《市制町村制》的说明,其中《自治制讲义》全部十回,内容具体详细,是相对来说较为详细的专门的地方自治理论阐述。
二
以往学者对莫塞的研究,分别侧重于使用某一资料,缺乏对所有资料进行系统而综合的分析,因而其论述的视角也不尽相同。那么莫塞地方自治理论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笔者通过研读这些资料,发现无论是莫塞来日前的讲义,还是其来日后或《市制町村制》发布后的讲义及意见,尽管其讲解方式和个别翻译可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其地方自治理论的核心内容贯穿始终。
首先是强调近代法治国的目标,也即近代的法治国家是莫塞追求的理想国家模式。那么,莫塞所谓的法治国,究竟是什么呢?
在众多的讲义中,莫塞总是最先强调近代国家的国权,宣称国权属国家所有,国权高于君权。如在《自治制讲义》中,莫塞开宗明义,称“国家的本义不可缺少的是国权”[1]1,“不论政体如何,统治各人各个意志的国权必存在于国家”[1]3-4。而为了保障国权的强大,莫塞由此主张实行君主制。盖“可抑制社会中存在的变幻无穷、争斗不已的利害的统一永久权力只能由君主来实现,国家的理想在君主制,有超然于社会之外的代表。当然君主亦是从社会有力者中产生,居于社会秩序之首位,但不曾为社会所役使,而是担当统治社会之任。代表共同体的永久的性质,对强者保护弱者,对使役者保护被使役者。”[1]16他在1885至1886年为伏见宫贞爱亲王进行的讲义中,开篇亦以普鲁士为例,称“普国胜于他国者无他,国法之力强,王权亦巩固,确立了议院制度。再详言之,即其国法的趣旨乃把王权置于稳固的位置。但绝非压制人民的权利。”[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莫塞因强调国权而主张的君主制,绝不是专制的君主制,而是“确立了议院制度”的立宪的君主制,“专制国的君主任由自己的意思施行国权,且君主的意思直接为国家的意思。而立宪国则不然,君主施行其国权必须获得国家独立机关的共同意思。即君主的意思只有得到机关的共意才能成为国家的意思。”[1]3
在莫塞的理论中,国权的“动作”被具体划分为立法和行政二者。由于强调国权的统一不可分割性,因此相对于当时流行的民主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主张,莫塞主张国权只可分为立法和行政,而“行政又分为司法和狭义的行政”[1]5,强调司法只是行政之一部分。不过,在立法与行政这二者中,“立法是国家的最高动作,其他动作悉遵循于此立法之下。”[1]6强调立法权的重要性。但立法权并非因此而没有限制,而是要受“德义”和“政略”制约。所谓“政略”的制约,即是顺应国家的目的[1]8-9。
莫塞认为近代国家的目的有三:其一是对外防御自己的国家,是需要国民所普遍负担的,由此而引出“服兵役”是国民的义务的主张;其二是国家对内保护个人的权利。即必须承认个人的自由,保障个人信教、学术、营业以及迁徙等自由。此外还有集会、出版、受教育等的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必须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其三是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观察国家对社会的关系,利害之争长存于社会而不绝。而国家愈开明,此争益加剧,社会中相倾轧、争斗愈多。在经济上尤其如此。故今日之国家对社会之任务已非昔日可比。今日之国家要保护被强者压制的弱者,防止强者独揽权利凌虐弱者,以维护社会的和平。”[1]15
在国家的三点目的中,莫塞特别强调第二点,也即“对内保护个人的权利”。他指出“昔日之国家并非不保护其臣民的权利,然其保护只限于受到第三者侵犯时,不涉及被国家自身侵犯者。反之今日之国家,在国家自身即国家机关损害个人的权利时,亦保护此个人的权利,此即现今所说的法治国原则的主旨。国家承认不可侵犯的个人的权利,在其权利受到国家机关侵犯时给予保护此即法治国的主旨。”[1]12由此而推导出他的近代法治国的目标。在《自治制讲义》的第九回,他再次强调:“说到法治国的本义,所谓的法治国,就是国家保障臣民各自的权利,政府的权利根据法律进行限定,根据法律实行。对于行政官衙的违法处分给予臣民以法律上的保护。”[3]2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近代的法治国是莫塞所追求的理想的国家,法治国理念构成了莫塞地方自治理论的核心,而其所强调的国权、立宪君主制、二权分立等等最终都是为其法治国的目标服务的。
三
那么如何实现法治国的目标呢?莫塞称“此所谓法治国的目的,唯有与自治制相联结才能够得以完全。”[1]14由此引出了他的自治理论。他还称“余辈相信,为使国家完成此务唯在与自治制相联结之君主国制度。”[1]15-16强调自治制与君主制联合起来,能够实现其法治国的目标。除此而外,莫塞还主张实行地方分权,把地方分权与自治统一起来,形成“基于自治的地方分权制度”[1]29,也即地方自治。
实行地方自治的益处在哪里?为什么实行地方自治就能够实现法治国的目标?对此,莫塞多次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论述了实行“基于自治的地方分权制度”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在《自治制讲义》中说明得更为详细,其要有如下七点:
(1)将国家职务中应分割给地方者分给地方,不仅可以减少国家因不熟悉地方情况而导致的不当处置,又可以节约经费。
(2)无论任何国家,多少在民间都存在着“可供公共之用的有力有为”的势力[1]29,如果只任命官吏执行国家公务,则这些民间势力不仅因无用而导致浪费,还可能变成威胁政府的反对力量,而实行自治制度就可以收集这些力量为国家所用。
(3)只由国家任命的官吏执行公务的话,政府的责任极重,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容易产生“危险的倾轧”,人民常常敌视政府,“抱有政府和人民利害不相容之妄想,不知一国之隆盛实在政府和人民之协和一致”。而实行地方自治后,使人民直接参与公务,国家和社会不直接对立,而是还存在一个中间阶层,“成为联结两者的脉络”。这样,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责任,人民也产生了国家心、爱国心。“没有中间阶层的国家的社会只喜欢对国家讲究权利,而不喜欢承担义务”[1]30-31,实行自治制后,社会亦知应对国家负有责任,领悟到对国家不仅有权利,而且必须承担义务。
(4)自治制使社会担当实际之事务,因此渐渐习惯于“相谋相让,舎小异而取大同”[1]32,调和社会的反对,保持其和平。
(5)基于自治及地方分权建立的国家,其基础甚为牢固,“可堪内外之冲击”。历史上权力集中于中央的国家,国家和社会直接对立,其中心一旦被击破,则全国忽而破碎。而如果使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则其“与国运的隆替和中央政权的消长关系不至于过分紧密”[1]33-34。
(6)凡欲实施立宪制度的国家,要先使人民有若干政治上的知识。那么如何养成这种知识呢?在这些国家的人民“往往对国家的事务漠然,认为不关痛痒,其眼界仅仅及于町村或者郡县,而不知其上有国家,或者谈政治之事而不理解,或者其所见所论只是基于单纯的学理上的架构”[4]1-4。自治制度可以培养人民政治上的知识,通过使人民参与公务,对公共团体事务负有重责,扩展人民对于公务的感情和见识,为将来的议院培养适当的人物。
(7)“实行立宪制度终不免政党的倾轧”,官吏作为政党的机关有可能被政党所左右,不能秉持公道,遵循法律,从而“违反法治国家的原则”。如果使官吏和名誉职共同执行政务则可“抑制政党横行之弊端”[4]7。
由上可见,莫塞从把国家事务分给地方以省政府之繁杂,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圆滑化,使社会的精英力量为国家服务,防止政府与人民的直接对立,培养民众的爱国心,奠定立宪的基础和防止官吏的政党化等多个方面论述了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最后,莫塞说:“自治之利,除以上所列之外还有很多”[4]8,但归结起来,实行地方自治,“不仅保护人民的利益和自由,而且是使国权强大的基础,是立宪制度必不可少的前提。”[4]8
地方自治理论在莫塞的国法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正是源于上述从国家与社会视角下对实行地方自治具有重大意义的认识。应该说这种认识产生于对欧洲,特别是英国、德意志和法国历史与现实的对比考察,而其根本原因是出于对德国建设近代国家现实的需要的思考。
四
那么,莫塞所谓的地方自治,也即“基于自治的地方分权”,其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如何实现呢?莫塞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该问题:
首先,是地方分权。何谓地方分权?在来日后不久在法制局进行的讲义中,莫塞开宗明义,首谈的是集权之弊和分权之利。“凡国家无不分割其版图,町村郡县是也。此郡县之事务有两种,第一为国家的机器,施行国家的意思,即行政的机关。第二的机关为一种有独立权利的政治上的团结体,称为自治体,自治体是权利的主体,权利的主体即无形人,在私法上可以缔结契约,拥有财产,施行一定的行为。而其在公法上一方面可以对人民发布规则,另一方面对政府可以独立地表示其意思。”[5]83莫塞所谓的前者,即是他提出的中央集权的“机械国家”。这种国家“一方为国权,一方为人民,二者相对立,无介于其中间之团结体,介于其中间者只有国家和人民间之行政机关。”[5]82后者即是所谓的地方分权,不是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直接的行政统治,而是要让地方结成公法人团体,分担国家的事务。集权之弊与分权之利是:在“机械国家”,“如有巧手之机械师能运转机关,则大大整顿可使政机圆滑,但一旦其运转失误,则导致秩序紊乱。然若国家和人民之间设置郡县之自治体,即便中央政府之秩序偶有不整备,其机械之运转仍无招致祸患之虞。”[5]83
那么这种具有公法人资格的地方自治体究竟怎样程度的分割中央政府的事务呢?莫塞指出,分任给地方者,“内务事项及财政事项最多”,如税收、警察等;“反之外务事项、兵事之大部分由国家独自担任”[5]84,如立法、外交、军事等。而且这种分权只是“行政上的分权,而绝不是立法上的分权。”[5]85其进而称,“自治政治的机关非议会,而是行政公署。自治政治的作用不是共同商谈,而在于共同执行……自治政治的机关不是制定法律,而是遵从政府制定的法律执行行政。”[6]可见,莫塞的分权,是分政府的行政权,重要的是执行国政事务,而不是干预立法。但尽管如此,莫塞也补充说,因为“国家的法律无法规定各自治体的细微事情,所以不可不赋予自治体以发布条例、制定适当的规则的权利。”但不得“妨碍国家的统一,危害国家的基础。”[4]10-11
其次,实行地方自治不仅任用官吏,还要使民众以名誉职参与地方事务,此即莫塞所谓的“自治”。“如欲明自治之真意,不可不先研究自治制最发达、取得最显著利益的国家。抑其所以奏自治制之功者,即在于以人民任荣誉职,使之参与公务。对于自治一词,或许有不同的意思,但如论起英德实施的经验,自治之要实在此荣誉职制也。”[1]20此荣誉职和名誉职同义,即指人民以非官吏身份无薪参与地方事务。实行这一制度,保障的是有资产有闲暇者参与地方事务,也即贵族。莫塞毫不隐讳地多次强调“对自治政治起重要作用的是贵族。”[2]自治制“不带有民政主义的性质”,而是“包含着贵族政治的主义。”[5]89由此,他甚而主张“多纳税者不可不比少纳税者在选举上拥有更多的权利,选举的权利决不能人人平等。”[7]
第三,实行地方自治要有充分的国家监督,并实行行政裁判制度和参事会制度等。“扩张自治政治同时却不忘国家之目的最为重要。国家之目的在于统领一国,不使其分裂。因此要不懈怠地监督各地方事务。”[6]但是这种监督同时也是有限度的。“在今日之法治国,不许滥用此等监督权,不允许超过其原来目的进行干涉。”[4]30但关于监督的具体方式,可以“立阶级,分其事业,由上对下进行监督”,而最上的监督“归于国权”[6]。关于行政裁判权,莫塞认为“行政裁判和地方自治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3]1-2“将行政裁判称之谓立宪国及法治国的基础绝无不可。行政裁判是对于行政进行权利上的监察,因此使行政遵从法律,希望在法律的范围内干涉臣民的权利。”[8]“在立宪政体国,共同体受到公法上的保护,由此行政裁判法进行保护。”[6]莫塞主张实行行政裁判制度有进步的一面,但同时也是其“二权分立”、反对将“行政置于司法之下”理念的必然反应[3]21。由此进而导出“参事会制”,居石正和指出,参事会制是莫塞自治论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他根据对资料《关于府县郡自治的山县大臣、野村、青木诸氏和莫塞的问答》的解读,提出了莫塞力主实行的参事会制,不仅是合议制的行政机构,同时也“被纳入到行政裁判制度中”,由此而“最终保障了自治及其发展”[9]。
结语
以上笔者通过对莫塞地方自治相关资料的全面解读,对其地方自治理论进行了梳理。也即,莫塞的地方自治理论虽然内容庞大,但其理论的精髓在于:为了实现近代法治国的目标,必须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其对国家与社会起到重要的调和作用。此地方自治应是地方分权与名誉职制度的统一体,国家应对其实行适当的监督和行政裁判制度。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莫塞的理论即便在当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保守性。如在国权观上,莫塞强调了“国家主权论,否认了人民主权论”,从而也反对了“民主主义”[10];主张“贵族政治”、等级选举,反对了民主平等。等等。但笔者在此还要指出的是,莫塞或曰其师格奈斯特的地方自治理论,根源于对欧洲历史,特别是英法德三国历史的认识总结之上形成的,是出于其母国德意志建设近代国家的历史使命感的产物。因此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对封建性、希望缔造近代的国民,建立和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性主张。因此,它对于同样进行近代国家建设的日本启示意义极大。莫塞地方自治理论不仅深为以山县有朋为中心的明治官僚所接受,即便在明治宪法的起草中,其理论也多超越了其他外国顾问而为日本所吸收[43],便可作为明证。
而当我们今天在重新读解其理论时,在摒弃那些早已不合时宜的保守落后的观点的同时,体味其法治国的理念,地方自治之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作用的论述,不也能从中收获些许的感悟么?
[1]鶴岡義五郎編.自治制講義(第一回)[M].東京:日本書籍会社,明治22.
[2]東京大学法学部近代立法過程研究会编.大森鐘一関係文書2モッセ氏講義[J].国家学会雑誌,第84卷7·8号,1971.
[3]鶴岡義五郎編.自治制講義(第九回)[M].東京:日本书籍会社,明治22.
[4]鶴岡義五郎編:自治制講義(第二回)[M].東京:日本书籍会社,明治22.
[5]モッセ氏自治論[A].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編.近代日本法制史料集第十[M].東京:国学院大学,昭和63.
[6]東京大学法学部近代立法過程研究会编.大森鐘一関係文書3モッセ氏講義[J].国家学会雑誌,第84卷9·10号,1971.
[7]鶴岡義五郎編.自治制講義(第三回)[M].東京:日本书籍会社,明治22:35.
[8]鶴岡義五郎編.自治制講義(第十回)[M].東京:日本书籍会社,明治22:1.
[9]居石正和.明治地方制度の成立とその特徴(二)――モッセの自治論を中心に[J].島大法学,第8巻4号.
[10]吉川末次郎.日本地方自治制の創案者アルバード·モッセの思想とその批判二[J].同志社法学,第11号,1951.
[11]堅田剛.独逸学協会と明治法制[M].東京:木鐸社,19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