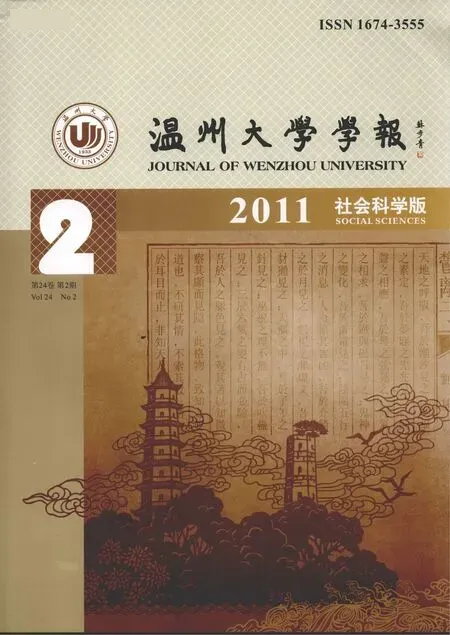“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嘎达梅林与土匪、英雄和革命者原型
何安妮,赵肖为(译)
(1.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美国哥伦布 43210;2.温州大学学报编辑部,浙江温州 325035)
“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嘎达梅林与土匪、英雄和革命者原型
何安妮1,赵肖为2(译)
(1.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美国哥伦布 43210;2.温州大学学报编辑部,浙江温州 325035)
内蒙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社会和政治激变。在满清官僚、军阀、蒙古贵族与蒙古族和汉族百姓之间的冲突中,嘎达梅林的悲剧无论在民众记忆还是官方记忆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嘎达梅林传奇因其可塑性备受关注:它能够直接地代表一场为了恢复已经逝去的时代所进行的斗争,以及一位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驱者。1979年汉文版嘎达梅林叙事诗呈现出科尔沁说唱汉文章回小说的口述传统“本子故事”的风格,代表着嘎达梅林故事的同步传统化及其在更多内蒙古人和全国人民中的知晓。
内蒙古;嘎达梅林;民歌;诗歌
1931年4月4日,老嘎达和他的游击队三面被奉系军包围住,第四面却是西拉木伦河。他的弟兄们都倒下了,嘎达骑马跃进滚滚的波涛[1]。嘎达宁死不降,而且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家乡的河流,不肯死于敌人之手。人们亲切地称呼他“老嘎达”,其实他享年也不过40岁。
曾经担任哲里木盟(今内蒙古东部的通辽市)达尔罕旗旗卫队“梅林(统领)”的嘎达成为反抗腐败当局的英雄,他为夺回科尔沁蒙古族祖居、1929年被达尔罕亲王卖给东北政府的“辽北荒”而战[2]564。关于他斗争和最后牺牲的故事在歌曲、交响乐、叙事诗和电影中永恒流传,2009年还拍摄了电视连续剧[3]。嘎达梅林(本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被认为是内蒙古英雄,他在“革命战斗”中反抗满清王朝和欺压百姓的贵族[2]565。在他进行斗争的年代,内蒙古已经不是作为政治实体存在,被推翻的满清帝国的疆域分裂为许多新划分的省份,这些省份名义上由中华民国控制,实际上却掌握在不同的军阀手中。嘎达梅林所进行的斗争的意义超越了当地、当时的形势,成为内蒙古人民及其“革命”精神的象征①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 参阅: Bulag U E. Inner Mongolia: The Dialectics of Colonization and Ethnicity Building[C] // Rossabi M. Governing China’s Multi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4.84-116.。
关于嘎达梅林的论著很少,已有的研究也留着许多待解的问题。描述嘎达梅林的叙事诗据说创作于 1950年代的某段时间,但是,创作者迄今找不出可以追溯其确切起源的文本以及可以证实其创作者身份的任何证据,而该诗的原始脚本究竟是口述的还是书面的更加不明了,它与起义“史实”的关联性也有点模糊,尽管某些“有技巧的不真实”非常明显:例如,在该诗的 1979年汉文版中,嘎达梅林面对着东北军阀张作霖,其实张在达尔罕土地出卖之前已被谋杀[4]185,[5]84。本文对张作为“革命者的原型”嘎达的政治映衬进行论证。但是,纪念起义的口述传统和书面传统显然是由用以建立这位英雄的“民族记忆”的“被发明的传统”所构成①参阅: Hobsbawm E J, Terence 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M]. Cambridge, U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2; 文献[18]: 77-98.。我们可能无法追溯英雄嘎达梅林的民间起源,但是那些起源在官方认可的故事中是显而易见的。
陈清漳和赛西芒根据蒙文和汉文书面资料整理的 1979年汉文版嘎达梅林叙事诗代表着嘎达梅林故事的同步传统化及其在更多内蒙古人和全国人民中的知晓[6-7]。由散文转变为韵文,再分成章回,该诗呈现出科尔沁说唱汉文章回小说的口述传统“本子故事”的风格。本文先介绍历史背景:与清朝政府关系密切、曾经权势显赫的科尔沁蒙古族,汉族移民对内蒙古东部地区所造成的改变,土地出卖,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起彼伏的匪患。然后通过与历史背景的比较,分析该诗,找出其与本子故事之间的联系。地域特点的总体性缺乏使得该诗的诉求超越了科尔沁,尤其是其妻牡丹和张作霖所扮演的角色赋予传奇故事更丰富的内涵。运用多萝西·诺伊斯(Dorothy Noyes)等人关于建构民族记忆②参阅: 文献[18]: 77-98.和格雷厄姆·席尔(Graham Seal)关于反叛者叙事及其对于边缘利益和官方利益的“便利性”③参阅: 文献[4].的研究,发掘该诗的地方性、区域性和全国性意义。嘎达梅林传奇因其可塑性备受关注:它能够直接地代表一场为了恢复已经逝去的时代所进行的斗争,以及一位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驱者。
一、科尔沁蒙古族:权力的转移中心
嘎达梅林的祖先曾经是东亚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但是,他们的权势是通过某种魔鬼契约获得的。明朝于 1368年将蒙元政府逐出中原后,蒙古各部落四分五裂,相互攻伐,名义上由北元政府统治、处于分裂状态的东部诸部后来受到西部卫拉特人的准噶尔帝国的威胁。满洲的崛起为和平和稳定创造了机会。1624年,科尔沁部与满洲结盟。后来,北元的额哲汗归附后金,他的帝国因此消失。清朝将蒙古地区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参照八旗制对蒙古人推行盟旗制度[8]451。“外藩蒙古”绝大部分属于喀尔喀部,对满清政府的臣属关系比较松散,与“内属蒙古”的许多部落渐行疏远。而“内属蒙古”诸部被各自的旗界彼此分离,旗界也限制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裹起毡帐四处转场放牧。不过,蒙古人还是以当旗人为荣,科尔沁部尤其如此。清朝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康熙皇帝与他的科尔沁祖母相当亲近[8]309。
地理和政府政策剧烈地改变了科尔沁部的生活方式。地处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兴安岭山麓、毗邻辽宁省的科尔沁部传统领地——哲里木盟的降雨量远大于蒙古腹地,其居民从事农耕起码已经几百年(即便不说上千年)[9]192。19世纪中叶,清朝开禁“龙兴之地”,允许汉族农民移殖到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和东北,而进入内蒙古东部的移民特别多,科尔沁部的生活方式因此演变成半农半牧,其民间文化也中原化[9]192。
19–20世纪之交,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人口已经大幅增加。汉族定居的农业比蒙古族迁徙的牧业能够滋养更多的人口,汉族人口因此超过蒙古族人口。到了 1940年代中期,蒙古族在这个地区变为绝对的少数民族[9]195。然而,汉族并非总是不受欢迎的,19世纪后叶,汉族移民为王爷做佃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哲里木以及其它东部各旗民族冲突最主要的根源在于,蒙古族的土地出卖给清朝政府以及清朝灭亡后的北方军阀。该地区的许多王爷穷奢极侈,恣意挥霍,他们失去了所有其它收入来源的时候就出卖土地。当武装人员按自己的用途“开垦”买来的“荒地”时,生活在被出卖的土地上的蒙古族农牧民失去了家园和生计[2]564。一些蒙古族农牧民决定在大兴安岭聚啸山林,与开垦人员战斗。最早出名的是白音达赉,他的团伙把苏鲁克旗变为“马贼”的领地,1904–1907年间在该地区纵马驰骋,神出鬼没。陶克陶于1906–1907年间在科尔沁和扎赉特地区起义抗垦[10]183。
张作霖,辽宁人,嘎达梅林叙事诗中弄错了年代的反派人物,年轻时自己就是土匪。1900年,在落草4年之后,张受招安参与镇压义和团。日俄战争后,张为清廷担当“巡边剿匪”的职责[5]63。事实上,正是张镇压了白音达赉和陶克陶[10]185。张投靠并利用袁世凯,最终控制了整个东北,包括先前属于内蒙古地区的察哈尔和绥远二省[5]61。张控制的东北从1917年到1920年代中期繁荣兴盛,但是,1927年前后,被谷物歉收和通货膨胀所击垮。当张无法从直系政府手中夺得对北京的控制权,日本关东军在他回奉天的铁路上埋下了炸弹。除了死于1928年6月4日的爆炸,张是嘎达梅林最好的映衬:不是与非正义斗争,张利用非正义。嘎达梅林脱下军官服投身绿林,而张与之反目成仇的正是昔日的战友。在英语为母语的反叛者叙事中,当人的法律违背了更高的道德准则时,反叛者就砸碎人的法律[4]184。相同的伦理理论适用于嘎达梅林:他与自行毁坏对本族族众合法性的腐败亲王和将蒙古族农牧民赶出“荒芜”土地使之陷于贫困和饥馑的政府作斗争。
提出反叛者叙事的“便利性”,不仅是因为被社会边缘化者,也是因为反叛者所代表的被社会边缘化者的敌对集团。19世纪澳大利亚抢劫银行巨款的绿林大盗Ned Kelly已经成为民族英雄,他的故事引起了西澳大利亚和北部领地许多土著的共鸣,他们“将Ned Kelly视为他们自己的不满和与政府争抗的合适代表”[4]179。考虑到Kelly的盎格鲁-凯尔特血统是其多灾多难的原因,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Ned Kelly出现在书籍、电影、电视甚至政府发行的邮票之中[4]177,148。反叛者叙事认为,政府将自己描述成对更高的道德准则和公民的需求敏感的管理机构,这也表明有必要将张作霖与嘎达梅林进行对比,因为张是顽固的反共分子。嘎达梅林在 1979年版叙事诗中从未谈论阶级斗争,因为他没有必要提及,他反对反动派、反共分子和封建主,总而言之,是一位革命者。
二、1979年版嘎达梅林科尔沁叙事诗
1979年版嘎达梅林叙事诗通过体裁、风格和意象得以传统化。该诗分成章回,包括序歌。每个章回以散文起首,然后切换着使用散文和韵文,其对话总是韵文。这种散韵相间的格式在本子故事中很常见[11]。汉文小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在有文化的科尔沁蒙古族中很受欢迎。琴手还对这些小说口述化改编了进行表演,他们一边弹着马头琴一边讲述故事[12]。表演本子故事时,琴手说散文、唱韵文,同时以类似于弹词的方式为自己进行伴奏[13]。1979年版嘎达梅林叙事诗的格式采用了这种因同汉族密切地文化交流而发展出来的科尔沁口述传统。
该诗的格式可能地方化了,其内容的受众却是非本地的。通篇许多地方采用了嘎达梅林民歌中的意象和诗句。民歌没有描述嘎达梅林的行动,而是以大雁的迁徙类推之。就好比大雁必须歇栖在西拉木伦河一样,嘎达梅林也必须为蒙古人民而战: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无论是蒙文版民歌还是 1979年版叙事诗都说是西拉木伦河而不是长江,主要河流的意象还是应该能够与绝大多数的读者产生共鸣。西拉木伦河和迁徙的大雁的形象出现在叙事诗的序歌和最后章回中,也零星地出现在其它章回。
尽管提及了西拉木伦河、二龙山以及其它地标,场景总还是设定在牧场和草原,也许达尔罕旗的居民都是牧民。但是,鉴于其区域位置,有人猜想达尔罕当时实行的是农牧混合经济,嘎达梅林其实可能是为了夺回农田而战。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内蒙古西部没有多少受众,那里的气候干燥,几乎无法开展农业生产。而让科尔沁蒙古族种地,绝大多数汉族会感到很别扭,在他们看来,内蒙古就是一片适合游牧的辽阔草原。如果说嘎达梅林叙事诗散韵相间的格式构成了传统化,那么执意于达尔罕旗想象中的游牧景象构成了被发明的传统。科尔沁实行混合经济的现实可能对于该区域之外的任何人完全没有意义。
散韵相间的格式体现了科尔沁特色,草原的祈愿送达非科尔沁读者,而有关嘎达妻子牡丹的故事使科尔沁本子故事和主流社会的叙事结合在一起。牡丹是嘎达的第三任妻子,诗中没有提及另外两位[2]563。按照嘎达梅林叙事诗的说法,如果不是妻子,嘎达可能一事无成。正是牡丹激励他为了将蒙古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而同王爷斗争。嘎达被解职时,她告诉他,这正是他所需要的、真正将自己奉献给自己的事业的好时机。在她的鼓励下,嘎达及其支持者赴奉天拜会张作霖本人。邪恶的张把他们押入大牢,遣返回达尔罕,准备开刀问斩。牡丹准备营救丈夫及其朋友,但是她知道情况非常险恶,敌对势力远比她和她的朋友强大。她做好战斗中失去一切的准备,索性在敌人抢走之前先行了断,尽可能地卖掉所有的牲畜和财产。她请求朱日喇嘛收养3岁的女儿天吉良,但是,囿于王爷的恩情和自身的落后性,喇嘛拒绝了:
老孟家族辈都是忠顺百姓,
反抗王爷有辱祖先的名声,
老嘎达已成了叛臣逆子,
你要是再去造反天理难容。
这房屋牲畜可以帮你料理,
交给我天吉良可不能答应,
不是朱日喇嘛无情无义,
老孟家不愿担造反罪名。
没有喇嘛的帮助,牡丹料定女儿最终逃不出黑手,她只有一种选择可以让女儿不成孤儿、不落魔掌。一次次犹豫,一次次痛哭,牡丹终于狠心向女儿开了枪,然后放火烧了房子。现在,没有东西值得她牵挂了。
蒙古人在 17世纪皈依藏传佛教。长期以来,蒙古知识分子和西方学者都认为蒙古人因此变得平静和软弱①参阅: Elverskog J.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 Honolulu, H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到了 19世纪,大约三分之一的蒙古男人做了喇嘛,导致人口下降[14]1。喇嘛的腐败也不是秘密[14]76。事实上,随着佛教从西藏传来的科尔沁版格萨尔史诗,描述了虔诚的英雄同邪恶的喇嘛所进行的斗争。在本子故事中,喇嘛变成“蟒古思(萨满祭司在战斗中所面对的具有巫力的恶魔)”[12]。朱日喇嘛就是蟒古思喇嘛的现代版,他没有巫力,他的罪恶在于他拒绝为起义提供帮助。早期的本子故事批评喇嘛篡夺蒙古本土萨满教的力量以及其它罪行。在嘎达梅林叙事诗中,喇嘛不是萨满祭司的敌人,而是人民的敌人。朱日喇嘛死抱着封建职责,不愿丢了祖先、王爷或者他自己的面子。该诗的整理者没有必要在故事中加入有政治意义的修辞,党要革封建主义之命的信息已经显现在字里行间。
牡丹的男女平等思想不是十分明显。她不只是简单地帮助丈夫的正义事业,起义也是她自己的事业——她通过丈夫所发动的事业。妇女和其他边缘人群有时候以强大、勇敢的英雄形象出现在关于起义的民间传说中。民间传说中有着某种程度的民主,虽然不是完全的平等[15]。牡丹的勇敢不仅适合于科尔沁民间传说,而且适合于主流社会的传说,它使妇女在革命中扮演了更活跃的角色。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查禁嘎达梅林故事,担心它可能传播“民族分离”思想[16]。粉碎“四人帮”以后,嘎达梅林重新成为革命英雄[16]。嘎达梅林是一个具有“便利性”的反叛者形象。从表面看,他的斗争只是为了重新得到土地,并没有寻求推翻阶级系统或者将所有的私人财产公有化,也许他只是领导了一次“社会型匪盗”运动——恢复科尔沁社会传统秩序而非为蒙古人民开创“崭新完美的世界”的农民起义[17]。我们不知道嘎达梅林是否支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不知道他是否会欢呼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8]247。如同其他反叛英雄,有关嘎达梅林的民间传说也被充满了政治含义[4]197。在边缘与核心的对话中,“民族记忆”最牢固地建立在民间传统之上[18]92。如同“破四旧”不能查禁绝大多数的民间风俗一样,由于无法查禁嘎达梅林故事,学者可以重新研究这个故事,并将其改编为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初期的故事。
三、进一步研究
关于嘎达梅林传奇的起源和演变还留有许多待解的问题。为了完全理解其对于不同的蒙古族群体以及所有中国人的意义,有必要研究关于嘎达梅林的叙事诗、歌曲和其它文本的作者身份和编写过程,以及它们的演变、所形成的不同版本和不同民族集团、政治集团的解读。例如,张作霖在所有的版本中都是反派角色吗?王爷以及其它人物都受到更多的谴责?张是如何成为核心人物的?还有,如果嘎达梅林与蒙独之间存在联系,又是怎样的联系?我对嘎达梅林叙事诗的表演也感兴趣。它从一开始就以本子故事的形式被说唱吗?正如用对过去的诠释解读当代的关注可以达到用其解读过去本身一样的程度,本文所分析的1979年版叙事诗也可以像解读1920年代达尔罕人的关注那样解读文化大革命之后内蒙古人的关注,如果不能解读出更多,也能解读出一样多[19]。2002年拍摄的电影增添了时间哲学上的纠结:导演冯小宁将故事发生的年代推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嘎达与日本人战斗。透彻研究所有印刷资料和手抄资料以及人种学现场工作,对于解答关于嘎达梅林及其许多象征意义的许多问题非常必要。本文只是试图透视嘎达梅林所蕴含的复杂现象的开始。
特别感谢Erdenebat Jamaa博士和Uranchimeg Borjigin博士誊写和翻译了蒙文版嘎达梅林民歌,和Christopher Atwood教授对研究所进行的指导。
[1] 陈清漳, 赛西芒. 嘎达梅林[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100.
[2] 卢明辉. 嘎达梅林传记[C] // 翁独健. 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 呼尔浩特: 中国蒙古史学会, 1979.
[3] 汤计. 电视连续剧《嘎达梅林》幕后故事揭密[EB/OL]. [2009-12-06]. 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9-10/14/content_12216184.htm.
[4] Seal G. The Outlaw Legend: A Cultural Tradition in Britain, America and Australia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Bonavia D. China’s Warlords [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 Hymes D. Folkore’s Nature and the Sun’s Myth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75, 88: 35-369.
[7] Bauman R. Contextualization, Tradition, and the Dialogue of Genres: Icelandic Legends of the Kraftaskláld [C] //Duranti A, Goodwin C.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28.
[8] Atwood C.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 Empire [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4.
[9] Hürelbaatar A. A Survey of the Mongols in Present-Day China: Perspectives on Demography and Culture Change [C]// Kotkin S, Elleman B A.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Armonk, NY: M E Sharpe,1999.
[10] 白拉都格其, 金海, 赛航, 等. 蒙古民族通史: 第5卷[M]. 呼尔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3.
[11] Heissig W.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Mongolian Epic and Some Topics for Future Research [J]. Oral Tradition, 1996,11(1): 85-98.
[12] 乌仁其木格. 论科尔沁史诗[J]. 民族文学研究, 1988, (3): 22-30.
[13] Bender M. Plum and Bamboo: China’s Suzhou Chantefable Tradition [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03:3.
[14] Hangin J G. Köke Sudur (The Blue Chronicle): A Study of the First Mongolian Historical Novel by Injannashi [C]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38. Wei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73.
[15] Beiner G. Remembering the Year of the French: Irish Folk History and Social Memory [M]. Madison, WI: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197.
[16] 武国骥. 民族英雄嘎达梅林[C] // 翁独健. 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 呼尔浩特: 中国蒙古史学会,1979: 566.
[17] Hobsbawm E J.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M].New York, NY: Norton, 1959: 5.
[18] Noyes D, Abrahams R. From Calendar Custom to National Memory [C] // Ben-Amos D, Weissberg L.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Detrio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Vansina J. 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 [M].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xii,119.
“For the Land of All Mongols”: Gada Meiren the Bandit, Hero,and Proto-revolutionary
HENOCHOWICZ Anne1, ZHAO Xiaowei2(transl)
(1.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hio State University,Columbus, USA 43210; 2.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Inner Mongolia, a vast region of northern China, went through great social and political upheaval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1940s. Among the clashes between officials of the Manchu Qing Dynasty, warlords, Mongol aristocracy, and the Mongol and Han Chinese commoners, the tragedy of Gada Meiren (1892–1931) has stood out in both popular and official memory. Gada Meiren’s legend flourishes because of its malleability: it can at once represent a struggle to regain a by-gone era, and a harbinger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1979 Chinese-language edition of the Gada Meiren narrative poem. Gesturing towards the idiom ofbensen üliger, a Khorchin narrative poetic genre, the poem represents the simultaneous traditionalization of the Gada Meiren story and its generalization for a larger Inner Mongol and national audience.
Inner Mongolia; Gada Meiren; Folk Song; Poetry
(编辑:赵肖为)
I276
A
1674-3555(2011)02-0044-07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2.009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10-27
何安妮(1984- ),女,美国华盛顿特区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蒙古民间文学,民歌,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