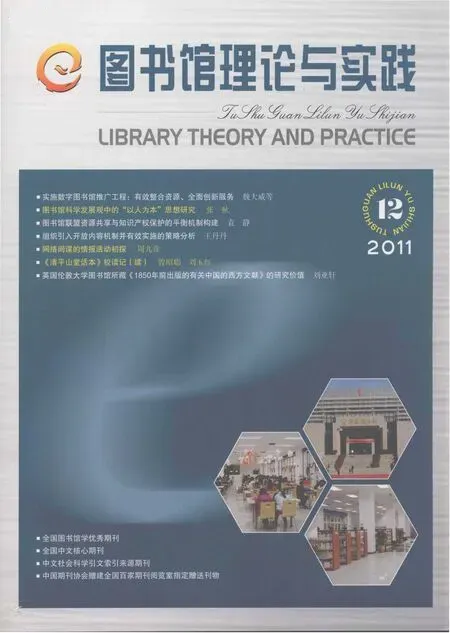《四库全书总目》之《四书》批评
●赵永刚(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3)
中国古代学人,未有不重视目录者。这是因为中国优秀的目录学著作,自刘向《别录》以降,无不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而传统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尤为中国学术史之渊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四书类》收录历代《四书》研究著作164部,四库馆臣对这些论著均有批隙导窾之精审批评,俨然是一部简明的《四书》学史,其中对宋、元、明、清四朝的《四书》学批评尤为珍贵。
1 《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四书》学之批评
中国传统经学可以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类。汉唐训诂发达,经学昌明,考据学兴盛;宋代理学蔚然兴起,成为学术的新潮流。理学是哲学兴味极浓厚的学术类别,它着重于宇宙论、本体论的探研,发展了儒家心性理论,强调为学工夫,推崇儒家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1]理学之所以呈现出以上诸种迥异于考据学的特征,其中的重要原因即是理学家所依据的儒家经典与汉学家判然有别。汉学家以名物考证见长,所据经典为“五经”;理学家以义理阐发争胜,所据经典为《四书》。朱熹集平生之力为《四书》作注,元代延祐年间朝廷又将其悬为令甲,之后科举八股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命题所出,天下士子皆被笼罩其中。学者自束发受书,无不从《四书》入手。以至于《四书》的地位日渐高涨,有凌驾五经而上之的趋势。
“五经”与《四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各自分途,发展出汉学和宋学两端,固然是因为后世儒者别择不同、分途致力,但其根源却仍在两者内容上的差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卷三十五《孟子正义》提要对此有精当的论述,其词云:“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赵岐《孟子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征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发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2]
《论语》《孟子》词旨显明,从汉学名物考证入手,未必有多少值得抉发之处,而义理阐发却有无限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孟子》文本的特质,是理学家选择它们的根本依据,而理学家的义理阐发,也符合《论语》《孟子》的文本要求。故此宋代理学家选择《四书》不是偶然,而以《四书》为代表的宋学之兴起,也是《四书》文本的内在要求所致。
汉学经历了汉唐的繁荣之后,在宋代遇到了理学的挑战,并逐渐被理学所取代,皮锡瑞称宋代是经学的变古时代,[3]而《四书》变古的标志性著作,四库馆臣以为就是宋代邢昺的《论语正义》,该书提要云:“今观其书,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2]将导源宋学之功归于邢昺,但若论宋学的集大成者,自然当以朱熹为大宗,而宋代《四书》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作,甚至《四书》学史上成就最高的论著,也应首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更是推崇备至,该书提要曰:“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况郑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尝不采用其意。‘虽有其位’一节,又未尝不全袭其文。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也。《论语》《孟子》亦颇取古注,如《论语》‘瑚琏’一条与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论者或以为疑。不知‘瑚琏’用包咸注,‘曹交’用赵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墙数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论者尤以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赵岐注也。是知镕铸群言,非出私见,苟不详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师心矣。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2]
可以说,此提要是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最为公允的评价,同时也反映了四库馆臣的两种《四书》学批评方法。
(1)汉宋兼采,不主一偏。清朝开四库馆,馆员集一时之选,纪昀、戴震等一大批汉学家主持其事,可以说四库馆是当时汉学家的大本营,以往论者往往据此推断《四库全书总目》的撰写也是以汉学标准为持论之绳墨,更有甚者,以为《四库全书总目》就是汉学家眼中的学术源流变迁,故此推断四库馆臣对汉学著作褒奖有加,而宋学论著,尤其是理学著作,则倍受讥弹,评介失允。不过,现在以《四书章句集注》的提要来看,这种观点是与事实相悖的。实际上,四库馆臣是主张汉宋兼采,不主一偏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就有明确的宣示,即“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除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经义明矣”。可见,四库馆臣是以“公理”“经义”为最高悬鹄的,而不是先存了汉学家的偏见,有意左袒汉学而贬低宋学。《四书章句集注》提要对汉学家以细枝末节的考证之疏质疑朱熹的做法甚表不满;当然,他们也无意推崇宋学,对于宋学家的回护朱熹,百般弥缝,也有尖锐的批评。所以,简单地以汉学标准衡量《四库全书总目》是偏颇的,并且学界流行的观点以为汉宋合流的趋势是嘉道之际才开始显露,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从《四库全总目》来看,这个汉宋兼采的学术潮流,最迟在乾隆中后期就已经出现了。
(2)尊奉经典,反对叛经。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考察,不难看出,宋学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是对汉学考证的反动,它的兴起革除了汉代学术的拘泥琐碎之弊,也纠正了六朝隋唐经学芜杂无宗之失,是经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重要革新,自然也推动了学术思想的进步。但利弊相仍,宋学也有疑古过勇之失,这就是四库馆臣所说的“悍”。《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云:“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2]这股疑古思潮也波及到了《四书》研究,尤以《孟子》为烈。据《礼部韵略》所附条式可知,宋代元祐年间就以《论语》《孟子》试士,王安石对《孟子》更是尊崇有加。但守旧派反对王安石变法新政,党争之火,殃及《孟子》,司马光等借《孟子》与王安石作难,所以有司马光《疑孟》、晁说之《诋孟》问世。清朝政府自立国之初就明令严禁党争,维护正统官学思想的四库馆臣也反对这种党争陋习、门户之见,而对宋代学者中能逆流而上、尊奉经典者则极力表彰推扬,从他们对孙奭《孟子音义》的评价中就可见一斑,该书提要云:“然则表章之功,在汉为文帝,在宋为真宗;训释之功,在汉为赵岐,在宋为孙奭。”[2]
2 《四库全书总目》对元、明两代《四书》学之批评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制定科举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三门,其中“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子章句集注,复以已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4]至此,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元代政府定于一尊。受官学强势政治影响,元代的《四书》学几乎都被朱熹笼罩,创获性的著作难得一见,即使是较为出色的论著也是依附朱注而行,如理学家刘因的《四书集义精要》等。朱熹《四书》学思想的精粹部分都被纳入到《四书章句集注》之中,平时答门人之问的思想与《四书章句集注》略有不同,朱熹生前未及订正统一。朱熹卒后,卢孝孙采集《朱子语类》《晦庵文集》关涉《四书》者,汇集为《四书集义》,计有100卷之多。学者以为过于繁冗,有鉴于此,刘因在《四书集义》的基础上,删除重复,保留菁华,编辑了《四书集义精要》28卷。四库馆臣对该书评价颇高,《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卷三十六该书提要云:“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于多岐。苏天爵以简严粹精称之,良非虚美。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2]
诚如四库馆臣所言,元代儒者“徒博尊朱之名”者很多,他们过于尊奉朱熹,以致泯灭是非之分,以至于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错误也是百般回护、曲意弥缝。张存中《四书通证》即是一例,四库馆臣批评说:“不知朱子之学在明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固不必为之讳也。”[2]泥朱过甚,难免偏颇,甚至出现了割裂《四书》原文,以之迁就朱熹注文的荒谬行为,较为极端的著作就有胡炳文《四书通》,提要说:“大抵合于经义与否非其所论,惟以合于注意与否定其是非,虽坚持门户,未免偏主一家。”[2]
元代也出现了很多为科举而设的《四书》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了袁俊翁《四书疑节》和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两种。尽管两部书都是科场参考书,但元代科举初设,当时学风笃实淳厚,士大夫尚有志于研究经书,与明代八股文影响下的《四书》著作相比,仍有较高的价值,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对二书评价还是颇高的。袁俊翁《四书疑节》提要云:“盖当时之体如是,虽亦科举之学,然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2]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提要云:“其书以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答以明之。盖延佑科举经义之外,有经疑,此与袁俊翁书皆程试之式也。其间辨别疑似,颇有发明,非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2]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5]明代科举分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三场之中以头场为重,头场又以三篇八股文为重。此制度一定,士子无不以八股文为头等大事,一切经史之学都废置不讲,所以明代成为经学史上的极衰时期,而其根本症结即在八股取士,无怪乎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哀叹:“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6]
《四书》研究在明代也是走到了低谷,可谓是百弊丛生,谫陋至极了,而开此恶俗风气的,即是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编撰的36卷本《四书大全》。此书乃是从元代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剽窃而来,仅小有增删,对于详略繁简的处理,还在倪氏之下,几乎无创造性的价值可言。然而,明成祖却为《四书大全》作序,颁行天下,有明一代,200余年,奉此书为取士准则。上行下效,影响极坏,四库馆臣说:“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至明永乐中,《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2]受《四书大全》的影响,明代为八股文而作的《四书》讲章泛滥天下,这些《四书》学论著,几乎都是为盈利而设,原本就与学术著作不同,所以陈陈相因、剽窃重复是常有的事情。而这些讲章几乎都是庸陋鄙俚,粗制滥造的。即使是受到好评的薛应旂《四书人物考》,也不入四库馆臣法眼,他们批评该书“杂考《四书》名物,饾饤尤甚”。而究其原因,仍在八股文,即“明代儒生,以时文为重,遂有此类诸书,襞积割裂,以涂饰试官之目。斯亦经术之极弊”。在讲章充斥的明代,《四书》本旨,甚至是朱熹的注解,都被淹没其中,隐晦不彰了。故四库馆臣感叹:“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2]
除了八股讲章泛滥之外,明代以禅解经的现象也十分流行。王学末流,尤热衷于此。因为王学在“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7]这种风气也波及到《四书》诠释之中。其实,以禅理附会《四书》,苏辙就已经开启端倪,其《论语拾遗》提要云:“其以思无邪为无思,以从心不踰矩为无心,颇涉禅理。以‘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为有爱而无恶,亦冤亲平等之见。以‘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虽死而不乱,尤去来自如之义。盖眉山之学本杂出于二氏故也。”[2]不过,北宋以禅解经的做法只是偶尔一见,不像晚明如此盛行。《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七《四书类存目》就著录了很多种,如管志道《孟子订测》,提要批评说:“测义则皆出自臆说,恍惚支离,不可盛举。盖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汝芳之学出于颜钧,本明季狂禅一派耳。”[2]姚应仁《大学中庸读》“阳儒阴释”;[2]寇慎《四书酌言》“纯乎明末狂禅之习”。[2]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还有一条重要的批评标准,就是“论人而不论其书”与“论书不论其人”,这是因为“文章德行,自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2]所以应该采取变通之策。如著录杨继盛、黄道周的著作,是“论其人而不论其书”;而耿南仲的《易》学之作能够厕身《四库全书》,乃是因为“论其书而不论其人”。这个标准也体现在对明代《四书》学的批评中,《四库全书总目》对刘宗周《论语学案》的评价就是如此,提要云:“盖宗周此书直抒已见,其论不无纯驳,然要皆抒所实得,非剽窃释氏以说儒书,自矜为无上义谛者也。其解‘见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错过义理关,而能判然于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阳之一饿,可谓大节皭然,不负其言矣。”[2]提要显然有表彰节义、彰善瘅恶的用意所在,其评价也不完全是从学术着眼。
3 《四库全书总目》对清代《四书》学之批评
皮锡瑞以为清代乃是经学的复盛时期,他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清初的右文之风,首先是康熙皇帝发起的。康熙十年(1671年),开经筵日讲,任命王熙、熊赐履等为讲官。康熙朝的经筵日讲有利于经学昌明,也有利于理学的复兴。经筵日讲的《四书》部分,结集为《日讲四书解义》,该书提要云:“是编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圣德神功,所为契洙泗之传,而继唐虞之轨者,盖胥肇于此矣?”因为该书标明为御制,四库馆臣揄扬有些过当,但提要所言该书有转移风气、接续道统之功,却是符合实情的。受康熙皇帝崇尚程朱理学思潮的影响,清初陆续出现了一批维护程朱正统思想的《四书》学论著,较为知名的有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提要评曰:“陇其笃信朱子,所得于四书者尤深。是编荟粹群言,一一别择,凡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其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诸人有过之无不及矣。”
另外,清初儒者几乎都经历了明亡的悲剧,对于明代阳明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风气深恶痛绝,一时人心思治,无不向往笃实严谨的学风。这正是梁启超所言,清代学术的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此外还有一个支流,即“排斥理论,提倡实践”。[8]《四书》研究也开始排斥晚明的不良习气,恢复汉唐考据传统,以考证见长的《四书》论著也开始问世。代表性的著作就有阎若璩的《四书释地》,《四库全书总目》称赞该书:“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盖若璩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观是书与《尚书古文疏证》,可以见其大概矣。”[2]
另外,江永《乡党图考》也是考据学的经典之作,四库馆臣也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提要云:“是书取经传中制度名物有涉于乡党者,分为九类,考核最为精密,亦可谓邃于三礼者矣。”[2]
当然,前明的影响在清初也并未消失净尽,清初王学家和时文家也不乏《四书》论著,阳明学派有孙奇逢《四书近指》、黄宗羲《孟子师说》等,时文讲章派则有杨明时《四书椰札记》、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但两派的作品都摆脱了明代的新奇谬戾之弊,呈现出案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的新特征。孙奇逢《四书近指》提要云:“盖奇逢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于穷则励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虽不一一皆合于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也。”[2]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也为四库馆臣所褒奖,说该书“疏理简明,引据典确,间与《章句》、《集注》小有出入,要能厘然有当于人心”。[2]
[1]陈来.宋明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14.
[2](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Z].北京:中华书局,1997.
[3](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220.
[4](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019.
[5](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96.
[6](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36.
[7]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50.
[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