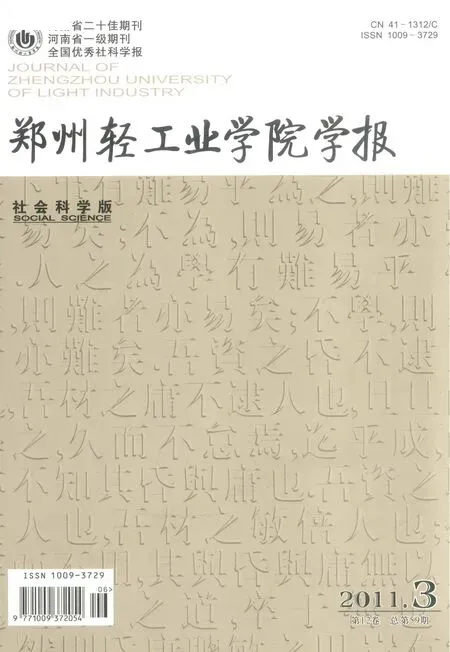韩国儒学与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
罗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一、儒学在韩国的发展历程
一般来说,儒学在韩国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卫满朝鲜时期儒学自中国传入,(2)三国时期初步接受,(3)新罗统一时期大规模传播,(4)高丽时期儒佛兼学,(5)高丽末及李朝时期性理学兴盛。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韩国儒学与朝鲜儒学的称谓之争多存而不论,而近代以来朝鲜半岛的儒学研究多集中于韩国,故本文采用“韩国儒学”作为文章之论题;而在发展过程中“朝鲜儒学”是其历史主体,所以行文中为叙述之便并契合朝鲜半岛儒学发展的实际,有些地方仍保留“朝鲜儒学”的称谓。
关于儒学何时传入韩国的问题,学界争议较大,大体有4种观点:一是箕子东来说,二是秦汉东传说,三是卫满朝鲜说,四是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说。[1](P1)笔者同意张立文教授所持的卫满朝鲜时期传入的观点。确如钱穆先生所言,孔子以前,中华文明已有两千多年之发展,而孔子集其大成,创立儒家学说,从而影响此后中华两千多年文明之发展。[2]虽孔子以前已有所谓儒者,然而其乃属于一种职业而非一家学说中人。至于孔子之前的“中华第一哲人”箕子于西周灭商后进入朝鲜半岛而建立箕氏侯国之说纯属传说,因此箕子东传之说不能成立当属无疑。秦汉东传说较之卫满东传说亦无明证。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而于朝鲜半岛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4郡以为汉朝之行政区域,儒学由此传入便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三国时期仍属儒学传入朝鲜初期,此时的朝鲜儒学较中国儒学尚无独特性可言。其间对于推动儒学在朝鲜发展传播的事件主要有:高句丽于小兽林王二年设立太学,颁布律令,并在全国各地设置扃堂;百济施行博士制度,并有学者高兴编撰《书记》,王仁去日本传授汉学和儒学;公元6世纪新罗确立古代国家的体制,编撰《国史》,花郎道吸收儒家思想。
新罗统一时期儒学成为其治国理念,统治者掌握了儒学修己治人的政治理念,从为政以力、为政以巫的神权统治开始转向为政以德、为政以礼的人治努力[3](P23)。由此儒学在朝鲜半岛始有较大规模的传播。此间,神文王二年(682年)扩大和整顿国学、元圣王八年(788年)施行读书三品科制度等,则无疑得益于政权对儒学的认可。其间名士有使用“吏读”讲授儒家经典的薛聪和入唐留学后创作韩国最早的文集《桂苑笔耕集》并提出儒佛道融会贯通说的崔致远。
高丽时期崇奉佛教,然此间儒学并未衰微,而是与佛学并立、互为表里,尤其是政治问题的处理仍遵循儒学之原则。正如张敏先生所言:“佛教被认为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修身治己之学,儒学被认为是现实生活方面齐家理国之道。”[3](P24)而在958年高丽光宗依唐制设立科举制度之后,由于儒学之士渐渐取得权位,佛教遭到排挤,儒学得到拥护。高丽后期安垧、白颐正等积极推广朱子学,而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曾任成均馆大司成的李穑,他力排佛说而极拥朱子学,其下名士如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皆积极响应,由此佛学式微,程朱性理之学始兴。[1](P5),[3](P24)
性理学时期名士迭出:有“朝鲜之朱子”美誉的李退溪和与之齐名的李栗谷,人称韩国儒学之“双璧”;赵静庵(光祖)、李晦斋(彦迪)与金宏弼、郑汝昌被称为“东方四贤”。这一时期的儒学真正代表了韩国儒学之精神。
二、从李朝儒学看韩国儒学的精神
程朱理学于高丽末、李朝初传入朝鲜半岛,构成了朝鲜半岛儒学的核心。其发展历程大致为:前期为勋旧派与士林派的对立;中期为以李退溪和李栗谷为代表的性理学;后期为实学。
前期朝鲜半岛儒学的基本特征是官学与士林的对立。这两派的思想渊源可分别上溯至高丽末以郑道传为首的务实派和以郑梦周为首的义理派。此二人皆出于李穑门下,前者注重时运天道的常变常新,因此注重扶持新政,后渐渐发展成为在朝的勋旧派;后者则注重传统儒学的义理,坚持不事二君的精神和效忠旧朝的原则,后发展成为在野的士林派。本来二郑只是思想不同,但勋旧派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日益腐败,遭到士林派的强烈反对,勋旧派则利用其强大的国家权力迫害士林派,从而制造出一系列的“士祸”,最著名的有“戊午士祸”、“甲子士祸”、“己卯士祸”、“乙巳士祸”等,其中尤以镇压赵静庵为首的士大夫改革的“己卯士祸”为人所熟知。“士祸”以后朝鲜半岛儒学从原始儒学的政治实践研究、理论研究转向了思索的、追求形而上学的性理学理论的思考[3](P28)。这一点与中国魏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由正始向元康思想风格转变之社会政治原因有相似之处。
朝鲜半岛儒学思想风格的转变引出了诸多思想名家,其中的先驱式人物当推花潭徐敬德。他终身未仕而潜心于对自然问题作自由的沉思,为后来的气论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徐敬德是否受到汉人思想的影响固不可知,然而其气一元论之阐发实与汉人对道等概念的宇宙论阐发有诸多相似之处。汉人于阴阳五行等多有所好,并将这一套理论用于宇宙万物之成毁和运动。徐敬德则将气视为宇宙之质料性的本源,此与张横渠之气的概念有颇多相同之处。朝鲜半岛后期的理学之主气派于此当有不少承继之处。
如果说气是花潭哲学理论之核心范畴的话,理则是李退溪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退溪被誉为“朝鲜之朱子”,朝鲜性理学发展到他已集大成,其功颇似朱熹。在退溪看来,世界之本之源是理,此理之概念受于朱子之学无需多论,而其对于朱子理的概念的发展则需引起我们的注意。虽然此间研究朱子理学之人皆自称忠于朱子理论之本意,实则多有篡改。张立文[1](P69)先生指出退溪哲学中的理有4层涵义:一是指万物本源之特性;二是指形而上之概念,无形影可指;三是指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四是指法则。上述4点与朱子之理的涵义大同小异,退溪之主要改造在于理之动静。朱子以为理无造作,若如此则与其为万物所以然之意冲突。退溪欲解此矛盾故赋予理以体与用的双重性质,于一角度观则见其体,于另一角度观则见其用,实则非二物,而是一物之两面也。此项修正较魏晋时王辅嗣、郭子玄对时人认体用本末为截然分离对立之二物而或执着于本而不见万象森然、或逐于纷繁之象而丧其本的观点的纠正有异曲同工之妙。盖依朱子之理言则理固为万物之本,然其若无动作之性则何以为万物之所以然呢?故退溪将体用合而言之便消解了此一矛盾。退溪之学自然远不止此,此处只择其一说而言。退溪之学乃李朝后期主理一派之一大思想来源。
与李退溪并驾齐驱同负盛名的哲学家是李栗谷。栗谷之思想风格较退溪实多有异处,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于正统之理学、于佛老均多有心得,尤为可贵的是他在阳明学受到排斥的李朝并不流污于世风而潜心学之,故其理论能博采众家之说而加以个人之创造,从而能建构起独具个性的理气妙合之理论。李朝中期有几个很著名的辩论,崔根德将此一时期定为“四七理气论”论辩期,其中有李晦斋与忘机堂(曹汉辅)之间的无极太极之辩(实则有曹汉辅与孙叔暾论辩在先),有李退溪与奇高峰大升四端七情之辩,这后又引出李栗谷与成浩原的辩论,还有卢苏斋(守慎)与李退溪、李一斋之间的论争。[4](P351-354)其中最要者自然属退溪与高峰、栗谷与浩原的四七之辩了。其争论主要源于各自对朱子学说理解之不同。四七之辩始于退溪对郑秋峦之云《天明图说》中“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言的修改,退溪将其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秋峦不解而问于好友高峰,高峰以为退溪之更正有误,二人互通书函,遂有论辩。盖退溪之修改于文意似无改变,然则其中确有微妙之处。退溪的修改是基于他对理气的理解,若如秋峦所言则似乎理气全然处被动之状态,而改理气为主体则立见其动之本性,而退溪一直都主理气自动来修正朱子理不自动之论。另外退溪在他致高峰的信中说他之所以要做出修改是为纠正秋峦违背先儒不分说理气的原则而对理气“分别太甚”之偏失。而高峰认为退溪自己的理论恰恰没有摆脱将理气截然二分的偏颇。退溪以理气绝对有分而不相杂,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则兼有善恶。在高峰看来此论仍不能得理气为一之妙合。退溪后又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一些修改,不过并未接受高峰的意见而更改其理发气发的互发说。[3](P46)其后栗谷与浩原间的人心道心之辩实为退溪、高峰之辩的延续。
性理学至退溪栗谷而达顶峰,此后渐渐式微,此前代表先进思想的士林派学者发生了严重腐化。理论之践行者本身是掌握权力的官僚,各派为维护自身名分和利益而纷争不止,本来有利于学术思想发展的自由辩争转而成为空洞浅薄的狡辩之末技。导致李朝中期向后期思想之大变的直接诱因是两次促使李朝由盛转衰的外侵所造成的动乱,一为1592—1593年日本发动的壬辰倭乱,一为1636—1637年女真发动的丙子胡乱。此二乱直接引发了李朝强烈的政治危机,而时为官学的性理学对此危机的解决毫无作用,有识之士为寻求危机之解决而不得不对性理学本身进行反思,这便导出后世所谓之实学。实际上,在中期盛行论辩之时已有人对性理学表示不满,然而一则李朝此时甚为繁盛,二则并未产生新的与之相抗衡的理论。至17世纪中后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间各种思想传入李朝,主要有阳明心学、清朝之实学和西学。阳明心学由于与程朱理学对立而在此前朱子学独占鳌头的时期受到排挤,此时则有不少人开始注意吸收其中精华。清朝实学主要包括以顾炎武、魏源为代表的经世实学,以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启蒙实学,乾嘉学派的考据实学。[5](P10-13)李朝实学家十分注重对这些学说的吸收和改造,从而使之能为士大夫之改革服务。西学在此前业已传入,然而性理学家们多抱以“斥邪卫正”的态度,从而导致了朱子学的绝对化和严重僵化;实学家们则不然,他们积极吸收其中有利于建设其国家政治经济的思想理论,其中丁若镛最为积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性理学并未至此断了流行,实学家对于性理学的异议和指责当是针对性理学之末流而发的。实学家对于性理学多有继承,尤其对李退溪与李栗谷之思想,甚至有实学家以栗谷为实学之祖。应当说,实学是对正统理学优秀精神的吸收,并对其一些概念和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因而实学对于性理学不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颠覆,而是积极的修正和补充。
冯友兰先生曾对中国哲学精神下过“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断语,实则亦可言内圣外王之道。[6](P4)这一论断同样适合于朝鲜半岛儒学。李朝中期之性理学其主要责任在于为其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家正是围绕这个使命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明之哲学;实学思想则注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而是道中庸的哲学。当然,这并非讲性理学不道中庸,只是其侧重点在形上之思,而实学因现实之危机更注重寻常日用之学。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极高明”与“道中庸”亦非截然对立之二事,而是一事。实学之先驱李芝峰(光)亦有此悟,他从庄子“道在屎尿”的论语阐明道非脱离世间万物而悬空存在,而恰恰就在百姓日用之中。[5](P140)这一点禅宗亦多有论述,而王阳明等更是百般强调。
三、崔济愚“侍天主”思想对传统儒学的改造
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1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变,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是朝鲜李朝末期哲学家,朝鲜天道教第一任教主,号水云,朝鲜庆尚南道庆州人。他出身于没落士族的地主阶级,1860年为对抗西学即天主教、基督教而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吸取儒、佛、仙三教创立东学,并周游各地宣传东学思想。1863年被捕,次年被李朝政府以“传播邪教”罪处死。著作有《东经大全》《龙潭词》《道德词》等。崔济愚从三个方面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改造:以“侍天主”的概念承继和改造传统儒学之“天”的概念;通过对基督教的批判继承,发展了传统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以“至气”概念改造传统理学中“气”的概念。
1.通过“侍天主”概念,阐释并改造传统儒学之“天”的概念
关于东学之“天”,崔根德教授这样描述:“第一是能够昂首仰望的天(可视之天);第二是同人类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的天(人格神之天);第三是抽象思维的天(形而上之天)。”[4](P159)传统儒学之天的内涵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万物之总全。推及社会人伦则有天理,即社会之最高法则。二是人与万物的主宰。然此种主宰性正如张立文教授分析朱子之理的主宰性时所言的那样:“并不是一种有意志的人格神的主宰,而是一种超人物、超自然的客观必然性,人物受其宰制而不可逃避,这种必然性亦是一种绝对性。”[7](P54)三是一种修养所及之境界。此即中国哲学所欲追求之天地境界。崔济愚之“天主”概念受此“天”之内涵的影响,并于其中注入人格神之内蕴。这无疑是受之于其传统宗教巫教(萨满教)。众所周知,在远古时候人类社会是神政不分的,拥有神权的祭司即是掌握政权的君王。在朝鲜之建国传说中,人类社会便是依照天国的模式所造。[4](P161)传统儒家学说之所以不被认为是一种宗教,是因为其没有对神的崇拜,而东学则是一种宗教信仰——崔济愚从固有的民族宗教和基督教之“天主”概念中吸取人格神的内蕴,赋予传统儒学之“天”以强烈的宗教意味,从而直接将儒学改造成为一种宗教。
儒学之“天”是没有喜怒哀乐等感情的,亦是无言的;而崔济愚之“天主”是有情甚至是有言的,天主像父母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世间万物。东学之天主能言,颇类似于基督教中上帝的启示。崔济愚在《东经大全·布德文》中自叙一次奇特的经历:“不意四月,心寒身战,疾不得执政,言不得杂状之际,有何仙语忽入耳中,惊起探问,则曰,‘无惧无恐,世人谓我上帝,汝不能上帝耶?’问其所然,曰,‘余亦无功,故生汝世间,教人此法,勿疑勿疑。”[8](P220)这当然是崔济愚杜撰的故事,但由此可见天主即所谓上帝者是怎样一个与人一样生动活泼的形象。此一点亦与巫教传统有关。盖天神自不理世间之事,而只委派一代理人来掌管万事;而崔济愚则自视为上帝之代理人,故而要完成上帝之圣功,布德于人世,消除世间之纷争,引导世人走上和平之路。而“天主”概念对于儒学之“天”的继承突出地表现在:儒家言天地滋养万物而万物不知,其圣德乃在无形无迹之中养成万物;东学之天主亦有此义。崔济愚《论学文》言:“夫天道者,如无形而有迹……四时盛衰,风露霜雪,不失其时,不变其序,如露苍生,莫知其端。”[8](P221)他又吸取道家之精神而有“吾道,无为而化矣”这样的言语。这一思想在其衣钵传人亦即东学第二代掌门人崔时亨那里有更详细的表述。
2.通过批判基督教,改造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是中国道家和儒家都非常注重的思想。在汉代,儒学家们说及天人关系无不依天而言人,其代表为董仲舒的《人副天数》和《为人者天》两篇论著。冯友兰先生似对于汉时之哲学家多有指责,盖因汉人思想对于阴阳学说多有吸收并以“极高明”的标准考察之,认为其思想离“高明”实在非常之远。他甚至说:“严格地说,汉代只有宗教、科学,没有纯粹底哲学。”[6](P93)若以哲学家之理论标准言之,固有一定道理,然窃以为董仲舒之理论其目的实在于提升人的价值,以确定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他的这一思想被后来者所继承,如张横渠、程明道等,后乃成为中国思想家对于人的理解的一个定论。董仲舒曰:“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依。”“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天之副在乎人。”[9](P17,18)表面上看好像是尊崇天的权威,实际上是抬高人在宇宙中之地位。又如朱子言:“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9](P264)人贵物贱、人尊物卑之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崔济愚也接受了上述传统儒学“贵人”的思想,不过很可能不是直接受之于董仲舒,而可能是受之于宋明理学。但不管怎么说他对于个体价值之重视当属确凿无疑的,这也是其天主观与基督教上帝观的一个不同之处。崔济愚曾经在《论学文》中说道:“阴阳相均,虽百千万物化出于其中,独惟人最灵也。”[8](P221)这显然是与理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基督教言上帝是绝对超于个体之上的,个体存在之价值只是上帝预先规定的目的而已,因此在基督教中个体是无独立价值可言的。如果说《旧约》之中人与神的关系尚不至于太过隔绝的话,那么到了《新约》之中上帝的言行就变得近乎邪恶无理了。这固然是基于西方人对于绝对力量的崇奉,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基督教经过了希腊哲学的改造,而希腊神话中的具有强大力量的神都是“不可理喻”的,因为拥有绝对力量的神被认为是超越善恶的,因此其行为是无善恶可言的。然而在崔济愚的思想中,个体是具有其内在价值的。
对于“侍天主”的“侍”,崔济愚是这样解释的:“‘侍’者,内有神灵,外有气化,一世之人,各知不移也。”[8](P222)王弼在讨论圣人与常人的区别时曾指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崔济愚言“内有神灵”,表面看是在讲天主在人内心之显现方式,即天主“在我心里面,它以神灵来现身”[10](P183),实际是讲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有觉悟真理之“神明”。这只是崔济愚出于一种宗教解释的需要而借天主之名加以表达罢了。“外有气化”,“气者,虚灵苍苍,无事不涉,无事不命……是亦浑无之一气也”;化者,即“无为而化”也。[8](P222)此处表面讲天主在人心之外表现自己力量的方式[10](P183),实则讲人能与天主同其德而至于“气化”万物,从而成为“侍天主”的人。这里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崔济愚对儒道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冯友兰先生在阐释儒道二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不同时曾经说道:“道家所用底方法是去知。由去知而忘我,以得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孔孟的方法是集义。由集义而克己,以得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孔孟用集义的方法,所得到底是在情感上与万物为一。道家用去知的方法,所得到底是在知识上与万物为一。”[6](P67)由此分析崔济愚之“侍”的概念,其天人合一之思想便一目了然了:其一是“神灵”,此即道家在知识上认识到我与万物本为一;其二是“气化”,此即儒家在情感上进入到与万物为一境界。
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这也是东学之宗教思想最不同于基督教之所在。这个内涵便是:“侍天主”实际就是成天主,即佛家讲的人人皆可以成佛、道家讲的人人皆可成圣人。个体的终极价值便是达到天主之境界。这在基督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个体是负有原罪的存在,在上帝面前永远是卑微而极渺小的;上帝对于个体而言是那样的遥不可及,他只对先知们显现其神灵,至于常人只能祈祷有朝一日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而进入天堂。基督教许诺给教徒的是彼岸的美好生活,而东学显示给人的是此岸的实际幸福。在东学中,“侍天主”即有可能成天主,成天主则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则可普济众生。
崔济愚曾经概括过自己的思想来源:“儒人之人伦大纲,仙之清净自修和佛之普济众生,足以成为吾道之三科。”[8](P215)崔氏之合和儒道释三家之思想甚明矣,但他的“天主”概念确受之于基督教,只是二者大不相同而已。
3.通过“至气”概念,阐释并改造传统理学之“气”的概念
传统理学中“气”的范畴的奠基者为张横渠。冯友兰先生曾有言曰:“横渠之学,亦系从《易》推衍而来。”[9](P278)汉人最擅为象数之易,以阴阳五行之学解释道家之道的概念,从而将这一形式概念拉入存有领域而成一积极的概念,使道成为构成万物的本原性质料。冯友兰的有关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汉人把本来“极高明”的道家哲学从形上之玄虚领域拉入宇宙论的实际世界里而成为“不高明”的哲学。横渠之所谓“气”与汉人之所谓“道”实有诸多相似之处。“气”有阴阳二性,由此又有“浮沉、升降、相感之性”。阴阳之气聚则物成,散则物毁。“气聚则能为吾人所见而为有形;气散则不能为吾人所见而为无形。”[9](P230)伊川亦多言气,以为万物之始有皆由气化。伊川之不同于横渠者在于“伊川以为已散之气,已散即归无有,其再聚之气,乃新生者。”似乎伊川之言“气”不如横渠简单彻底。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9](P235)“气”是形下之器世界的构成,其内涵同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质料”。
朱子哲学是一个精微严谨的理论体系,其核心范畴是“理气”,故而言“气”则必须将其置于朱子之整体理论框架之中考察。朱子对于“理”与“气”的阐述有这样一个逻辑结构:理—气—物。这是由本体出发的逻辑结构,是由上到下的理路;他还有一个认识论的结构:物—气—理。“理”在朱子哲学之中是一个本体范畴,它是万物生存的本源和根据。因此“理”与“气”之关系首先是理本气末之关系。然则理气虽不杂,却又是不可分离的,即使就理先气后而言这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关系而不是实际的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这一点冯友兰[6](P260)和汤用彤[11]二先生言及“道”与“物”之关系时亦是如此说的。汉人把这种逻辑关系借阴阳五行之解说成了实际的时间关系,因而招致批评。张立文先生在论及此理气关系时亦持此观点:“理与气的关系不离不杂,并非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逻辑上的关系。”[7](P45)按朱子所言,气乃理的搭挂处、安顿处、附着处,理气相依不离。理通过气而为人所认识和体悟,这有些类似于柏拉图所谓“自然万物是理”的影子。不过朱子之意并非言理实际生出气,而是说气的存在和运作要以理为根据。由此“气”在理学中之地位就比较明了了:“它是理的安顿、附着、搭挂处,无气理便悬空无着落,而无所谓‘实理’;它是勾通理—物的中介,无气则理塞,而无所谓‘发育流行’;它是构成万物的质料,无气而理无以和合,而无所谓万殊之物。”[7](P85)
崔济愚的“至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他在《论学文》中说:“气者,虚灵苍苍,无事不涉,无事不命。然而,如形而难状,如闻而难见,是亦浑无之一气。”[8](P222)此处言气似与朱子之言气并无大区别。但是他在“气”前著一“至”字并解释说:“至者,极焉之内至……今至者于入道,知其气接者也。”[8](P222)如此则可知“至气”乃天主的造化力量。气于朱子理学中本只是理的依附处、搭挂处,而“至气”在崔济愚这里被赋予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天主的造化力量。“气化”是天主一种行事的方式,即利用“气”而“化”,此“化”是“无为而化”。因此气之为物是天主的一件宝贵的工具,如宝剑之于武士。然则气之为物又是“如形而难状,如闻而难见”的。那么我们如何感知它呢?崔济愚采取了一种宗教的手段——“气接”,即人们可通过这种方式感知到气这种事物所体现出的天主的强大力量。
综上所述,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改造的核心便是引入“天主”这样一个人格神,从而把传统儒学改造成为韩国之一种新宗教,它既含有大量的儒学传统思想,又吸收了部分佛仙的内蕴,同时也有对西方基督教和韩国传统巫教的批判与吸取。
[1] 张立文.李退溪思想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2] 钱穆.孔子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
[3] 张敏.立言垂教:李珥哲学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崔根德.韩国儒学思想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5] 葛荣晋.韩国实学思想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6] 冯友兰.新原道:中国哲学之精神[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7] 张立文.朱熹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 金勋.韩国新宗教的源流与嬗变[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0] 黄棕源.东学与近代文明的出路[C]//哲学门(第1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1]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3-55.